【OCAT上海馆|"8102"讲座回顾】亲爱的!千万帮我留住人(下)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讲座:亲爱的!千万帮我留住人
对谈人:杨健、安妮
时间:2019年1月6日(周日)
14:00-16:00
《曲线系列》是我这次参加展览的作品,这个作品就是我今年在北京的一个个展的时候的作品。
个展的名字很好听——“在不可能相遇的时间和利维坦的注视下”,所以这个展览肯定没有人写展评。
我相信这种东西都可以找高洁老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应该找高洁的艺术参数来完成。这个展览当初是分为两大块,杨健也有跟我们介绍,然后其实关于曲线的这个系列是你想在这两个个展之间的一个链接,用这件作品,用这件曲线作品做一个沟通,做两个展览之间的一个沟通。
这就是我这次在华侨城OCAT上海馆展览里面的一件作品,以前是在墙上的,这次是悬空的布置。这个大的曲线就是淘宝的日浏览量的一个变化曲线,上面那些小小的方块都是我画的一些画,每张画其实都是处理一个不同的关于曲线的主题的东西。这个从2010年开始我在做一个关于曲线的系列作品。
这些曲线大家可以看得到是杨健根据网上找到的不同的一些曲线图,就是网上有非常非常多,不管是生命工程,还是生物,还是包括我们的股票,还有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图……就是各种他可以从网络上找到的一些,他觉得可以用的曲线图,然后根据这个曲线图再来转换。
比如说第一个著名的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还有和一篇论文叫谢杰瑞的《少数忠诚群体如何影响主流意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我当时会做这样的一个作品。
这就是我当时在网络上读到的一篇论文,这个论文就叫《少数忠诚群体如何影响主流意识》,这个是一个华人学者写的一篇论文,然后他做了很多数据分析、定量分析,这是其中的一个图表叫准静态分布图,这个图我当时一看就特别有感觉,因为一看就想到了马列维奇黑色方块,你就马上可以有一种很直接的联系。首先他的课题是关于这种少数群体,这种忠诚的少数群体意识形态,而在至上主义时期就是一个由少部分人发起,前卫运动的一个艺术组织,关联着早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目前还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力。当时就想把这两个联系在一起,所以就把它画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转化。然后这个论文其实你在写出来之后,就是长期被大量的引用来论证说伊斯兰群体在移民欧洲之后,可能在有可预见的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欧洲这种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这种变化,所以很多欧洲学者都是有一些忧心忡忡的用这个去论证那个东西,当然这个跟我的作品没有关系,但是只是说明这个论文它其实是非常的有广泛性的,得到了广泛的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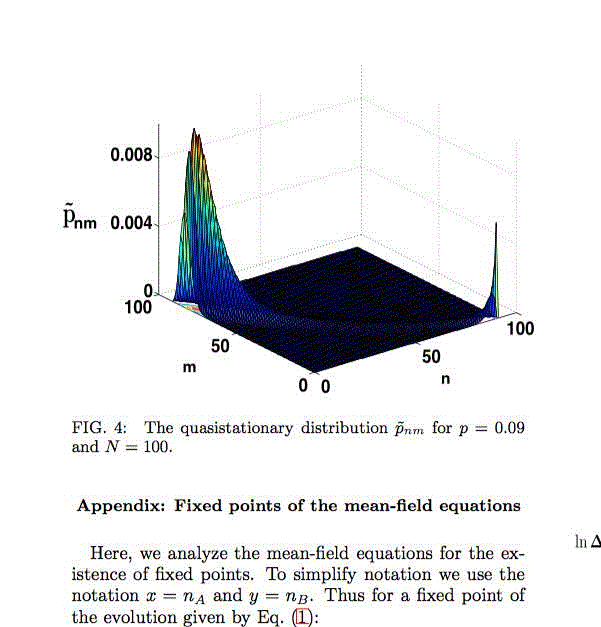
这个现在肯定是会很多,尤其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聊过很多那种曲线它都是随便任何的一个小小的参数的一个调整都可以为各方不同的利益诉求者所利用,所以看似科学、清晰、准确的图表式的,因为现在在广泛的所谓的社会学、就是各个领域,包括地理、历史都有大量的统计这种图表,包括在人类学用到很多,尤其是在美国,是用了大量大量的图表式来研究他们的地理和历史,这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经典的案例。比如说白人在回顾他们对印第安人的那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抽取的数和黑人的或者说那种左派的,肯定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都会出于自己的一个目标然后来选择一个这样的数据,或者说同样的数据最后因为参数的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白人会说我们统计的时候,印第安人的存活率是多少,但是他省略了可能只是活下来,比如确定100个人有20个人活下来,但是还有70个人可能都是缺胳膊少腿的,这里面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但其实也是一样,一直也存在着一种屏蔽,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讨论的就是像这次我们在广州三年展也有大量的关于信息的讨论。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其实还是一样,还是在被屏蔽。
屏蔽有时候是主动的,有时候是被动的,但是更多时候可能在这个时代是技术性的屏蔽。比如我之前做的《WIFI》那个作品,有wifi功能的手机和没有wifi功能的手机,那有wifi功能的手机肯定就可以看到我的作品,没有wifi的是一个模拟机或者什么,你就不能看到我这个作品,所以这个展览对你就是屏蔽的,还有说你有密码和没有密码,你进到一个店里去或者一个所谓的私人空间里去,你有他的wifi密码就可以连上,没有密码就连不上,所以这其实是在用一种更广义的方式去区分,把人分成一个团体一个团体,一个非常非常琐碎的,散沙式的阶层,当然你也可以说它积极的一面就是人的需求和其他更被细分化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其实是更容易被管理的,是一盘散沙的,而你是被互相隔离的。通过技术的手段,或者通过一种阶层的手段,因为你有钱可能买了更高端的东西,你可以用更高端的设备更高端的网络,因此你就只能跟那一部分人,有钱有权有资源可以使用这部分资源、网络的人在一起聊天;另外一部分没办法进入这个阶层的人,他可能只能跟自己那一类阶层的人使用同样设备,使用小米、锤子这样的人聊天,所以这样的社会其实被硬生生的因为各种非常可见的方式去达到了一种阶层的分隔和隔离。
比如说这里面还有另外三张图片,上面这个图片(紫色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关于参数可以被改变,如何去以不同的方式看同样一张图。它很简单,可能对理工科的人来说是特别愚蠢的一种东西,就是一个X轴一个Y轴,当把左边的X轴设定为时间的投入、把Y轴设定为收获的话,那可能这样的一条曲线就代表时间投入非常非常多,然后收入非常非常少。但是假如把它颠倒一下,左边是一个收入,下面那个是一个时间投入,那肯定就表示的是你的投入非常非常少,但是收入非常非常可观,出乎意料的可观。所以一张图表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解读,你可以改变它的单位、大小、间隔多一点、少一点,整个图形的曲线就变得完全不一样,可能一个特别悲观的图形在被你放大某个局部的话,他可能变成一个非常乐观向上的这种符号。
黑色的图是长江,我把长江这个图,把长江这个线画下来,然后把它放在一个X轴、Y轴里面,里面隐藏了一个坐标系,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特别自然的景观被转化成一个数据性的景观。这张绿色的图,一座山被放到这个坐标轴里面去就变成一个纯粹数据的风景。
在2010年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讲的其实是平面设计,但是里面有一小段段落讲到在北美洲印第安人有一种传说中的唱歌的方式,他们可以根据山的曲线来歌唱。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优美和诗意,我就想去找这样的部落。所以我在2015年的时候得了一个华宇奖之后,就是他们会给我一笔钱,然后我在2016年的时候就去了美国,我就去大盆地地区去寻找,我租了辆车然后去沙漠里找这些部落,然后看是不是这些部落还存在,还存在这样的歌唱方式。我后来跑了一个多月,走了十几个州我也没有找到这样的部落。
我通过google搜索说可能有这样的歌唱方式存在的部落,应该是在大盆地地区,它那块是特别大,所以我当时就去那个地方,谁也不认识,我就敲门进去到他们部落的议会中心。
还不是营地,他们像农民一样,就是和普通的农民一样定居的,没有什么所谓的奇装异服,就是些很正常的普通人。我就说我是艺术家,中国的艺术家,我想找你们当地的歌手,所以经常就是这样很奇怪的敲个门进去,特别傻的那种感觉,但是确实也很有效。他们因为部落也不大,通过这种口口相传,通过介绍说我知道有个人会唱歌我们部落有个人不错的,你可以找他,然后我就去找跟他讲这个想法,对我来说这些山的曲线、河流的曲线,都是特别传统的景观。
对,我想我们现在的人可能并不再生活在这样的自然景观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现代景观是一些什么景观?就是以所谓的背后依托的这些大数据分析而导致的所谓的曲线和各种各样的图表,这些才是我们生活的景观。所以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我想让他们唱现在的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图,一些我认为可能比较能概括目前现在这种社会各种方面的曲线,比如关于同性恋非罪化的时间表,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同性恋慢慢的被接受了,不再被视为一种犯罪了这样的一种曲线图,还有恐怖活动造成的死亡率的曲线图,还有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一个曲线图,大肠杆菌的这种生长曲线图。
啥都有了,还有婴儿的心跳曲线图,地震波、汶川地震的曲线图,还有这个是缅甸的一个地雷清除的曲线图,然后就想让他们来对待山一样去歌唱这个东西。
如果你受过一些基本的音乐训练的话,就会知道不管是哆瑞咪发嗦啦西,其实它不是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关于音的高低造成的这样一种音符的印象,所以其实这种曲线的高低如果你能定一个调子的话,你可以根据这个高低来哼唱。我就想让他们来唱,但是很可惜的是,唱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让他们哼,鬼哭狼嚎,他们那边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受过这种现代的音乐训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的。
我给他五线谱他也看不了,所以后来我找了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把这个通过电脑软件转化成音乐、声音,让他们去听,然后去回忆,去跟随、合唱。像我这次展示了五个录像,有两个基本上已经失败了,一个是哼不下去了,只哼了几十秒,另外一个也是哼了一边,其他几个基本上哼完,所以它是好几个人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一个声音的呈现。
就是这样不同的部落,像这个是部落是白山阿帕奇部落的这个音乐家,然后这个ute部落的一个女生,这个是Shoshone Bannock部落的,这个是纳瓦霍部落,这个是Chememvei。经常我去到一个部落,他们就会推荐我下一个部落的人,就是一个找到另外一个,或者纯粹就看地图哪里有保留地,我就开车过去找他们。反正都特别友好,除了对白人特别仇恨,对亚洲人或者长得跟他们挺像的人,他们还是挺友好的。
有,但是只能唱他们传统的歌,就是我去那么多部落,基本上都有很类似的,一定要有一个鼓或者什么东西。
一般就是一个鼓,我忘了,我的记性特别不好,我得看录像才能记得。然后就是一些歌,它们分成两大类,为什么这个名字叫《盐与鸟》,就是因为它们有两类歌唱的方式,一个叫盐歌,你可以想到眼泪,就是一些比较悲伤的、庄重的场合歌唱的东西、一个叫鸟歌,就是比较欢快的这种东西,我当时去录制也拍了一些他们在表演传统音乐的那种现场。但像盐歌他们是不允许拍摄的。
是不是可能跟他们某种生命的仪式或者一些特殊的时间有关系?
就像我们以前去世或者什么的一种,现在很多少数民族还会有这种仪式,喜庆的时候肯定唱的就不一样。
他们部落的长老就提醒那些年轻人说,你这个歌不能唱给他看的。他们都很好的,我走的时候还送我T恤,送我水瓶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我当时拍的我去探访不同的部落,在过程之中我会用手机记录附近的山脉,这个背景音乐也是一个印第安音乐。
他们部落特别多,有几百个部落,分布于不同的州,也有互相仇视的。比如说有人认为有些部落以前是跟白人混的,所以现在政府对他们特别好,给他们什么补贴,各种东西,都会这样说这些人以前都是他们的狗腿子。因为他们大部分部落确实生活得一般,都不是很好,他们好地方都被白人占了,白人会把他们赶到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去,当地能发展经济的资源是很有限的,大部分要么就是现在所谓的景区,一些干枯的宽阔的景区,要么就是允许他建一个赌场,靠赌场做生活的收获,所以有的确实是很破败的农村。好像以前一些艺术家做过一些类似的项目,就是关于所谓这些自暴自弃的印第安部落的人,有好多这种长期酗酒、吸毒。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乡村一样,只留下一些留守的儿童、老人或者一些懒人,然后整个村庄都废了,都是这样的。他们也是很伤感的回忆所谓的过去,因为他们一直还是特别边缘的一个群体,即使是说美国政府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去弥补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的这种伤痛还是没有办法被消弥。
比如他们一直跟我说到他们以前所谓的boarding school运动,好像听说我们中国政府对新疆也进行这样一种政策,就是把他们的孩子从父母亲身边运走,运到大城市去受所谓的现代教育,我不知道这算好还是不好,如果是融入现代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但确实这个方式是很残忍的。
最早白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把当地土著的孩子偷走,集中管理。
对,然后很多人、很多部落都丧失了自己的传统语言,有些部落只能找到一两个会说,他们每个周末会组织一个语言学习班,去学习以前的语言,很多人可能只能说英语,就是有这种很强烈的关于文化的焦虑感。
一种强烈的,很失落的,无能为力的......
我觉得我们接下来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因为还是有朋友看过你的作品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提一些问题。高洁老师因为一直在研究关于神话、历史,各种对很宏大的到很微观的,你有看杨建的这个作品吗?关于印第安的这个,因为他对这些都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可以让高洁来跟我们聊一聊。
因为杨健一直是一个好艺术家,他的作品一直都口齿很清晰,所以说看完这些作品以后我都特别没有问题。就像你使用这些图表拿给这些印第安人看,我也想到那些资料里面的这些,比如说当时比较早的一个书里面写的,就是他们拿着一张照片,他们想要印第安人的东西的时候,他拿了一张老虎的照片,问他们关于这只老虎的问题,但是印第安人看不懂照片,他没办法辨认照片是什么东西,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色块,然后那些印第安人要求白人用他们一些护照、身份证这些东西,他们发现他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上面的照片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辨认那些照片上面的身份证有什么区别。我们对这些照片的思想都是以前被一些训练过,就是你拿这些图形给他们看,你看得懂这些图形但是印第安人看不懂,他们其实对这种图形有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是你把这个解读方式用你现代的方式,包括音高,你都翻译完了给他们,所以说他们已经把它们当成了一个发声桶,一个乐器,没有经过他们的灵魂,所以他们唱的那些歌里面没有灵魂,这本来就是一个被文化强奸过的民族,你再用你的东方文化再强奸一遍,挺惨的。
感觉我要为白人殖民主义者道歉了,不过你说的确实是如此,我觉得你说得很好。
这其实也挺好的,一个艺术家能体现一个很干净的灵魂的这么一个人,在面对这些状况的时候,你就把自己对这个东西的判断直接强加给他们,最后从这个当中能看到的是你,而不是他们,所以我觉得杨健是个好艺术家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对,这其实也是我在做作品的时候一直有反省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视角确实是那种强奸式的视角,但是我的另外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因为放得太久了,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必须把它做出来,做出来以后我才能稍微从这个方案里面解脱出来,才不用继续困扰在这个东西里,可以到下一步去创作。所以我当时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比如说最后其实是解释了我的方案之后,用一种声音转换成音乐的方式让他去聆听,让他去作为一个纯粹的歌手,他们里面好几个人是专业的歌手,就是去听这个音乐你有什么感觉,然后你再去附和或者说去跟随。所以从这点来说的话,后面就变成了一个类似音乐家交友的方式,即使我自己不是音乐家,但是我这个音乐的转化其实是找了一个音乐家朋友让他去做到,他们等于说是一种隔空的媒介,让他们产生一种对谈、交流。这个可能是一种稍微缓和了一下这样的一种关系的一个处理手段。
是很诗意的,我是觉得你用它作为一个诗的材料来写你自己的诗,你能读到的是你不是他们。
对,是。看下一个作品吧。可以快速看一下我之前2016年在北京的一个展览。
其实你刚才说到所谓的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些用这种数据篡改或者偷换是最多的,用在人类学、社会学,包括后面的地址,比如说地理,这些学科就开始了大量的数据的引进,但其实我们在那个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说到,其实美国有很多写这些的书,有一本就是讲公共分子的这种话语,这种权威,一种数据,然后这里面有很大的一点就是提到的是大学教育,大学教育这个数据式的,统计式的,是最容易去渗透到各个学科里面的,然后这些数据图表生成出来的不管是在文化批评,还是在社会的批评里面它一直是包括媒介、媒体的采用,一直是属于这种被当局者,或者说被一种权利的那种应用,其实在这里面是很厉害的。那包括说我们这个社会学,你刚才说的人类学用的那种印第安人,它有很多时候是白人至上主义,会利用筛选的数据的时候,所以我也在问杨建,我说这些都是基于我们一个很长久的认知,但是你能用这些曲线和你作品的创作,我觉得这个之间,尤其是我说我一看到那个著名的马列维奇的黑色方块,我一下子就觉得很震惊,为什么会用到了这么一个著名的符号式,因为这很不杨健。
人类学的开端就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没有殖民就没有人类学,或者没有人类学也就没有更好的殖民。这个好不是站在我的立场,是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因为他总是派遣传教士、科学家去作为他们的目标、目的地的被殖民社会,或者和殖民者同去的,去研究他们、他们的语言,这些当然是在促成一些学科的建立和知识的收集,同时,确实是更好的、更方便的给了这些所谓的殖民者一个更好的角度、视角和手段去统治去控制所谓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所以是相辅相成的,既是结果也是一个原因。
这是我当时2016年在北京做的一个个展,这个展览就是基于我写的几页很短的一个小说,我建了一个迷宫,这些我写的文本就是关于一个建筑师,他想建一个完美的建筑,这个建筑就是迷宫,这里面有一些具体的物件、具体的作品、建筑师每天的一些思维的痕迹或者运动的轨迹,然后这些布帘上面都会印一些我写的某些短篇小说的某些段落,穿插着散落在现场。
这个就是现场图。看起来特别的白,上面有一些文字,就是我写的东西,以丝网的方式印刷在上面。第一件作品叫《车轮碾过的河流》,就是处理关于两种时间的关系。这个作品已经讲了很多遍了。
还好,看多了。因为我每次再讲一遍的时候,总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又重复着说一遍。
讲到了时间的关系,艺术创作里面的时间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今天做当代艺术,尤其在阐述这个时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呈现它?
和时间有关系。一条车轮印碾过了一条河流,大家都知道很著名的那句话“逝者如斯夫”,这个时间就与河流一样,不停地往一个方向去流,永远不会再回来,这是特别传统的时间观念,现在的时间观其实就像车轮一样,可以进可以退,可以前可以后。
可以随意的碾压,可以随意的从这个所谓的这种线性的时间里抽离出来,所以我就把这两组做了一个结合,把它们并置在一起,所以两种时间观念就在这里面呈现。
这是另外一件作品,里面有一个监控器拍到的一个视频,地底下的一个电钻,在缓慢地钻东西。当时我做的另外一件作品是关于监控的,我写了一个剧本,关于发生在一个未来的监控室内两个保安的对话,他们后面是电视墙,电视墙就是我从几千个视频里面收集到的几十个监控的视频,两个保安在讨论一个关于末日的话题,但是这种末日不像我们平时生活里经历的或者是看到的那些科幻小说里面的这些末日,什么外星人袭击,大冰河时代之类的东西,其实是描述的一个特别日常的,特别无聊的,特别没有激情的一个末日,就像我们现实生活一样的末日。都是我在国外网站上翻拍到的一个监控视频,特别缓慢,因为大部分的监控视频都特别无聊,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而且大部分的监控视频其实都从来没有被看过,即使是监控室保安也肯定都不会去瞟它一眼的,除非有些事情发生,有些坏事发生了。
你才会去调出来看,这个项目的名字叫“世界监控器——末日已经开始,只是没有坏事发生”。这个有三场,有一场在北京、一场在上海,一场在三亚。
所以杨健的很多作品其实是和监控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今天聊天之前我们沟通了一下,我们不讲监控。
监控其实在你的作品里呈现挺多的,还有包括你的作品很重要的一些关于机械类的感应线,我们也谈到了。
另外一个作品叫《爱丽丝的漫游》。《爱丽丝梦游仙境奇遇记》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本小说,一只兔子带领主人公进入了一个很神奇的世界里面去,这只兔子在我这件作品中也是引导大家进入这个小说的视觉化呈现的一个世界里去。那这个兔子是死兔子,它的身体内部有一个wifi,就是一个路由器,然后它背上穿出了三根天线,后来在它被人买走之前,我就把它那个电线掐掉了,防止被买回去做成路由器,他本来是个路由器的,我说不行,不能把它买回去做路由器,所以把它的电线给剪断了。
没多少钱,所以卖的时候也不兴奋,所以我才要把它剪断。(笑)
这个也卖掉了。叫《环形山》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看过的那些月球、星球表面上的那些陨石坑。
我去废品收购站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容器,圆形的容器,锅、碗、瓢、盆……只要是圆形的我就买了,很多这样的破烂东西,然后在铅皮上拓出来,就像环形山一样,所以这些特别具体的生活的微观的东西就转化为特别宏观的、巨大的天文现象。
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也是杨健一直痴迷的一个创作的主题。
我的目标就是用尽量少的廉价的材料去偷偷的骗取那些藏家的钱,把他们的钱换成一些廉价的、无用的东西,这就是我的革命的手段。(笑)
这是另外一个很早的作品叫《肤浅的隐喻》,上面写的2016年只是三角架是2016年的,但是那个东西本身是2009年到2010年的。这个光本来是在导引路线的,比如中国的样板戏里面《红灯记》,灯和光只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示,指引方向与拨除迷雾的,这里把它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转化,变成一个问号,这里打出的光不再是那种可以给你正确的东西,就是比较可怀疑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很无聊,所以我叫它肤浅的隐喻,所以是一种双重的肤浅。
所以有些作品也是这样做成的。比如还有一件作品好多年前做的是个录像,就是我为一个挖掘机的一个局部来配音,挖掘机挖掘然后配上怪兽那种哇哇的叫声。我做的时候一开始觉得这个东西挺蠢的,是2004年的时候做的,我给我的导师看导师说挺幼稚的,后来我就配了个题目叫《愚蠢的电影》,然后就参加了英国的一个展览。
地上也是一个录像,是我翻拍的一个监控录像。它检测到风,一些监控器它有很多功能,假如有风、移动的东西在面前经过,它会标识出来它的轨迹和它的大小,比如说风刚才闪了一下。把它放进来,因为小说总是有很多不同的面相,作为这个视觉小说里面一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来展示。
另外一件作品叫《SDSS-3939》,应该说这个盘其实不是个很简单的盘,它是一个用到天文望远镜背后的一块,有个国际天文项目叫斯隆数字巡天计划,就是他们计划用一定的时间去把我们肉眼可见到的天空上的天体进行一个光谱的像户口普查工作一样把它们的光谱记录下来。你知道每种不同的光会提示你这个星球存在什么样的物质,它离我们的灵魂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以及它的各种属性。所以科学家当时就是把每一块,像这个基本上是一块手掌大小的一块天区,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星系或者一个星球,看这个就是那个望远镜,每个天体都定点的去观察,去收集那个点上的光,收集到电脑里面去进行一个分析和归类。
然后当时知道这个天文项目,我就写信给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天文台,我说我有个想法特别想跟你们合作。我小时候听过一个传说故事,说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大象,假如你能找到大象的腿往上爬,你就能抓到星星,我觉得就像你的工作一样是在捕获星光,所以我说我想做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需要用到你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一片?后来他们觉得挺好的,就把这个东西寄到北京的中科院天文台,再通过中科院天文台给了我,但是他们要求的是以后你做完作品拍个照片给我。作品是大象它的一条腿变特别大,下面就垂着这个东西,里面LED灯。
这个是《不建议使用》,这三个灯泡,灯泡经过加热改造之后有的地方会起泡,有的地方会凹下去。
它的玻璃的厚薄就产生了变化,但他还是可以使用的,但假如你去使用它,可能会因为受热不均爆破、爆炸,所以它的题目叫《不建议使用》。这个作品也被上海的一个藏家收藏了。
这叫《切分的人》,这个作品就是源于很多年前我听到的一个科学的突破:就是说他们研究出来一种工具可以把人切得特别特别的薄,一个人可以切成几百万份,然后来研究他内部的结构,那这些数据是上传到一个网络上去给很多科学机构共享作为研究的一个数据库。我根据这个轮廓设想一个1米8的人,从他的头顶开始一直做到他脚底,就是把这些切片都做出来,然后把它连在一起,就像一条高速公路一样。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展览,所以特别多人喜欢,男女老少、老少咸宜大家都喜欢,连买家都喜欢,第一次买我作品的人也在这个时候出现。特别简单,特别容易进入,又有一个文本在,所以大家看得很开心,觉得很文学很诗意,又觉得作品也不错。
因为文本很诗意,所以作品也就容易了很多?就不会那么干涩。
对,所以是给了观众足够的拐杖。
下一个,这个作品挺差的,我处理展览的时候不是把每个作品都处理为一个很独立的作品,它必须是为整个展览服务的。
它需要这个东西,所以它在这里面,即使可能通过平时的创作标准来看它可能是不行的,但是在这个展览里面它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这也是里面的一个动画,就是这个展览其实引用了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有展出过,但也是很老的动画,这个展览是一个链接、引用各种不同作品的展览。像这个动画是我之前做的一个纸板动画,基本上不会动的动画。
这是展览最后一个作品,就是大家前面都讲过了《我的生命倒计时器》,我为什么把它排在最后呢?是因为就像我前面介绍的第一个作品是大理石《车轮碾过的河流》,都是处理时间的。入口的作品其实是一个很宏观的关于大的时间,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小的个人的私人化的时间,所以你从一个宏观的口进去然后出来,又回到个人的自身的个体的角度去,就完成了一种循环,一个展览结构上、视觉上的安排。但是它的数字已经在变化了,之前是15开头的,现在是13开头的。
这些年其实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在用自己的生命还有比如说自己的脉搏,因为我们身体本身每天也有很多信息,它也都是可以转换成数字的,这个作品我们看到的也很多,包括你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次OCAT上海馆展出的《修剪时间》这个作品。都是和时间有关系的。
我也是不小心做了一些关于时间的作品,很多人都会问你作品处理的关键词是什么,你的线索是什么东西,我其实特别反对去描述或者归纳总结这样的东西,但是好像确实我的作品里面有一些关键性词汇是会串联在一起。2005年,我在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就特别困惑,因为看到很多大师他们总是有一个很清晰的线索,你看他的作品发展很清晰,但是我的作品好像没那么清晰,我就是各方面都感兴趣都想做,所以就很困惑,是我做的不对吗?后来我想可能真的完全是因为创作方式的不同。我当时总结了一个模型,有人可能是一直往下走的,就是所谓的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但是我的呢,你想象一个三维模型,从这个角度看它可能是一直往下的,但是你把这个模型整体转个角度的话它可能是一些平行的不同深浅的线,但是你把整个模型转过来的话,这些原先平行的线就会重叠互相遮掩成一条不停的往下的线。 这个听起来似乎是在恭维自己的创作一直在深入什么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那个,我想说的就是这种创作线索的不同。所以当时可能就是为了应对后来要出现的关于我的作品的关键词的问题,我先提前制作了一个模型出来去回答。
你先有了前窥你很厉害,在那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个其实可以让现场的朋友来沟通一下,从第一直观对你的作品有什么样的认知或者问题。
其实我很感兴趣的是我看到今天讲座的标题《亲爱的!千万帮我留住人》,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你突然会选这个标题,但是我看完你最新的那个作品,我又好像理解了,本来是想提问这个问题,但是又自己解答了。
我的理解是因为很早之前知道你在做这个项目,我一直很好奇你会怎么去呈现你的旅程去美国的经历。我想的可能会更诗意,就是你去探访一个古老的民族,但是那个古老的民族其实就好像是安妮老师有提到的,你只是宏观的、微观的去角度去换,你可能影射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这样,可能我的理解是这样子,所以很自然我就解答了这个标题的名字,我不知道这样解读是否合理?
其实这个题目其实完全是随意的,安妮去广东看三年展,那个晚上她来得特别晚,我正好跟一些艺术家在一起喝酒,她就说千万帮我留住人,我要去做采访,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
对,我发现你创作的有一些灵感就是你生活当中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被果实压弯的那棵树,我就觉得那个灵感非常巧妙,所以就自己消化了这个问题。
所以他才会说什么三维模型,就是他自己勾勒出来的。其实杨健他的问题就是,他总是被身边转瞬即逝的东西吸引,虽然他说宏大的宏观的,但很多时候他是被很多很多的很细微的、很微观的东西所影响或者干扰。我觉得就很好,因为如果我们总是是麻木的面对身边很多细微的东西,他没有感知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的线索我觉得肯定是有的,一个做了十几年的艺术家他否定不了,因为作品就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像我熟悉的这些艺术家,如果一个艺术家他实际能创作说我们找不到一个线索,这就太扯了。
这也很难说,我觉得我之前也是提前为这个问题准备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说只要你是真诚的,你不是抄袭的,就是你的思维是在真诚的在思索,在仔细生活的话,你做的任何所有的东西,它肯定是你做的,肯定是有条线索在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回答,因为艺术家不需要去总结这样的东西,他做过的历程,只要他是一个真诚的、诚实的人,他不需要总结,他也没有必要去总结,因为总结有一种危险,这个总结有可能是狭隘的总结,是局限化的总结,然后你把所谓的总结反过来作用到自己身上去进行你的下一步创作的话,这可能就引起很大的问题,比如会提前很久说我是创作关于时间的,关于生命的,我下一步要做出这样的东西,这可能一下子就把你局限住了,所以这种总结是有危险性在的。当然我同时也想说不总结和去总结其实都有问题,不总结的问题就是说有可能让你的创作一直停留在一种特别浅薄的、散漫的程式上,妨碍你去向所谓的深入,但是深入这个东西是特别的成疑问,什么是深入?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说深入这个东西,这是它的危险;总结的危险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可能会狭隘化,会框定住你的兴趣点和方向,所以两种总结和不总结都是有问题在的。
所以我们决定了,我们今天的谈话是游牧式的、没有重点的、很散漫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完全是对艺术没有什么概念的,但是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艺术展,我其实对你们举办的一些活动是非常支持也非常崇敬的,崇敬一点不夸张,是发自内心的跟你们这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的一种敬仰。说实话现在不管是在教育还是在一些商业,或是一些价值观的取向方面,我们的文明已经稍微有一些在消逝的感觉,当然这些年可能也受到更多的一些重视,也是因为受限于很多社会现象的一些影响,没有一个人的生存是不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精神文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太高尚的一些东西,也是需要一些社会各种发展的一个阶段来去不同的呈现。所以我想说的是,因为我去一些城市去旅游,我很希望真的对这个城市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方面的东西太少了,我说为什么成都那么受人喜欢,可能他们就保持了他们的地方特色,还有台湾,像这些地方它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文化特色保持下来,而且是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现在很多其他的一些地方,可能真的是缺乏这些作品,让这个城市有温度,我们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我们看到的都是好像就是像你说的都是曲线,都是用各种数字或者数据来描述的,但是它的温度在哪里,说实话我确实感受不到,我也不知道现在这方面做文化保护或者文化继承的队伍有多少,或者是怎么样的,我真是没有概念,我想你们都是从事这些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可能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些解答。
其实我也没有概念,因为你说的这些东西其实更多的是政府主导的,又是城市规划这样的东西,其实艺术家在里面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像我这种艺术家更没用了。
我知道,我想说的不是说你们完全不盈利,我的意思是说可能需要这些组织去对你们进行一些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不管资金支持还是场地支持,反正各类这方面的支持。
我非常喜欢你的作品,我觉得他刚刚提出问题就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你的作品都是环绕在你对生活的观察,对很多事情的提问,我好奇的是关于很多提问,比如说有很多宏观跟微观,用你不同的视角,所以你观看的视角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揣测的,我觉得可能是有很多自我矛盾、自我提问、自我解答,但是我好奇的是你对这些自己的提问是不是有一些批判,是不是有意图想要提醒观者,想让观者提出一些问题,这些事情背后是有一些批判性的。
那就可以了。因为艺术家做作品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法知道众多不同的个体是怎么去看这个作品,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生活、知识背景、精力都不一样,所以他对你的解读也是千千万万种的,你没办法从这个方面去考虑是不是会有反应,然后最后以此反过来去创作东西,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更多的创作就是基于自己的一个观察,这种观察可能是有意义的,也可能是无意义的,但是他只是去做了,有时候恰巧的是提出了一些问题,或者不恰巧的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也仅此而已。
最后谢谢大家,我们的对谈差不多就结束了。另外插播一个广告,杨健老师他自己刚刚办了一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是关于艺术家来写艺术家,很有意思的是只能让艺术家来写艺术家,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公众号的名字叫艺术家批评艺术家,我还有另外一个公众号叫东吾洋,公众号太多了其实大家也不会去看的,像我订了很多公众号最后现在都不打开了,所以看不看也都无所谓。
不是,我们自己还是会找自己想要看的,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当成一个任务,生怕漏掉一丝信息,生怕落后于这个时代。他做艺术家批评艺术家这个公众号最重要的是他觉得现在听不到真实的批评的声音了,所以大家送给他最好的新年礼物就是批评他。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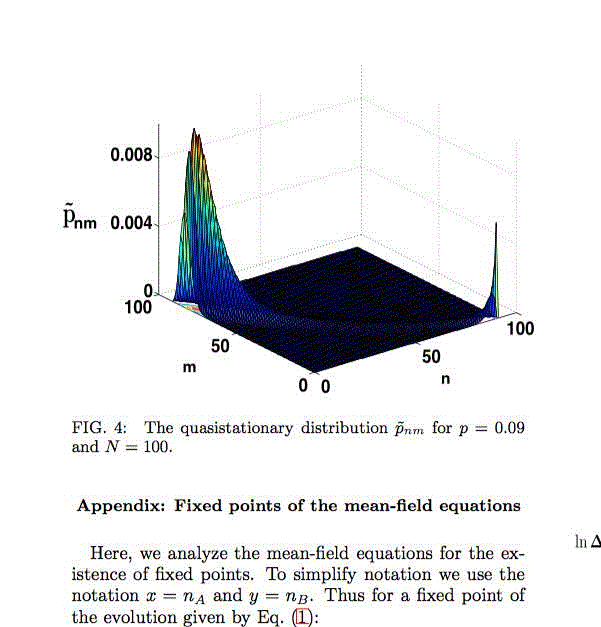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