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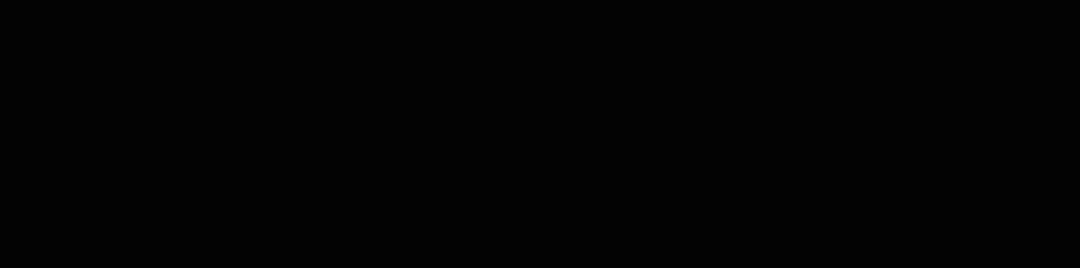
开始一场场不可思议的采访!
A4新展“不可思议的行动”正在展览中,我们开始了一场场不可思议的采访。希望你可以在观展前或观展后,一起看看艺术家们和我们聊了什么,或者你有没有产生什么新想法,可以在展览现场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在文章的下面给我们留言。
在今天到美术馆来看展,还是为了追寻某种意义吗?不论你来到A4,或是看到这篇文章是一件多么的偶然和随机的事情。但是一旦进入,对话和连接就开始了。2023年的春天或许适合尝试着去理解别人认知里的世界 ,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思议的行动。



"行为研究项目——重复”展览现场
“行为研究项目”由艺术家童文敏发起,A4美术馆提供支持,在本次年末大展“不可思议的行动”中呈现。项目以研究行为艺术相关的议题为目的,邀请艺术家在不同的议题之下,对行为艺术涉及的各种问题加以回应和探讨。
“行为研究项目”的首次议题为“重复”。项目试图通过这一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以及行为艺术中的经典要素,打开我们对行为和日常的重新思考与想象。
展期过去了一段时间,我们对这次参与“行为研究项目——重复”项目的艺术家们——邓上东、董洁、胡佳艺、李海光、李鹏鹏、李锐、普耘、清水惠美、松郎、王溪曼、谢静、薛萤、杨俊峰、于名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采访由两个问题展开。期待以此引发线上线下更多的讨论与交流。
1. 在疫情这三年中创作作品,和之前创作作品有什么不同?
2. 现在大家常常都被鼓励,去行动,去选择,不要停留在想象这个层面。“行动”和“选择”哪一个比较重要?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

邓上东
1. 疫情前,我每年初都会做计划,然后会按部就班的去进行创作。实施作品更是风雨无阻,只要有了想法,就会去实施,去实现。限制最多的是自己对作品的思考。疫情这三年限制多的是外部的环境。做作品会变得更加的内敛,然后以前会全国到处跑去做作品,这三年,几乎是待在一个地方。疫情这三年的不确定性,不可控性,然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迷茫,困惑。都会对创作造成影响。疫情前,我的创作媒介主要是行为、摄影、录像,然后疫情这三年,我又重新开始捡起了画笔,开始进行架上绘画的创作。
2.我觉得行动更重要。重要的是去做,要去不断的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很多新的可能性,然后在这种可能性里面,你再去做选择,然后你就会生成很多新的作品。两者他并不矛盾,也并不冲突,你可以先选择,选择好了方向,你再去行动,或者你先去行动,在行动过程中发现问题,然后再调整方向,再去选择,我觉得这两种方式都是可行的。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不一样,所以他的工作方法就不太一样,有些会先选择,有些会先行动,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的。最终目的肯定是把作品做出来。

董洁
1.有不同。之前的创作很注重现场,尤其是在现场与观众的互动。但是疫情期间,人们很难聚集,很多事情事情只能线上远程完成。比如我今年的个展,就因为疫情被关闭延期了三次。为适应这种情况,我也开始尝试着在做一些行为录像,这一类更适用于线上传播的作品。
2.我认为“行动”和“选择”并不矛盾冲突。这两者并不是在“择其一而必须得放弃另一个”那种对立面上的。每一个当下都面临选择,每一种选择都有带来不同行动的可能性。以我的一件作品为例来说,《保护仙人掌?还是刺破气球?》就是,用气球把进门的通道堵了,观众手持仙人掌进入,就面临两种选择:a.用仙人掌的刺,刺破气球,打开通道进入,但是气球爆破的巨大冲击力会冲击到仙人掌;b.选择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仙人掌,从气球间的缝隙挤进去。美国人类学家马立安对这件作品的解读是:每一个当下都面临选择。我想这就很好地解释了“行动”与“选择”的关系:选择刺破气球的行动,就得面对仙人掌被冲击的结果;选择保护仙人掌,就得采取用自己的肉身护住这个小小的生命的行动——当下的面临的每一个选择,怎么选决定了怎么行动,怎么行动决定了面对什么结果。

董洁,一束光,行为影像、单频高清影像(彩色,有声),11‘,2022

胡佳艺
1. 想去哪里去不了,空间上受限制,时间上也受限制。这些限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2. 谁被谁鼓励呢?我能感受到的都是被压制。选择和行动不就是一回事吗?

胡佳艺,Shooting — 行动的方式,行为影像、单频高清影像(彩色,有声),1'27",2022

李海光
1. 我觉得我的创作经过这三年更走向了自我,求助于时间。
2. 有选择的情况是很少的,大多都是被迫行动。

李鹏鹏
1. 会有不同,疫情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彻底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节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极其的被动和不确定,这对我的思考和行动的影响是很大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带来行动上的极大不便,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种行动的不便,使得行动更加可贵、更显态度。我认为疫情的三年,是包括政治、资本、人性等方面的问题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而我自身处于这段历史之中,没办法遗世而独立,所以,它促使我要对周围进行思考,对社会暴漏的问题产生反应,因为每一个暴露的社会问题,都变得跟自己息息相关,不做出反应就会让自己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三年的创作我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生活状况、社会的环境变化以及自己和社会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状态、应该如何翻越围墙等。这些放进我的创作,就表现为自由创作空间的压缩、关注的议题的变化、行动方式的变化以及会产生一些对抗性的行动目的,这里我想提到对抗性,因为跳过它对我而言是不真诚的。
2. 我觉得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行动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这两者的关系不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并且在行动中也是要进行不断的再选择的,选择是一种思维上的确认,而行动是一种身体的反应,这个问题其实是知行关系的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其实不认为思维和行动是同步的,它们之间具有很难感受到的时间差,有时候人的行动并不受思考选择的“支配”,所以,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只不过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它们好像能达成某种契约,有点像集合,这种集合在人上呈现出最大化的状态,就是我们常说的和谐,行动和思考的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身体和精神的和解状态。不过从社会属性来说,行动又必然是具有社会性的,特别是你问题里提到“被鼓励”这样一种被动语态和动词,它其实很容易让我联想到一个词叫“被煽动”(哈哈,开个玩笑),不过这里确实存在一个主体性的问题,即行动者是否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行动者的“选择”是被鼓励的选择,还是自己思考后的主体性的“决定”。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只停留在想象的层面,停留在想象,那不是想象,那是一种梦淫状态,我们必须要行动,但是我们的行动一定是自主决定的有主体行为,而且我们的行动也是在时刻变化的,我们需要准备好在行动中来再思考。

李鹏鹏,在有雨的路口,行为影像、单频高清影像(彩色,有声),23'42",2022

李锐
1. 这是谁也逃不掉的时代背景,在作品不会刻意的去强调它,更多地还是回到个人处境
2. 当然行动更重要,尤其是对于艺术家来说。在持续的行动中,选择则会慢慢显现出来。

李锐,窄门,行为影像、单频高清影像(彩色,有声),12'26",2022

普耘
1. 在疫情之前的创作和疫情之后的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在疫情之前相对比较自由,涉及的主题或者内容、对象都会比较丰富,比较多一些,创作没有太多负担。但是疫情之后,不是特别重要的,或者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主题就会放弃掉,更多是集中在更加关注人或者是人的存在,幸福,、生命、热爱相关思考上。疫情之后,会觉得艺术创作非常的不容易,很珍惜一些创作的机会,所以也就会有更多的舍弃。
2. 行动和选择相比,我觉得行动更重要。行动是开始进行创作,开始动起来,开始去关注,开始去思考,当一切开始了之后,才有可能去选择,如果没有行动起来,先去选择,我觉得是有点像空中楼阁,或者闭门造车,你想象的世界,跟你真实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而且很多问题可以在行动当中去选择,只有在行动当中去选择,才是一个真实的选择。如果不是在行动当中的选择,他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选择,也可能是一个假设的选择,所以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是不不成立的。

清水惠美
1.我来中国之前画风景,来中国的原因是学习山水画。后来发现,在北京的生活和文化范围我没有感觉到具体的山,但都市和个人的身体里能感觉到和山一样的东西(可能是与自我或孤独、存在有关),就开始做行为艺术。在东京,我对人的感觉很少,比较来说人都是个系统里的一部分而已。一个人爬山的时候(包括和山里人的交流)就能感觉到那东西,所以行动的力量都放在爬山了。
2.原来我是对社会语言没有太大感兴趣的人,是喜欢流浪的背包族。所以外面的人说的那些表面上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关系。为了行动,自己的选择是对我最重要的。

清水惠美,在光影的空隙,行为影像、单频高清影像(彩色,有声),3'10",2020-2022

松郎:
1.三年疫情是我们共同的伤痛记忆,波谲云诡的现实不停地击破心理防线,让人不清楚自己是被什么控制或是被什么欺骗着。疫情后这种强烈的感觉在创作中无法忽视。具体且真实的无力感使我更加用力地去感知、去反馈,保持清醒并诚实反应自身和环境的变化,用艺术行动来保持住自己的生命主权性。
2.行动是选择的基石,我会先让自己处于行动中,此时选择会在经验之外的路径下发生。如同在行为艺术创作中,身体力行的方式会使人摆脱惯性,从以大脑作为主导的观念传达里跳脱出来,在真实的、变化着的世界中重新作出选择。

王溪曼
1.比以前想得多做得少了。
2.没有“选择”的时候,“行动”最重要。

谢静
1.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一些直觉的东西有了更深的根基,许多无意识变成了有意识。三年前跟现在有区别,这三年间也经历着变化。有些疫情期间想做的作品现在不想做了,觉得语境变了,或者不合适了。有些疫情前想做的作品,在疫情来临后,瞬间觉得它们不迫切了,或者有更迫切想做的事情。不变的是,它们伴随着我们身边一直在变化着的事件和现象而在变化。
2. 都很重要。于我而言,它们不是二选一的关系,而是伴生关系,是形成一个动作共同需要的环节。行动就是一种选择,选择也是一种行动。我们每天都在做成百上千的选择,从醒了要不要睁眼开始,而睁眼就是一个选择后的行动。
当然,这也涉及我们如何定义这里的“行动”和“选择”。“行动”是指代什么?它指向的是当代艺术语境里特定的艺术形式,还是更广泛的做点什么,或者其他。如果与艺术有关,去选择最能贴合自己的表达的方式就好。它们都只是方式,而导向它们的意图更为重要。一个不熟悉“行动”作为工具的艺术家,ta必然有别的工具。而你此刻不想行动,决定缓一缓,也是一种选择。另外,停留在想象层面也不代表它没有在工作,没有在起作用,它只是肉眼不可见的行动。
是否行动?如何行动?这本身就是选择,而它们由无数个想象而形成驱动力。

谢静,怪兽,行为影像、单频高清影像(彩色,有声),12'19",2022

薛萤
1. 疫情的这三年,社会问题更加密集,极致的显现,无论是作为创作者还是女性在生活中,都是举步维艰的,最大的不同就是不需要再浪费时间在模棱两可的暧昧地带识别和辨识,在这种极端的政治情境下,更明确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际的一步一步实现。
2. 全球的行动主义者在这些年提出了许多有关政治想象力的策略。行动,站在前线,积极的,实操的参与公共生活,确认和不让渡个人权利,同时在生活中保持警惕警觉,监管个人权利被侵犯和剥夺的信号,这些是非常具体和实际的。我不认为“想象”和”行动“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将它们看作一体两面甚至一体多面。在女权主义的话语中,仅仅是”拒绝“和”提出今天的女性不要什么“是不足够的。主动地争取、竞争、占有、创造,这都需要想象力。简单来说,就是除了我们不要现在这样的生活,那我们想要的,需要的,竭尽所能所去创造的女权主义者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而这样的想象并不是泛泛而谈的空想,幻想,不切实际的,而是关乎我们当下如何行动。我喜欢愿景这个词语,vision,也相信只有我们拥有更加多元,广阔和丰富的愿景,才有可能接近我们那个心中所要的未来。

杨俊峰
1. 疫情对生活和创作的确有一些影响,比如在疫情前创作更偏向于艺术现场,以作品来说《关于蔡家场的24小时》是在2018年DLAF复归的艺术现场创作的,我在24小时期间不断的与蔡家场发生关系产生联系,在大街小巷游走,不断的穿梭于室内室外。而疫情期间艺术现场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创作开始了项目化的探索,比如《限速40km/h》《迁移》《轮廓》,到了2020随着疫情的种种变化,导致外出的欲望逐渐显现。
2. 我觉得行动和选择同样重要,首先不要停留在想象层面是肯定的,想象是不可或缺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不经意的出窍,思考,或者是想象,而行动是至关重要的,想象与行动相互延伸。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既有身体先行的方式,以行动的方式开始,同时也有预想方案下的实践,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的问自己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甚于作品开始前的一瞬,所以我觉得想象、选择、行动都是重要的。

于名晶
1. 以前作品的方向是和政治无关的,疫情开始关心政治和实时的新闻,作品里也开始涉及这方面的思考。
2. 行动很重要,选择也是一种行动。

于名晶,记忆的重奏,行为影像、单频高清影像(彩色,无声),30'3",2022
更多阅读
Learn More about Exhibition

与葛宇路开始一场不可以思议的对话!

与胡尹萍开始一场不可以思议的对话!
正在展出
On Exhibition

点击图片够买“不可思议的行动”入场券

关于A4美术馆
Learn More about A4 Art Museum
A4美术馆于2008年3月由成都万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创办,2016年8月迁入麓湖生态城艺展中心,正式注册成为民办非营利机构。在创始馆长孙莉的带领下,A4美术馆从推广国际先锋艺术的项目空间,逐渐升级为一个拥12个空间、共6500平米的城市生态型美术馆。创办以来,A4美术馆共举办了近百场专业的当代艺术展览,超过2000场人文类讲座、沙龙、工作坊,与国内外近600位知名艺术家,40余位专业策展人合作。
文案编辑 江雨杉
内容排版 江雨杉
内容校对 黄驿舒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