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
新绘画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已经摆脱了线性发展的模式,而呈现出一种多元、折中、融合和混杂的局面。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当代艺术从“文革”的隔绝,到改革开放后的全面借鉴。这里面包括有许多不成熟的模仿和“挪用”。中国的当代艺术可以说是“话语与欲望并存,喧哗与骚动同在”。中国的艺术家们可以采用任何前人发明的手法,模仿古今任何一种风格。中国当代艺术要往哪里走?我们确实比较彷徨。艺术不创新,何来进步?而绘画不创新,哪来生命力?那些专注于图式化和符号化的群体创作已经告一段落,那些仅仅通过视觉图像的移用或转借做出简单化处理的流行诠释也早已成为过去。随着艺术市场的深度调整,学术更为逐步趋于理性,新的绘画创作呼之欲出。黄庆、李昌龙、彭涛三位优秀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方面做出扎实的探索。

离岸
李昌龙绘画的转向
文 / 杨鉴
1918年,勒柯布西耶与纯粹派艺术大师阿梅德奥占芳一起发布了纯粹主义宣言《后立体派》(Après le Cubisme),自始,勒柯布西耶发展出了纯粹主义,一种追求简洁清晰的建筑风格。此后的《走向新建筑》更是将这一理论进行强调,否定了复古主义和折衷主义,强调建筑这一功能性媒介。如若仅仅如此,柯布西耶的名字只会被作为一个革命者被世人铭记,而人们更愿意将他推崇为艺术家,这是凭借“朗香教堂”中无可言明的窗户排列、透彻其严谨个人生活逻辑的魔方“柯布西耶小木屋”及其为母亲所创作的“小屋”(Villa Le Lca)。在此引用此例的目的是注意到柯布西耶想要诉诸于建筑这个媒介本身的功能属性,而最终无可不免的指涉了艺术家内在的确定性因素,如其政治与历史立场、其对于所面对的观众的叙述方式以及深层次的感性。
 ▲李昌龙《白色方体》120x160cm 布面油画 2015-2018
▲李昌龙《白色方体》120x160cm 布面油画 2015-2018
 ▲李昌龙《引擎》60x80cm 布面油画 2016-2018
▲李昌龙《引擎》60x80cm 布面油画 2016-2018
 ▲李昌龙《台阶No.1》160x120cm 布面油画 2016
▲李昌龙《台阶No.1》160x120cm 布面油画 2016
 ▲李昌龙《修昔底德陷阱》80x125cm 布面油画 2018
▲李昌龙《修昔底德陷阱》80x125cm 布面油画 2018
大抵是从2014年起,李昌龙不再笃信绘画中一次性的感觉,或者说作为一个精炼的绘画者,他选择去主动的扬弃了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反复锤炼才有可能在一次性的绘画行为当中获得的成熟画面效果——即使是带有惰性的思维和惯性的手段也能较为容易的达到国内学院化绘画体系中所谓的“技艺精湛”的画面效果。李昌龙从色层与边界为研究切入点与突破口,在色层叠合与边界挤压之间的拉扯关系中定位出画面的内在结构,使得画面所留下的部分都有很强烈的相互服务与照应关系,构成画面层面上的功能属性,而绘画结构多是经验性的,而非知识性的,所以只能通过多次的叠加与覆盖来找出其最小公约数,作为最为接近画面准确机构的因素保留在画面上。因其每一个形色关系都具备一定的功能性所赋予的结构性意义,分解的形体和交错的画面视觉通道也时刻提醒着周围的造型与颜色的贯通关系,也关乎着画面向外延伸的空间及尺度。
 ▲李昌龙《无名山》200x420cm 布面油画 2016
▲李昌龙《无名山》200x420cm 布面油画 2016
 ▲李昌龙《偶像》120x160cm 布面油画 2017
▲李昌龙《偶像》120x160cm 布面油画 2017
▼请点开图片横屏观看
 ▲李昌龙《重启》30x120cm 布面油画 2018
▲李昌龙《重启》30x120cm 布面油画 2018
与李昌龙早年激进的画面冲突与带有显著政治与社会现实指涉的表达相比,此次转向后的作品体现出了应对自我认知和处境反思所带来的周全和严谨,而非冒失寻找对立。在此,李昌龙的创作与上文提到的柯布西耶在寻找媒自身的功能性指涉具有相似的目的性并且也都触发了背后相同的问题,一件作品就是由一些以创作者具有涉身经验的事件构成的,这些事件捕捉到了能证明自身身份的证据,并打开了能够回顾性地重新阐释这个艺术家身份的各类其他可能性,使得作品除了作品本身的表达之外具有衍生的可能。艺术实践的行为一直被视为是创作中最为主观的部分,这种主体性具有一种对话性(dialogique)。劳作便会实现一种社会交往,哪怕是我们最为私密的劳作,我们俗称的“主观”劳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性的。它涉及社会性的内在化或内在性的社会化。这种说法其实近似于萨特所说过:“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同时人是从自己的角度体验(vit)整个社会的社会存在。”所以一个人只要画出他的所是,也便是社会的化身(incarnation)。也即是如此,李昌龙在此前创作的图像性创作的基础上向绘画的结构转向——亦可理解为向绘画本体性靠拢,其实并未削弱其对社会性问题的思考,而将我们带入他的个人线索当中去更具整体性的思考他的创作方法论,形成上下文的呼应关系,此前的创作实践也成为了现阶段转向的根本基础与合法性支撑。
 ▲李昌龙《完美模型》240x600cm 布面油画 2018
▲李昌龙《完美模型》240x600cm 布面油画 2018
▼请点开图片横屏观看 ▲李昌龙《悬池》30x120cm 布面油画 2018
▲李昌龙《悬池》30x120cm 布面油画 2018
 ▲李昌龙《王座》160x120cm 布面油画 2017
▲李昌龙《王座》160x120cm 布面油画 2017
因此理解李昌龙的绘画回到他此前的个人线索当中整体性的观看会显得更为有效。如果粗暴的划分,李昌龙此前经历了学院遗产与图像与景观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李昌龙虽然身处国内绘画的流变当中,无法避免的与同代艺术家具有很多思想上的相似性,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则是这两个阶段确立了一个鲜明的个人政治立场、艺术观和通过颇具质感与力量的作品虏获的艺术表达层面上的话语权利。纯粹的自我、晦涩、反复、充满了喃喃自语与深厚的情感……这些东西集成了一个具有厚度、立场及个人性的个人史,皆成为最新阶段的转变提供了有效支撑。李昌龙最初的创作便展现了非常尖锐和明确的表达对于社会政治的切身感受——例如《中国景观》阶段作品,再后来又如现代主义电影一般的蒙太奇式的非连续性并置,刻意创造碰撞而建构意义,映射景观化的社会现实——以《景观写生计划》为代表。这些语言方式在发声时都与当时国内艺术世界具有有效性的表达方式吻合,不但在表达上生效也成为重要积累。然而随着时间的消耗和认识能力的提升,艺术家不再甘愿将这种情绪与荷尔蒙表露于绘画最浅层的表面,而是更愿意将其藏匿在绘画结构之下,像是自己编撰了一套符码将它们封印起来,原本直接具体的图像信息随即转换为带着某种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东西,比如意象簇的构建和有节制的抒情,浸染出此前并不具备的诗意化氛围。像透光一般释放一些信号,也并不期待真正被谁完美破译,这也是对绘画当下处境和内容容量的具体性理解,也这个表达欲望旺盛的时代的逆向行。
 ▲李昌龙《色层与边界No.7》25x30cm 布面油画 2016
▲李昌龙《色层与边界No.7》25x30cm 布面油画 2016
 ▲李昌龙《色层与边界No.22》25x30cm 布面油画 2016
▲李昌龙《色层与边界No.22》25x30cm 布面油画 2016
 ▲李昌龙《色层与边界No.4-6》25x30cmx3 布面油画 2017-2018
▲李昌龙《色层与边界No.4-6》25x30cmx3 布面油画 2017-2018
李昌龙现在的绘画当中依然延续并且发展了了他创作当中最为重要的个人遗产, 那便是借用具有另外一种逻辑的结构,嫁接到绘画的结构,也即“形式”当中。其中最为显著的“另一种结构”便是舞台与装置语言。他绘画中始终存在对于某种实体空间的压缩,舞台的戏剧感和舞台相对应的现实空间被反复嵌套,镇压在空间概念之上的画面主体内容或者说是信息与能量密度较重的部分,而它们时常是横跨多个艺术家在底层铺设的空间与时空观。在如《完美模型》(2018)和《修昔底德陷阱》(2018)这些作品当中,李昌龙在画面表面制造了具有形式感的几何“凸起”,一方面这像是画面结构当中充当某种功能性的部分,另一方形成一种以画布表面为中轴的内外空间概念的双向伸展,辅助画面内的多层空间更为显著的同时也勾连了现实空间,而对于现实空间的调动本不是绘画最为擅长的事情,这种调动更像是给予处于现实空间中观众一个由视觉投射心里的扶手,跟容易走入艺术家设下的舞台“陷阱”。
 ▲李昌龙《白色手套》120x160cm 布面油画 2017
▲李昌龙《白色手套》120x160cm 布面油画 2017
 ▲李昌龙《国际通道》150x300cm 布面油画 2017
▲李昌龙《国际通道》150x300cm 布面油画 2017
本次展览所挪用的“离岸”概念来自英国小说家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的小说“离岸”(Offshore),它是一个主动概念而非被动选择,主动的在选择与高效的世俗化的功利主义的现实生活保持一点距离,但绝不是傲慢的离群而居或者无政府主义的狂欢理想,而是一种保持一定有效距离的在仔细遴选想要与必须的一切。李昌龙想要离开的岸是艺术中被他以及同辈艺术家已经了然于心的部分,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其实本就应该是不安于身处偏远的象牙塔之内,不谙世事与科学发展,更应是与之相反的,当代艺术其实是被新自由主义稳妥的包裹其中。艺术家自觉的生成与出现是个重要的事情,李昌龙的创作其实是对中国语境中的现代绘画的逐渐演进进行反思,其中重要的是带着一种对于绘画边界的僭越与思考,以及对于绘画行为这一状态的触摸与展露。在艺术媒介这一角度上,进行着对于媒介或者自身艺术生成的反动与批评超越。

丨
李昌龙
1975年生于贵州
1999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2002年任教于川音成都美术学院油画系
现居中国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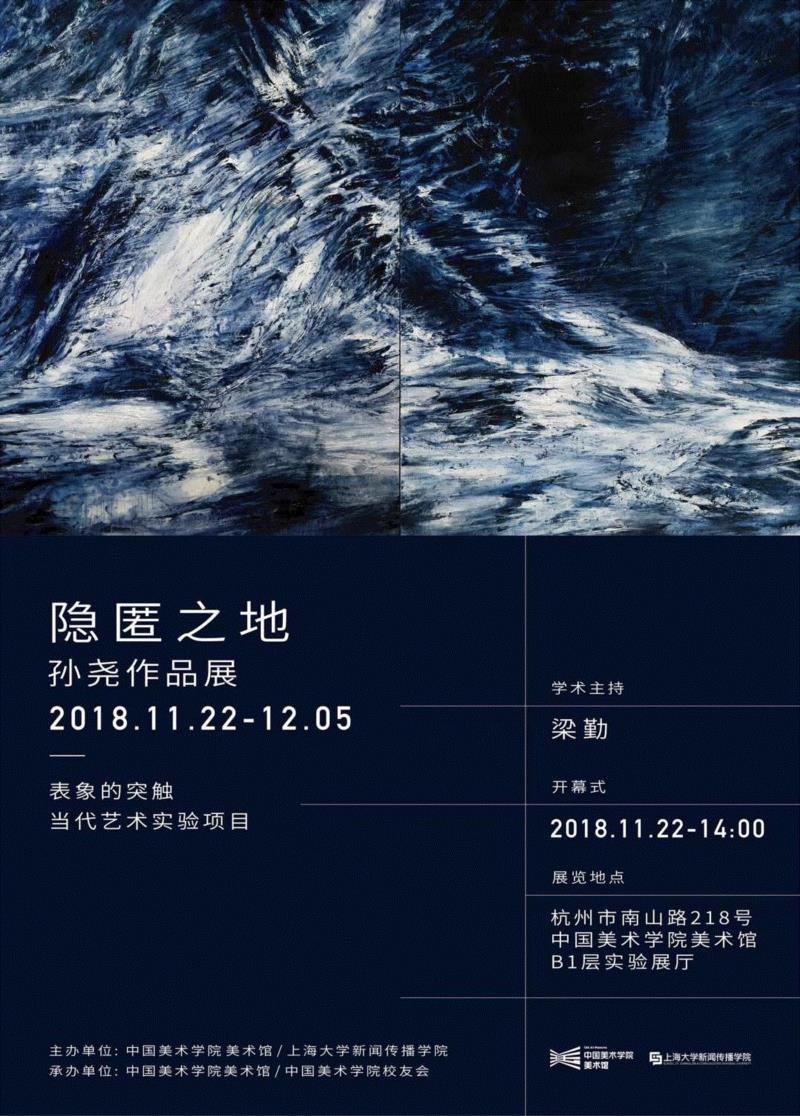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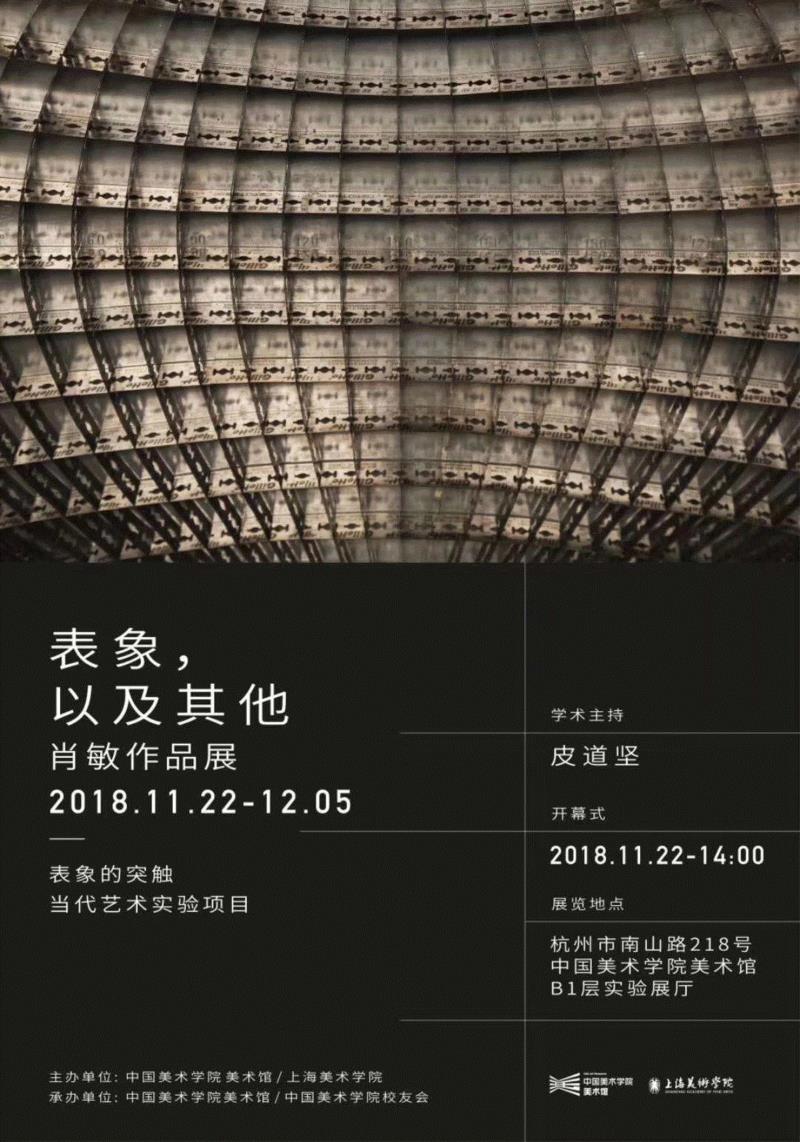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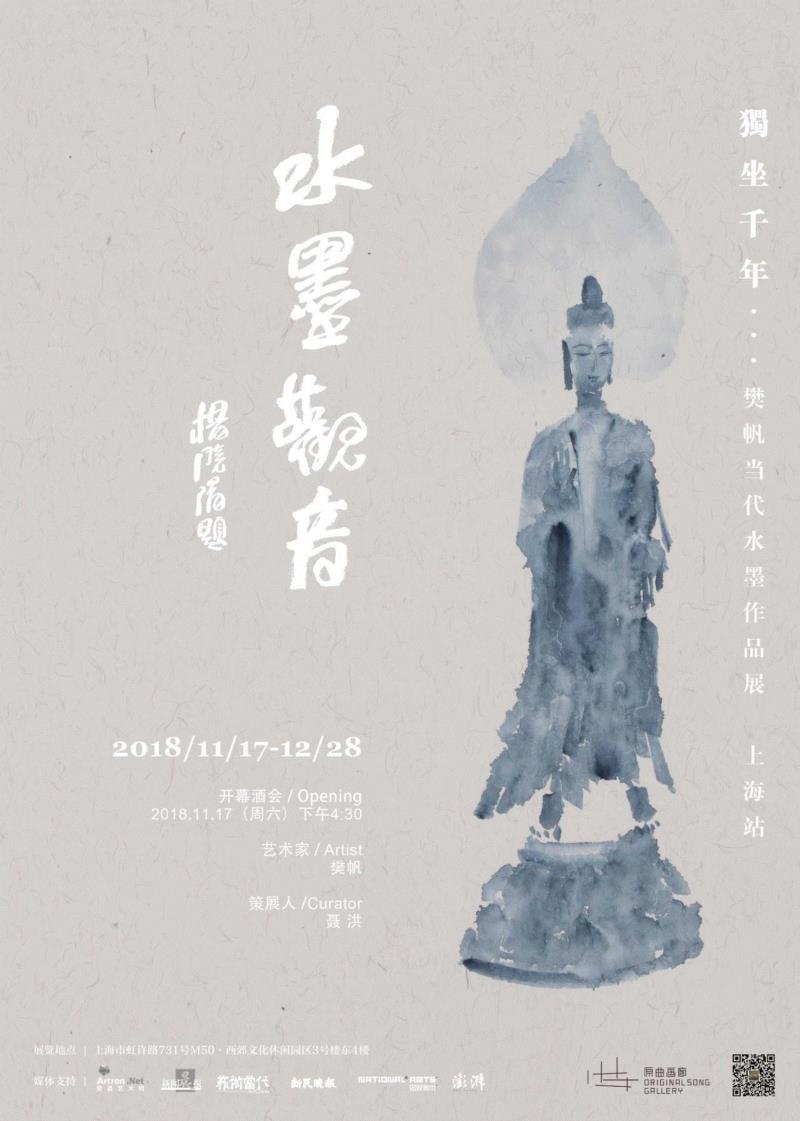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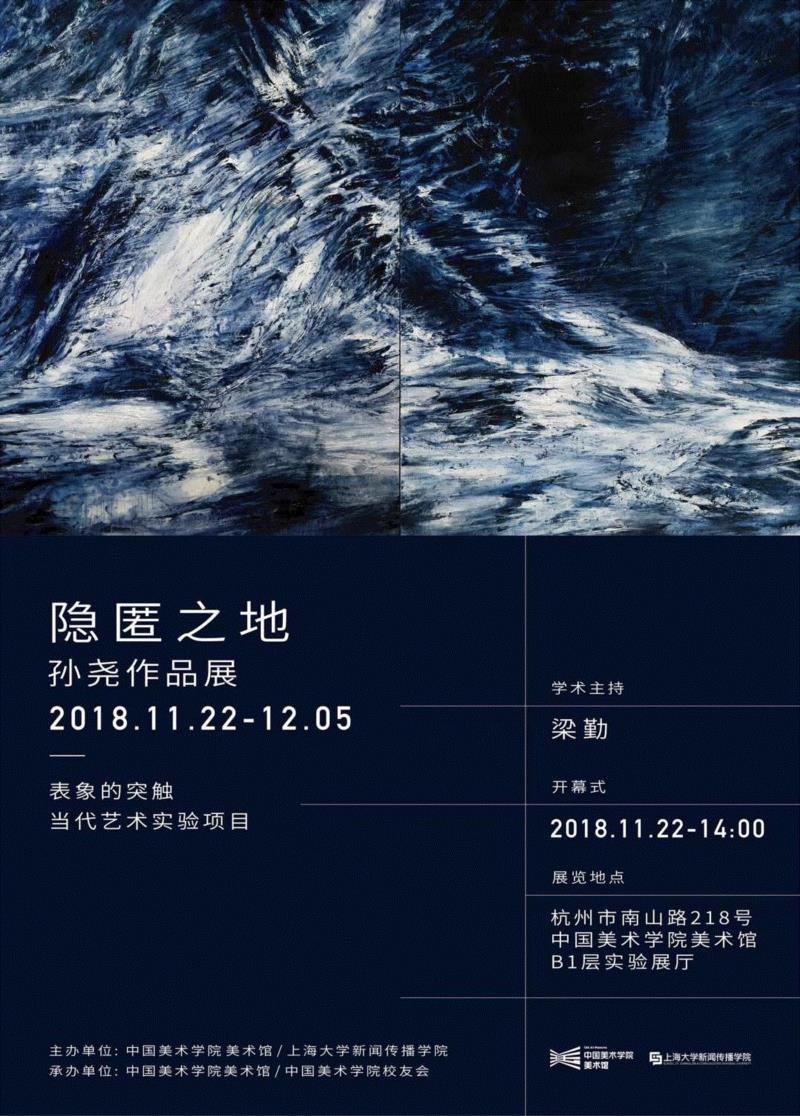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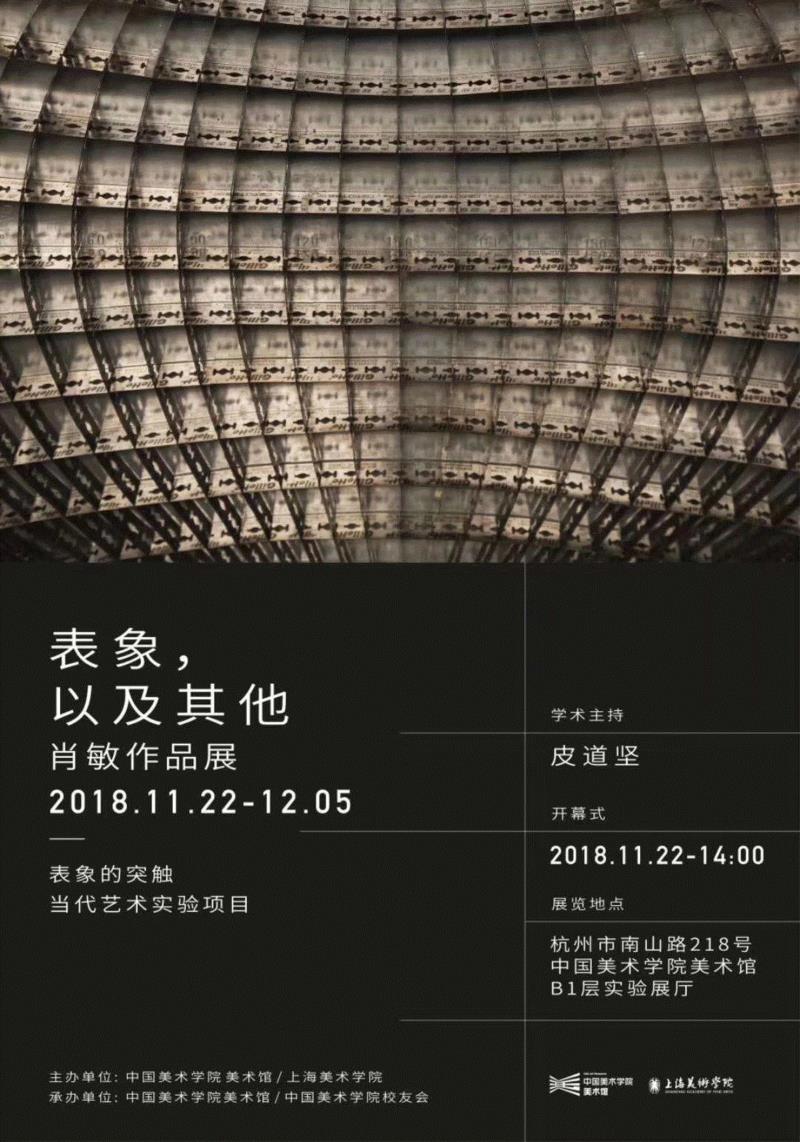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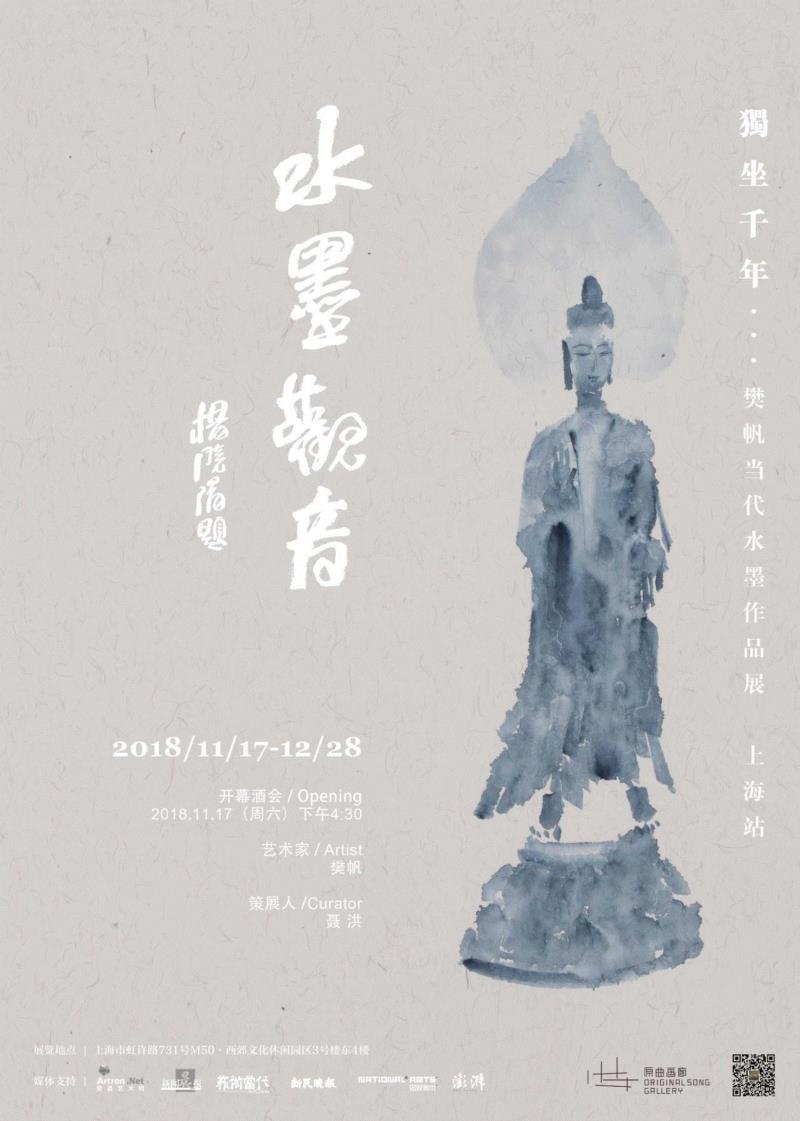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