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位发言人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唐宏峰副教授。唐老师以《影的考古:物、影像与媒介——从康有为说起》为题,通过康有为观看普法战争影戏而思考共通感的事件为例,分析了物、影像与媒介的关系。康有为记述的几段技术化观视经验,呈现出物-媒介-影像之间的现代性脱域本质。这可以解释米切尔所力图证明的形象的生命/欲望的问题,因为媒介构成了形象的身体,形象就成为了物的新身体,因而引发情动。所以康有为才会将情感与媒介紧密结合,将桑塔格所思考的“他者痛苦”的问题及古老的“不忍之心”归结为媒介问题——摄影、幻灯、“以太”,并由此借以思考“图像是什么”“图像有什么用”。

唐宏峰
《大同书》开篇序言康有为将其置于一个宏阔而精微的世界观定位中,上溯世界历史、地理、文明之变迁,“神游于诸天之外,想入与血轮之中”,在其中省察自身之成长。全球世界、文明历史与个体生命,乃至血轮(白血球)被放置在一起,近代以来空间的全球化意识与显微科学视野中的人体构造被结合在一起,至宏阔至精微,康有为的世界观囊括“诸天之外”与“血轮之中”。无论是全球地理意识,还是微观人体世界,这里都显示出一种视觉性,因为无论是星球还是血球,都是望远与显微等现代性技术化观视的视野。由此进入对世界苦难的描述并且记录了自身观普法战争影戏的感受:
且俾士麦之火烧法师丹也,我年已十余,未有所哀感也,及观影戏,则尸横草木,火焚室屋,而憷然动矣。非我无觉,患我不见也。夫见见觉觉者,凄凄形声于彼,传送于目耳,冲触于魂气,凄凄怆怆,袭我之阳,冥冥岑岑,入我之阴,犹犹然而不能自已者,其何朕耶?其欧人所谓以太耶?其古所谓不忍之心耶?其人人皆有此不忍之心耶?宁我独有耶?而我何为深深感朕?
在这段话中,康有为先提出了一个“我为何可以感受到他人的痛苦”的问题,人无法与他人沟通肉体感受,但为何依然会体会到他人的痛苦?他给出的答案是人有“觉”,即一种“不忍之心”。但这种“觉”与“不忍之心”与视觉相关,“觉”源自于“见”。普法战争发生时康有为已十岁有余,但这一事件并未让自己产生哀感,直到观看了一场展现“尸横草木,火焚室屋”的普鲁士攻占色当的“影戏”[应当为摄影或绘画的幻灯(magic lantern)展示],才感到巨大的冲击,即是“非我无觉,患我不见也。” 由“见”到“觉”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

Prussian Victory
(From london stereoscopic company)
唐老师认为在康有为的论述中,他思考人类社会,从共通感走向政治乌托邦,一方面复苏古之“不忍之心”与“大同世界”,另一方面则赋予这种思想、感受和治理策略等虚事以现代科学或物质层面的基础,比如新式视觉技术和物理上的新发现物质“以太”。无论是幻灯还是以太,在康有为这里,都被理解为一种传播图像、进而传递情感、激发共情、形成情感共同体的媒介。将幻灯所形成的影像与一种古老而又新近的物理概念“以太”相联系,反映出康有为的一种独特的媒介世界观,即影像同以太、气、光、电、声波等一样,是填充于世界空间的特殊物质,其为物质而又不可见,只有当它获得一个“身体”(body)时才外化显现出来(比如在幕布上投影,在纸张上画出波动线条)。无论是气或是以太,还是影像,媒介将彼此隔断的身体相通,那些基于身体的痛感或快感得以沟通,共通感建立在身体与沟通身体的媒介基础上。情动媒介,不只传递信息和形象,还可以传递身体感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觉知”与“不忍”仿佛“吸摄”,是必然发生的。(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无物无电,无物无神。夫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有觉知则有吸摄。磁石犹然,何况于人。不忍者,吸摄之力也。)这样,康有为自己的大同世界与人类共通感信念奠立了一种带有科学性、物质性和观念性的媒介基石。
与康有为类似,谭嗣同的《仁学》(1897)和《以太说》(1898)也将19世纪中叶进入中国的“以太”与儒道的“气”结合起来,并连通光、电等物理学进展,将西方近代科学、基督教观念、儒家思想与佛学观念融汇一炉。在康有为、谭嗣同等中国第一代启蒙知识分子那里,“以太”成为一个特别可以缓解古今中西焦虑的概念。它既可以上升到比较抽象的观念层面又可落实到具体的物质基础,它成为一种沟通性的媒介,是社会共通和组织的物质基础,也是观念依据,能够传递遥远时空的思想、形象乃至身体感受,从而形成一种共通的社会与组织。

而这种相似的媒介世界观至1940年发表的一篇电影理论文章依然存在。包卫红在《“空中的波动艺术”:电影、以太和战时重庆的电影宣传理论》这篇文章中分析李丽水1941年发表于《电影纪事报》上的一篇文章《电影无限大》。李丽水认为电影连续不断的传播,以情感做基础,语言的极限将会被突破,最后,电影不仅会成为“全国性的大众语”,而且也会是“全世界性的大众语”。她关注于传播的力量和人类共通的情感,认为这是电影无限的能力。包卫红更是直言:“电影有一个巨大的身体(指它的活动领域)存在于茫茫的无极,……和茫茫无极的以太结合在一起”,“电影是一种以地球为出发点运动于无限领域中的艺术”——“空中的波动艺术”。 电影本身具有一种特殊的“能”,这种“能”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中放射、广播,以致超越任何界线。电影是一种即时传播和共时扩散的技术,一种情动媒介。
然而,这种媒介世界观、这种奇怪的认识与想象,需要被理解吗?康有为的、谭嗣同的、李丽水的,他们的经验、感受和判断有什么意义?唐老师认为,这种被遗忘的媒介世界观也许提供了一种理解图像作用的思路。康有为为什么说“觉”来自于“见”呢?看见是什么呢?为什么看见就可以感受了呢?由此可以思考米切尔在《图像何求》中提出的“图像的欲望”“图像是什么”“图像的作用如何产生”等核心问题。

点石斋画报,“影戏同观”
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关于“以太”这一媒介的想象,给人以启示性的思考。影像作为物的传播媒介实现了物的脱域与再域,投影将遥远事物的形象传递到眼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了一个“身体”重新具有“生命”。影像感人,因为它像“以太”一样可以实现身体之间的沟通,它是物的新身体,尽管以一种“缺席的在场”的方式出现,但“知觉的激情”是真实的。所以,“看见”是重要的,看见的是影像,同时也是再域化的身体,所以特别能够引发情动。这似乎可以解释图像的神秘力量,那种无法区分形象与实体的于今仍在的前现代图像崇拜,在图像作为媒介可以连通身体这种理解之下,可以得到一些解释。
但依旧存在的问题是康有为当时到底看的是什么,唐老师借以同时期的放映事件展示和想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整体观感、视觉经验是怎么样的。1885年11至12月,为助赈南方水灾,华人牧师颜永京在上海格致书院举行了其环球旅行的幻灯放映会。事后《点石斋画报》特请吴友如手绘成16幅版画以记此佳事,其中一幅《影戏同观》极为精细的呈现了幻灯放映的场景。且幻灯放映在近代中国口岸城市非常流行,《申报》等当时报刊多有报道,也呈现了当时的观影感受。它依靠机器、环境黑暗、影像硕大逼真、快速变换,让人有身处幻境之感,带来了与传统中国的戏曲、皮影戏等不同的新的视觉体验,建立在“身历其境”的真实感与“变化奇异”的震惊感基础上康有为形容为“憷然动矣”。

点石斋画报,“影戏同观” ,局部
在影戏、影灯、摄影等称谓词中,“影”成为表达某种视觉性的主要词根,幻灯和电影也被归属于影戏传统,表明中国观众对这两种影像性质的基本认识——它们是一种不同于有物质载体之图像的虚拟的视觉,即虚拟影像(virtual image)。幻灯与电影作为现代虚拟影像,其本质正在于实现了物、影像与媒介之间的脱域(deterritorialization)与再域(reterritorialization)。再现形象装置的发明,使得物在自己身上榨取出一个副本,将事物从特定空间中解放出来,最终物与影的关系形成了一种“缺席的在场” (the presence of an absence)。如同麦茨所言,电影是“想象的能指”,“它所包含的知觉活动是真实的(电影不是幻觉),但是那被知觉的并不是真实的物体,而是在一种新式镜子中所展现出来的它的影子、它的虚像、它的幽灵、它的复制品。”《味莼园观影戏记》的作者发出慨叹:“夫戏,幻也,影亦幻也,影戏而能以幻为真,技也,而进于道矣。” “以幻为真”概括出了早期观众对于电影之媒介特性及其所带来的视觉特性的感知,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这都是早期电影观众感官经验的核心。媒介是作用于人之感知的装置,“以幻为真”,并不是观众无法分辨真与幻,而是现代虚拟影像的媒介属性,观者的震惊与惊叹,恰恰是源于充分知觉于这种幻与真、缺席与在场的辩证关系,观众知道这是虚幻的影像,但却如此真正的相信、真实的感受、充分的知觉于此种幻影。

使用玻璃圆盘表现运动影像的幻灯机(1685)
图片来源:Anne Friedberg, The Virtual Window: 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 MIT Press, 2009, p. 69.
米切尔思考图像的欲望问题,回答长久以来困扰人类的图像的双重意识问题,即“图像不是活的却好像具有生命”,我们相信形象可以影响人。米切尔将之当作一个欲望的而不是意义的或权力的问题提出。这是客体的主体性,物的人性问题,图像展示物质的和虚拟的身体。所以米切尔复活了古典的对待图像的态度——把图像视为一种磁力和引力,图像的欲望是一种吸引的欲望。 这种媒介世界观,并不是随着人们启蒙、现代化就被扬弃,相反,它让我们正视图像的意义。通过像康有为、谭嗣同、李丽水这些已经被我们所遗忘了的一些关于媒介、关于图像的看法,重新再去造访他们,能够得到一些解释,也许能够构成一种通路,能够帮助我们去形成一种现代的图像理论对图像的看法,从而构成一种沟通。
注:以太(Luminiferous aether、aether 或 ether)或译为光以太,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一种物质,为五元素之一。19世纪的物理学家,认为它是一种曾被假想的电磁波的传播媒质。但后来的实验和理论表明,如果不假定“以太”的存在,很多物理现象可以有更为简单的解释。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观测证据表明“以太”存在,因此“以太”理论被科学界抛弃。

活动现场
第四位发言人是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动画艺术与影像美学研究所的孙松荣教授。孙老师以《记忆的影形力:论影像艺术的思性》为题,通过三组不同的影片组合之间的链接,将问题锁定在影像如何召唤记忆之上,进一步阐释媒介和记忆、媒介和历史之间的潜在关系,以及从电影和录像之间关于记忆的记录到数位摄影如何重新拟构记忆的历史系谱来审视当代艺术中西影像的思性。

孙松荣
法国导演裴黑克(Léonce Perret)1912年拍摄了一部默片《卡铎岩石的秘密》(Le Mystère des Roches de Kador)。它讲述了一位女子和男友在一次外出海边时被情敌暗算,男友在救她之后死去,女子因此陷入失忆。心理治疗师为治疗她的失忆拍摄了创伤事件并将重拍的影片放映给她观看。在影片中,投影的光线聚集在女子的脸上,她慢慢从模糊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当她看到男友死去时的特写时,放映立即结束,她面对着白色银幕高举双手往后走了几步之后随即晕倒在地。在她醒来之后恢复了记忆。这一片段为影像如何召唤记忆这个论题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可视化表现。如果,媒介和记忆之间会发生某种作用,它们并非处在一种直接对应和指涉的关系,而是某种影像在某个时刻以一种召唤记忆深处的事件形态,诱发并触动了观看者,让他从某种迷糊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如同戈达尔(Jean-Luc Godard)在《电影史》[Historie(s) du Cinéma,1988-98] 中的论述:“电影重新召唤了失忆的历史,甚至具有重新救赎历史的力量”。

Jean-Luc Godard《电影史》(1988-98)
电影《恋恋风尘》的一个片段与《卡铎岩石的秘密》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涉及观看者因影像内容触及创伤记忆而昏倒在地的情景。在电影片段中,男主角阿远坐在营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节目正在播放描绘矿工在地底采矿的画面,交替镜头转换为对电视机拍摄的固定镜头,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导演以蒙太奇的手法连续剪辑了几个与之相关的镜头:
1、男主角的父亲和工友们搭着矿车,迎向刺眼的光线;
2、母亲和小时候的阿远一边在隧道口奔跑,母亲一边大叫着父亲的名字;
3、营区内,看着电视的阿远突然晕眩倒地;
4、小时候的阿远和妹妹跑入坑洞口,喊着父亲;
5、工友们背着父亲在吊桥上;
6、阿远躺在床上被法师收惊,他慢慢醒来。

侯孝贤《恋恋风尘》(1986) 电影海报
这些交叉剪辑的内容揭示出阿远昏倒在地的原因,指明引发他创伤记忆的事件。电影《恋恋风尘》根据吴念真的生命经验改编而成,也成为侯孝贤关于身份认同、社会意识和历史变迁的杰作。而影片中电视节目播放的片段则是来自张照堂、杜可风、阮义忠等人于1980年制作的《映像之旅》纪录片第十二集《矿之旅》。纪录片对煤矿工人困苦危险的工作环境的真实记录,曾在当时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无形中也弥补了《恋恋风尘》无法直接再现被官方压制的现实主义内容和精神遗憾。
因此《矿之旅》除了意味着影像让男主角回忆起童年的创痛之外,还有更丰富的象征意义。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制作的这套关于纪录乡土的作品,以一种移植记忆赋予了“新电影”重回不可重回、想象不可想象,以及再现不可再现的历史现场。如同《卡铎岩石的秘密》中心理治疗师重拍意外事件一般,侯孝贤在《恋恋风尘》中重构了《矿之旅》纪录团队事先拍摄的历史现场(电影中纪录片的顺序和声音被重新配置了),让剧情片能在多年后重现矿工的历史样貌。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历史现场,男主角不可能因童年创伤而晕倒,《恋恋风尘》更不会有恢复历史记忆的可能。

张照堂、杜可风、阮义忠等《映像之旅》(1980)
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2010)和录像艺术《烟火(档案)》(Fireworks Archives,2014)则更进一步地呈现了被禁锢的历史暴力事件,以及对集体失忆的反抗和抵抗。《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讲述了患有肾脏病末期的布米叔叔拥有记忆前世今生和看见未来的超能力。其中的一个片段是布米叔叔失踪多年的儿子变成一只猴灵回来,给家人讲述自己如何被山林中的猴灵吸引,进而追随他们最终成为了他们的一员的事情。事实上,影片中的猴灵是一种形象的隐喻,是一种对不可说以及不可再现的形象的代替,即是共产主义的化身,影片实际所讨论的是1960年代至70年代泰国军政府剿共这一段至今也是禁忌的历史。
1965年8月7日,泰国政府军派兵到那布哈村(Nabua)屠杀信仰共产主义的农民,甚至进行了屠村行为;1976年10月5日发生了政法大学屠杀事件,为农工争取利益的学生被政府军视为共产主义者被封锁在校园内进行屠杀。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下,电影中布米叔叔的儿子进入山林,追随其他伙伴,则隐喻了在暴力事件中生还的学生躲藏山林以求生存的状态。录像艺术《烟火(档案)》则是象征性地模拟了军政府夜袭清剿时在夜空中释放信号弹,一旦发现有人现身立即开枪扫射的状态,暗夜中不停闪烁的烟火是枪火的转换,也是显影暴力历史的光影。回到电影《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中能记忆过去与未来的能力,实则是导演赋予电影召唤记忆的力量,并试图反抗失忆和展开抵抗。

“法政大学屠杀”( Neal Ulevich,1976年10月6號)
最后一部影片是台湾艺术家高重黎称作“幻灯简报电影”(运用静态图像制造出电影的幻觉,并结合艺术家旁白的创作形态),挪用了许多数据影片和档案的系列作品《延迟的刺点:堤2》(2015)。艺术家引述了日本导演木下惠介1954年拍摄的反战影片《二十四只眼睛》和法国导演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经典黑白短片《堤》(La Jetée,1962)。从片名到引述的画面,高重黎一方面是对克里斯·马克的致敬;另一方面则是试图重新建构穿越时间、展开回忆的命题,借以批判日本殖民主义、政治、视觉现代性等问题。例如,影片中的一个画面将《堤》和《二十四只眼睛》的影像并置,某种联系被建立起来。画面左侧《堤》中沉睡的男主双眼蒙上进入来未来的旅程,终于知道自童年起便纠缠着他的一幅影像原来就是自己的死亡;左侧《二十四只眼睛》的闭着双眼的失明士兵同样被童年的影像所纠缠。

高重黎《延迟的刺点:堤2》(2015)
三组作品,从台湾新电影和纪录片、泰国剧情片和录像艺术到高重黎的“幻灯简报电影”,共同的特点都在藉由各自媒介特征和影像技术,以及某种潜在的或者直接的互文关系来表现记忆的命题。《恋恋风尘》和《映像之旅》之间关系的讨论让跨类别的作品被联系起来,并进一步扩大现实主义的向度;《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和《烟火(档案)》则试图解放禁忌的记忆,拒绝集体失忆,显示出当代政治影像的企图;高重黎的《延迟的刺点:堤2》在重构经典的基础上,把可见和不可见、可预示和不可预示的历史暴力交织在一起。几位影像创作者都在引诱着创伤影像的力量,试图体现出某种"可思性”;而这些影像艺术对光的造型,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辩证和重新创造,呈现出一定的抵制/反抗的力量,即“影形力”的展现。媒介和记忆,或者说影像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实则是对未来(世界、人民乃至影像)所展开的一种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抵抗、悬置和转化。

高重黎《延迟的刺点:堤2》(2015)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中山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的冯原教授。冯老师以《文化漂变与视觉再造——20世纪的现代转型:绘画、建筑与声乐》为题,藉由生物学上的“漂变”为关键词,通过考察、分析20世纪中国的绘画、建筑、声乐的发展类型、路径,展现视觉文化的再造过程。

冯原
“漂变”即随机的遗传漂变,原意是指基因在传递/遗传过程中偶然发生的变异,因而造成下一代的基因突变的生物现象。此外,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过“迷因”(meme)假说。把生物学基因漂变的概念发展到人类社会的文化变异之上。 沿着这一从生物学转向文化变异方向的学说,冯老师提出“文化漂变”的概念,籍此来考查20世纪中国在文化、艺术等领域所发生的文化转型的前因后果。
文化虽然是一个最为复杂的现代概念,但大体上依旧可分成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所有的人类生产活动都是文化(非自觉的);二是自觉的文化主体创造的观念上的文化。进一步说,文化的发展会有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纵向是传统的累积;横向是文化间的传播与碰撞。其中,纵向文化是第一性的——在人类生产的纵向积累中,文化在特定的地域独立发展,并构成各地的文化传统。随着人类的扩张与交流,文化开始进行跨地域的横向传播,因此不同的文化传统发生碰撞,激发了各种变化与再造。
因此,不必追溯人类文化的纵向起源,仅仅把目光放在纵向与横向共同发生的时期,以现代中国的进程来看,这一时期就是近世三百年左右。18世纪前后,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来到了东方,为近世中国文化的横向漂变创造了前提。文化漂变并非独立发生,而是根植于经济贸易活动之中,与历史的脉络一致。冯老师将文化漂变划分成局部早期与全面自觉两个阶段,也对应着政治经济上的“被动现代化”与“主动现代化”两个阶段。

广州 十三行 景象
早期文化漂变实际上是经济贸易的副产品,是一种局部和非自觉的现象。自1750年代起,康熙定广州一口通商,由十三行垄断中西贸易,这一政治性举措为早期的文化漂变创造了前提条件,从18世纪中到19世纪初,广州成为“文化漂变”的发生地。一方面,西方商人把文化的载体——建筑、绘画等带进广州;另一方面,位于十三行后面的同文街上的上千名画工绘制了各式“纪念品”,洋商们则带着“外销画”回到家乡,西方人借此发现了另一种“异国情调”。
关于早期局部的文化漂变,其典型案例是辗转从印度来到澳门,以画为生的英国人钱纳利,和跟随钱纳利学习油画的广州人关乔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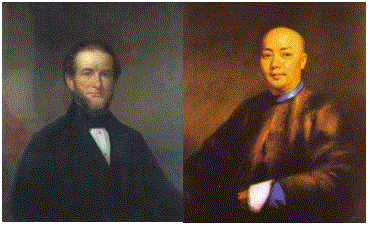
钱纳利 (左) 关乔昌(右)
从技术来看,关乔昌基本上掌握了西方古典油画的技艺,关的“庭呱画室”也生意兴隆。但关乔昌没有文化上的自觉意识,因为中华帝国还没有为接纳关乔昌的文化漂变做好准备。所以,18世纪末的“钱—关漂变”仅是一次局部的横向漂变,没有更多的文化影响。其基本模型如下:文化类型A(英国绘画/西方艺术)——经由使者B(钱纳利)传给来自——文化类型C(中国文化)的——文化接受者D(关乔昌)。但是B+D模式并不涉及到A与C的关系,所以局部漂变就是一种没有自觉为文化的文化。其次,文化上的纵向漂变表达了同种文化中的演进与代际变异。所有的绘画史(艺术史)的书写都是纵向的,因此纵向文化(英国)的出走者钱纳利成为了横向的(来到中国)文化使者,却在西方绘画史上没有位置。
以18—19世纪的局部性文化漂变为参照,不难发现,发生于20世纪的文化漂变,其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文化的自觉性。20世纪的文化有一个普遍性的两分结构——中西对照。这被建构的结构造就了20世纪文化漂变的重要表征。文化主体的自觉性,首先表现在中西框架中对于“中”的再造,对于“中”的再造反过来重新构建了中与“西”的关系。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用两个自觉来表示——自觉的留洋与自觉的重构民族。其中,自觉的留洋塑造了20世纪文化漂变的自觉性。
与庚款留洋不同,20世纪的留洋,不论是官费还自费,到西洋(东洋)都是文化主体自觉、主动的去另一种文化学习和获取他者文化的技术和经验。关于第一种自觉,所有的留洋都一样;关于第二种自觉——重构民族,就要取决于留洋之后的选择,到底是返回母国,用习得的技术和经验为母国的文化重建服务,还是继续留在西方。

国立杭州艺专的部分西画老师与国画老师
两种自觉性的相加就会产生出不同的变体。首先,20世纪早期的西方文化也处于从古典向现代转变的大时代,所以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因选择学习西方古典或现代而分化为两种类型;其次,返回母国后,因重构民族的需要所造成的选择又提供了变数。如此,则产生四个基本问题:1、去哪里学习?2、去学什么?3、回国后如何作用于母国文化?4、如果不回国如何作用于他者文化?对着四个问题的回答便可划分出不同的变体类型。然而,所有的变体都出自于去他者文化留学,在文化自觉时代的文化漂变,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他者文化,而是取决于自觉者主体与母国文化的共同效应,这种效应衍生出文化漂变的典型变体(模式)。
第一种变体(模式)以徐悲鸿(美术)、梁思成(建筑)、冼星海(音乐)等人为代表,可以简述为:去西方留学,学习西方古典文化,回到母国,并按母国的需求再造中国文化。从文化漂变的概念出发,这一变体可称之为“母国文化中的转型自我”。这也是20世纪再造中国文化的主要类型。典型如徐悲鸿先生,他在法国学习古典主义油画回国后以西方油画技法来创作中国民族油画以提升母体文化。

徐悲鸿(左) 梁思成(中) 冼星海(右)
第二种变体可以简述为:到西方留学,学习西方现代文化,回到母国,并按他者文化的需求再造中国文化,这一类型可称之为“母国文化中的转型他者”。其代表人物为林风眠,林氏回国后的现代主义倾向,在特定历史中被认为非政治正确的,所以这一效应使他不得不成为母国文化的“转型他者”。
第三种变体可以简述为:去西方留学,学习西方现代文化,留在西方,并按他者文化的需求成为“他者文化中的转型他者”,这一变体以赵无极为典型。赵选择留在了法国,因此他有机会成为了法国抽象绘画的东方代表。设想一下,若是赵无极如林风眠一样在同时期返回国内,以当时中国社会和艺术环境的双重压力,他能否开创他的抽象主义呢?所以,赵无极成为第三种变体的前提是选择留在法国。但也有趣的是,留在法国并按西方潮流来进行抽象艺术创作的赵无极,依旧未能进入法国文化的内核,实际上,他被当成了抽象艺术的“东方代表”,不过他所代表的那个“东方”却不能在母体文化中发生,正因为如此,赵无极才是“他者文化中的转型他者”。

林风眠作品
三种典型的变体告诉我们,文化漂变是双向发生的,一方面,来自汉文化语境的主体可以到西方学习,这一文化漂变的后果可在视觉文化上称为“西化”;另一方面,当文化主体回到自己母国的语境中,又可将在西方文化学到的观念转化为本国需求的内容,这一后果又可称为“汉化”。两者其实是一个手掌的正反两面,如何定义则取决于文化主体所处的位置与转型的强度。
总的来说,冯老师的研究提供了20世纪文化漂变的两个基本模式:B+D+A模式(西化)与B+D+C模式(汉化)。将文化漂变的内核(观念)与表观(风格)综合观察,冯老师认为视觉的“汉化”要比“西化”的强度更大,这一倾向显示了20世纪的文化转型中民族与国家的需求对于个人的文化选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后,冯老师用“文化漂变”的理论模型,结合了中山大学的一百年的校园建筑为例,阐释了20世纪新民族国家如何构建民族—新古典建筑这一历史命题。
中山大学的校徽上有一个建筑——钟楼,因楼顶设立四面时钟而得名。其所在地曾经一直是清朝的广东贡院,1907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东贡院的旧址上创建了两广速成师范馆,后改为两广优级师范学堂。从贡院到学堂是向西方教育体制的学习与模仿,因此在建筑表观层面的表达与内核的变化相适应——脱掉旧制服换上新制服,以“新式”的西方建筑样式来建造(当然,这里的新式其实是对西方古典样式的模仿)。

两广优级师范学堂
但到了1925年之后,问题发生重要改变。孙中山先生去世并被尊为“国父”(广东大学也因此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当时的国民政府迫切地需要创造一个跟民族自尊心相匹配的一种建筑表观,这一愿望决定了建筑样式不能是模仿西方,也不能照搬古制,两者相加就催生了文化漂变的动力,一种融合中西的建筑样式应运而生。它的目标是要冠以民族的符号和现代—西方的内核,从而获得一种具有民族自尊感的民族—新古典建筑,这种建筑习惯上一直被称为折中主义建筑。

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
所以,用文化漂变的B+D+C的模型(汉化模式)解释由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它不仅是民族—新古典建筑的奠基之作;也是延续了几乎整个20世纪的民族式建筑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回到中山大学的校园建筑群,建于1930年代初的国立中山大学校园完全采纳了折中主义式的民族—新古典建筑样式。直到今天,这一发生在1930年代的文化漂变不仅建立了中山大学的典型符号风格,它还决定了21世纪中山大学建设新校园的风格选择。2017年以来,中山大学正在建设的深圳校区,其所选择的校园建筑风格依然是以1930年代奠定的风格为来源的;而且在新的条件下文化漂变仍然在继续发生。
最后冯老师还从声音—歌声角度简略地讨论了文化漂变框架内的地域、民族、政治表征的问题,并区分出“外向漂变”与“内向漂变”的向度,他以两首诞生于不同时代和文化环境中的著名歌曲《我的祖国》《情人的眼泪》为例,以两首歌曲的词与曲的配合,来说明“内向漂变”的特殊模式,并认为现代歌声既可以是民族融合的媒介,也可是民族分裂的边界。
活动现场
OCAT研究中心
OCAT研究中心(OCAT Institute)是OCT当代艺术中心(OCT Contemporary Art Terminal,简称“OCAT”)在北京设立的非盈利性、独立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是OCAT馆群的有机部分。它以研究出版、图书文献和展览交流为主要功能,研究对象包括古代艺术和自上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主义的视觉艺术实践,研究范围包括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流派、艺术展览、艺术思潮、艺术机构、艺术著述及其它艺术生态,它还兼顾与这一研究相关的图书馆、档案库的建设和海外学术交流,它还是OCAT馆群在北京的展示平台。
OCAT研究中心旨在建立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历史研究”的价值模式、学术机制和独特方法,它的学术主旨是:知识、思想与研究,它提倡当代艺术史与人类精神史、观念史、思想史和视觉文化史整体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和开放的学术研究精神,关注经典艺术史著作的翻译出版与现当代艺术史与古典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贯通。
欢迎转发我们的信息至您的朋友圈
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