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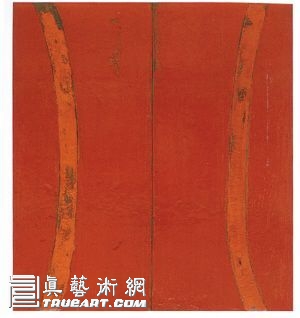
图:苏笑柏作品
手记:有幸请到1987年入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留学的苏笑柏老师谈柏林墙与德国艺术的话题——其实“德国艺术”只不过是一件冠冕堂皇的外衣,但必须穿上它——原定一个简短的十分钟访问,但是苏老师讲了太多精彩的东西,令人难以舍弃。因此在节选四分之一刊登于杂志之后,我将全部的谈话内容简单整理,赶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今天呈现于私人化的博客,与有同样思考或者疑问的朋友共享。
另,刚上市的《艺术世界》杂志11月刊专题就是“柏林墙”,当然是穿着上文提到的这件冠冕堂皇的外衣。
正文如下:
偶然开始的德国艺旅
我去德国非常偶然。80年代国内的艺术家都想出去,在艺术上的追求到了一定程度总想看看世界上是怎么回事,尤其我们学油画的,想去看看这个艺术的本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是想去美国,但是偶然得到了德国政府的奖学金,钱很少,但是时间很长,资助我四年。两个原因让我最终选择了德国,一是我当时英语、德语完全都不会,到美国去会有很高的奖学金,但是只待一年,我一年时间把语言学完就得流落到社会上去。到德国则有四年,我一年时间把语言关过了,还可以继续学习。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德语比英文好学,德语看到就能说出来,英语有音标,每个音标的发音不一样,还有一些特殊的例子,我是没有任何声音记忆的人,我只有视觉记忆,看到这个句子我马上能读出来。而且德语越学越容易,怎么写怎么发音,中文写的和读音没有任何关系,英文是有关系但不是那么紧密。我看到一句德语我就能读出来,别人就知道我要什么材料。我读一句英文句子,读完了人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我去德国之前对他们一无所知,但是德国的哲学、文学那些高端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我觉得中国的1984年到1985年,即使不能算作“复兴”,也算是一种启蒙,是一种新的文化的起因——经过’85的我们全都知道这些东西。
出国前以为到了美国是到了西方,到德国也是到了西方。后来才知道到美国和到德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德国人也不认同美国艺术,美国人也不太认同欧洲的这些。我们亚洲、欧洲和美国,我们常常把欧洲和美国统称为西方,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文化形态也不一样。我在德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当然觉得学艺术是应该去德国。比如我到意大利就是看看古迹,就像我们今天去看故宫,到法国则看到的都是明日黄花,看他们印象派后期那些辉煌的东西。到德国就感觉跳过了美国。因为西方艺术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就到了法国,然后到了英美,现在世界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特点,但是德国包括荷兰比利时英国,法国算不在这个系统里面,他们的当代艺术非常强势。
用“理性”和“爆发性”两个词来表述德国艺术的特定是非常准确的。他们非常有理性,任何事情都要想清楚,要说个头头是道,还要产生工具,比如理论方面辅助的东西,一个大的框架。但同时又很有爆发力,不是软弱的,不是浪漫的,甚至不是抒情的,是一种很深厚的东西,有积淀。要么出不来,平平无奇,但一旦出来就是另一个面貌。有人说德国艺术是深沉的,但我觉得是浪漫派也可以很深沉,不同点在于德国艺术爆发的力度非常大。我所读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我觉得是德国最好的艺术学院,因为他们的老师是最好的。老师在那儿,学生就有了一个方向,老师是我的对立面,我要模仿老师,或者要超越他、发展他。学校里没有哪个学生的作品像自己的老师,像自己老师的学生非常没有出息,老师就有这样的包容性。我非常庆幸在这个学校里待了五年,拿着国家的一点奖学金不用出去打工,没有浪费时间,每天都待在学校里画画,跟那些老师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随柏林墙消失的东德艺术
1989年前后,德国社会空气的变化还是挺明显的。之前艺术家和政治家对这件事并没有预见性,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出现了这场爆发。当年年初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德国的总理、外长和很多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柏林墙有可能消失,但是两国统一还需要很漫长的道路——柏林墙只是城市的一座墙,不是德国的边界,柏林是一个孤岛,遥远地在东德的境内。现在国内有些很活跃的艺术家当时都生活在柏林,他们对现场的情况非常了解,我一直生活在德国的内地,这是两个概念。柏林这座孤岛靠近波兰,里面有一半属于西德,物资需要西德空投过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两个完整的国家,西德到柏林有三条空中通道和三条封闭的高速公路。
两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很少,但是私下里交头接耳,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四十年的分离却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我了解了他们的媒体语言之后,就非常惊讶于东德媒体的腔调和说话的方式,包括他们的小说、诗歌、绘画等艺术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东德的东西有很多深沉的人文关怀,对专制体制的抗争和对社会公平、民主的向往。两德统一之后,之前这种在慢慢表现的常态突然之间全都喷发出来,提前消耗掉了。大家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东德这边,因为他们是“潦倒的兄弟”,但是拥有很厉害的艺术家。但是这种爆发不持久,好像一两年就把话都说完了。也可以这么说,东西德的艺术家其实非常期待与对面的同胞、同行交流,这种期待本来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在释放,但是一夜之间铁幕没有了,这种束缚解开了,好像一朵花一样,哗一下就开完了。
但我觉得顶多不过两年,东德艺术家特殊的表现力、焦虑感和人文关怀就都没有了,而这本来是东德艺术非常明确的一个特质——西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自由的东西,按照艺术自己发展的脉络在走,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大家基本上在同一个框架里。而东德不是这样,他们始终在挣扎,寻找一种突破。当时两德德交往并不畅通,很多人逃到西德就不回去了。这样逃过来很多很优秀的艺术家,比如我们现在熟悉的里希特,格哈特、彭克。留在东德的艺术家则一直在追求一种认同感,他们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有很多很多的波普艺术。这方面西德都没有,他们更多的是在艺术流派延续之下一种总体的东西。两德统一后这种同化的发展非常迅速,因为两边不同的艺术家,从表面上来说已经彻底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同样的信息,国家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艺术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了,东德艺术的消失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事。
^^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前,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没有想过这件事真的发生,即使有也是乌托邦的理想主义,所以真的发生的时候,甚至可能有些失落。我作为待在西德的艺术家,对东德艺术家非常好奇,他们的语言让我觉得很熟悉,而且绘画的功底很扎实,虽然已经不是现实主义的东西,但是面貌的基础是我非常非常熟悉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和情感甚至表现方法都能找到共同之处。但是我生活在西德,接受着另外一种教育,我也有意识地在我的艺术生涯里呈现这种全新的东西,所以对东德的艺术就是远远地看一看,有一种很会意、很同情的、很了解的感觉。
东德艺术有自己的爆发点,比如布莱希特。他有他的意识流,是很典型的东德艺术家、文学家,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文学性表现在他的社会观和世界观上。同样的,我们作为生活在西德的艺术家,对那些东德艺术家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没有感觉到自己在领先艺术潮流,什么时候感觉到呢?是他们到西德以后,就不走了——比如里希特,他就留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重新当学生、受教育,他作品的深刻的社会性和当代新的艺术潮流结合才成就了他这样的艺术大师。
东德艺术也有他的流派,比如莱比锡画派,21世纪初的时候也有。但是在两德统一之前他是非常微弱的,没有呈现一种清晰、完整的状况。我感觉小说、文学、音乐、美术里面意识形态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比我们当时还要多。但是他们同一种文化,同一种语言,多多少少享有同样的信息源,还是与时俱进的,只是表现出来的形态不一样而已。
德国——整个民族的诚实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当统一的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接触的那些大知识分子,知识阶层,他们的反应反而非常冷静——事情到了自己不能把握的时候,未来会怎样,每个人都在考虑,而不是欢乐。欢乐的人也有,比如一些刚从东德过来的人,但是欢乐的时间非常短。很多人说中华民族和日耳曼民族是很了不起的两个民族,这话也对,但是日耳曼民族在世界史上起到了一些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他们跟我们的民族性是不一样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没有过照射别人,而是始终被照射的一个民族,日耳曼民族则不仅被照射,自己也照射。他们的内心非常高傲,但是产生这种高傲的根基是一种谦虚的、愿意向世界开放的、善良的、严谨的、主持公道的基础。他们觉得,这些美德我都具有了,才会有一种潜意识的高傲,不是清高,而是一种贴切的社会化、人文性的普适的价值观。尤其在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因为自己经历过所有的专制和不民主而不愿回到那个时代。他们反思希特勒,反思希特勒对别的国家的侵略,反省为什么当时整个德国都支持希特勒。
一个民族的自大不是说我这个民族很辉煌,我就自强了。德国人有很多很多怪毛病,但是他们对普适价值、对社会的判断水平非常非常高,他们对非人性化的东西,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包括环境的,包括我们接触的一支钢笔一张纸,一种对自己造成束缚的东西,他们都在不断改进、不断抗争、不断向前发展。
而且德国人特别容易反省自己。德国的国家电视台比如一台、二台类似“新闻联播”的节目之前都有一个节目,就是播放二十年前的今天我们的新闻联播播了些什么。我觉得这真了不起,大家都说德国对二战的反省非常深刻,而日本人不反省,我不知道日本人是不是不反省因为我没有去过日本,我也不知道日本人会不会播出我二十年前的新闻联播播放了什么。二十年前的东西有时是多么伟大的事件,但有时又多么可笑。二十年前德国的主题的媒体、政治家他们是怎么想的,老百姓怎么做的,文学家音乐家当时有哪些活动是达到了公认的高峰的,都被电视台诚实地播放出来。
我1987年的时候去德国,他们在放的就是1967年的新闻,不是一个回顾,不是选择性地去隐瞒一些东西,不像大多数人只公开有些东西,而不光彩的东西我全都隐瞒——为什么不能公开,为什么要隐瞒?我真不明白。就像我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要隐瞒,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德国人在二战中再可恶,但这一点他们做得多么多么好,你想想看知识分子会怎么想,老百姓怎么想,他们对政治家的期待是什么样的?谁愿意绑在一个历史的弱者身上?我现在做的事要对后代负责,对世界负责。短视的人称不上思想家,能想这些的才是优秀的艺术家、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把事实真正地还原到整个民族,每个人。除了电视要反映二十年前的新闻,文学也要反映这二十年发生了什么,政治也要谈论二十年前。还有一个电视台播的是二十五年前的新闻,一个电视台播十五年前的新闻,但是德国的大多数电视台都播的是二十年前,比较严肃的电视台都在播。我不知道日本播不播,他们播的话肯定就把南京大屠杀播出来了。他没有电视也有联播,有声音。我们播不播?为什么不播出当时的一些实物,让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发展?现在不是说要改革吗?不是中央领导说步子要大吗?我们都愿意步子更大一点,中国这么勤劳的民族,改革的步子更大一点,生活不是会过得更好一点吗?一样的道理。在这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真的应该考虑这样的事情,不仅仅政治家需要去考虑。
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天天看到这样的新闻。我自己感觉到我非常惭愧,我不能要求别人、要求我的国家怎么做,至少我可以要求自己怎么做,去想我这二十年要怎么做才是负责。我刚到的时候1987年,看到这个节目没有任何反应,因为1967年我在中国,到北京去接受毛主席检阅。第二年播到1968年,1968年的德国崇拜毛zd像崇拜神一样,觉得毛zd是真正伟大的改革家,是真正反官僚主义的伟大的改革者,他让中国人真的革命了,消灭阶级了。这里面当然有些误解,但是毛zd是个形象,胡志明也是个形象。我当时看了之后没有这种感觉,而且我当时德语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一直跟踪这个节目,突然有一天,到2007年的一天我看到1987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我脑子里“轰”的一声就开朗了——1987年这件事事刚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在议论,我当时德语不是很好,只是朦朦胧胧知道大家在议论,具体在讲什么不知道。二十年后,电视里这个新闻突然之间把我带回去了。我会一直跟踪这个节目下去,让我一直年轻二十岁,让我知道当时我所经历的社会和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