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尔维斯特:您是否有过一种想要从事抽象画的渴望?
弗兰西斯•培根[1]:我最初基于“基督受难”母题画出了那幅三联画。当时,我确实有一种想要进行抽象艺术的渴望。我的“基督受难”三联画,受到了毕加索20世纪末作品的影响。
西尔维斯特:那幅三联画之后,您开始用一种更加具象的方式去画:这种具象绘画的方式是源于一种满怀信心的渴望,还是出于当时您感到无法再继续下去的某种感觉?
培根:嗯,我曾在1946年画过一幅画。它像一个肉铺店一样,忽然意外跃出在我眼前。那时我正想画一只降落在田间的鸟。画的时候,也许早已预设了惯有的三联画的方式,然而就那么猛然间,我所画出的那些线条却暗示出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就这样,沿着那启示的踪迹,这幅画诞生了。而我并非刻意如此去画,亦从未用此种方式设想过绘画。它就类似一个个层出不穷,持续不断的偶然,一次次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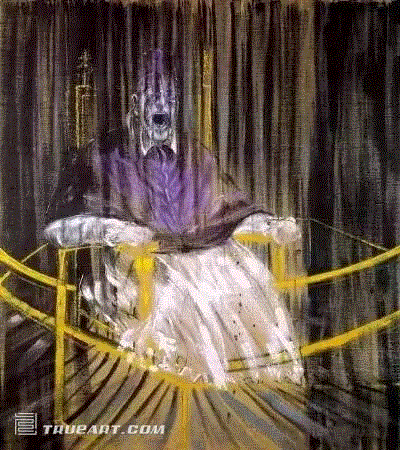
西尔维斯特:是那只降落的鸟启示出了“雨伞”,还是别的什么?
培根:是猛然间,有一个感觉的场域完全敞开了,紧接着我就画了这些东西,逐渐地画出了它们。所以我想并不是那只鸟启发了雨伞(的形象),而是(感觉)启示出所有的形象。当时我画得非常快,差不多只用了三四天的时间。
西尔维斯特:工作的时候,这种形象的转变是否经常发生呢?
培根:确实经常发生。我总是希望这种启示能够更加频繁,更加积极地到来。现在我想要创作更为独特的东西,纵然这发自于一种荒谬至极的例证欲求。我想画的那种尤为奇特的东西,譬如肖像画,它是关于人的肖像,但是当您想要看清它时,您将完全不知道——或者相当难以辨别那种“形象”究竟是如何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它如此令人困惑。因为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是一次意外。比如说,有一天我想画一个人的脑袋,当您仔细辨认它时,那些所谓的眼窝、鼻子、嘴巴,仅仅成了与之无关的形式罢了。但是从一个轮廓到另一个轮廓的变形,同样也能产生出与模特之间的相似性。接着,我就会停下来思考一会儿,觉得我应该更加贴近我想要的东西。然后,第二天,我试着继续下去,使它更加深刻,更加接近于我想要的东西,从而完全丢掉了“形象”。这个“形象”是一种介于所谓“具象绘画”与“抽象主义”之间,危险的摸索。它从抽象主义而来,却又与之无关。它是一种尝试,试图把具象的东西提升至神经系统的更加激烈,更加深刻的尝试。
西尔维斯特:在创作“基督受难”三联画时,您是三张画布同时进行,还是分别单独创作的?
培根:我先是一张一张逐渐画出来。等完成后,我就在画室里一边踱步穿梭,一边在三张画布上修修补补。我用了大约两周的时间来画这幅画,那时我沉溺于酗酒的糟糕情绪里,常常是在惊人的宿醉与昏沉的笼罩下画画。有时,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甚至,这是仅有的一幅在我酗酒时还能创作出来的作品。我想,也许恰恰是酗酒使我多了一点自由吧。
西尔维斯特:这种酗酒的绘画经验,没有在其它的作品再继续使用吗?
培根:没有。但是,我耗费了巨大的精力来使自己变得更加自由。我的意思是,(这种自由)既不借助于吸毒,也不借助于酗酒。
[page]

西尔维斯特:是否能借助于极度疲惫呢?
培根:极度疲惫?可能吧,也许下次试试看。
西尔维斯特:一种为了达到无意志的意志?
培根:完全正确!正是这种“无意志的意志”使一个人完全自由。意志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词语,也许到最后您会称它为“绝望”。一种真正源于对做此事完全不可能的绝对的感觉。所以,也许我已做过所有的事情。恰恰是通过这所有的事情,一个艺术家就会看到发生了什么。
西尔维斯特:假如从未有人来过这里,也没有谁离开过。我把这视为没有什么东西,远离过画室。那么您当继续,直到把它们完全毁灭为止。
培根:可能是这样。
西尔维斯特:您能谈谈是什么促使您创作三联画的吗?
培根:我特别容易被有关屠宰场与肉的摄影作品感动。对我而言,这些完全符合“基督受难”的整个事件。摄影作品本身已经非常卓越,动物屠宰前的死亡气息弥漫着整个画面,这是您无法想象的。那些动物,其实早已意识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它们千方百计想要逃避。所有这些都通过摄影显现出来了。我想,摄影作品所预示的东西与“基督受难”已极为接近。我知道对于宗教人士,对于基督徒而言,“基督受难”有着截然不同的寓意。但作为一个无宗教信仰者,“基督受难”仅仅意味着一种人类行为的表演,一种行为交流的方式。
西尔维斯特:但是事实上,除了“基督受难”外,您确实还画了一些与宗教有关的作品。您过去30年不断返回的绘画主题——教皇。您为什么总是持续不断地去画那些与宗教有关的作品?
培根:“教皇”作品与宗教无关。仅仅出自对委拉斯凯兹[2]笔下教皇的迷恋,因诺森特教皇X。
西尔维斯特:为什么您单单选择了教皇?
培根:这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肖像画之一。
西尔维斯特:有没有与委拉斯凯兹同样伟大的肖像画会令您痴迷?您确定在您的“教皇”作品里没有什么独特的东西吗?
培根:我想是它瑰丽的色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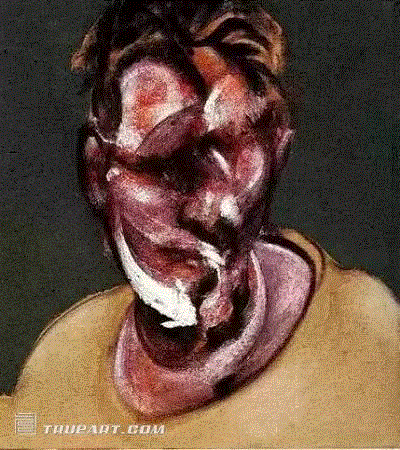
西尔维斯特:但是您基于摄影已经创作了两幅现代教皇油画,加上XII,三幅,好像您对委拉斯凯兹的兴趣已经转移到对教皇本身——对英雄人物的迷恋了。
培根:的确如此。教皇是独特的。作为“教皇”,他被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因此,就像某些伟大的悲剧,他似乎总是被聚光灯笼罩着,类似一个舞台形象,他面对世界,展示他的崇高。
西尔维斯特:既然存在同样的独特性,那么在基督形象里,难道真的没有再寻求一种悲剧英雄式的独特性观念和特殊处境吗?譬如,悲剧英雄注定是卓越的天才。
培根:我从未这样想过,也许可能是吧。就像在悬崖边上,他步履维艰,摸索前行。委拉斯凯兹如此接近我们所说的“例证”,启示给我们某种高深莫测的东西,这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情!这也促使他成为一个奇谲瑰丽、神秘莫测的画家。当一个人凝视这幅画,他就会笃信委拉斯凯兹确实雕刻下了彼时庭间审判的时光。从而看到,那些事件是怎样正在发生着。 当然,自委拉斯凯兹之后,发生了太多事情,有太多原因导致了整个艺术状况变得愈加复杂难懂。其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就是为什么摄影术彻底改变了具象绘画,完全颠覆了它。
西尔维斯特:以一种积极方式,还是消极的方式?
培根:我觉得是用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我想委拉斯凯兹相信他正在记录彼时的庭间审判,记录彼时的某个人。然而今天,一个真正优秀的艺术家却会被逼无奈去戏拟同一场景。因为他知道电影同样能记录这些,所以(绘画)行为的记录功能就被别的东西(摄影)替代了,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形象把感觉彻底打开。我想,即便委拉斯凯兹、伦布兰特都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去画画,不管他们的生活态度如何,他们仍旧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被某种宗教的可能性束缚着。现在可以说,它完全被消解掉了。如今人们完全可以把意义加诸到任何事情上去,譬如出于一种习以为常的自我欺哄;譬如靠吞食大量药物,拖延尘世的生命。你看,所有的艺术都变成了混乱的游戏,你或许会说,艺术从来就像游戏,可是现在它却彻底沦为一场游戏。什么都在变化,对艺术家而言,令他迷恋的东西,唯有日益步履维艰的艺术境况了。艺术家要将游戏进行到底。
西尔维斯特:您能谈谈为何摄影如此令你着迷吗?
培根:嗯,我想,一个人所散发出的感觉总会被摄影捕获到,在电影那里则有99%的几率。摄影比抽象绘画、具象绘画更有意思。我常常沉醉其中,不可自拔。
西尔维斯特:在您作品中有一种非常独特而明显的内部结构,就是基督受难意象与屠宰场意象的紧密交叠。 “肉”,在您这里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吧。
培根:确实是这样。假如你路过那些不可思议的屠宰场和肉铺店,就像沿着一排排死亡的走廊,看到肉、鱼、鸟,所有的一切全部躺在那里,奔向死亡。那种色彩,极为瑰丽的肉的色彩,总是令画家们过目难忘。
西尔维斯特:肉与基督受难的联系似乎是以两种方式发生的:一方面,通过肉的场面的直接刻画;另一方面,通过把基督受难的形象转化为悬挂的骨架残骸。
培根:的确,我们是肉,也是潜在的骨架残骸。每一次我走进屠宰场,看到悬挂在那里的是动物,却不是我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莫大的惊奇。但是使用“肉”的独特方式,可能就像有人会用到脊柱骨一样。因为我们总会不断看到X光片上人类身体的形象,这确实改变了我们看待身体的方式。你一定在国家美术馆里见到过德加[3]漂亮的彩粉画,一个女人在擦拭她的背部。你会发现,那极为绝妙的脊椎骨,它几乎凝聚了所有的肌肤。它是如此紧凑,扭动起来,使你立刻意识到身体其余部位的缺陷,而不再想知道画家是否还沿着脊椎骨向上,画出了她的脖颈。画家沉醉在那里,好像脊椎骨就要从肉里翘出来了。不管德加是否有意为之,这让它成为一幅颇负盛名的绘画作品。你会猛然感到,他画的脊椎骨带着血和肉,一起遮盖了骨头。在我看来,所有的这些,肯定都受到了X光片的影响。
[page]

西尔维斯特:从您的作品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肉,最令你着魔的是它的形式与色彩。然而“基督受难”作品,显然因有了惊悚色彩而备受责难。
培根:是的。他们确实总是强调它惊悚丑陋的一面。但是我自己从未感到这一点,也从未刻意为之。
西尔维斯特:那张开的嘴巴,就是他们指的“尖叫”吗?
培根:不是所有人,绝大部分。你是知道嘴巴如何改变形状的:嘴巴的运动、嘴巴与牙齿的形状,我总会因此深受感动。现在人们会说里面有各种性暗示。以前我会对嘴巴、牙齿的精确外观深深着迷,现在也许失去了那种迷恋。但在从前的某个时刻,它确实是一种非常有力的东西。你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嘴巴的诱惑与颜色,而我总是在一种感觉的期盼中去画嘴巴,就像莫奈画日出时一样。
西尔维斯特:那个教皇是爸爸吗?
培根:我真的从未那样想过,但是我也不知道,想要知道是什么构成了这些困扰非常困难。 我父亲的思想很保守。他是一个从未开发过智慧,却很有智慧的人。你知道的,他是一个驯马师,常常与人争吵。他特别固执己见,与所有人都要争吵,一个朋友都没有。当然也不能与他的孩子好好相处。
西尔维斯特:那您对他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
培根:嗯,我不喜欢他。但我年轻时曾被他的性吸引过。当我初次意识到这件事,几乎不知道那是性的原因。只是后来,在和马厩里的马倌与男人们厮混时,我才知道对父亲有一种性的情感。
西尔维斯特:所以,也许对委拉斯凯兹教皇的迷恋有一种强烈的个人意义?
培根:嗯,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作品之一。我想,作为一个画家,对它深深痴迷,一点也不奇怪。我想有许多艺术家都会承认,在某些方面这幅画非常杰出。
西尔维斯特:(在你的作品里)很多人好像都感觉到某种程度上有一种疏离感,或者暴力的威胁。
培根:嗯,这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1909年我在爱尔兰出生。那时我的父亲是一个驯马师,我们的居住地就在库拉富营地附近。那里驻扎着一个大不列颠骑兵团。我总是记得,就在1914年战争前夕,他们骑在父亲的马背上,策马疾驰,进行军事演习。战争期间,我被带到伦敦,父亲就在军队里工作,在那里,我渡过了漫长的时间。就这样,我非常小的时候,就知道了什么是所谓的恐怖的可能性。后来,新芬党执政时期,我回到了爱尔兰,在那里长大。那时,我和祖母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经历过数不清的婚姻,最后嫁给了基尔代尔的行政长官。我们居住在一个用沙袋加固的房子里,出门的时候,我就看到被挖成沟壑纵横的街道。那是为了陷住汽车、马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当它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时,就会有狙击手等在角落里。后来,在我16岁还是17岁的时候,我去了柏林,看到了1927年或1928年的柏林。那时的柏林是一个相当开放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它非常非常暴力。柏林之后,我去了巴黎,就在那些混乱时期与1939年战争之间的年代里,我活了下来。所以我会说,也许我早已习惯于在暴力的形式中存在。
西尔维斯特:我们已经聊到了赌注与情感,有时人们会陷入一种调子,这样他就不会做错任何事情。这如何与绘画过程联系起来?
培根:嗯,我确定这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联。毕竟毕加索说过:“我无需玩机会主义的游戏,因为我总一直在独自工作。”
西尔维斯特:和绘画联系起来呢?
培根:我再说一遍,不会有人知晓那是出于运气的驱动,还是出于本能的恩宠。它究竟是出于本能,还是有意而为之,我不得而知。在你被恩宠眷顾时,所有的东西都纠缠起来,共同起作用。
西尔维斯特:您很喜欢赌博,不是吗?那你喜欢俄罗斯轮盘赌吗?
培根:不喜欢。假如有可能选择自己想做的事,那就是活着。然而,某一天有人告诉我,德·斯塔埃尔被俄罗斯轮盘赌深深困扰着,他常常夜半时分沿着海岸线,以极为可怕的速度,驱车逆行。目的仅是想看看他能否能逃离死亡的深渊。我深深懂得他如何渴望死亡,那是一种绝非源于自杀欲望的死亡。但是对我而言,俄罗斯轮盘赌完全无效。当然,我还没有获得那种所谓的“勇气”。我知道身体的冒险确实会令人振奋不已。但也许是因为我过于懦弱而无法面对死亡。当我还想继续活下去,还想让自己的作品更加出色,而绝非出于虚荣时,你可能会说,我必须活着,必须存在。
西尔维斯特:您当初去的哪所学校?还是说您没有去过学校?
培根:当时,我在切尔滕纳姆的丁克洛斯学校读过很短的一段时间。那是一个公立小学校,我不喜欢那。我总是逃学,最终被开除了。我只在那儿只呆了一年。所以,我所受的教育极为有限。后来在我大约16岁的时候,妈妈每周给我3英镑的费用,靠着它们,我就足够生存了。我到了伦敦,然后去了柏林。年轻总是有好处的,人们都喜欢年轻人。不管你怎么想,当时我和那些青睐我的人住在阿德隆酒店,最棒的酒店。我常常记起,那里清晨送上的花样迭出的早餐——盛满硕大鹅脖子的餐车总是在四处出现。并且,柏林的夜生活也给了我巨大的惊喜,那时我刚刚从爱尔兰投奔这里。但是,我也没有在柏林过久停留,一段时间后,我去了巴黎。在那里,我看到罗森伯格推出毕加索的画展,就在那一瞬间,我想,嗯,我也要试着画画了。
西尔维斯特:你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的反应如何?
培根:他们对我想成为艺术家的想法感到非常震惊。
西尔维斯特:你总是说你在画画的时候,更喜欢独处——比如说,你在画肖像时,你完全不喜欢有旁人在场(包括模特)。
培根:在我独处时,我感到更加自由。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画家,他们在被别人环绕时会更有创造力。但我不行。我发现只有独处的时候,才会受画作本身的引导。我画在画布上的那些形象牵引着我,作品就这样慢慢建立起来,活起来了。这就是我喜欢独处的原因,仅仅与自己的渴望为伴,那种要在画布上横扫一切的渴望。
注释:
[1] 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l909--1992)堪称20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架上画家。
[2] 委拉斯凯兹(Velasquez,1599—1660),十七世纪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
[3] 埃德加·德加,法国印象派画家。
(西尔维斯特,1975, 1980 ,1987年 撰写修改,艾蕾尔 译)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