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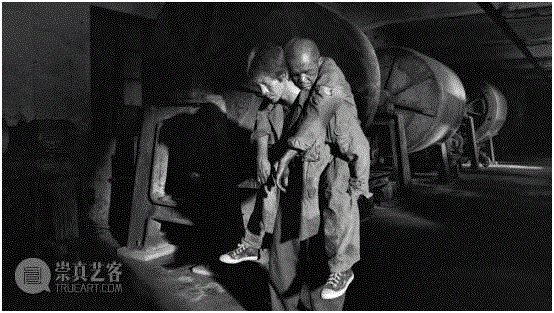
帝国边界Ⅱ– 西方公司(2010),图片:陈界仁
陈界仁,台湾著名艺术家,因其多媒体装置及影像作品著称。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广泛展出,其中包括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2009)。近期的个展包括MUDAM (2013),台北市立美术馆(2010),REDCAT,洛杉矶-美国(2010)。在日本,他的作品曾在第三届福冈亚洲三年展(2005)中展出。
陈界仁最近为了在群展“Disordant Harmony”的开幕而重返日本,展览在广岛城市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同时,受日本独立艺术机构-东京艺术公社(Arts Commons)之邀而准备的以《残响世界》(2016)为主题的‘演讲’,作为东京艺术公社演讲系列的一部分,于2月在东京的Shibaura House呈现。ART iT趁此机遇与他在广岛会面,共同讨论他作品的创作心得。
记者:当我看到Empire's BordersII - Western Enterprises, Inc. (2010)帝国边界Ⅱ– 西方公司(2010)中的档案照片时,让我不由得开始思考关于日本冲绳当下的处境(这件作品在广岛城市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群展"DiscordantHarmony"中展出)。尽管我了解所有的作品是关于你自己、你的家庭以及台湾的历史,但是当我在作品的录像中看到美国军方的纪录片片段和台湾的过去,还是让我产生了关于冲绳过往的奇怪感受,并且不能自已的感伤。你之前描述过在你父亲离世之后如何搜集他所遗留的文档资料和物品,这也成为创作这件作品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这件作品含有高度的政治视角,以此为起点,这件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发展进行的?
陈界仁:大概是1970年前后,我忘记了是谁,一位女性说: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有一段时期,我没有再创作作品,但是大概在我36岁左右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度过了某个节点然后开始重新创作。自那时起,我开始相信:不管问题有多复杂,如果我认真、严肃地考虑它,就能解决它。这样做,让我可以多角度的与世界展开对话。创作的行为关系到人、世界以及社会。就是这么简单。
记者:但是另一方面,持续性也是你作品中很重要的因素。它并非‘漫无目的’,或许会在没有一个明确目标的时候你也会徘徊不定、甚至走弯路,但也正是你思想建立的过程。。我感觉,观者在观看作品时,也实际经历了这个过程。换句话说,这种体验无关理性的判断之后去得出某种结论,而是伴随身体感受缓慢前行的,而体验本身也成为作品内在表达的一部分。



《工厂》(2003)
陈界仁:举个例子,我的作品《工厂》(2003)涉及到一个服装厂以及在那里工作的女工,但是事实上,它也与我姐姐的生活经历有关。我的姐姐一直是在工厂做工。如你所知,这些工厂通常是美国和欧洲在中国或者东南亚所投资兴办的。。工厂可以迁移它处,但是工厂里的工人是不允许自由迁移的。她们承受着的其实是来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这些问题早已众所周知,但是真正困难的问题是:这些被压制的工人如何能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讲述这种处境。
所以在我创作这系列作品中,我第一次与几位女工见面,然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来随访她们的日常活动,不携带相机或者录音设备,只是用一种友好的方式与她们交谈、互动。然后,当这些场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才最终开始思考这件作品。实际拍摄最多用了5天。但和这些女工交流的时间相比,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你问我这件作品的起始点,事实上,就连我自己也不清楚。它可以是我20年前的记忆,当时我的姐姐还在一家工厂工作,或者它可以是我自己开始进入工厂时的记忆。在没有一个明确的起点的情况下,作品和项目就简单的开始了。
[page]

帝国边界Ⅱ– 西方公司(2010),图片:陈界仁
记者: 在《帝国边界Ⅱ– 西方公司(2010)》作品中,镜头中浮现的事物,是与过去、当下和未来有关的各种元素。你如何看待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
陈界仁:这些全来自于个人经历。比如,现在和我讲话的‘你’并不是现在当下的你自己,也许是5岁的你自己,也许是10岁时候的你,乃至未来的‘你’- 来自不同时刻/瞬间的不同的‘自我’在一起对话。我觉得可以在作品中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这也同样取决于你(观者)的个人经历。这不是一个很难的哲学概念,或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想许多人拥有相似的经历。
记者:但是这件作品中体现的时空场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儿离奇。随着这些相似的场景不断的重复,或纪录片片段的插入,观者不可能掌握这件作品总的时间与空间框架,也就会混淆自己所处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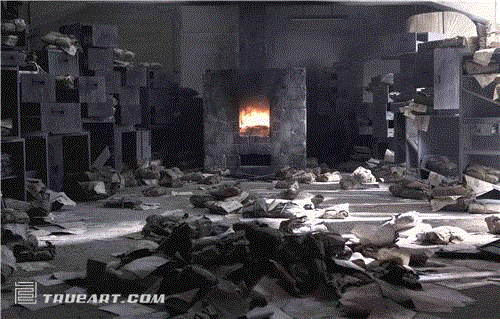
陈界仁,《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2010,三频道录像装置,录像截屏


陈界仁,《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2010,三频道录像装置,录像截屏
陈界仁: 这就是我的意图所在。这件作品中,燃烧的火炉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场景,这是一个无法被身处作品中的人能注意到的场景,只有观者可以看到。(尽管这件作品此次在广岛展览中作为单频作品展出)原本的装置有三个屏幕,其中两个屏幕置于中央主屏幕的后方,像是有意隐藏着,屏幕上呈现的是在火炉中这些文档被烧毁的场景。主屏幕中,作品中的人物不停的徘徊,或许永远不会发现这个正在烧毁文档的地方;然而所有的观者却不得不围绕着主屏幕走动,不断观看这些文档接连被烧毁的片段。
在另外一个场景中,工人们手中握着标记着潦草数字的纸张。这些数字代表了他们被解雇的天数,但是对于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更多细节是无法给出判断的。观者在观看作品的时候,会对意识到作品中的某些事情,但是实际上会有更多的事情被人们忽视。也就是说,观者与作品之间总存在一段距离。多数人会在看作品之前阅读介绍性文本,并且认为这件作品是关于台湾CIA(中情局)的历史,但是所有观者看到的是人们在一些建筑四周走动。即使你去追溯图像,也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台湾CIA历史的内容。
作品的结尾,所有人汇聚在一个大房间内,起初看起来,似乎是他们无法离开这座建筑,但是,此时并没有任何信息提示观者这座建筑可能是什么。最后的场景是从火炉中弥漫出烟雾,看起来像一个洞,也像一面镜子。看到这个场景时,观者或许好奇火炉中究竟在烧什么,或者这些烟雾需要多长时间会消散。并且,从这一刻起,观者开始思考他们自身的处境。所以,作品始于人尽皆知的问题,但是通过持续观看它,观者开始思考自己的处境。
记者:事实上,人与数字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这件作品中,也出现在你拍摄的疗养院作品里。用数字来指代特殊人群是你的兴趣所在吗?目前,日本政府正在推介一种名为“我的号码”的新系统,这个系统用于公民个人信息的集合与管理。所以我在思考这种匿名化的方向和人与数字之间的控制关系。
陈界仁:恩,我觉得没有任何方式可以脱离数字。比如,我有一张台湾身份卡,嵌在卡片背面的芯片中涵盖了各种数据。我们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由数字代表?这种方式的控制扩展到了生物政治学的任何方面。或许艺术可以是与之抗争的方式,(或许艺术可以反抗它)。一种通向生物政治学的进程,艺术作为一个与这种进程背道而驰的方式而存在。
对政治保持批判的立场是艺术的政治角色之一。艺术的政治潜能在这里得以体现,而不是在谈论政治问题时。我们通常批判性的谈论关于CIA的问题,但是你也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批判性的谈论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谈论人们被资本主义压迫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这就像是,在“西方公司”中四周徘徊的人们一样,也正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受控于权利之下的的游走状态。回到带有烟雾的最后一幕,没人知道这些烟雾将会去何处。自这一幕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也许观者会想要远离烟雾的画面,并且开始思考其它事情,就像你说你想到了冲绳。那个瞬间在脑海中的浮现,就是艺术。所以艺术并不是指一种物化的艺术作品,而是通过可见的作品去创造这种艺术瞬间。
[page]


上:帝国边界Ⅱ– 西方公司(2010) 下:《残响世界》(2014),图片:陈界仁
记者:你怎么看待《残响世界》(2014)?这件作品讲述了不同人物的故事,他们各自出现在作品不同的片段。我觉得与《帝国边界Ⅱ– 西方公司(2010)》相比,它更加关注‘人’。
陈界仁:这件作品的首次展出,是在作品的拍摄地‘乐生养老院’的户外放映。当观众观看其中一个录像时,其它三件作品的声频也在同时播放。四个片段的影片长度各不相同,所以每个片段可听到的声音是不停变化的。所以这里也一样,艺术的瞬间是由观众生成的,而不是艺术家。
而且,每一个观众或许会经历各自不同的艺术的瞬间。当然,也有人丝毫感受不到艺术的瞬间。
重要的是,观者自身可以进入一个深度思考的状态,然后跟随自己的想象。这样,观者的思想可以形成一个艺术家所不能预测的形态,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应有的样子。比如,《残响世界》涉及患有麻风病的人,这是故事的起点,但是在看完作品的四个部分之后,也许一些与麻风病无关的联系会在观者心中产生。
“去创作”是什么意思?这里有四点,相同的发音,含义却不尽相同。
首先,你有一个‘kiten’(起源,起点),接着在kiten(分叉点)的路上出现分裂,kiten的数学(奇点,奇数的点),以及一个消失的或者爆发的kiten(初始奇异点)。
比如,在《西方公司》中有一个被高度限制的禁区空间,其中包含过去的历史,不同历史之间的连接点,不同阶级的历史,当代工人的历史。你可以称它为“真实的纪录片”。但是事实上,观者知道所有都是虚构的。这些所有的历史被压缩进了一个单一的发散点,我觉得当观者看到最后一幕冒烟的火炉时,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或许你可以称它为‘爆炸的瞬间’。然后你退回到起点、重复。这就是我的作品。
记者:有没有可能去考虑将这里发生的事件与‘集体记忆’(communal memory)联系起来?比如,所有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取代每一个被个性化的个人记忆。实际描写由来自不同语境的人群所构成的集体记忆并不容易,但它必然是存在的。
陈界仁:是的,尽管‘集体记忆’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回忆。我们是不同的,但是我们拥有的相似记忆具有交叉点。观者不需要去了解出现在作品中的所有历史和语境。当观者观看作品时,如果他们拥有某些相似的经历,那么他们可以与作品建立起联系。
作品有意在最初迷惑观者,它始于一个简单的开头,接着开始逐渐令人困惑。作品中有多重的发散点,所以观者不可能拥有相同的观看体验。
[p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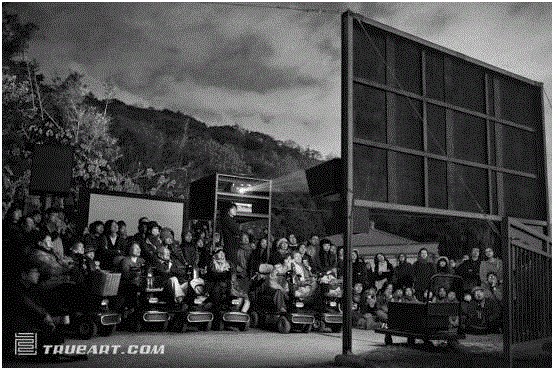
《残响世界》(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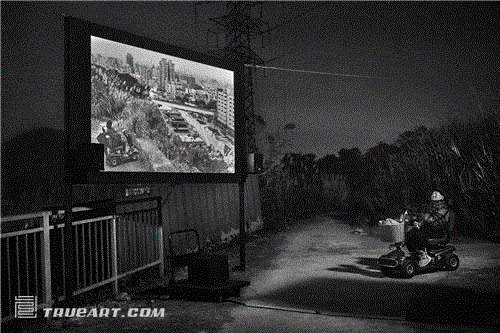
《残响世界》2015年1月18日放映现场,院民周富子与銀幕內自己的影像对望
记者:在这层意义上,《帝国边界Ⅱ– 西方公司(2010)》中除了代表你自己的人物之外还有其它的角色,但是你在东京二月呈现的‘演讲’中,你将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讲述。之前你有没有扮演过自己?
陈界仁:目前为止,我从未在自己的影像作品中饰演自己,尽管我曾做过表演。此次‘演讲’的地点,ShibauraHouse,是一个几乎全部被玻璃表面组成的特殊建筑,它给我了这次‘演讲’的灵感,而不是表演。我计划它有浮动之感。我同样以乐山疗养院的故事作为作品的开头,然后会加入其它的故事,包括日本年轻派遣工的问题。我认为,在最后我自己将成为‘演讲’的一部分。当然,我也会谈论麻风病,但是其它故事关于排外、生物政治学、临时劳工的进入,我认为,将会有一个瞬间,观者开始思考这些涉及他们在东京自身经历的问题。所以,这个‘演讲’不仅关于台湾的历史,或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历史。我期待观者可以经历他们自己的艺术瞬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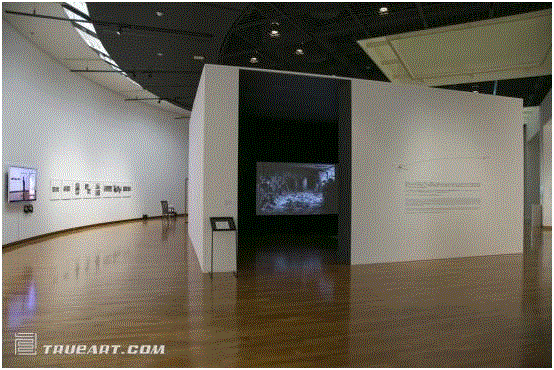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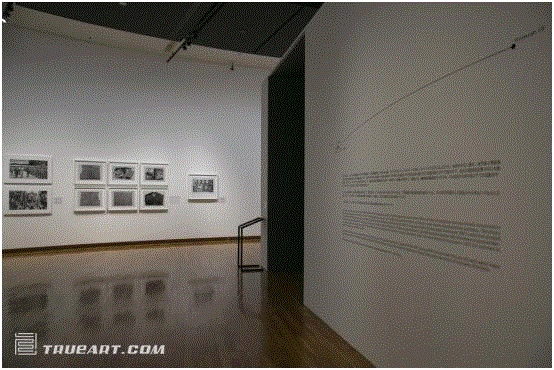
群展“Disordant Harmony”展览现场,广岛城市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ART iT.
撰文:Natsuko Odate、Akira Rachi
来源:ART iT-Asia
陈界仁《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背景说明与作品简介
1950年韩战爆发后,原本在国共内战时已放弃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为了围堵共产主义在东亚的扩张,转而重新支持败退至台湾的国民党,并于1951年由CIA在台湾成立了「西方公司」,与国民党合作训练突击中国大陆的「反共救国军」,以及进行将台湾改造为东亚反共基地的计划。
CIA使用「西方公司」这个名称虽然只有5年﹝1951─1955﹞的历史,随后即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4─1979﹞下,改以其它名称继续其在台湾的任务。就如同「西方公司」这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命名,不仅已明示美国准备对台湾进行长期宰制的「帝国」计划,也预告了美国对台政策一系列演变的目地──通过支持独裁政权对左翼人士与异议者的残酷镇压和全面性的洗脑教育,把台湾塑造为亲美/反共的基地,以及随着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发展,将台湾逐步纳入其全球帝国「公司」阶层化的治理结构中。
《帝国边界II─西方公司》是陈界仁以父亲过世后所留下的遗物为出发点,而拍摄的影片。他的父亲当年曾是「反共救国军」的一员,其留下的遗物包含了一本半虚构的自传,一份「反共救国军」突击中国大陆时,突击舰在海上被解放军击沉的阵亡名单,以及一本空的相簿,和一件老旧的军服。
陈界仁在创作自述中写到,「我大哥说:父亲告诉过他,那些『反共救国军』跟他一样都是穷人的小孩,在那个时代,他们除了当兵,没有其它的路可走,甚至连薪饷都拿不到。那本自传也只是为了给上级的忠诚检查所写的报告,并不是真的,而相簿上的照片,很早以前就被他烧掉了。小时候,我偷翻过那本相簿,我记得上面贴了很多父亲和『反共救国军』接受『西方公司』训练时的照片。」﹝注一﹞
陈界仁并不清楚出身贫穷渔村的父亲,是否想过他们在「保卫」的是什么?是否知道当反共救国军在突击中国大陆时,台湾岛内也正在进行着一场对左翼人士与异议者的镇压行动?以及他是怎么看待冷战/戒严下的「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对台湾所谓的「经济援助」和在台湾内部长期进行的「文化冷战」?而这些与当下全球的新自由主义,又存在着什么样的连续性关系?
他的父亲与那个时代许多的「父亲」一样,在冷战/戒严体制的监控机制下,对他们的人生经历选择了「缄默」,然而「父亲们」的集体「缄默」,不仅在台湾当代社会留下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和集体精神上的黑洞,同时使台湾成为一个去历史的「无档案化社会」﹝注二﹞。
影片以父亲忌日时,「儿子」在重新审视父亲遗留下无法见证历史现场的空白相簿、无法呈现真实经历的半虚构自传、真实却又无从考据的阵亡名单、以及父亲肉体消亡后所留下的军服后,在焚烧银纸祭拜父亲的烟雾缭绕中,「儿子」穿上父亲遗留的军服,在想象中开始了一场进入「西方公司」内的旅程。
在恍如是「西方公司」的废墟里,在残留着「美军顾问团」的标志与「美援时期」建立的化工厂遗迹中,在迷宫般的大楼内,「儿子」与回来寻找自身档案的「反共救国军」、以及从未能离开过这栋大楼亦无档案纪录的「白色恐怖受难者」﹝注三﹞、和被解雇的当代失业劳工们,在不同的房间内陆续地相遇……。
然而,这部虚构的影片并非为了对「西方公司」进行另一种「实证式」的历史考据;对陈界仁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在被「西方公司」改造为「无档案化的社会」与「集体记忆空白化」的台湾当代社会中,被改造区域内的人民,可以如何从个人与群体的历史经验出发,通过往返于历史和当代现实的连结中,藉由「再想象」、「再书写」和「再身体化」的拍摄行动,进行自我疗愈和自我重建的可能性。
陈界仁在创作自述中提到,「拍摄这部影片,是为了在『西方公司』制造的『集体记忆空白化』的场域内,一次除魅与自我治疗的行动,一次在『无档案化的社会』里对人民记忆进行的『再书写』,以及与『被消音者』的再次相聚。
「这个想象的旅程,不是为了走向过去,而是为了重新建构『家』的未来意义。」
注一:前「反共救国军」尚存之老兵,曾长期努力希望台湾政府补偿国民党当年所积欠的5年薪饷,唯至目前为止,台湾国防部以查无案卷资料为由,继续搁置此案。
注二:此处所谈的「无档案化的社会」,不仅指过去国家对人民的治理档案,已被国家机器销毁或持续地遮蔽;同时指在长期被宰制的状态下,台湾当代社会失去了通过「人民书写」与「自我脉络化」的过程,建构「人民记忆」的历史。
注三: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档案,从1987年解严至今,依旧有大量关键档案尚未被公布。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