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LOFT一人一世界讲座回顾】梁铨:深圳文化最大的可能性在“边缘的力量”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9月18日晚上,由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主办,《打边炉》和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协办,《打边炉》主编钟刚策划的OCT LOFT “一人一世界”讲座第20季“对对碰:深圳艺术和设计的100个问题”在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举行。
第三场活动的对话嘉宾是艺术家梁铨和建筑师张宇星,主题为“在深圳,艺术和设计可以互相拯救吗?”以下是活动下半场张宇星向梁铨提问的部分,发表前经过双方审校。
张宇星:有人说,在未来的人工智能AI时代,人类将被机器剥夺工作机会,大家可能会整体失业,最后剩下的一个职业就是艺术,您作为艺术家认同这一点吗?梁铨:英国大科学家霍金也提到过这点,他比我们聪明,比我们眼界宽,比我们占有的资料多,连他都有所担忧,所以这有可能是对的。但是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很多工作都被机器代替,人类会无聊。无聊会产生很多新的形态,会不会又让机器跟不上呢?最后剩下的不一定是艺术,甚至很多工作被机器代替以后,人类会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维、新的动作,还是会让机器跟在后面,一步步地模仿。有可能将来人的变化越来越多,像孙悟空一样,互相变,互相拯救。当年猿人在进化的过程中,他不一定有想法,不一定能够畅想到几千年以后,他们的后代会坐在流水线上装配苹果手机。如果知道,那些猿人有没有冲动不停地制造工具来进化?现在说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很多事情用不着想那么多,尊重生命。张宇星:艺术可能拯救不了建筑,当然也不能拯救世界,但艺术能否拯救艺术家本人?梁铨:比如,梵高做了艺术,把自己的耳朵割掉,罗斯科做了艺术,自杀了,他们都没有拯救自己。艺术能不能拯救艺术家本人,我觉得因人而异,艺术不是万能的,它可以拯救一部分人,让一部分无聊的人不无聊,如此而已。张宇星: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今天,纯粹的原始自然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中国古人绘画中的自然山水意境是否对中国当代现实社会具有拯救意味呢?
梁铨:中国的文人画,尤其是山水画,具有中国精神的宗教功能,它是有拯救性的。艺术家在画它的时候有一种心灵上的拯救感,观众在看它的时候也有拯救感,但是这种拯救感在今天数码化时代能有多强?我觉得是越来越弱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物质化、碎片化,好像需要拯救的只是瞬间的情感,有时候可能吃一个冰淇淋就可以拯救。这很浅薄,还需不需要通过看中国的山水画来拯救,现在来讲还是一个问题。张宇星:这个问题再深入,中国古人所反映的山水可以被定义为自然,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状态,难道不也是一种自然吗?梁铨:现在人工的东西太多了。人是一个丑陋的动物,尤其是现代人,完全就是破坏地球的一个癌细胞。所以人生产出来东西很不好看,不像大自然的春夏秋冬,它的产品很美。张宇星:举个例子,我看过很多影像展,一边是数码化的,表达了人对自然的抽象认识,完全没有山水的形象,但是我特别喜欢,很漂亮,很震撼,而另一边是一张很正常的自然山水照片。我更喜欢数码化的东西,因为它反映了一种新的自然,为什么只有表象的自然才是自然,数码化的东西不是自然吗?梁铨:数码化的东西也是一种自然,和你的学养有关,你的学养和它的表现频率合拍了以后,你能在艺术中感受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应该是更普及的、更容易让大家理解的一种自然。张宇星:您喜欢禅宗,这是一种自我心灵拯救方式,还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性的心灵拯救方式?梁铨:我觉得它具有普遍性。但现在整个强势的西方世界,凡事都要用科学来衡量,他们不一定认为这是一种拯救方式。然而,西方人佩服日本的禅宗,但他们不知道日本的禅宗是学我们的,就像梵高能理解并临摹浮世绘,而浮世绘的画家却是临摹我们宋元的绘画、理解了我们的精妙。所以,我觉得肯定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中间的载体,它不一定是中国的,可能是日本的,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只有中介才能让西方一点点了解到禅宗的优美,这是有普世意义的。像西方当代艺术,双年展上的一些摄影作品、装置、录像、偶发艺术等,好的东西都与禅宗里的公案有关,禅宗里有趣的公案可以转变为一段好的当代艺术。张宇星:著名建筑理论家柯林·罗(Colin Rowe)曾经写了一本书《拼贴城市》(Collage City),而您也喜欢用宣纸碎片拼贴的方法来创作,您觉得这两种“拼贴”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性?梁铨:这本书我没看过,上网查了一下,也不是很懂,毕竟我不是做建筑的。“拼贴”是西方来的词,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装裱”或“托裱”。清朝有一类画法用的就是托裱,现在我也是用这种方式来画,但翻译成英文就变成拼贴,实际上两者可能没什么关系。张宇星:如果让您用水墨来表达现代城市,同时需要呈现出中国古人的绘画意境,您觉得有可能吗?梁铨:有一点难。中国所谓的现代就是西方化,但纯粹的西化不一定等于现代。改革开放到现在,不单是艺术家,甚至有些建筑师都以模仿西方为荣,就是要摩天大楼。当时改革开放,贝聿铭造的香山饭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能理解,也包括我,觉得应该造高楼大厦。过了这么多年,我们才慢慢理解,但现在香山饭店已经被破坏得惨不忍睹了。贝先生生活在美国,走得太前,有时候也是要有一段很痛苦的回味过程,才能得到承认。张宇星:有的艺术家喜欢喝茶,有的艺术家喜欢喝酒,有的艺术家喜欢看美女,您认为这些“癖好”是否构成艺术家创作行为的一部分?梁铨:只能说有这个可能,你讲的这个“癖好”也是大部分人喜欢的。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很多都是有团队的,经常要和人打交道,工作体量大,密度也大。相比之下,艺术家是个体,自由时间比较多,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张宇星:曾经有一种说法,“深圳是文化沙漠”,您如何评价?梁铨:要看跟什么城市比,但是深圳肯定不是文化沙漠。跟伦敦、跟纽约比,深圳的文化活动确实少。跟广州、上海比,深圳有一些创新的活动,但基层的活动,也不见得比这两个城市多。深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艺术发展是由建筑师、设计师来推动的。深圳建立的时候,没有艺术院校,但有平面和建筑设计的需要,所以深圳的建筑师和平面设计师一开始就走向市场,进而造成整个深圳艺术的繁荣。后来,深大艺术系成立,有毕业生了,加上外面调进来一些艺术家,艺术活动一点点开展,到这两年开始有当代艺术活动。这与深圳的设计师、建筑师、华侨城的贡献分不开,他们为深圳当代艺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才有了后来的一切。张宇星:前两天我去考察了沙井老区,发现里面有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客家文化以及广东本地的文化,中国古代那一整套乡村机制所体现的空间形式,全都完整保留。我也经常来回长三角,但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只剩下几个化石一样的古村。而恰恰在深圳,这些现实的土壤里有大量活的真正的文化基因,那里面的人都在用它。这根本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湿地,甚至是文化森林。梁铨:这就是边缘的力量,边缘能保存很多以前被中央淘汰的一些文化体系,就像海外华人,在东南亚还保留了很多中原文化,但现在的中原已经没有了。张宇星:职业艺术家需要长期的训练,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艺术作品,而业余艺术家,比如我,似乎可以靠“观念”来创作。您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有可能或者有必要吗?梁铨:这种说法比较激进。前卫艺术是相当左派的、也是政治很正确的一种艺术,这对和不对,我觉得要观望。“观念”是一种创作方式,它可以迅速拉近思想者和实践者之间的差距。如果你用观念创作,说明平时你已经投入了很多的思考,肯定比一般人不一样。所以用这种方式,可以成为一个观念艺术家,但是不一定人人都是观念艺术家。张宇星:如果人工智能有大把的时间训练,可以在技法上提升很快,那么职业艺术家的训练时间比不上人工智能,画出来的东西就有可能赶不上它。这样看来,是不是需要观念的放大,才能打败它呢?梁铨:你讲得对,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专业就已经失去了尊重。比如身上装了人工韧带,就会跳舞;嗓子装了软件,就能唱歌,在专业不受尊敬的情况下,成不成为什么“家”都无所谓了,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张宇星:回到艺术的本质问题。艺术是一个人经验的长期训练,跟观念、手、心、脑都是关联的,这种训练几乎是人类跟机器的边界。但现在出现人工智能,似乎我们已经到了这个临界点,比如3D打印和人工智能一结合,用图灵测试测不出哪个是由艺术家创作的,哪个才是机器人。这种时候,观念的表象和艺术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样的?梁铨:如果真到这一步,每一件作品都很平常,就瓦解了权力,一切都归于平淡。就像我跟你都烧一碗饭,即便之间有很微妙的变化,但都只是一碗饭,我绝不会因此认为自己是烹调大师,你也不会因为你烧的比我好吃,就觉得了不起。张宇星:有的艺术家靠卖画成为亿万富翁,有的艺术家终其一生穷困潦倒,您认为金钱是艺术的敌人吗?梁铨:以我个人的经验,艺术家不是那些内部结构非常坚强的人。如果艺术家接触到很多钱,一般是挡不住的,是会出问题的。我尊重那些从市场上赚钱的艺术家,而不喜欢靠其他手段从政府里拿资源的艺术家,赚很多钱,但我觉得不怎么样。实际上,金钱和艺术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大家都是看哪个人的画卖得贵,就认为他画得好,没有办法。梁铨:艺术家也是人,得看他追求什么。有的艺术家在画画过程中很享受,希望一辈子画画;有的艺术家就希望画画能卖钱,数钱的时候很高兴。
OCT LOFT “一人一世界”第20季特别策划
对对碰:深圳艺术和设计的100个问题
时间:2019年9月12日、17日、18日、19日
主办: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协办:打边炉 华侨城策划规划联盟
场地合作:华侨城创新研究院
策划人:钟刚
讲稿编辑:劳秀汶(实习生)
视频制作:王若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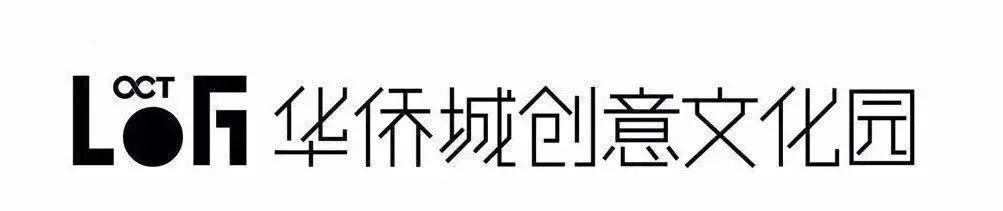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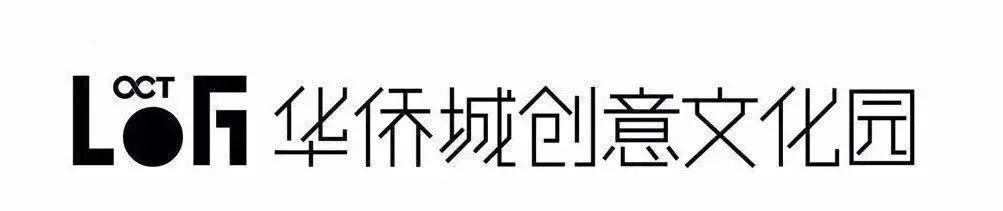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