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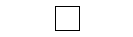
2019年9月底,笔者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观看了音乐剧《血色湘江》的首演。对于湘江战役这场重大战争悲剧的历史背景介绍,以及此剧在传播核心、正向意识形态方面取得的重大价值,已有很多专家学者撰文详细表述,本文不再赘述。作为没有经历过战争动荡时代的青年一代,笔者更想针对此剧因何艺术处理手法会深深吸引自己这样的“计划外观众”而做出深度分析。
该剧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广西演艺集团创排,根据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最关键的湘江战役中,红军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在长征中受命掩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受伤被捕后断肠取义的事迹改编,表现了共产党人绝对忠诚、坚守信念、敢于牺牲的革命主义精神。红军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撕开了敌军的封锁线,留下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中国戏剧是个环境与体制都十分特殊的地方,有时作品成就有着更复杂多维的成因,并不完全依赖于艺术卓越审美、体系完整或人文价值的深刻。大量作品被束缚到审美的象牙塔、形式的高楼阁上,你听不到个人自我的澎湃情感、冲破困境的渴求与欲望、个人的理想与野心、以及要记录与阐释时代的使命感,然而这些东西,却是戏剧最能感染大众、掀动起浩大感召的“生命力”。
国家层面对表现革命历史重大题材的主旋律戏剧,政策上的扶持激励、投入上的重视力度都是有目共睹。然而我们的戏剧舞台上,存在着大量概念僵化、流水线式的人物塑造和高歌猛进、千篇一律的事件冲突。
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于主旋律题材的拒绝,原因往往是对刻板处理人物和剧情的排斥,正面人物必定“高大全”“伟光正”,反派人物皆是脸谱化的丑化,善恶对立,非黑即白。舞台上急需与时俱进的创新讲故事内容和方式。

《血色湘江》的总导演陈蔚、编剧钱晓天、作曲张巍在剧情设置和曲目编排上,既表现为集体、民族、国家牺牲的大场面大情感,亦重视个体人物“小我”的情感;既有对崇高信念的膜拜,又不缺失对人性怯懦、自私的悲悯,对生命的深层敬畏;写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更难得的是展现出被战争肢解的人间烟火。
作为更高意义上的当代戏剧创作者,应将戏剧当成自我真诚情感倾诉的载体,在宏大与崇高的东西面前,更不能把个人心声看小。

《血色湘江》表面是庞大而完整的明线在牵动——陈湘率后卫师为掩护中央度过湘江与敌死战,底下是撕裂的暗线,用大量情感细节去描写乱世之中平凡个体被卷入战争的命运悲剧——同窗情、儿女情、母子情、战友情。
陈湘和朱大姐
陈湘是担任总后卫的红军师长,朱大姐是怀有牺牲丈夫遗腹子的红三军团政治部干部,二者作为红军领导干部的正面形象,在面对人生最冷峻的拷问时,皆在苦难中焕发人性如金子般的光芒。
心愿了了吗?不再享受自由人生,不能体会人间繁盛,不能感受真挚爱情,不能目睹孩子成长。他们的选择那样简单,那样绝情,但个中藏着多少道不出的遗憾,说不出的永别。
原来世上有这么多,再不想承受但也不得不施与的决绝和凄凉。极致单纯、向死而生的壮烈,令笔者想起电影《风声》中,演员周迅在结尾处给观众的那段自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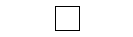
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我爱的人不知我因何而死。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
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

导演与编剧将陈湘与凤鸣的感情、朱大姐为产后病重不再拖累他人而自杀,分别这两段情节设置的极富戏剧张力和说服力。因为人物如果没有真正的冲突,也就无所谓真正的选择,最终也会缺乏真正的人物魅力,那种在两难境地里迸发的人性光芒也就无从展现。
主旋律之魂,在此二人舍生取义的选择中,得到最有力的释放。
凤鸣
剧中,凤鸣是桂北地区瑶王的女儿。这个敢爱敢恨、浑身散发着野性的凤鸣是陈湘人生中那不规则的一角,突出且明亮。苦难战事中保留着珍贵的无邪浪漫,千篇一律的男女衷情中暗涌着另类独特的天性。


这个人物设置,从一开始对红军不信任时无所顾忌的狂放与粗粝,到逐渐了解红军战士优良作风、感受红军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尊重、对军阀围剿时的英勇无畏后,她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发动寨子里的瑶胞主动给红军提供食物、当向导,并对陈湘焕发了深刻而生动的柔情。
月朗星稀之夜,她与陈湘互诉衷情,直面战前高压的苦难与惘然。这是两具灵魂的磨合与救赎,如同汪洋中两叶扁舟的相遇,拥有的是黑暗时代共同燃烧的心。紧张激烈战争后,悠扬的少数民族女声吟唱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君已远去”释放满腔柔情,词曲写得极有情感和节奏把控。
最终凤鸣带着红军遗孤“小湘江”来到湘江边祭拜英灵,面向血水染红的湘江和写满红军战士姓名的军旗,瑶族女声如招魂般的悲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代表着守望的人们,凤鸣对下一代讲述着要永远记得。场景庄严高洁、温柔静谧,凤鸣经历苦难沧桑后,依然保有着纯粹的悲悯与传承的力量。

作曲张巍在宏大构架的炽热与澎湃里加了几段瑶族原生态女声,腔调是冷感的空灵,却是化作风化作雨的意境,融入了婆娑众生的情感。对民族不复往昔的悲叹有融于自然万物的怜悯与联想,打到心底、穿透灵魂的柔与美,令笔者汗毛立起。
人物经历了成长的弧光,令观众更深切感受到在这动荡灾难的战争时代洪流中,吞没了太多情感,她从未真正停止的爱恋如沧海一粟,渺小无力,心碎而不得。
黄复兴
我们看过太多战争题材剧,把敌军反派塑造成傻子,或是单纯的奸与坏。
而《血色湘江》不曾轻敌,与真正的共产党红军相对立的,是真正的国民党精英。在国民党早期,也曾有多少为国为民的仁人志士。这是用严谨严肃的历史观,表达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悲欢。

黄复兴心思缜密,意志如钢铁,但囿于自己的格局,甘为他所信奉的信仰牺牲一切。
同是黄埔军校同学的陈湘与黄复兴,当年怎曾想到国共关系会破裂至此。过命的兄弟、同校相惜的情意,现在成为信仰相悖的敌人。
两难之时,信仰与人性,到底哪个更重要?
不是纯粹的坏人击败英雄,在此刻是英雄将英雄毁灭,这其中掺杂的痛苦、无奈、复杂人性,成为了充满宿命式的人间悲剧。

视觉总监刘科栋调动当代的舞台观念打造一台震撼心灵的、沉浸式的体验,舞美设计既有诗化的虚,又有史诗感的实与厚重,与灯光设计王琦和多媒体设计胡天骥协调统一的通过综合手段,来共同营造从视觉到内核都散发残酷气质的血战意向。
三维层面的形象,动荡而野生;
三维层面的意象,神秘又复杂。


舞美设计有一种打通事物本质的连接能力,提炼出了浮桥的意向,转台上的桥由老百姓拆自己家的门板链接而成,既构成了红军与百姓之间深重情感的寄托,又与湘江战役乃是共产党走向最终胜利的关键之役这一主题背景相勾连,构成过即重生、断即灭亡的意向, 是一座连接着覆灭与希望的生死桥。
布景由多媒体、拼接皱褶纱幕、吊悬的景片,共同打造被战争搅碎和碾压过的湘江地貌,以碎片表达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形象被解构和重组,令人亦联想参差锋利、恐怖嶙峋的枯骨状态。


转台转出了一个幽深密集、层层叠叠的深穴,笔者对于用混沌而有自然秩序感的树根造型来表达复杂的湘北战场地貌印象极其深刻,舞美设计把树根做上内发光血红的灯光,满眼恍惚的琳琅满目、波光粼粼。在人性与文明的对立面,将战争的粗暴与残忍、狭隘与毁灭勾勒展现。
陈蔚导演的舞台调度与场景非常有机的结合,使舞美有了别具一格的生命力,当情节发展到不同阶段,使人有不同联想。
1、一开始树根像战争像刀一样凌冽,掀起中华大地,人们躲在其中、后区,表现出红军战士刀尖舔血的残酷。
2、树根红光隐透,配合吊挂在头顶的巨大血剑,光与暗交织的生命基调,打造战场炼狱般的史诗感。


3、明天就要突围之前的星空下,陈湘与凤鸣的浪漫对唱。最亮的星与最美的鹰在浩瀚时空中相互倾述迷茫与爱恋,想要靠近却不可得,明明如此亲近却无限的遥远。温情的释放后是对共同理想坚定的各自守护。最终一切都将在轮回中远去……

4、树根红得像烙铁,如红军战士“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信仰在人间”的铮铮铁骨,是不死的魂灵。
5、最后陈湘受伤被捕后,与黄复兴二重唱着“竭尽全力还是班长手段高”“多么希望你能逃掉,哪怕我被人耻笑”,陈湘断肠取义。这时脚下树根的形象令人联想血涌至枯竭的红色血肉肠肺。

6.终场时湘江边祭拜英灵,脱凡又悲悯的人声、配乐与画面的融合,往事如烟。凤鸣与留守的人们站在那里,在前面无情而宏大的交响乐对照下,经历毁灭浩劫的焦虑、挣扎后,此刻显得如此深远、柔软又隽永。
转台打造了桥、江水、瑶寨、森林等关键场景。转台的分界上是黑暗与光明相互吞噬的所在,配合剧情推进的表演,残酷与浪漫、理想与现实,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撕扯。


灯光设计王琦首先在剧中使用的灯光色彩大胆而瑰丽,极少使用面光,大量测光塑造对比强烈的雕塑感。
他和多媒体设计胡天骥,共同打造了层次丰富、整体厚实凝重的“红”——战争残酷阴森的深红,寸土千滴红军血的血红,党旗庄严的正红,曙光到来温情的红,情感涌动时的暖红。



笔者写过很多剧评,着重于舞美各专业的,但很少着重提到过造型。但此剧服装设计彭丁煌和造型设计申淼非常值得好好说一下。
笔者视力比较好,而且坐得离舞台比较近,仔细观察了服装与造型。《血色湘江》的造型设计是能经得起电影镜头推敲的,不像市面上很多战争题材的演出,无论在表达何等惨烈的场面,脸上常常追求干净漂亮,而全然不顾舞台艺术规律。此剧做得如此大胆、真实而具有质朴的美感,非常难得。
这种战争题材的服装设计其实非常难做出创意,既受制式束缚,又不可随意加减。服装设计首先把很多心思用在由新到破损血污的渐进层次上,用服装的语汇传递出:
“人”,被战争凌迟过的残酷。



伤口处使用了红网格材质,这种艺术处理非常精彩,既高级又有新意。
凤鸣一出场,服装造型我一开始是不太理解的,非常惯性思维的觉得为什么如此中性,甚至太男性化,服装是否可柔美一点。但随着后来剧情发展,笔者懂了。凤鸣的祖先是战神瑶王,她作为瑶族女儿,歌唱得豪迈嘹亮,爱恨亦胸怀坦荡。到后来产生真正的儿女柔情,服装造型皆有越来越女性化的层次变化。


关于音响设计,笔者有一点建议。国内无论歌剧还是音乐剧,有一个通识(在笔者看来亦是通病),演员皆带麦演出。笔者理解行业的实际国情,也知道优秀音响的效果能极大丰富歌剧、音乐剧的艺术内涵。
但因此,也饱受有时会非常刺耳的技术干扰,甚至会出戏。
所以诚挚期盼中国的音响设计师们,能够充分重视这一点,从技术处理上,在声量控制上,注意该强化、该弱化的微妙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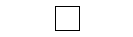
主创团队
总导演:陈蔚
视觉总监/舞美设计:刘科栋
编剧/作词 :钱晓天
作曲:张巍
指挥:朱曼
合唱指挥:周君
执行导演:李大海
舞蹈编导:梁克虎
灯光设计:王琦
多媒体设计:胡天骥
服装设计:彭丁煌
化装造型设计:申淼
道具设计:李红超
音响设计:敖元
钢琴艺术指导:张佳佳
舞台技术总监:黄志高
执行制作人:李百宁
作者:赵妍
摄影:粟国光
责编:赵妍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