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厉槟源"开幕论坛:从厉槟源到厉槟源
时间:2019年11月22日(周五)15:00-17:00
地点:昊美艺术酒店二层昊美厅
论坛嘉宾:
杨北辰 | 策展人、研究者
厉槟源 | 艺术家
论坛主持:
付了了 | 昊美术馆策展人

视频拍摄/剪辑by栗子
/
昊美术馆(上海)新展“厉槟源”于11月22日下午举行了开幕论坛 | “厉槟源”:从厉槟源到厉槟源。此次展览作为厉槟源的第一个同名个展,在较为全面的呈现艺术家过往十年的创作同时,亦试图开启一次对身体和行动的全新探索。
厉槟源将引入电影的镜头语言,雕刻一个新的情境和现场。区别与以往的行为记录方式,电影镜头在这里或许将如“庖丁解牛”一般,深入身体空间内部,挖掘身体之下的身体,将其打碎并重塑。
“厉槟源”已于11月23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作为首创“夜间美术馆”运营模式的昊美术馆,夜间将开放至晚上十点,欢迎大家夜游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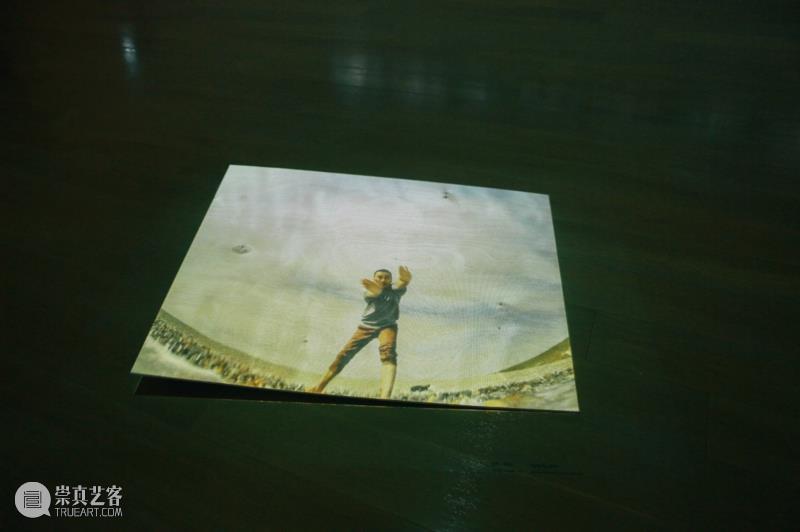


🔨🔨🔨
#导览现场
11月22日下午14时,此次展览的策展人付了了为“厉槟源”展览进行了导览环节,向到场的观众介绍本次参展作品,并指引大家走向深层次的艺术创作理念以及作品背后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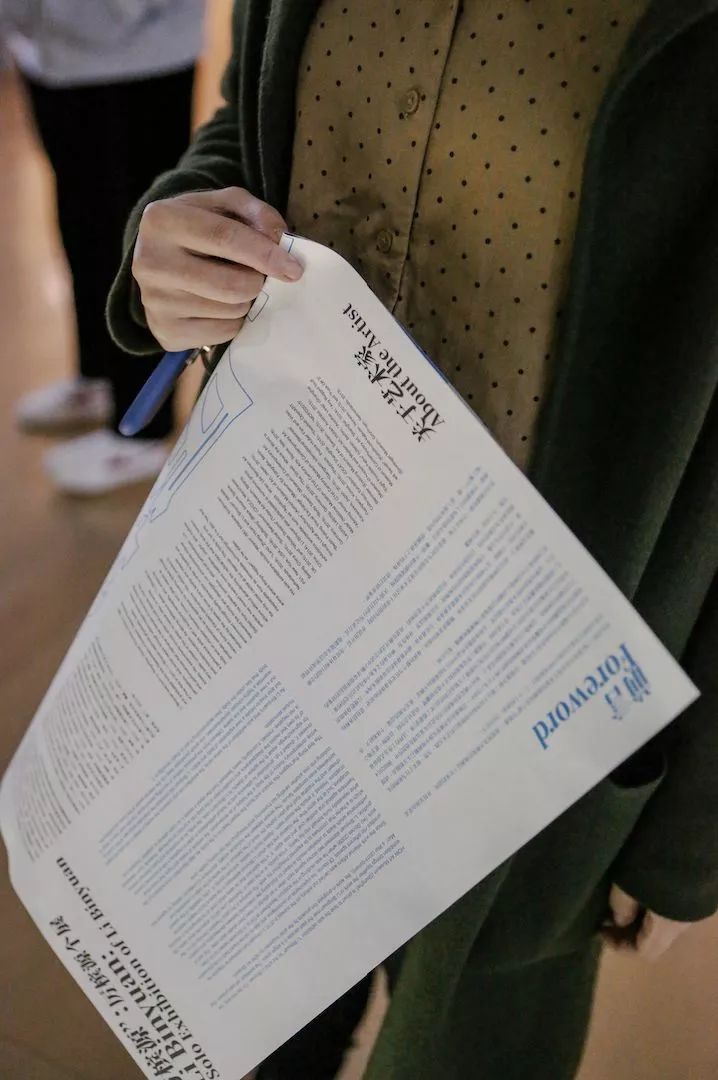

🔨🔨🔨
#开幕论坛
导览结束后,观众和策展人移步论坛现场,共同开启“厉槟源”开幕论坛:从厉槟源到厉槟源。
在此次开幕对谈中,昊美术馆邀请了当代艺术研究者、写作者杨北辰,与艺术家厉槟源、昊美术馆策展人付了了围绕厉槟源多年来的艺术实践展开对话, 并试图开启一次对身体、行动和图像三者之间的关系对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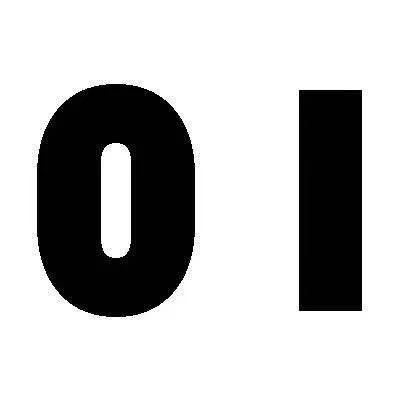
杨北辰:
我想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厉槟源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望京裸奔”这个事件。在那个时期,厉槟源以现在看起来比较“网红”的形式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然而,回到作品创作的层面,它实际上是对日常现实进行了某种干预。
厉槟源:
裸奔是我的一种“表达”。从我个人经历和生活习惯、或者是表达方式出发,会有这么一些“极端”的事情发生。“望京裸奔”的最初起因是我与女友吵架,她认为做行为艺术就得“脱裤子”,特别丢人。我觉得她对行为艺术有些误解。
中国存在一种现象,把什么都归为行为艺术,说不清楚的或者是怪异的、丑陋的、恶心的,都与行为艺术划等号。那时候我不服气,在和她分手那天,就脱了衣服去跑,有一种报复的感觉。后来发现受到了网络上的关注,我就想用网络这个媒介来创作一个作品。

付了了:
刚才厉槟源提到一个点,为什么会去裸奔?可能是他周围的人对行为艺术不太理解。实际上不仅是在中国,往往在世界范围内都有过、或者是正在发生一些对行为艺术的污名化和片面理解。你作为一个雕塑系的学生,为什么会希望在行为艺术这个领域进行创作?
厉槟源:
事实上,我没有对创作进行明确的归类和定义,它是行为还是雕塑。行为艺术只不过是我用身体这种媒介进行表达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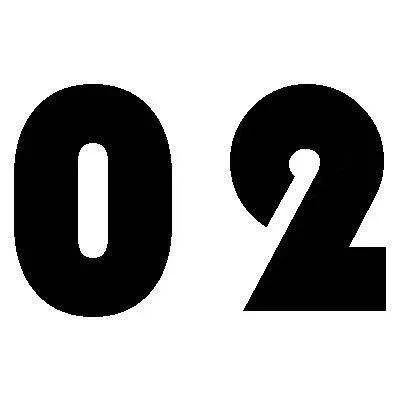
社会雕塑、反向雕塑、自我雕塑与忒修斯之船
杨北辰:
昊美术馆二层是博伊斯的展览。博伊斯提出“社会雕塑”的概念,是对于社会进行某种干预和介入,以此重塑这个社会。博伊斯所言的 “历史是由我们决定的,人人都是艺术家”,即是强调艺术家对于社会的干预和介入拥有美学上的绝对权利。很有趣的一点是,三层厉槟源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反向被雕塑的过程。厉槟源通过对自我的雕塑,暴露出整个社会语境对他形塑的痕迹。
在早期的作品中,厉槟源比较主动地进入到某些社会性的环境中。但后来他趋向于一个人出现在作品中,通过自己身体的消耗去展现脆弱的一面。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你进入到一个越来越孤独的状态?
厉槟源:
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非常强烈的表达,似乎很难引起其他人的共鸣。因此,我慢慢开始跟自己对话。
我认为“从厉槟源到厉槟源”这个议题非常贴切,让我想到忒修斯之船的悖论,是一种有关身份更替的悖论。一艘船不断地更换零件和木头,直到所有的零件都不是原来的零件,那现在的这艘船还是之前的那艘船吗?人的肉身也一直在更替,人的细胞和基本粒子一直在分裂和死亡,大概七年就可能脱胎换骨了。你的肉身跟七年前的你完全不是一个物体。
那我还是我吗?我何以成为自己。在我砸石头的那段期间,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些问题了。我还做了一个作品,用两张A4白纸相互扫描,我们看到的这张白纸它是否还是原来那张纸,也许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张白纸的影像。现在来看《两个石头》这个作品的重要性,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建立了个体创作的面貌了。我跟我,石头跟石头相互敲击,然后从中破碎再构建。


2015年在一个展览的契机下,我做了一个所谓作品关系图,试图用这样的方式了解自己的工作。我当时称之为“关于厉槟源的实验”,它将发展成什么样子还是未知的,但是已经初具规模了。
我的很多作品都从 “力”出发,基于“力”衍生出一些创作:它们有感受力和想象力,这是抽象的一种力量;有身体、人为,事在人为的力量;重力、地心引力、自然规律等自然之力;外在的“力”,包括社会环境等。自然和外在的“力”是不受控制的,身体和感受力、想象力都是主观意识。
这些潜在的力量是驱使我创作的最原始的动机,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在它们的有限和局限中迸发出来。最终通过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空间会发生不同的事件,所有事件都会回馈到身体上,所以最终还是要面对自己。
杨北辰:
在你自己的创作中,“失败”也是一个关键词。“力”经过你的身体后,并不一定成全你或者帮助你,反而有时候伤害你、破坏你。你的一系列工作,像是在把你自己内部的力量消耗掉,形成一种状态。你很多作品不太追求一个所谓的完成态,甚至有时候是更期待一个“失败”的结局。
厉槟源:
我很多创作都是在做某种练习,可能这种练习会持续一生。不是每一个作品都能说明什么,但它们在时间维度上有持续性。我一个朋友胡波他说过一句话:“爱是沉默着的行径和牺牲。”我很懂得牺牲,用一种牺牲来获取某种我想要的精神,我也称之为一种雕塑,用身体塑这种潜意识里面的一个感觉的形状。
付了了:
对于厉槟源自己来说,可能他并没有去预设成功或者失败,很多时候是一种反馈。他和他的工作对象之间产生了一种反馈,这种反馈没有正面或负面之说,而是一种纯粹的,和对象之间的互相关系。
譬如说在《测试》中,有很多的力在里面。比如地心引力、你施加的力、竹子回弹的力,它是一个分分钟的反馈。你抓着那个竹子,你不确定你什么时候会掉下去,但是可能从观者的角度里来说,这个失败仿佛是已经注定了,人最终很难与地心引力抗衡。

杨北辰:
我从小厉的作品中总能看到某种史诗性的悲剧感,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非常古典的姿态。跟构成这个世界非常基本的元素进行互动的时候(经常是水、火与土地),你就仿佛是从过去来的人。你和它们博弈的时候,有种史诗或者寓言自然地流露出来。
厉槟源:
你刚刚说到成功和失败的概念,它也可能是一种造化:被某种声音控制了以后,不受自己使唤。《测试》这个作品,我最开始的意图,是我爬上竹竿通过我的重力让它坠落下来,再用脚穿鞋。第一次就很顺利得完成了这个动作,但是当我穿上以后,我思考了我能不能穿上以后爬回竹子去,再返回地面,让这个行为变成一个零,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当我再爬上去的时候,竹子不受我的控制,竹子开始说话了,不是我想的那样了。
第二次我没有爬上去,连鞋都没有穿上,还不如第一次。于是爬了第三次,但是再做第三次就已经没有力气了。我被这种声音控制,我觉得我应该去完成这个事情,虽然没有任何意义。当时是挺危险的,赤手空拳,身边也没有任何人,只有一个摄像机,三脚架,水泥板。我爬到三四米的时候没有力气了,下也下不来,上也上不去,挂在那儿,但是我还想完成这个事情。
我也很好奇当时为什么这么入迷,明明没什么意义、没什么实际作用的一件事情。我甚至是着迷,冒着生命危险,在已经没有力气了之后只能松手掉下来。摔下来时磕到了头,导致颈椎受伤了。从这个作品来看,它肯定是失败的,未完成的,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导致了一个意外的结果。
我在身体上得到的一个直接的反馈。我意识到危险,从而感到恐惧。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害怕那种会剥夺生命的危险,我特别恐惧,这种感觉非常真实,十分具体。如果我没有碰到这种事情,我可能特别不知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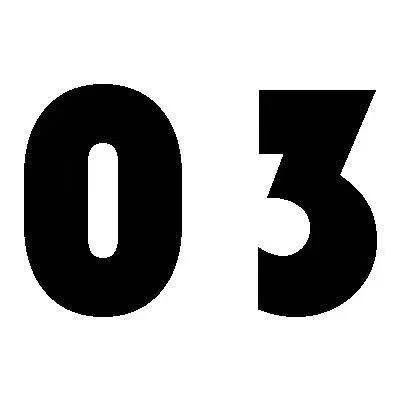
艺术是一种牺牲,它从危险之处摘取
杨北辰:
我认为《自由耕种》指向了中国历史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制度的问题。使用权、交易权、流转的空间在哪里,这对中国来讲都是非常核心、非常棘手的问题。通过这个作品,厉槟源几乎进入了一个思想家的工作维度。
他不再是自我对自我雕塑,而是有点要延展到博伊斯的那个维度,去塑造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小厉表现出了非常有趣也很灵活的策略。他脱离了农民的身份,但是他可以用自己的身体耕种,而耕种的不再是庄稼,而是他自己的身体。这就涵盖了一个非常有趣、也很辩证的含义。
厉槟源:
我回到永州时总是有想创作的冲动和欲望,好像回到了母体一样特别温暖。可能是这种熟悉感,同时又很陌生,这种心理的跨度会产生很多东西。可能就是这种感情,它的基础是家庭,是童年的生活。幸好我是个艺术家,我才能将这些问题连根拔起。


杨北辰:
你工作所借助的很多元素,如炮仗、石头,也跟你母亲的工作相关。比如《2CM》这件作品。听说你站在那个锯前面,按纽是你母亲按的。
厉槟源:
我母亲在石头加工厂工作,就是切割石头的地方。我有一次去江西工厂看她,突然特别留意了这个锯。那天正好下雨,她不工作,我就跟她说:“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比划了一下,反正就手心手背两公分,“你可以帮我开一下那个机器吗?我录一段视频。”我给了她一个三分钟的倒计时。她特别信任我,就去控制室打开了那个开关。我挺感动的,她能那么做,非常伟大。因为一般的父母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但是她完全信任我。
我有一个朋友评论这个作品说:“危险的临界点,亲情的手心和手背”。我跟母亲的关系,在这个很危险的情况下面,这种交流很有意思。我有什么闪失她会非常难受,她亲手按下这个开关,所以我也要保证我的安全,保持一个很平静的状态。在锯子打开的一瞬间,我条件反射般的全身抖了一下,锯子产生的压迫感非常强烈。我在一分钟左右就适应了那种节奏,三分钟关闭之后,它因为惯性仍然在转动,完全停止大概是六分钟。
我看到过关于惜命一段话,说危险跟惜命是相对的,越惜命的人越懂得牺牲。我认为艺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就是一种牺牲,它必须从从危险之处摘取。

杨北辰:
“危险”这个词也贯穿在你很多的作品中,或者说是“临界点”,你总是要达到某种到临界点,或者是一直拖延到临界点才愿意停下来。某种程度上,非常像运动员,为了不断地打破记录,他们愿意接受某种程度的风险,挑战自己临界的状态。对我来讲你的工作里有一部分像运动员、有一部分是演员、有一部分是工匠。工匠并不是制造一个规矩、形制,恰恰是要破坏一些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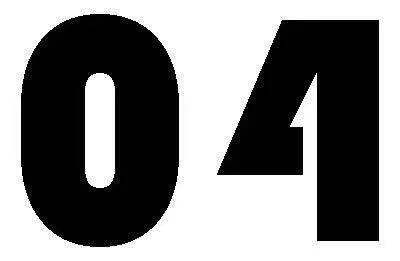
用电影镜头重启行为表演的现场性
杨北辰:
小厉他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职业当代艺术家的状态,在他身上有更多其他的成分,他的身份相对来讲是很柔软的,是可以延伸到其他的一些职业和工作领域去的。比如你即将在展览期间放映的作品《一个人的战争》似乎就代表了你最近对于电影的兴趣。
厉槟源:
我的兴趣是通过镜头的语法和行为来雕刻一个新的场景和现场。简单来说,我把镜头当成了一把雕刻刀,我自己就是这个雕塑对象,我用镜头语言为自己“造像”,通过不同角度的镜头和剪辑,重新书写了这个行为,不遗漏表演中的一丝一毫,包括呼吸、情绪和状态。这是超越表演的表演,超越记录的记录,超越观看的观看,超越现场的现场,它既是还原也是创造。
它是一个行为的长度,我不在时间上编辑它,比如我砸了90分钟,这个电影就是90分钟。只是通过在镜头上切换不同的角度,我把最关键的地方呈现给观众。

杨北辰:
你提到的电影镜头和雕塑,很像塔可夫斯基说的“电影是雕刻时光”。电影的工作就是要在原石里提炼出潜在的形态。艺术家的工作,是用电影的方法将原本质朴时间的流动塑造成一个电影的形态。从相对粗糙的现场式记录中提取出一种更加精致的、让观众能够从更多元的角度去欣赏的状态。
付了了:
刚才提到的《一个人的战争》和《死了都要爱》,都是砸锤子的行为,还有就是《进程》这个作品。在厉槟源的创作里面,他从来不排斥这种重复性的、或者说排演式的工作。比如说《死了都要爱》这个作品,从2012年开始就反复地做过好几次。行为作品发生一次,再来一次,好像有一些艺术家比较排斥这件事情,觉得会变成好像剧场式的东西,反复排演。
在小厉工作中没有排斥这个东西,包括《进程》这个作品。他要反复去移动摄影机的位置,在自己已有的资源和处境、包括这个行为的时间紧迫性当中,去调动一切的可能性。厉槟源的创作,给我的感觉是他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环境下去面对某些危险的处境。他对于一个人在社会中普遍的处境是非常敏感的。

杨北辰:
厉槟源的敏感性,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史诗的感觉。史诗的主人公是全人类,或者说一个共同体的标本。而他就是这个标本,所有人类故事里面的某种原型。通过自己的经历、通过自己的身体、通过这些行为,让很多东西通过他的身体构成了某种连接和联系,再通过表演把这些潜在的联系,将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基本认知里忽略的东西凸显出来。这就是我所说史诗、寓言的维度。
嘉宾介绍
![]()
![]()

杨北辰
当代艺术与电影研究者,策展人。先后毕业于法国巴黎第十大学与北京电影学院,以论文《作为档案的电影》(Film as Archive)获得电影历史与理论博士学位;并作为资深编辑在《艺术论坛》(Artforum)中文网工作多年;现任教于中央戏剧学院,并担任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特约研究员与《艺术论坛》中文网特约编辑。
他长期致力于当代艺术与电影研究之间的跨领域工作,曾发起并策划多项运动-影像的展览与放映活动,如“王兵:经验与贫乏”(魔金石空间,北京),“新冶金者”(Julia Stoschek Collection,杜塞尔多夫),“刘窗:在地宇宙”(乔空间,上海),“反投影:中国早期录像艺术中的媒体雕塑”(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微纪元”(Nationalgalerie,柏林)等;并担任过北京独立影像展(2012)、中国独立影像展(2013)、FIRST青年电影展(2016)与北京国际短片联展(2017)的评委,以及“拜德雅‧人文丛书”与“新迷影丛书”的编委会委员。他亦曾为艺术家曹斐、奥玛‧法斯特(Omer Fast)、劳拉‧普罗沃斯特(Laure Prouvost)等艺术家撰写画册文章。目前主要从事当代运动-影像理论、媒体考古学与新物质主义方面的研究。其博士论文《作为档案的电影》即将付梓。

厉槟源
1985年生于中国湖南永州,201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厉槟源通过行动、录像和行为艺术表演介入日常中国社会的不同领域,探索身体、物质、观念认知和社会价值。其艺术实践占据了城市和农村空间,包括公共空间,自然环境或偏远的后工业区。正如Murray Mckenzie所言:“厉槟源是一位具有雕塑意识的行为艺术家,他征用身体——有时候还有烟火、刀具和其他义肢一般的身体延伸——作为探索不同场域的临时干预装置。”他艺术实践的动机是通过身体互动来了解自己所处的空间和物质环境,以便质疑和超越我们对环境所强加的规范和意识形态。
厉槟源的近期个展包括:“汲取”(MU艺术中心,荷兰,埃因霍温,2019),“土地——张洹和厉槟源双个展”(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PS1分馆,美国,纽约,2018)、“众重行事” (华人当代艺术中心,英国,曼彻斯特,2015)、“谁的梦”(今日美术馆,中国,北京,2014) 等。群展包括“农耕地——当生活通过当地农业变成艺术时”(青森县立美术馆,日本,2019)、“柏林-北京:视觉转换”(德国国家摄影博物馆,柏林,2019)、“身体研究”(莱比锡当代艺术美术馆,德国,2019)、“街道·世界生成之处”(罗马国立二十一世纪美术馆, 意大利,罗马,2018)、“家的变迁”(金泽21世纪美术馆,日本,金泽市,2018)、“邪恶的词典——江原道国际双年展”(韩国,江原道,2018)、“回放——皮埃尔·于贝尔电影与录像收藏展”(OCAT上海馆,2015)、“瑞典OpenART双年展”(厄勒布鲁市美术馆,瑞典,2015)、“MOFO2015”(新旧艺术博物馆,澳洲,霍巴特, 2015)、“八种可能路径”(Uferhallen,柏林,2014)、“小跃进”(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2014)、“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卡布索美术馆,挪威,2013)、“不合作方式-2”(格罗宁根美术馆, 荷兰,2013)等。

付了了
昊美术馆策展人,她的策展研究涉及社会经济体系中的艺术介入和理论批判、技术发展与人类处境的关系、表演性与参与式艺术实践等。她曾经为丹尼尔·阿尔轩、托马斯·赫赛豪恩、何子彦艺术家策划个展,策划群展包括“严肃游戏”、“流动者会议”等。
编辑:Cora&雷灵
* 点击以下链接了解更多展览相关内容:

票务信息
![]()
![]()

普通票
¥30
使用期限
2019.11.23-2020.03.15
(展期内均可使用)
观展时间
周二至周五:13:00-22:00
周末及节假日:10:00-22:00
(21:30后停止入馆)
扫码购票

昊美术馆

HOW Art Museum
(Engl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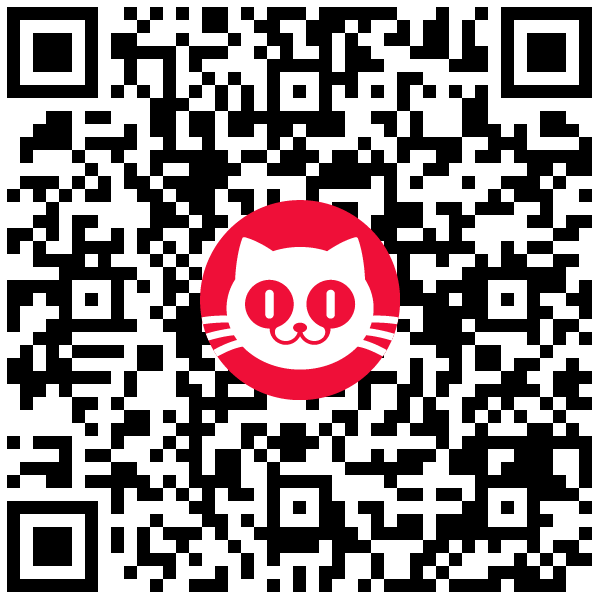
猫眼

大麦

摩天轮

昊美术馆(上海)
HOW ART MUSEUM (SHANGHAI)

图片©昊美术馆
昊美术馆(上海)是具备当代艺术收藏、陈列、研究和教育功能的全新文化机构,坐落于上海浦东,共有三层展览和活动空间,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于2017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昊美术馆首创“夜间美术馆”的运营模式,常规对外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五下午1点至夜间10点,周末及节假日开放时间为上午10点至夜间10点。此举能让更多观众在工作之余前来美术馆观展,昊美术馆也举办“国际策展人驻留项目”、“户外电影节”、“雕塑公园”等国际交流项目和户外活动,以此建立全新的艺术综合体和浦东新地标。
昊美术馆(温州)
HOW ART MUSEUM (WEN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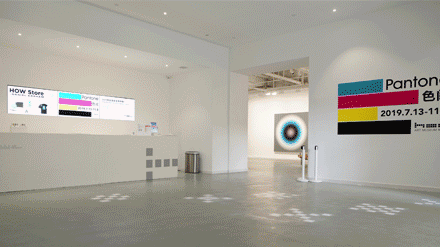
图片©昊美术馆
昊美术馆(温州)延续昊美术馆(上海)的“夜间美术馆”运营模式,是浙江省首家"夜间美术馆",常规对外开放时间为下午1点到夜间10点,周末及节假日开放时间将向前延长为上午10点至夜间10点。昊美术馆(温州)将持续为公众呈现丰富的公共教育及户外艺术项目,引领融合艺术、设计、科技的全新生活方式。
即将展出 Upcoming
昊美术馆(上海)
HOW ART MUSEUM (SHANGHAI)
昊美术馆(温州)
HOW ART MUSEUM (WENZH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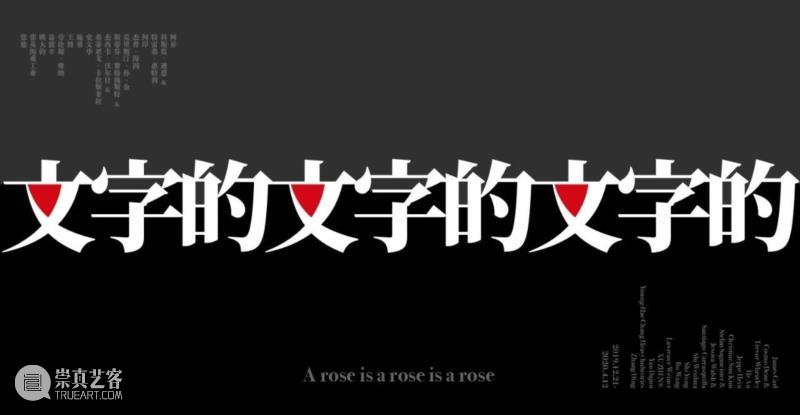
正在展出 Current
昊美术馆(上海)
HOW ART MUSEUM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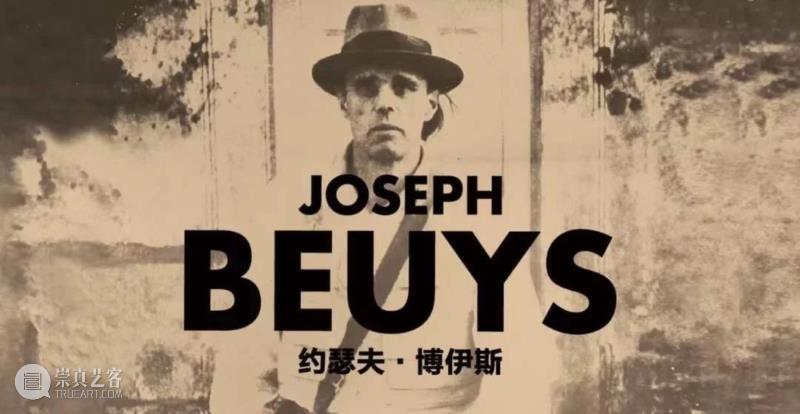
昊美术馆(温州)
HOW ART MUSEUM (WENZHOU)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