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5日@武汉·2019 “《艺术》谷文达回顾展”在合美术馆开幕当天,武汉纺织大学时尚与美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贤根教授带领传媒学院艺术学理论研究生到合馆观展。
他们细细品读了谷文达的展览作品,在老师的指引下走进谷文达的文字世界。领略了谷文达四十年来的艺术实践活动后,深深地被这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所打动,于是,他们尝试用文字与谷文达这样对话。


合美术馆的谷文达回顾展以“艺术”为题,像“艺术的故事”一样展现了谷文达四十年的艺术旅程。展览分为四个不同的系列:首先是当代创新水墨艺术,令人印象深刻的《超现实的地平线》与《静止的森林》,打破传统水墨画的框架,将传统水墨画的技巧与西方现代主义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汉字也成为谷文达水墨艺术的表现手段,他以漏字、错字、伪字开辟了国内观念水墨的先端,并完成了《遗失的王朝-静则生灵》这样的水墨装置艺术。不得不说,这种反传统的表现形式也恰好成就了传统。
其次是语言和翻译。从碑林到《简词典》,谷式通过词典的形式将不同的汉字重新组合,从室内到户外、从平面到三维的不同形态展示了传统与当代的结合,让观者感受到文本所诉说的历史故事。再次是生物时代之谜。在谷文达《联合国》系列装置作品中,以全球600万人的头发基因创作出的长城、装置、伪汉英语合并体,不仅从艺术形式上有很大突破,也体现出艺术作品的社会性。
最后是大众当代艺术日。这是由公众介入的一种行为艺术,从《天堂红灯》到《青绿山水画的故事》,都是由成千上万的小学生共同完成,展示出了谷文达艺术作品的时代性与参与性,与其他作品一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谷文达是中国艺坛反叛意识最强、破坏性最大的国际知名当代艺术家。上世纪80年代他用错位、肢解的书法文字做水墨画,并影响了后来一代艺术家。史密斯曾经称他为“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来自中国的新生代前卫艺术家代表人物”。这次谷文达回顾展选择以“艺术”这样一个开放的词作为展览的主题,它既可以很深奥,也可以很通俗,亦或是很有人情味。就像海报上合成的四个词:信仰、执着、挑战、超越,便是对谷文达作品最好的概括。
谷文达以传统水墨起步,到后来的抽象水墨和实验性水墨,都是通过水墨表现个人主义和反叛精神。他的艺术创作总体分为三个阶段,从制造伪文字水墨画到水墨行为艺术再到水墨装置艺术,最后阶段尤为重要。谷文达对材料的使用:比如人的头发、婴儿的胎盘等等曾遭到颇大争议。他解释说:“只有人体材料,才既是主体又是对象。我的意图是用人发装置艺术和所有的人进行交流,因为每个人的头发中都隐藏着基因密码,都代表着每个人的个性以及种族属性。”的确如此,最本质也最能打动人的不是普通的物质材料,而是人体物质本身。
金·莱文曾写道:“头发所表现出的不仅是男女性气质,更是种族、民族和年龄。而正如历史所证——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辫子,到法国君主时期象征权力的假发,从军中平头到嬉皮蓬乱长发或爆炸头,我们如何塑造头皮表现出来自社会政治和精神文化的影响。”看谷文达后期的作品,个人主义思想不再那么凸显,更多的是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文化结合,强调对传统的继承与转变,谷文达成为国际上推崇水墨艺术的文化使者。

实际上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而已。在艺术史发展的时区里,艺术家赋予了作品生命力,使之成为艺术作品。当下,艺术一词被赋予太多内涵,谷文达在回顾艺术历程时,给予了它独特的意义,信仰、执着、挑战、超越,是他对艺术人生的思考和总结。他以讲述艺术故事的方式将作品带入大众视野,从水墨书法到大众当代艺术,从《联合国》到《天堂红灯》,无一不体现当代艺术卓越的时代性。
观谷文达作品,他将视角放在当代公共艺术上,他的艺术离不开城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一定和中国本土的文化有关系,这点正体现在他的作品《基因与蜕变》中。谷文达通过现代艺术手法,传承和发扬“孝”这一传统文化,由千名孩童在一千平米的红丝绸上书写下孝经,以此方式表达孝道,用独具匠心的当代艺术来表达情感,凸现了当代公共艺术的时代性。
谷文达表示:希望通过新公共艺术展示,向公众提供一个向祖先表达孝道的机会,希望能够推动大众对传统艺术文化的认识,促进社会与公众对当代文化艺术认知的普及,让当代艺术成为大众生活的一分。这是他对当代公共艺术的态度,也是公共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性标志。

《碑林 - 唐诗后著》
石碑#1-#50装置艺术 ,每块碑110cm x 190cm x 20cm,重1.3吨,1993-2005年创作于中国西安谷文达石刻工作室



“对于艺术家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通过历史去拓宽人类认知的界限,情感、思想和表达人性中最深刻的向往以及最有力量的理想。”这是《艺术史》中提到谷文达时的词条,谷文达就是一个将大同世界的乌托邦与现实社会连接起来的艺术家。谷文达是一名野心勃勃的理想主义艺术家,对文字水墨的执着贯穿始终,好大喜公。观念融入个性,表现在艺术中,但现在的艺术同质化大于差异性,谷文达的特别显得尤为珍贵,他的艺术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交错调整,不断回到自己的起点。
这次回顾展的主题是信仰、执着、挑战与超越,我想这八个字除了是这次回顾展的主题,更是他一直以来的创作主题和观念延伸,从早年对水墨的实验,随后反叛到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批判,从联合国系列的创作到回国之后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文字系列的产生,传统的基因在他的作品中毁灭重生,他用解构的手段达到建构的目的,从古墨起步,将古墨与当代艺术相结合去超越古墨的边界,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再创造。在他的《联合国》中,用头发做成的艺术品,带给人的除了视觉上的冲击,更是心灵上的冲击。
如他自己所说,过程就是目的,在创造的过程中,他感受到历史带来的冲击震撼,并通过艺术传达出来,他有着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从无国界划分。

参观了“艺术——谷文达回顾展”,感受颇深。谷文达以40年40国的艺术旅程,为古老的中国水墨语言在国际上找到通道和出口,被当代艺术界称为“文化使者”。作为当代实验水墨的奠基者,谷文达的水墨实验主要围绕“文字图像”“文化语词”和“生物材料”三项观念课题展开,涉及到哲学、文化学、语言学、生物学和艺术史等广泛领域。
谷文达善于用人的头发和胎盘进行创作,他认为只有人体材料,才既是主体又是对象。他的意图是用人发装置艺术和所有的人进行交流,因为每个人的头发中都隐藏着基因密码,都代表着每个人的个性以及种族属性。他的作品《联合国》系列出自全球各地600万人的捐献,这在艺术史上史无前例。人的头发可以作为政治、文化、种族和性别观念的表达,他试图把世界上所有人联合在一起,让不同的文化进入到作品中。
谷文达将生物科学和语言学融入到艺术创作中,是无比新奇和震撼的,谷文达对艺术的创新和贡献感染着我们,吸引着我们,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谷文达是当代艺术潮流的先锋。他的作品格局大开大合,以对西方艺术的全方位批判和实验为手段,结合自己中国艺术的传统基因,创作出了超越民族性的,有国际性视野的艺术品。虽然他的作品属于当代艺术,但他依旧没有完全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像他水墨实验类型的艺术作品是将母语文化重新构建,创作出新的表达方式。他要把中国艺术与世界艺术无缝对接,形成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打开方式。我最喜欢的作品是《碑林》系列,每一块石碑上的文字都是谷文达自创的结构,同时他又用使用了正楷的书写方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谷式特色。

谷文达自1993年开始实施《联合国》这一大型装置艺术计划,如今全球已有近六百万人为之捐献了头发,《联合国》以手工胶粘方式结成了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旗帜和文化符号。谷文达对头发材质的选择和粘结头发的天才创意,向世人证实当代艺术已不只是单纯的技艺表现,而是人类各种文明成果的相互渗透和综合智慧。头发这一特殊的艺术媒介蕴藏着绝少相同的人类基因,涉及了人类的宗教、文明、历史、政治等元素。谷文达这一形式跨越国家和人种、政治与文化、年代与世纪,来表现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族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团结。
除此之外,头发这一质料的运用体现了当代艺术家对于人类命运、文化趋势等宏大话题的无限关怀。谷文达认为唯一能避免用客体来表现主体的途径是用主体来表现主体,《联合国》对头发的取材则还原到人的本质属性,这种返本于内,至大无外的关怀,是对人类诸多问题的集中关照。置身《联合国》中,既可以兴奋于陌生隔距的视觉震撼,也可以细细咀嚼血肉牵连于你的人生滋味;既可以感受到历史和传统的深厚积淀,也可深思当代存在的问题与困惑。一个人类伟大的理想——“联合国” , 在现实中是几乎或永远无法实现的,但谷文达让其在艺术中实现。

《联合国-血肉长城》
1500块中国人发砖,人发帘1220厘米长X 732厘米宽2001于上海工作室

《“天堂红灯上海站”》
25500阻燃布制钢口灯笼、脚手架、钢绳,100米长X85米宽x23.5米高,2014年起对上海21世纪民生美术馆体实施设计方案


谷文达先生从事艺术创作40年来一直在探索创新,多年游走中西方文化的经历,让他不断去发掘当代艺术的意义与边界。另我感兴趣的是他所提出的“全主义艺术”的概念,作品创作中强调艺术的大众参与性。比如1992年开始的《联合国》系列,有全球500万人捐献的头发在里面,2014年广东佛山的1060名儿童在红绸缎上书写的《孝经》,2016年在深圳和1500余名学生共同绘制的《青绿山水画故事》都体现了他注重作品的沟通性和人文关怀,让观众亲身参与创作,能够更容易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曾在《艺术论》中谈到“唤起心中曾经体验过的情感,然后借由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语言表达出的形象,使他人也能体验相同的情感——这便是艺术活动”,谷文达用他的创作拉进了与观众的距离,让他们能够把艺术作为一种交流手段,并用情感将人类紧紧相连。


自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建立以来,西方艺术的中心便由巴黎转向了纽约,美国人大推现代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使“非艺术”成为“艺术”,艺术品与寻常物的差别被消解了,不客气的说这是美国文化扩张的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是打倒旧主(古典主义和巴黎),拥立新王(现代主义与纽约)。《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不得不说美国人对艺术的变法是成功的,美国的艺术中心不是迁移过来的,而是营造出来的。现当代艺术彻底解放了思想,但也将艺术变得光怪陆离。如今当代艺术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该如何走,谷文达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谷文达将艺术与政治、科学、文化、人种等诸多宏大命题联系起来,以艺术作品关照当代问题。他的作品《联合国-血肉长城》将200万中国人的头发做成发砖,1500块与明代长城城砖同等大小的发砖被砌成烽火台,带来了极具震撼的效果;《联合国-绿宫》则以几十万美国人的头发,做成了大型装置作品。《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在古代中国头发对我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头发象征着婚姻、阶级甚至是生命,于是出现了“结发夫妻”“削发明志”“割发代首”等极具中国意味的文化与行为。谷文达的眼光是非常独到的,他敏锐地捕捉到了头发这一重要介质,这正是中西文化的根脉所在。
他的另一件作品《天堂红灯》也另我印象深刻,《天堂红灯》由两万多枚八彩灯笼组成,它们将上海21世纪民生美术馆的主体建筑牢牢包裹起来,多彩的灯笼在阳光照射下,金光闪闪蔚为壮观。值得注意的是灯笼也是极具中国化的产物,早在西汉时期我们便有了张灯结彩的风俗,后来灯笼上加了寄语,就变成了孔明灯、许愿灯,还衍生出了打灯谜等节日活动。有趣的是谷文达将他个人特色的文字组合“西游记”绘于每枚灯笼上,“西游”不仅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敬,也正是他近些年旅居海外的写照。谷文达说,三十二年的西方生活经历,使得他能更好地看清楚东方,有了世界视野的铺陈他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中国当代艺术究竟该怎么走,我想谷文达的艺术实践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聚焦中国,放眼世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谷文达通过他历时十年完成的“碑林-唐诗后著”对文本和文化的翻译作了一个视觉的陈述。这件大作品涉及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与再翻译,而其文本被镌刻于50块大石碑上,同时也制作了50张拓片。首先是英文翻译,然后英文版本发音的中文回译,最后是艺术家自己根据“第三版本”翻译的英文“诗”。这些作品在文本的相互转换之间告诉我们,误读甚至歪曲在翻译中常常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结果。当不同背景的人们在沟通中常常会有混淆、误解和挫折时,将一个古典的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以特定文化为底蕴的语言往往会带来一些啼笑皆非的闹剧。谷文达通过这样一种视觉艺术形式直接展示出文化间的差异以及相互沟通的困难和荒诞。


在后现代的哲学思想中,德里达以解构主义来反对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主张通过文字来取代语言的本体性地位。而维特根斯坦与其老师罗素在语言学问题上的争辩,对谷文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认为文字或者语言并不能够揭示或者一一对应世界的万物与知识,这随即产生了他对文字本身的不信任以及对传统艺术与文字的解构。通过书法、正字与反字、对字和错字等各种不同的文字形式,他希望能够将这些传统文化中的象形符号与整个西方现代艺术相区分,从而形成一套自我的反中国传统艺术的形式。这如同他所崇尚的杜尚的现成品艺术一般,杜尚以一种反传统审美的方式宣告了古典艺术的终结,而谷文达则在中国水墨画中找到了目标,他的“实验水墨”便是他通过艺术的表征方式来对传统水墨画发起的挑战。他大胆地将中国传统水墨画与文字结合,水墨的抽象与文字的具象,既达到了表意的效果,又极大程度上远离了现代艺术的普遍特质。

《血之谜(重新发现的俄狄浦斯系列)》
四张床,裝置艺术,人的胎盘粉(来自正常﹐非正常﹐堕胎﹐死婴的胎盘),1993年创作于美国纽约

24节气与人体24节脊椎骨中枢神经构成“天象-人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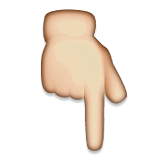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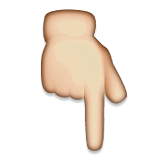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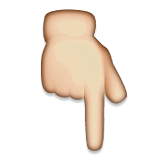

2019.12.15 - 2020.05.15
黄立平
合美术馆1-7号厅
布莱恩·肯尼迪 & 鲁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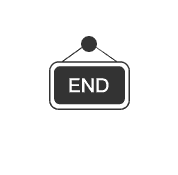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