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时的机器Ⅰ
(1960年)
京特·安德斯丨文 范捷平丨译
节选自《过时的人》第二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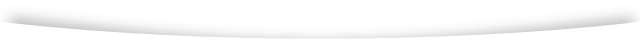
§1
机器的梦幻
机器世界的胜利在于它造成了科学技术产品和社会产品之间的差异,并且将这种差异变得让人无法看清。一家企业中的机器设备若要工作,那么就要与无数其他的机器功能配套,这些机器设备从电话到数据处理穿孔机都是机器的一个部分,就像机器(德语Apparat)这个词的本意一样。机器就是物理的、技术的物,这点在它的名字里面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不仅如此,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一台机器中蕴含的能量和功效越大,机器的理念就越能得到完全的实现。事实上,假如某台机器没有融入整个机器整体,而只是个别的、字面上的所谓的机器,那么它就不能真正起到有意义的作用,只说机器而缺少了原材料和劳动目的如产品的营销等则没有意义。今天的所谓“企业经济学”按照其自身的倾向来看,无非是一种将两种不同的机器形式放在一起教学的尝试。无论怎么说,宏观机器的运作是微观机器运作的前提,而从宏观机器视角出发来看,微观机器已经降格到了机器零件的地位,同样,假如宏观机器想要正常顺利地运作,那么它说到底还必须与其他所有宏观机器体系的运作达到协调。无论这个结果听上去多么美妙,这样的状况说明一点,机器设备从本质上讲应该调控到一种“理想的状态”上去,在这样的状况下,最后只存有惟一的一台毫无缺陷的机器,也就是一台将所有的机器都在其中得到 “扬弃”的机器,只要这台机器正常运作,其他的所有机器也就正常运作了。
这样,我们终于替我们的想法找到了一个核心概念。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机器世界实际上只是一种将来式,我们只有在此之中才能窥透(durchschauen)其目的意念。因此,我们必须尝试来揭示这个目的状态,最起码应该来尝试揭示这个状态的发展趋势。
§2
机器=世界
假如所有的机器融合成了惟一的一台机器(因为此中蕴含着上述的目的状态),那么我们所说的“一切都会顺利运作”不再仅仅只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在孤立的机器“内部”不发生任何故障,而是说明机器根本不存在什么“外部”的概念(如同哲学体系那样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外部环境)。机器世界成功地涵盖了一切,所有可以想到的功能都被机器囊括,所有现存的物都获得机器的功能,所有在机器世界中出生的人都成为机器操纵者而融入这个世界,一言以蔽之:“所有的都正常运作”可以总结为一个公式,那就是“机器=世界"。虽然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在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前进,我们虽然还在路上,但是我们已经是“候选人”,我们正在自豪地成为“机器宇宙”中的组成部分。
机器不仅自己是如此,而且机器之间也是如此。不仅机器之间是如此,而且所有现存的“物”都是如此。假如我们在这里提出“机器存在论”,以提出机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以及机器的存在本质问题,那么第一个原则性的答案就是:每一个物从自身的视角出发看都是机器的一部分。或者更加准确地说:只有向机器出卖自身的,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3
掠夺的存在论
将原材料、能源、物和人称为“自身”实属荒诞。它们只有被称为“自身”的企求。即便在最为平常的“有东西”(es gibt Dinge)这句话中,存在论的意义也已经遭到了颠覆,“存有”、“状态”、“数据”等已经变得陌生。无法获取的、无法掠夺到的就不再是“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存在”和“得到”的词义可以相互置换,存在即掠夺(esse=capi) ,“世界”只是一种虚幻的占有区域,能源、物、人说到底只是机器可获得的材料。从严格的意义上看,它们作为材料只在被机器利用、被机器融合的那一刻起才被认可为“此在”,也就是被强制性地要求在一起发挥作用。这时,机器是否将这些掠夺物在狭义上当做原材料或者机器的某个部分还是消费者来加以利用则完全不重要了,因为原材料和消费者都属于机器运作的范畴。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们也都是“机器的某一部分”。
十九世纪曾经有一个低级的机械世界理论,它将世界描述为宇宙的一种实际状态,当年这种观点只是为了将世界视为机器劳动的整体,而今天这已经成了机器的目的,对于机器来说,整个宇宙都应该成为机器,以往友好地向人类微笑的月亮已经不再孤独,许许多多小月亮被送上了天,成了电视转播卫星,它们作为信息源竭诚地为自己转化为机器宇宙而服务。
§4
幸福的王国
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拉美特利(La Mettrie)提出了一个与上述观点相符的所谓“人即机器”理论。现在这个理论变成了前提,即我们人必须将自身转化为机器或大机器中的一部分,最终成为机器。而其实这个最终目的就在于机器本身的目的,但这点在每一台具体的机器中却不会实现。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所有的具体机器都是宏观机器中的某一部分,它们都融化在宏观机器之中。所有的机器从一诞生起就在梦想一个机器转世论的幸福王国,今天它们继续在做着这个美梦,因为只要它们尚未完全融入和完全受宏观机器的操纵,它们的效应就尚未达到最优化,那么它们作为单独的机器就会诅咒自己,就会不断地继续做自己的美梦。它们顽固地坚持“科学技术原罪”的立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定律是“个体即否定”(indivituatio sive negatio)。在斯宾诺莎看来,个体割裂的存在就是非完整的存在,也就是悲惨的自我信念。或者我们可以不那么形而上地来表述:由于从本质上看,机器生来就具有扩张性和包容性,也就是说,机器极力试图不错过任何可以发挥作用的机会,不,机器恰恰没有能力不去执行它们能够完成的功能,因此,当机器还没有完全侵吞一切的时候,比如说那些与机器“离心离德”存在的物或者人,或者那些对机器不忠诚的力量,竟然胆敢独立行事不听机器指令,或者那些可以继续抵制机器的真空地带,或者那些还继续抵制成为再生性原材料的垃圾等等,只要这些领域尚未被机器全盘统治,那么就不能说机器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在机器的眼里,每一小块尚未占领的处女地都是它们痛苦的理由,宇宙中每一颗遥远的星辰都是它们错过的机会,不,都是它们错过的任务,或者是错过的责任,因此也是它们的羞愧。当机器感觉到自己“个体和整体”(hen kai pan)都成了现实,或者感觉到“机器即上帝”( deus sive maschina)的荣耀,也就是感觉到自身充分得到发挥,感觉到自己降格为杠杆、螺丝、燃料等而全部融入机器并且和整个机器世界共同作用,那么它们才会因为自己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而感到幸福。
§5
绝对的宰制
这种机器宇宙所蕴含的灾难性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机器之间绝对的相互依存关系成为现实的话(这点在所有的机器都降格为机器部件的时候会发生),那么只要某一个机器零件发生故障就会自动地影响到整台机器,也就是说整台机器就会停止工作。很明显,“绝对机器”从自身利益出发是不愿意“绝对地绝对化”的,而是愿意让其部件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大机器会保障其部件的相对独立性。大机器在部件面前的绝对定律是:我需要你,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我不需要你。我们在这里无法继续深究这一“物的社会学”领域里的辩证法。
十几年前,德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当时纳粹分子甚至将它写在标语牌上招摇过市:“……明天就是整个世界。”这种刺耳的绝对宰制的口号今天虽然听不到了,但是如果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足够敏感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听到诸如当年纳粹口号的那种声音,那就是机器的声音,我们甚至从今天无声的忙碌中也能听到这种声音,因为这种不断出现的声音来自科学技术。今天科学技术的统治地位丝毫不逊于过去,它甚至比过去更加具有统治力,早在纳粹的这个口号出现之前就出现了机器令人可怕的声音。纳粹的口号与机器铁的嘴唇里吐出的声音丝毫没有区别。当年的纳粹分子正是继承了机器铁的衣钵,让自己作为法西斯国家机器中的零件而声嘶力竭地在大街上高喊着口号游行。
§6
单一性的最后状态
假如真的存在着一种“物的社会学”,那么它的假设也许会是“从来没有单独的机器”。每台机器都是政治动物(zoon politikon),机器若在“机器社会”之外,诸如鲁滨孙式的物没有任何作用。“社会”这个词不仅仅只是描述机器的集合,不是千百万同样的机器以及它们的数量,而是指与机器形态相似的关系,即给机器提供存在条件的,供机器赖以存在、维修保养的,由加工原料、生产者、消费者、配套设备组成的生存大环境。要让单独的机器能够完美地运转,则需要一个同样完美的环境来作保障,这样,这个环境自身也就成了机器。如果“机器a”从物理性上看只是一台鲁滨孙式的机器(我们知道这是虚构),但是它是在某一个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在某家工厂里运转,并且成为工厂里的一部分,假如这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说“机器a”需要一个世界,以保证自己能够最优化地工作,而这个世界自己也应该是由机器组成,也就是一台宏观的大“机器A”。这个大机器给予小机器存在的环境,也就是给予“机器a”一个结构性的、功能性的补充以及扩展。当然,这样的需求是容易的,但是要实现这个需求就不那么容易了。不,“机器A”这样理想的需求甚至从原则上说应该是无法实现的,其原因是:单个的机器((a到∞)需要各自的单一性,它们试图将自己所在工作的世界按照自己的形态来进行塑造,但是这样的世界很难按照机器自己的意愿形成,就像每个不同的人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建造世界一样困难。因此,每一台机器都必须虚心地与千千万万其他机器(a到∞)一起来共享机器世界。只有在所有小机器自我否定并成为机器大家庭的一员之后,也就是说,只有它们共同地为一台大机器的胜利而工作的时候,它们才能够真正完美地与宏观大机器协调运转。这是为了达到一种单一状态的宰制性,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一台小机器都被迫降格为大机器的某一个零配件。在这样的降格羞愧下,单个的机器方能换取完美的运转。这种成为机器大家庭中一员的争斗尚未结束,但这场争斗早就已经开场(其实第一台机器出现后,这场争斗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胜负已经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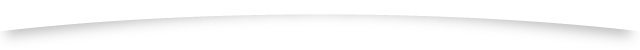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