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回归“正常”如此艰难?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 PLAIN Magazine
常听人说起,他们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整体社会氛围:人人都在谈论萨特,朦胧诗盛行,邓丽君、霹雳舞、地摊儿文学……但这种怀旧禁不住仔细的推敲。实际上,如果套用今天文章的主题,那个年代恰恰是一个不怎么正常的年代:官倒,物价飞涨,出国潮,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处在一种激烈的动荡和转折过程中。这种怀旧其实往往是一种对于当下缺失安全感的代偿。
所以,“正常”与“非正常”其实是充满变量的:黑人现在当然可以和白人同校,但这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是不可想像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同性恋者在美国等很多国家已被视为正常,但如果他们处在伊朗、也门或者苏丹,其行为非但不是正常的,而且是违法的。
歌单陆续更新中
在虾米、网易云、QQ音乐上搜索
【利维坦歌单】即可获取
此刻我正穿着睡衣,坐在家里 写这篇文章。近期我需要遵循居家令,也就是说,除了购物或医疗需要等特定情况,不得离开家半步。这还意味着我不需要遵守办公室着装要求。一个多月来,除了丈夫以及邻居之外,我没有和任何人有过实际接触。我通过视频聊天和父母通话,通过Facebook Messenger和其他家人聊天。朋友们时不时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自己的状态,因此我能知晓他们的最近生活。我大部分购物都通过网购实现,每天只有一小部分时间待在户外。
这多么不正常啊!即便在新冠病毒爆发之前,我也经常在家写作,用各种软件联系家人朋友,上网购物。居家令也许以前没有过,但我不能假装社交隔离是一件从未有过的事情。近年来,科技和社交媒体已经将我们彼此分隔开了。当然,我是幸运的那一方。如今,地方经济步履蹒跚,医疗系统应对不暇,人们不断地意外失去亲密的人,遗憾自己没能在最后的时候伴其左右。这使得许多人开始思考“常态”:什么时候才能“回归正常”,而“新的常态”又会是什么样?一篇名为《我们所知道的生活》(Life As We Know It)的文章讨论了新冠肺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文章中写道:“我们总是忍不住去想什么时候一切才可以回归正常,但事实上,世界回不去了——至少不是原本的那个正常。但是我们会到达一个新常态,即便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在根本上会有所不同。”(www.thinkglobalhealth.org/article/new-normal-covid-19-next-steps-we-must-take)根据这一标准,旧常态下我们的医疗系统和政府无法应对像新冠病毒这样的大灾难,相比之下,新常态和旧常态大体相同,但我们将能够应对全球性大流行病。换句话说,新常态修正了旧常态原本错误的事情而保留了正确的事情。但如果旧常态不正确,为什么我们还要称其为正常呢?同样的,如果新常态不同于旧常态,我们又怎么能说自己仍然处于“正常”之中呢?“正常”(normal)一词简单明了。但正如很多其他词汇一样,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这个词的意思,它就不再那么简单了。比如,韦氏词典里“normal”的第一个解释是“符合某种类型、标准或规律的模式”,例如:“他有个正常的童年”。同样地,词典上继续解释:“遵循,符合,或不偏离一种常规、规则或原则。”
在一个精彩的哲学谈话播客中,哲学家查尔斯·斯科特(Charles Scott)指出,“正常”一词包含某种权力,即“区分和辨别事物的力量”。这个词看似是一种描述,实则是一种规定。我们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大多数人都是异性恋),快速构建出一套等级制度,为首的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异性恋是最自然的性取向)。分类所基于的事实就成为了标准或者规范,任何偏离这一规范的事情不仅仅是有差异的,而且是不正常的,因此低于正常水平。但正如斯科特所提问的那样,为什么我们认为正常要比不正常更好呢?在美国,肥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这样来看,许多医生似乎都建议他们的病人变得不正常。斯科特的意思是,我们对于正常的概念引出了一种双重责任;除了告诉我们什么“是”正常的以外,还指出正常“应该是”什么样的。
不经意的善举即便很稀缺,在理想的状态下也可能被视为是正常的。
正如社会学家艾伦·霍洛维茨(Allan Horowitz)指出的那样,我们所面临的“常态”困境指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正式的规则或标准来界定什么情况是正常的”。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定义“正常”的人通常会从三种不同方法中的选择一种。第一种方法是通过数据来定义,“即‘正常’是一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正常”是一种典型状况,是大多数人会做的事——也就是说任何个人行为都不可能是“正常的”。
(www.jstor.org/stable/41801169?seq=1)人多有两条腿,能呼吸,有社交欲望,因此这些情况就被视为“正常”。通过这种办法来定义正常的问题是,它会让我们陷入认为“数据上的多数即为好”的陷阱。霍洛维兹举了个例子,20世纪30至40年代纳粹党执政时,大多数德国人支持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的政策,那么,难道纳粹主义就是人们应该持有的一种“正常的”观念吗?
1941年,众人在国会大厦向希特勒行纳粹礼。© 维基
霍洛维兹说到,第二种方法来定义“正常”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来自于normal这个词的词源。在拉丁语中,norma意思是木工的方尺,可以帮助木工做出一个完美的角。方尺提供了一个有形的标准,如果遵循这个标准,就能不断复制出某一特定的样式。然而“理想的正常”和“普遍的正常”可能相吻合,但也可能截然不同。比如,德国纳粹主义盛行,但这并不是正常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希望到达的理想社会。相反,不经意的善举即便很稀缺,在理想状态下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希望同情成为领导社会的一种规范。
当定义“常态”时,我们会先从所认为的“正常”入手,而非“不正常”。© Reuters
第三种方法涉及到进化学,即“从生物学上来看,人类是如何受自然选择的影响来生活的”。此时,那些使人类能在特定环境中生存的行为即是“正常”。在这一定义下,背叛爱人时感到羞愧是正常的,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生存下去也是正常的。这三种定义“正常”的方法——(1)数据法、(2)理想法、(3)生存法——在日常交流中经常会切换使用。这在我们讨论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世界的“新常态”会是什么样时得到了充分验证。新常态意味着我们将回归疫情爆发前的生活(1),但我们的社会将变得更好(2),而这将有利于我们人类的生存(3)。因此,我们既希望又不希望世界恢复原样;我们希望一切一如往常,同时也希望有所改变;我们想要回归正常,但内心深处却知道,我们的旅程与其说是一场回归,不如说是一次启程。“正常”的定义也许很难去确定,但其作用是很清晰的:正常就是安全。面对一战带来的灾难余波,沃伦·哈定(Warren Harding,美国第二十九任总统)的总统竞选主张很简单:“美国当前急需的不是英雄行为,而是医治创伤;不是灵丹妙药,而是正常化。”哈定知道,美国人希望回归战前生活,因为战争打破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节奏和秩序。他明白,当面对恐惧时,人们渴望回到恐惧来临之前的日子。他的言辞符合公众心声,因此1920年11月2日,公众投票选举他入主白宫。最终,怀旧成为了对一个不同时代的渴望,更具体来说,是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时代的渴望。
我们可能会说,哈定和他的支持者怀念正常。我们也同样如此。

©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怀旧(Nostalgia)一词由两个希腊词语组成:一个是nostos,意思是回家,另一个是algia,意思是渴望。组合起来就是渴望回家的意思。1688年瑞士医生约翰内斯·霍弗(Johannes Hofer)在他的学术论文中创造了这个词,“用来形容渴望回归故土的悲伤情绪”。霍弗认为他的病人的主要病情是想家。(www.jstor.org/stable/pdf/44437799.pdf)怀旧本来是说渴望去某个不一样的地方。最终演变成了渴望回到某个不一样的时代,更具体来说,是渴望回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时代。斯维特拉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美国作家,著有《怀旧的未来》(The Future of Nostalgia)】写道,怀旧“是带有自我幻想的浪漫”。在《渴望天堂》(In Longing For Paradise)一书中,荣格心理学分析员马里奥·雅各比(Mario Jacoby)探索了人类盲目崇拜过去根本不存在的常态的倾向。“我们回溯了20世纪的黄金20年代,巴黎的美好时代,候鸟运动时代(译注:1896-1933年在德国青年团体间兴起的反抗政府,号召回归田园生活的运动),中世纪城市的生活,古典时代,或亚当夏娃‘堕落之前的’生活。”完美的世界大多存在于回忆之中,这是对我们当下受威胁的、支离破碎的世界的一种补偿。当定义正常时,许多人认为我们会从什么是“正常”出发,然后就像马后炮一样,再去定义什么是“不正常”。那如果反过来会怎样呢?如果我们从思考“不正常”开始,思考那些让我们非常紧张的事情,然后再去想象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无忧无虑的日子。我们不是先去思考“正常”,再去归类那些“违背正常”的情况,而是先去靠直觉找出“不正常”,再试图建立能够消除焦虑的规范,找到舒适的状态,然后再从“过去”里定位到这些规范。毕竟,这种方法比那种需要竭尽所有努力来创造“正常”的方法要容易。我们不需要从零开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返回“正常”。几个月后,我的生活就会“回归正常”。我将穿着淡紫色的睡袍坐在家里写稿,通过视频和家人聊天,为没有经常去锻炼找借口。
许多人都幻想着有了空闲时间就去学一门新技能,但当这样的时间真的到来时,我们又会被其他事情所分心。© EPA
对其他人来说,回归正常可能要更久的时间。一些企业会重新开业,有一些则会关门大吉。一些人将永远走不出ICU,一些人则会继续为饮食起居而奔波。一些政客将再次承诺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他们会提醒我们,在渡劫疫情之后要时刻保持警惕。一些人会同意政客的话,另一些则会表示鄙夷,在社交媒体上嘲弄他们。事情改变得越多,他们就越会保持原样。我们都会继续打“没有准备的仗”。而科学家和医护人员会继续试图战胜困难;在某些方面他们会取得成功,可挑战仍将继续。现代医疗不管再怎么先进,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依旧还是太年轻了。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将会”,这不仅是人类的准则,更是所有生命的准则。
在过去的5亿年里,地球经历了5次大型物种灭绝。许多科学家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第六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人类将不再是进化的顶点,会有其他的物种超越人类。然而尽管我们个人、社会和全球层面都在经历巨大的挑战,我们依然记得,我们将会回归正常。也许,如果这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坚持的话,那不是我们对正常的定义,而是对“我们将会”的坚持。我们不确定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谈论未来时,更愿意用我们熟悉的过往好时光来描绘未来,但我们知道未来一定会到来。正如20世纪初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所思考的那样,我们将继续坚持“我们将会”,这不仅是人类的准则,更是所有生命的准则。柏格森用“生命冲力”(élan vital)一词来形容一种走向开放未来的神秘动力,在这样一个未来里,似乎所有生命都充满活力。实际上,这种动力就是生活本身。柏格森说到,生活“从其起源开始,就是在同一种动力下继续向前的,这种动力使生命本身走向不同的进化路线”。不管它是什么,不管我们如何命名,它似乎都是我们的常态,即“我们将会”。文/Brandon Ambrosino
译/Rachel
校对/boomchacha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00424-why-it-will-be-so-hard-to-return-to-normal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Rachel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往期文章:
投稿邮箱:wumiaotrends@163.com
点击小程序,或“阅读原文”进店
☟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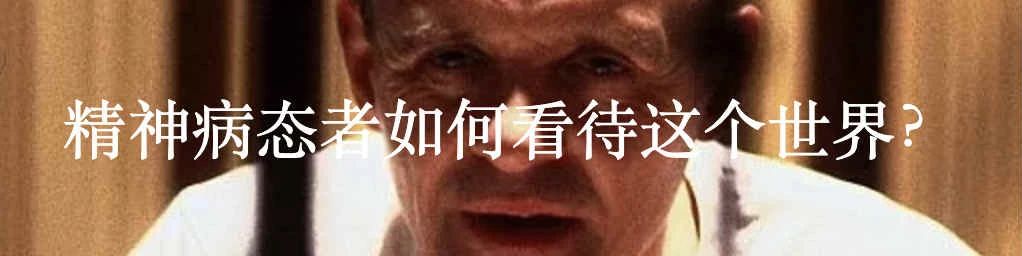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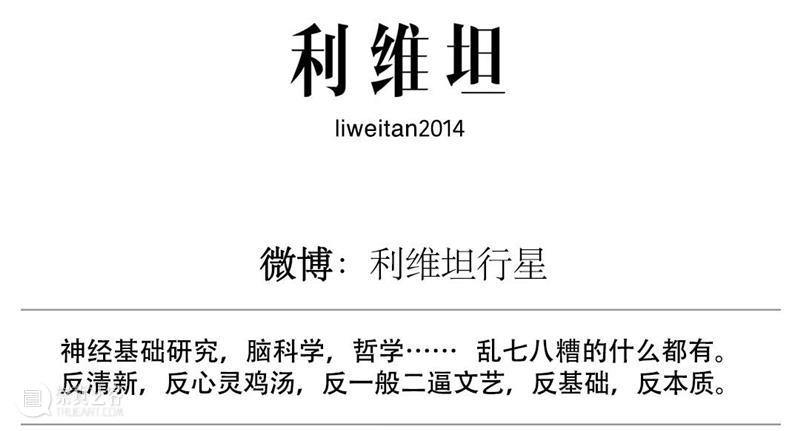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