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ndex}}/{{bigImglist.length}}
通过与艺术家对谈与讨论,揭开创作背后的神秘面纱
在解答问题的同时,检视不不同的创意过程
得以⻅习艺术家们的想法,以思考表达如何得以成形
「
我不确定我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
在这个存在中的位置
我需要相信艺术才能活下去
」
——山本昌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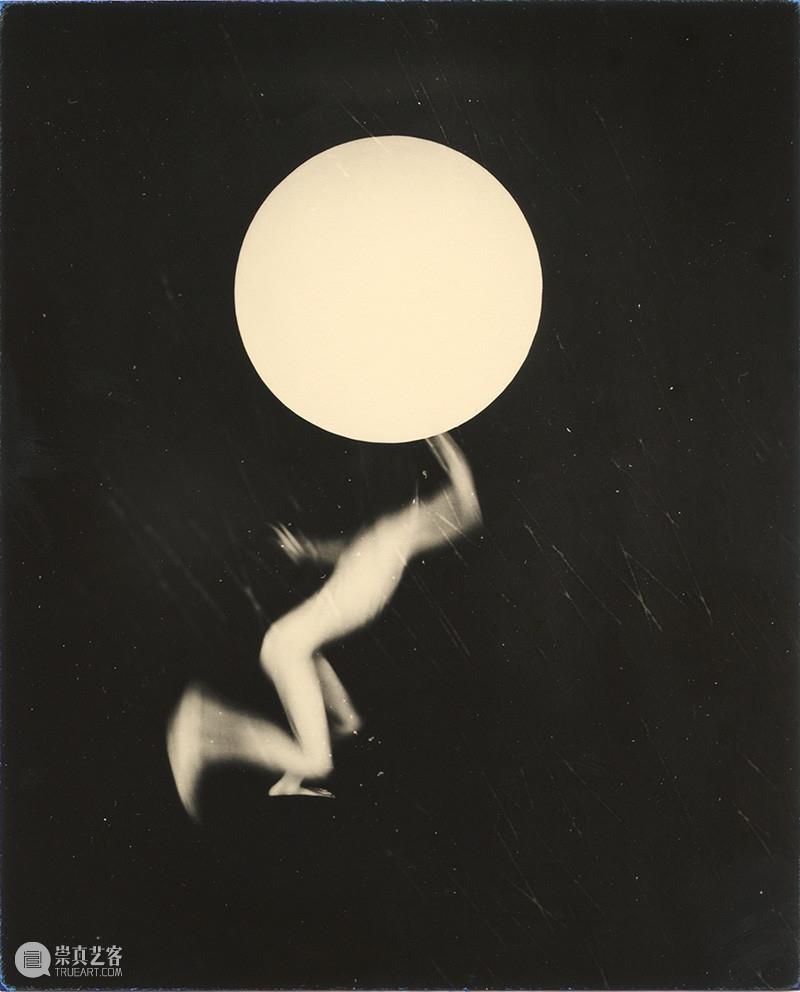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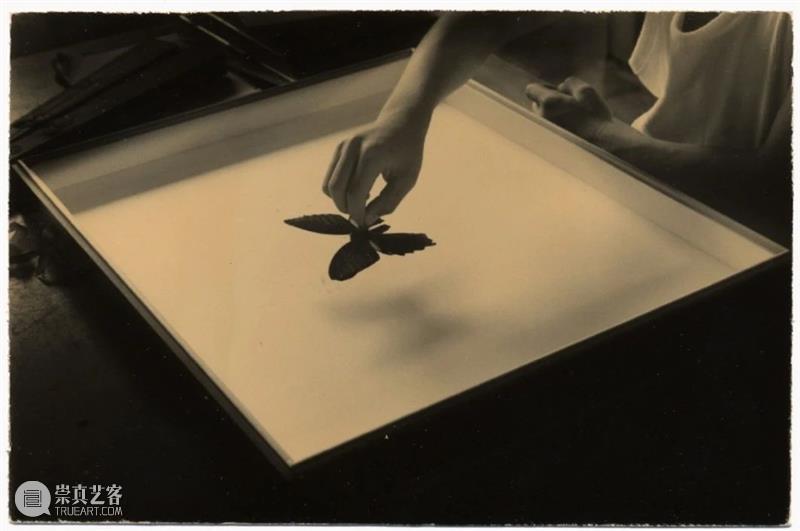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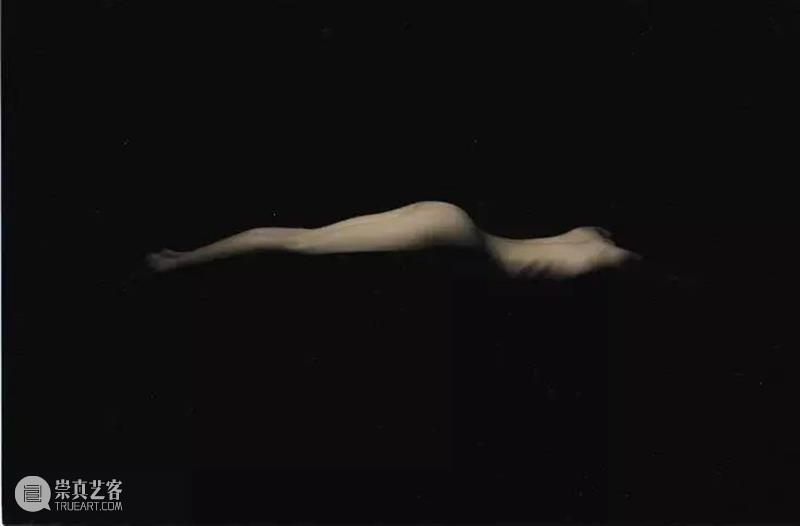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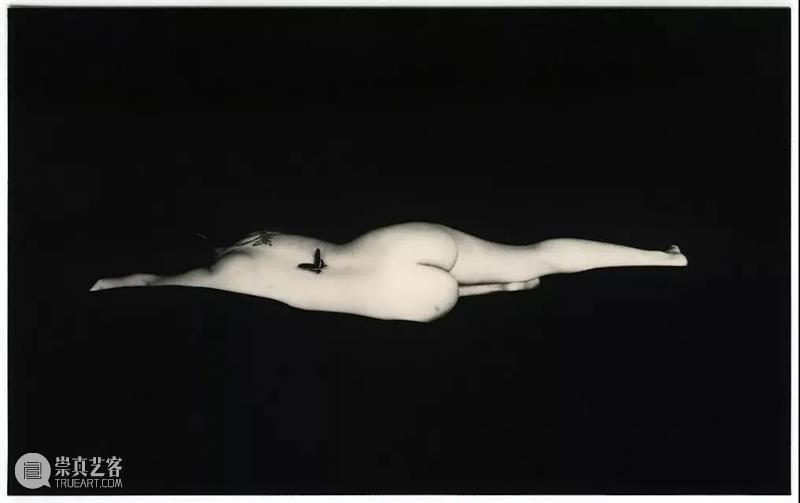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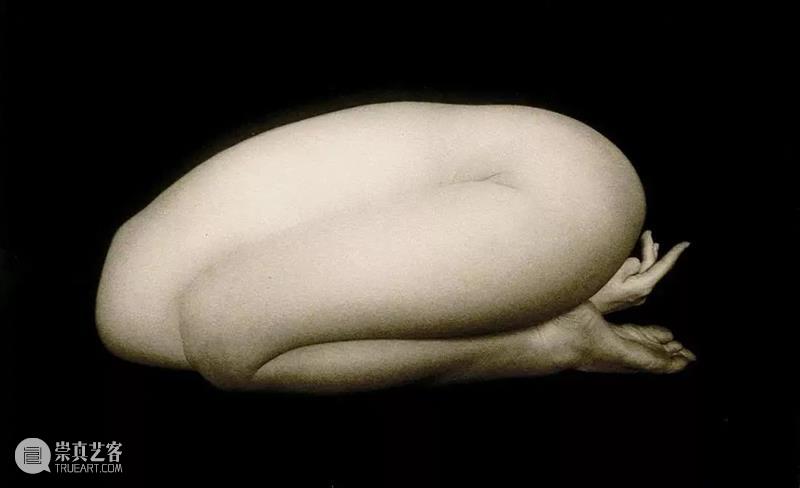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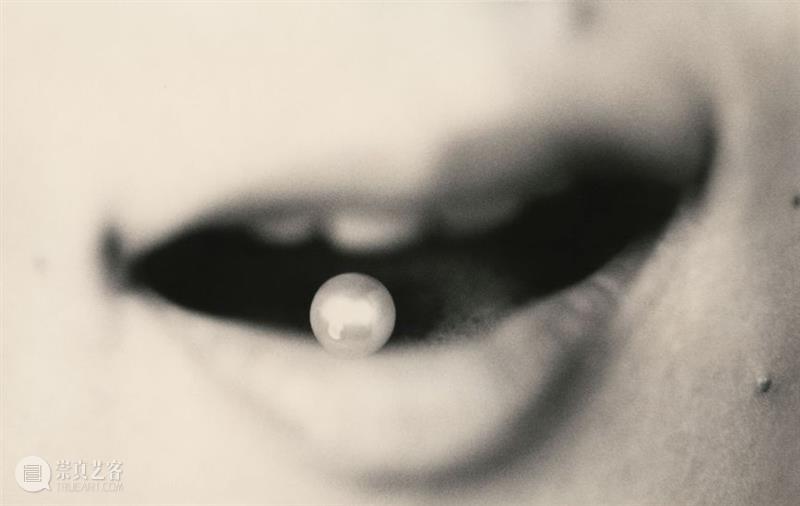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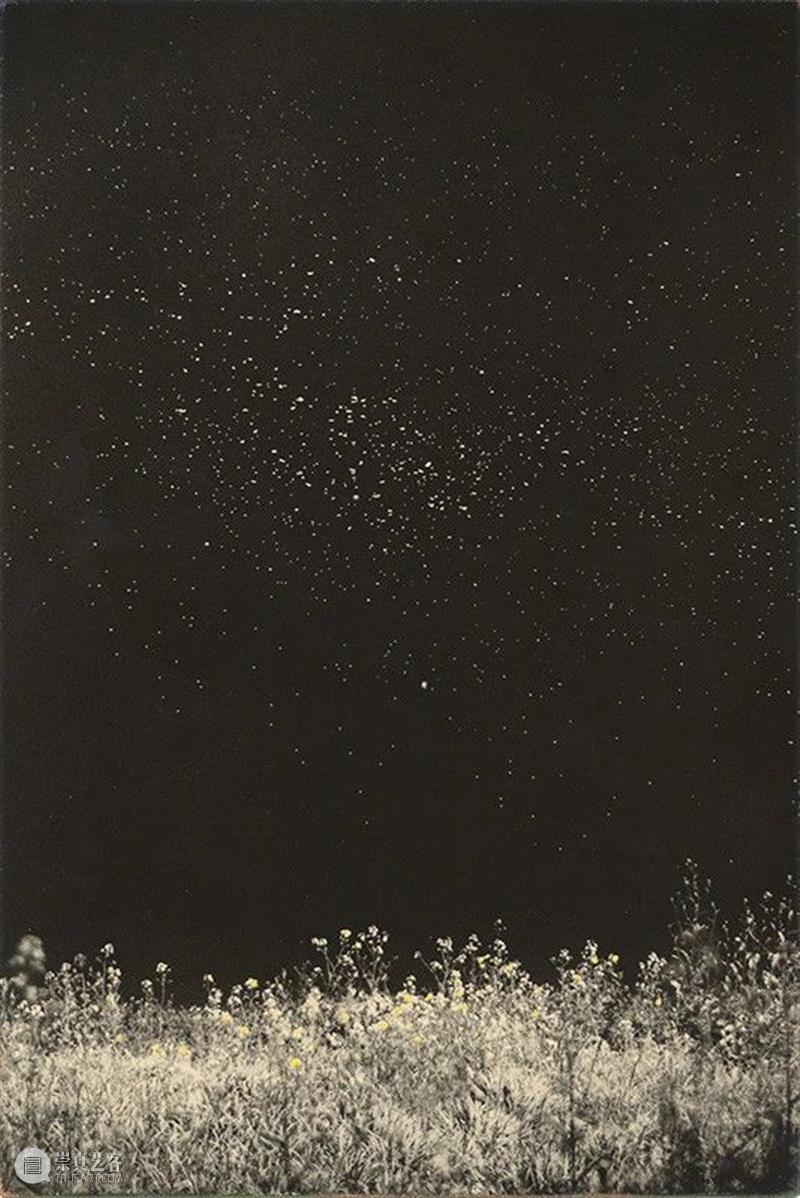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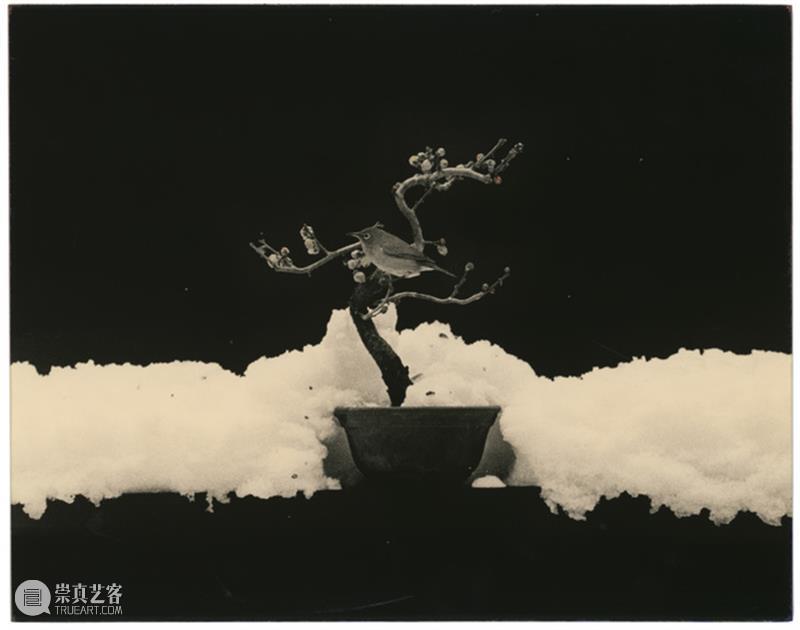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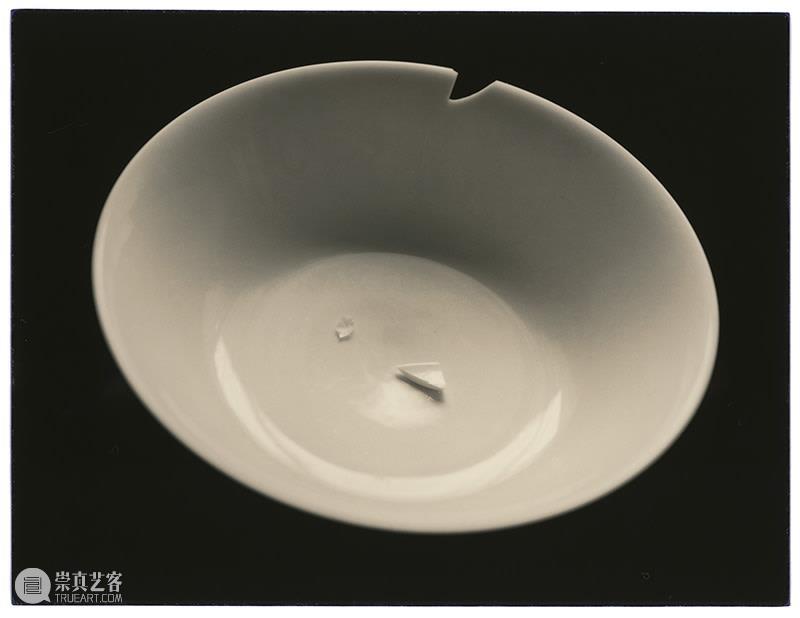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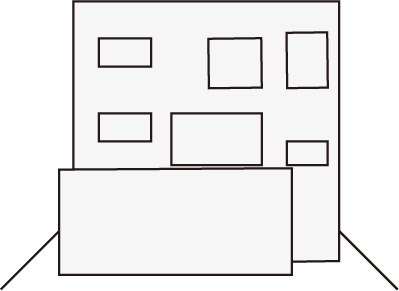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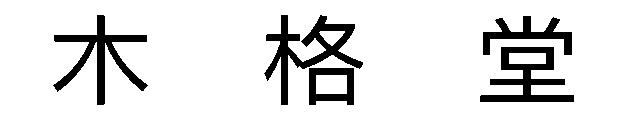
{{flexible[0].text}}


Find Your Art
{{pingfen1}}.{{pingfen2}}
吧唧吧唧
加载更多
已展示全部
{{layerTitle}}
使用微信扫一扫进入手机版留言分享朋友圈或朋友
长按识别二维码分享朋友圈或朋友
{{item}}
编辑
{{btntext}}
继续上滑切换下一篇文章
提示
是否置顶评论
取消
确定
提示
是否取消置顶
取消
确定
提示
是否删除评论
取消
确定
登录提示
还未登录崇真艺客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立即登录
跳过
注册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