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论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的摄影实践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摄影是一种志“异”的最佳手段。它不仅有其快速凝固影像让我们凝视细看的高超能力,也因其凝视对象所带来的感受与知觉的变化,可以进而磨砺我们的感性与知性。摄影的志“异”,在充分展示其能力与特权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关世界的全新感受。现在生活与工作在柏林与伦敦两地的德国摄影家、艺术活动家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以他持续的摄影实践,尤其是以摄影志“异”的非凡实践,令我们对于摄影的认识与能力有了新的展开。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阿尔戈船员》,2017
世间所谓“异”者,多种多样,其丰富多彩不遑多言。虽然分类不是我所擅长,但也可以想见,在我们的现实中,至少有以下诸“异”存在。第一种“异”,是因为人所共识之不宜公之于众者,比如人之私处,其实它是一种人皆有之的常,但因为文明的原因而被遮掩起来,因而成为一种被禁外露的“异”。第二种“异”,确实是因其稀奇古怪而被视之为“异”者。不过这种“异”之所以为“异”,其实往往被在相对与绝对之关系中所定义。其“异”之所以为“异”有时会因社会、历史与文化之条件的不同而有变化。第三种“异”,是被表征之“异”。它们是作为人类思想的视觉表征的“异”。它们有时是实际存在的“异”被视觉艺术家突而显之为“异”,有时它并非真“异”,但被人看过(凝视过)后才成“异”。它可能明明不“异”,但可能被有意框取或取裁之后而变得“异”了起来。总之,世间之各“异”,各有其所以为“异”的原因。而摄影,则生来就是热衷于志“异”。因为摄影所具有的逼真再现能力,在它要证明世界的不可思议性时,其所志之“异”所具有的说服力是其它媒介手段所无法抗衡的。也因此,它始终吸引了人们把它作为一种了解、呈现、分享世界之丰富复杂的手段之首选。面对现实中的这些有可能解释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异”,提尔曼斯如何去面对与处理,在我看来,他可能是以这样的三种不同手法来实施。这三种手法我称为志“异”、变“异”与制“异”。也许,这三种手法在他的创造实践中并不可以截然分开,在他的观看与呈现的努力中,它们可能具有某种内在的自然的联系,在他则是一种自如有机的联系与转换。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虽然我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但我仍然要重申,摄影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志异的方式。世间万物,摄影是不“异”不志。对于“常”,它根本就是无动于衷。志“异”,作为一种考验每个摄影家现实敏锐度的手法,在提尔曼斯那里有着充分的表现。在他那里,这种志“异”,既志自然造物之“异”,如《沙克区的树》(1995年)、也志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人为之“异”,如《反无家可归装置》(2000年)、《维斯塔望远镜:欧洲南方天文台》(2012年)。同时,对于人的存在与行为一直保持高度敏感的他,也会在外力作用于人的存在的一瞬间作出迅速反应,记录下人在某个瞬间的“异”形,如《象人》(2002年)。所有这些志“异”,都在捕捉与呈现现实变动中的突兀之处,有些是长久生成,有些是瞬间展开,有些是自然所为,有些是社会实践(姑且不论其好坏),提尔曼斯以此展示人类生活与社会现实中充满的不确定性与无穷魅力。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但是,摄影在有些人手里,比如像提尔曼斯,并不仅仅而且也不可能只是志“异”的手段。摄影更是一种变“异”的强有力的手段。他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可以把人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常”转变为“异”,通过这种由“常”而经摄影家之手转变来的“异”,来唤起邂逅“异”的惊喜。更重要的是,他的摄影,通过他给出的“异”所带来的视觉的与心理的震惊与意外,来唤起对于“常”的重新认识,以此告诉人们不要轻易忽视由“常”变“异”的可能性。变“异”需要敏锐的发现,先发现可变之“异”,然后要见“异”思现(再现)。如此,摄影家不断地拓展人们的日常经验的疆界,也改变人们对于日常的态度与认识。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变“异”,就是要考验摄影家如何把人类现实中常态的事物,经过他的主观的取景与视角决定后,去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感受,以此刷新人们的视觉经验与生活体验。比如,《褶裥(伯恩住宅)》(2002年)、《颈部》(2011年)、《裸体》(2014年)系列等,都是从特殊的角度来给出一种独特的视像,以此挑战人们的日常视觉。曾经有人说,无法将提尔曼斯的摄影放在德国摄影史的谱系里将其脉络化。但至少就变“异”这一点来说,我认为20世纪初的卡尔·布劳斯菲尔德(Karl Blossfeldt,1865-1932)的《自然中的艺术形式》(Urformen der Kunst,1928)、阿尔伯特·伦格-帕契(Albert Renger-patzsch,1897-1966)的《世界是美丽的》(Die Welt ist schon,1928),都可以被认为是提尔曼斯摄影的精神来源之一。摄影也是一种被超现实主义赋予了求“异”特权的观看与表现手段。法国超现实主义摄影家雅克—安德烈·布瓦法尔(Jacques-André Boiffard,1902-1961)也是以将人体的局部予以特写而成为摄影变“异”的先驱。看看布瓦法的将一个大脚趾赋予特写关照的手法,就知道变“异”手法的出处了。在“异”的谱系里,有用与无用也经常成为入“异”与否的标准。现代社会的取舍标准以有用为上,无用之物则多被视为“异”。而提尔曼斯的《兰佩杜萨》(2008年)则以投注予无用之物的垃圾的凝视目光,将我们忽视的事物提升至一种审美实践的视野中。在此,摄影的凝视、定睛的特别功能,再次帮助我们意识到关注日常复杂性的可能性。而这样的照片,从手法上说,既以志“异”拍摄得,也有变“异”观念在,无法截然确定是志“异”还是变“异”。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大千世界永远不会无“异”可志或无“异”可变,但对于作为摄影家的视觉艺术家来说,无中生“异”,或者说制“异”也许是最具吸引力的挑战。与上述志“异”与变“异”所不同的是,第三种手法的制“异”,则是摄影家自己亲自改变物质与拍摄对象的存在状态,并以一种独特的看法来呈现之,以期更新人们的视觉体验,以此打开人们对于现实认识的新地平。在提尔曼斯的摄影中,最典型者如《安德斯(布莱顿阿尔钦波托)》(2005年)和《纸水珠》系列(Paper Drop)。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办法对于他的杂志与书籍编辑、展览布置与艺术空间运营等实践作出评述,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制“异”的实践,目的是为了通过更自主的行为来拓开人们的各种视觉体验。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在讨论了提尔曼斯的以上三种摄影手法后,我们也许有可能进入到对于“异”的更深入的讨论中来。“异”,有的时候并非单纯的“异”,它可能就是一种正常、日常的常,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状态或行径,但由于在太多的日常现象中无以显现其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细微的特殊性,因此成为一种常。成为常,因此平庸。平常成为了庸,而且是俗的庸。而艺术则一定与平庸为敌。这种处于日常中的微妙的特殊性的“异”,最需要像提尔曼斯这样的摄影家来发现它,确认其价值(从形态、色彩、散发的气息到所具有的意义等多个方面),并进而以某种方式将其视觉化,给出全新的观感。比如,不经意叠放的一堆衣服(如《河床》(2017年)),散乱摆放在冰箱里的一些食品(如《冰柜静物》(2017年))等,如果不经过提尔曼斯的摄影凝视,恐怕不会给我们以这么新奇的感觉,而我们也就此忽略了其存在的魅力。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异”属于少数,甚至是极少数,因此与“常”这个多数或绝大多数相比,始终处于弱势。我认为,提尔曼斯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么一种将少数的“异”提升至与多数的“常”平起平坐的积极的努力。这也是一种打破“常”所占据的对于日常意义解释权的暴力性垄断与遮蔽的努力。他的一系列工作,既让我们了解到了其实无所不在的“异”的魅力与光辉,也同时让我们了解了“常”的意义与价值。他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异”而“异”,无论是志“异”、变“异”还是制“异”。从根本上说,他是为了令“异”与“常”关系变得平等而在始终不断地志“异”、变“异”与制“异”。好在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如此的丰富,而且人们还在不断地制造各种事物,因此通过从“常”中发现“异”来拓展人们对于现实丰富性的认识的可能性,拓展摄影认识与再现“异”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永远不会使我们陷入无“异”可志有状况。即使是从大量生产的汽车局部,提尔曼斯也能够凭其敏锐创造出《车头灯》(2012年)这样的令人惊异(惊其“异”)的作品。何况他还有能力创造出像《纸水珠》系列这样的新“异”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敏感于“异”,寻求与发现“异”,并且追求把“异”精彩地呈现出来与更多的人分享的欲望与能力,其实正是激发艺术创造的原动力。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年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诞生了达达运动,继而从达达又产生了超现实主义运动。超现实主义艺术所明确宣布要追求的“惊挛之美”,就是志在从平庸的日常中发现“惊挛之美”,给予资产阶级的平庸价值观与美学观以打击,不惜通过耸动视听的“丑闻”(所谓“丑闻”不就是一种“异”吗?)来推动人们的意识解放与社会革命。虽然作为一个艺术运动的超现实主义最终消失了,但其精神,尤其是追求与呈现日常中的“惊挛之美”(一种“异”)的目标与理想,从来没有过时过。提尔曼斯的工作,可以认为是从现代艺术开始的寻求“惊挛之美”之旅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新的而且是重要的一环。通过对于作为边缘、少数、无用的事物的“异”的关注,提尔曼斯挑战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对于“异”的艺术处理的美学化过程(同时也是创造新的视觉体验的过程)中,他并不是把要处理的“异”只限定为怪诞(grotesque)。他是要将被因了各种目的与企图而被粗暴定义的边缘、少数、无用纳入到他的视觉审视的视野中来,将“异”的边界打开至更为广阔的境界,从而为最终令“异”与“常”的对立的消失而创造条件。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提尔曼斯的摄影的最吸引人之处是,经过他的视线的魔杖的点化,不起眼的日常事物会变得焕然一新。这是他的点化平庸的独特本领。日常掩盖世界本来满是“异”的本质,使世界变得平常。但如果我们真的只是为日常的表面平淡而无所动心,而不想探究日常表面下面涌动着的无数的“异”,那真的说明我们的心灵已经麻木不仁了。如果日常的平淡令我们无所用心,只能说明我们自身的感觉被日常平庸了。而提尔曼斯的努力,则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日常为何。他让我们从“异”入手、从“异”入眼来思考日常为何。对于提尔曼斯来说,世间万物同样重要而且从来没有孰轻孰重的问题。从佛教的角度说,这就是众生平等。虽然他密集拍摄他所遭遇的各种事物的观念与方式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个众生平等的态度,但无法穷尽的现实,宿命地决定了他分配于世间万物的关注与视线仍然是有限的。但是,即使是如此有限的出自于他的对于无限的关注,也已经令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他对于世界的、对于生命的以及对于摄影的态度与看法。对于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提尔曼斯保持密切关注是为了不让世界上的值得关注的事遭受忽视。因为所有的悲剧可能产生萌芽于忽视与忽略。而给予关注则给予了进一步面对的可能性。对于生命,有的时候,这种关注就是一种能量注入,本来有可能夭折的生命可能就因为这个哪怕是一瞥的关注而获得重生。摄影,能力有限的摄影,它所能够给予的只是一种关注。在中文里,关注同时包括了关心与(目光)投注的双重意义。摄影,在投注目光的同时,其实也同时是把摄影者的心一起交付给关注对象的观看实践。只有物我一体、心眼一致的时候,对象的生命才会被摄影所点燃与焕发。摄影要做的,其实就在于此。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异”,无论以什么手法获得,它无论如何都是辉煌的。在提尔曼斯的摄影中,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其实就是这个由对于万物众生的态度决定了一切的真切关注。顾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1998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人类文化研究科比较文化研究专业,获学术博士学位。曾任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终评评委。2017-2018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9年德国海德堡大学第九届中国艺术史海因茨·葛策杰出客座教授(9th Heinz Götze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rssor of Chinese Art History)。曾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理论评论)(2001年)及第一届沙飞摄影奖学术奖(2007年)。著有专著多部,并在国内外策划多个摄影展览。本文原载于《普通高校摄影专业系列教材》之《当代摄影家研究》,顾铮著,浙江摄影出版社,2019年。此发布版本略有修订,经作者授权转载。
《线上巴塞尔:15个房间》
卓纳画廊是位处纽约、伦敦、香港及巴黎的当代艺术画廊,现代理近70位在世艺术家和已故艺术家遗产,拥有过百人的专业团队。画廊自1993年创立至今,成功举办了众多具开创性的展览。卓纳画廊活跃于一级和二级艺术市场,一直致力于培育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当中许多已在当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列。卓纳画廊的香港和巴黎空间已于5月重新开放,伦敦空间将于6月15日恢复开放。于此同时,卓纳线上展厅将依然保持活跃,担任向国际观众呈献画廊艺术家与作品的重要渠道。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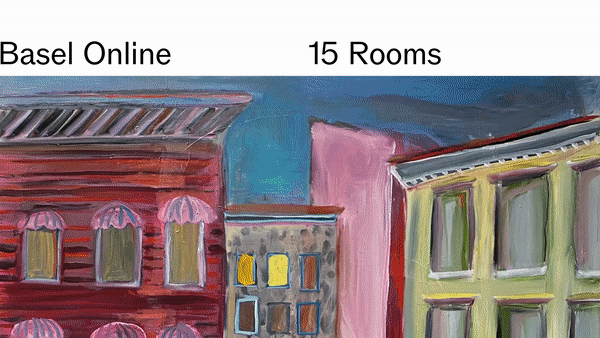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