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ndex}}/{{bigImglist.length}}
“我认为我的绘画过程本身就是作品,而不是作为预备联系。我对运动和空间的探索感兴趣。这在画的过程中,更容易看到。有些画会给你一种永远无法完成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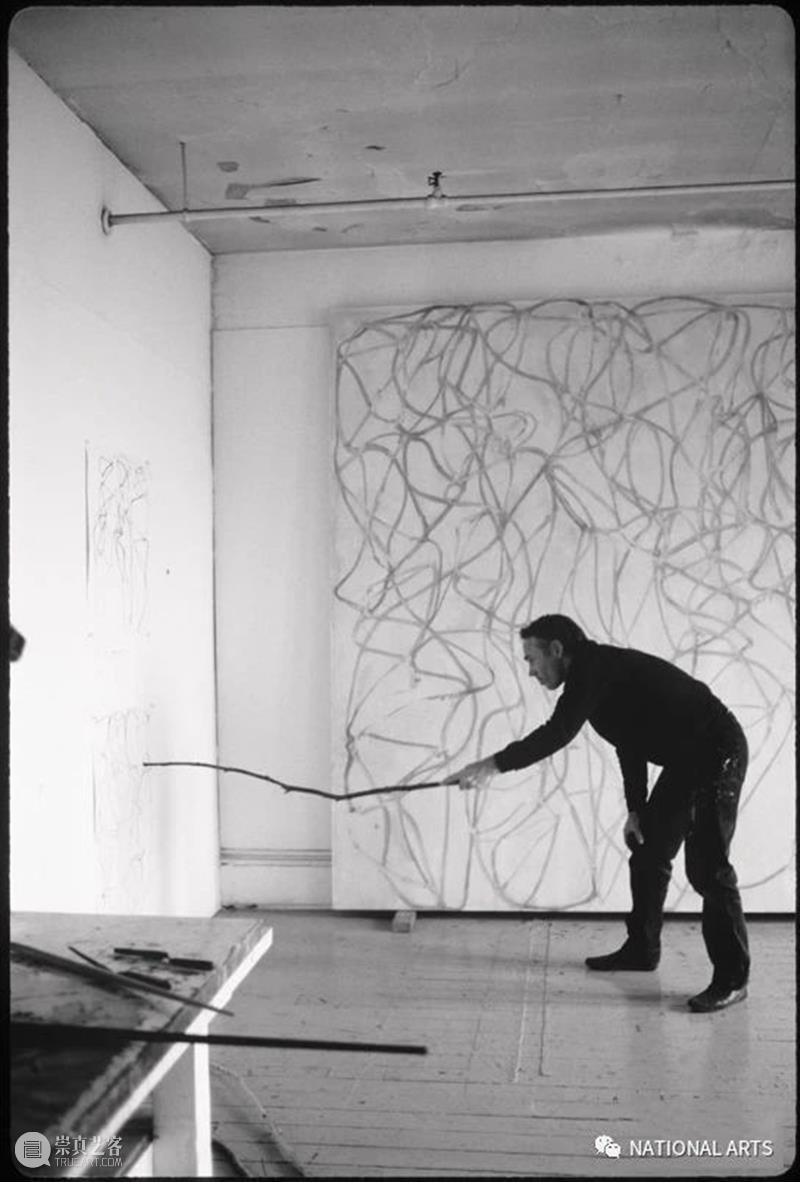 ▲正在用树枝创作的布莱斯·马登
▲正在用树枝创作的布莱斯·马登 ▲劳森·伯格与布里斯·马登
▲劳森·伯格与布里斯·马登

▲马登还和鲍勃迪伦等人玩过流行音乐

▲布里斯·马登在工作室中


作为成功“转译”中国传统艺术的先驱者,布里斯·马登笔下最基础的形状、色彩和线条,因不再具备传统的“再现”功能而成为了个人精神的象征和情感表达的载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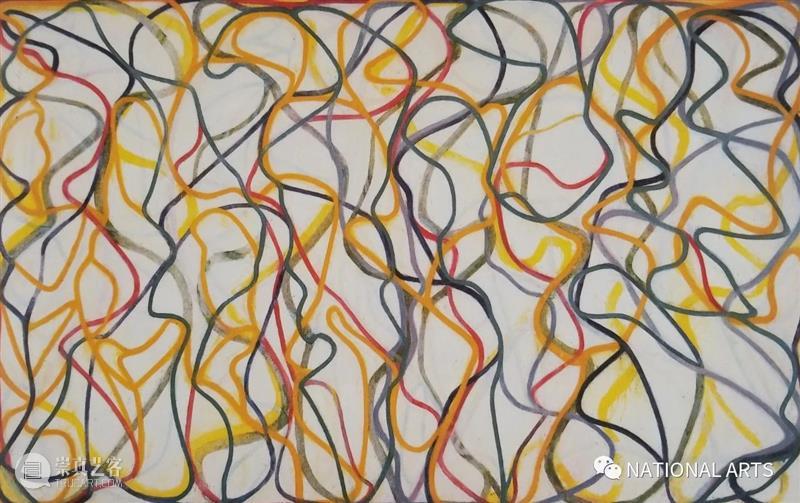 ▲布莱斯·马登《为缪斯女神学习》210x343cm 布面油画 1991-1997
▲布莱斯·马登《为缪斯女神学习》210x343cm 布面油画 1991-1997



▲布莱斯·马登《贝尔》213x152.4cm 布面油画 1996-1997
 ▲布莱斯·马登《关于贝尔》212x151cm 布面油画 1996-1997
▲布莱斯·马登《关于贝尔》212x151cm 布面油画 1996-1997

鸟语情不堪,
其时卧草庵。
I can't stand these bird songs,
Now I'll go rest in my straw shack.
——寒山子《鸟语情不堪》节选





▲布莱斯·马登《岩石》29.2x63.5cm 布面油画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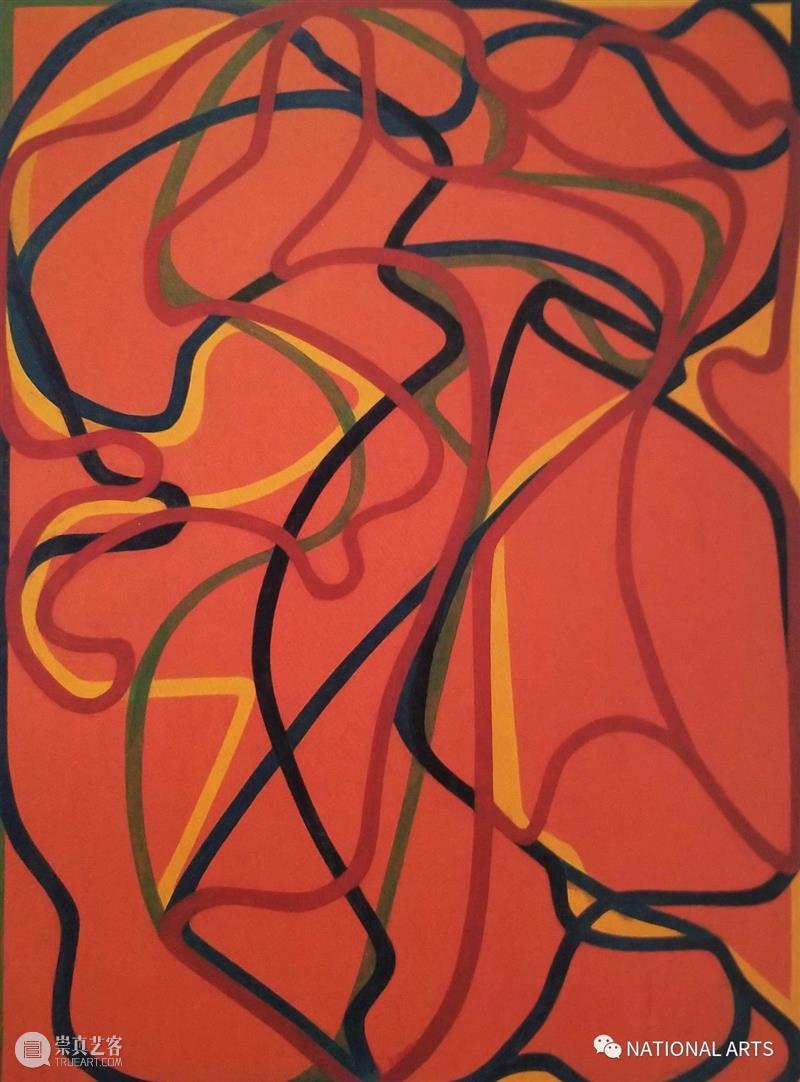







































展览现场









{{flexible[0].text}}


Find Your Art
{{pingfen1}}.{{pingfen2}}
吧唧吧唧
加载更多
已展示全部
{{layerTitle}}
使用微信扫一扫进入手机版留言分享朋友圈或朋友
长按识别二维码分享朋友圈或朋友
{{item}}
编辑
{{btntext}}
继续上滑切换下一篇文章
提示
是否置顶评论
取消
确定
提示
是否取消置顶
取消
确定
提示
是否删除评论
取消
确定
登录提示
还未登录崇真艺客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立即登录
跳过
注册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