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9日,由西安崔振宽美术馆、水墨长安艺术博物馆主办的第二届新写意主义——中国当代艺术名家邀请展在西安崔振宽美术馆隆重开幕。展览主题由著名美术理论家刘骁纯先生、王林先生共同提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可君任此次展览策展人,刘骁纯先生、夏可君先生共同提名并邀请具有“新写意主义”创作取向且取得较高学术成就的国内外知名当代艺术家(按姓氏拼音排序):陈九、崔振宽、顾黎明、郭全忠、侯珊瑚、胡又笨、金锋、李惠昌、梁绍基、刘庆和、刘西洁、邱振中、隋建国、孙大壶、王冬龄、王非、王舒野、王昀、王小信、吴冠南、吴国全、夏福宁、于振立、张大我、张方白、张浩、朱金石共27人参加展览,展出作品约150余件。当日下午15时,以“新写意主义艺术的文化诉求”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崔振宽美术馆学术报告厅举行,研讨会由著名美术理论家王林先生、策展人夏可君教授共同主持。著名美术批评家贾方舟、陈孝信、程征、彭德、王林、殷双喜、马路、夏可君、张渝、郭红梅、杨卫与参展艺术家共同出席。此次研讨会就主题“新写意主义”、“写意—表现”艺术创作倾向,以及如何推进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等议题展开梳理和研讨;同时,研讨会上还对本届展览的学术主持——刚刚去世的著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策展人刘骁纯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以及他对构建中国当代美术批评理论体系的学术贡献进行了梳理、回顾和深切缅怀。夏可君:我讲一下这个展览的基本理念。作为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感谢刘骁纯老师对我的信任,为什么让我做这个策展人呢?他很信任我,这个题名我不干涉他,他也不干涉我,每人提了一半。他是非常好的可以深入交流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敏感透彻有自己理论的批评家。为什么他提出写意主义,王林老师提到了新写意主义,到底新写意主义的基本语法是什么!基本的句法是什么?这是最为根本的问题。一个批评家和策展人,应该能明确新写意最基本的语汇。今天几位批评家提到的这些非常好。新写意之敞开的边界在什么地方,收敛的边界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敞开的张力。
中国文化的意不在意,而在无意之意,在于空无的敞开,打开新的场域。如果落到"意义"里面去,肯定会被一个所谓的套路或程式化套住,怎么从‘有意’到‘无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分。
从这个"意"也不是到"象",从意到象是传统的语汇,整个迈出的一步关键在于不是西方的形式,不是一个想象,更不是后现代的幻像和仿真,而是形态学,在一个似与不似之间。也不是相似性,相似性靠近程式化,一直在似与不似之间更靠近但不相似,但又不是抽象,又保留了一点余意,是余。在传统的意象与西方的抽象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空间一一余隙的"余象"!对于自然有着某种残余的相似性,尽管有抽象性,但是不是抽象画,而是力量的变化,是不断的变形。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性是原创性的想象性,这是生命的意志力,而不是要落在主体的意愿、主体的风格化上。写意主要需要把心灵、灵魂、魂魄的力表现与抒写出来。
为什么水墨很重要呢?因为水性、墨性是一种自然的材料,魂魄是心魂,是与生死相关、超越生死的那个力,不是西方的抽象、形式的精神。而是余象与材质的共生!
敦煌是一张画吗?只是一张壁画吗?它是多维空间的展开,是一个力量的场,必须把多种媒体的媒介结合起来,而不是传统的二维空间的一张画。
这个展览里我用"逸派"来自于骁纯老师,我作为晚辈非常尊重刘骁纯老师,从意到象,不能落在象的层面讨论,这样就摆脱不了具象和抽象的东西方模式,除非作为:余象,既是万物的剩余之象,也是所有象的剩余。而西方说到"意"有三个含义,它是意义,是感知,是方向。真正的意不是意义的所指与限制,也不仅仅是感觉、感知的发泄,而是一个心意之力,是方向的意志力,甚至是来自鬼神、魂魄的力之表达。
这是行动性、形态学的力,可以与书卷气跟文气连接在一起,跟场域联系在一起,它是生长的、无限延展的,是所有魂魄产生共感的力。
我们要结合这三个方面:保留传统的笔墨功夫,借鉴抽象的表现形式主义,又要扩展开力的场域。新写意主义要把水墨功夫、形式主义与力的场,都做出来,让所有生命可以共感,就像盛唐有佛教托着,没有心力的立场托着,可能就只是一个风格的表现,达不到历史、灵魂的深度。
为什么刘骁纯老师孜孜以求新写意主义,因为他比我们所有人更能领悟到生死的残酷方式,他对生命脆弱性的感受,应该激励我们更好的感受生命力的脆弱和不朽。
崔振宽:我们平时几个朋友在一起经常会讨论关于画画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画画各个方面的问题,可以争得面红耳赤,也可以滔滔不绝。但是今天在理论家的面前,我可以说是哑口无言,不知道该说什么。从我个人来说,考虑的都是画画中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跟有些理论家的发言好像还关联不起来。我很崇敬刘骁纯先生,作为一个理论家、批评家,他的理论很有高度和深度,但是他写的文章又是深入浅出,可以去读,去理解,而且对我有指导作用,也有一种可操作性。但是有一些理论家的文章就看不懂了,这是我自己理论水平不足。刘骁纯先生提到的有一些理论我也不太理解,但是大部分还是理解的。陈孝信先生最近写的关于纪念刘骁纯先生的一篇文章,把刘骁纯先生水墨的一些理论框架和具体的观点都梳理了一遍,这是非常好的。在这个文章里面,有一些地方我不是能特别的理解,这个不理解不是对陈先生的文章,而是对刘骁纯先生关于笔墨的问题,一个是文人系统的笔墨,一个是中西结合、非文人系统的笔墨。非文人系统的笔墨他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又提出了一个笔墨的新形态,对此我不是太理解,因为举一些例子的时候,我总是考虑传统的笔墨形态。刘骁纯先生还举过一些例子,比如新形态笔墨里田黎明的笔墨,田先生的画我是很喜欢的,他的画很有新意,有独特的制作的方式,但是要提到一种新的笔墨形态,好像我还看不出来,因为他的笔墨基本上是传统笔墨中“没骨法”的一种演变。所以我觉得作为新形态的笔墨,应该有更多的个案研究来说明这个问题,才能更有说服力。现在我个人还没有感觉到新形态的笔墨是什么样,所以不太理解这个问题,这些都是理论问题。从逻辑上来说的话,除了原有的笔墨规范,笔墨形态,还要有新的发展,但是新的发展究竟怎么样的?需要个案来说明。所以刘骁纯先生说“它的成熟需要更多的时间”。再比如说关于结构的问题,刘骁纯先生谈到结构的时候,分为理性结构和灵性结构,首先考虑的不应该是理性结构,不要对结构进行太多设计,这个问题我赞同,但陈先生对此提出质疑。有一次我跟刘骁纯在一块,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结构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一下,他说结构就是疏密,没有进一步的阐释这个问题,当时我感觉不太满意,疏密我知道,但结构是什么东西,后来感觉到他说的有道理。他后来也说了结构是类似于传统的构图、章法、排势布阵,里面就有疏密、动感气势等等。他又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齐白石就很讲究结构,但是他的结构却让你察觉不出,潘天寿也很讲结构,但齐白石的这个结构要比潘天寿的结构更有力量,他强调的是灵性结构。中国画的结构不是西方的几何体的结构,刘骁纯先生对这些问题的解释,都是带有中国传统精神的一种说法,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东西。再比如说写意画,刘骁纯先生在文章里面说,石鲁的野、怪、乱、黑又把大写意提上日程,说得很有道理。西安受长安画派的影响比较多,受石鲁的影响也比较多,当时6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我很有体会,在我个人心目中这就是写意精神,就是现代感,就是传统现代的一种转换。之后刘骁纯先生又说了大写意、纵笔大写意希望在陕西,也有道理。拿野、怪、乱、黑来说,在西安大家都很理解这个问题,甚至都在践行这方面,但是真正到外地,特别是到江南,到了笔墨重镇的浙江,那些画家确实接受不了这个东西,画的重一点,他觉得太黑了,力度强一点,他觉得太野了。对我来说,很多东西都是一些具体的理解,没有太多的理论深度,也没有思考的那么玄、那么深奥。吴冠中先生说,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导师给他说绘画有两种路子,一种大路子、一种小路子,大路子给人震撼,小路子使人愉悦。所谓写意,我追求的东西就是想能够对人有所震撼,至于说做到或做不到那就是一种理想。郭全忠:上一次在‘新写意主义和表现主义’画展研讨会上,我跟王林先生争了几句,王林先生说:看来理论家和画家不适合坐在一起谈问题。我看也对也不对。因为许多理论家说得都很好,虽然有些理论家发言语速因太快没有听清,在谈纯高深理论时我一时还未听懂,但在艺术评论范围内,还是能够交流的。多年来,我和刘骁纯先生交流的就很好。今天大家都在怀念刚刚去世的刘骁纯先生,在座的恐怕没有一位有我和骁纯相处的时间长,算来整整50年了。我们原来同在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工作,我们不仅是朋友,还是兄弟。1994年我们在美国参观访问,学术考察,日夜相处45天。对刘骁纯的认识,他首先是一个有思想有深度有雄心建立完整学科的大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家,他有敏锐的艺术慧眼。对画面把握有独特的见地,甚至对笔墨的具体技法运用,像个有经验娴熟的画家,其意见和想法会给画家以启迪。如他说‘结构大于笔墨’;如1987年一个进京展,刘骁纯给我们陕西几位画家定义为‘乡土表现主义’——此后一直都在影响着我。这次画展前,他又提出了关于‘恭笔’与‘纵笔’的问题,把陕西画家的艺术风格和对陕西画家的期望放到美术画论很高的位置上。关于‘纵笔’这个学术问题,恐怕需要专门搞一个研讨活动进行深入探讨。刘骁纯对陕西画界期望这么大,或许我们有的画家可能只是无意识的在做,还未认识到它的真正学术价值。所以我们有责任也有热情把刘骁纯的这一学术主张深入研究,通过今后的创作实践有意识的往纵笔这个方向努力。刘骁纯对现代艺术,抽象艺术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记得1994年在美国学术考察时,我们在纽约苏荷画廊区看了很多美国当时现代抽象艺术的东西,他当时感慨说:看来西方现代艺术是‘大师和流氓分不清,天才和骗子分不清’。多年以后,我问骁纯你当年那个话说得太精彩了,现在能分清吗?遗憾的是他却有些诧异说:“我说过吗?”。我虽然感到有一点遗憾。但我确认他能够分清大师和骗子、天才和流氓。可惜这位中国美术理论界真正的理论精英正在发出强光时,人走了。我坚信刘骁纯先生对艺术的思想光芒将永存。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刘庆和先生刘庆和:相关水墨这个领域,刘骁纯先生、郎绍君先生、鲁虹先生等多年来一直持续着关注。今天研讨会所涉及的已经不仅仅是水墨的问题,更多的是当代性的问题。骁纯先生把中国当代水墨跟国际当代艺术进行对比,有着冷静的思考。这个展览的呈现也能看到刘老师的初衷,是要把本土的民族的文化与当代的艺术现状做个梳理,策展人我想也是按照这个思考进行的展览筹划。我所感觉到的刘骁纯先生在关注当代水墨发展的时候,并非是一任往前的,往往会前行的时候收起步子,与艺术家的沟通也是在长久的观察下的对话,不是仅限于对画面语言符号的概论,所以,能感受到刘老师对于水墨传统根基的在意,其次才是它能否承载的当代性和可以与外界沟通的语言。我不否认别人在追求被西方认可的努力,但我自己是觉得离开了中国本来的东西,走出去会心虚。 刚才殷双喜先生提到2009年我在苏州做了一个空间表达的展览,几乎声、光、电等科技手段都用上了,可是,在展览开幕之际我的快乐也就到此为止。是因为,我忽然觉得就情感表述来说,一个手稿一个笔墨戏谑,同样可以表达个人的情怀,不仅仅是做大、做响亮。回到相对传统的方式,获得的东西没有少。在当代的这条路上我的胆子越来越小,越来越退却。当一个人的思考可以落地的时候,思考才能唤起你最朴素的感知,无边际地夸大水墨的作用和含义,就会空,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水墨到底应该怎么走,这次展览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同行切磋理论建议。作为水墨,不可能是一个屏蔽或者围栏保护在里面自说自话的东西,要打开,但是往外看的时候还要坚持“本”,就水墨而言,是要保有书写性的东西,书写与绘画关联可能才是具有世界语言的可能,或者说,更适合我自己。大连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大连油画学会会长 于振立先生于振立:我能再次参加“新写意主义”展,当感谢刘先生。记得七六年春刘先生与李松涛来约稿,写“怎样画水粉画”一书,半途而费的缘故於唐山大地震等事件发生。后来我一头扎进油画为主材料的各种实验艺术之中,直到九八年由尚扬等参入的“8人油画展”后我租借北京北锣鼓巷,从那“吃喜酒的女人们”的表现主义绘画中抽出笔划,成就了我近60多幅综合材料的抽象艺术的试验。虽拒绝发表“中国美术报”末期,但93年3月2日我与刘先生合作,在美术馆所搞的本应是“抽象的绘画个展”,当时遭遇阻碍所就。回想我的艺术不断的变现,与刘先生及时关注我的笔划自身隐喻与张力,给了我不小的追求信心。“坐忘”“离形”“虚静”则是庄子的精神,书法、尤其行草也给了我艺术实践启示。当然了,我关注灾难、废墟等水、油、火冲撞等等。自九四年至今在山上,刘先生多次到场并与栗宪庭为我在“今日美术馆”搞了综合之展。当然有在坐彭德、王林、贾方舟、双喜等关照,皆此谢意。邱振中:坦率地说,我很少思考各种口号和标签。听了大家的发言,对“新写意主义”有了自己的一种理解。所谓的“新”,就是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有过的就不新;什么是“写意”,就是表达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独特的生存的感受和思考;什么叫“主义”,“主义”就是坚持到底,一条道走到黑——越沉重、越深刻,面对的空间越广阔,越好。作为艺术家,我们做的是具体的事情。我们总是从一笔一划做起。这一笔一划是要去思考的:怎么让它做成前所未有的一笔一划,或者说一笔一划下手前的动机、动手时的感觉、做完以后的阐释,都要有新意,这才是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做不到,或做得不好,就失败了。——当然,这只是以一个笔画为例,创作是一件无限复杂的事情。在这里我没有办法去追溯历史,只能说一说这次展出的作品——《被删除的<金瓶梅>》。1989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做了一个展览,《最初的四个系列》。人们一般不关心文字作品的文词部分,但我认为文词与作品的观念密切相关。展览中给人们留下印象的作品,如《日记》《待考文字》《汉语词典以“三角”为词头的词》等,每一个题材的获取都非常艰难,有时为了寻找一个题材,要把我手上所有的书翻一遍。这样的创作有意义,但无法成为一条道路。利用书法来表达当代观念,成为让我绝望的一件事情。——人们利用文字(不是利用书法)来做当代作品,是另一件事情。书法,按照我的标准,按照“新写意”的标准,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没见到什么有意义的作品。不“新”,没有“写意”,也没有“主义”。2018年底,偶尔得来的1600平米的展厅,让我很快构思了一批作品:在墙上书写几组德里达的哲学文本和策兰的诗歌作品。我要用书写的不可识读暗示当代哲学与诗歌文本阅读的艰难。书写时使用重叠、省略的方法,使阅读几乎不可能进行。同时,由于拒绝阅读的心态,个人所积累的对线和运动的感觉,获得从未有过的自由。不过当代哲学和诗歌的原文本不是不可读,是难读。因此文本和书写之间还留有一道缝隙。在这个叫做《语·默》的展览之后,我挑选的是80年代出版的“洁本”《金瓶梅》中被删去的部分。我不想,也不能让读者读出作品中的文字。在这里文词的拒绝识读与书法的不可识读达到理想的结合。它建立了一种我所期待的文词与书写的关系。做完三组《金瓶梅》以后,一个美术馆约稿,我做的作品是《徐渭狱中上明世宗书》——这是我虚拟的一个文本。没有这样一封信。它为这个思路开辟了新的前景。人们问我,为什么要横写?中国书法所有的技巧都是从竖写发展而来的,我们掌握的所有技巧都是从竖写得来的——可以继续做下去,但这是一条几乎已经走到尽头的道路,还有没重要的、根本的变化,可以继续探索,但必须开辟新的道路。横写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也带来新的可能性,加上避开阅读的重叠、省略,它带来想象的广阔天地。三千年来,书写都是要让人阅读的。虽然我们同样从文字出发,但拒绝阅读,于是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机制。在这里,文字、视觉、身体、工具、图形,获得了一种新的,从未有过的张力。中国文联艺术家联合会副主席、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名誉院士王小信:首先,借今天这个机会悼念已经去世几十天的刘骁纯先生。他是我的导师,我是最后一个跟他谈话的人,我跟他谈话的第4天他就去世了,他留下了这么两句话:“我什么悼念会都不开,把我葬在大海里”。多么伟大的胸怀,他整整抱着氧气袋带了我5年,一个学者在用他的生命来教育他的学生。今天是对他的一个悼念,我用了一个礼拜出了一本关于刘骁纯先生的书,是出于对老先生真正的悼念。第一点,刘先生一直要求我在艺术上运用的必须是中国的纯正语言,要表达出它的现代性、当代性,或者说是一种自我的新的格式或者样式。第二点,不断的探索和研究自己的笔墨系统,这是他老人家一直在讲授的和要求的两个核心问题。中国画有很多禁区大家必须突破,比如说现代建筑,皮毛,玻璃器皿等等,目前在中国当代的领域还没有一位艺术家用写意的手法把它表现的淋漓尽致,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禁区……在85美术思潮中,我们一直在探讨中国画的发展问题,当时最核心的问题是缺乏理论体系和指导的审美标准。后来我们很多艺术家讨论并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中国画“三气”论。这应该算是对当代美术重要的发展和贡献,因为那时候很多东西是从西方移植、栽培出来的,能在中华土壤上长出自己的东西吗?不太可能。两种体系、两种文化要进行嫁接,出来的自然是不伦不类。85美术思潮以后大家有了冷静的思考,一直在思考我们本民族、本土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直在强调中国画的纯正语言,想着去表现它的现代感。这个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太难。为什么呢?因为我50年来才发现了那么一点点,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在当代文化发展方面,可能会吸收来自其他领域绘画里的一些营养,这个临界点是特别难把握的,要么偏向油画,要么偏向设计,要么偏向版画。纯正的语言要找出那一丝、一点是非常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作为一个艺术家50年来只有那一点点的体会,我想,这可能需要几代人来完成。朱屺瞻艺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原艺术总监 陈九先生陈 九:各位好!我今天十分高兴以一个画家的身份参加这场研讨会。以前我一直在美术馆工作,退休以后我才从管理者的身份转换成画家。画家是我从小的一个念想,也是我从事美术馆多年工作的一个理由。本以为自己有时间画画了,其实业余时间很少,虽然如此,我从未放下过画笔。因为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业余画家,这倒好,沒有了包袱,画起画来倒也轻松自在了。在坐蛮多老师,我都熟悉,出于对他们在学术上的尊敬。我曾邀请他们到我们馆里做过展览或研讨,其实,我更享受着他们对艺术的造意和理解,并喜欢聆听他们的学术高见,就如今天。我的画室在上海山阴路,鲁迅故居的隔壁,民囯时期那儿聚集过许多新文化名人,是个环境比较安静地方。每次回到画室,既有一种疏离感又有一种归属感。可以让你安静下来面对自己,重新审视本我。过去忙忙碌碌的我不曾有过,忽然,我好像找到一个回家的路径。在接待刘骁纯先生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艺术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和天对话的通道"于是,我问自己,艺术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在画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常追问自己。当你工作在一个有政府背景的事业单位(虽然是美术馆),更多的还是在体制化的规范里的挣扎,这种程式化的语境,并不是一个属于人性的语境。和我内心是有冲突的。让我越来越来不了解自己,甚至透不过气来。画画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和宣泄。这时,画什么或如何画对我已经不重要。那些日子我一有空就躲到了画室,只有这样我才感觉自己还活着。然而,当我真正地回到画室一本正经画起画时,另一种纠结感又会找上门来。这个纠结感在十多年前慢慢开始的,因为你有了更多被参展的机会了,当你正儿巴经想创作一幅参展作品时,一种固有的方式就会自然而然潜入进来,不断左右你,假如你不这样画时,你的画挂在展厅里就不太像话(画)。于是我想,我不就是那个业余画家嘛!我见过太多的挂在展墙上的画作,又不甘心去画那种司空见惯的东西,总期待在水墨上有所发现,或许是陌生的、或者是意外的,就如偶遇或邂逅。反正难以言表的那个视觉状态。于是开始挣脱束缚,慢慢地又找回那种业余画画的状态。我不再考虑笔下的东西像什么,更在意纸本下的水印或墨迹本身随时间的流淌与变化,沉溺于一遍遍刷笔和渲染的感受。我像个农人在默默耕耘,仿佛总有一种莫名的期待……这样一来,心思慢慢淡了,想法也许没了,画纸上腾起一片紫烟来,兴味昂然时不舍离去,既便离开画室的路上还有些牵肠挂肚……时而获得,时而失落;往返与重复。我开始享受起这个过程。刚才殷双喜老师讲的那种无意当中很难描述的感觉,可能有,可能无,反正很难画出来,即使画出来可能又不达意,往往摆在展厅里的画又是另一番境象。那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我向来就有一种表不达想、画不如意的状态。新冠疫情把我们更深地锁定在画室,什么地方都不能去,一遍一遍的在画,疫情残酷之际,让我感到生命是如此脆弱!画画显得那么无聊,它对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但同时,又似乎找到活着的理由,画室既然有了,你一定得用,还有事情可做。每天回到画室铺开纸,调起墨,这种习惯成为了一种寄托,成了我的日常,今天有昨天的痕迹,明天就有了期待,安全感与归宿感,便油然而生。画着画着,水染墨晕,宣纸上便有了呼吸,与窗外的梅雨宛如呢喃细语。张 浩:26年前,1994年,刘骁纯先生主持了我在北京的第一个个展,并特意为我写了文章,这篇文章由陈孝信老师编进了展刊。当时刘先生组织了研讨会,通过刘老师接触到一些老师,并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那个展览,陈孝信老师专程到北京支持我,没有任何报酬。所以我今天要感谢的人特别多,这也是我对刘先生的怀念。一晃26年过去了,1995年前这些老师对我都很熟悉,95年以后,因为我个人对艺术的认识有所改变,就渐渐淡出老先生的视野。不知道今天三幅作品挂到展厅的时候,刘先生有没有感觉到,我相信刘先生应该看到了,至少在回应,他创建的新规范:结构第一、笔墨第二。我用我的方式理解了这个结构。关于艺术,我思考的是什么呢?是艺术发展的逻辑,包括了对西方艺术史和对中国艺术史的认识,包括了从古代到现代风格演变的认识,不仅对各种形式风格和主题感兴趣,而且对为什么会发生形式的改变?改变的原因是什么更感兴趣。关于当代艺术,我对当代艺术的认识是先发生再认识的,是我自己的水墨发生了根本改变,脱离了原有的知识和原则,也不能用原有的理论来表述,所以有了当代的概念。20年前,也就是2001年,我在艺术上发生改变,那时候我对当代还没有什么认识,只是知道西方有了后现代的概念。2003年,我在杭州有个个展,我为自己起名叫“超现代水墨”。陈孝信老师那年到杭州给我说了一句话,说你的水墨已经不是现代水墨,而是当代水墨。那是我第一次以当代水墨看自己。在今天,当代的概念已经非常流行和普及,艺术发展到今天,世界变得越来越透明。中国如果有了当代艺术,需要在世界的当代艺术中有一个定位成为了一种愿望。作为中国的当代艺术有一些问题必须考虑,这种艺术是否具有国际性?与自己的传统是什么关联?艺术的国际性方面,不要选择从哪一种艺术形式、流派入手,而从他们共有指向上为什么要有艺术?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怎么产生的?艺术与自己到底是什么关系?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艺术与人的灵魂相关,与人的内心相关,与视觉相关。在传统关系方面,对中国所有时代、所有时期的艺术进行研究,抛弃所有艺术的表象方面,留下了艺术语言这个最基本表达方式,就是用毛笔的思维。崔振宽的作品解决了用毛笔的问题,好像线刻在石头上面,非常有力量,解决了艺术与我的问题、与自我内心世界的问题、与自我身体的问题、与灵魂的问题、与宇宙世界的问题、与艺术视觉的问题。这次展览以新写意主义为主题,一个是进一步阐述这个学术命题,二是阐明中国当代艺术有什么特别之处,与西方比较,与传统比较有什么关联。中国与西方在生活和文化方式上正在融合,而且在加速,没有必要为了区别而区别,唯有语言的表达方式有不同。语言就是核心,这是我对艺术出发点的认识。吴国全:要了解我们的创作思想,去看作品是最好的。我的作品这几年最重要的几个方面,具体就是改变工具、改变材料、改变自己。人的改变最重要,不同的温度应该穿不一样薄厚的衣服。今天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于30、40年前。王 昀:首先非常荣幸能参与到新写意主义主题的展览和讨论当中。新写意主义这个展览,或者说这个理论层面的探索,艺术理论家们在前半段已经谈的非常深刻了,我自己感觉这次的新写意展览显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状态。比如说,能够容许我的这个根本上没有什么意义,同时也不知道是在画的什么东西,更没有意在笔先,或去表达某种意义的“划痕”系列的参与展示,这让我感受到了新写意的包容性所在。前面老师们在讲,新写意是为了最终与西方的表现主义进行一个对话,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但同时也不免让人感觉到悲哀,为什么一定要分东方和西方?要把我们的一个概念看成东方的去和一个西方的概念进行对话?质疑这个事情是因为在艺术或在文化的讨论上,先行在感念上划分出东方和西方。我个人感觉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我看来不同是显而易见的,而不同中有哪些相同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谈到两个理解,一个是我们能不能以一个共通的人作为思考的起点?讨论人和艺术、人和绘画、人和我们所要表现东西的关联,而不是说柬埔寨人、越南人、老挝人、中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艺术的关系。我认为人种问题是第二属性,因为国家的概念、民族的概念究竟是在什么范围里面,艺术或文化是以哪个朝代,哪个时间点来划分比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讨论问题的基础问题。比如对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讨论,谈到宋代建筑时,同时还有辽代建筑。可如果放到当时的状态,宋国和辽国曾经是两个敌对国,当然从今天看来,这是在中国的大概念下来进行阐述和联想的,但问题是,一旦变得非常地域和在狭隘的范围来讨论艺术问题,往往会带来非常多的额外的并且和艺术本身没有关系的问题。其实今天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表达的当然也应该是中国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囊括了从细胞生物开始一直到今天的所有积淀,我现在的身体,是从我的祖先、从那个微生物的小虫子开始,一直到过程中的所有生物状态的那些遗传基因的凝聚,成为我目前身体的表象,因此我做的一切也是中国人做的一切,同时也是人所做的一切。谈到“划痕”的概念,其实人生就是一个留下划痕的过程,我的划痕系列就是这种表达。过程中的工具是否那么重要,也是有疑问的。在纸上留下划痕,有毛笔就用毛笔画,有铅笔就用铅笔画。第二个问题,我想说,其实单独的去看西方表现主义,它并没有完成真正的“表现”,因为那些表现主义艺术家其整个的表现过程还受“视觉”的影响和支配。作为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如何超越视觉的制限,将表现的充分性再向前推到哪一步,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在以往的不断的观察中,我发现表现主义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是因为在作品完成的过程中有视觉的存在,一旦眼睛看了以后,表现就会受到牵制,之前学到的知识、所受到的影响就会体现出来,如此以来,这是否可以被称为是纯粹的表现?这是第一个疑问。之所以产生这个疑问,是因为所有的表现主义绘画的画面中还存在有构图,而构图其实是理性的表达,如果继续推进表现,构图是否真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绘画其实也是一种实验,那就是在某一特别想画画的瞬间,闭上眼睛,拿起笔来盲目地一画。2号厅陈列的几个作品是我一系列盲目划痕的结果。刚才有一位老师谈,在画画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很多是在画完之后想的,我很认同,画的时候不知道,画完之后感觉这不就是一个老虎、一头大象、一条龙嘛。所谓的意,有可能在于你的发现,“胸有成竹”应该是一种‘再现’,而在‘表现’层面上可能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儿。 其实我在这个屋子里发现了两个巨大的大写意画(笑,边说边指开会的会议厅天花板上两块漏水形成的污迹),这两个天然的水墨画非常精彩,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具有某种灵性的东西,而且在某个部位还有着光亮(边说边指被污迹包裹的天花板上的筒灯,笑),这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写意的内容之一呢?我想,写意可能是一种‘发泄’和‘发现’的过程,‘发泄’在先,随后从所‘发泄’的结果中再去‘发现’意。但问题是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的人可能面对同一个‘发泄’出的结果中所‘发现’的意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感觉这才是写意这件事儿有意思的地方和他能够造成多种可能性的价值,而不是上来就说我的写意是一个大老虎,传达给所看画的人都必须只能够从中看出是一只大老虎。如果一张画,有人说这是大老虎,那人说不是,是一只大猫,那个人说是一头大象,使得更多人发现了更多有意义的东西,这种东西才是我想的“新写意”。关于是否是中国的绘画的问题,实际上,即使闭上眼睛画也逃脱不了你是中国人的事实,因为你作为中国人的身体积淀的本身已经决定了结果。我想,中国人做的艺术作品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中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高兴,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国际视野,能够让世界各个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人,换句话来说,让“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作品是一个好东西,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艺术家应该为之努力的一个方向。胡又笨:所有的表达都在作品里,我讲两句话。为什么评论家和画家需要坐在一起,如果我们艺术家特别能说的话,特别能理论的话,就可以当理论家。画都放在那了,第一,纪念刘老师,不忘刘老师,第二点昨天和以前的作品都是废料。李惠昌:西方表现主义的意义,不能仅仅理解是艺术家个人的一种宣泄式的绘画样式。在西方很多表现主义优秀作品中,其实他们很重视用笔及对笔触意味的讲究。如梵高,德库宁以及莫兰迪画的瓶子等等,他们在形态上及用笔上同中国文人画一样,很重视用笔的气息及笔触。刘老师由此处切入对话,我猜想,其目的是把写意精神同格林伯格的笔触意味相对的研究出中国“意”的丰富性,加上中国独有的逸品美学思想,就会占有主动性,进而与西方平等对话。这是中国批评家的睿智。因为我们面对西方庞大而有序的整体阵容是无法对等的。我想刘老师提出的新写意主义是面对西方整体阵容,是从局部切入,这个角度也正是形态学从整体到局部,再从局部到整体研究的一种方法。是从水墨艺术的本体而考虑与采用的。中国“意象”有别于西方的抽象思维。中国的意象根基是庄子讲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可见中国之写意,与格林伯格对比不是笔触的意味,而是临界与“逸”的高层美学观。我们从刘老师、王老师、夏老师共同打造的多元水墨呈现方案中,就不难理解,这个新写意主义,绝不局限在书写性作品的表面,更拓宽了“意”的思想含义,并纳入了对社会批判性作品及装置和新媒介作品。这个展示即运用了国际化现当代的呈现方式,也守住了中国意象的“核”。这说明刘老师的学术研究不仅限于形态学或者语言学范畴,他一贯对艺术本质的强调,并不等于对社会学、意识形态的轻视,而是水墨的本质性,迫使他更着力形态学研究。与欧美对话,水墨艺术恰恰不易从社会学、意识形态切入,这是老批评家思想成熟的选择。中国的“意象”的意指性,同样体现了我们每个艺术家对“意”的新思考,新建立。我有幸加入,深感荣幸。张方白:很多年以后我们再来回看今天的场景,会觉得太震撼了。中国人一直是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争夺话语权,显示我们民族的力量。我觉得今天是20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的体现,是理论家跟实践者一起合力的结果。从杜尚之后,西方的艺术也是到了一个节点。博伊斯也好,安迪 · 沃霍尔也好他们都无法再超越了。因为艺术所有的界限都已经被打破,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如果是完全打破的话,那么以西方为主线的现代艺术其实已经终结了。那么终结之后,他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更民主更开放的一个世界,就是各个民族、国家都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实际上这又回到了艺术的本源,艺术的本源就是表达自己的生存意志。所以我觉得杜尚之后实际上对全世界来说,机会都是平等的。那么就应该去选择我们自己最有力的东西,最能表现我们的东西。这种选择又是基于潮流和个体的选择。中国艺术从85思潮、政治波普,到今天大家称谓的文脉精神、新写意、意派等等,包括我也提出了一个“中国表现”这个概念,还建立了一个中国表现艺术研究中心——其实这些都是20年来我们在这个语境下做出的共同的努力。这个命名最终会呈现一个最能体现我们这个艺术本质的名字。但是谁提出来他就是伟大的评论家;谁把这个作品画出来,他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回顾历史之后,我们会发现这20多年来是中国人非常幸福的时光。我自己也感觉到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幸运的时代的。去年我和靳尚谊先生去维也纳领一个奖,靳先生总结他的艺术时说“他一辈子在研究油画”。问到我的时候,我灵机一动,我就说“我的艺术是孤独的自我的抗争”。后来我发现我这句话概括的挺好,就是从艺几十年来啊,我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抗争中,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一点点存在感。那么我在抗争什么呢,它有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说我看波洛克的画,我就觉得波洛克的线条就是装饰性线条,他只是发泄他内心的情绪缺少内涵,没有像中国人对于这个线条的品质的把玩——比如看崔振宽先生的线,刚才张浩在说崔先生的线是刻出来的——这个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积淀,没有这个积淀,没有这个修养,就达不到这个高度。这点对西方人来讲是真的没法理解的。艺术是没办法得到互相的承认的,西方人他不理解这个线,而我们理解。我们也不理解西方的很多东西,所以艺术是一个战争。这个好像是马路老师从德国回来时说,艺术是一场文化战争。我赞同此说,必须强有力的争夺才能获得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再回到毕加索的画,毕加索晚年一直想超越的就是打破形,得到一个更自由的境界。这点波洛克后来把那个形彻底的解放了。那么波洛克之后基弗呢,其实是用了波洛克的满幅构图——地平线直线条,他也是找到了他的一个存在感。但是基弗也不是神,基弗的形其实还是有一些简单,我们只是被他庞大的气场震住了。这20多年,从我个人来说,其实就是在画室里度过的。每一天我可以对我的一笔一划进行揣摩……我的线就是毛绒绒的线,这是欧洲市场选择我的时候的一个理由,他们说“基弗也不是,塔皮埃斯也不是”,反正是说这个线是你自己的线。我找到了一点存在感。还有一点,我希望我的笔墨能达到塞尚的那个厚度。再者,我更多的关注点是在结构上,我希望每一张画都能够超出我最强的那个结构感。这个时代已经是图片化的时代,对于视觉的张力已经忽略了,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话题。在20多年的抗争中,我渐渐找到我自己的感觉,渐渐地建立了我的自我的存在、物象。每次当我把这种内心的一个心象展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作品完成了。西安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刘西洁先生刘西洁:首先对已故的美术理论家刘骁纯先生深感怀念,对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崔振宽先生、郭全忠先生致以敬意,感谢策展人夏可君,感谢崔振宽美术馆及崔迅馆长。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参加“新写意主义”的展览,对我来说又是一次很好的展示自己艺术创作同大家交流的机会。今天,理论家和批评家对我们的作品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在这个展览上受益匪浅。下面对刘骁纯先生“新写意主义”概念的提出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关于“新写意主义”,从我自身绘画实践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明确这个概念的含义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从地域文化、地理方位、空间与时间等的关系中而产生的。改革开放这40年以来,西方现当代艺术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以往有巨大的不同,多是艺术家凭借直觉直接接纳,少有较完整的做理论的比较梳理。从东西方艺术整体形态的比较来讲,其方法论上有很大不同,我们少有体系并概念模糊而朦胧,这同我们传统的哲学观以及天人合一思想有关,也从未有过什么主义。有关“主义”,自然是从西方借鉴而来。今天提出的“新写意主义”,大家都清楚和这些年绘画界所讨论的表现主义有关,与表现主义的绘画行为方式有关。但非与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德国表现主义、还是抽象表现主义以及其它各种主义的产生直接发生关联。因为文化历史的不同,东方的写意性和表现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其差异,刘骁纯先生提出的“新写意主义”的概念实际也就不难理解了。怎么样去理解呢?比如说,徐渭的大写意绘画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根脉上阐释的,“新写意主义”可以从这里找寻到它的根脉和根源。从徐渭到齐白石实际上是纯粹的写意画,但是在“新写意主义”的展览中,崔振宽先生的山水画作品《山之皴系列》已不是传统借物抒情的大写意绘画了,是带有观念性的,是对艺术的本体的重新认识,是对传统写意概念的延伸,从而生成一个与“新写意主义”相关的写意形态。当然展览中的有些作品是借鉴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语言形式的。“新写意主义”所阐释的并不是客观的、简单的意象,已经贯穿了现代人对宇宙观、社会观的重新认知,尤其是对艺术本体概念的重新建构。刘骁纯老师作为理论家,在对“新写意主义”的梳理和归纳中做出了贡献。艺术家应该更多的是感受,从而去创作出自己的作品。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展览,谢谢!夏福宁:感谢西安崔振宽美术馆对我的邀请,感谢策展人夏可君,把我的作品归在新写意主义里面。夏可君是我2018年个展“呼与吸”的策展人,他对我作品的精神性、呼吸和生命感有独到的评述。刘骁纯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一个视野开阔、胸怀宽广、与艺术家相通的评论家,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对作品的意念、精神性表达情有独钟,对画面的神性和意外之处有深度的探索,对书写性有深入的表达,打破常规追求“不正确”意料之外的东西。在不断的探索中离神性愈来愈近,与本真愈来愈近。写意的概念对我的启迪应该是开拓视野,把西方的表现、观念等与传统的东方写意相融、并消化吸收后,表现出你内心的、深刻的、独特而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我以为艺术家作为个体,作品的个性及私密性尤为重要,好作品的内核都是具有深层次的潜藏和极致的表达。绘画不是一个表象的东西,深藏才有意思,藏得越玄妙越有味道,其实后面的东西更有感染力,为此我打破所有的禁忌,探寻更多的可能性。谢谢大家!王 非:“写意”就是书写性,是释放能量、表达主体意志的技术方式。“新写意”与传统写意不同,是针对历史文化下水墨集体意志、集体道德的现代性反判和精神超越。“新写意”亦不同于德国表现主义尼采式的“酒神”救赎和布勒东自动主义的偶发性发现,它更趋向一种隐遁文化的现代诠释,是内空间的超道德完善,它与现实政治、公共伦理以及普世的未来主义保有一定距离。“新写意”属于中国式的艺术模式,有待于将历史压制下的生命灵性从程式化的符号中解救出来,并赋予崭新的、高贵的艺术形式,即形态学的世界发现。在所有参展艺术家中,各位是前辈或师长。在你们面前,我是晚辈、后辈。但我年过半百,在年轻人面前则是一个前辈。我刚刚回国5年,我给自己定位为老年新锐,没有压力,自由地感受生活,艺术创作上就没有什么负担。我一辈子想秉持着一个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地胡思乱想。我创作最基本的要素:我活着、我体验、我感受,把它物化在我的作品中,希望一生如此。谢谢各位!孙大壶:谢谢主办方崔振宽美术馆,谢谢策展人,谢谢各位评论人。我是孙大壶,来自上海。我的这次用于新写意主义的出展作品和概述,画册里面都有了,遗憾有几幅没有带来展出,大家可以再做一下了解。我想说的是,艺术家很努力地根据独自的理念和手法创作出来的作品,一旦离开了作者自己,对作品的认知和评判已然属于观者。还有,想提一下,那些很强调概念先行和地域性比较的论述,很难被认可其能为当代艺术的前行带来裨益。希望艺评家们能更开放视界和知识结构的升级。就说上这几句,谢谢大家。夏可君: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各位批评家,各位艺术家参加今天的活动,谢谢各位媒体和听众,陕西有文化、陕西有未来,我们新写意主义也有未来,谢谢大家。
展览时间:2020年9月19日—11月1日(周一闭馆)
免 费 对 公 众 开 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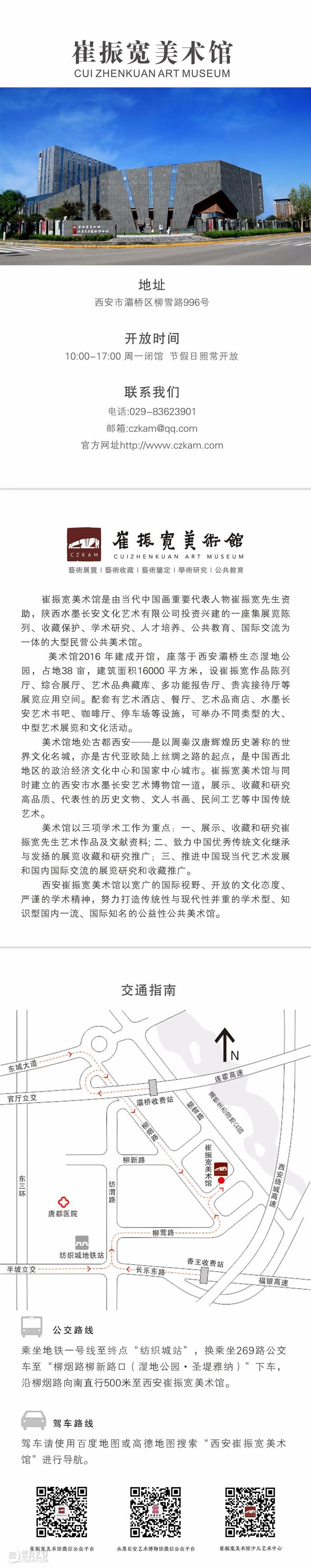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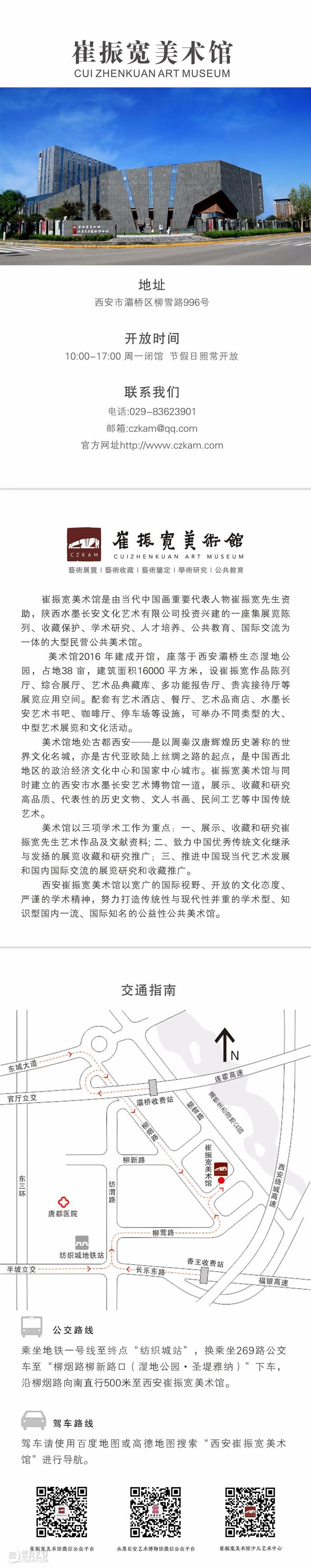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