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格尔论爱的转变
弗雷德里克·拜塞尔 著,王志宏 姜佑福 译
选自《黑格尔》,华夏出版社,2019年
无论精神概念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有一点应该是明显的,那就是,黑格尔后期的精神概念和辩证法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他早期关于爱的经验的反思。这些概念初看起来是如此晦涩难解,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到它们的原初语境之中,似乎就具有了它们完满的含义和要点。但是现在一个困难的问题出现了:一旦它们的原初的语境和目标消失了,这些概念又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他的后期著作中,黑格尔继续使用精神和辩证法等概念;但是,他不再赋予爱以他曾经在早期著作中赋予它的那种重要性。这意味着精神和辩证法等概念失去了它们原初的意义吗?
在如何处理爱这方面,在早期黑格尔和成熟的黑格尔之间至少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差异。首先,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认为,爱的经验是一种神秘,确切地说,是一个奇迹,它不能用推论的形式加以表达。然而,在他后期的岁月中,黑格尔将要尝试着以某种推论的形式来把握爱的经验、生命的过程。他一方面继续强调,这种经验和过程超越了知性的诸概念;另一方面,他也强调说,它们能够通过理性的辩证法加以把握。知性作为一种分析的能力把对象整体加以划分和解析,所以无法把握住它们;但是理性作为一种综合的能力能够把诸部分统一为一个整体,并指出,除去整体,没有任何部分能够靠其本身而存在。然而,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依据知性来看待所有思维;因此,任何不可划分的事物,任何必须被理解为有机整体的事物,都超越了知识的理解的范围。我们必须经验它;但是我们不能构想或者证明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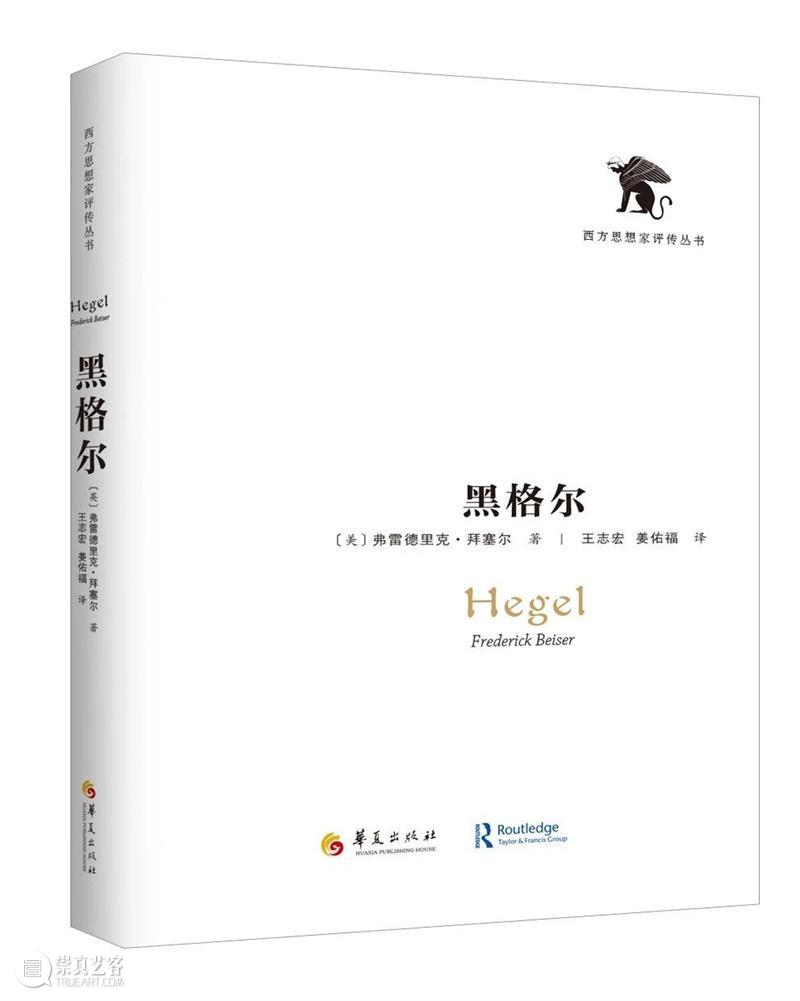
在黑格尔早期和晚期关于爱的讨论中的另一个基本的差异涉及他后期的体系中爱的意义。从他早期耶拿时期开始,黑格尔就不再赋予爱以他的体系中那样一种核心的和至关重要的位置。与爱相比,伦理生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关联很快就后来居上,赢得了他的青睐,最终,爱被相互承认取而代之。在1802年~1803年的《伦理生活的体系》中,黑格尔声明,主客同一之实现,不是在爱之中,而是在共同体中公民之间的相互承认之中。他论证说,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不能在爱中发现的,因为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只是一种自然的联系,而这些伙伴不是处在同等条件之下。男性是理性的,代表着科学、商业和国家等普遍的兴趣(利益);女性是情感的和直观的,仅仅代表她的家庭的个体利益面行动。1805年的《精神哲学》沿着这一方面继续前进。现在爱限制在家庭的范围之内,它只是伦理生活的初级的无意识的形式。现在,黑格尔争辩说,不再是爱,而是只有伦理生活的道德的和法律的关联才赋予某人作为理性的或者普遍的存在者的自我意识。尽管爱的确是对立中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不同的人通过对方而成为具有自我意识者,但是它只是自我意识的初级形式。爱人自我意识到的只是他们特殊的人格,而他们的联系只是被他们的稍纵即逝的自然欲望创造出来的。耶拿时期的这些发展,在黑格尔1821年的《法哲学》中达到顶点。在该书中,黑格尔把爱限制在家庭的领域。
在后期的体系中对于爱的贬黜和黑格尔后期对于一种关于精神领域的理性解说的需求是齐头并进的。由于它变成了理性的对象,精神自身变得更加理性了。后来黑格尔把理性变成了精神的一种定义性的特征。就其本性而言,爱更不适宜以理性讨论的方式来处理;它的欲望,感觉和直观都低于理性把握的门槛。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发展似乎证实了黑格尔最初对于概念思想所持的浪漫主义异议;在试图构想爱之时,理性使得它变得更加合理,而这样做又会破坏它的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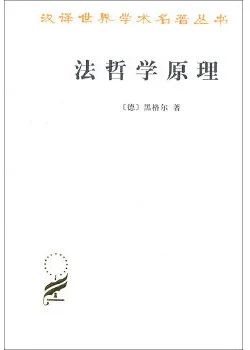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也早已在黑格尔的早期岁月中有其滥觞。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就曾经把爱提升到宗教和道德的最高原则之中。但是,即使在他的伯尔尼时期,他对基督教的伦理仍然心存怀疑(参见第126页~第131页)。这些怀疑在法兰克福时期,甚至是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又开始浮出水面。在这本著作中,黑格尔已经拥护他的浪漫的福音了。当然,爱的伦理就是耶稣的福音。但是,黑格尔在那种福音中看到某些致命的弱点。他论证说,这样一种伦理更适合一个教派,而不是共同体整体,因为我能够爱我的教会中的兄弟们;但是,我很难爱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和我没有共同信仰的人。还很难的是把基督教的伦理——这种伦理要求我们放弃一切东西——等同于对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而言如此重要的财产权。尽管如此,一切之中最糟糕的是,基督教伦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实在是太美、太好了!它非但不通过斗争以使得这个世界变成更好的地方,相反,它试图躲避它,向我们应许在天堂的得救。基督徒非但不为了他的各种权利而斗争,相反,他们完全放弃这些权利,转过另一边脸来让人打。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解释了耶稣是如何由于饱受他的教义不能在犹太人之中扎根之苦,他自己最终和尘世一刀两断,把自己仅仅限制在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之中,并且宣扬一个人应该把凯撒的归凯撒的。耶稣面临一个困境:进人世界而让自己妥协,或者坚守一个人的纯洁性而逃离世界(第328页)。耶稣选择了坚持它的纯洁性,因此他从生活中撤离了出来。结果,他的伦理变成了与这个世界毫无干系。因为他拒绝和这个世界相妥协,因为它从这个世界撤离出去以维护他的纯洁,耶稣只能在虚空之中发现自由。然而,黑格尔教导说,一个只能通过逃离世界才能试图拯救他的灵魂的人只能失去它。一颗被高高举过所有的权利之束缚的心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与或者宽恕(第286页)。从黑格尔关于优美灵魂的解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认为,它的(按指基督教的)伦理品质高贵而充满瑕疵:说它品质高贵,是因为它克服了道德法则、正义的需求,并且特许了宽恕和避免了诸权利之间的冲突;说它充满瑕疵,是因为它从诸法律的瓜葛和冲突中抽离出来的行为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那么,早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我们就看到黑格尔后期哲学的一条基本学说: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不是来自于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逃离,而是来自于如何与他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
正是对于基督教伦理的这些疑虑后来迫使黑格尔在他的成熟的体系之中贬黜爱的角色。早在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就已经意识到,爱并不能拥有他想要赋予它的那种最高的重要性。这只不过事关彻底思考这个主题、放下爱的伦理,以及最大程度地发现一种更适合于共同体的伦理而已,这种伦理和世界上的生活更加相宜。黑格尔在耶拿岁月的后期,在《伦理生活的体系》和《精神生活》中所转向的正是这个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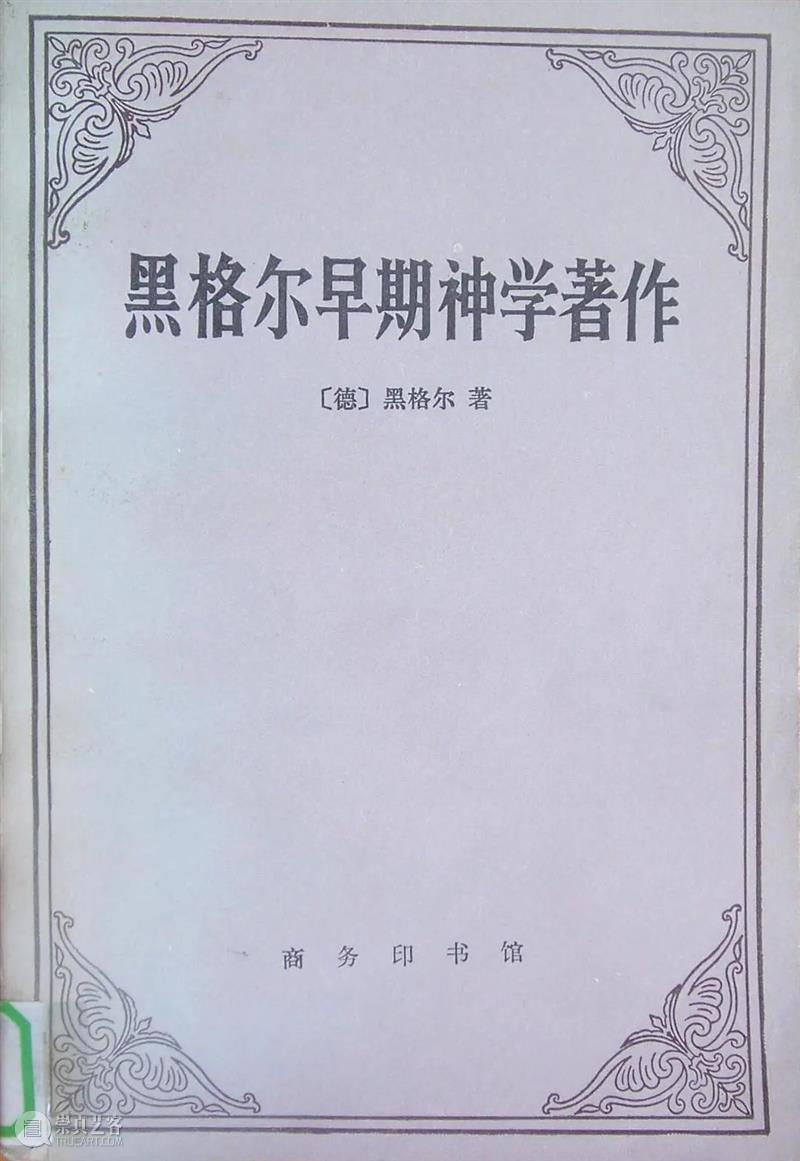
尽管在法兰克福时期以后,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据此推断黑格尔最初关于爱的反思对于他后期的精神概念意义寥寥,或者毫无意义,那也是错误的。后期的概念仍然显示出和爱自身一样的结构和发展:其中存在着自我发现和自我破坏的环节、外在化和内在化的环节,以及存在着同样的有机的发展模式:从统一体到差异,再到差异中的统一。所有这些爱所独具的特征都被整合进了相互承认的主题,而现在黑格尔将之看作是精神的定义。只不过爱的主体间的维度被转换成了理性自身的定义特征。
认为爱在后期的体系之中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是错误的。尽管爱不再是精神的顶点,它仍然保持为它的原初的家和出发点。在他后期关于爱的讨论中,家成了伦理生活的最初的基础,它是精神自身的出发点。在1821年的《法哲学》中,黑格尔将坚持认为精神是如何在伦理生活的领域中现实化的(第156-157节),以及家中的爱是如何成为伦理生活自身的基础的(第158节)。可以肯定的是,爱仍然是精神的一种初级形式,因为它还没有意识到自身是一个理性的而只是感觉和欲望的中介形式;尽管如此,爱的确标志着精神的“直接的实体性”(第158节)。
现在要看到的要点是,在黑格尔早期和晚期的精神概念之中的最终差异,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的差异,而非实质的差异。精神在早期和晚期黑格尔那里保持为同一物;只是在后期黑格尔那里,精神才变成了对它自身的自我意识,而它的自我意识牵涉到理性的理解。为了成为自我意识的,精神必须知道它自己是受制于权利和义务所组成的道德的和法律的领域的。当然,爱存在于欲望和感觉之中,而感觉和欲望是低于理性的理解的门槛的;但是黑格尔认为,反思不是破坏而是实现了爱,并且在爱之中达到顶点。在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一点,即黑格尔后来在他的宗教哲学中强调:尽管理性的反思改变了感觉和直观的形式,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它的内容;实际上,它是那种内容的实现和现实化,而那种内容只是在感性的领域以萌蘖的和混乱的形式存在着(参见第146页~第152页)。理性的反思因此就不是爱的破坏,而是它的最高程度的组织和发展。那么,最终,黑格尔成熟的哲学中的精神就无非是他在法兰克福时期一度颂扬过的那种爱的理性化和制度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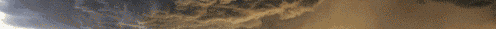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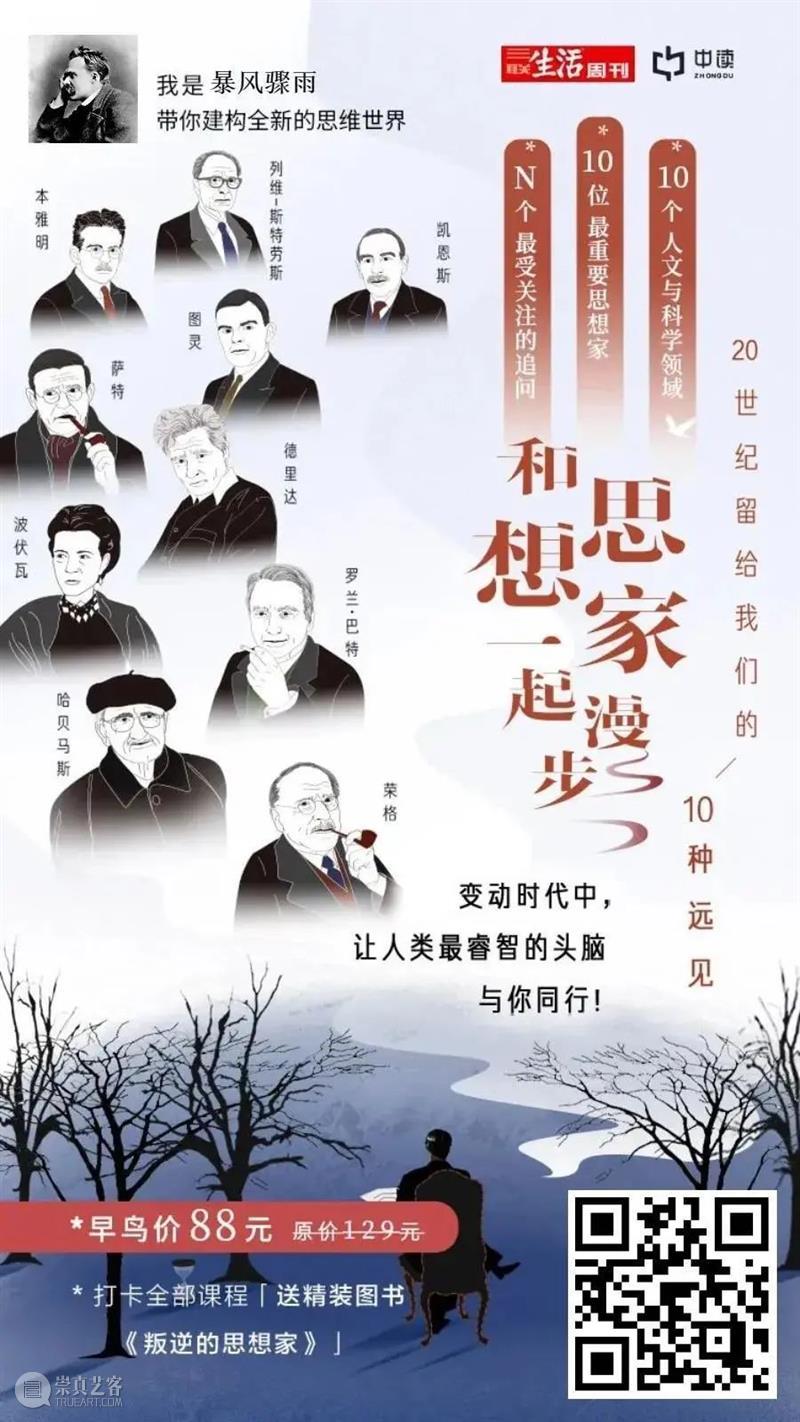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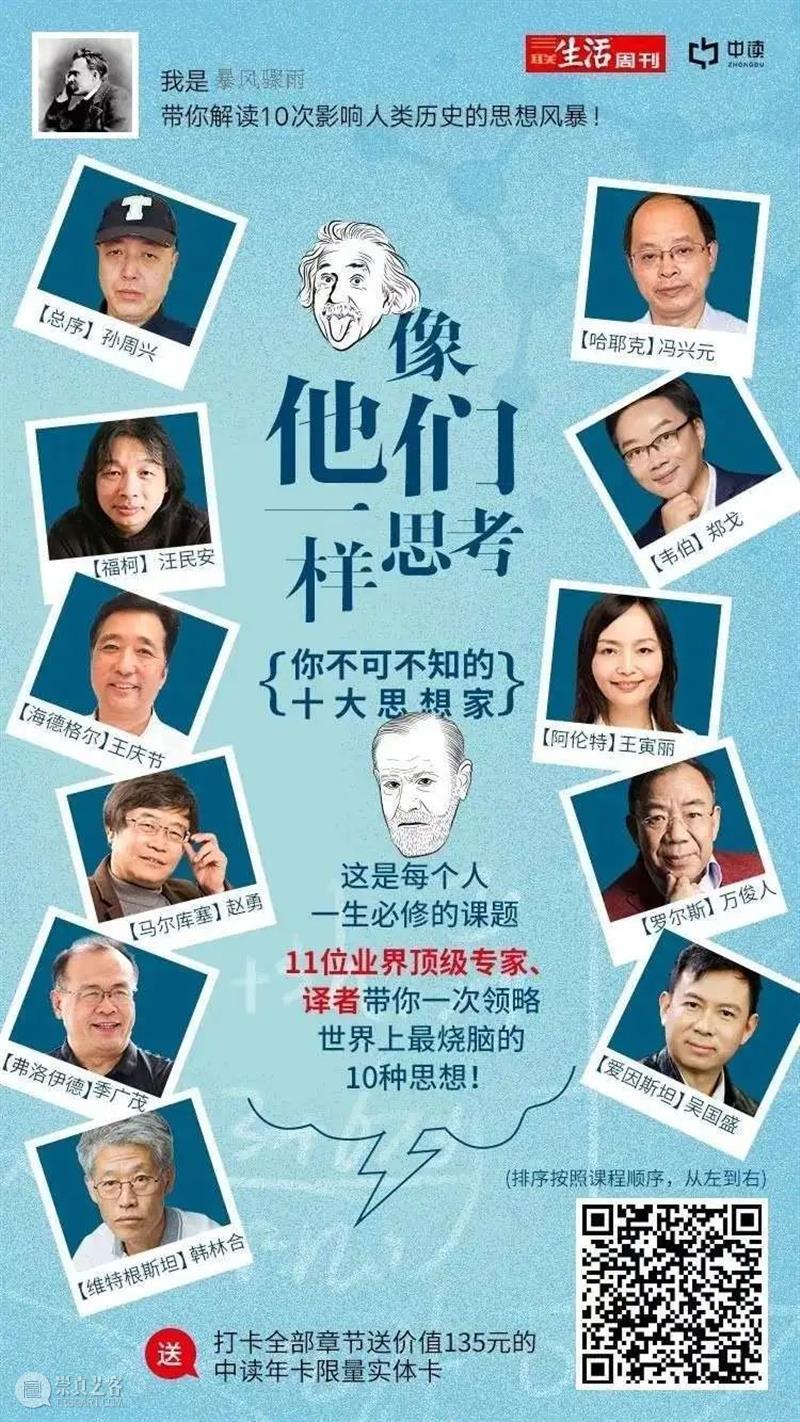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