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艺术与死者纪念
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
选自《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文化记忆的人类学的内核是死者记忆(Totengedächtnis)。意思是说家属有义务在记忆中保留死者的名字,并尽量使其流传后世。死者记忆有一个宗教的和一个世俗的维度,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尽孝”(Pietas)和“声望”(Fama),并将之对比来看。尽孝是指后人的义务,保证对死者进行满怀敬意的纪念。尽孝只能由他人、由生者为死者进行。而声望,也就是说一种光荣的纪念,却可以由每个人生前在某种程度上就做好准备。声望是自我不朽化的一种世俗的形式,它和自我演绎关系密切。中世纪的基督教关注末日审判时灵魂的得救,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古希腊罗马对死后光荣纪念的关注。
但是即使宗教性的死者纪念也需要依赖生者的回忆。把生者和死者联系起来的最原初、最普遍的社会性回忆的形式是死者崇拜。在古代埃及,死者纪念,也就是个人名字的不朽,在文化生活中具有核心的意义,那里每年都会举行“沙漠谷的美丽节日”,在这个节日里全家人(在后来以阿拉伯人为主的埃及仍然如此)会到家人的墓地去,在死者面前和死者一起举行一场盛宴。吃喝是建立共同体的基本形式,在坟墓边完成这种形式使得生者和死者能够达到想象中的联合。
死者盛宴这种做法在古罗马和早期基督教世界中仍很普遍,直到4世纪的末期,教会在安布罗斯主教的主持下把这种家庭形式的死者崇拜排挤出去,推出了一种集中化的形式。对殉道者的集体纪念取代了为家庭成员举行的死者纪念,殉道者的骨殖被移葬到城市教堂里;家庭内部举行的小范围的死者盛宴消失了,一种社会化的新形式出现了,那就是教区全体信众参加的最后的晚餐。
中世纪死者纪念的实践由两个元素构成:关怀死者(Totensorge)和关怀穷人(Armensorge)。它们之间的联系可以用第三个元素来解释,那就是炼狱。炼狱作为一个神秘的地方,人们对它的想象越清楚,得到救赎的不确定性就变得越大,基督徒也就愿意付出更大的努力,为减轻可能的炼狱之火的折磨而提前做好准备。炼狱的岀现在个人的死亡和上帝的末日审判之间留出了一段受难的时间间歇;死者在这个过渡期的命运,按照格里高利一世的说法,可以通过生者来施加有利于死者的影响。因此每个人在生前都致力于通过尘世的功德保证他们灵魂的得救。而教会和修道院就提供这种服务,就像克吕尼修道院专门致力于完成这种任务,并由此发展出一个大规模的救赎工业一样。
关怀死者就是使他的名字不朽,他的名字会在每年的命名日和节日被放进弥撒祈祷文中,并写进的的确确名为“永生册”(Buch des Lebens)的簿子中。这种记录工作被从万能的上帝的手里接了过来,交给修士们来做。宗教团体以友爱书的形式相互交换他们的名单(有时其中的名字会多达三万个)并且保证相互进行记忆的工作。关怀穷人则包括赠物和施金,以此给穷人们提供饭食,这些慈善的行为可以消除生前的罪孽。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留在集体的记忆中,因为集体可以通过弥撒仪式和施舍穷人对灵魂在炼狱中的命运施加积极的影响。
死者纪念(Totenmemoria)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8世纪,直到法律制度和主体概念发生了一场具有文化史意义的转变之后,它才被取消。历史学家把死者权益的终结看作是死者纪念传统断裂的最明确的证明:
对死者在场的想象,也就是说在生者的记忆里死者仍具有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想象,尤其在18世纪的进程中渐渐退却了,大约在1800年,随着现代社会的开端,这种想象开始消失。……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的时期相比,已经不存在死者权益了。死者不再是法律主体。按照现代法律, 法人资格随着死亡就消失了。
死者纪念作为文化记忆的典型案例,其意义从两个传奇故事中表现出来,这两个故事都围绕着一个古希腊诗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故事被西塞罗看作是记忆术的产生传奇,合唱诗人、来自凯阿岛的西蒙尼德斯(Simonides von Keos,约公元前557—前467)就是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西蒙尼德斯被视为第一个收费的诗人,他除了歌颂神祇和英雄们之外,还为尘世的凡人唱颂赞歌。关于这位西蒙尼德斯有一个故事,他受聘于拳击手斯科帕斯,在其家中举行的一次庆典上用赞美诗来赞扬他。为此,西蒙尼德斯在参加庆典的客人们面前吟诵了一首诗,这首诗却没有得到他的雇主的赞赏。按照这种题材的传统,除了对商议好的对象的歌颂之外,还通常包括一段较长的关于神祇的内容,在这首诗里是关于宙斯的双生子卡斯托尔和帕鲁可斯。斯科帕斯的反应充满讽刺意味:西蒙尼德斯只能指望从他这里拿到商定好的酬金的一半,另一半他应该去找被他极力赞颂的那两位神仙讨要。这时,这位古希腊诗人被叫到外边,据说门口有两个陌生人找他。西蒙尼德斯走出房子,但是根本没有看到这两个人。与此同时,一场不幸发生了:斯科帕斯的庆典大厅倒塌了,把主人和他的客人们都埋在了瓦砾堆下。西蒙尼德斯是这场灾难中唯一幸存下来的人,这就是神祇给他的报酬。但是故事到这儿并没有结束。诗人还要再发挥一次作用,这次不再是为了荣誉和声望的目的,而是为了祭奠死者。如果辨认不岀死者的身份,祭奠活动就无法进行。西蒙尼德斯已经把所有客人的详细座次都储存在记忆里,他能够把每一个肢体残缺的死者的身份辨别出来。基于这种辨认,家属才可以对他们的死者表示敬意,将他们体面地埋葬,并且能够确信他们为之哭泣的死者没有搞错。从古希腊罗马记忆术的角度来看,这个灾难故事有一个欢喜的结局:西蒙尼德斯第一次实践了以后可以系统地讲授和学习的东西。他的事迹显示了人的记忆力可以超越死亡和毁灭的力量,并在这个传奇中变得永恒。
但是古罗马记忆术的产生传奇却不一定能证实它本身是一个可靠的记忆。昆体良就已经引经据典地对这个故事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他表示不能肯定,故事中提到的庆典大厅位于什么地方,是在法萨罗斯还是在克拉侬。对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的怀疑今天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斯特凡·戈尔德曼曾经考察过这个故事的流传历史,他视之为一个“过去的和当下的经验通过社会想象力而进行变化和融合的过程”。还有,他认为,西塞罗展示的文本“已经被许多代的人歌唱过了,并且把历史事件和神话融合在了一起”。所以在说起这个传奇时,戈尔德曼甚至把它称为一个“历史的掩饰性回忆”(historische Deckerinnerung)。记忆术的起源故事本身并没有把一个真实的回忆保留下来,而是把回忆的可塑性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关于同一个西蒙尼德斯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流传下来。按照这个故事的说法,他在异国他乡旅行时,曾看到路边躺着一具没有掩埋的尸体。西蒙尼德斯中断旅行,为这个陌生的死者亲自操持了一场体面的葬礼。在其后的夜里,死者的魂灵在他的梦中显现,警告他不要踏上已经计划好的海上旅途。西蒙尼德斯本打算乘船,因为这个警告就没有上船,船后来确实遇到海难沉没了,所有乘客都丧了命。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很久之后用一首十四行诗为这位西蒙尼德斯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这第二个西蒙尼德斯的传奇并不是凸显他的记忆力,而是强调他对死者的特别的敬意,因为他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操持了一场合乎礼仪的葬礼。华兹华斯把他称为“温柔的诗人”(the tenderest poet)并且让这首诗以"虔敬”(piety)结束。因为西蒙尼德斯用他的行为证实了人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人之为人,并不应该局限在自己的群体内,而是已经扩展到普世的范围。就像发明记忆术的西蒙尼德斯那样,执行死者纪念的西蒙尼德斯也得到了报答,那就是在一场灾难之前神奇地获救,而这场灾难毁灭了除他之外所有的人。死者的魂灵在这里不像人们害怕的那样还魂或者复仇,而是与之相反,变成了一个个人的守护天使 和行善者。尊重死者在这里也就有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安抚死者,阻止他们进行危险的回归。
在这两个传奇故事中,西蒙尼德斯的名字都在死亡、毁灭和遗忘的黑暗背景之上闪闪发光。只有他的名字,只有他的故事找到了进入文化记忆的渠道,当然西塞罗的传奇故事和华兹华斯的十四行诗也为此做出了贡献:“使其免于泯灭”(Saved out of many) 。另外,通过两个西蒙尼德斯的传奇故事,多种记忆维度之间的原本的联系也隐隐显现出来:死者回忆、纪念、声望和记忆术。两个故事都提到死者回忆,但是在第二个传奇故事中并不是有关死者个人的名字,而是更根本地关于人们应该为死者做的事情。死者记忆中尊重死者的原则正回答了一个普遍的文化禁忌。死者必须得到埋葬和安息,否则他们就会打扰生者的安宁,危害社会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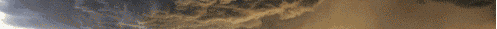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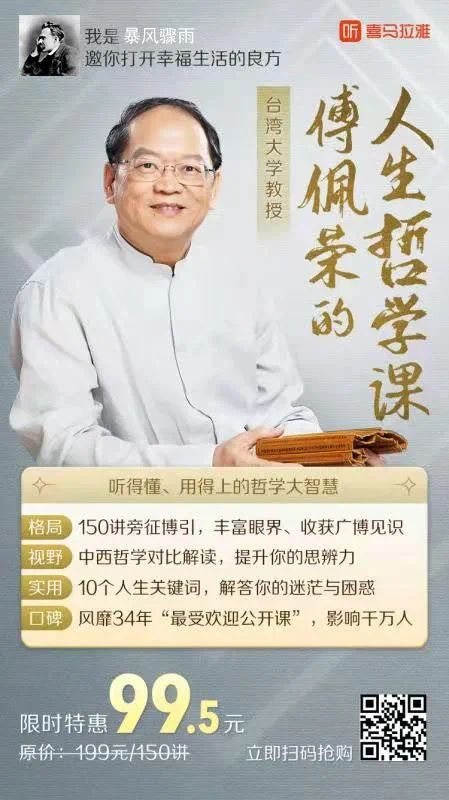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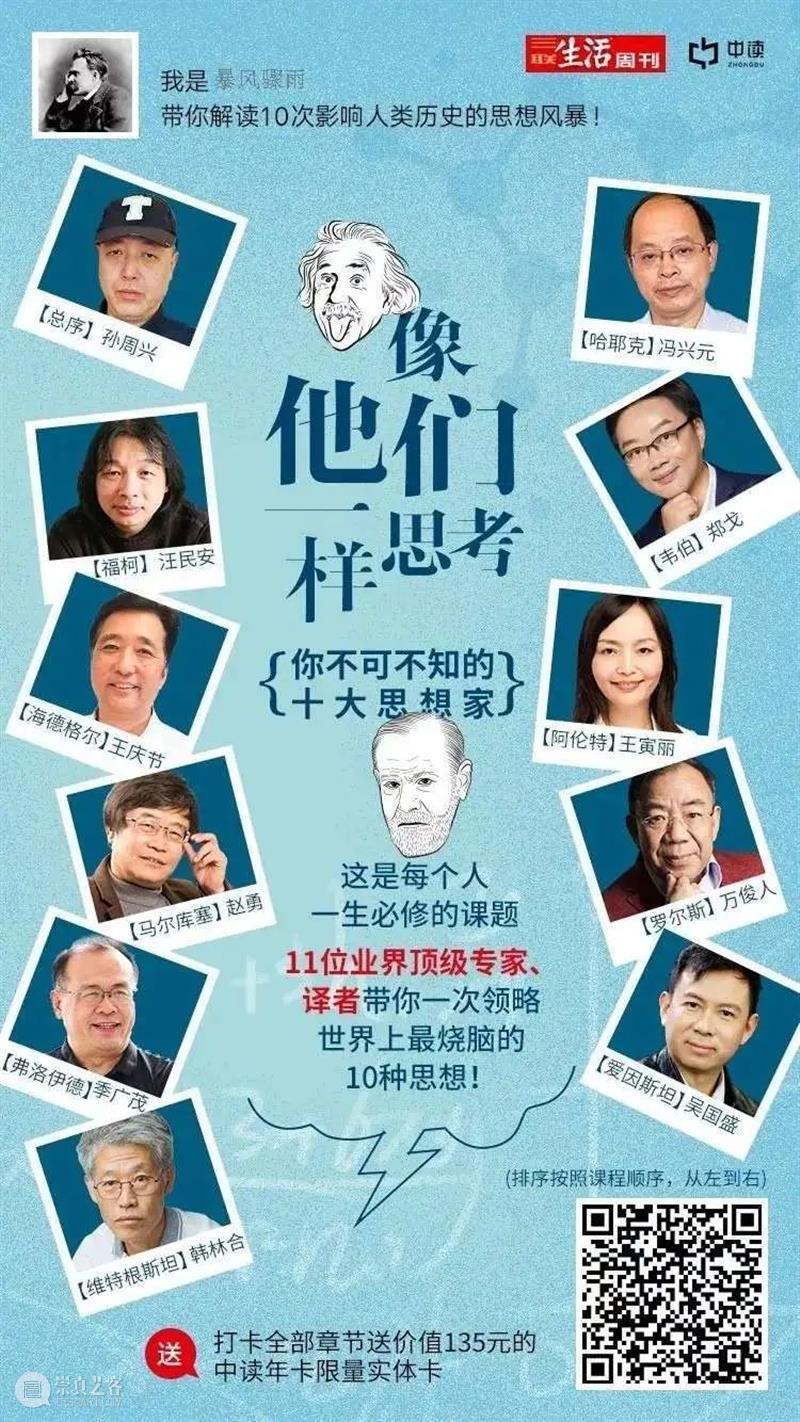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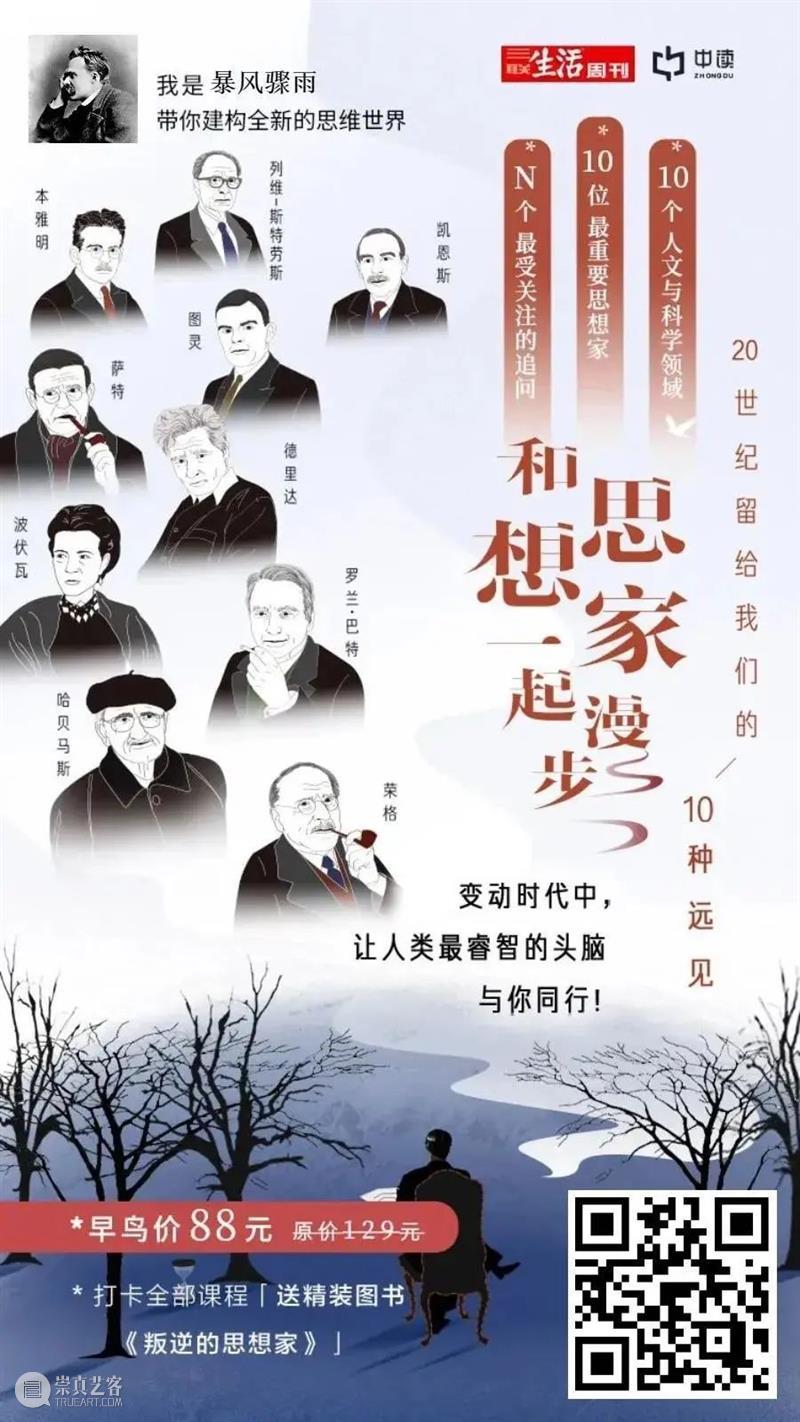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