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观众、民主和权威:当代博物馆的公众参与项目
文/Helena Robinson
来源/《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在新博物馆学的语境里,公众参与活动如今被视为博物馆民主化策略的中心。博物馆不再像从前那样,被定义为自上而下的教化机构,新博物馆学的民主思潮致力于重构博物馆经验,重视博物馆多元诠释的可能,关注社群的需求和期待,使其在智识、文化和政治上实现平等主义。公众参与项目被认为是新博物馆学实践的规范化象征,但同时在它身上也存在争议:一些当代的博物馆参与项目在设计之时就带有对公众态度和行为的特定期待,即使项目本身的意图是包容和参与,在项目执行阶段也并未显露机构权威,博物馆是否无形中制造了新的权威话语,以将公众教化成新语境下合宜、有效和道德的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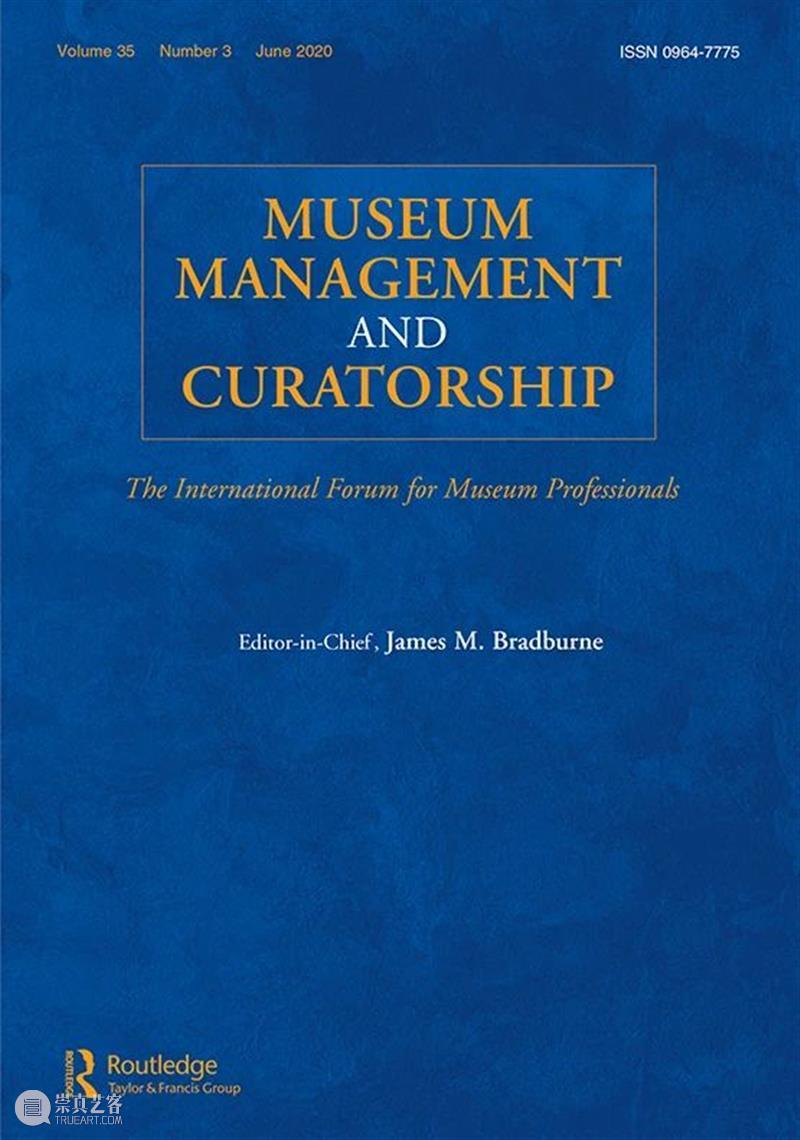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作者对从国际文化组织、国家级文化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地区文化组织和媒体与公众讨论收集来的发表于1997至2018年间的25篇涉及参与修辞的文稿和记录进行了文本分析,并将分析结果嵌套进国际公共参与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AP2)制定的公众参与图谱的框架下。图谱上的五个过程——告知(Inform)、咨议(Consult)、介入(Involve)、协作(Collaborate)和赋权(Empower)——从轻到重,定义了参与式活动的参与度。虽然作者承认,对文本的分析不能完全代表博物馆的实际实践,但通过对文本的研究,作者认为最关注“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的机构反而最不愿意放弃机构权威、赋权参与者。这些机构将自己的身份重构为“社工”而非文化材料的诠释者,这使得它们更像是带有明确立场的政治激进主义者,而非客观中立的文化机构。这时便出现了过程导向和结果导向之间的矛盾:前者注重参与式项目的过程,希望实现文化民主,符合新博物馆学的理想;后者意图通过参与式项目实现社会公义,但却可能因此忽略了过程中的民主和平等。
同时,作者也发现,不同机构对“参与”五花八门的定义和其中隐含的过程与结果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对参与式博物馆学定义的不明确和讨论的匮乏。学界需要进行更多针对博物馆公众参与项目的研究和讨论(尤其是在博物馆实践层面),以厘清当今博物馆在概念、社会和政治层面应当承担的角色。

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