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社会是表面上的独立,思想上的同质
搜狐文化:你觉得现在有全国解放的那种感觉吗?
黄燎原:对,我刚才也提到,早期大家是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现在可能是千人千面但还是万众一心,大多数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想的是怎么发财怎么成名。
搜狐文化:是不是成功学?
黄燎原:对,就是一个成功学。我们那个年代没有想过这种事情,那是一个极端讲究个性的年代。后来很多人都说70后、80后这一代人才是最独立的,确实是这样,我们这些60年代和50年代出生的人,要靠互相拉紧胳膊才能够站立,才能够抵抗风寒,有一种很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大范围内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是一个对抗大集体的小集体。现在是一个属于个人化的世界,但这种个人化在我看来又有一种同质化,虽然表面上每一个个体都很独立,但在思想上他们又更加同质。
搜狐文化:你觉得这个同质化是什么造成的?是消费时代造成的的,还是互联网和消费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
黄燎原:我觉得是消费时代,它可能是历史进步的一个必然趋势。
搜狐文化:摇滚乐是在二战后的和平年代产生的,西方年轻人想要寻求一个出口进行突破,在中国很多人也曾幻想过,一旦进入消费时代,大家就有钱去买琴、有空间去排练了,就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摇滚乐,但现在看来,虽然摇滚音乐、摇滚乐队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像崔健那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和人物出现了。
黄燎原:因为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有更多选择的世界,选择一多就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而我们那时的选择比较少,容易把目光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另外文化偶像跟大众偶像的区别就在于,大众偶像很容易产生也很容易消散,而文化偶像是很难消散的,比如哪怕你现在不听摇滚乐了,但你对崔健还是有情结的,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摇滚乐诞生在二战后的美国,除了婴儿潮之外,我觉得它产生的一个最好契机是和平反越战的情绪,比如著名的旧金山的爱之夏,这些东西一下子就给了我们一个刺激,让大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去反对,这种力量也就容易出来,而现在社会已经失去了明显的靶子,只有你细心地去体验这个社会,体验体制内你觉得不对的地方,才有可能写出一些批判性的东西。事实上除了对现实的批判,摇滚乐也有对美好生活的歌颂作用,类似一种对乌托邦生活的向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题材。
搜狐文化:从2000年左右开始,有的乐队开始签大的唱片公司了,比如汪峰就慢慢脱离了鲍家街,鲍家街里面有很多他对生活的理解和反省,还有对社会的观察,但后来就变成了像《北京北京》这样有摇滚色彩的流行歌曲。还有一些八九十年代的摇滚音乐家因为创作状态的原因已经消失了,你怎么去看待这一群人?
黄燎原:江山代有人才出,每一代都会有自己的代言人,我确实很怀念鲍家街时代的汪峰,他们那时的音乐素质都很高,做的东西也很好。但汪峰现在的状态我也理解,他也一直说自己还是摇滚音乐人,起码他在给摇滚音乐做一些传播和普及,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我相信汪峰还在努力地写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歌,只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和以前有了不同。虽然我们走的道路慢慢分开了,我也很少听他的创作了,甚至很多乐迷会说汪峰是伪摇滚,但我个人觉得他还是在努力地去写一些他认为不一样的、有关怀的东西。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对汪峰也很反感,但这些年就平和了很多,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而且他的努力大家也看得到,所以他的作品我是否喜欢已经不重要了。
搜狐文化:你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还有什么比摇滚乐更具有打动年轻人的力量?
黄燎原:对于我而言是读书,书有很多的形态,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的智慧,你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东西。我到现在还保持每天读书的习惯,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没有比读书更刺激人的事情了。
搜狐文化:可是读书和摇滚乐一样,都是很宽泛的一个概念,你所说的是哪一个类型的书呢?
黄燎原:这就是各取所需了,我只是看自己喜欢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搜狐文化:你还会看类似于《光荣与梦想》这样的书吗?
黄燎原:我会看,我还会看一些关于左派右派、流亡知识分子的书,还有很多新左派论战的书,比如说左岸和右岸,或者德国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俄罗斯前苏联的一些东西,我都会看。但其实我关心的不是政治,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去看。比如美术史这种跟我的工作有关的一些内容。
中国摇滚乐现在仍然没有停下进化的脚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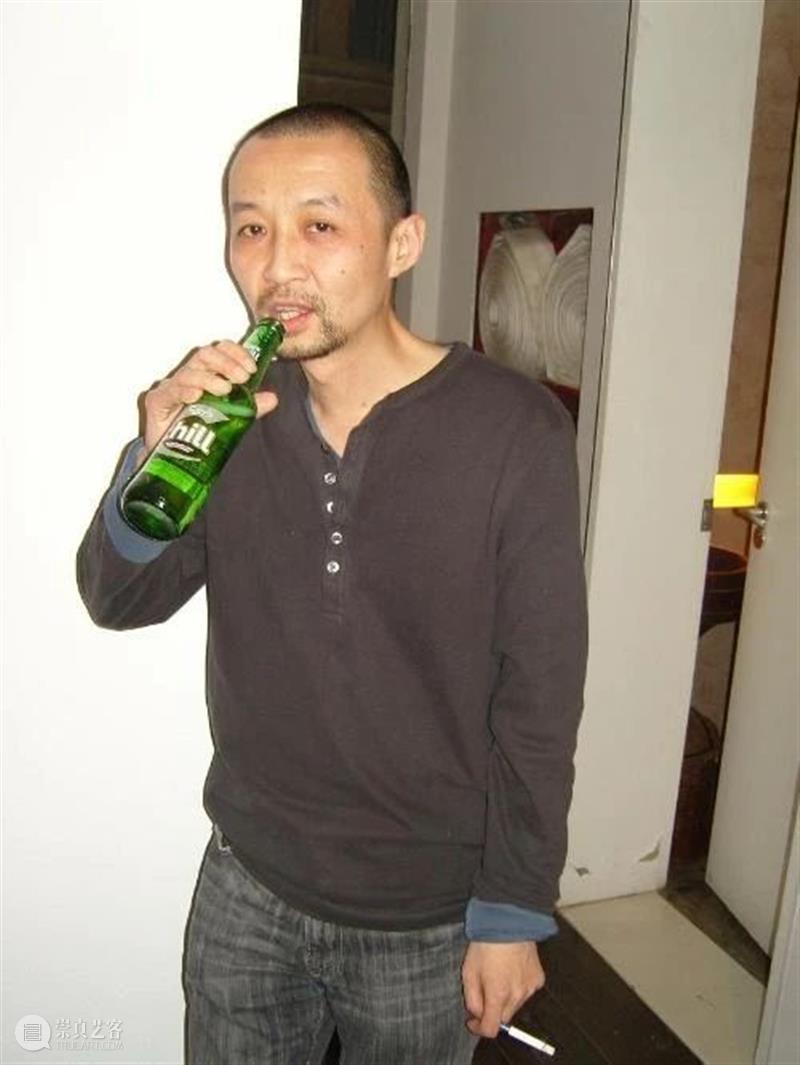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