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业务涉及古代文史哲的出版社不多,以古文史读物为专业的出版社更少。当时有不少青年读者开始接触古代文化,阅读愿望很强,可是中学教科书中有关古代文史的篇目极少,适合高校文科学生或中学教员学习使用的广谱性文史类读物同样缺乏。那时,固然也有一些文史专家耆宿所提供的高层面选注性读物,也总因专业性偏强,传播面不广。于是,选目广泛、注释深入浅出,而又价格低亷的《中华活叶文选》也就应运而生,成为初入门或者自学自习的广大青年读者的最佳选择,并成为当时“中华上编”在广大读者群中渗透力最强的出版物之一。
余生也晚,虽然在求学时期已接触到过《中华活叶文选》,但正是处在懵懂的求知状态,与《活叶文选》说不上有什么联系。《活叶文选》创刊于1960 年,1962 年开始结集为合订本,而我进入“中华上编”并参与《活叶文选》的编辑工作,已是在《活叶文选》合刊之后。1966 年《活叶文选》停刊时所谓的“清官讨论”已消歇。我所接触到的最后一篇有关清官的《活叶文选》单篇稿件是《李三才传》(此人是明朝人,位居高官,能干而贪墨),虽已编辑加工基本完成,最终还是成为“中华上编”时期《活叶文选》未能出版的末尾之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重生的“中华上编”更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活叶文选》奇迹般地仍以原本的编辑方式重新刊行,不过是以单一的合订本的形式出版。在此期间,我重操旧业,仍然担当《中华活叶文选》的编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改编其他书籍。我和《中华活叶文选》的遇合断断续续,特别是现今距当初已逾五十年,不但与《活叶文选》有关的记录文件之类荡失已久,连原始状态的单篇样书也难以觅得,而今已谈不上全面地记述《活叶文选》的编辑缘起、体例认定、约稿方针等等重要编辑环节。于我个人来说,惟能以琐忆的形式,追记当年的点滴见闻,聊供依然关心《活叶文选》者参考。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中华活叶文选》的出版意图是很明确的,可以从合订本“出版说明”中的一段文字得到印证:
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从1960 年开始,我们把历代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科学家等的各类文章,选辑精华,详加解释(或附今译),有系统、有重点地供给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学教师、大学学生及一般古典作品爱好者阅读,定名为《中华活叶文选》。目的在于帮助读者对古典作品的了解和欣赏,从中吸取营养,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提供一些条件。
与如此明确的出版意图和方向相对应,当时社内可以说从领导到编辑上下都全力投入《活叶文选》的体例、选目、作者认定等诸多具体工作中来。我初入第二编辑组,即参加《活叶文选》的编辑工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徒”。查一部书,参加一次工作会,对自己都是非常紧要的事。那时编辑工作会的与会者,有本社党组领导成员、编审、编辑组组长,《活叶文选》执行编辑,经常还会有第一编辑组的精于本会议题的资深编辑来参加。可谓“顶层设计”到“广采博议”、具体执行,无一不在此中。从中也可感知工作之扎实认真、效率之高而可靠。
《活叶文选》注释者的选择,也是有其特定性的:主要作者大致框定在本市高校的文史哲教员(诸如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院),以及市内著名的文史研究耆宿。另外,文史研究水平高而又与上海邻近的南京大学、南京师院等高校的教师学者,也属《活叶文选》的主要作者资源。
说到《活叶文选》的作者队伍,要注意的是,在1966 年停刊之前的成品篇目上,有题具撰注者姓名,也有无撰注者姓名的。例如,《活叶文选》合订本第一辑中第一篇《风赋》(宋玉)即是不具注者姓名的;第二篇《七发》(枚乘)则是具有撰注者姓名,是为当时的名家余冠英和萧平。再进一步统计,我们可发现合订本第一辑20 篇中,撰注者具名的为:余冠英和萧平、白由经和续枫林、沈起炜、马茂元、顾易生、万云骏、瞿蜕园(又名兑之,其人为本社的特约编审)。
为何那时《活叶文选》中有不少的选篇不具撰注者姓名?我认为这与当时一定的社会背景有关,因此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也就是说凡是本社编内人员选注的都不具名。当然,此中不排除会有极少数是另有特殊原因而不加具名。复刊后的《活叶文选》合订本第六辑(此时已专出合订本,而不再以“活页”形式面世了)及其以后诸辑中可以看到,每篇都具撰注者姓名,不仅本社成员可以具名,连直接操作《活叶文选》工作的编辑也都可具名。要说明的是,有的因作者个人意愿而使用笔名,甚至出现一个注者在一辑多篇时具两个笔名,或者本名、笔名一起使用。这种情况,在社内一时成为谈资。事实上,这种情况也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又逢上一个蓬勃兴旺的高潮,高校教员把更多精力投放到学术研究上去,约稿常常不太顺当,而凤凰再生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正聚集了一批精于古文史作品的精英,当然也包括不同层次而已成熟的编辑,他们正好“驾轻就熟”地支撑了《中华活叶文选》的半壁江山,舒解了那时约稿上的诸多纠结。
我还是想把话题回溯到五十年前初加入《中华活叶文选》工作时的情况。
那时,我作为一个新到岗的“学徒”,对社内编辑事务有关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什么都想学一学。《活叶文选》的工作流程,诸如篇题的选定、体例的认定和变化、作者的选择和走访,都需要在反复的操作中熟稔和积累。而如何将古文献或作品转化为一般读者可以卷而藏之、诵而咏之的读物,这更是对做好《活叶文选》撰述和编辑工作的根本要求。从大的方面说,“信、达、雅”是当时对注释性读物的整体要求,而如何使每篇选文都能符合这个大要求,的确不太容易。
每篇选文的最前面,一般往往是“历史背景”、“作者介绍”,以及对本篇选文的“文体”(特别是那些特定的文学体裁、样式)的界定或介绍。这些或都可从资料室或上海图书馆去找到有关的参考资料。有时,连如何找寻、找寻哪种参考书,编辑组的领导和直接指导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详加指引。最要紧的是如何处理好选篇中的注释点。《活叶文选》的注释点,有时是一个字,有时是一个词,乃至一个典故,或者一个古时文坛上某个唯此一现的话语。要解决好这些注释点,不是几本字书词典可以了事的。并且即使原注者看来已经完成了这个词条的诠解或译述,但从当时的编辑流程来说,还是需要编辑重新审视一遍,目的是使每个词条都能尽量更贴切古人心意。在出版圈中所谓的“文责自负”,在当时的编辑要求上是行不通的。随手翻到复刊后的合订本《活叶文选》第七辑(注释者本来就是“上编”时期第二编辑室的成员,作注时已调往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词组任职,应该是一位深谙《活叶文选》编辑要求的人),其中《长沮、桀溺耦而耕》一则,有“怃然”一个注条。“怃”在字典中有二解:一作“爱怜”解;一作“失意貌”(也有作“怅然失意貌”)解。但是这位注者并未简单地采用字书词典上解释,而是注为“发愣的样子”。对此,我当时的理解是,孔子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又是一位坚定的用世思想的哲人,其内心应该是非常强大的。他不会因长沮、桀溺这两人所谓避世隐者的质疑(包括前一则《楚狂接舆》中的更为偏颇的“何德之衰”的责难)而恍然若失的。所以孔子只是在愣一下后,随即仍用温敦而坚定的言语去表白一番自己的信念。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对“语境”的体认问题,尽量更深切地体认注释点的“语境”,才是《活叶文选》作注的不二法宝。所以还是采用了注者的注解。当然,《活叶文选》的选法,包括这里所谈论的注条处理,不一定都是最完美的,但是,《活叶文选》作注专重“语境”的考虑,是使注文最大限度接近古人心意的重要手段。

中华活叶文选(全十六册)
《活叶文选》编辑在审读注文时,使用工具书也别有讲究。一般通用词典当然经常翻阅使用,主要是为处理注音、书体的准确性,对词意的认定更多的则是使用《册府元龟》(主要是名物典章)、《艺文类聚》、《佩文韵府》、《中华大字典》(叶氏)和各种古人对文史要籍的笺注或议论。我的指导老师傅元愷先生(他是“上编”时期《活叶文选》的执行编辑,后来为《汉语大词典》编纂时的主要执行者之一)曾对我说过,《佩文韵府》看来是作诗填词的集大成式的工具书,但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容忽视的特点,就是它不像一般字书词典侧重在对字、词的直线型的诠解和征引,而是一个字的上下左右多方位的扩展,可以从中获得更丰富深入的信息。在使用中能认真体会,再加上对注条的历史背景、作者生平的多方位观察,就可能找到该注释点更贴切古人心意的结果。
这种通过力求寻觅、体认注条注文的“语境”,来析解古字、古词、古文的思考方式,很使我心折,也让我终身受用。
(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副编审,本文选自《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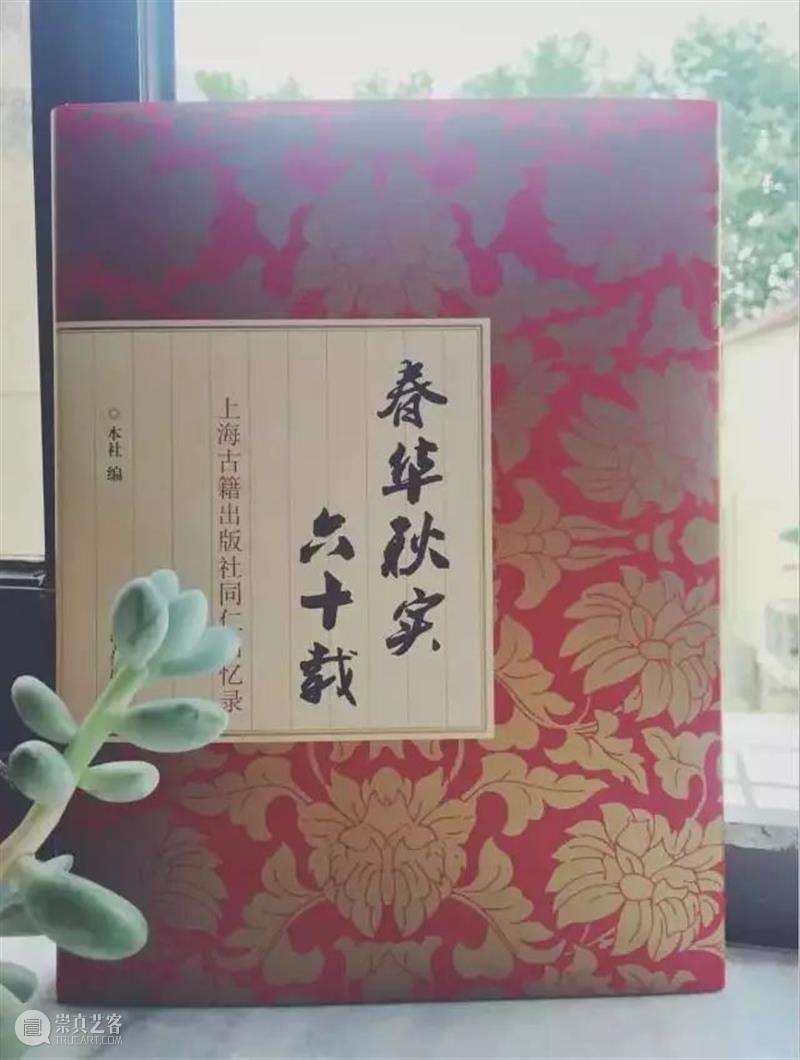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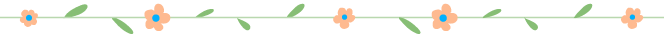

长按二维码关注我们
上海古籍出版社
传播千年文明 奉献传世好书
微信ID shanghaiguji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