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我的作品,需要去发现掩藏在下边的东西,表面看是抽离现实,但其实后边有很多和现实相关联和延展的部分,这需要观者去细心地体会和体验。❞
——李俊
从2013年获得三影堂摄影大奖的“无常时”,到去除物象的“物影”,再到探讨相机与记忆关系的“记之暗面”、“被排除的剩余目光”,李俊创作的主题,似乎一直都围绕着时间、记忆和存在的真实展开。他采用一系列诸如等待灰尘、操控反光和阴影、翻拍照片、折射光线等的方法,将这些不可言说的主题具象化,让观众得以在语言的暧昧中,找到一方出口,思考图像本身的力量。
此次李俊老师的作品在成都当代影像馆《双城记——成都·重庆当代影像展》参与展出,让我们有机会得以进一步感受他作品下隐藏的力量。而通过分享这篇关于李俊老师创作历程以及背后思想的访谈,木格堂希望能帮助大家拓展对摄影的了解以及自身的创作思路。

蔡燕欣(以下简称“蔡”):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拿起相机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您成为了一名影像艺术家?能否简单聊一下您的学术背景与创作历程?
李俊(以下简称“李”):我和摄影的渊源很早。中学时候母亲就给我买过一个国产华夏205旁轴相机,但那时对此并无太多兴趣,所以相机就在衣橱里一直放着。直到大学读新闻专业,才回家把相机翻出来,开始一边学习技术,一边四周游荡拍摄。

“无常时”系列作品,《母亲和儿子》,2010
大学以后,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成都一家媒体做摄影工作,而之后几年都在媒体行业中从事摄影媒介相关的工作,比如记者、编辑。但我对于直接记录现实的兴趣越来越弱,不愿止步于此,所以后来去了中央美术学院进修摄影。2008年回来后我就创作了《无常时》。在此之前我拍过两个系列,一个是川剧人物,一个是藏区藏族肖像,但这两个系列都没有自觉的创作意识。可以说《无常时》是我有完整自觉意识的创作作品,是我第一个以“艺术家的身份”来创作的作品。

“无常时”系列作品,《一个人用的》,2008
蔡:您在2013年凭作品《无常时》获得了三影堂摄影奖大奖和新星星艺术节新人奖,您对获奖的态度是什么,您认为奖项对您的创作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还是限制了自己?

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环境没有真正经历过物质丰裕阶段,这个环境下成长的艺术家对于物质和社会名望来说,免疫力是缺失的,很难迈过金钱、名望对人性的考验。我并非说这些社会名望和金钱利益不重要,它们是一个外在的、附加的东西。人是需要这些东西的,但在艺术创作中不一定需要。在一个相对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中,金钱、社会名望和作品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呈正相关状态。
我得奖的时候当然很高兴,因为从现实层面来说,得奖意味着得到承认,意味着作品会得到更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正向的鼓励。所以我觉得奖项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创作上的压力其实更多来自自我,是一种想要不断超越已有创作的压力。

蔡:您在拍摄《无常时》的时候为了等待灰尘的堆积“熬了很长时间”,为什么当初不直接用在“物体上抖灰尘”的捷径,而是选择“等待自然灰尘堆积”?这是您特定的、喜欢的工作方式吗?
李: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它涉及到我们是怎么来理解“人工”和“自然”的。在等待的过程中,堆积的灰尘看似自然,但是实际上也是人为外在活动引起的结果。这种“自然”的感觉,是因为你看不到灰尘直接落下来的动作,灰尘堆积的速度缓慢得你发觉不了。换个角度思考,当我在这个环境里面走动、跳动、抖衣服,这种行为激起来的灰尘算不算“自然”?

另外,可能大部分人在理解摄影作品的时候,会更多地把它和记录现实联系起来,是一种使用相机机械式的直接记录。但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创作是需要很多干预的,比如我对《无常时》的干预在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在于物件的摆放位置;第二个层面在于拍摄物件外轮廓的选择和构图;第三个层面在于我对灰尘厚度的控制。这些干预都意味着,我的摄影、我的创作不仅仅只是对现实的直接记录。这个问题背后指向的其实是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摄影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自觉的艺术创作就是在“介入”和“干预”。

蔡:在谈及本次影像馆中“双城记”展出的作品《被排除的剩余目光》时,您曾提到“只有那些被我们看到的存在,才能被知觉确认为真实的存在”,能就此展开谈谈吗?
李:其实我觉得人作为感知的关键物体,如果去掉感知,人就不复存在了,“我思故我在”嘛。我们每个人的经验、体感都是和感知直接相关的。作为一个肉体,人只能感觉到他所能感觉的全部,以为我们身体所感觉到的就是外界的所有。但感知也是囚笼,我们被禁锢在“自我”感知中是无法脱身的。


所以相机镜头也好,眼睛也好,都被设置成一定的观察视角,这个视角是有其物理极限的,固定的镜头和固定的眼睛都无法观看到超出视角之外的光线。从现实的层面来说,“观看”之外有大量的被“视角”所排除的现实存在,有些是主动排除;有些是被动排除。这些没有被“看到”的存在是多余的,也是剩余的。因此除开现实层面的隐喻,媒介和感知的局限性、同构性也是我通过作品想要提示的。

蔡:在一定程度上相机和摄影都可以被称为媒介,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您是怎么看待相机和摄影的关系的?
李:实际上文艺复兴早期就已经发明了暗箱。大卫·霍克尼有一本书《隐秘的知识》就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写实绘画有伟大成就的艺术家,其实都是通过暗箱的帮助来制作作品。从这个层面上看来相机成像的技术出现得很早,但是为什么摄影是到了1839年才被发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底片的发明,让我们所看到的影像可以被存留下来。所以我们对摄影的定义是能够记录影像,我们看到的图像,需要一个物质中介来呈现,才被称之为摄影。

蔡:在看您的作品的时候像是在读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总是透露着“缓慢而静谧的诗意”,您是有意要对抗“犬儒主义漩涡”下焦躁、永不满足的生活节奏吗?若是,对“诗意”的追求,是否会脱离社会现场,导致“过分精致”?
李:“犬儒主义漩涡”是我2008年一篇创作简述中提到的,我发现十几年过去了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过时,在现实中反而越演越烈。不论从大的社会环境,还是个人经历来说,现实都越来越让人感到无力,当你和现实靠得越拢越近,你的沮丧、绝望就会越多越大。

至于脱离社会现场和过于诗意空洞的问题,首先于我个人而言,我尊重所有艺术家的个人选择,所以不会去要求艺术家一定要符合我对现实的理解。尊重个体就要尊重个体的选择,只要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做任何选择都可以,这个标准放到艺术创作里也是一样。艺术家首先必须对自己真实,他没有感受的东西就不需要去做,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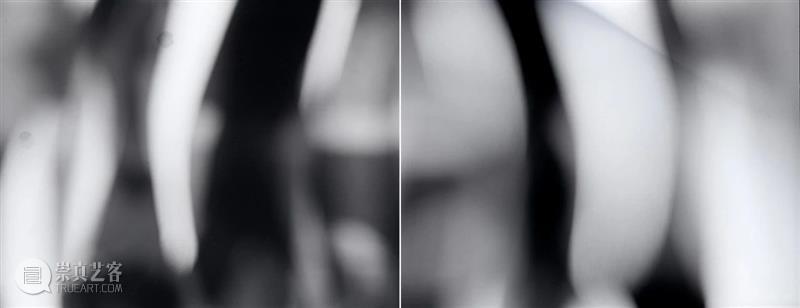
120cm x 300cm,2017,出租屋里站立着的一个女孩.穿着男子的衣服,和男孩并肩而立的一个女孩.街上闲聊的两个街坊.穿着大衣独行的妇人.冬日巷子口光秃秃的槐树.女孩伸出右手展示彩绘指甲
在社会现实紧迫的环境下,民众对艺术家介入现实的期望会很高,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要求,或者道德绑架,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家其实是被某种道德期待作为“牺牲”献祭到“神坛”上了。而且很多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表现现实,但其背后的隐喻、方法和指向其实和现实息息相关,并没有脱离现实,因为艺术家在现实里也是有经历和感知的。这也就需要美术馆、批评家这些中间角色去向公众传递作品中隐含的信息。

蔡:您在“记之暗面”系列作品中为作品做了较长的说明,后来又用“诗歌”为作品命名,您是怎么看待“文本”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的?作品名、叙述等文本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框定并限制作品本身?
李:在创作早期我也认为好的艺术作品是不需要做过多文字阐述的,但随着我的创作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复杂,我发现只通过视觉表面的感知没有办法理解更深入的复杂体验。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也不是能够凭着视觉、触觉和感觉就能对一个事情做出判断。那不然为什么电子电器总是随带说明书,我们需要研读说明书才能了解操作方法。
因此我现在对文本的解释持相对开放、宽容的态度,因为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理解进入复杂而丰富的层面。当然也会出现很多故作高深玄妙的文本,这最终需要时间去沉淀和判断。

蔡:生命经验、历史情感或者政治立场,您诠释的图像/影像的原则是什么?能否聊聊您在创作中对生活的思考、提取到呈现的过程是怎么发展的吗?
李:生命经验、政治立场、历史情感这三个是相互渗透的层面,而政治立场和历史经验其实在很多时候还是需要通过个人的生命经验来体现的。如果一定要在这三个里面选一个作为创作底色,我肯定首选生命经验。
创作的时候,我会在我的生命经验里、所感知的事物中去寻找一些刺点,然后通过某种方法进行扩充、呈现。这个方法涉及到我认为的摄影媒介和感官感知的关系,以及媒介、社会和我个人的关系等。

成都当代影像馆于2019年4月27日正式开馆,坐落于成都北三环内、府河河畔,位于国内首个以摄影为主题的公园——府河摄影公园的核心位置。摄影公园占地面积150亩,影像馆建筑面积7500平方米,拥有6个专业展厅、1个学术报告厅、1个专业影像图书馆以及多个公共教育空间。作为专注于当代摄影及影像艺术的文化机构,成都当代影像馆与全球著名的影像艺术机构紧密合作,致力于高品质的影像艺术展览、有深度和高度的学术研究以及公众视觉修养、审美教育的传播和普及。致力成为观测中国影像状态,促进国内、国际交流与对话,推动艺术与学术生产的专业影像美术馆。
图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成都当代影像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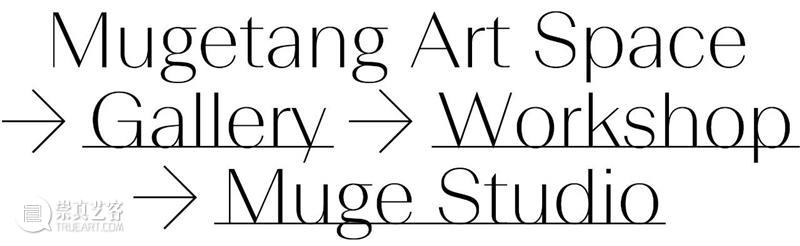

CONTACT US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