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作为一种时刻
——关于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的写作
书写我们和当下的关系,是多么的困难!尤其当我们意欲不以感性的艺术作品,而以凝练、抽象的艺术理论本身,来明晰这种浑辨难言的关系时。事实上,任何一种清晰化当下的行动企图,如若不是具有内在的历史意识、极强的现场感知力、洞察力,并且还辅以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都很难去启动它,更别说触及它。即便这些都完备,假若写作者缺乏一种对于当下时刻的敏识,对于自身问题的关切,并能够时刻切分出一种批评的距离,也就依然,无法有效启动这样的行动。
对于哈尔·福斯特、本雅明·布赫洛这几位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现当代艺术现场来书写的学者而言,写作的兴趣虽不能全然归结于对这种难度的挑战,至少部分也在于此。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提到过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极简主义,之于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微妙距离感。它是:
既非过去又非现在,同时既接近于我们,又区别于我们当下的存在,是时间的边缘,围绕着我们的在场,笼罩其上,并在它的他者性当中指出它来;这是在我们之外,指出我们的东西。[1]
在我看来,将这段话借用来界定当下的世界与我们自身再恰切不过了。这恰好是一种建构一个新平面,使周遭的作品(物)得以成象的佳途。这个途径的秘诀写在了这段话里,那就是,将纵向的差异投影为横向的差异。把过去拉近,把当下则推远,同时亦将它们深深立基于当下的生活中,关切艺术与理论中历时的(历史的)和共时的(社会的)两轴之间的协作。[2]这个当下的生活,放在艺术史家的专业框架里,就是当代的艺术创作。经由这样建构出来的平面,作品才能成其所是的活动,显现自身,表达生活,随而再被研究者编织为可反思、可分析的文本。
当代作品文本化的原因,来自其迫切性。而这迫切性的由来,首先是与全面来临的传媒化或者说景观化有关,在《实在的回归》的最后一章节《后现代主义遭遇了什么?》里,哈尔·福斯特别提到了麦克·卢汉和居伊·德波对于媒体如何作用于精神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二者一位热烈拥抱技术对于“人的延伸”,一位则痛感于媒介景观化后对于人的隔离。通常来说,作品是事实的显现,显现或者说成象为能够直接理解的建构。文本则是需要解读的作品,是带有思想性反思性的东西,是心灵的一种表达。[3]然而在传媒时代,我们迎来了一个改变:作品的大量文本化。媒介带来海量可以显现的平台,带来真真假假的图像,也给受众发出诸多的邀请函,因而解读作品,参与建构作品的机会大增。“每一种声音都迫不及待地要求获得认可和成为权威,以便将自身同符号场缝合起来,这一符号场的经济魅力和强大的符号交换价值忽然演变成一整套象征体系”[4],大量的媒介化文本、标签化文本产生了。当我们的社会主体变成一个由网络空间、虚拟现实、智能手机、大数据等各种可能性组成的社会,媒介机器的过度文本化(图像化)已在所难免,对此福斯特是这样回应的:
……无人能够逃避当下,甚至艺术史家也不能。要获得对历史的洞察力,依靠的不是对当代的赞美,而是对当下的投身参与,无论是关于艺术、理论,抑或政治的参与,恐怕都是不可或缺的。[5]艺术史家投身的结果,正是我们之前所谈的,对当代作品的切入、编织,再建构,是一种新知识框架下的文本化。以哈尔·福斯特、本雅明·布赫洛、乔纳森·克拉里等一群当代艺术史家的工作为例,他们面对当代艺术的现场,就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战”后以来的艺术创作和背后的文化现象发声。他们从关切的视觉事物和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出发,阐释历史上的艺术实践和当下实践的关系,据此来葆有适当的距离,随后产生批判,产生缝合的抗力。《实在的回归》这本书里,有一处关键的立论,作者哈尔·福斯特在“导论”以及译者杨娟娟在“后记”里都提到了,即“延迟效应”(deferred action,指弗洛伊德认为,对于一个创伤性事件的确认,只能是通过一个后续事件在延迟的效应中对原事件进行的回溯性解码)。基于这一点,他对新前卫运动的分析认定就是,它与历史前卫主义(指20世纪初期的艺术风潮)的关系,“是一种彼此联系的持续伸展与停滞过程,是由预期的未来和重建的过去所组成的复杂的接力,是一种延迟效应。这种效应推翻了过去那些如从前和后来、起因和结果、原创和复制的简单方案”。这样一种超拔的识见,就使纵向的差异转而投影为横向,将时间投射于空间上而又不带有必然的进化论执念,一个言说的界面就此真正建立了起来。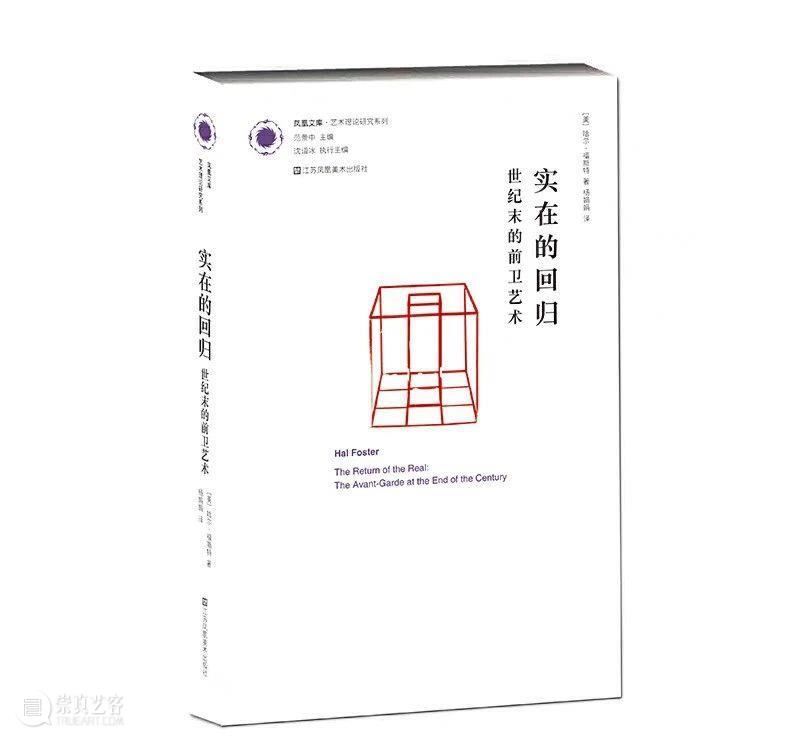
《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
哈尔·福斯特著,杨娟娟译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5年
正是得益于这个界面,福斯特展开其犀利、精准、华丽又充满幽默感的论述,在以极简主义为核心构建的当代艺术谱系里,展开对当下艺术实践在语言学转向、犬儒理性、“实在”的表现和人类学转向方面等诸多面向,既揆诸常情常理又抽丝织锦的文本化行动。这个界面,是万物自我显现的面,也是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里谈“苦难”时说的那个“客观的中介”,“让苦难说话,这个需求是一切真理的条件。因为苦难就是主体所要担负的客观性;主体当作最主观的东西来经验的,它的表达,是客观地被中介的”[6]。在这里,苦难(suffering),可喻世上一切遭逢之事物。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不光是艺术理论写作该有的文本化,事实上,随着过去近50年中艺术的极简主义谱系的发展,艺术媒介的转向、感知空间的转向和身体的转向,使得当代艺术家的身份早就突破了边界,艺术创作中的民族志朝向变得十分普遍——作品先于艺术评论迎来了过度文本化。在这样的现状下,福斯特才在最后一章《后现代主义遭遇了什么?》中,在讨论了变迁的主体、文化他者还有技术的幻想之后,大力呼唤“距离的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我认为与当代作品的文本化(景观化)紧密相连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如何超越景观而成象。他接下来的回应,或许是我们迫切进入过去或现在文本工作的另一个原因:当代性就是一个人与自身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通过分离和时代错误来依附于时代的关系。那些与时代太过于一致的人,那些在每一个方面都完美地附着于时代的人,不是当代的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目睹时代;他们无法坚守自身对时代的凝视。[7]福斯特则从艺术史书写的角度来谈,这一小节的论述非常精彩,他先从本雅明对“种种视角和远望担保了批评距离”[8]这样一个慨喟出发,接着引出艺术史中的一个重要文本,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潘诺夫斯基在此书“导论”里以透视法作为一种真实观看的方式,提到从正确的视角看问题是批评历史的前提条件。在对适当距离与批评历史问题的不断追问中,有关凝视的问题就转化为认识论上的“视角”问题。而这一点和整本书除延迟效应外的另一个主导概念关系尤为紧密:视差结构模型(parallax)。“视差”概念本身就是指由视角(观者的实际运动)造成的在其视野内的观看对象的位移。“视差”概念的设定,担保了观者先天的认识论上的反身性,这宝贵的特质使得我们多少可以抵御一些当代艺术思潮中对于他者的过度投射。虽然投射不可避免,但至少,福斯特的见解带来了对于投射的新的预警机制。对他者的挪用,是许多现代主义作品的基础,也始终存在于后现代主义中。福斯特援引意大利哲学家弗朗哥·雷拉在《他者的神话》中的观点,谈及这种他异性政治。“如拉康、福柯、德勒兹和瓜塔利这些不同类型的理论家,都将他者理想化了,当作对于相同的拒绝——这在文化政治上引发了有害的效应。”[9]而“视差”这个不断转换中的视角的提法,有助于将他异性这样的二元结构推进到差异模型,推向混合边界,甚至推进到对于最难察辨的“自我他者化”的预警中。何为“自我他者化”?以福斯特的说法,就是指在当代文化中那种倚赖无意识和他者寻找真理的思维汇于一点,栖身于一个卑贱主体、一个受伤的肉身时,一个被绝对权威化主体化了的自我,一个“以浪漫的反对来支撑着自我,以辩证的挪用而保留了自我,从超现实主义的探索中拓宽了自我,在后结构主义者的困扰中延展了自我”[10]的那个他者化自我。或许只有依靠视差,才能跨个人、跨主体地彻底切断这种自恋式的自我塑造实践,感伤癖的自我沉浸,带来分(出)神(distraction,此文中译者杨娟娟译为“消遣”)的瞬间,击溃极化思维,并容纳了景观时代下的批判。这就是此时代下批判与消遣的辩证法,反过来说,日益景观化的今天,也只余留了这么一点空间容批判侧身,以击破景观的网罗。然而,光有认识还不够,远不够。“批评的距离是不能放弃的,又是必须重新设想的”[11],福斯特最后写道。那种设想的过程令人想到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意义判定,它总是回溯性构建的,而非去“被发现”的。因而批评距离的设想,首先是一种文化行动,是人去冲破被扫描,逆转为主动去写的状态。因为“批评”从词源上说,就是判断或者决定,它连着的是种种价值判断。“批评理论以另一种方式秘密接替了前卫主义的职责……激进的理论修辞算是对衰落的行动主义的一点弥补——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担当了文化政治的职务。”[12]私以为,哈尔·福斯特用以命名全书的第六章《实在的回归》应该算作是当代艺术史写作的一种理想型。这一章带来全书的一个转折,如果说之前四章还是在做前卫艺术以来艺术现象的梳理,到了第五章,他以拉康的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理论为言说的开端,把全然是艺术史范畴的话题,灌注入当代艺术甚至生活鲜动的观察里,使理论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块面发生着富有弹性的牵连。此章之后,他更是将笔伸入人类学,剖析当艺术家具有了“作者”意味,当代艺术与理论发生了民族志的转向时,艺术的问题从对特定媒介的追求,转向到有特定论题的艺术项目,这样一个社会意义上更激进的话题。时间轴越拉越近,这一章从讨论沃霍尔的创作开始,发问道,究竟那是一种指涉,还是一种再现?福斯特说我们的解读得用第三种方式:创伤写实主义(traumatic realism)。不过他立即注释:不可能存在这种东西,尽管如此,它作为启发式的观念还是有用的——只要借以走出新艺术史(符号学相对于社会—历史方法,文本相对于语境)和文化批评(能指相对于指涉物,结构主义的主体相对于自然主义的身体)的对立僵局。[13]接着他就借由这个临时概念展开对于沃霍尔新的阐释。探询的重点在于,被“受惊的主体性”和“强迫性重复”这两个概念定位了的沃霍尔图像中的“重复”意味着什么?是对创伤意义的躲避和敞开?对创伤影响的防御和产生?重复肯定不是复制,福斯特援引拉康理论开始其对于由沃霍尔作品引发的一系列当代波普艺术作品的分析。重复的空洞指向的是作为症状或能指的被压抑感受的重复,还是与实在的创伤相遭遇的回归?福斯特创造性地把拉康关于“凝视”的言说拉进对当代创作的分析里。主体的观看与物体本身之象基于一种投射的交合,支撑起一个观看的屏(在眼下这个技术—逻格斯情境的算法时代谈“屏”就更容易理解了),凝视而成像(“凝视”的词意似乎有一个施动的目光,但它恰指既非来自观看主体也非来自物之自体,既在主体之内又在主体之外的某个东西的凝视,是在他者那里失落的原质之“物”,即“对象a”的凝视)。在拉康看来,所有的艺术都是对凝视的驯服,对投射的驯化。而福斯特说,当代艺术就是在拒绝这种由来已久的授命——平定凝视,它们在面对不可能的看,即“对象a的凝视”,实际上就是“实在界的凝视”(gaze of the real),并且联合想象界和象征界来对抗实在。此时他再邀来克里斯蒂娃的“卑贱”理论,进一步深究拒绝使命之后主体与凝视的角力。当代艺术一再表现出由被侵犯的身体和创伤主体唤起的向着“the real”的回归,那里面隐藏着一个卑贱的计谋或者驱动,似乎经由卑贱的途径才能够将创伤完全地把握住并且投射出来,成为对消费主义俘获的想象界和被文本化惯例化收编的象征界的有力反抗。走笔至此福斯特不无担忧地写道:“一个人无法质疑另外一个人的创伤。……那么,在创伤话语中,主体既是撤走了的,同时也是被抬高了的。”[14]这一章大约勾画尽了当代艺术的主要轮廓,那里面的身体感、淫邪感、空洞感、感伤癖、反崇高的冲动……这些纷乱、琐屑的众镜之影竟在他的关切中终有庄严的显现,众镜相照,成其无尽复无尽之意。但驻笔于此,他就没有再跟随克里斯蒂娃的女性主义理论一径追踪下去,直捣黄龙,索性起底整个俄狄浦斯情结与象征系统了,没有继续调用克里斯蒂娃关于前俄狄浦斯情结的阐释,给予“创伤”与“卑贱”视野一个超越的维度,收尽天地造物间的“游魂”。(“游魂”指不唯指向创伤,也并不单倚重于身体感的某种当代表达。这类作品独特,虽不多然而也已有所展露,比如高洁的《伪艺术史》系列[图1],大嘴突击队[Gob Squad]、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的作品等。[15]就这一点来说,福斯特也依然带有几许男性白人精英知识分子的标签吗?)假如加入这一反证的维度,也可多少抵消学者为了言说而不得不总体化抽象化的某些实践现象。
图1 高洁,《伪艺术史》,2016年至今
不过,就已做出的书写来说,福斯特的确做到了在点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和拉康对弗洛伊德的解读时谈到的这些:并不是要求这类解读是终极的真理。相反,这是要澄清它们随机应变的策略,那就是与一种消失已久的实践重新联手,好脱离当下那种陈腐的、误入歧途的,或者压迫性的工作方式。第一步是暂时的,它只是为了在空间性的第二步中,打开新的工作场域。[16]福斯特用拉康和克里斯蒂娃极其漂亮地引爆了对于当下艺术现象的透视。德勒兹曾说:“哲学是一种建构主义的。建构主义有两层意思,创造概念和构拟平面。”[17]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斯特的写作也不啻这样一种建构主义的写作。他建构出的内在性平面将概念统统裹卷,再将其层层展开。从沃霍尔到拉康,到弗洛伊德,到罗兰·巴特,到理查德·艾斯蒂斯,到乔治·巴塔耶,到辛迪·舍曼,到克里斯蒂娃,到布勒东……思维的问题就是无限速度,它需要一个腾挪自如不受限制的平面,一个新的工作场域。福斯特使理论和实践块面之间碰撞后释放出恣意的能量射线,在他建构的平面里滑行嬉戏。“理论通过一种新的图像循环与检验,生产出跨越个人化的新循环,所有知识都由此产生。知识这时才是逆熵的:知识包含着通过认识的行动使它自己脱—自动化的可能,而这种认知内化了这一知识所构成的自动机制,不然这知识也会通过自动化而变成反—知识,也就是成为教条,而知识如此地成为教条,只是因为它向自己隐瞒了它的教条性,也就是其自身带有的自动机制。”[18]这是斯蒂格勒寄望的书写理想状态,这应该也是福斯特的写作工作最令人记取之处。身处一个矛盾重重的时代,危险之一并非知识的沦落,而是反智主义的知识化,是无知的知识化与专业化。如果不去致力于这样一种方向的书写,那么书写只剩下它的毒(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书写是新的技术,但新的技术是便利也是毒药),越写越致贫瘠化。这贫瘠化是什么呢?福斯特说正如当代文化中的卑贱叙事,那是一种将人与事推向虚无的力,而这种虚无或许就是贫困(impoverishment)的缩影。[19]此处的贫困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荒芜或贫瘠,它比毁灭更可怕,因为毁灭消除以往和现存,也消除了虚无,而荒芜化则“禁阻未来的生长,阻碍任何建造”[20]。苦啊,怀藏荒漠者![21]毫无疑问,福斯特是阿甘本笔下的当代人。阿甘本说:“要在现时的黑暗中觉察这种努力驶向我们但又无法抵达我们的光明——这意味着成为当代的人。”出于这样的原因,阿甘本说,做一个当代的人,首要的就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能够坚守对时代之黑暗的凝视,也意味着能够在这种黑暗中觉察一种距离我们无限之远、一直驶向我们的光明。换言之,成为当代的人就像等待一场注定要错失的约定”[22]。一个当代人,首要的就是这种和时代的关系,和过去与当下的关系,或者以西美尔对时尚的定义,是一种独具时尚感的人:时尚的问题不是存在的问题,而是同时存在和不存在的问题;它总是站在过去和未来的分水岭上,因此,至少在它达到顶峰的时候,它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比大多数其他现象更强烈的当下感。[23]何为当代的艺术史写作?在哈尔·福斯特精心编织,然而又总是自我质疑(他常在正文里写而在注释中疑,此书的注释彩蛋迭出,令人应接不暇)的写作行为里,我们看到的是以一种书写拉通一种伦理,展示当代的开放性行动。以理论概念引领一切的写作在今天是那么的不合时宜,这不光是因为今天已不再是一个“沉思”的时代,一个抱守着怀旧和批判,秉持哲学的虚骄就足以话术天下的时代,更重要的是作为理论学者,要以职业的操守,把哲学传统(理论)引申到更加具体而复杂的跨学科和跨文化问题上去,以迫使学院哲学以“不纯粹”的方式发挥其效应,去接受具体经验的碰撞。让概念破碎于经验前,见山不是山,再激起新的表达,构建出一个内在的平面,任表达和经验不停地相互校正,以至见山还是山。比起别的学科,天然跨学科的艺术史学者,显然更接近这个迫急的任务,而有天赋的直觉去领受这份工作的利好者,和别处一样寥落。因此当我们谈当代的艺术史写作,就是在谈当代的写作,它首先是一个愿意面对黑暗、不合时宜(以阿甘本语)的当代人的写作,它是形式上的道德论,是写作者决定把其语言活动的本性刻写入社会空间所做的选择,是嵌入不同的语境中以各种方式参与到对当下的表达的一个自由的时刻,而这种时刻,“是历史最为清晰的时刻之一”[24]。
本文原载于《艺术史与艺术哲学集刊》第一辑,文章经作者授权,转载请联系后台授权,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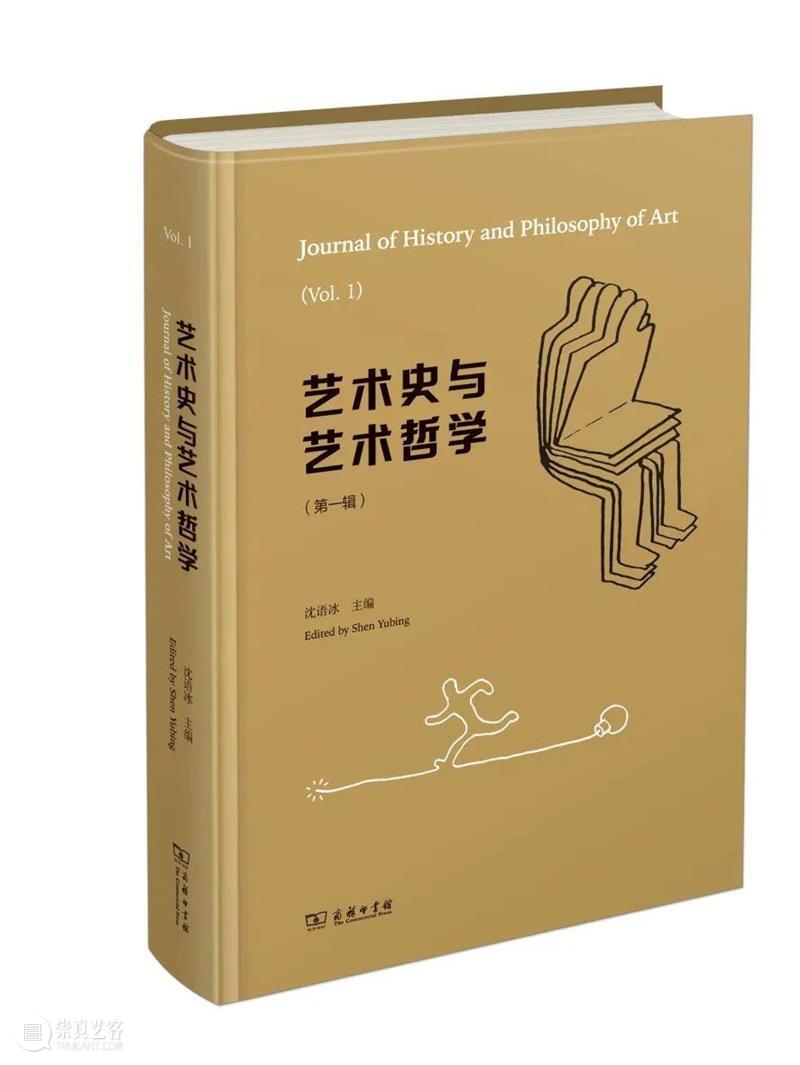
《艺术史与艺术哲学》(第一辑)
沈语冰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20年
(购买请点击阅读全文)

作者简介:王音洁,艺术史博士,剧场导演,浙江理工大学服装学院表演系副教授。研究领域集中在当代剧场和影像艺术的创作、表演理论、批评理论、女性主义等。出版有《复象与镜像:当代剧场与影像创作流动图景》,即将出版有《被悬置的演出:「场外说」谈话剧场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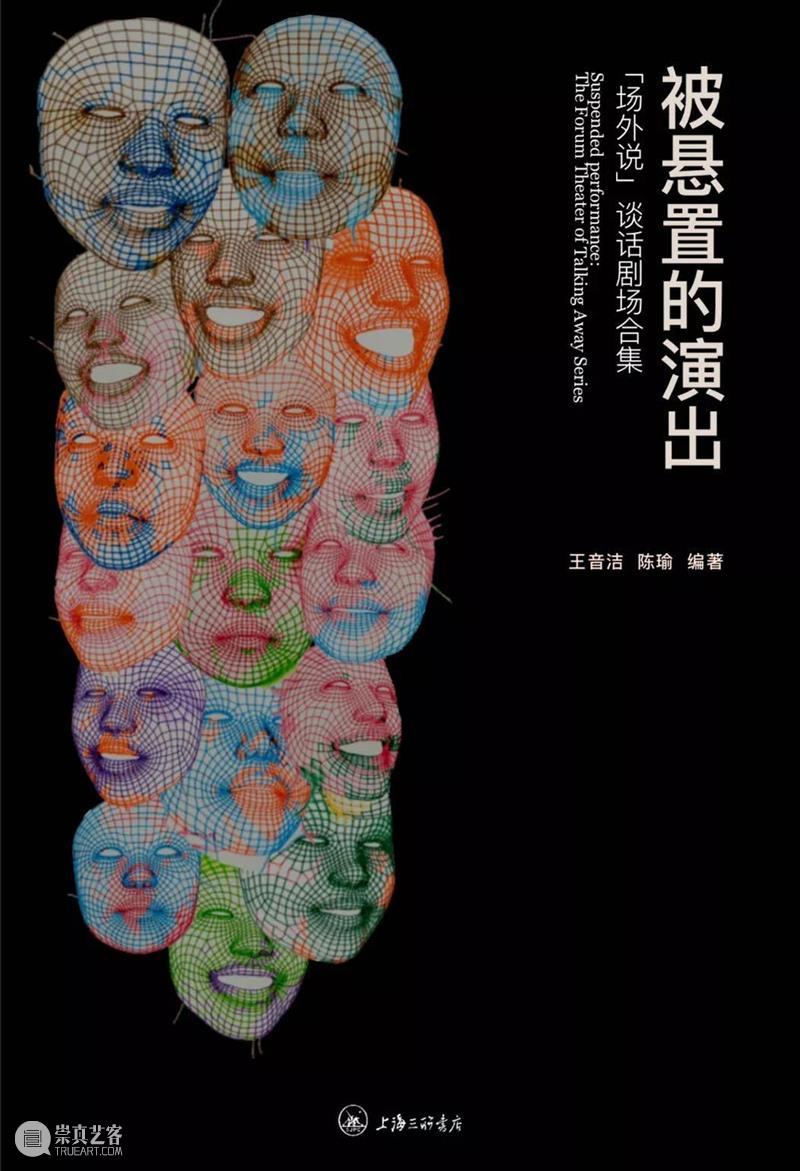
新书《被悬置的演出:「场外说」谈话剧场合集》
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即将于2021年4月推出
相关链接:
哈尔·福斯特的双重角色——《实在的回归》译后记(上) - 杨娟娟
延迟的效应:哈尔•福斯特对前卫理论的推进——《实在的回归》译后记(下)- 杨娟娟
哈尔·福斯特|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精神分析法(诸葛沂译)(上)
哈尔·福斯特|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精神分析法(诸葛沂译)(下)
杨娟娟|实在界的目光——哈尔·福斯特论创伤性艺术(上)
杨娟娟|实在界的目光——哈尔·福斯特论创伤性艺术(下)
注释:
[1]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杨娟娟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255页。[2]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第4页。[3]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华夏出版社,2016年,第100—104页。[4]本雅明·布赫洛:《新前卫与文化工业:1955到1975年间欧美艺术评论集》,何卫华等译,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5页。[5]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第5页。[6]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3), 17-18. [7]阿甘本:《什么是当代人》,白轻译,译文选自Giorgio Agamben, Nudities, trans. David Kishikand and Stefan Pedatell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19,是作者在威尼斯建筑大学(IUAV)艺术与设计学院2006—2007年理论哲学课程中正式讲座的一个文本。中文译文引自公众号“惊奇的房间”,见:https://mp.weixin.qq.com/s/csPu74n30IQ0vPj9-uuSPQ。中译本《什么是当代》由刘耀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8]Walter Benjamin, Reflections, ed. Peter Demetz, trans. Edmund Jephcot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m, 1978), 85.[9]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第188页。[11]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第237页。[13]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第267页。[15]《伪艺术史》是艺术家高洁重构艺术史的一个项目,该作品以音频形式出现,每一期谈论一个著名的当代艺术作品,将它脱离于原有的背景,而作为另外的作品放置在另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样的方式,人们能够以另一种艺术史、哲学、美学、社会学的知识去看待当代艺术。以此希望听众能够得到不是板结了的当代艺术知识。公众号和音频资料可查阅:https://mp.weixin.qq.com/s/qI1ZLUouG3FfWejBqjl_Ng;大嘴突击队成立于1994年,初始成员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和德国吉森大学应用戏剧系的在读大学生。1999年,他们的创造中心从英国诺丁汉迁往德国柏林。他们是非常早就开始探索舞台表演和影像结合的团体。作品当中影像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拍摄机器就是普通的家用摄像机,在舞台上刻意追求一种非常粗粝、低保真的视觉传达。在他们看来,影像不是一个认识真实的工具,而是需要被认识的工具。影像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不是技术,而是主题。他们的作品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舞台美术设计,而是一个包括表演、视频、广播等各种艺术领域多方面的跨界和融合。演出空间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非传统的剧场空间去做戏,把当代城市的日常生活容纳进戏剧的视野;另一类是进入传统剧场当中重新定义剧场空间,把日常生活引入剧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现实和戏剧并置的情况下,探索媒介化时代真实的含义;皮埃尔·于热1962年出生于巴黎,现工作生活于纽约。于热曾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校。他以20世纪90年代使用的“后期制作”(post-production)手法闻名,重新运用电影和大众媒体中的图像。于热创作的电影、装置和偶发事件艺术作品探索哲学思想,混淆事实与虚构,并用展览这一模式进行戏谑的实验。于热的许多作品融合了一系列生物元素,如昆虫、动物、植物和人类,以此探索他们的行为和彼此之间的互动。这些作品成为于热阐述复杂社会现象以及当代信仰系统的实验场。他在作品主题中加入心理学的元素,探讨幻想与真实之间不确定的界限。作品通常包括多种叙事和碎片化的含义,召唤梦想、权力与征服,以及对乌托邦的探索。近年来,于热的作品开始在博物馆和传统艺术场域以外的空间展出,进而拓宽了其艺术实践的范围。 以上三组的创作都具有某种巴迪欧在称赞德勒兹写作时所言的“用感觉的逻辑代替了对真理的追求,以创造性的生命内在性之名与超验观念进行斗争”,参见阿兰·巴迪欧:《存在的喧嚣》(节选),陈永国译,载汪民安主编:《生产》第5辑《德勒兹机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6页。[16]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第15页。[17]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18]斯蒂格勒:《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陆兴华、许煜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9页。中文译文还参考了陆兴华译《写屏》,载公众号“艺术—小说”,见:https://mp.weixin.qq.com/s/MmF_Vv7M-aWIanx6HptcMA。[19]哈尔·福斯特:《实在的回归:世纪末的前卫艺术》,第178页。[20]马丁·海德格尔:《什么叫思想》,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7页。[21]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3页。从贫困(impoverishment)这一点来说,福斯特还是有突破俄狄浦斯情结的意识的,只是粼光一现,未及深入。荒漠之苦是对摩涅莫绪涅的全力驱逐,它收编一切,包括实在之伤。[23]Georg Simmel, Simmel on Culture, eds. David Frisby and Mike Featherston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77. 中译本参见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吴㬫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24]语见罗兰·巴特所写《什么是写作》,收于他1953年出版的著作《写作的零度》,载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百花出版社,1995年,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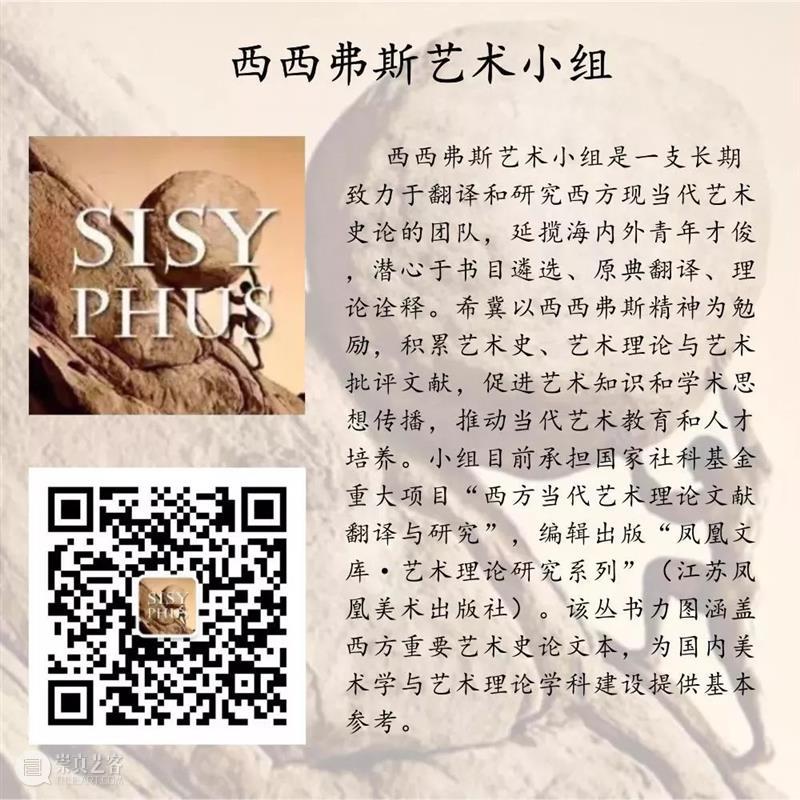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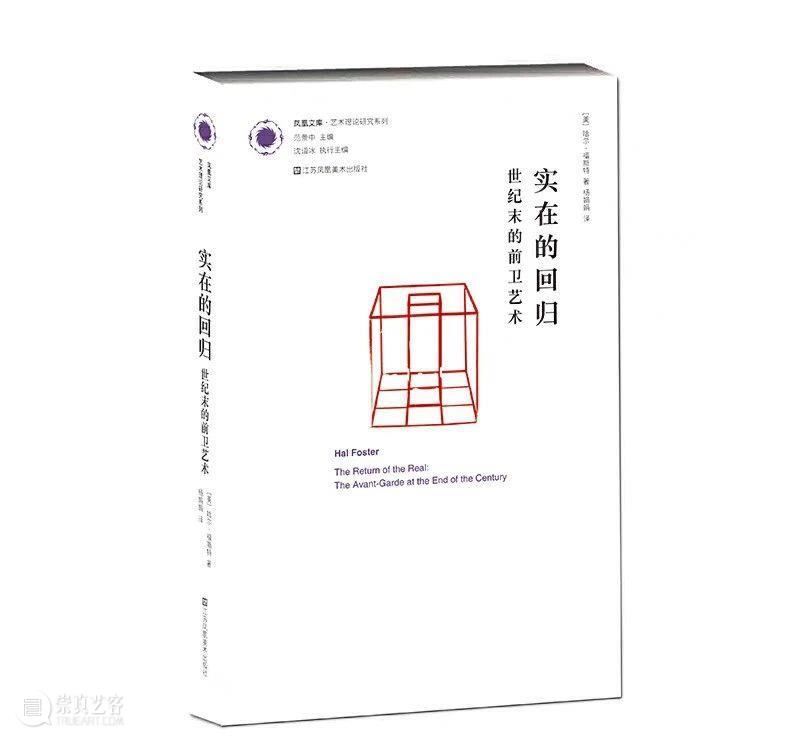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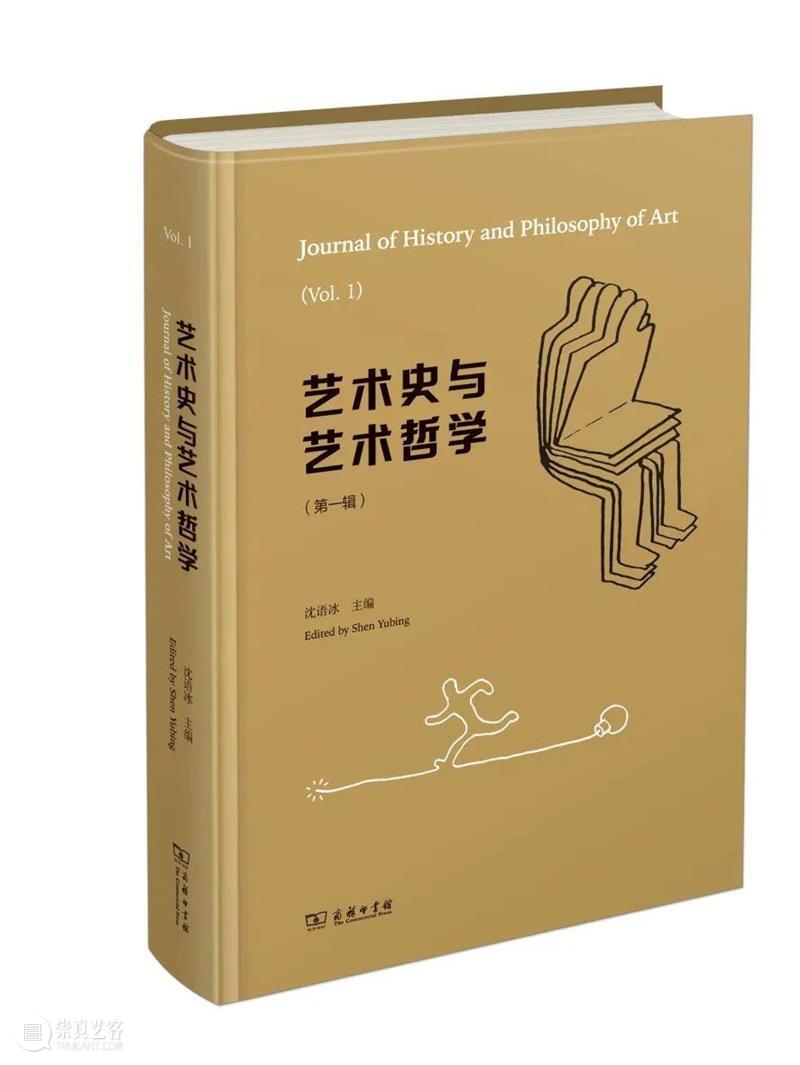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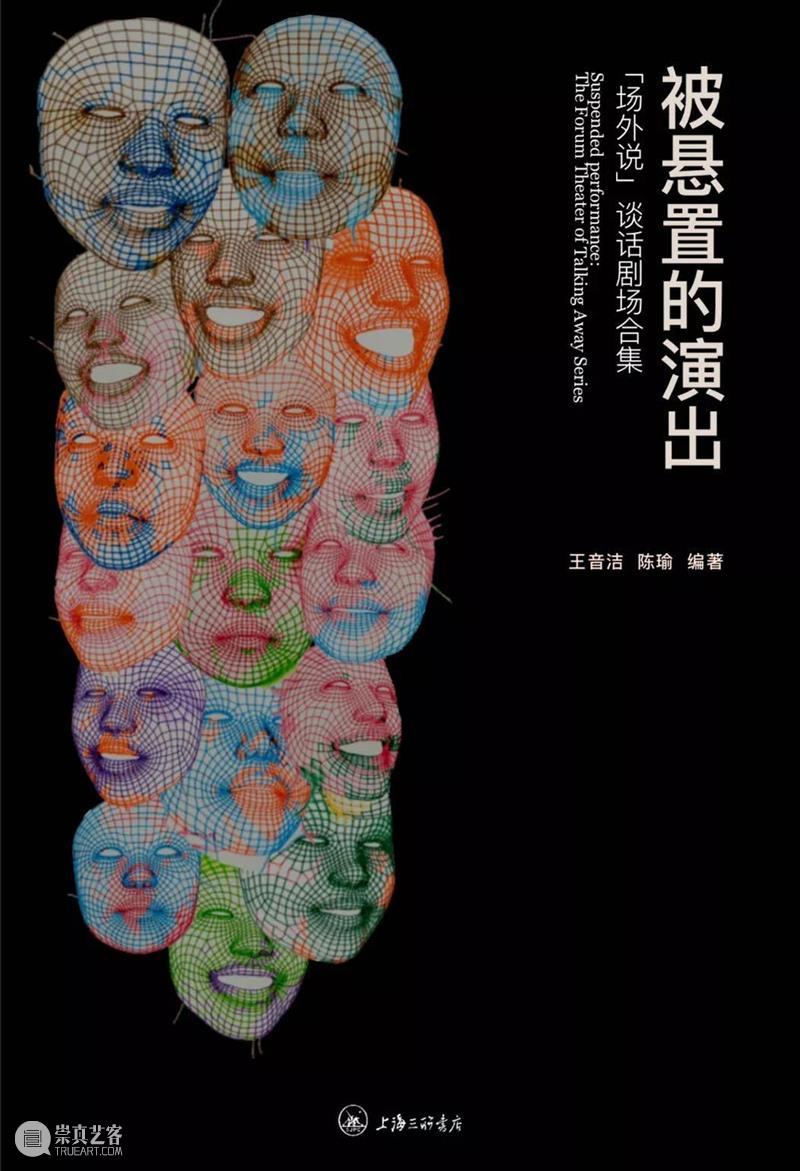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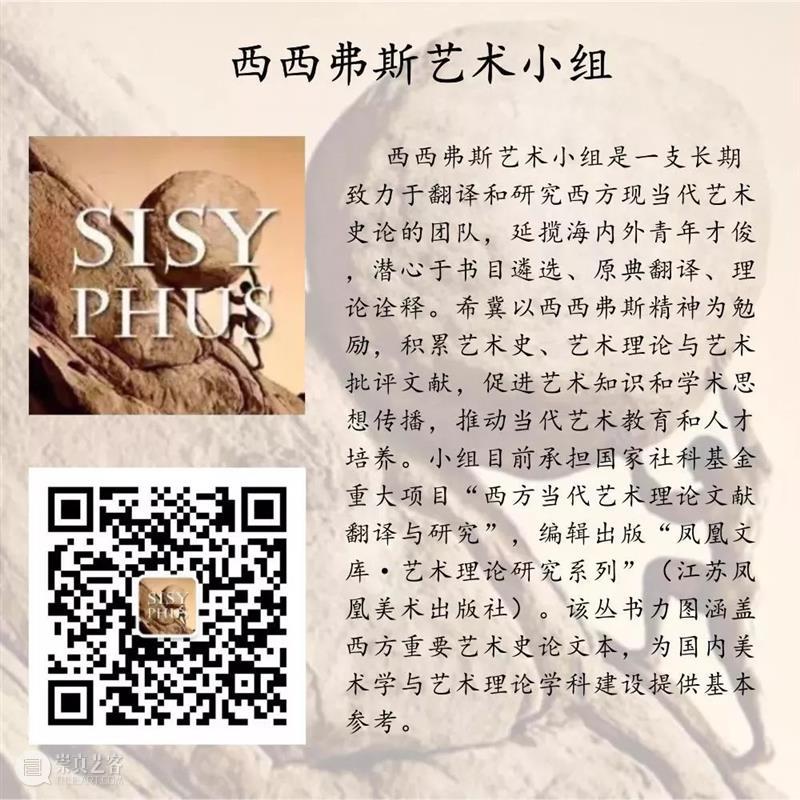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