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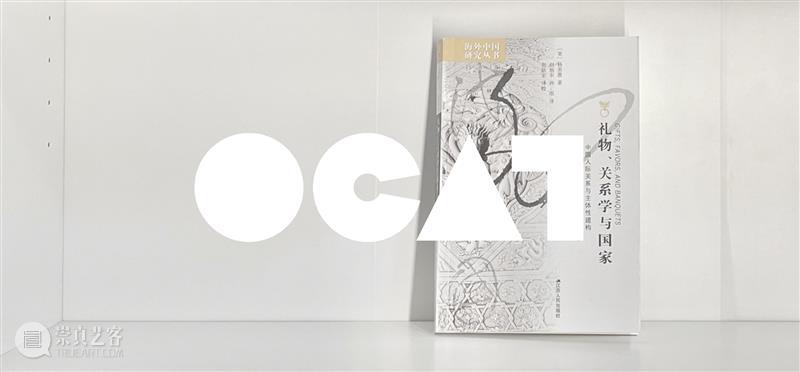

[美]杨美惠,华裔人类学家
(图片源自网络)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一书曾获美国民族学会最优奖,利兹都市人类学奖荣誉提名,维克多·特纳奖提名。本书的内容在于探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人情和面子。杨美惠称这三样东西对无论身在何地、何时的中国人都是谙熟于心的。随着“关系学”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应运而生,这一学科在世界范围上也不断地演变出了其最为复杂缜密的形式、并成为无处不在的社会现象。
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一书中,杨美惠力图呈现在1980年到1990年间,关系在中国大陆是如何运作的,并将这一系列的实践置于国家再分配经济,初现端倪的市场经济以及毛崇拜的背景当中。笔者沿着古代关系学的谱系,进而追踪到清代之前的儒家伦理制度,这一制度被她认为是一种“古代对建立国家官僚权力的法家的抵制”。而20世纪之际,杨美惠认为,关系学在掀起密集的关系学网络并阻止和切断国家机器垂直运作中扮演了同儒家伦理制度相似的角色。
01
关系和关系学
在关系中,有人从中获利,却也难免有人从中失意。将其作为一门学科,上升到学术层面后,关系学的复杂程度也不亚于任何一个学科。更为有趣的是,关系学在所有学科中有着独树一帜的优越性。这是因为这个看上去并不那么正经的学科,却能够让人得到比其他正经八百的学科多得多的学问。本书第一章节里,杨美惠也作出推测:“关系学”一词,是在社会主义中国才出现的。可以说,一个对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的基本要求就是社会联络能力,而关系学恰好赋予一个人应对生活、寻找门路的能力。
杨美惠认为,关系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值得考察,除去它模糊和善变的文化意义,人们对其褒贬不一、模棱两可的态度的特殊观念外,还在于一种展示其讽刺性意义的、民间的虚饰赋予其语义学上的意义。严格来说,“学”一字,本属名词尾码,附在某个词后,意思是对其的研究。因此,“关系学”可被理解为对“关系的研究”。而“关系学”同时暗含着讽刺之道。因为这一“学问”把培养人际关系的艺术提高到了一门完整的学科,似乎与其他学术专业一样必备。在体现这一讽刺意味上,有如俗话说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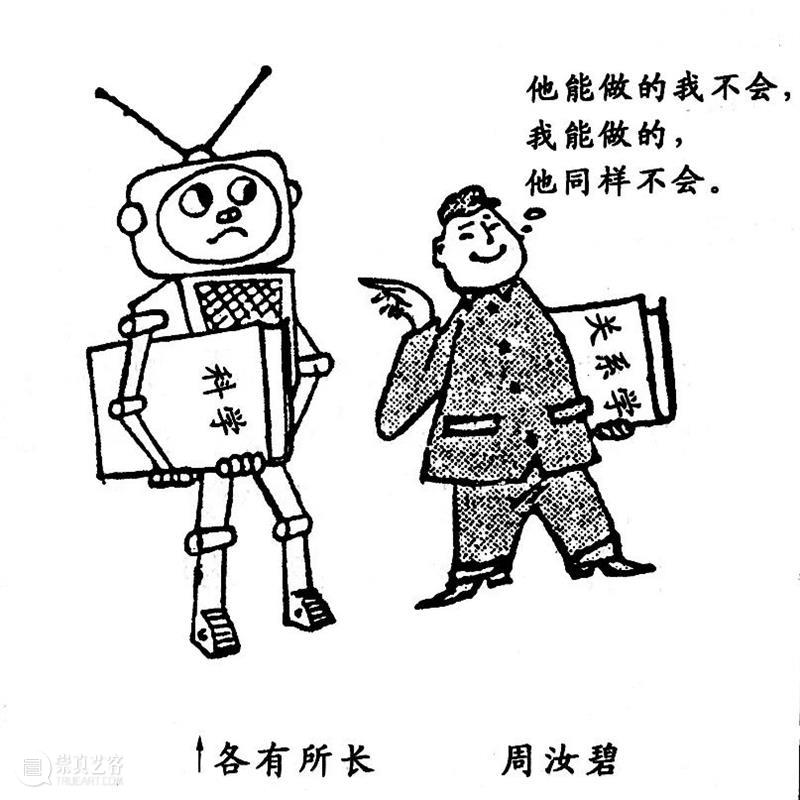
02
关系和礼物
关系和礼物是一直出现在杨美惠研究中的两个关键词。本书中,她称关系学为礼物经济。杨美惠在导论中讨论道:“关系学”强调相互约束的权力和人际关系的感情和伦理特性。“礼品经济”突现礼品、好处、宴请交换这样的成分。而在她的研究中,礼品经济之所以是个有用的术语,在于关系学运作中的逻辑与礼品互惠中所具有的许多属性有着共同之处。
杨美惠的礼物经济通俗来讲就是人与人间的礼物交换。而礼物的交换可谓是建立和维系关系的纽带。从不甚了解的两人建立关系开始,礼物可以从几瓶酒、几条烟开始。用礼物的交换来拉近关系、维系关系则需要更微妙的策略。在人际关系的艺术中,送礼的种类、场合和形式非常讲究。根据杨美惠的观点,不仅送礼的种类取决于要办事情的大小和收礼人社会地位的高低,而且还要巧妙地利用暗示让收礼人明白送礼的意图。此外,礼物的价值也应基本等同于送礼人想要索取的事物。
例如,本书中曾提到“80年代初,送一件30-40块钱的瓷器或布料子给工厂劳资科的主管,就能把三班制的工作换成固定的白班。”如何送礼是门讲究,礼物要送得恰如其分。杨美惠还举例道:“在那个时候(80年代初),把户口从农村掉到城市,或从小城市掉到大城市是最主要的需求,因为这比其它关系交换更加冒险、非法,这就需要送600块钱的黑白电视机或1200块钱的彩色电视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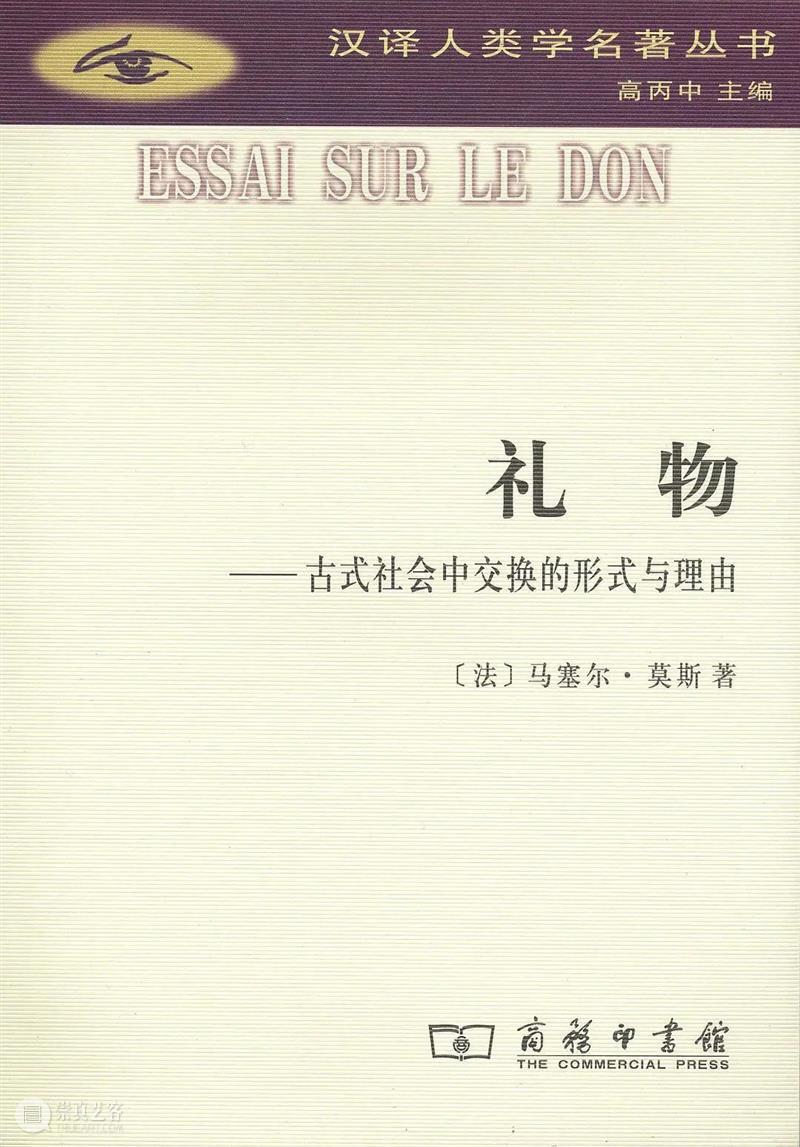
《礼物》一书封面,[法]马塞尔·莫斯|著 ,汲喆|译
(图片源自网络)
03
礼物、关系学与国家
第二部分则具体关注关系学重新出现的历史意义。杨美惠的观点在于:关系学的重现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中,属国家权力的对立。在对关系学的对立面进行关注的同时,作者试图对本地人和西方人经常作出解释的方式拨乱反正。杨美惠想要使读者看到的,是一种关系如何对立于权力的分析,以及针对这一套对立作法的分析可以依据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和道德政治话语。她认为,这是对国家的现代性和权力作出诊断和批评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美]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赵旭东、孙珉译,张跃宏译校,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年。
[法]马塞尔·莫斯,《礼物》,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
作者/图文编辑:李新运

OCAT研究中心图书馆旨在提供一个公共空间,激发和促进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特别是研究、创作的生发与实践。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