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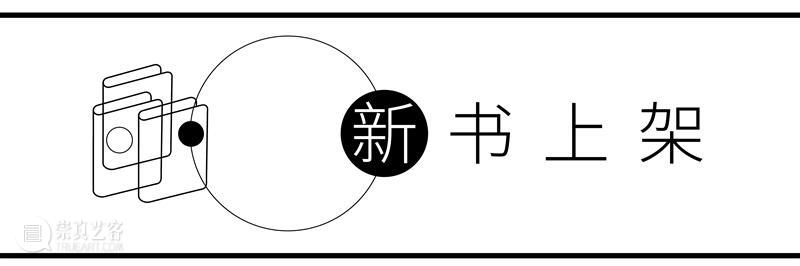
大家好。大前天我们发布了三本新书:
01.米歇尔·福柯《自我坦白:福柯1982年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的演讲》(潘培庆译),“福柯思想三次重大转变的交汇点”;
02.罗伯托·埃斯波西托《非政治的范畴》(张凯译),“埃斯波西托首个正式出版的中译本”;
03.让-弗朗索瓦·马太伊《被毁灭的人:重建人文精神》(康家越译),“人文主义的未竟之语”。
这三本好书均已在拜德雅微店上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让-弗朗索瓦·马太伊的《被毁灭的人:重建人文精神》。
先介绍下作者:

让-弗朗索瓦·马太伊(Jean-François Mattéi,1941—2014),著名法国人文主义者、哲学家,曾任尼斯大学和普罗旺斯艾克斯政治大学哲学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出版多部专著,在西方学界声誉颇高,包括《内在的野蛮》(La Barbarie intérieure)、《柏拉图与神话之镜》(Platon et le miroir du mythe)、《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Heidegger et Hölderlin)、《思想的奥秘》(L’énigme de la pensée)、《空无的眼神》(Le Regard vide),以及《毕达哥拉斯和他的信徒们》(Pythagore et les Pythagoriciens)等。

《被毁灭的人:重建人文精神》(L’Homme dévasté. Essai sur la déconstruction de la culture)则是马太伊的遗世之作,是他留给世人的一份哲学遗嘱。他用自己这最后一部著作道出了人文主义的未竟之语。
是什么让“人”走上了毁灭之路?马太伊在本书中给出的答案是“解构主义”。
可以想到,这是一部充满争议的著作。马太伊主张回归柏拉图的遗产,重拾加缪和阿伦特的信念,追溯人性的本原。同时,他痛斥福柯、德勒兹、布朗肖、德里达等人的信众,批判“毫无意义的”解构主义,与“人之死”的观念斗争。
但千万不要就此以为本书只是愤懑之辞的铺陈。
相反,本书是十分独到且严谨的。从《华氏451度》到《黑客帝国》,从《阿凡达》到《第二人生》,马太伊以其独具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些耳熟能详的科幻电影和虚拟游戏,发掘人之毁灭的证据。他从四个面向描绘了解构主义如何让世界分崩离析,让“人”走向毁灭。从叙事到肉体,作者的分析层层递进,让我们震惊于世界的面目全非,也震惊于“人”的面目全非:(1)叙事终结:语言分崩离析,思想面临斩首;(2)现实虚化:虚拟取代现实,拟像大行其道;(3)艺术破碎:绘画失去脸孔,音乐失去旋律;(4)肉体枯竭:人从身体缺席,迎来改造人的未来。
在本书中,马太伊对后现代思潮及其艺术、文化和政治影响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他认为,福柯、德勒兹、布朗肖、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的思想“破坏”和“毁灭”了西方知识的根基,模糊了是非界限。信息技术的兴起更加剧了这种混乱。人,将被引向一个失去意义、失去价值的荒诞世界。
那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办?这正是马太伊在本书中邀请我们一起来思考的。

下面推送的是马太伊亲自为本书撰写的精彩导言。
最后之人:人性已死?人文主义已逝?
我们,露茜和我,生活在一个毁坏的世界中;由于不懂得报之以恻隐之心,我们与之疏离间隔,使它的厄运,和我们的,都更加深重了。
米兰·昆德拉,《玩笑》
必须承认,时代精神与人之间已不再合拍。无论是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谈《文明及其不满》,还是与查尔斯·泰勒谈《现代性的隐忧》,我们在这一点上都意见一致:人正陷入一种颓丧,而这种颓丧预示着人之终结。这时代的天际也阴郁晦暗,证实了托克维尔的预言——一个不再照亮未来的过去,使精神独步于一片漆黑之中。如果说时代精神不再拥有光明作为向导,那是因为人已丧失了方向感。阿尔贝·加缪在他的《札记》(Carnets)中提到,他本能地追寻着一颗隐密之星,因他在自己身上看不到光亮。这是在承认我们已经不可能在人的身上看到光亮了。一个已然弃绝了其文化遗产、投身于致命放纵的欧洲人。两次世界大战的震荡,在犹太大屠杀的创伤中达到顶峰,使诉诸人文主义的希望几乎无存。
人之被废黜,于今日早已司空见惯。在奥斯维辛和广岛之前,一些欧洲作家就已敲响了警钟,宣告人性正在向着兽性——或随之即来的灭亡——倒退。D. H. 劳伦斯在1920年出版的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毫不犹豫地告诉他的一个角色:“人性已死。将会出现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以一种新的方式。就让人性尽快消失吧。”同年,年轻的古斯塔夫·亚瑙赫(Gustav Janouch)在布拉格遇到卡夫卡。在一次交谈中,他对《变形记》的作者宣称,他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已被摧毁的世界。卡夫卡回答他,如果一切都已被摧毁,那么人们就可以重新开始了。不过,引领他们向他们期盼的未来走到此处的路径已经消失,他们从此将只能活在“一个无望而漫长的堕落”之中。卡夫卡还补充道:“我们不再能辨认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了,赋予事物超越个人意义的相关性。虽然看上去一片熙攘喧嚣,可每个人都哑不能言,孤绝于自身之中。世界的准则和自我的准则重叠交错,不再能协同生效。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已被摧毁的世界中,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错乱的世界中。”(1978,135)
这位小说家感觉到,事物不再由一个至高的意义所支配,世界和人也不再相偕相接。正因如此,“从外部支撑人之存在的那些脚手架倒了下去”(1978,166)。当时间挣脱了铰链,世界就会错乱得如同大钟的梦魇。况且,又没人能将过去与未来的发条连接起来。
人之终结
从埃斯库罗斯(Eschyle)到季洛杜(Giraudoux),悲剧中从不缺那些珈桑德拉。她们在历史中也不曾缺席,总是在为科学提供预告。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预言人类将在200年内灭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往后推迟到1000年。微生物学家弗兰克·芬纳(Frank Fenner)就更急迫了,把这个消亡缩短到百来年左右。至于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Francis Fukuyama),在出版了《历史的□□》(La Fin de l’histoire et le Dernier Homme)后,旧病复发,又在《人之终结》(La Fin de l’homme)里研究起力图消灭人类的超人类主义论题。那些高深的生态学拥护者也不屑于掩饰其意愿:用被视作“大地母亲”的生物中心主义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其中最激进流派的奋斗目标是消灭人类,因为人类活动扰乱了自然,并摧毁了大量的活跃物种。
这些关于人之灭亡的假说期待着在未来得到验证,但这甚至比届时无人能够见证更加不可能。它们只有在与西方文化决裂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这正是解构主义意识形态所宣称的目标。我们一般把我们的文化称作“人文主义”,一个既含糊又新近的词,因为它只能追溯到19世纪。“humanismus”这个词是德国哲学家阿诺尔德·鲁格(Arnold Ruge)在1840年创造的,并非是用来表示文艺复兴中重新燃起的对古典作品的鉴赏热潮,而是用来指称他提出的与□会主义“单面人文主义”相对立的“全面人文主义”的概念。马克思在1843年写给鲁格的一封信中,采纳了这一“人文主义原则”,以便将其运用到□产主义之中,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对把人放入“一部新作”无甚兴趣,但用他的话说,他正在试图让“他的旧作重获良知”。这绝不是说□产主义学说已与先前的人文主义分道扬镳,而是他自己喜欢到未来中去“实现那些过去的理念”。
说这些是为了看清楚,如我将在下文所展示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中有着至高地位。我们随时都可以宣布人之终结,连同人文主义一起终结。然而,某一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它所依持的理念也一同终结。若是我们不再对人性理念的持久性抱有信念,那么我们很快就会使人的现实连同这个理念一起解体。这是京特·安德斯在《过时的人: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灵魂》(L’Obsolescence de l’homme, Sur l’âme à l’époque de la deuxième revolution industrielle)中所确立的。作者假定人存在于其稳定持久之中,就如我们在古代神话中所读到的那样,而如今人正在变得过时。“过时”这个词专用于消费产品,其时效是事先设定好的——他选择用这个词,是为了强调现在的人把自己视作与工业产品没什么差别的东西。因此,人能够顺从地接受自己的消亡,好像知道自己已完成了使命,必须让位给更精良的产品了。
安德斯把对需要除去的过期之人的批判集中在人的自然性上。这种自然性与暴露出仿造性的可制造性——也就是其虚假性——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正是他所揭露的“普罗米修斯之耻”,成为其所是——即人——的耻辱,而非被制造成其所不是——即东西——的耻辱。在诗人和哲学家们的不懈教诲中,有一条简洁的命令:“成为你自己。”但是,要成为一个人,就必须走到这个连自己都不甚明了的人之存有(être)面前,并将其看作一个奥秘。当安德斯力图复兴那些往昔的理念,力图凭借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的、对人性的信仰重建这些理念时,他是属于人文主义传统的。当他断言“人的边界须从人之所是之上如实地勾勒出来”(1956,33)时,他承认了人是存有,而非东西,并且,这个存有拥有边界——他禁止自己跨越边界,让自己不至于抛弃人性。
技术产品随着革新相继而来,又随着革新转瞬过期。它们的朝生暮死取决于生产的仿造性,而人的存在却取决于诞生的自然性。如果人去和在力量及繁殖能力上均比他优越得多的产品对抗,那他将立即因为其所是而羞愧不堪。于是,存在的重量从主体转到了客体,从被生下的不便——按照萧沆(Emil Cioran)的说法——转移到了被制造的不快。普罗米修斯之耻驱赶着人去仿效其所不是,仿效一团阴影、一种虚构,或一个拟像(simulacre)。安德斯毫不迟疑地写到,作为一个伦理学家,他还真狠不下心来“为人的理念送葬”(1956,59)。的确,当我们细看人之存有的行程,从出生到死亡,我们无法避而不提:使他抵达其人性的,并非某个没有成为其所是的真实的人,而是柏拉图意义上的这个词——理念(Idée)。
人性之消解
人之存有能变得和其制造的产品不相上下,这使人在民主社会中的丧权失势清晰可见。那些□权政体对此也并无不同构想。纳粹在流放关押犹太人时,并没有把在聚居区以及之后在集中营及灭绝营中集中起来的人看作人之存有。艾希曼(Eichmann)也没有把自己视为犹太人的敌人,他只把自己看作一个运输部部长,只对运送乘客去死亡营的那些列车负责。当一个人在其他人看来并非其所是、并非人之存有,当其他人也不思量这个在他们眼前遭受痛苦的是不是一个人——因为他们对于人之理念已经盲目无视,而且,借用列维纳斯(Levinas)用在□帝身上的话,他们对这出现在理念中的人毫不在乎,将其视作完全被抛弃的型号,那么,他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像对待东西一样对待这些人之存有。
犹太大屠杀揭示了现代性使人沦落到产品的地位,被社会为了行政管理所利用。悖论在于,这个人之存有的社会不再自问人性之存有是什么了。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将这一点讲得很明确:官僚机构的合理化改革是如何使希特勒分子毁灭犹太种族、使□大林主义者毁灭有产者成为可能的。□权主义的出现带来了文明的进程,但这个文明进程并不能阻止□权主义误入罪恶之途。最让人吃惊的是“犹太大屠杀是在一个现代的、理性的社会中,是在我们达到了高度文明的、处于人类文化顶峰的社会中出现和实施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是这个社会、这个文明、这个文化的一个问题”(2008,17)。当鲍曼强调是官僚机构为□权政体铺平了道路时,他指出,伴随着人性的丧失而出现的,正是对创造工具的人和使用人的工具之间的混淆。如果说我们不管怎样都能做到“在非人的条件下仍然是人”(2008,250),这是因为我们在自身中仍保持着一个人的理念——不毁掉我们的人性,就抹不掉这个理念。
齐格蒙·鲍曼揭示了一个时代的特征,他将其看作人性的液化。在诸如《液体现代性》《液体爱情》《液体生活》《液体恐惧》《液体时代》《液体现代世界中的文化》等一系列作品中,这位社会学家观察到有一种主导力量切断了之前几个世纪给文化带来的东西。什么是液体生活?一种消费生活,将人降格成产品用户,而产品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消失,为新产品腾出位置。身陷永不停息的欲望和消费之中,人的存在与物体的转瞬即逝混为一谈,而物体的出现只是为了随之消失。我们生活的框架则更加变幻不定,因为它被一条我们难以追随的消逝痕迹拖走了。虽然在法律上仍服从于陈旧如破衣烂衫的人文主义,但事实上,人已降格成了一片含糊不清的形象拼凑。
一旦生命进程转变为生产程序,也就是说,成为一堆被剥夺了目的的理性手段,时间就会风化,不再向人性敞开意义的天际。人不再旅居于这个世界,离开了一切居所,消散成一大堆碎片。人及其文化——“一种解除了约束的、断裂的、遗忘的文化”——的毁灭,鲍曼强调(2013,101),是经由它们的解体,或者说它们的清洗,而完成的。存有之间的永久联系以个人的爱、艺术文化和社会团体的形式,一点点地被液化,人性的理念无法再建立起一个人或者一部作品。在一种液体的生活和一种被清洗过的文化中,一切都被平等化,损害了创造的品格。真实的人之间的实际关系让位于虚拟连接,而每一个操作者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切断连接——按下“删除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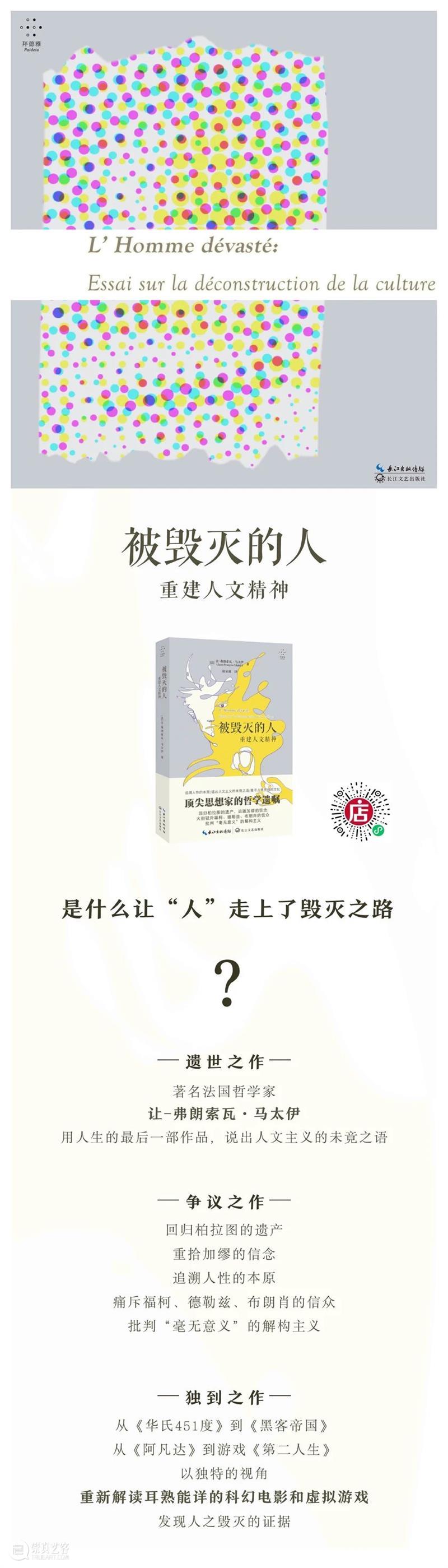
疯子的宣言
毁灭,与没有品质的人无关;毁灭的,是自身带着人性理念的存有。人文主义的消失是其晚近的意识形态。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人类安魄曲是早先的真相。这部献给消逝之人性的弥撒曲中最富丽的管弦配器便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对于先知来说,人是“某种必须超越的东西”,先知告诉群众:超人将要到来。由于他的话只引起了哄笑,因此他决定向他们描述“最卑鄙者”——“末人”。这个角色与仍保持着人形但几乎已不再有人性的“最丑陋的人”不分彼此。这种人之残渣,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形容之物,先知指责他就是杀死□帝的凶手。
谁是末人?一个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混乱、无法孕育一颗星星的存有。
无力创造。当被问及存在之时,他不知道这些词的意思:爱、创造、心愿、星星。
不理解世界。由于受不了太阳的光芒,他向其同类递了一个默契的眼神。
目光的贫瘠。他对世界之宏大无动于衷,将一切事物都缩减到一只蚜虫大小。
歌颂无足轻重的事物。最后,他满意地宣称自己发明了幸福。
理想的枯竭。末人不再想创造也不想孕育、建立一个新的开端。群众为在末人的肖像中看到自己的形象而心花怒放!他们跺着脚,眯缝起眼,时不时咳嗽两声,咂咂舌头,尼采写到,无法回归安宁生活的征兆倍增。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与《快乐的科学》中的辩解者(他的名字叫“疯子”)是交相呼应的。群众没有听到先知和疯子的宣告:一个是人之死,另一个是□帝之死。尼采描绘了一个场景:一个疯子在正午时分点起一盏灯笼,仿佛太阳陷入了日蚀。这个人去了市场,不是为了寻找超人或末人,而是为了寻找□帝。群众嘲笑这个失去了□帝的人,就如一个人走丢了孩子一样。于是,疯子向人们发出愤怒的呼喊:“□帝去了哪儿?我要告诉你们。是我们杀了他,你们和我!”人们是杀死□帝的凶手,并且,也是毁灭人类的间接凶手,因为人之消除,就是□帝之消失的另一面。
世界失去了基石,正在极度的混乱中瓦解。疯子声称人类已经抹去了天际,还使地球脱离了太阳。我们的星球失去了光明,在堕落中粉身碎骨,从四面八方沉陷并被锁入了暗夜之心。因此,我们才不得不在正午点亮灯笼,就像那白痴在演讲之前做的那样。还有,丧钟敲响了它的主旋律:“□帝死了!□帝活不过来了!”疯子此刻才明白,他来得太早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可怕:□帝死了,□帝被他的创造杀死了。因此,疯子才会突然冲进城里的教堂,唱起他的□帝安魂曲。
束缚地球的太阳之消失,象征着末人对人性的无动于衷。没有方向,则象征着人不再将自己看作人。在尼采的观察中,有一场对星宿(astre)的遮蔽,一场灾难(désastre),就表现在末人听到“心愿”(désir)或“星星”(étoile)这些词时的无动于衷。“星星”的意象被视作去除了人的□帝,这阐明了与“心愿”之间的亲近关系。“心愿”这个词源自“星星之不在”(desiderarium),是吉兆。末人不仅是在没有考虑其行为后果的情况下杀死□帝的存有;在失去了星星之后,这个存有已经不再能承担其人性了。
主体之死
就像患了失忆症一样,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去向何方。“‘我不知道向哪边转;我就是那个无法找到出路的人’,现代人呻吟着……正是这种现代性使我们生病了”,尼采在《反基□》(L’Antéchrist)中如此写道。但病人可以考虑两种策略。要么在哀痛中坚持寻找引领生活的星星,为此,他需要继承人性的遗产,按照马克思的设计,他的人文主义将会实现过去的理念;要么为□帝之死和人之终结欢呼鼓掌,享受在这两堆灰烬中获得的自由。我要在本书中探索的正是这第二条路,看看人——按帕斯卡(Pascal)的话来说,远非无限超越人的人——能否放弃他登上人类之高度的意志。
康德将关于存在的问题归并为三个质问:
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关于真相的问题,由形而上学负责。
我应该做什么?这是关于正义的问题,由伦理学负责。
我可以期望什么?这是关于善的问题,由宗教负责。
然而,康德又为这些基本问题加上了第四个:人是什么?这属于人类学,研究人类的各个方面,为了将其多样性归于统一。正是这种统一——我们称其为意识、我思、灵魂或主体的统一——为现代性所质疑,现代性否认这是一个实体的现实。在人这个词之中,不存在一个个人能在其自身中抵达的稳定核心。无论如何探索人性的内在性,我们只会发现一个越来越黑暗的虚空,我们好像抓住了它,但这是凭着——借波德莱尔的意象来说——旋涡的吸引力。
在柏拉图眼中,人无非就是他的灵魂,而且,由于它与他人的灵魂互相一致,因此他更应该关注它。当圣奥古斯丁走入他的思想圣殿时,他发现了□帝,比他自己的内在性更为内在。相反,对现代人来说,降临自身却只会遇到虚无。因此,尼采指出,几个世纪来科学一直在寻求的真实世界,对于我们而言,已成为一种传说。但真实的人同样成了一种传说、虚构或幻觉。事实上,后现代性成了一种解构人类所有决策机能的游戏。人们可以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作品中看到这种例子。这位《词与物》的作者援引了尼采的思想脉络上的人之终结或人之死。它要采取行动,革除以主权主体的形式统治了2000年的存有。这便是由哲学、科学、艺术、道德和宗教所建立的关于人的理念,于此被废除了。
在尼采重述地球脱离太阳的形象之前,康德就提到过哥白尼革命。现代人已不将□帝视作中心,而且很快也不会再将自己视作中心,因为他不再占据创造的中心。随后,人们对将人置于物种序列、归入动物进化环节的达尔文理论胡乱评论。最后又为这些弗洛伊德做过反思的耻辱加上了最终润色。革除意识的耻辱成了一棵在无意识的洋流中消失了的珊瑚。福柯于此得出逻辑结论,假定“选择一种革除主体的举动是伪主权”(Dits I,1095)。这种假造的主权以何种形式呈现?在奥古斯丁主义神学传统中受到神圣诫命的灵魂,在康德主义的伦理传统中受制于法律普遍性的主体,以及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中受制于城邦□法的公民。
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起源和基础”(Dits I,816)的主体的虚假主权在历史中屈从于“大写的主体”的三个形象:“□帝、良知和社会”。因此,它依赖于他律的决策机能(instances hétéronomes),最终成了它们的奴隶。人之死和人文主义的终结,就如那些被囚于其处境限制中的生灵的故事,是大写的主体死亡的映像。从这堆瓦砾下浮现上来的,是一个解放的个体,他致力于他唯一的权力欲望。因为权力是福柯对人之死押上的真正赌注。一个挣脱了锁链的欲望,就有理由取消一切禁忌,尤其是和性与毒品有关的禁忌,也有理由取消所有对个人享乐加以约束的规范。
沙中的面容
20世纪下半叶,反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从全球斗争中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政治手中接过了班,将□帝之死等同于人之终结。众多思想家毫不内疚地迎合着解构主体的癫痫假设。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用科学工作的必要性来解释他对“可笑的人类概念”的拒绝:为了学习历史辩证法,有必要“将人的(理论上的)哲学神话化为灰烬”(1965,236)。至于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他一直在否认精神分析是一种人文主义,甚至提出“精神分析的对象不是人,而是他所缺失的东西”(1966)。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则推敲出了将人从科学中排除出去的决定性公式,人成了不能存在的对象:“我们相信人类科学的最终目标不是构建人,而是消解人”(1962,326)。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兴趣不在于人,而在于其相关性、网络、知识领域的结构,简而言之,就是他的语言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系统。
吕克·费希(Luc Ferry)和阿兰·雷诺(Alain Renaut)是最先采用这种激进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方法并揭示其矛盾的人。在研究1968年左右发表的代表性文本时,他们强调了当时法国哲学的共同基础:在理论上“对理性的解构”,导致了在实践上“主体性的毁灭”(1988,55、68)。无论是福柯、德里达、德勒兹、拉康还是布迪厄(Bourdieu),他们都在追求一个相同的计划:去除被认为是幻觉的自主主体,为一种失去了重心的匿名个体腾出空间。仿佛“68思潮”(la pensée 68)的一切目的就是颠覆人文主义传统,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以“思潮”为基础的《知识分子的坟墓》(Tombeau de l’intellectuel)中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哲学变得不近人情”。事实上,知识分子们——带着一种真正的“对普遍性的仇恨”(1988,59、194)——提出要摒弃的,是人的坟墓,是我们所继承的那个人的经典形象。
如果说“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向野蛮敞开了大门”(1988,195),那么解构主义似乎确实是一件野蛮的事。因为,野蛮不就是毁坏文明所建立的事物吗?如果打算建立一座更坚固、地基更安全的建筑,那么拆除一座旧建筑则是合理的。但是,解构的概念——更有甚者,破坏的概念——是对未来建筑的禁止,因此,是一种对不育的首肯。费希和雷诺将解构主义的意识形态解释为“有条不紊的清算事业”和“消除主体”(1988,233、246),并强调它们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野心更大的企图,即在与世界的交叠中取消人类的身份状态。解构主义的冲动只是一场深远运动的表面部分,这场运动旨在取消人之构成的本原。这种蹂躏是一种真正的毁坏。
在卡夫卡描写现代人变形为动物之前,尼采就已经用矿物的隐喻来呈现人性的倒退了。在《朝霞》(Aurore)的第174段,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不是在取最短的道将人性化为沙子吗?精细、轻柔、圆滑、无穷的沙子!”正是这人之沙洲展现出了毁灭之貌。毁灭(devastare),恰恰就是“变成沙漠”(rendre désert)、“掏空”,因此,毁灭正是一个背弃自己和世界之人的行为。海德格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这一点的:“毁灭发生在一切之中:世界、人类、大地,导致对所有生命的遗弃”(2006,28)。汉娜·阿伦特也曾用类似的语言来形容□权主义,对她来说,□权主义就是“运动中的沙漠”。她对“有组织的荒芜”的分析击中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性,与卡夫卡对“错乱”世界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它的危险:它将会毁灭这个世界——一个似乎到处都是穷途末路的世界。”(1972,27、231)
要理解这种形而上破坏的意义,我们必须重新思索一下已经耗尽了资源的人文主义这个词。我将用更严密的建筑学术语代替它。如果说解构意味着在宗教、艺术、哲学和科学中将人抛弃,我将首先审视一下在现代性将人瓦解之前人之构成的本原。这种组成在希腊哲学、罗马法和基□教的交汇处,建立了一种以人性模本为中心的、建筑术的文化。古代哲学、基□教教义,以及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的综合,已经发展出了先于人文主义概念的、严格的人性理念。正是这种人类灵魂的文化,铸就了尊严的概念,建立起一种作品的结构,而人正是在这个结构中认清了自己的面貌。
与之相反,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近期的现代性对解构建筑术思想和作品的计划已经商量妥当。当海德格尔谈到对存有之历史的破坏时——被看作人文主义实现之基础的形而上学传统,他为哲学性解构的激进运作开辟了一条道路。从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开始,这种实践并不是以一种方法或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作为一种分解西方思想之“基础概念的传统结构或建筑术”的练习(Psyché,1987,338)。在液体生活声称自己是时光流逝之际,解构主义思想正在为世界的崩溃欢欣鼓舞。我们将看到这种做法是如何通过拆解一种在思想中禁止诉诸中心和基础的语言来颠覆建筑体系之遗产的。
第三章是关于模本之解构,鉴于拟像之来临。由于缺乏调节的理念,现实成了其影子的影子。京特·安德斯在雅克·德里达之前,就已揭示了让存在沦为类似于柏拉图式洞穴的光影游戏。他书中的主要文章聚焦于广播和电视传送的幻象,标题为“作为鬼魂和作为母体的世界”(“Le monde comme fantôme et comme matrice”)。安德斯认为,世界已进入了一个解体的过程,虚拟鬼魂取代了真实的人。没有什么能比当代艺术更能说明这一点,我将在第四章中展示这一点。自希腊和文艺复兴以来被视作普遍的建筑术的西方传统艺术,正随着人类存在的虚化而破碎。列维-斯特劳斯对绘画中风景和面容的消失以及音乐中对音调和旋律的摒弃表示遗憾。似乎当代艺术的前卫先锋们都急着要摆脱以一元的方式布局的作品。在文学中——写作的中性,绘画中——画布的空洞性,音乐中——乐器的沉默,都成了艺术的终极限制,一种已变得面目全非而不自知的艺术。
最后一章对人的终极解构进行了定位,这已不在人业已枯竭的精神理念之中,而是在他的肉体现实之中。我想谈谈那些为了人之继承者的利益而想要废除人的后人类意识形态。当福柯认识到“实现□帝之死的,正是人之死”(2008,78),这份死亡证明是先兆性的,但还不完整。因为从这时起,在人之死中,改造人(cyborg)诞生了。人们还可以用其他名字称呼它:后人(posthumain)、超人(transhumain)或神经元人(homme neuronique),并给它铺上硅基集成电路的神经植入物。无论这虚拟形象是什么,它都不再会回复到前人的身体、智力和精神特征,它的生理性别也中性化了。人自己宣布的人之终结,将使过去的人性成为一种废品、化身或拟像。描绘一个人将成为其自己鬼魂的时代的,并不只有安德斯。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一篇关于“二战”大屠杀的精彩文章中,质疑了丧失人性之人的命运。“这话虽然还是人话,但从这个词的基本意义上说,它是由幸存者、记忆中的人和鬼魂说出来的。”(1987,261)
人不是鬼魂,虽然他们的特征可能会像画在海滩上的沙脸那样被冲没。可是,他们见证着,某个并非影子的人正在真实面孔的模本上勾勒这个轮廓。
昨天,小编说:
三本新书营业第三天效果:福柯44分,埃斯波西托36分,马太伊36分。卫冕冠军福柯以8分优势稳居榜首,种子选手埃斯波西托和黑马马太伊仍然在第二名上缠斗。最终如何?答案明晚揭晓,敬请期待。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