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艺术文献 | 什么是数字电影?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什么是数字电影》(Digital Cinema)选自2009年劳特里奇出版社的《电影与哲学指南》(The Routledge Compagnion to Philosophy and Film),第75页至第84页。这本书是目前最重要的电影哲学参考著作之一,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51位哲学学者和电影学者参与了撰写,其中包括诺埃尔·卡罗尔、大卫·波德维尔、弗朗西斯科·卡塞蒂等,学术背景偏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该书中文版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购买,由我主持翻译。这篇文章尝试从根本上定义“数字电影”,尤其是从本体意义上与“其他”电影的可能区别在何处,文章充分结合了技术性的维度,作者贝瑞斯·高特(Berys Gaut)是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教授,是分析哲学中电影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曾出版《电影艺术的哲学》(A Philosophy of Cinematic Art, 2012)等著作,并与美国分析美学家围绕电影问题展开过比较深入的争论。原文是《指南》中的一个章节,采用了英美图书出版时的注释格式,在网络发表时没有一一调整,如对注释内容和参考文献感兴趣,可以结合文中信息在原书中查证。译者王亚南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大旗虎皮
(北京大学李洋教授)

贝瑞思·高特(Berys Gaut)
什么是数字电影?
我们需要对全流程数字电影和非全流程数字电影加以区分。从策划到放映,电影的制作过程可被分为以下五个阶段:筹备期,前期拍摄阶段,后期制作阶段,发行期,以及展映期。非全流程的数字电影是指在上述过程中,并非所有阶段全部运用了数字技术,而是仅有其中一个或几个阶段采用了数字流程;而全流程数字电影则贯穿着电影制作的全过程。电影的数字化技术最先被运用于后期制作领域。通常,为了加入特效或动画,要对电影进行数字化处理和操作。作为最早的非全流程数字电影之一,《电子世界争霸战》(1982)利用电脑生成的图像来模拟游戏世界。《侏罗纪公园》(1993)和《阿甘正传》(1994)则让数字特效进一步广为人知。工业光魔公司由乔治·卢卡斯创办,这间公司不仅操刀制作了以上电影中的特效部分,还在很多其他电影的特效制作中大展身手。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数字调色(使用数字工具对电影胶片的色彩进行控制的方式)得到大面积的应用。化学方式的调光配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同时,数字剪辑也逐渐成为标准流程。《玩具总动员》(1995)是第一部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动画长片,该片由皮克斯工作室制作(皮克斯曾是卢卡斯电影公司的计算机研发部门)。我们来看前期制作阶段:在最早使用数字摄影机拍摄并得到大规模发行的电影中,有两部“道格玛95”的早期作品——《白痴》(1995)和《家宴》(1995)。此后,许多独立电影人都选择使用数字设备来进行拍摄。再看发行和放映阶段:1999这个年份不仅见证了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前传1:幽灵的威胁》一片以数字形式在四家影院的大规模上映(虽然该片由传统胶片拍摄,但后期对胶片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还见证了圣丹斯电影节对数字放映机的首次采用(在此之前,数字制作的电影需要通过激光扫描重新转录到传统的赛璐璐上,用胶片来进行商业放映。)再看筹备期:对动态分镜(被制作成动画的分镜头脚本)的使用于20世纪90年代大幅增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了数字全流程的实验电影。最早的全流程数字商业电影则出现在新世纪伊始:如迈克·菲吉斯的《时间密码》(2000),再如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前传2:克隆人的进攻》(2002)。这些影片在实拍时就采用数字拍摄的方式,使得全流程的数字电影更广泛地流行开来。
电影《电子世界争霸战》海报 (1982)

电影《玩具总动员》(1995)
综上,对电影制作和发行的所有阶段均采用数字方式来处理的电影才能算作是全流程数字电影,而实际上,全流程数字电影只有不足十年的历史。但鉴于乔治·卢卡斯、罗伯特·罗德里格兹等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人已经选用了全数字流程,再加上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数字电影的制作与发行成本低于胶片电影。所以说,全流程数字制作很可能在二十年内变为主导的制作模式[1]。全流程数字电影将使电影制作的实践活动加速脱离于好莱坞体系,并使得电影制作与发行日益民主化,尤其是通过互联网渠道。
我们应当如何为这种新型的电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呢?电影是移动影像的媒介。在历史上,移动影像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得以构建。最古老的方式是通过物体来投射阴影到舞台背景上,如传统的爪哇影戏(亦称哇扬戏,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一种木偶戏或真人舞蹈表演)中那样。手工制作的图像也曾被使用,正如埃米尔·雷诺于1892年定期于巴黎放映的电影中那样,移动影像由手工绘制的画面组成,被投影在一块银幕上。而大家最熟悉的则是光化学影像,即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由当时的先锋人物发明和使用的摄影术。再后来,视频影像得到应用,并形成了数字影院。视频可以采用模拟信号或数字信号来呈现画面。模拟图像是可以且仅可以被连续变化的值所表示的图像。无论是通过物体投影、手工绘制、光化学方式产生的图像,还是前数字时代的视频影像,均是由模拟信号生成的图像。与之相反,数字图像由离散的数值定义,通常为整数集(完整的数)。当使用设备对客观对象进行机械记录时,需要对连续的变量进行采样和量化,进而生成信息来构建起这张数字图像。拿物体发出的光波来举例:每秒要对光波进行上千次的采样,每个采样点的振幅都会被记录为一个整数,这些整数集被储存为位图。位图是由画面元素(像素点)所构成的网格,网格中的每一个点都被赋予一个整数值,该整数来自相应像素点所代表的被摄体局部发出的光波,是对光波进行采样后所得到的。这些整数使用二进制数字(比特)进行存储,即逢二进一的整数。网格中的每一个像素点,都存储着数百万个表示颜色的整数中的其中一个:24比特是通用的色彩标准中的一种,即任何一个像素点都可以用2的24次方(超过1670万)种颜色中的任意一种来表示。数字电影就是一种由位图生成移动影像的媒介。
因此,数字图像可以直接用于计算机操作:计算机被设计为处理二进制数字的机器,可以处理位图。而与之相反,模拟信号的图像只有在进行数字化之后,才能经由计算机进行操作。因此,由于可计算性的不同,我们能通过计算机对数字图像进行无限的操作,且不会损失任何画质:对于任何数组来说,都有一种算法,可将其变为另一个数组。被存储为数字的信息在复制的过程中不会遭受损失。与之相反,对于像传统照片这样的模拟图像来说,用计算机操作起来相对会更困难。模拟图像的复制,需要从原始的模拟信号来复制出新的模拟信号,这样就会造成代际损失:通过对一张已有的照片进行拍摄而得到一张新照片,新照片所包含的信息量会少于原始的照片。数字图像中的信息量是固定的(由位图给出),但对于模拟图像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在一个包含连续变量的图像中,很可能存储着无限量的信息。最后,考虑到计算机可以对信息直接进行实时处理,数字电影就可以做到实时互动,而传统的光化学胶片则无法做到这一点。(欲查阅更多关于数字电影和图像技术方面的有效信息,见 McKernan [2005] and Monaco [2000: chapter 7];关于数字动画,见Kerlow [2004])所以说,数字电影与传统的模拟信号、光化学呈像的胶片电影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不同生发出许多哲学层面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我将对其中的四个问题进行思考:数字电影究竟能否被算作一种新的媒介;互动性的本质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数字电影中的实在论是怎样的;以及数字电影归属于单一作者的可能性。数字电影是否能算作一种区别于传统电影的新媒介呢?甚至于,它是否能被称作一种媒介?蒂姆希·宾科力(Timothy Binkley)认为,数字电影压根不是一种媒介。因为数字图像是一种抽象的物体——一张位图,而媒介必须是实物——如绘画的媒介是颜料。所以说,与之相反,“计算机不是一种媒介”(Binkley 1997: 114)。然而,宾科力认为媒介须为实物(或曰为物质)的假说是错误的:文学也是一种媒介,但它由语义结构组成,而非实物。准确地说,一个媒介是一系列对材料加以运用的实践活动,无论材料是符号的还是实体的。所以说,数字图像可以构成一种媒介 (Lopes 2004: 110)。有些学者认为,数字电影并不是一种新的媒介,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媒介,而数字电影只是其中的一种;一种媒介无法包含其他的媒介。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印刷是一种媒介。但也可以说木刻印版、雕刻术、蚀刻术、石印术等等这些都是媒介,而它们又都属于印刷术中的不同种类。由此推论,一种媒介可以包含其他媒介:请容我如此措辞,媒介可以嵌套。又因为数字图像的特殊性,诚如我们在上一节中所讲明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相信,数字电影形成了一种新的媒介,而这种媒介嵌套在更广义的电影媒介之中,与皮影戏、手绘电影(如埃米尔·雷诺的电影)、传统的光化学胶片电影,以及模拟电信号电影这些媒介处于同一层级。这种媒介是怎样区别于其他媒介的呢?根据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的观点,数字图像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图像。他认为,对数字照片的讨论只能通过比喻来加以说明:“虽然一张数字图像可能看起来跟刊载在报纸上的照片没什么差别,但它跟传统照片的区别,实际上就像照片和绘画的区别一般大” (Mitchell 1992: 4)。为了支撑这个论点,他探讨了数字图像的不同特征,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也都有谈到,比如图像中存有固定量的信息,以及对其进行操作的便捷度和速度。他还谈道,“一张数字图像可以由扫描的照片、电脑合成的、特定视角的影像,以及电子‘绘画’来共同组成——将以上部分流畅地融合进一个明显是被整合在一起的整体之中” (Mitchell 1992: 7)。米切尔的论据是准确的,也是重要的。数字图像主要由三种方式生成。第一种是利用机械捕捉技术:这不仅包括(我们通常称之为)摄影术,还包括二维或三维的扫描技术,以及动作捕捉技术,一种将表演者的身体或面部动作记录下来的技术。第二种,我们可以手绘制图,如利用一个编辑图像的工具,像Adobe Photoshop,或是Corel Painter这样的软件,在数字平台上“画”出一幅图像。第三种,我们可以通过运行一系列算法,从而用电脑来合成一幅图像:例如,渲染就是通过某个物体的3D计算机模型来运行一系列定义其透视关系和光影关系的算法,进而通过计算机来生成图像的过程(而这个3D模型,可以通过捕捉技术获得,也可以手工搭建,还可以利用合成技术来获取)。正如米切尔所主张的,这三种技术均可被无缝整合在一起。举例来讲,在影片《指环王》三部曲中(2001,2002,2003),要呈现出咕噜姆这一角色,就要先对演员安迪·瑟金斯(Andy Serkis)进行肢体动作的捕捉,然后以此为基础对数据进行编辑,并进一步通过计算机生成,才能完成咕噜姆的制作:当时,动画师所采用的是传统的关键帧动画制作技术。他们通过关键帧,在计算机所记录的动作上“画出”每一张图像。然后,计算机会将三维的虚拟模型渲染成二维的画面。最终,工作人员再对这些图像进一步加以手工调整(Jackson 2004)。这些技术在影片《金刚》(2005)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金刚》中,动作捕捉技术不仅用以捕捉瑟金斯的肢体动作,还对他的面部表情进行了捕捉(Jackson 2006)。最终得到的成品影像着实天衣无缝,观众完全看不出任何因为多种技术参与制作而留下的人为痕迹。综上,共有三种技术被用来制作数字影像(捕捉,计算机合成,以及手绘),且创作者可以选取每种技术所占的比例,最终得到符合其创作初衷的、天衣无缝的成果。由于这些技术的融合,我们可以将数字影像当作一种混合(或曰融合)的影像——也就是说,它可以由三种彼此不同的技术中的任意一种来生成,且每种技术在图像制作中的重要性会根据具体图像的不同而变化。
数字影像是一种融合影像,这个事实非常重要:它说明数字影像与传统摄影术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并为“从根本上讲,数字电影是一种全新媒介”的论点提供了支撑论据。然而,米切尔由此认为,在严格的界定下,数字图像并不存在。他的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一幅融合图像也可以选择只通过一种生成方式来获取,而非三种全用。比如,可以只用捕捉技术来获取一张数字图像。的确存在这种可能,它与传统照片的获取方式相当类似。其中关键的差别在于,数字摄影机用电子感光元件(一种电荷耦合的器件)取代了传统摄影机中基于光化学反应的胶片;而镜头,光学系统,机械快门[2]等等,则是完全相同的。所以说,数字图像存在,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鉴于数字图像可以由非摄影的方式生成,它又与模拟图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数字电影是一种新的媒介,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新的艺术媒介。电话也曾是一种新的沟通媒介,但它并不是一种艺术媒介。要想成为一种艺术媒介,就必须要成为某种艺术形式的基础。似乎可以这样说:人们可以在此媒介中创造出的艺术效果,在其他媒介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或实现起来过分困难。以这样的标准来评判,数字电影可以算作是一种新的艺术媒介。让我们想想完美的照片真实(Photoreal)渲染动画吧。照片真实级别的渲染动画是指,观众在观看被呈现对象的动画画面时,看不出与其真实照片之间的任何差异(假设真有拍摄这样的照片,并涵盖了动画画面所赋予该物的所有属性)。举例来讲,金刚的动画图像看起来就与真实的金刚照片并无二致(如果动画中展现出的金刚真的存在)。与之相反,传统手绘的卡通金刚则肉眼可见就与真实照片相去甚远(假设金刚存在)。如今,很多数字动画都由照片真实渲染的理想模式所驱动,且多次被成功实现。照片真实渲染的动画是一种艺术成就,它影响着人们在艺术层面对于图像的反应(举例来讲,更加逼真的动画画面可以帮助观众与金刚共情,并更好地被代入到他所处的困境之中)。而照片真实渲染在传统动画中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想象一下,如果一帧一帧地画出能媲美金刚照片的画面,那得有多难!正常情况下根本无法做到。所以说,至少有一个美学方面的差别,将数字电影这一媒介与其他媒介区分开来。这样的特质还有很多,最显著的是涌现在交互性方面的新问题;但它们在特效领域也会出现,而不仅有赖于动画。综上所述,数字电影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媒介,还是一种新的艺术媒介。计算机可对信息进行实时处理,由此,数字电影便具备了交互性。大部分数字电影的确有这样的潜力。这一观点乍听上去很惊人,但以移动影像的概念来看,由数字图像所组成的视频游戏也属于数字电影的一部分,如大型多人在线的角色扮演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再如基于虚拟世界的电影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以及真人实景交互电影如《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I’m Your Man 1992);还有加入了数字互动元素的戏剧,比如《表象》( Façade 2005)。本文第一节中所讲到的数字电影简史仅限于非互动的数字电影;但有趣的是,互动电影的历史实际上要更久远:最早的视频游戏诞生于1962年,也有人认为是1958年 (Poole 2004: 15)。但就画质而言,早期的视频游戏远不及非互动的数字电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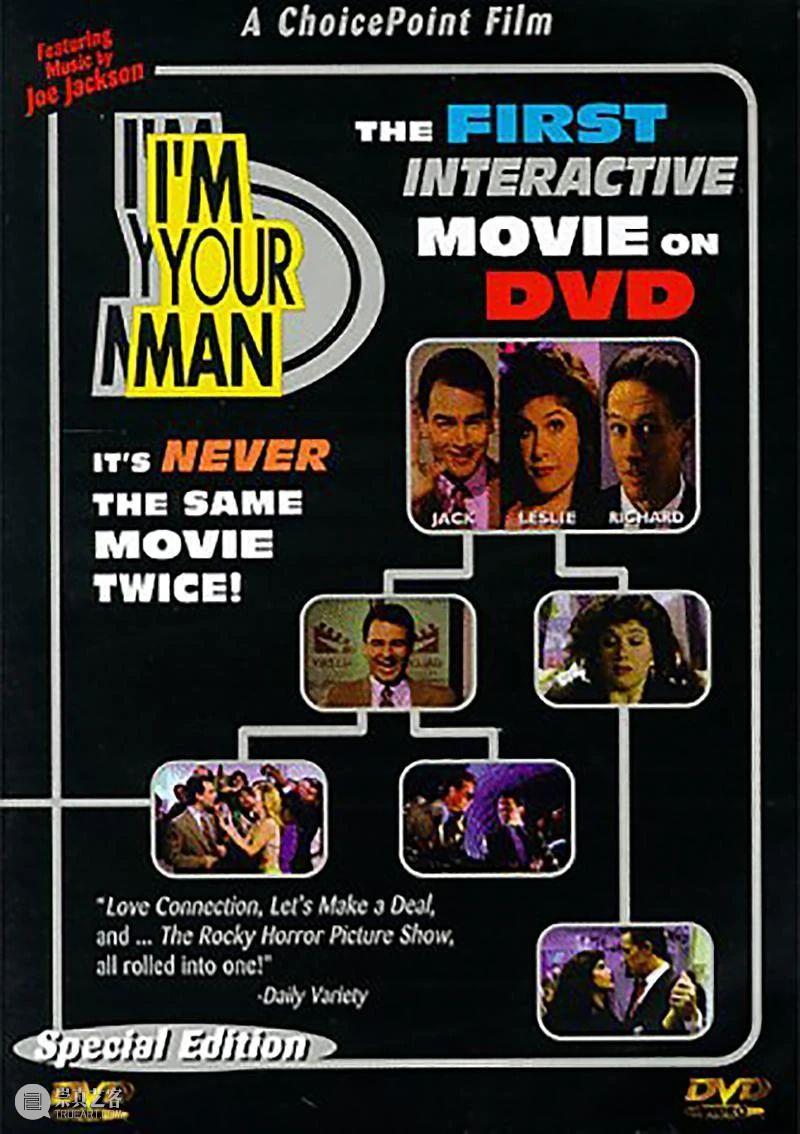
电影《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海报(1992)
对互动性进行哲学辨析的工作少有展开;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将关注点聚焦在对“互动性”的定义上,也有一些研究谈到了互动性对观众代入感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议题是对弱互动性和强互动性作品的区分。DVD播放时会出现章节选择的界面,观者可自行选择他要观看哪些章节,以怎样的顺序观看。相比于影院观众,DVD观众在观影中拥有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作品的结构依然独立存在于观众的观影活动之外:这样的作品被称为弱互动性,就像桌上放着书本内容,并配合有该书的索引卡,其与传统作品并无本质差别(虽然Rafferty [2003]认为,即使是这种形式的互动,依然威胁到了电影的完整性,因为它将控制权从导演那里转移给了观众)。与之相反,在强互动性的作品中,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作品结构上的属性由观众自身的选择来决定:互动电影展现给观众的画面和声音,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观众自身的选择,至于这些声音和画面最终如何被展现出来,并没有一套权威的规则。强互动性与弱互动性不同,它在本质上属于一个新的类别。这是因为,具有互动性的作品由一系列有信息源的规则所指定:具体说,就是由计算机软件,即算法来决定相关规则,只要互动主体输入他的选择,即给出特定的输入,便可确定其输出结果(Lopes 2001; see Saltz 1997)。就观众与作品的互动关系而言,强互动性作品与传统作品是相当不同的。从字面意思来看,对于互动性作品,建构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银幕上的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观者的选择,所以观者就是她所看到的影像的部分作者(虽然由一系列算法所决定的作品本身独立于观者的选择而存在)。再者,对于发生在银幕上的事情,传统作品的观众被置于一种默默沉思的位置之上,而互动作品的观众则通常抱着务实的态度,因为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将要如何(假扮角色去)行动。特别是,与非互动作品所提供的那些适度的情绪体验相比,互动中的观众能将其触角伸到更大的范围中去,感受到更为丰富和强烈的情绪: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在视频游戏中进行角色扮演,使其产生内疚感就很有意义 (Tavinor 2005)。虽然洛佩斯(Lopes)对此表示反对,但互动中的观众真的好似音乐剧和戏剧演出中的演员一般:正如演员们在以作品为边界的可允许范围内,不得不做出特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所呈现的表演;互动者也一样,他们在以作品为边界的规则中做出一些特定的选择,这些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与作品会产生怎样的互动(即他们的所见所闻)。在实在论这个问题上,数字电影与传统电影是否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无法被简单地回答,因为实在论的内涵本身就具有多面性。“实在论”有一种涵义,在于其透明性(transparency):以肯德尔·L·沃尔顿(Kendall L. Walton)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认为,摄影术是透明的。意指当我们看到照片时,就如同我们实际上看到了被摄体。当我们观看祖先的照片时,简直如同看到了其真人。这个观点很普遍:对所有照片来说都是如此,包括传统照片和数字照片。然而,在沃尔顿维护摄影术的透明性学说时,有一个关键点极为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摄影师无法通过自身的意图来改变照片中的某些特性,因为这些特性由其被摄主体的特性所决定。与之相反,非摄影图像则是以艺术家对其表现主体的理念为中介的:有鉴于此,沃尔顿认为(除了少数通过机械方式完成的绘画以外),手绘图像并不具备透明性(Walton 1984)。所以,从这一观点来看,非摄影数字图像是不透明的。考虑到融合影像在数字电影中的普遍存在,沃尔顿的观点就等于说,数字电影在一些情况下是透明的,而另外一些时候则是不透明的。而在同一张图像中,可能存在一些方面是透明的,而另一些方面则是不透明的。数字影像也许看起来是透明的,即使它们实际上是不透明的。与之不同,洛佩斯提出,不仅照片如此,对实际事物的手绘图像亦是如此 (Lopes 1996: chapter 9)。这种说法有利于将数字影像透明性的相关阐释统一起来。对于实际存在的物体而言,不论是否用摄影术来呈现,都伴有沃尔顿观点所引发的问题,进而使其自身走向反直觉的倾向。另一种可替代的解释也能保证阐释的统一性,但这种观点认为,不论是否通过摄影术来获得,所有的图像均为非透明的;这个观点的优势在于,既统一了对图像透明性的阐释,又避免了如洛佩斯所谈到的那种违背直觉的后果(Gaut forthcoming: chapter 2)。 对实在论的另一种意向在于本体论的实在论(ontological realism):这种观点从摄影术的存在谈起,讲到其被摄物的存在。照片与被摄主体之间呈因果联系;而手绘图像与被描绘物之间则存在一种意向性的关联。从获取一个因果联系的角度来讲,照片的被摄物在照片被拍摄的过程中是存在的:没有人能实拍到一个不存在的对象,比如金刚。从获取一种意图性关联的角度来讲,被表现的主体并不一定存在于图像被制造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创造出一张描绘金刚的画作。所以无论是传统照片,还是数字照片,摄影术都只能拍摄实际存在之物。(一部传统的动画电影是对现实存在的动画逐帧绘画进行摄影;真人实景拍摄的虚构电影则是对人进行摄影,如装扮为角色并让观众信以为真的演员;在上述两种情况中,观众也可以假装这些图像是对虚构之物的展现。)相比之下,通过非摄影术所得到的数字影像,或是数字图像中非摄影的部分,则可以展现虚构之物。所以说,传统的电影从本体论角度来讲是具有实在性的,而数字电影则不全是。(请注意这些特性仅能表明被摄物曾经存在过,而非被摄物拥有那些表面看上去所具备的特性:无论在传统电影还是在数字电影中,都充斥着大量对画面的人为操纵。)用皮尔斯(Peirce)的术语来说,传统电影影像可被称为一种指称(index,与其所指有一种因果关系),而许多数字图像则仅仅是图标(icon,虽看上去与其所表现的事物相似,但二者缺乏因果联系) (Prince 1996)。 实在论的第三种涵义是感知实在论(perceptual realism),指一个实在的描绘看起来就像其所描绘的对象本身。众所周知,很难对感知实在论进行精准的表述,但有种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照片与其描绘对象占有相似的视觉特性。正是这些视觉特性引发了我们对被描绘之物的识别能力。一张描绘马儿的图像与一匹马相似,它们均可激发我们在视觉上对马进行识别的能力。之所以说照片更具实在性,是因为照片以实在的方式呈现着更多的视觉特性(Currie 1996: chapter 3)。这个观点为论证特定的电影制作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具实在性打下了基础。雷诺阿的深焦、长镜头风格比爱森斯坦的蒙太奇风格更具实在性,因为观看深焦风格的电影与观看蒙太奇风格的电影相比,深焦风格跟我们日常对被摄物的观看方式更为相似。以这种对于实在论的解释为标准,可知数字电影对于实在性的传达能力要强于传统电影。例如,与传统胶片相比,数字电影可以将镜头时长拉长很多,而胶片的镜头长度则只能受限于15分钟,因为胶片摄影机内所能容纳下的一卷胶片只能记录15分钟的影像。数字电影可做一镜到底的尝试,单镜头长度即为全片片长,达到了一个半小时:如菲吉斯的《时间密码》(Figgis’ Timecode),亚历山大·索科洛夫的《俄罗斯方舟》(Alexander Sokurov’s Russian Ark 2002)。
实在论的第四种涵义是错觉论。有些学者认为,电影观众处于错觉之中,即经由这样或那样的虚假信念,观众好像已然设身处地于影片的情境之中。几乎所有类似的观点都能直截了当地被证伪:举例来讲,如若观众相信她真的身处于恐怖片中的情境里,面对着狼吞虎咽的怪物,她就应当逃离电影院,而不是满意地大嚼爆米花。然而,数字电影的观众也许会被带到传统电影通常未涉及的错觉情境之中,比如说,观众也许会认为她看到演员在实景中行走,而实际上,其中的场景是纯数字搭建的。再如,观众也许认为她看到了演员在行走,而实际上她看到的只是纯数字角色:拿《指环王》和《金刚》来举例,在影片的制作过程中,数次利用“数字替身”来完成一些对于演员来讲过于危险的戏份。无论观众观察得多么细致,还是无法分辨出数字替身在片中的足迹,尤其是出现在远景镜头中的人物。与传统电影相比,用数字方式来对人物和场景进行创建与操纵,将数字电影对错觉的作用领域推向了新的广度。
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过第五种对“实在论”的阐释,那就是照片真实(Rhotorealism)。与传统胶片电影不同,数字电影相对而言能够更为容易地实现这种极致的真实感。只有当一幅动画图像看起来像一个实际物体的照片一样真实时,才能被认为达到了照片真实。数字动画利用动态模糊和镜头眩光等特点,使得其图像看起来以假乱真:这里的标准并非要让图像看起来如同真实生活中的物体一般,动态模糊和镜头眩光只是摄影机所造成的技术瑕疵,并不是我们人眼在观察一个场景时会看到的东西。准确地说,照片真实的概念是一种派生物:它将照片当作真实性的标准,并力图使动画图像看起来如同照片一样。传统的手绘动画也能达到照片级别的真实感,但正如前所述,这虽在理论上有可能,但实际操作起来几乎完全不可能实现。在数字电影中,对幻想和特效进行超写实呈现的最主要方式,就是照片真实级别的动画制作。最后,还有一种对实在论的阐释,我们称之为认知实在论(epistemic realism):如果一幅图像能提供强有力的(即使是可被作废的)证据来证明它明显描绘了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就符合认知实在论。在传统的方式中,照片作为证据,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威:对于某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们更相信一张照片的证明,而不是绘画作品,无论该画作将场景呈现得多么真实可信、细致入微。一部传统的电影可以为“某些特定演员在过去某个时间在某个特定的地点”这一事实提供有力证据。但数字影像经过过多的操纵,导致“它的描绘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很可能已被置于系统性的无解之中,比如,通过对模型进行数字操纵,就可以让它们看起来更吸引人。正如芭芭拉·塞维道夫(Barbara Savedoff)所说,数字照片的兴起,为通常所说的“对照片可信度的摧毁”雪上加霜(Savedoff 1997:212)。显而易见,广义的数字影像对于某事是否发生过丝毫不能提供任何证据(如金刚从帝国大厦上坠落)。照片真实渲染的可实现性让这个问题更为严峻:我们用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出眼前的影像究竟是动画中纯数字生成的一帧画面,还是对被摄体拍摄的一张照片。因此,数字电影与传统胶片电影相比较而言,有着更强的能力去制造更具真实感的视觉影像。然而讽刺之处在于,当观者开始了解数字电影中的可能性,他们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去怀疑看似可信的一切,怀疑画面中的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实在论中,数字电影只能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见多识广的观众愈发戒备起来,在对数字影像能否成为权威佐证的质疑中,观众将评判的结果悬置起来。对于数字电影,是否可能存在唯一的作者呢?更温和的问法是,相较于胶片电影而言,导演是否在数字电影中进一步扩大了其控制力?有一些导演会这样认为,比如罗伯特·罗德里格兹就曾这样描述数字电影,“它的速度和力量简直让你觉得,画笔就在你的手中”(Waters 2005: 16)。技术方面的成果似乎支持着这一观点。正如我们所见,融合影像提升了电影人操纵画面的能力。在制作咕噜姆和金刚这两个角色时,对于角色的行动呈现来说,动作捕捉、动作编辑,以及关键帧动画等协同制作方式与演员相比,得到了更大的控制权。因为演员的表演只有一些方面被有选择地整合进了角色的动作中。然而,即使电影主创对影像的集体控制力得到了加强,并不意味着相对于其他主创而言,导演的控制力得到了提升。恰恰相反,即使是简单扫一眼绝大多数数字电影的片尾字幕,我们也会发现,参与工作的演职人员数目大幅增多。这并不意外,毕竟要考虑到数字电影制作在技术和艺术两方面,均对任务分工和团队配合有着天然的需求。目前,数字电影比传统电影需要更多的协作。而且,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曾表述的观点,只要还有一个导演之外的演员,传统电影在本质上就是集体创作,因而单一的作者身份就不存在。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演员是表现角色的中介,所以导演并不处于如小说作者那样的位置上。并不是导演单独创造了角色,导演必须要依赖对其他演员动作表演的数据记录才能塑造角色(Gaut 1997;关于支持单一作者身份归属的最佳辩护,见Livingston 1997)。也许会有人认为,数字电影带来更多合作的这一事实,仅仅由当前技术现状所致。随着技术的进步,终有一天可以实现导演一人独揽所有的数字化表演。也许真会这样,但我们不可能准确地预测技术发展的路径。那么我们假设技术的发展使得导演可以独自更改数字影像的所有特性,而导演也真会自己去更改每一项参数。那么,如果演员的贡献依然在成品中可见,则该片仍不能算作由单一作者完成,因为其中至少有两个表意中介。再看另外一种可能性,当大量的修改导致成片中已然看不到演员所留下的痕迹时,此片也就与纯动画电影并无二致。不容置疑,动画电影可以拥有唯一的作者。所以说,这样的数字电影可以拥有唯一的作者,但这是由于演员在表意贡献方面的缺席所致,同动画电影的唯一作者归属是同一种情况。数字电影为表演方面的合作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如今,我们可以将演员的角色进行分解:瑟金斯的声音、肢体动作,以及面部表情均被编入金刚这一角色。而瑟金斯的其他方面,比如他的外形外貌,则未被展现。而从实际情况来看,金刚这一角色的表演,是由集体创作达成的。动作捕捉的素材会经过后期编辑,在此过程中,我们会对瑟金斯的表演进行部分修改——一位动作编辑师谈到对金刚的“表演修正”以及“保持眼中的张力”(Jackson 2006)。由于当时的面部捕捉技术无法精确记录微妙的面部表情,而且在一些场景中,真人演员也无法演出金刚的动作,所以关键帧动画师为表演加入了更多细节,尤其是面部细节。所以,这里又要再次说明,数字电影相较于传统电影,具有显著的差别,但并不在于其对单一作者身份的加强,而在于其对电影集体创作的拓展。(本文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文献翻译与研究”课程成果,翻译版权归译者所有,此为初译稿,纸媒尚未发表,欢迎交流。)
[1]本书首次出版时间为2009年。此处为作者于成稿时做出的预测。
[2]对于胶片摄影机和数字摄影机来说,快门的机械构造多是不同的。胶片摄影机为叶子板机械快门,数字摄影机则绝大多数为全局快门或卷帘快门。只有极个别的机型沿用机械快门的设计。此处存在技术细节方面的偏差。影像艺术文献相关链接:
影像艺术文献 | 比尔·维奥拉:作为艺术的录像
影像艺术文献 | 布鲁斯·瑙曼:你自己的中心
影像艺术文献 | 电视、家具和雕塑:美国视角下的房间
影像艺术文献 | 肯特里奇:把太阳还给我们
影像艺术文献 | 克里斯蒂安·麦克雷对话迈克尔·斯诺
影像艺术文献 | 比尔·维奥拉:黑暗视频 ——影像的死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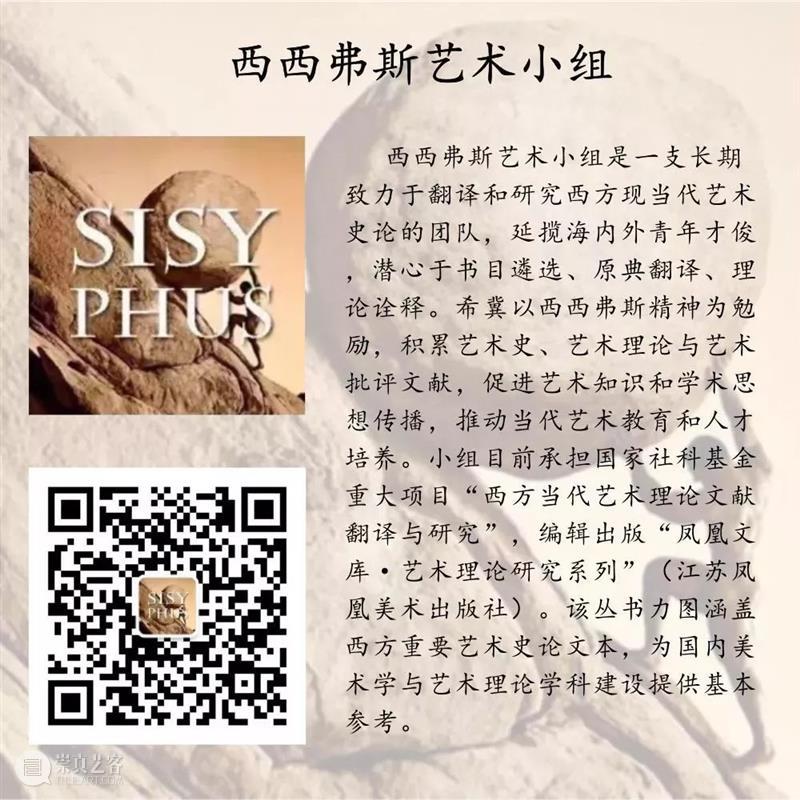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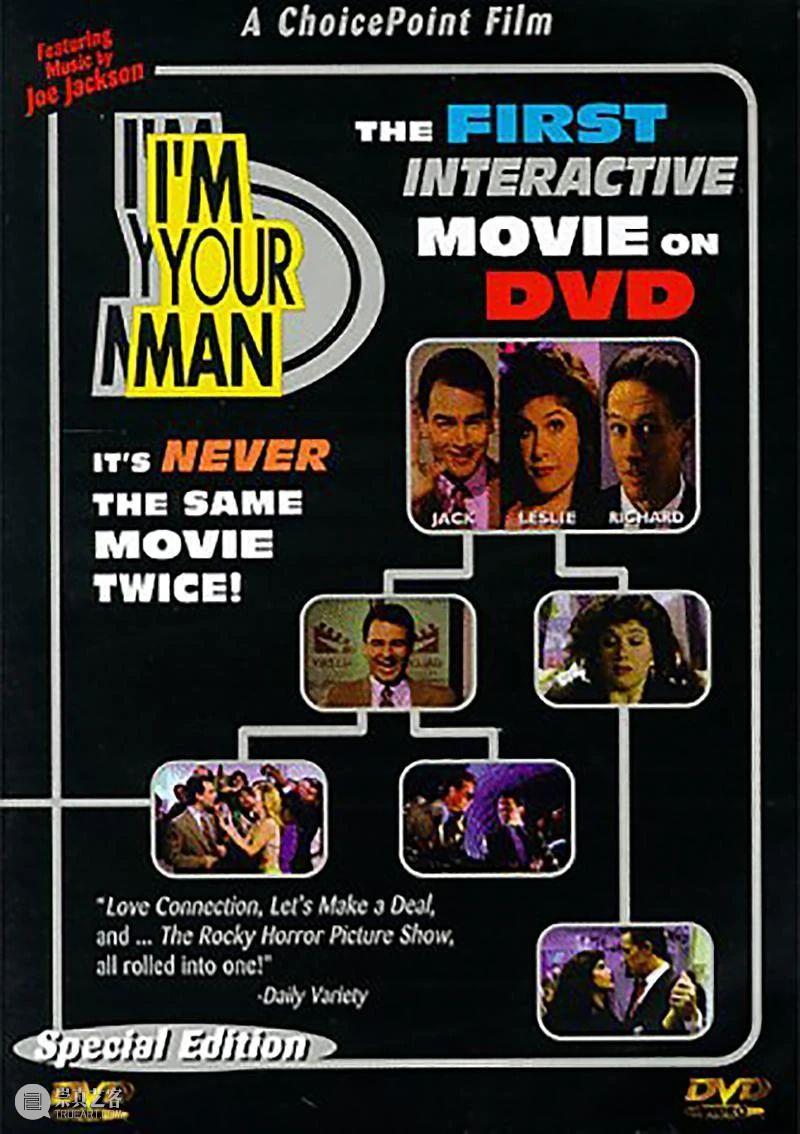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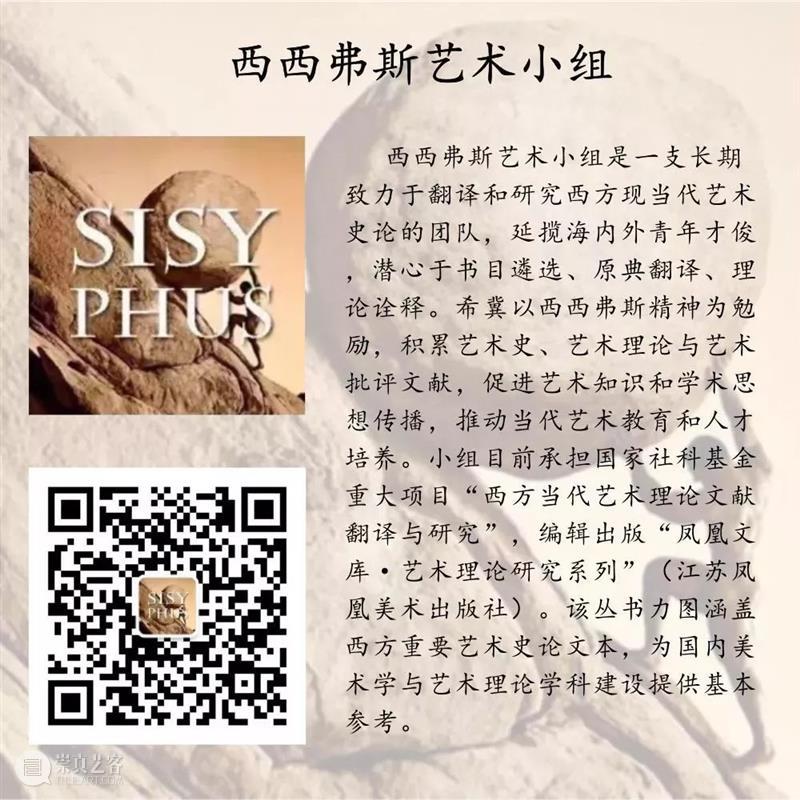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