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年与死亡
加雷斯·B·马修斯著,刘晓东译
选自《童年哲学》,三联书店,2015年。
有两部现代儿童文学经典之作直接谈论死亡,许多成人了解后极为惊诧。之所以惊诧,是因为他们深深感到与儿童谈论死亡,这个主意本身是极为不妥的。E.B.怀特(E.B.White)所著《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以及娜塔利•巴比特(Natalie Babbitt)所著《塔克一家长生不老》(Tuck Everlasting)不仅是儿童真正喜欢的好书,而且还是试图严肃谈论“人必有死”这一常识的书。
《塔克一家长生不老》是一部富有哲理的探险故事。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再配以一气呵成、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文学特色,最终让女主角温妮(Winnie)相信:有着生老病死的凡人生活远远胜过滞留在十岁或十七岁或四十二岁的那种长生不老的生活。
十岁的温妮•福斯特正从她家树林里那眼泉水接水喝,突然被梅、塔克及其两个儿子劫走了。塔克家的人后来向温妮解释,他们全家人——爸爸、妈妈和俩儿子——在八十七年前喝过那泉水。结果他们都不再变老了。“如果你今天喝了,”梅告诉温妮,“你会永远滞留在小女孩的状态,再也无法长大。”
塔克这家人说,他们无法融入周围社会,甚至不能在某个地方久待。正如梅所说:“人家会觉得我们稀奇古怪。”更根本的是,塔克这家人就是难以融入这个世界。在夏天的某个晚上,乘着小船,梅的丈夫塔克想做些解释。他说:“每件事物都像轮子,转呀转呀转个不停。青蛙是轮子的一部分,虫、鱼、画眉鸟也是,人也一样,可是永远不会保持不变。一直会更新,一直会生长、变化,一直会变动不居。事情本该如此,其实也是如此。”这时小船搁浅了,塔克先生便以此类推:
这不,小船现在搁浅了。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挪走小船,小船就会永远停在这里,想挣脱但动弹不得。温妮,我们塔克一家就处在类似境地。搁浅了,动不得了。我们不再是轮子的一部分。温妮,我们被落下了,被甩在后面了。可在我们周围的所有地方,事物都在运动、生长、变化。
温妮一度破口而出:“我不想死。”塔克回答:
现在你不会死,还没到你死的时候。可死是轮子的一部分,死紧挨着生。你无法只拣你喜欢的部分,其余全丢掉。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这是福分。可它却离我们、离我们塔克一家远去了。活着是不容易,可脱身走到另一边,走到“我们"这一边,也没劲。真没意思。假如我能知道怎么爬上轮子,我会立马爬上去。没有死,就没有生。所以你不能称这就是活着,不能称我们现在是活着的。我们只是像路边的石块,我们只“在场”。
《塔克一家长生不老》逐步将读者(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推向这一结论:一切生命(包括正在活着的生命)都有一个起点、中点和终点。当故事的女主角面临如下选择,是永远留在童年还是过常态的生活时,她最终选择了必有一死的常态生活。读者无论是九岁还是八十九岁,很可能赞同这一选择;如果不赞同这一选择,至少可以理解这一选择。
学校的教师和图书管理员报告说,孩子们都非常喜欢这本书。无疑,对于许多成人,尤其是那些无法直面自己难免要死的人来说,你要是告诉他们儿童读物应当直面这一话题,或者,他们能在阅读这类书中受益,那么,他们会产生反感。这就是他们的错了。其实,我曾听到一所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证明,让父母与孩子在公开场合讨论该书是不无价值的。这位图书管理员组织了“最佳儿童读物”读书会,《塔克一家长生不老》就是“最佳儿童读物”之一。相互讨论这部作品时,儿童放得开,想得深。他们尤其好奇父母对该书有何反应。由于死亡话题在家里从未提及,所以他们不知道父母对这个话题会说些什么。讨论会促使父母们向自己的孩子发表他们对死亡的看法。尤其是在对如此睿智的故事发表自己看法的时候,父母们表达了自己对死亡的畏惧和焦虑。对于有机会就此话题在孩子们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父母们在讨论会的最后表达了感激之情。
与《塔克一家长生不老》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夏洛的网》流行之广、影响之巨更是令人吃惊。这是因为这本书里有不少段落与下面这段类似:
他一想到死,就开始战栗。
“夏洛,听见了吗?”他轻轻地说。
“威伯,什么事?"
“我不想死。"
“你当然不想死。”夏洛轻声抚慰他。
无可否认,威伯只是一头猪,而夏洛只是一只蜘蛛。可是,人们读到这里毫无疑问会认同这些角色很像人。故事发生的背景设在谷仓外面的院子,角色不只是动物,而是会说话的动物,这就多多少少让我们与“人必有死”的话题,至少是“真实世界”里“人必有死”的话题,拉远了距离。毕竟,这是关于一只会说话的猪难免一死的话题,这是关于一只会说话的蜘蛛难免一死的话题。
虽然如此,角色尽管与“真实生活”有一点点隔膜,但也并不遥远。它们对自己处境的谈论,让人感同身受,让人感觉这与人类的生与死几乎无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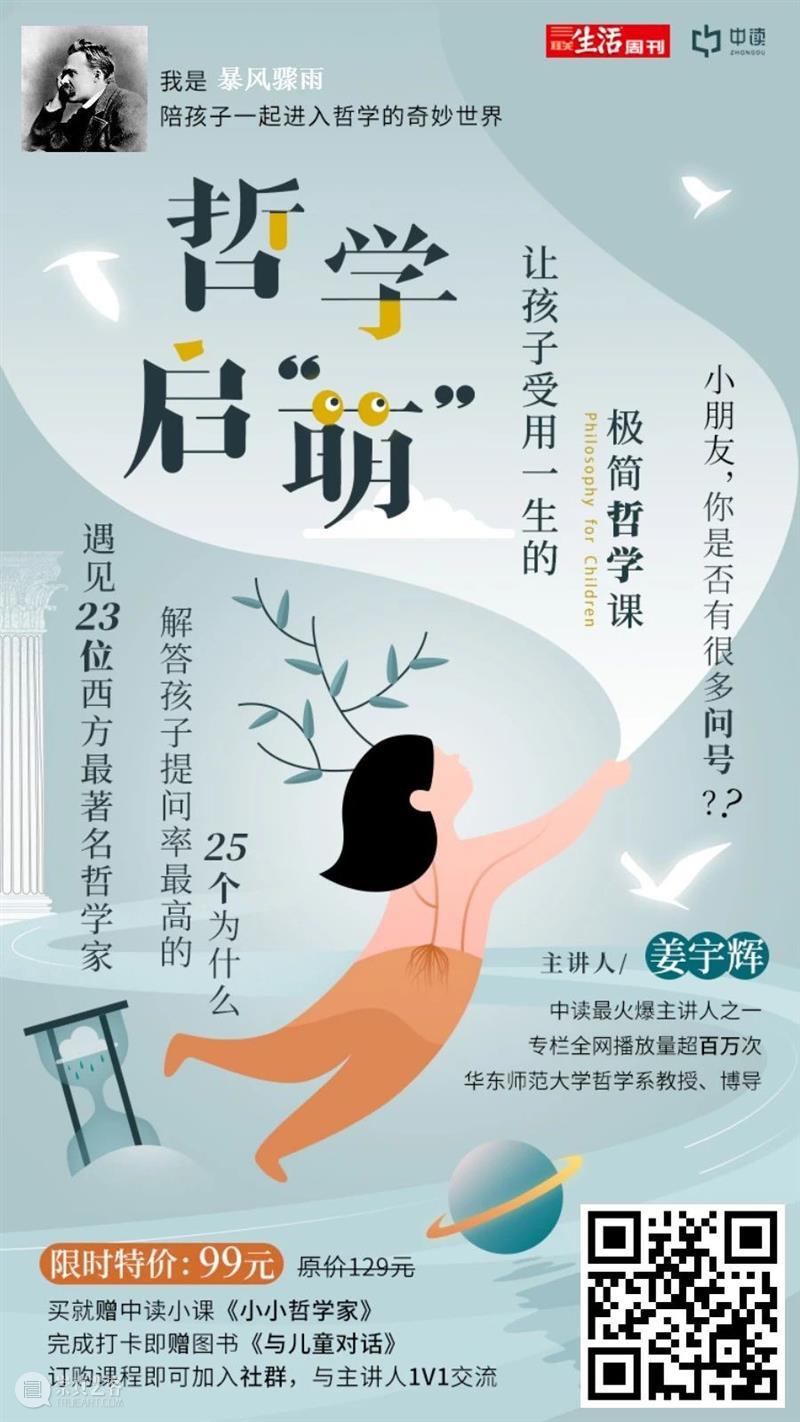
在长大成人以前,我们大部分人都曾说过或听过极类似于威伯所说的话。我还记得在我读研究生期间,我的朋友、柏林来的交换生克劳斯告诉我,深更半夜里,他被我们俩都认识的一个学数学的印度研究生仙提叫醒。
“什么事呀?”克劳斯问,他正挣扎着清醒起来。
“我不想死。”仙提说。
克劳斯曾是“二战”时随德国军队驻苏联前线的卫生兵。我亲耳听过,他将自己的战争经历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公爵参加前线战争的经历,做过绘声絵色的对比Q那时他自己头脑中就多次闪现过仙提的这一想法。
“你当然不想死。”他对仙提说。
在《夏洛的网》中,夏洛所做的可不只是安慰她的朋友威伯。她在自己的蜘蛛网上写下赞美威伯的话,这就让威伯变成了一只出名的猪,从而免遭屠宰。E.B.怀特让这篇故事的读者明白,作家有时确有本事让其笔下的人物比其作者活得更长久。夏洛一开始就知道,她自己注定要在夏末死去。这一动人的讽喻手法将故事的悲剧色彩凸显出来。她气力将尽,所能做的最后的努力,就是生产一个大袋子装卵,这是她拥有来世生命的唯一希望。
在那些未经历过疾病或死亡威胁的儿童中间,《夏洛的网》大受欢迎。可在那些濒于死亡而与疾病作斗争的儿童生活里,该书也享有特殊的位置。这正如米拉•布鲁邦德-朗格(Myra Bluebond-Langner)在其研究白血病儿童的开拓性著作《临终儿童的私密世界》(The Private Worlds of Dying Children)中所写的:
这帮儿童最喜欢的书是《夏洛的网》。当玛丽和杰弗里到了第五阶段(完全了解到自己的病情),这是他们唯一想读的书。处于第五阶段的几个儿童在临终时让人将其中的几章读给他们听。可正如一位家长所说:“他们从来不挑欢快的章节他们总挑夏洛将死那章。这些孩子(在小儿科肿瘤病房)去世后,这本书在余下的孩子们中间又流行起来。
在近期出版的一本论文集《儿童与保健:道德与社会问题》里,两位哲学家罗莎琳德-艾克曼•莱德(Rosalind EkmanLadd)与洛雷塔•科培尔曼(Loretta M. Kopelman)就《夏洛的网》之所以在临终的白血病儿童中如此流行的原因,以及他们从中会得到怎样的信息这两个问题做了探究。根据莱德所言:“整本书所表达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然的便是善的;自然的、与自然一致的死亡是善的死亡,是可接受的死亡;但是,不自然的死亡是恶的死亡,是应当对其抗争的死亡。”以此而论,威伯还是一只嫩嫩的小猪时所面临的首次死亡威胁以及稍后所面临的被屠宰以做成肉食品的死亡威胁都是恶的、应当抗争的。而夏洛正常地过完一辈子后,她的死是善终,是可以接受的。莱德试图以此说明夏洛的死是善终:
她知道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她为此做了盘算,产了卵,告诉朋友去日无多,并向他们告别。她的先见之明和及早安排,让浓浓的平和安宁将其死亡笼罩。尽管蜘蛛一生的长短是个定数,难以改变,可夏洛依然能够对自己的死法做些选择。她的第一个选择是与威伯一道赶集,尽管这意味着,她可能死在外头而不是在家里寿终正寝。其次,她选择用最后的日子在自己的网上编织文字来帮助威伯。
莱德指出,家人和医护人员会帮助儿童做些选择,这会让他们的死更接近于夏洛的“善终”模式。可是,临终儿童或罹患致命疾病的儿童会从不同渠道获知,儿童的死根本就不是自然的。
洛雷塔•科培尔曼在与莱德进行商榷时,将《夏洛的网》看作对恶的问题的回应。(“如果造物主是善的,是全能的,那么,为什么会让无辜者受苦受难并早夭?”)她将怀特这本书对“恶的问题”的回应与柏拉图的回应做了对比:
柏拉图和怀特对世界上的苦难与邪恶的描绘似乎不同。对柏拉图来説,无关道德的痛苦、早夭、损毁等邪恶是无法从世界清除的,这是因为它们是世界的一部分。人无法让无序的世界完全适合于善与正义的真实概念。这不能怨谁,这是有限界的必然特征。但是,怀特《夏洛的网》所描绘的是,不仅世界是如其所能的善(柏拉图会同意这一观点),而且,从正义的角度来看时,恶有其目的,否则会如梦幻泡影般消失。生命本身就是胜利、奇迹和荣耀。
为了支持她的理解,科培尔曼引用了《夏洛的网》倒数第二段:
在威伯余生的那些日子,朱克曼先生对他精心照顾。经常有朋友和仰慕者来看望威伯,谁又会忘记威伯的胜利和(夏洛)蛛网上的奇迹呢?谷仓里的生活很不错——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冬天还是夏天,春天还是秋天,不论是雾霾密布的阴天还是阳光明媚的晴天,谷仓里的生活都是一样美。威伯想,这真是能待的最好的地方了,这温馨的仓底,有鹅嘎嘎不休,还有季节变换,有太阳送暖,有燕子去来,有老鼠为邻,有绵羊相似得难辨彼此,有蜘蛛们相亲相爱,有农家肥气味飘荡,一切都是喜气洋洋。
儿童将死,这是一种特殊的恶。对这种特殊的恶有两种反应,科培尔曼对这两种反应做了对比:
柏拉图认为,自然会被“玷污”,苦痛与折磨只是有限界的病态特征。儿童患病和受罪是自然里有“一只黑手在捣鬼怀特所认为的另一种观点可以解释,面临死亡的儿童为何会发现《夏洛的网》有抚慰作用。这本故事书表达了恐惧,但也向我们保证:一切都是尽其可能的善;它解释说,邪恶与苦难是必需的,死亡没有苦痛,那必死者(威伯)会得到拯救。人“绝对不会没有朋友”,所以他不会遭到抛弃。这临终之人(夏洛)善良又智慧,是人们关心关注的焦点。她作为善良友人和成功人士会受到永远的爱戴与缅怀。生命会得到重生并世代相续:“每年春天里都会有蜘蛛宝宝诞生。”
我怀疑并不会有许多父母或医护人员会跟儿童严肃讨论恶的问题。因而他们可阅读一些故事书,以故事的形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至少是回应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这种做法是不会有错的。
有人肯定会持不同的意见。这些人会说,所有这些讨论都情绪化地过度诠释了幼小儿童的能力与反应。这些持异见的人会坚持说,发展心理学家已经揭示幼小儿童没有能力充分认识死亡概念。因此,罹患致命疾病的有效儿童难以理解他们所面对的威胁,也难以将致命疾病看成恶这一问题的呈现而加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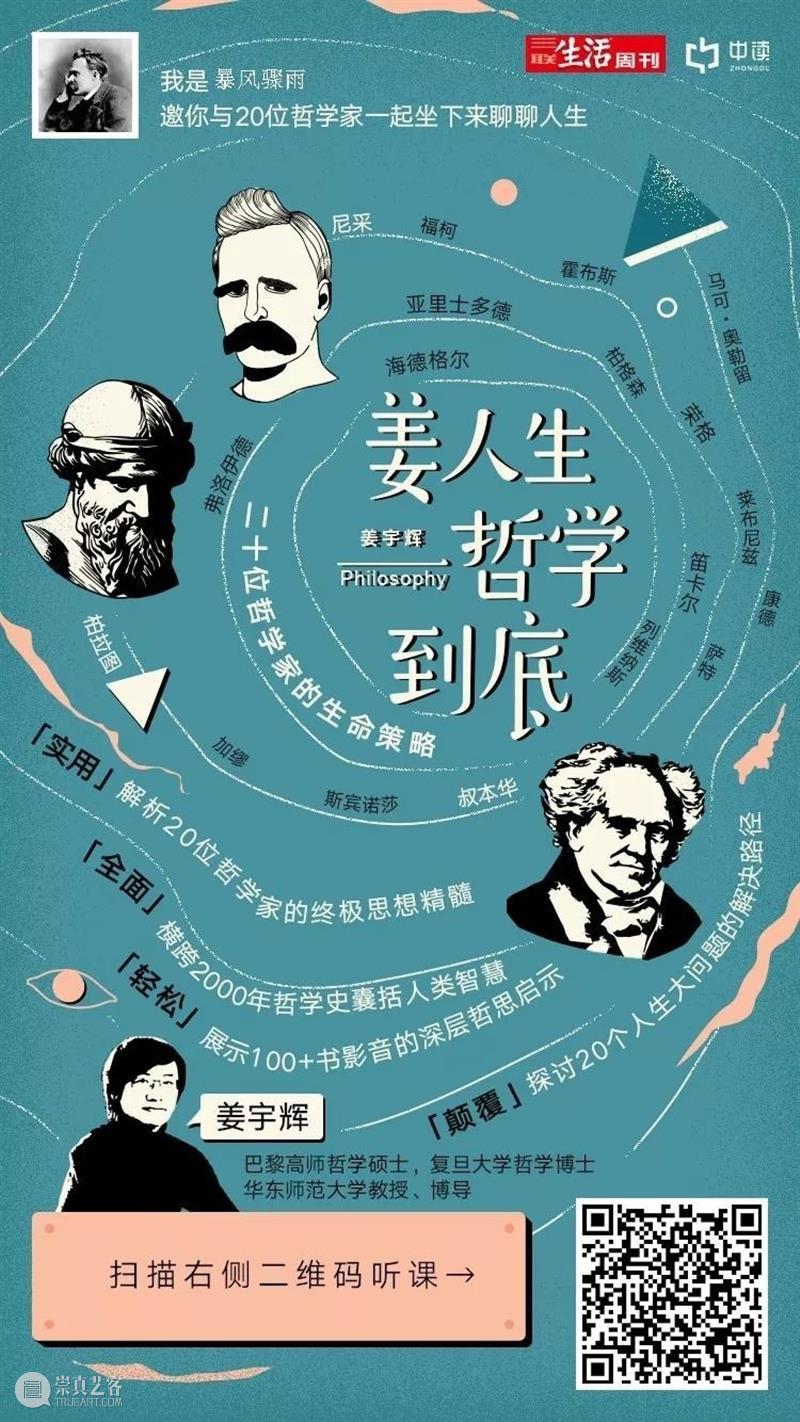
苏珊-凯利(Susan Carey)在其《童年概念的变易》中报告:“有关儿童对死亡的理解.这方面的临床研究文献是十分丰富的”,所有作者“一致认为儿童对死亡的理解经历三个时期”。对儿童理解死亡的发展阶段的研究文献,凯利做了综述。其中,儿童对死亡理解的第一阶段是这样的:
第一阶段以五岁及其以下的儿童最为典型,死亡概念与睡眠、离别相似。死亡对情绪的影响,来自于儿童的以下看法:死亡是悲伤的别离,也可能是最大的攻击行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在此阶段,死亡不会被视为无可更改或者无以避免的。就像人从睡眠中醒来或旅途归来,所以人能死而复生。尽管儿童将死亡与合上眼睛与身体不动联系起来,就像睡着一样,但是,他们不能领会死亡是身体各种功能的完全终止。他们也不理解死亡的起因。尽管他们能提及疾病或事故,但很明显,他们难以想象疾病或事故导致死亡的机制。
她对下一阶段的综述是这样的:
儿童理解死亡的第二阶段(小学低年级)正处于过渡状态,不同的研究给出不同的特征。所有作者都认为,儿童这时将死亡理解为最终的结局,他们也能理解死人不再生存的含义。然而,儿童依然将死亡视为由外部行为者引起……儿童还不能将死亡理解成这些外部事件在身体内部所引发的结果。
以下是第三阶段:
在最后一个阶段,死亡被视为一个必然的生物学过程。这样的死亡观大约在九岁或十岁首次明确起来……当问及死亡的原因,一位非常聪明的十二岁儿童答道:“当心跳停止、学业停止循环,人就会停止呼吸,这就是死……对的,有许多情况会引发死亡,可并非真的就一定死亡。”
儿童对死亡的理解是分阶段的。无疑,人们会对这一主张提出各种各样的诘难。如果这一主张是大致正确的,那么,我们便没有正当理由与幼小儿童——比方说九岁以下的儿童——讨论死亡,更不用说讨论儿童的死是恶问题的展示了。这是因为比较年幼的儿童还不理解死是最后的终结。
在对几乎所有病人(包括儿童患者)的治疗方面,有一套涉及病情告知的伦理议题。医生应当将诊断和预后告诉病人多少?儿童如何获得一个适切的死亡概念,对此问题所做的标准的发展理论解释(the standard developmental account)向我们提示,对于遭遇危及生命的事故或疾病的第一、第二阶段的儿童来说,病情告知根本就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于这些病人对死亡只有原始的理解,因此,对危及生命的事故和疾病引发的威胁,他们的认识是有缺陷的,所以他们无法处在认知的立场上评估所告知的病情。或许医疗团队需要以处理成人恐惧症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儿童的恐惧;可是这些病人在认知上显然没有能力来理解所告知的真实病情。
这就引出一个相关的问题——决策。一个受重伤或得重病的儿童在事关治疗的决定上(如果需要儿童参与决策的话)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尽管同意治疗对于儿童患者来说不是法定的必要条件,可是,假如儿童被尊为具有其自身权利的人,那么,或许在决策过程中做某种参与是道德方面的要求。但是做何种参与呢?
同样清晰的是,这似乎与标准的发展理论解释存在相关性。为了在自己的医疗决策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患者必须多少了解一些自己的疾病或创伤的严重程度,并对相应的各种治疗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或遭遇失败,心中多少有点儿数。对死亡所知有限,或者对死亡的理解存在欠缺的儿童,还不具备了解致命的疾病或伤害的能力,因而他们在选择最佳治疗路线上难以扮演理性的角色。
儿童对于死亡的理解是如何逐步发展的,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发展心理学的解释,为九岁以下儿童在告知病情的诊断与预后以及同意治疗两方面完全由家长包办代替,似乎提供了担保。这会鼓励人们这样认为,尽管对儿童病患者的管理应当最大地减少患者的痛苦,但这并不真的需要(也不可能真正地)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于是,自主权所要求的认知能力便在幼小儿童那里不知所踪。
在我们如此心安理得地接受儿童患者医疗中的家长包办代替之前,我们需要反思一下那些作为“死亡概念”研究对象的儿童的经验。他们许多人仅仅有过宠物死亡的经验。即使在研究的年龄范围内的儿童经历过家人的死亡,那也很可能是祖父母的死亡,而不是父母或手足同胞的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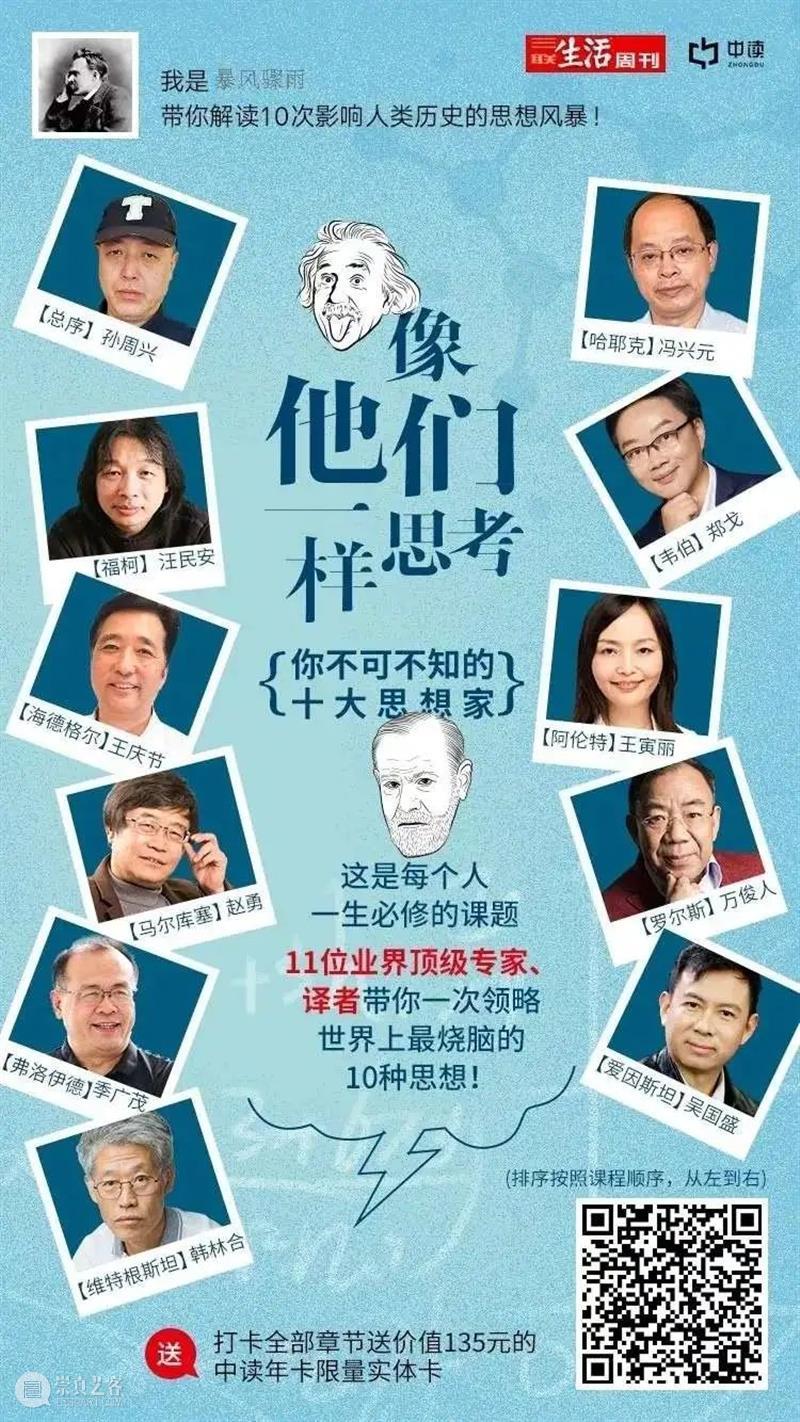
当然,在这一年龄范围内也有儿童失去父母、手足同胞或好朋友,也有儿童自己遭受危及生命的创伤或患有绝症,他们其实就是我们重点关注、追问他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应当被告知病情或允许参与治疗决策的上面那组儿童。这些特别的案例,在建设儿童如何获得死亡概念的理论方面,难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需要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即标准的发展理论的解释是否可用于这些案例。
米拉•布鲁邦德-朗格在其《临终儿童的私密世界》中的研究与此有特别的相关。布鲁邦德-朗格研究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受害人。她是1971—1972年做这项研究的,那时对患有此病者的预后几乎是没救的。在其研究的五十名病人中,三十二名是“报告人”,十八名是“主要报告人”。他们的年龄是从三岁到九岁。十八名主要报告人中,有六名在这项为期九个月的研究结朿后依然活着。五年之后,当布鲁邦德-朗格完成该书写作时,所有患者均已过世。
布鲁邦德-朗格的研究显示,尽管儿童在理解与应对可能突然降临的死亡方面存在可识别的阶段特征,可是,这些阶段是与他们对绝症的生命体验相关的,而绝非与他们的年龄相关。以下这些阶段为布鲁邦德-朗格所发现:
儿童首先了解到“它”(不是所有儿童都知道这种疾病的名称)是一种很重的病。[第一阶段]他们此时会累积药品的名称和副作用等信息。儿童到了第二阶段,他们知道药品何时用、怎么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在第三阶段儿童了解到,配药需要特别的手续,副作用发生时需要额外治疗。儿童有能力做这种了解,是第三阶段的标志……但他们只是将每次手续、每次治疗视为相互独立的事件。到了第四阶段,他们才能将治疗、手续、症候放入一个更大的视野内考虑。此时,儿童已能了解疾病的整个过程——该病是一系列的复发与缓解,人会以相同的方式一病再病;即使药物有点效果,可药效持续的时间总不如预期的那样久。直至第五阶段,儿童才了解到,病痛的循环至死方休。于是他们意识到,治疗该病的药品种类有限,当这些药品对病情不再有效,那么死亡便会来临。
当然,每个到达第五阶段的儿童,都将死亡理解为一切生物功能不可逆转的停止。达到这一阶段的每个儿童都知道,死神的降临不是在虚幻未来的某一时刻,而是很快就会到来。因此,布鲁邦德-朗格所研究的到达第五阶段的每个白血病儿童患者,对死亡的理解包含发展心理学所说的最后阶段的所有要素。
布鲁邦德-朗格的阶段理论可能被视为皮亚杰学派的理论,但它有一个关键特征与皮亚杰不同,即这一阶段理论与儿童的年龄顺序完全无关。这一特征也让布鲁邦德-朗格对阶段的阐释与标准发展理论的解释有所不同。布鲁邦德-朗格如此解释儿童经验的重要性:
经验在社会化进程中的地位有助于阐释儿童为何能以不同寻常的长度留存于既定阶段而不进入下一阶段。例如,汤姆在第四阶段留存一年,而杰弗里在第四阶段只留存一周。由于进入第五阶段的时长依赖于听到另一儿童患者死亡的消息,而汤姆进入第四阶段后没有患者死亡,所以他难以进入第五阶段。当詹尼弗死亡时,她是那年死亡的第一位儿童,所有处于第四阶段的儿童,不论其在第四阶段留存多久,全都进入了第五阶段。
经验在意识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能解释,年龄和智性能力何以与儿童经历各阶段的速率和完整性是无关的。一些智力平常的三四岁儿童所知道的自己病情的预后要比一些非常聪明的九岁儿童还要多——这些九岁儿童还处于第一次病情缓解期间,很少去看医生,因而缺少经验。
显然,标准发展理论对儿童何以获得死亡概念的解释,并不适用于那些与其他绝症病童一起住院治疗的绝症病童。或许人们可从这些发现中推断,如果我们将儿童放入一个连续体中,该连续体以“对死亡没有任何直接经验”为一端,以“病入晚期并与其他绝症病童一起接受治疗”为另一端,那么,绝大多数儿童的经验会居于两个极端之间;大多数儿童或许会更靠近对绝症极端无知这一端,而非另一端。
标准发展理论对于儿童何以获取死亡概念的解释,充其量只是对于那些在“常态”范围内对危及生命的事故与疾病一无所知的儿童来说,是令人满意的。这种解释不适用于那些与绝症抗争而获得大量经验的儿童。因此,这种解释也与以下伦理问题难以关联,即是否将残酷的病情预后向绝症病童透露,或者是否征求儿童参与医疗决策。
其实有些证据显示,治疗患绝症的儿童时,将病情预后告知他们,在决定治疗方案时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真正尊重他们自主权的做法,极其明显地会使儿童在获得心理健康并免于严重沮丧方面获得更多机会。
无疑,面对死神即将来临的一些儿童,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们会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们并与我们一起讨论,假如我们有足够的坚强去听去分享的话。可是,与这样的儿童讨论,即便有诸如《塔克一家长生不老》或《夏洛的网》这样的故事相助,依然要求我们不仅要有开放的胸怀面对儿童,而且还要有开放的胸怀面对那我们成人也极难驾驭的死亡之思。家里有受到致命创伤或患有绝症的儿童,对父母的自负与虚荣是极大的威胁。如果我们能学会真诚应对这种威胁,学会以尊重和爱的心态应对这样的儿童,那么在自身成熟度的发展上,我们将会迈出一大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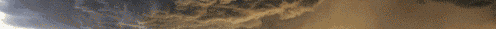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