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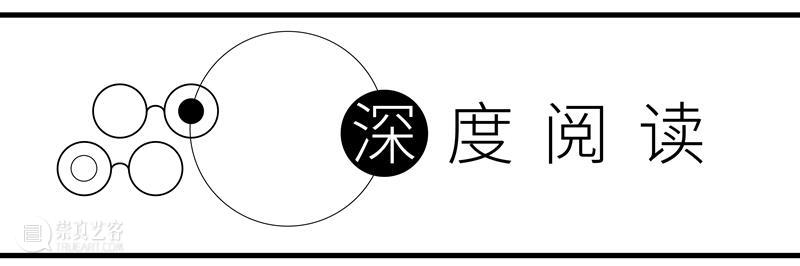
打个广告先:十分推荐大家阅读我们前不久推出的新书《自我坦白:福柯1982年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的演讲》(米歇尔·福柯 著,潘培庆 译),此书在我们微店已所剩不多,欢迎订购。

真理与司法形式
米歇尔·福柯 / 文
郝晓宇 / 译
1973年5月21—25日,福柯在里约热内卢的罗马天主教大学作了五次讲座,也就是“真理与司法形式”。我们将陆续推送这五次讲座的中译本。
该中译本主要根据英译本(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Judicial Forms”, in Power: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Edited by James D. Foubion, Trans by Robert Hurley and others, The New Press, 1997, pp.1-89)进行翻译,并对照法文版(Michel Foucault, “La vérité et les formes juridiques”, in Dits et écrits, t. 2, texte n°139, Gallimard, 1994, pp.538-646)进行修订。
【 】里的内容,为英译本标注;[ ]里的内容,是中译本据法文版所作的修订和标注。
今天推送的是第五讲(上)。
第五讲(上)
在最后一讲中,我会尝试定义我所谓的“全景敞视主义”。全景敞视主义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它是一种适用于个人的权力类型,采用持续监视个人的形式,采用控制、刑罚和补偿的形式,采用矫正的形式,也就是以某种规范来塑造和改造个人。全景敞视主义的三个方面——监视、控制、矫正——可能是我们社会中权力关系存在的基本、特有维度。
在封建社会中,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与全景敞视主义相似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类型的社会或17世纪的欧洲社会,就没有任何社会控制、刑罚和补偿的机构,尽管它们的布置方式与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建立的方式完全不同。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基本是边沁规划的一种全景社会,一种全景敞视主义所统治的社会。
在这一讲中,我会试着表明,全景敞视主义的出现包含了一种悖论。就在它出现的时候——或者更确切些,就在它出现之前的数年里——我们看到一些刑法和刑罚的论述,建构了一种根本基于严格法律主义(legalism)的理论,贝卡利亚是最为重要的代表。这种刑罚理论,使刑罚和刑罚的可能性,从属于明确的法律实存,从属于对已发生违法行为的清晰建构,最终,从属于一种可以补偿的刑罚,或在可能的范围内阻止犯罪行为损害社会。这种法律主义理论,这种真正社会化、几乎是集体主义的理论,完全与全景敞视主义相对立。在全景敞视主义中,不是在一个人所做而是在一个人所是的层面上,不是在一个人做了什么而是在一个人可能做什么的层面上,对个体展开监视。在这种体系下,监视就越来越倾向于对行为者的个体化,而不再考虑司法性质以及行为本身的惩罚条件。这样,全景敞视主义就站在了之前形成的法律主义理论的对立面。
现在,十分重要的是关注到这种根本性的历史事实:在开始阶段,法律主义理论还被全景敞视主义——它在法律主义的边缘或附近形成——所重复,随后就被遮没和彻底隐匿。正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诞生——从17世纪到19世纪,贯穿于整个社会空间,通过权力之位移所构型和驱动——正是中央权力对人口控制机制的收回,描绘出17世纪以来的进程的特征,并解释了在19世纪开端如何会开启全景敞视主义的时代,而全景敞视主义的体系,注定扩展至全部实践,并在某种意义上,将遍及刑法的全部理论。
为了证明我所表述的论点,我将援引一些权威之作。在19世纪之初的那些人,或至少其中一部分人,并没有忽略我所谓的——多少有些武断,但至少可以表达对边沁的敬意——“全景敞视主义”的出现。事实上,好几个人被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被刑罚机构的组建或者国家伦理所吸引并且进行了思考。在当时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作者,既是柏林大学的教授,也是黑格尔的同事,在1830年写作出版了一部含有数卷的伟大著作,名为《监狱课程》(Lessons on the Prisons)。[1]我推荐你们去阅读的这个人名叫尼古拉斯·海因里希·朱利叶斯(Nicolaus Heinrich Julius),他在柏林开设了好几年关于监狱的课程,是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某些时候,几乎是以黑格尔的声音来说话。
[1]N. H. Julius,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fängnisskunde (Berlin: Stuhr, 1828). 法译本:《监狱课程》(Leçons sur les prisons, trans, Lagarmitte, Paris: F. G. Levrault, 1831),该课程在1827年向公众讲授。——法文版注
在他的《监狱课程》中,有一个段落说道:“现代的缔造者正在发现一个之前不为所知的形式。”提及希腊文明,他说到:
以前,缔造者主要关心解决以下问题,即如何把一个事件、一种行为、一个个体向最大多数人进行公开展示。这是宗教献祭的情景,是最大多数人必须参与的一个独特事件;也是更多衍生自献祭的剧场情景;是竞技比赛、演说、演讲的情景。现在,这个问题——就像在我们所知的希腊社会中所呈现的那样,正是共同体,才会参与到构成其统一体的戏剧事件:宗教献祭、剧场或者政治演讲——继续统治着西方社会,直到现代。教会的问题也完全如此。每个人必须在场,必须充当弥撒献祭的观众或牧师布道的听众。现在,现代缔造者所面对的根本问题恰恰相反。我们想要做的是最大多数人向负有监视任务的单独个人提供景观。[2]
[2]Julius, Leçons sur les prisons, vol. 1, pp.384-86.——法文版注
在写作中,朱利叶斯想到了边沁的全景监狱,还有比监狱建筑在某种意义上更为普遍的医院和学校。他所提及不是希腊式的景观(spectacle)问题,而是监视的建筑问题——这种建筑可以使一种单独的凝视,在尽可能多的监舍中,审查尽可能多的人脸、身体和姿势。“现在”,朱利叶斯说:“这种建筑的出现,既与生活在精神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形式下的社会的消失相关,也与国家控制社会的出现相关。国家将自身呈现为个体的某种空间性和社会性安排,其中,所有人都臣服于一种单独的监视。”在总结这两种建筑学的阐述时,朱利叶斯说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问题……这种区别在人类精神历史上是至关重要的。”[3]
[3]Ibid., p.384.——法文版注
在那个时代,朱利叶斯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现象的人:从景观到监视的倒置,或者全景敞视主义社会的诞生。在同时代的许多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相同类型的分析。我只援引其中一例,这些文字由国会议员、帝国法官的让·巴蒂斯特·特莱拉尔(Jean-Baptiste Treilhard)所撰写,是关于1808年《刑事诉讼法典》的介绍。特莱拉尔在其中声明:“我向你们呈现的《刑事诉讼法典》,不仅在司法历史和司法实践上,而且在人类社会中,构成一种真正的创新。通过这部法典,我们给予了公诉人——在被告面前他代表着国家权力或社会权力——一个彻底全新的角色。”[4]特莱拉尔还用了一个隐喻:公诉人一定不能仅仅具备起诉罪犯的职能;他主要和首要的职能,应该是在违法行为甚至尚未发生时就监视个人。公诉人不只是法律的代理人,不只是在法律被违反时才有所行动;公诉人,首先是一种凝视,一双持续瞄准人口的眼睛。公诉人的眼睛应该和总检察长的眼睛传递信息,总检察长接着又把信息传递给监视的巨眼,在那时也就是警察部长。后者则把信息传递给位于社会顶点的那双眼睛,即国王,国王在当时正好是眼睛的象征。国王是观察社会全部延伸区域的普遍之眼,并由一系列凝视所辅助,它们按照始于皇权之眼的金字塔形制来部署、监视整个社会。对特莱拉尔而言,对帝国的法官而言,对那些创建了法国刑法的人而言——不幸的是,它在全世界已经有了广泛影响——这个巨大的凝视金字塔,构成了司法程序的新形式。
[4]让·巴蒂斯特·特莱拉尔(Jean-Baptiste Treilhard):《[刑事诉讼法典]构成规则的缘由说明》(Exposé des motifs des lois composant le Code d’instruction criminel, Paris: Hacquart, 1808, p.2)。——法文版注
在这里,我不会分析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具备全景敞视主义特征的全部机构。我只想从其底部,从其仍未清晰显现之处,在远离决策中心和远离国家权力的地方,来理解全景敞视主义和监视;在最简单的层面上,在机构的日常运作中——它们涵盖了个体的生活与身体——也就是在个体生存的全景敞视主义[层面]上,来指出全景敞视主义存在的方式。
这种全景敞视主义包括什么,它服务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来猜。我会描述一个法国在1840—1845年间真实存在的机构规章,这恰好位于我所分析的时段开端。我会描述其规章,但不指明它是工厂、监狱、精神病医院、修道院、学校还是兵营,然后你们来猜我说的是哪一个机构。这是一个拥有四百人的机构,他们都没有结婚,而且,他们必须在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在5:50,他们必须完成洗漱、着装、整理床铺和饮用咖啡;早上6点开始强制性劳动,到晚上8:15结束,中间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晚上8:15,晚餐和集体祷告;晚上9点准时回到宿舍。礼拜日这天例外。该机构条例手册第5条规定:“我们希望保持礼拜日的应有精神,将其奉献给[践行]宗教义务和用来休憩。然而,倦怠会使得礼拜日比一周其他的时间更为劳累,所以需要开展多种活动,从而以基督徒的愉悦举止渡过这一天。”在早上,进行宗教练习,接着进行阅读和写作练习,最后,临近中午的几个小时才是娱乐活动;下午,进行教义问答和晚祷,如果天气不寒冷的话,[4点后]还有散步。如果天气严寒,就会聚在一起阅读。宗教活动和弥撒不在附近的教堂进行,因为那样会使本机构的居留者接触外部世界;因此,为了防止教堂本身成为与外界接触的处所或托辞,宗教仪式在机构内部修建的小教堂举行。“教区的教堂”,条例手册解释道:“可能成为接触外界的地方,这就是为何小教堂要修筑在机构内部。”外部信徒不许进入。居留者只有在礼拜日的散步中允许离开机构,但始终处于宗教人员的监视之下。这些人员监视着散步和宿舍,并确保车间的安全和运作。所以,宗教人员不仅[保证了]对工作和道德的控制,还[保证了]对经济的控制。居留者没有工资,但有一笔报酬,每年一次性支付40到80法郎,只有在离开时才会给他们。如果因为物质或经济的原因,某位异性需要进入该机构,那么一定要对他精挑细选,而且不能久留。他们应当保持缄默,否则就会被驱逐。根据规章,一般而言有两个制度性的原则:居留者一定不能单独待在宿舍、咖啡间或院中;一定要避免与外部世界的任何混杂,并在机构中贯彻一种相同一致的精神。
这是什么机构呢?这个问题基本上无关紧要,因为它可能是任何一种机构:一个针对男人或女人、青少年或成人的机构,一所监狱、寄宿学校、学校或者管教所。它不是医院,因为谈及了很多工作。也不是兵营,因为工作在内部完成。它可能是一所精神病医院,甚至是有营业许可的妓院。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工厂——在罗纳地区雇佣了四百人的女子工厂。[5]
[5]这是1840年安省地区Jujurieu丝织厂的规章。福柯曾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coll. « Bibliothèque des histoires », 1975, p.305)中引用。——法文版注
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一个讽刺、滑稽的例证,一种乌托邦。在监狱工厂、修道院工厂和无薪工厂里,工人的时间被一次性全部购买,每年的报酬只有在离开的大门口才能领取。这一定是雇主的梦想,或者是只在资本家幻想层面才出现的愿望,是从来不会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极端情形。我则答复为:正相反,这个雇主的梦想,这个工业的全景监狱,真实存在,并在19世纪初大规模地存在着。单在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就有四万名女子纺织工人在这样的制度下工作,这个数字在当时相当巨大。相同类型的机构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同样存在,特别是瑞士和英格兰。事实上,这也是欧文(Owen)何以会提出他的改革观念的原因。在美国,有一整套复杂综合的纺织工厂,就是按照这样的监狱工厂、寄宿学校工厂、修道院工厂的模型来组建的。
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谈论的现象具有非常广阔的经济和人口范围。可以说,这一切不仅仅是雇主的梦想,而且还是一个已经实现的雇主的梦想。事实上,存在两种乌托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具有永远不会实现的特性;还有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拥有经常得以实现的不幸趋势。我所说的乌托邦,即监狱工厂的乌托邦,确实已经实现。而且,不只在工厂中实现,还在同时出现的一些列机构中实现。这些机构基本上遵循相同的原则和相同的运作模式;教学类型的机构,诸如学校、孤儿院、培训中心;矫正机构,诸如监狱、管教所、青年惩治所;同时是矫正和治疗的机构,诸如医院、精神病院:所有这些机构,美国人统称为“收容所”(asylum),一位美国的历史学家最近在一本书中对其进行了分析。[6]在该书中,他试着说明这些横贯西方社会的建筑和机构如何在美国出现。美国开始书写这种历史,其他国家也应该这样做,应该首先尝试权衡它的重要性,量化它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范围及影响。
[6]Erving Goffman, Asylums, New York: Doubleday, 1961;台湾译本为,厄文·高夫曼:《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者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
我们则必须更进一步。这里不仅有工业机构和其他一系列的伴生机构,而且实际发生的事实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工业机构是完美无暇的。人们立即集中精力开始建造它们,它们也正好成为资本主义的目标。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它们既不可行也不受资本主义掌控。这些机构的经济成本随即被证明极为沉重,监狱工厂的僵硬结构很快就导致了它们的失败。最终,它们都消失了。事实上,只要出现生产危机,就必然要解雇一些工人以重新适应生产,而只要生产增速加快,这些巨大的公司,拥有固定数量的工人和永久组装的设备,就会完全无用。更好的选择是,逐步淘汰这些机构,并以某种方式保留它们履行的功能。于是,在工业界里,就组织了一些侧面或边缘的技术来保证这些功能——这些功能最初由僵硬、空想、略带乌托邦式的机构来提供——对工人阶级的监禁、隔离和固定。因此,采取的措施,诸如创建工人住宅区、储蓄银行和救济金,这一系列方式都是为了把劳动人口、形成壮大的无产阶级,固着在生产装置的实体上。
有待回答的问题是:两种形式的监禁[réclusion]机构想要追求的目的是什么?一种是紧密、坚固的形式,出现在19世纪初,后来甚至也出现在诸如学校、精神病院、管教所和监狱的机构中;另一种监禁的形式,更加温和也更加分散,表现在诸如工人镇、储蓄银行和救济金的机构中。
乍看之下,人们可能会说,这种[现代的]监禁——[即出现在19世纪我所指出的机构中]——是我们在18世纪发现的两种趋势或倾向的直接遗产。一方面是法国的监禁技术,另一方面是英国类型的控制过程。在前几讲中,我试图表明,在英国,社会监视如何起源于宗教团体在内部自我施行的控制,特别是在意见分歧的团体中;而在法国是国家装置如何进行监视和社会控制——可以说,国家装置受到个人利益的强烈渗透——主要的制裁,就是囚禁于监狱或者其他监禁机构。结果,人们可以说,19世纪的监禁是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的结合,它在英国孕育,也包括法国专有的、国家控制的监禁机构,监禁在某个地方、某个房屋、某个机构和某个建筑物之内。
然而,就英国的控制模式和法国的监禁而言,19世纪出现的现象是一种创新。在18世纪的英国体系里,团体向个人或向该团体的成员行使控制。至少在初始阶段,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情形是这样。贵格会和卫理公会,总是向该团体成员,或者向处于该团体的社会、经济范围之内的那些人,施加控制。直到后来,控制机构才上移到顶端,移至国家。某人属于团体的事实,就一定会使他接受本团体的监视。早在19世纪形成的机构里,一个人就不是因为他是团体成员而处于监视之下,与之相反,恰恰因为他是一个个体,他才会被置于某个机构,该机构则会构成团体、构成需要监视的集体。正是作为一个个体,一个人才走进了学校;正是作为一个个体,一个人才进入了医院或监狱。那些监狱、医院、学校以及车间,不是团体自我监视的形式。而正是监视结构——把个体吸引聚集、各个控制、吸收整合——才会把他们构建得从属于团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监视与团体的关系中,两个时段(即18世纪的监视和19世纪的监视)如何会存在至关重要的区别。
就法国的模型而言,18世纪的监禁与19世纪的监禁非常不同。在前一时期,囚禁一个人,总是因为他被家庭、社会团体和当地所属社团边缘化——他不按照规则行事,并且由于他的举止、无序以及不规律生活而被边缘化。监禁,用惩罚的形式,用一种再次边缘化来回应事实的边缘化。似乎要告知个人:“既然您自己隔离于您的团体,那么,我们将会永久或临时地把您隔离于社会。”所以,在那时的法国,这是一种排除性监禁。
但在我们所谈及的时代,所有这些机构——工厂、学校、精神病院、医院、监狱——的目标,不是排除个体,而是固着个体。工厂不是排斥个体,而是把个体固着在生产装置上。学校不是排斥个体,甚至监禁他们,而是把他们禁锢于知识传递的装置。精神病院不是排斥个体,而是把他们固着于矫正装置,固着于个体的规范装置。管教所或监狱也同样如此,即便这些机构的效果是排除个体,其首要目标也是把个体嵌入规范大众的装置中。工厂、学校、监狱或者医院,都有把个体束缚于生产过程、培训【formation】生产者或矫正生产者的目的。这是根据特定的规范来确保生产或生产者。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两种监禁之间进行对比:18世纪的监禁,从社会圈中排除个体;19世纪的监禁,则具有把个体固着在生产装置以及培训、改良或矫正生产者的功能。因此,这里涉及一种排除性纳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监禁[reclusion]与监管[sequestration]区别开来的原因[7]:18世纪的监禁,主要功能是排除边缘个体或者加强边缘化,而19世纪的监管,目的则在于纳入和规范。
[7]本文把réclusion、internment(英译本有时用confinement来对应)译为“监禁”,以表达福柯所谓“边缘化监禁”、“排除性监禁”的意思;而séquestration一般指隔离证人或陪审团、扣押财产以及征用、征收等,此处译为“监管”,以表达福柯所谓“排除性纳入”、“排除性规范”的意思。
最后,对比之下,还有第三组差异,而且18世纪的监禁为19世纪的监禁提供了原始配置。在18世纪的英国,控制方法一开始明确地独立于国家[超国家主义],甚至对立于国家[反国家主义]——它是宗教团体通过自我控制的方式对抗国家统治的防御反应。另一方面,在法国,这种装置至少在形式上和工具上完全由国家控制,因为它根本依存于国王封印密札的机构。所以,英国是绝对的超国家主义(extra-statist)样式,法国是绝对的国家主义(statist)样式。在19世纪,出现了一些更加温和、多样的新事物:一系列机构——学校、工厂……——很难说这些机构是否是简单的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或是否是国家装置的一部分。实际上,根据机构、国家和情境的不同,其中一些机构是由国家装置直接控制的。比如,在法国,先于基础教育机构出现的冲突,就能交与国家管制——政治事件由此而来。但是,就我所着眼的层面而言,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对我而言,这种差别无足轻重。实际上,新奇、有趣之处在于,国家和非国家决定之物在这些机构的内部互相融合和交错。既不是国家主义也不是非国家主义,应该说有一种监管的机构网络,它是内国家主义(intrastatist)。在分析这种普遍的监管装置的功能时——在监管网络之内,我们的生存就是被监禁——国家装置与非国家装置的区别无关紧要。
那这些网络和机构所服务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描述其功能:首先,这些机构——教育学的、医学的、刑罚的或工业的机构——具有非常奇特的属性,即掌控并负责个体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机构接管了个人生活的全部时间维度。
就此而言,我认为应该把现代社会和封建社会区别开来。在封建社会和许多人种学者称为“初民”的社会中,对个体的控制基于融入当地,基于他们属于特定地域的事实。只要他属于某一采邑,即可对他行使封建权力。当地的地理登记就是行使权力的方式。权力通过人们的地域定位而铭刻于人。对比之下,形成于19世纪初的现代社会,基本对个体的空间归属漠不关心或者相对漠视,它对个体属于某一地产或地域的空间性控制并不感兴趣,只是需要人们按照它的支配来安排时间。人们必须把时间提供给生产装置,而生产装置必须能够利用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时间。控制,以这样的理由和方式来施行。工业社会的形成必须达成两件事:第一,个人时间必须被投入市场,提供给希望购买的人,并用工资来交换购买;第二,他们的时间必须被转化为劳动时间。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机构中,我们都会发现最大限度抽取时间的问题和技术。
- 相关推荐 -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