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学科视阈下的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与研究
选自 | 《西泠艺丛》2021年第4期 总第76期 |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教授
【摘 要】
当代书法研究正在发生着学科意义上的转型,促使书法批评在视角、标准、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调整。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与研究,也面临着视野的扩展和新方法的运用、呈现方式的转变等问题。文章从批评主体、对象、视角、观念、史料等方面对学科视阈下的书法批评史的叙述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书法批评史 书法学科 批评者 观念 叙述

书法学科可大致分为书法艺术创作、书法史论、书法美学、书法教育、书法批评等几个板块,其中书法批评包括书法批评史、书法批评理论、书法诠释学、书法批评标准、书法批评史料学、书法批评语言学等内容。
古人进行书法评论,有见个人之喜好者,有欲扭转时风、倡导某种风气者,有指导学子寻求学书途径者,有以书法作为个人性情抒发之载体者,也有以书法为教化之工具者。古代书法评论可不拘系形式,或长篇大论,反复言说,或寥寥数语,随性而发,并无一定成规,表明自己的态度与看法即可。而作为现代书法学术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当代书法批评正处于学科意义上的转型期,多重因素对书法批评的影响,促使书法批评在视角、标准、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调整。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与研究,也面临着视野的扩展和新方法的运用、呈现方式的转变等问题。
01
学科视阈下的书法批评,是从学科框架、学理层面探究书法的价值及其内在的依据。书法批评是一个有着众多因素参与的综合过程,除了艺术因素外,还有很多非艺术因素如政治、道德、经济利益、社会关系、个人喜好等介入其中,有时甚至还在某些环节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现象是如何造成的?非艺术因素是如何渗透影响书法批评的?艺术因素又是从什么时期开始在书法批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书法批评史的叙述能否梳理出各类因素介入书法批评的原因和状况以及又从书法批评中隔离或凸显出来的过程?
书法批评的主导线索是批评者以书法创作者之外的身份与视角对书法价值的评价与阐释。书法批评并非随意性的信口雌黄,也不是跟在书写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学理式的研究与诠释。
如果我们将书法批评不是当作“评”,而是当作“学”,看待书法批评史的视角就会发生改变,书法批评史也就有了多种叙述的可能。书法批评史就是批评学术的流变史,是批评者视野中的书法史、观念史。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与研究,需跳出高下等级编排模式的窠臼,从传统的褒贬臧否,转向批评学术体系的有意建构,转向对书法发展方向、趣味的主动干预和全方位的探索。
书法批评包括诸多分支或方向,而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与研究则需考察这些分支或方向的影响和关联,批评史可看作是这些分支或方向关联的交结点。在进行书法批评史的叙事时,就要综合书法批评的各关联对象,进行学术的分析与阐释,建立观念、史料之间的关联,而不是醉心于知识的堆积与罗列,这样才有可能构筑学科视阈下的书法批评的流变史。
书法批评史的写作,需要与书法史、书法理论史区别开来。通常的书法史的叙述模式是以书家和作品为中心,书法理论史的叙述模式是以作者和书论为中心,书法批评史则是以批评观念与方法为中心,更类似于史学史的写作。
02
书法批评的效用或者说是价值和意义可简单概括为:总结、干预、引导,即总结前代书家和作品的特点,干预当下书法的风气,引导书法的趣味表现和发展方向。
历代书法批评所涉及的问题颇多,如:书法的属性,书家的身份、地位,书品与人品的关系,字学与书学的关系,对历代书家和作品风格的概括和评价、书法评价标准的建立与调整、对待古今的态度,有关取法的对象、顺序、取法的方式以及对法度的遵守与个性的抒发之间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使我们明了历代书家和批评者书法知识、观念的来源和变化脉络,厘清各时代书法批评对前人观念的继承以及与前人的不同之处。
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书法批评所牵涉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所讨论的相关话题的流变脉络的梳理与研究;二是对批评者自身状况以及观念的形成过程、阐发机制等的研究,如批评者观点的建立与传播的过程和机制、所使用的批评方法以及批评的客观性与批评者的关联等问题。
书法批评的主体是批评者,批评者可以是特定的批评家,也可能并不只是具体的个人,还包括泛化的群体甚至是舆论氛围。书法批评的对象则指向书家、作品以及书法事件、风气与潮流等。从批评主体、书家、作品、事件、风气、潮流等视角审视书法批评,可以梳理出古代书法批评内部各要素的变化脉络,这些变化实际上基本指向了现代学科视阈下书法批评所涉及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在汉唐以来的书法批评特别是明代后期书法批评所发生的各方面的变化,与现代书法批评的要求多有吻合之处。而书法批评史就是从现代史学的学科要求对书法批评历史的梳理和建构,探索批评语境下的书法发展状况。
在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与研究中,首先需要关注批评者的知识构成状况和批评史料产生的语境和流传的过程,包括批评者书法知识的构成,批评观念的形成与批评方法的运用,以及批评者在当时的身份与地位,时人对批评者的评价,批评史料的产生、流传、保存、选择、裁剪与阐述的过程以及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意味等均是书法批评史所关注的对象。
例如在考察明代中后期书法批评的历史时,就需要尽力厘清这一时期书法批评和批评者的状况,回答书法批评是一开始就具有独立地位、具有影响时风的效力,还是在书法历史的发展中逐步凸显出重要性、确立独立地位一类的问题。通过对这一时期书法批评各相关因素的探究,我们发现此期书法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主要体现在书法批评独立的价值上,书法批评具有干预、引导书法发展的机遇和能力,批评者在当时书法领域的话语权也有了极大提高和巩固,不再只是对前朝书家和作品的考证与评说,而是直接臧否时人,倡导风气,宣扬特定的审美趣味,对其时的书法风气施加影响。
另一方面,版刻的兴旺、刻帖的增多、书画碑帖商品交易的频繁,改变了书法批评的知识基础,建立了新的书法批评的知识、方法、观念和传播方式。大量书法批评著述或相关著作被刊刻,使书法知识和观念的接受与传递的途径更为顺畅,书法批评观念的延续也成为常态。摘录前人语句成书或略加评点的批评著述多有出现,正是知识传播功能增强的表现。而这种有选择的摘录和评述,又使得相关评论的指向性和观念性很强,形成了特定群体或地域的书法批评意识和观点,这些意识和观点又通过版刻和口耳相传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和接受。书法批评“网络”的建立逐渐成为可能,带有群体特性的书法批评意识逐渐形成。书法批评开始从个体性的批评向既有个体性的特色,又有群体性趋向的集体批评意识转变。
03
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以什么为中心?如上文所说,应该是批评观念而非作品或书家,应该是站在批评者的立场,而不是书家的立场,虽然书家也可以同时兼有批评者的身份。
批评者和书家的知识结构并不完全相同,看待书法的立场、对书法批评的价值与作用的认识也不一样。不同的批评者的立场也各有不同,如可以作当下的立场与古代的立场、字学的立场与书学的立场、教化的立场与艺术的立场等区分,这些不同的立场交叉贯穿于书法批评史中。当然,除了这三类区分外,还可以有更多的分类。
同样是对书法中的古、今关系的讨论,站在当下的立场去看古代,与站在古代的立场来看当下是不一样的。站在当下去看古代,会倾向于从古代资源中寻找当下的依据,以阐释、证明当下的价值和合理性,更侧重于当代与古代的“同”,对当下的否定相对淡化些。站在古代看当下,则会倾向于以古代的标准和方式来评价当下,论证当下与古代的“异”,强调当下所存在的欠缺,对当下更倾向于持批评、苛刻的态度。
字学与书学立场的差异也是如此。书学立场更关注风格与技巧,而字学立场则强调六书、重视字法、结构的正讹、重视对传统秩序的遵守。在书法往追求风格、审美的道路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批评者会时时以传统的字学立场去修正这种变化,试图施加影响,并将所施加的影响与人的修养、朝廷的治统等联系起来,借助朝廷和道统的力量对书法进行干预,对书写赋予更多的内容。
书法批评的文字学立场和风格审美的立场的产生和变化,以及这些立场下对历代书家、作品的评论、对书法评价标准的确定等存在的明显歧异,对书法风气有着不同的导向作用。强调六书的观念是如何影响其时的书法观念和书法风气的?产生了怎样的实际影响?明了六书,会对书法产生怎样的益处?符合六书会使书写者获得怎样的评价?不符合六书又会给书写者招来怎样的批评?书学立场的批评又是如何促进书法的表现特性和风格变化的?这些问题都是在考察字学、书学不同立场时所需关注的。
批评的语言也是书法批评史叙述中需特别关注的对象。书法品评术语最初受到文学批评语言的直接影响,随着书法批评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立的书法品评语系,建立起文人群体均能理解和接受的品评概念、范畴和专用术语。早期的书法批评曾有对品评语词作专门解释的,批评者们已意识到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对品评语汇含义理解的不同,词义的含义是在不断变化的,因而存在理解上的歧义。但宋代以后的书法批评,对批评语汇含义的关注减少了。批评语汇含义的演变与批评者对这些语汇的运用,需要后来的叙述者尽量回到评论的真实语境,分析语汇的真实含义。例如神、妙、能、雅、俗、韵、法、意、古、淡、正、奇、雄强、朴拙等术语,都是书法批评中的常用语汇,但在具体的批评语境中,有不同的理解和阐述方式,要准确理解、叙述书法批评史,书法批评语言学成为不可或缺的知识与学问。
以新的视野和立场审视书法批评史,可使我们挖掘出大量书法批评史中曾出现过,但又被忽略和掩盖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常常包含着批评史中很重要的线索和价值。除上文所列举的外,其他还有诸如官方意识形态与文人趣味、观念的冲突与交融,政治力量、经济、市场因素、民俗习惯、风水观念等对书写和书法批评的影响等,都蕴含着新的动向和话题。
如果书法批评史的叙述选择以观念为中心,则在确定叙述框架时仍需以时间为线索,围绕观念的变化而展开,但不能简单地按朝代来硬性分期。这样体现的是书法批评意识的内在发展脉络,而不是以朝代更迭来统领书法史和批评史。以朝代来分期批评史,按批评者活动时间先后排列其平生、著作的主要观点的叙述方式,固然与大家所习惯的历史知识的建构模式合拍,方便对时间线索的把握和个体批评者的观点的了解,同时朝代的更迭,也的确在政治、文化、社会、时尚风气等方面对特定群体和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直接辐射到书法领域,但这种叙述方式,是将批评史置于政治史之下的视角,并没有真正地将批评史置于叙述的中心,没有体现出批评史自己独特的视角。
虽然最终我们在叙述书法批评史时,仍然主要采用按时间分期叙述的方式,但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带来对书法批评关注的角度、关注的重点、叙述的方式等的不同。这种区分虽然从表面上看区别不大,似乎只是分段时间上的些微挪移,但实际上则是对应着不同的书法批评史观和研究方法,在叙述模式和观点的呈现等方面有着根本的不同。
04
如果我们将史料的记载、收集、编辑和使用看作是批评者主观有意识的行为,则这些史料就不仅仅只是固定的史料。除了史料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外,对相关史料的比对和分析,还可使我们窥见书法批评史料的流传、保存、裁剪、编排与阐释的过程,分析这些行为和评论背后的意味,得以对批评者的观念有更准确、更深刻的判断。
除了常见的书论文献外,书法批评史料范围还可扩展,还有很多史料可以在书法批评史的研究中发挥作用。若以学科意识、新的眼光看待书法批评史,则会发现很多新的研究空间和课题,史料范围也会随之扩大。
例如,若将书法批评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不仅仅看作是批评者个人的行为的话,则研究的空间和史料范围会有进一步的扩大。对师友以及同时代其他书家的批评中存在的人情问题的关注,自然会将有关交游往来的史料纳入书法批评史的史料范围来考察,探讨主观评价与客观状况之间的协调与认知、言说的问题。
各类书法人物传记、行状、神道碑、墓志等也是书法批评史可以关注的史料,其中也包含着批评意识。传记等文献除记录基本信息外,实际上立传或汇集成传行为本身就带有批评、选择目的,而传记内容也是批评的表现和结果,即使只是一份善书者名单,也能透露出名单的开列者的观念和态度。以王羲之为例,王羲之的各类传记资料众多,比较这些传记资料的异同,可以看出不同的批评群体对王羲之关注点的不同、对王羲之评价的不同,并进而窥见这些批评者看待书法的态度和立场。
书画收藏与鉴赏,也是特殊的书法批评,在收藏、鉴赏过程中有着明确的选择、评价标准,蕴含着书法批评意识。收藏、鉴赏氛围有着强烈的暗示效应,即使是无声的鉴赏和口头的评论也仍然会在书画圈中口耳相传,形成书画圈中书法批评的舆论氛围和集体意识。收藏品的著录文献、有关鉴赏、雅集的诗文记载等都可作为书法批评史研究的史料。
在书学研究中,伪作与翻刻常被忽略,但实际上,伪作与翻刻仍然是书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伪作与翻刻以及批评者对待伪作与翻刻的态度和评论,也成为书法批评史叙述的重要对象。传说中的记载、伪作、翻刻等并不妨碍批评行为的进行、标准的建立,也不妨碍后世接受者的接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风格与观念。
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与研究,主要在致力于辨析古代书法批评史料的立场和史料属性,而非仅仅简单地辨别真伪,否认伪作与翻刻等另类资料在批评观念的建立和标准的形成中所发挥的作用。明代批评者对宋人辨伪方法的批评即透露出明人对此问题的认识。
05
书法批评中有很多影响很深远的议题、观念或模式,如书品人品论、雅俗论、古质今妍论、法度与心性等。批评史的研究就需探究这些不同的议题、批评模式和标准的形成机制、内涵以及演变过程。此处,以书品人品论为例略做展开。
书家是书法批评主要关注的对象,在早期书法品评中有以人为观照的风气,将书法比拟为各类不同形象、气质的人物。而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与道德世界有了紧密关联,书品人品论成为书法批评的核心议题之一。
书写本身与道德世界关联不大,但书法批评却可以与道德世界紧密联系。书法批评与道德世界的关联,在于书法的人格化,将作品与书家的道德、人品紧密相连,同时书写内容也道德化。在书品人品命题中人品的内涵是广泛的,除政治、道德人格外,人的气质、风度也包括在内,两者可合于一体,也可各有侧重。
在书品和人品密切关联的倾向中,什么时期开始出现对书家、作品的品评与书家的人品密切关联?人品的内涵又有哪些变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第二种途径。关注于书法作品本身、使作品评价与书家的道德评价相脱离的倾向又是怎样的状况?在书法批评中对人的道德问题关注的降低,带来书法与道德关联的松散和分离,也会带来对书法本身属性认识的变化和评价标准的变化。
这里可以颜真卿为例。后世对颜真卿书法的推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其忠义形象的接受,一旦在书法批评中剥离了政治、道德因素的影响,更注重于风格本身时,对颜真卿的评论就会有所改变,批评者们不再无条件地认可和推崇颜真卿楷书方正工稳的形态,而会发觉颜真卿楷书偏俗的特性,作出颜真卿“真法入俗”的评价,使之与科举考试、朝廷公文等规范的实用书写一起成为文人们批评的对象。
关注作品本身,则更倾向于从风格等角度评价书法。明代中后期不少批评者更倾向于第二种途径。这两种途径的矛盾,在明代后期对心性的强调和阐述风气中得到缓和和融合,即将道德评价转向对个人心性抒发的关注,看重的不再是抽象的忠义道德和外在的气质、风度,而是个人心性的体悟和表现,而个人心性的体悟和表现,又正是书法风格塑造和书法艺术性成立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对书写本身更加关注的批评,也即倾向于艺术性的书法批评又是怎样呈现的?又有怎样的理念与内在机制?
另一方面,书品人品的衍生问题也需引起注意。在书法的人格化过程中,也有强调“隐”的倾向,将“隐”视为人品高洁的表征,并与艺术造诣的高低相关联。那么,在哪些时代或针对哪些人物的评论中会更明显地涉及这一点?“隐”的行为对个人评价、个人书艺到达一定的高度有着特殊意义,“隐”在个人形象、书法形象的建构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体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隐”是因为什么机制和途径演化为个人形象高下标志的?是否可成为书法评价的通行标准?又是如何演变为评价书法作品高下标准的?
书家的身份问题也是如此。批评者对书家的身份问题是否有足够的关注?在书家身份独立之前,书法通常只是一种文人、官吏的附加技能。可以说,从明代中期开始,文人书家的概念和群体真正在批评视阈中形成了。而书家身份一旦独立,则书法批评所关注的内容和视角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文人书家身份的独立带来书法批评中的哪些变化?批评者对这些变化是否有及时的反应和论述?批评者在评论书家和作品时,是否区别开了书家和书手之异?这种区别又意味着怎样的对书法认识的变化?
文人书家身份的独立,带来对书家形象、知识学养、风格等方面新的要求,以与职业写手区隔开来,这些要求,在随后的书法批评中渐渐体现了出来,并影响到对书法本身属性的认识。多数批评者不再认为书法是小道,有时甚至还会将书法作为自己留名青史的主要寄托。在书品人品关系的议题中,政治、道德因素就会进一步淡化,体现文人趣味与喜好的隐逸趣味与风格会得到更多的青睐,并在品评标准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书法批评会更集中于与风格相关的因素,在品评标准中,对风格和书写内容的关注进一步加强。
06
对文献解读的视角和方法的不同,也会帮助我们从易被忽略的细节中获得新的发现。
书法批评中常有议论书道衰微、贬低当世的倾向,认为当世徇末忘本、怪诞浅薄,将对前世的推崇建立在对今世整体或某些局部的批评之上。古人对书道之衰问题的论述为何较为多见?为什么会有书道衰微的观念?这是一种真实的体会还是习惯性地情绪抒发?衰微的表现是怎样的?哪些书家和作品是和衰微之象有联系的?不同时代批评者所总结出的衰微的原因为何?是否提出了解决方案?
明人评论书道衰微,与南宋人、元人所论是否基于相似的立场和原因?不同时期的批评者评论书法衰微有着不同的立场和指向对象,早期提到书道衰微与人们观念中的笔法传承断绝有关,元人评论南宋书法衰微、明末人评论当世书道衰微,又是站在什么立场?是古法的失传、断绝还是时人不重视古法?是对人心、习俗改变的反应还是仅对书法本身状况的不满?是以此为靶子和线索,推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还是通过此类理由,显示批评者自己不与世合的高人姿态?
在传世书法文献中,众多传说中的、早就无作品流传的早期书家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而有较多真迹传世的当朝名家或前朝名家常常被忽略。例如在郑枃、刘有定《衍极》并注、盛熙明《法书考》等著述中,实际没有书迹传世、仅有传说流传的上古书家都受到青睐,流传作品存在真伪问题的中古著名书家也广受好评,而对有较多真迹传世的宋、元书家则常常是不置一词或多加指责。这种记载和评述的目的何在?在实际书法学习、书法史的建构中的意义和作用何在?其接受性如何?读者是否会因此而怀疑其论断的可靠性?是否与当时整个接受群体都是以古为核心,只要有记载,不管有没有实际作品传世,即使并不知道对这些书家取法什么、如何取法,这些书家也仍然都是需要推崇的、都是值得学习的观念有关?这种批评模式和方法什么时期开始发生变化?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与批评者对传统、古法、当下的态度是否有关?
对传说中的、无实际流传作品的前代书家的反复记载与强调,建立的是对书法传统、古法的崇敬意识,通过此类批评强化了传统、偶像的地位,而这种意识是书法领域的基本意识之一,强势影响着书法的走向。一旦人们将视野全面转向当下,对形象模糊的前代书家不再关注的话,意味着批评观念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对魏晋的崇尚也是如此。大家都崇尚魏晋,不同时代的不同批评者对魏晋的崇尚有什么不同?既然崇尚魏晋是大家的共识,那为何大家又不厌其烦地强调要崇尚魏晋?崇尚魏晋是否有名与实的差异?对于取法者或批评者来说,代表魏晋古法的往圣和在当下受到追捧的时贤之间是否存在着观念上的矛盾?时贤对往圣的地位经常产生冲击,从流行风气来说,时贤更易于占据时人关注的焦点位置,因利益关系,很容易取代往圣的地位。批评者的作用,就是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一方面是时时去纠正这种时贤压过往圣的状况,提醒学书者注意往圣的意义与价值,并强调书法与传统的关系、源流与古法在书法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会对过于尊崇往圣,贬低、忽略当下、忽略艺术家个人心性的倾向进行抨击。
在书法批评史的叙述和研究中还要注意批评效用的滞后性、湮没性、超前性。在前代没有影响的批评或在前代很有影响的批评在后世有可能因某些机缘、人物的重视、阐发或反对而对后世的影响发生变化,其中既有后世对前代批评意识、观点的挖掘与阐发的情况,也有后世对前代批评观点的淡化与湮没的情况。
书法批评中对前代价值的挖掘与诠释的例子有不少。一位书家的作品或风格、批评者的言论或著述,因各种原因,在当时不一定得到众人的重视,甚至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到了后世,因某种机缘才引起某些书家和学者的注意,得到诠释,才产生广泛影响。明初对宋儒书法言论的收集、后世批评者对杨维桢、徐渭书法风格的阐发、对北朝写刻作品的推重等俱是如此。
宋代理学家们关于书法的论述在宋代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随着明初朝廷官方编纂的《性理大全》中对宋儒书论的著录,宋代理学家的书法批评,在明初才被真正重视、挖掘出来,才开始在朝廷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据一定位置,影响着其时的书法批评和书法发展。明初对理学的重视,使书法批评中书法教化功能和规矩法度的意识得到强化。
学科意识会非常注重批评的诠释与引导作用,会更侧重于对书法批评史中超越时代的倾向进行总结、概括,对不被时人所重视的书家、风格趋向等进行诠释和褒扬,特别是对创造出新的风格、新的范式的人物和评论会格外重视。而古代批评者对此总体来说比较忽略,有时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和倾向,但往往缺少进一步的阐发和扩展。如明末董其昌将自己对“淡”的理解付诸书法实践,创造出不同于以往书法的新的范式和趣味,但董其昌的追随者们在总结、诠释、评价董其昌时多有欠缺,陷入简单褒贬和模仿之中,并没有从学理层面阐发其在书法风格演变脉络中的独特的价值。
在书法批评史的叙述中,就要尽力提炼出批评的主题,揭示出这种滞后性、湮没性、超前性,探究这些事件、行为、风格等真正在书法领域产生影响的时空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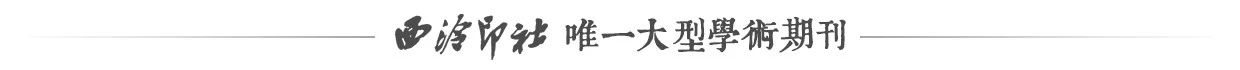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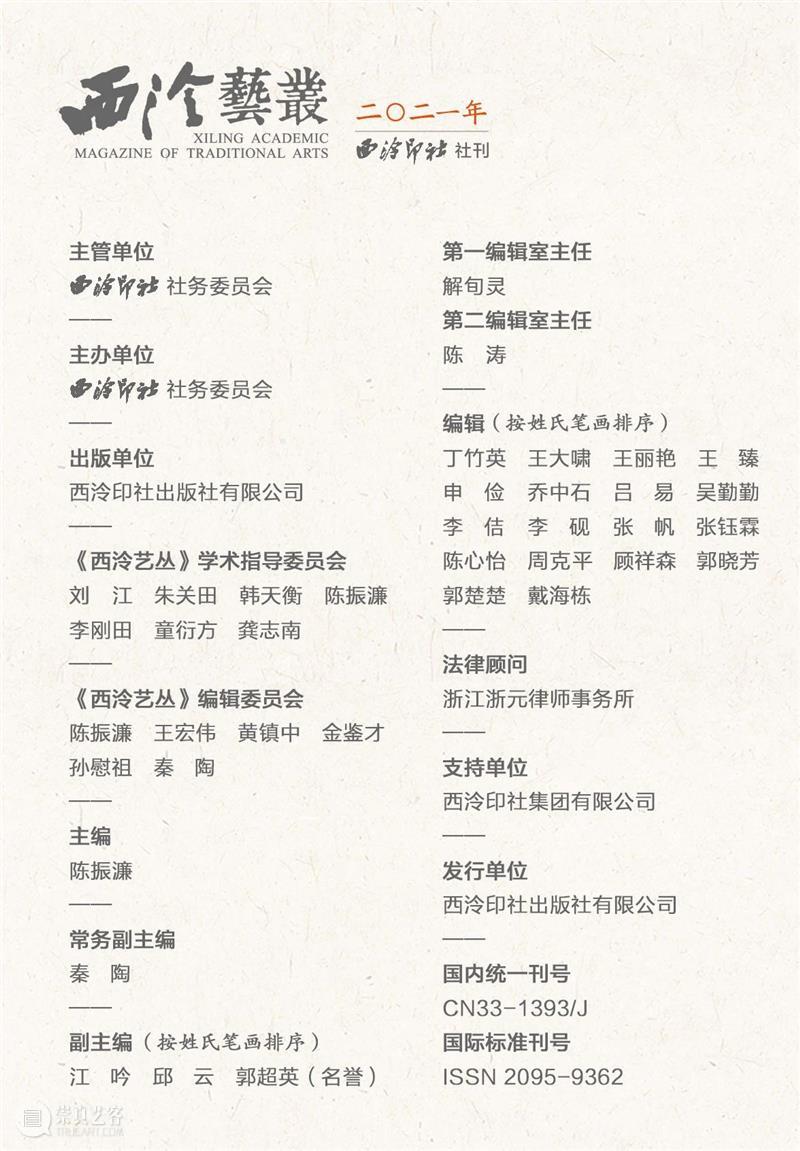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