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我们是谁?
——福柯、普鲁斯特、德勒兹
Miguel de Beistegui、Richard Marshall 文,何啸风 译
原文源于3:16网站,链接请点击“阅读原文”
感谢译者授权
Q(Richard Marshall):是什么让您决定做一名哲学家?
A(Miguel de Beistegui):一切都始于在法国上学的最后一年。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堂哲学课,内容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我觉得,世界被打开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打开了。我感受到“概念”那种指引我们见识世界复杂性的魔法般力量。我惊叹于各种各样造物的存在,它们既抽象又真实,既是理念的,又是物质的。破天荒地,我懂得了,思考意味着什么。
Q:您最近研究了欲望。在《欲望的治理》一开头,您提出福柯的问题:“现在的我们是谁?”福柯的问题,既来自尼采的诊断,又来自康德的历史本体论,对不对?这同样是您思考欲望的方法吗?您能不能谈谈尼采和康德对您思考欲望的影响,尤其是康德,他把考古学与谱系学结合起来?
A:我越来越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应对“永恒的哲学难题”(昨天有效、将来依然有效的难题),而是应对那些塑造我们主体性的力量、话语、实践的难题。借助这些难题,我们可以理解、体验“我们是谁”。这就是诊断的问题。福柯认为,诊断的问题在尼采那里凸显出来。而且,把尼采与康德联系起来的,是批判的问题。这种批判,不是对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判断力的批判,不是对主体性的那些机能(faculties)的批判,而是一个难题化(problematisation)和历史化(historicisation)的过程——对于各种力量和关系的发展演变 的历史条件(而非先验条件)的考古学和谱系学。这种方法,正是我的《欲望的治理》一书的方法。从这个角度看,本书提出的问题不是“欲望是什么”。与此相反,本书提出的问题是:现在的我们如何欲望?如何建构和组织欲望?如何理解和体验现在的欲望主体?如何定义“现在”?我们能追溯到多久以前?现在与过去有什么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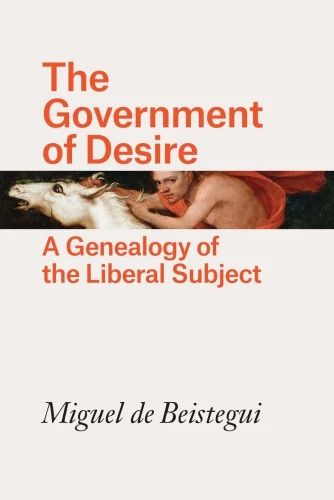
Q:从谱系学角度看,欲望的难题是什么?
A:我想,我刚才就在讨论在欲望的难题。接下来,我来谈谈为什么要分析欲望。我们到底 为什么关注欲望?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欲望的难题贯穿了整个哲学史,还涉及神学、政治经济学、性学、承认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欲望在我们(西方)的历史中有如此重要的位置?第二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自由主义有了新的解读(也是福柯的解读)。根据这种解读,自由主义不是思考个体自由,思考如何消除、弱化暴政,而是一种“治理术”,是对他人和自我的治理。这种解读,可以真正揭露自由主义的各种形式,包括右派和左派的自由主义。
我的《欲望的治理》一书的主张是,伴随着自由主义的出现,欲望发生了决定性的变革。欲望不再是需要管理、控制、支配、压抑的事物。相反,欲望成了治理工具,成了我们治理自我的工具。因此,在我看来,政治经济学、性气质、承认这些自由主义的合理性,都是赋予欲望新的含义、方向、角色的话语。这些话语,持续塑造了现在的主体性。这些合理性,以及维持它们的机构和权力关系——市场,医疗机构,把儿童培养为性主体的家庭和学校,把欲望阐述为对承认的欲望的法律——是自由主义的支柱,是欲望的规范性构造。
Q:西方社会真的是福柯所谓的欲望文明(the civilisation of desire)吗?这种情况如何发生?萨德是不是关键转折点,像堂吉诃德一样?这个转折,是快感伦理学向欲望伦理学的转折吗?
A:我不能判定,西方社会是欲望文明。我只能说,西方社会是一种欲望文明(a civilisation of desire),而且这种欲望文明让位于某种对欲望的特殊构造。福柯的主张是,我们对欲望的痴迷始于古典时代末期,尤其始于斯多葛主义。早期基督教在斯多葛主义中找到了天然的盟友。那么,萨德在这个过程中有何作用?福柯在《词与物》中说,萨德是一个关键转折点,类似于塞万提斯是古典主义到文艺复兴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何种意义上的?塞万提斯的转折指的是,“相似性”(resemblance)这一文艺复兴的认识型,取代了“再现”(representation)这一古典主义的认识型,从而产生了语法学、自然史、财富科学。萨德的转折指的是,随着再现的衰落,产生了现代的认识型,从而语法学、自然史、财富科学变为语文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
在福柯看来,主体性的这种新的维度摆脱了再现的要求和限制。它体现在萨德身上。萨德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他既受制于再现的时代,又是尽情释放欲望的全部力量。正因为如此,福柯说萨德是浪子而非变态,萨德的时代是浪荡时代而非性的时代。不同于堂吉诃德,萨德笔下的角色,“不是再现战胜相似,而是欲望之晦涩的强力拍打着再现的边界”。对萨德而言,他必须对一切事物进行言说,命名,再现。可是,因为萨德试图对不可再现之物进行再现,所以,他在古典主义话语的界限上写作。
但是,我不想夸大萨德对欲望发展史上的重要性。我只能说,萨德是一个浪子,或许是 最后一个浪子。在萨德这里,性行为的问题不取决于19世纪的规范化、临床式的性类型学,而取决于我们解读萨德的方式。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萨德是纯粹快感的伦理学家。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萨德关注的是欲望在法律面前的地位(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把transgression提升到jouissance的层面)。后一个维度,福柯并未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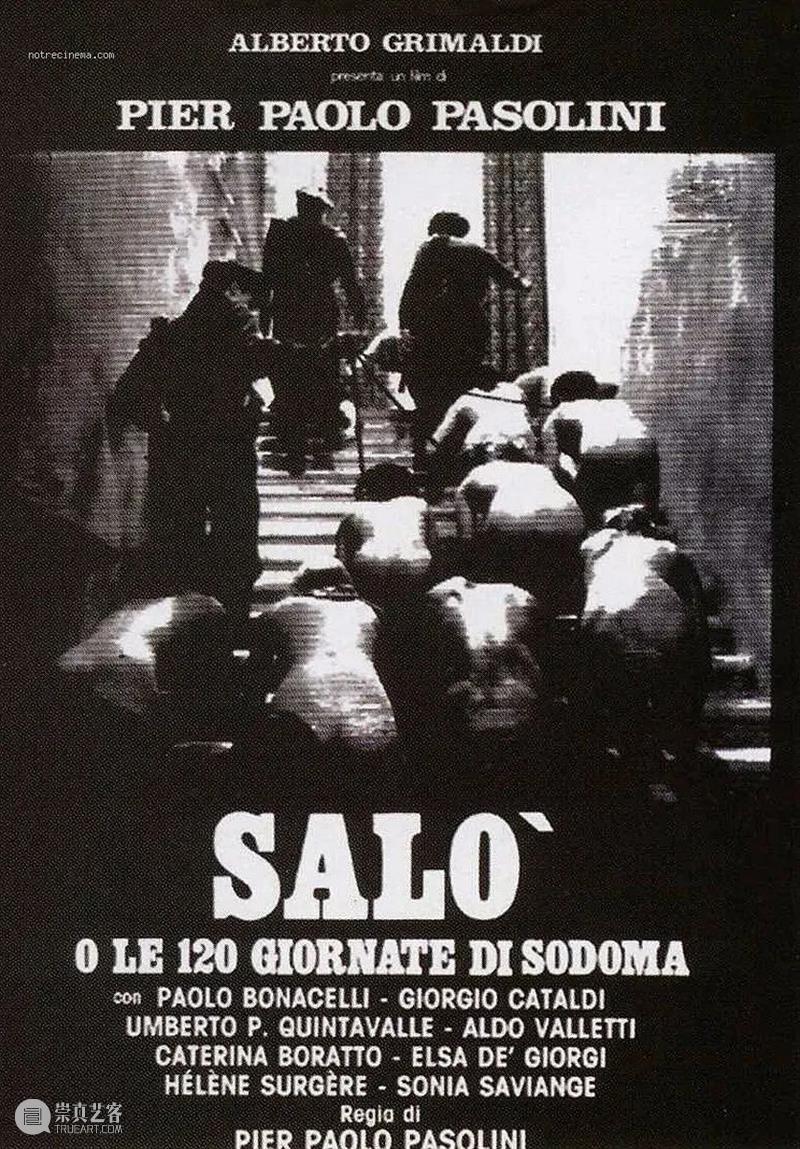
萨德 作品《索多玛120天》
Q:斯多葛主义为何是这个发展过程的重要部分?
A:像我刚才说的,福柯认为斯多葛主义是“自我伦理学”关键转折点:对于性行为和快感的运用来说,“行为”是伦理学的焦点。而在斯多葛主义和基督教中,“意图”和“欲望”成了我们与自我关系的焦点,成了一种释经学、禁欲主义的来源。
Q:除了性的领域,欲望还在哪里得到发展?您能不能进一步说说,欲望如何促进自由主义发展?
A: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我已经给了部分答案。接下来,我再补充一点。我的《欲望的治理》 一书的观点是,18-19世纪,西方社会的欲望概念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正好符合当时一系列话语的出现,以及某些场所和机构的变化。我不能说,这种分析已经是面面俱到的。但是,18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出现确实改造了欲望。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表示欲望是人性固有的、不可简化的维度,不可以无休止地压抑它。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把欲望翻译为新的概念,比如利益、利己、效用。政治经济学的论证是:对“利己”、“自私的欲望”(斯密语)进行治理而非压抑,不光实现了自我的福祉,而且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福祉。这种新的治理术,要求政府承担新的职能,市场变革为新的场所和机构,从而表达、实现自私的欲望。
与此类似,我想证明,19世纪的性类型学,甚至性学本身,都是自由主义的“罪与罚” 概念的一种替补(supplement)。“罪与罚”的概念,基于利益,动机,“理性的”欲望。人们把罪行依次归类为自然的本能、冲动导致的欲望,从而归类为各种各样的临床式、规范化的合理性:性行为归类为常规与反常两种类型,常规指的是生殖、异性恋、繁衍。违反常规的行为在临床上都是变态,会导致各种犯罪。虽然今天我们不再用单一规范定义性行为,可是,我认为,性行为依然是解读、分类、思考“我们是谁”的一个框架,同时也是建构自由主义的“自我”的关键机制。
除此之外,从卢梭、斯密、德国观念论,一直到最近(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的欲望),哲学本身把欲望解读为承认——承认自我,内在价值,认同,存在方式——的欲望。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第一种解读(康德、卢梭、黑格尔)关注的是尊重和尊严的价值,从而促进了宪法和国际法的发展。第二种解读是更加象征性的,推动了围绕空间、纪念物、语言结构、文化表征的合法性的斗争。许多人把后一种解读同差异政治联系起来,从而让它具备了某种自由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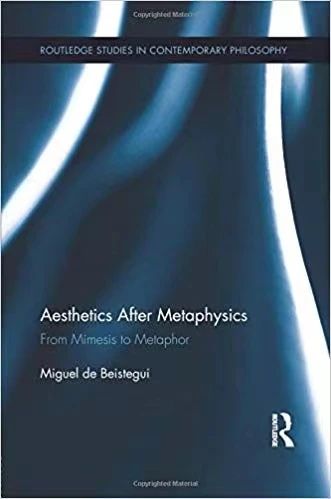
Q:《欲望的治理》与您过去的思考有关。在《形而上学之后的美学》中,您提出的问题是:“隐喻的欲望”从何而来?而且,您说明了美学如何借助隐喻克服旧的“摹仿”范式。我想,可以请您谈谈这一议题。隐喻是什么?隐喻与摹仿的差异是什么?
A:很高兴你注意到两本书的联系。起初,这两本书以系统性的方式联系在我的脑海中。它们都来源于《真理与起源:哲学作为差异本体论》一书。《真理与起源》的目的是,在海德格尔和德勒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差异本体论。不过,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因为《形而上学之后的美学》同样来源于《作为哲学家的普鲁斯特》一书。归根到底,《作为哲学家的普鲁斯特》和《形而上学之后的美学》的主张是:隐喻是本体论差异在美学上的等价物(当时我还想证明,欲望是差异在伦理学上的等价物)。由于diapherein与metapherein有某种密切关系,所以,我想在《形而上学之后的美学》中用一些例子来证明。
第一步,我首先说明,美学和诗学,在悠久的历史上,没有真正质疑亚里士多德(基于类比本体论的)对隐喻的解读,从而没有公正地看待隐喻的现实及快感。可是,从作家、诗人对隐喻的言论(普鲁斯特、荷尔德林、曼德尔斯塔姆、克洛岱尔、圣奥宾)中 ,我们看到截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究其原因,作家和诗人不用背负形而上学的包袱,而该包袱重重压在思想家身上(甚至包括海德格尔,德勒兹与加塔利)。
你正确地指出,《形而上学之后的美学》主张,哲学对艺术、文学、隐喻的处理采取了摹仿范式。这种范式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产生了象征、寓言,等等。假如我们用非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解读隐喻——不借助某种独立于隐喻的类比结构,不把隐喻翻译为其他术语——那么,隐喻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摆脱了摹仿范式。那么,隐喻如何摆脱摹仿范式?我认为,就像普鲁斯特所说,隐喻是在他物身上发现此物之美的能力。更准确地说,隐喻是把美视为发现美的能力的结果。在他物身上发现此物之美,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从日常角度看待此物,而要从隐藏的、奇异的角度看待此物,让此物与他物相联,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显示了现实的不同秩序、不同维度。在我看来,我们体验到快感,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一个隐藏的世界存在于日常生活的表层之下。在这个世界里,常规情况下互不相联的人、事、物,从不一样的角度(立体的,而非平面的)看,竟然互相关联起来。与此同时,这意味着,我们的时空体验,以及这种体验的性质,远远不像康德想的那样局限。
Q:您在书里讨论了“高感性领域”。您能展开谈谈吗?它对隐喻有什么作用?
A:我所谓的高感性领域,是脱离可感物/可知物这一(形而上学)图示的一个维度。在哲学史上,大多数学者都借助可感物/可知物这一图示,来思考艺术的意义与价值。高感性领域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可感物,隐喻可以在其中找到存在的理由,同时打开这种可感物。这种可感物,不需要可知物(概念、理念)的中介,就能够在哲学上生效。这种特性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说明隐喻与高感性领域有很强的本体论联系。当然了,这不意味着,我们把概念和思想排除在过程之外,排除在超感性领域之外。这不意味着,概念只产生一种低级、庸俗的经验主义。概念必须从高感性领域内部产生,而且只能在摆脱ontotautology of metaphysics之后产生。正因为如此,隐喻与概念有紧密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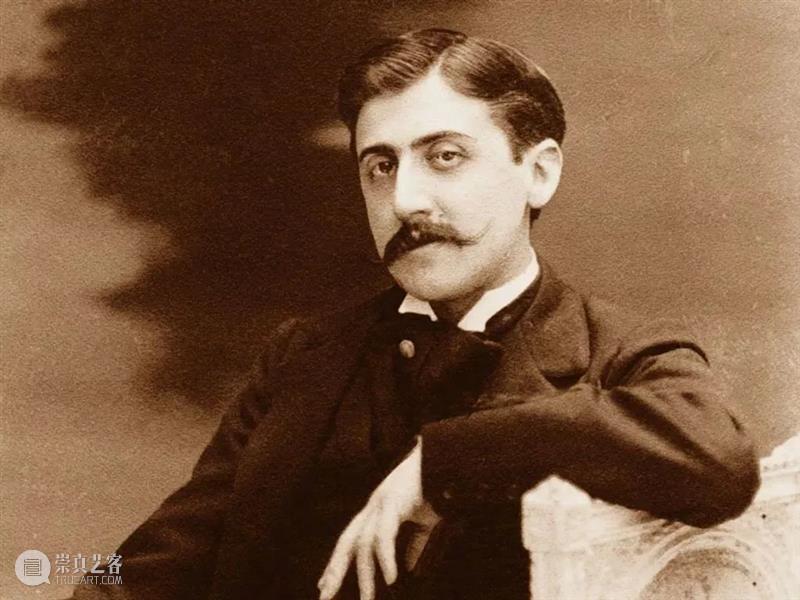
普鲁斯特
Q:隐喻为何如此可贵?
A:隐喻之所以是可贵的,是因为它需要一种与众不同、非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它不来自柏拉图的Idea或 eidos,而是奇异的点和关联的差异本体论。而且,隐喻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学。它不来自摹仿范式,不来自可感物,而来自高感性领域。正因为如此,我遵循康德的用法,认为隐喻是对超感性领域的“图示”或“生动描绘”。而转喻、寓言、象征,都是在摹仿范式中发展起来的。而我所要克服的,正是摹仿范式。转喻、寓言、象征,都是为了让感性之上的理念或意义获得感性表现。我在《形而上学之后的美学》考察了寓言在新古典主义艺术中的作用,以及象征在浪漫主义艺术中的作用,从而把它们与德库宁、奇利达等人的隐喻艺术进行比较。
Q:您认为普鲁斯特不是斯多葛主义者或叔本华主义者——虽然许多人认为他的作品说明生活多么糟糕。那么,从作为哲学家的普鲁斯特那里,我们能学到什么?借助隐喻,我们在普鲁斯特那里看到的,不再是“对时间(痛苦和怨恨的来源)的憎恨”?
A:我认为,《追忆似水年华》包括了一种叔本华的情绪,这种情绪贯穿了《追忆似水年华》,学者们已经讨论得很多。我所强调的是,小说的叙述者(以及斯万)对他发现的地点和人物感到失望。这些地点和人物不符合他丰富的想象力,不符合他阅读的书籍,不符合欲望生命的性质。在我看来,《追忆似水年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克服书中的生活?我们如何避免虚无主义?普鲁斯特的答案是:通过艺术。前提条件是,我们不能把艺术视为一种现实主义(摹仿)、寓言,而是把艺术视为这样一种经验——高感性领域的经验——其典范就是“非意愿记忆”。在时间上,这种经验脱离了单调的年代学。在空间上,这种经验脱离了生活经验的日常分配。小说的叙述者之所以获得快感,是因为他意识到,这种经验是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是不在场的纯粹过去,是无法简化为日常平面空间的纯粹空间。这样一种经验,才是文学的实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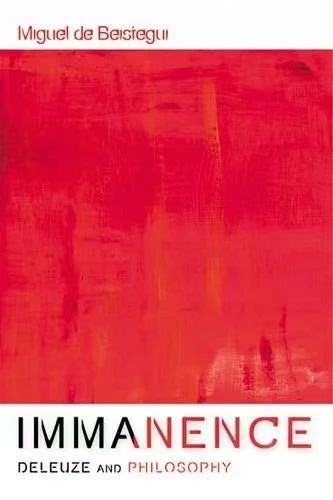
Q:您对德勒兹研究已久。我觉得他很难懂,常常会让人沮丧。很多人说,他的思想是有力、深刻、革命性的。我怀疑,是我没把握他的内涵。您在《内在性:德勒兹与哲学》中问道:“引导德勒兹思想的是什么?”您能不能简单回答一下?
A:要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概念的作用和意义的问题,回到德勒兹对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创造概念)。针对创造概念,德勒兹给出两个观点。第一,概念很难创造——像交响乐、绘画一样难。我们不是仅仅下决心,然后凭空创造概念。概念必须具备自身的必要性、紧迫性。第二,既然要创造概念,那么,概念肯定不是既定、现成的(知性的范畴,理念)我们要把概念生产出来。可是,为什么呢?概念要在“难题”(problems)的压力之下产生。难题不断产生、发展、演变,从而迫使思想消除惯性,消除麻木。难题在思想中引发一种冲击、暴力、危机,就像库恩所谓的科学概念构造的危机,或者马拉美所谓的诗歌的危机。
难题是真实的:它们可能是是物理的、生物的、社会的、艺术的。而难题的解决方案是先验的,截然不同于难题本身。眼睛截然不同于它所解决的光线难题,肥皂泡截然不同于它所解决的能源效率难题,绘画截然不同于它所解决的线条和色彩难题。与此类似,哲学概念截然不同于难题。举个例子:柏拉图的“理念”。虽然柏拉图拼命证明,理念与它所阐释的各种现象(美、公正,等等)有摹仿关系,可是,德勒兹认为,理念这一形而上学概念,是为了解决另一个难题:谁有资格谈论美与公正?谁有资格管理新建立的雅典民主制?
在我看来,德勒兹的做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改造了先验哲学的性质(参考了迈蒙对康德的批判):假如先验之物与经验之物有相似、摹仿关系,同时先验之物又归属于某个特殊的存在者(主体、意识、此在),那么,哲学始终不过是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一种认同(recognition)。
Q:您说过,作为德勒兹主线的“内在性”是矛盾的、问题重重的。您能不能试着澄清一下该术语?它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德勒兹的哲学?它为何如此难以把握?为什么我们很难澄清它?我甚至不禁奇怪,这样一个抵抗哲学思考的术语,为何在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A:归根到底,我认为“内在性”、“内在性平面”是“先验领域”的另一种说法,同时也是“先验经验主义”的基础。内在性平面或先验领域,是产生独特的、成形的(物理、文化、社会)现象的一系列前提条件。它是产生难题的场所。它是真实的,却是非现实的(潜在的)。可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前提条件指的不是主体性领域。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对先验之物的解读截然不同于康德或现象学。把先验之物变为主体性(先验之物的主体化),恰恰背叛了内在性,从而把超越性再次铭刻在内在性之中。于是,它也就背叛了哲学本身,因为“内在性是一块烫手的试金石,任何哲学都必须接受它的检验”。内在性正是哲学区别于宗教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德勒兹严厉批判康德:他发现了先验之物,却把它归属于另一种超越性——主体。弗洛伊德同样如此:他发现了无意识,发现了欲望的先验结构,却把它归属于俄狄浦斯情结,归属于家庭三元结构(顶点无疑是父亲)。真正的先验之物不是以经验之物为模板,而是(在现实化、差异化的过程中)产生经验之物。内在性之所以很难把握,是因为它是一切概念的可能性条件,是哲学的视野。内在性产生概念。对特定的难题(理念)来说,这些概念始终是当时、当地的解决方案。因此,内在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滋养一切概念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我们很难提出统一的“内在性”概念。一切概念都照亮内在性,像萤火虫一样环绕着内在性,却没有哪个概念能涵盖内在性本身。我不知道,这样能否回答你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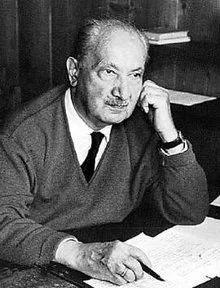
海德格尔
Q:您刚才说的,让人想到海德格尔。他提出思想起源的问题,而且认为我们的时代是最缺乏哲学的时代。您能不能谈谈,海德格尔如何看待当时的哲学?德勒兹是否同意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当前的哲学处于危机之中?
A:德勒兹不喜欢“危机”之类的词,它会让人想起所谓“哲学的黄金时代”。不过说到思想起源,他确实喜欢引用海德格尔的《什么叫思想》:“这个最可思虑者就是我们尚未思想。”海德格尔所谓的“尚未”,说明思想不是我们的能力、意志的范围内的事(像我刚才说的,思想是非意愿的)。思想不是仅仅下决心,不是仅仅按下按钮,像笛卡儿所想的那样:我们不具备这种天生的与真理的联系。与此相反,思想来自外部,来自这个世界,来自一种冲击和暴力。我们是被迫去思想的。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力量是存在的力量,它在技术时代遭到遮蔽和压抑,因为世上充斥着人类的权力意志和支配意志。不过,海德格尔同样认为,技术提供了思想的食粮。面对技术所导致的抛弃感、紧迫感、全球危机、荒凉,我们应该对技术进行思考。德勒兹没有对思想进行历史性的解读。不过,他做了类似的尝试:他认为,思想的可能性不在现成的概念和理念中,而在难题中。难题是多种多样的,能够促使人们创造概念,创造函项(functions)、感知物(percepts)、情感(affects)。思想向来是罕见的,困难的,并且将会一直如此。
Q:最后,请您为本杂志的读者推荐五本书(除了您自己的书)。
A:我一直在阅读并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书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德勒兹《差异与重复》、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但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读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政治神学论》,而且越来越被它们吸引。最后,我想提一下福柯的短文《什么是批判?》,这是我当前研究危机和批判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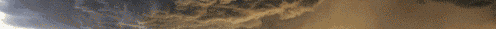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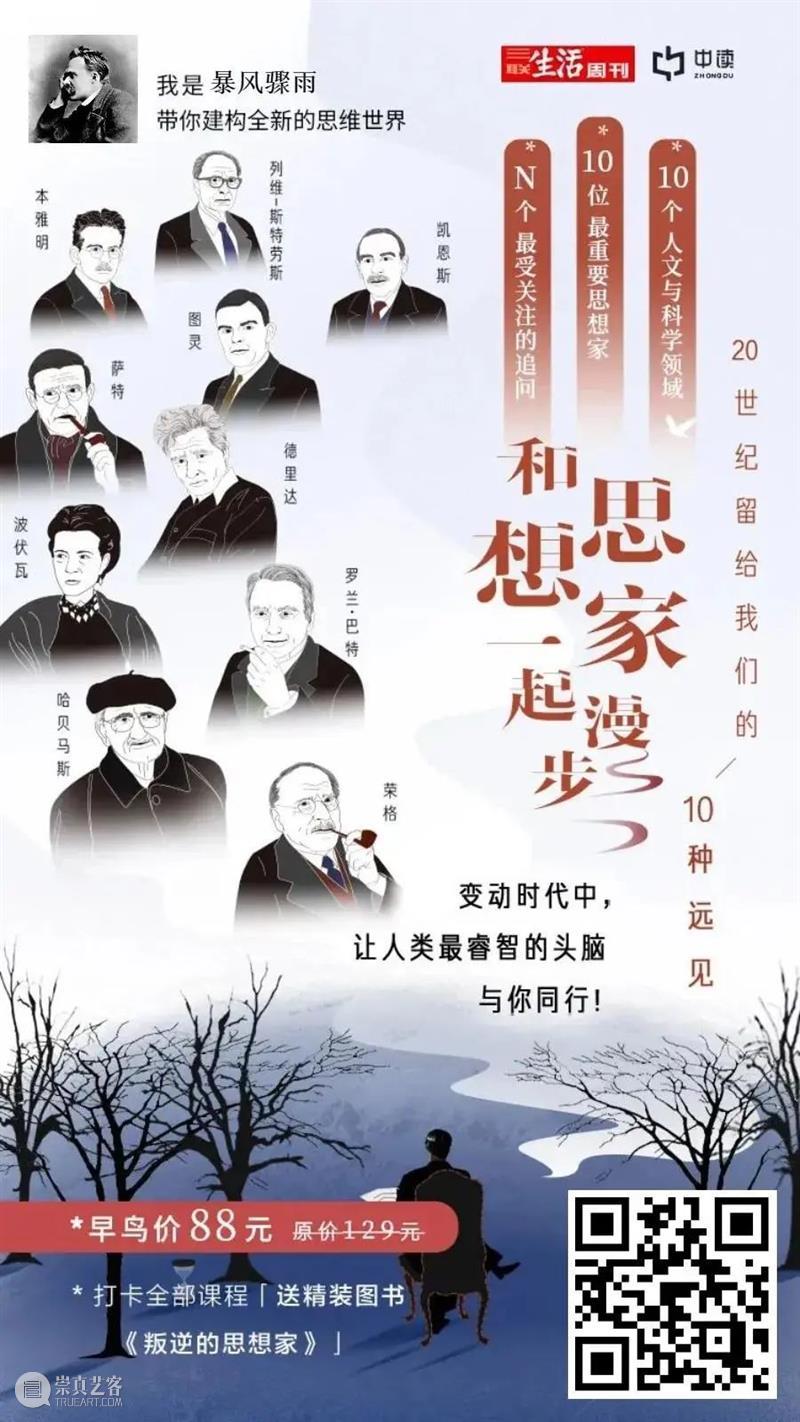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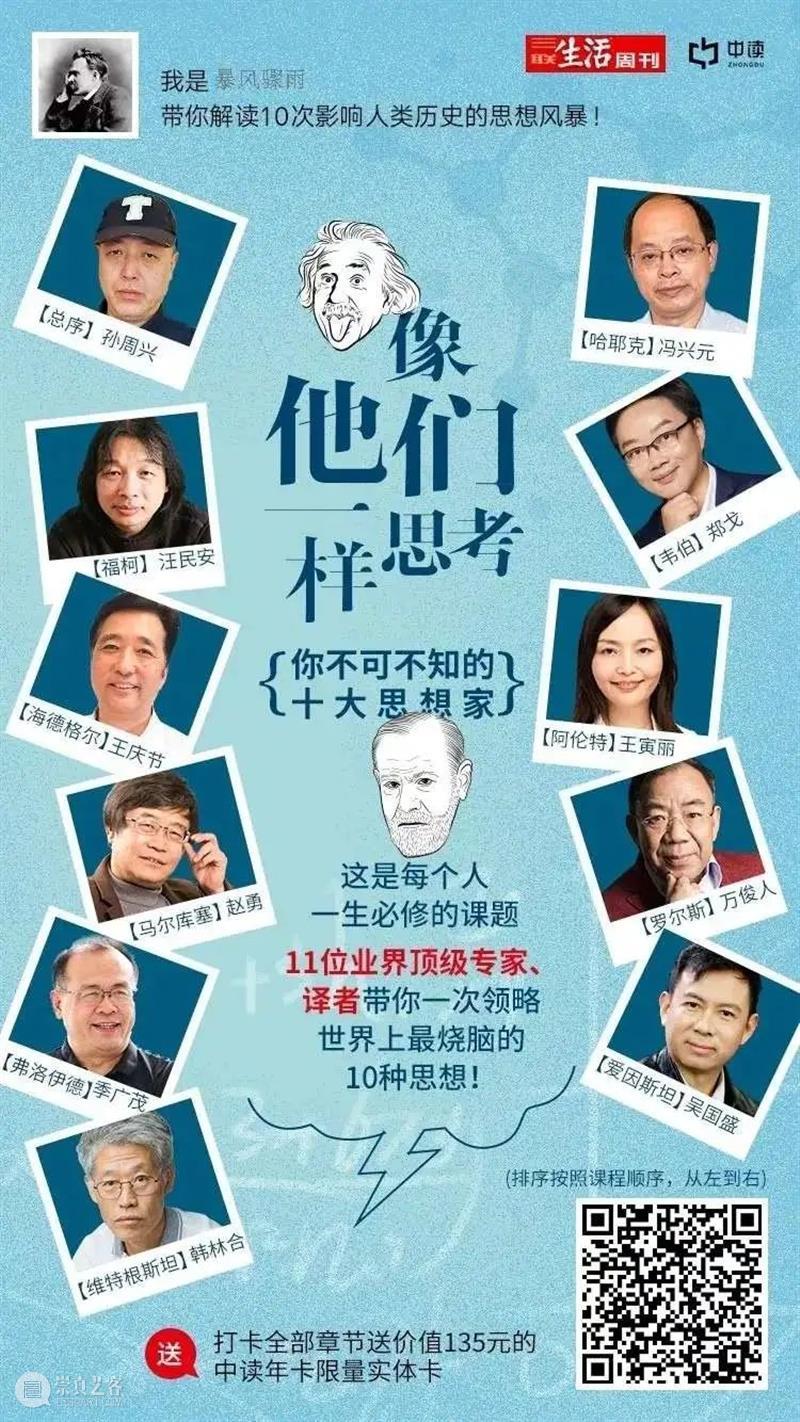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