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无言—— 瞿小松对话哲学家(上)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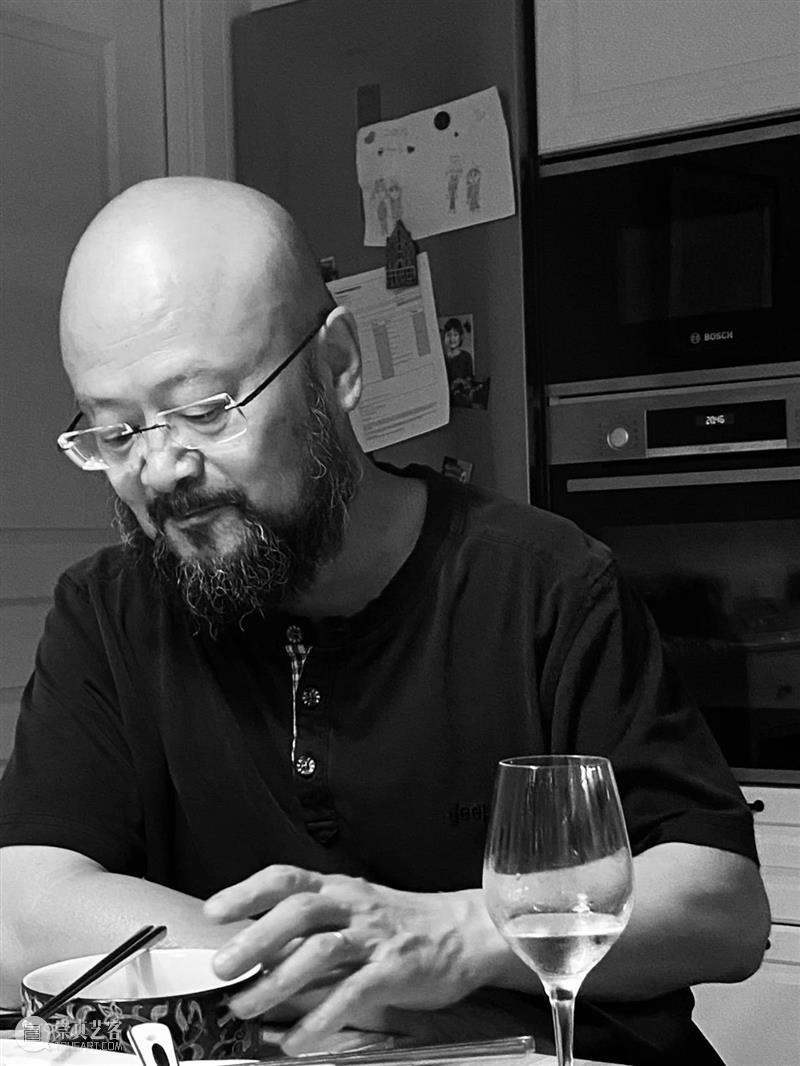
各位好!今天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外国研究所,和今日美术馆合办的百科哲学沙龙第二次,话题是“哲学对话音乐”。我们所里有一些做哲学的同事,希望能够与做音乐的艺术家,聊一聊音乐是什么。我们请来了作曲家瞿小松先生,他会给我们做主题报告。之后我们大家从当代音乐角度、现代音乐角度、哲学角度互相提一点问题。接下来我介绍哲学所的几个人:尚杰老师是做法国哲学的,他是我们所里的头。李剑是做英美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李河老师是《世界哲学》的主编,做阐释学,也做英美哲学、政治哲学。 好了,我想现在我们能准备的是沉默,或者准备好我们的耳朵洗耳恭听。我没什么主题发言,想把时间留给音乐。王歌给我三十分钟,我打算读一篇短文《我的灵魂之友才让旦》,争取十分钟以内完成。然后我们听音乐。“若干年前,一位北京的摄影家在甘南藏区遇见了才让旦,喜欢他的歌声,也告诉他,他这么年轻,应该到民族大学深造。好心的摄影家凑足了学费、路费,才让旦到了北京,进入中央民族大学。上了两节课,才让旦讲,我不知道这些老师教什么,也不知道这些老师要什么,但是我知道,好的音乐在我的家乡。才让旦离开了北京,回到家乡,继续他原本的人生路,在自己民族难以言说的美妙音乐里头继续他真正意义的深造。不认同学院座标,不愿被学院体系改造,清醒重返自己的传统深入学、习、承传,我觉得才让旦的天性,独立、自然,柔软而强大,少有的与众不同。才让旦讲,在藏区有很多非常独特、非常有意思的音乐面临失传。他焦急,他要学它们,他要唱它们,他要承传它们,因为他深爱他们。”关于“承传”这个说法,我想稍加说明。我们以往习惯用“传承”,事实上,对于传统,我们必须先将它承接下来,才能往下传递,所以我以为“承传”更为贴切。“在那片广袤的世界屋脊,在草原,在深山,才让旦遍访民间高人,以他令人无法拒绝的真诚,帮他们耕地,为他们干活,以他的真心,学习并承传那片令人神往的高原代代口传心授的天籁之音 —— 藏民族独有的天籁之音。”王歌给我的电子邮件里头说,今天的主题是“人籁、地籁、天籁”,去年秋天我写下这个“天籁之音”,也算是个缘分。才让旦的歌,天、地、人,都有了。乔美仁波切是一位年轻的活佛,是我的上师。五年前的一天,他把才让旦带来我家,我们一家对仁波切心存感激。“我有一个很好的铜磬,藏区叫‘静心碗’,当我轻轻地摩擦铜磬的边缘,无中生有的静心之音悄然飘散。一直没言声的才让旦,天然素淡的藏族歌手才让旦,在隐隐漫溢的静心之音中轻声开唱。在他不期而至的歌声里,我被洗净了,清洁了。安宁流遍我的身心,我感到通身透明。那是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我记得那天他唱的是观音菩萨六字大明咒。观音菩萨的加持,不着痕迹将我们的心融合。此后,才让旦每年都会从藏区来京城看望我与我的家人,以他那颗珍贵的真心,将佛菩萨的慈悲用他难以言表的歌声,清洗我们身处城市的杂染。才让旦讲话很少,但我们并不因之遗憾,因为让我们心意相通的,无需言说,不被言说。几年前,才让旦落脚云南北部的香格里拉。他租了一所房屋,用以囤积他以步代车丈量大地采集来的藏族原声音乐。每到夜晚,才让旦点燃酥油灯,轻敲法铃。夜空中铃声飘荡,深幽清澈,才让旦以他悠扬的嗓音,安宁地吟唱佛与菩萨的祝福。来听唱的,三教九流,白道黑道,有当官的,有平民百姓,也时有强人。进屋的姿态有傲慢,有谦恭,有强横,有柔顺,临走都平顺宁和,无语寂然。”他讲,有一次来了一个黑道,搬一大箱啤酒,进门把脚往桌上一架,旁若无人,说,唱吧。以前才让旦遇见这样的事,心里会不舒服。现在不一样,没有不舒服,因为来听唱的都是众生,没有差别。他安静地唱,那人不知不觉把脚放下,轻声叫随从将酒撤走。之后,这人时常带人来听。也有政府官员,进得门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才让旦依旧安静地唱。听着才让旦的歌,官员们渐渐平顺,离去的时候,都不言声,一个一个,安安静静出门。“北京有朋友想帮才让旦‘做大’,才让旦讲:‘不要大。我安安静静地唱,有人安安静静地听,我的心愿就满足了。’今年初春一个雨天,才让旦在北京一个四合院唱给几位朋友。雨声安静地滴落,才让旦安静地吟唱。之后他告诉我,这是他第一次倾听来自天地的伴奏。他的心融化在安宁的雨声。歌声渐轻,他慢慢将自己的声音隐去,四座清宁,屋外,满园雨落芭蕉 …… ”他讲,听到雨声,感觉美好。从来没有听到这么好的、来自大自然的伴奏。他希望在座的人也能听到天籁,听到自然的声音,所以就停了下来。“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友人,才让旦在一旁轻声提醒,说,那是今年北京的第一场雨。听过才让旦的,不被触动的少,其中也有不少朋友,操心他的前途。我想才让旦自己清楚自己。他说过去来北京,觉得北京太燥乱,总巴望早早回归他宁静的香格里拉。近年却有不同的感觉。他说北京的燥乱反而成了他修行的助缘,他有了不同于、以致胜于身处寺院的感觉。也是最近,才让旦皈依了乔美仁波切。仁波切为他剃掉了一头长发。他说,仁波切帮他揭掉了头上压了三十多年的烦恼,他感到浑身轻松,通体清净。我有一个体会,其实才让旦自己的天性,远比身处尘世而历经杂染的我们大家,清明,强大。前不久,美国斯坦福大学办了一个亚洲传统音乐节,邀请世界各地上了年纪富有经验并且名扬一方的民间高手,也请了年轻的才让旦。他刚刚回来,路过北京,我正好借这个机会请他来唱给大家。开唱之前我想多说几句。以佛家的说法,凡是以善良的心愿做的事情,都有功德。借今天的机会,哪怕有些微的功德,我们希望把这个功德送给日本和云南正在遭受大地震的所有众生,回向给所有遭难和没遭难的众生。我刚才唱的第一个是四皈依,大家都知道四皈依,它是用印度的梵文唱的。后来是六字真言,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最后这个曲子是莲师心咒。我们每天所作所为都是按自己的心态。我今天也是发自内心,这一刹那希望能给各位带来平静和喜悦,也是真正内心祈祷这次灾难的每个人。前几天我在从深圳到北京的火车上,一直观想这次日本的自然灾难,得到的恐惧是如果我这一刹那死了 …… 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火车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又吃又喝,聊的都是买房子、买车啊这样的话题。如果我们真正经历过猛烈的自然灾难,别提房子,能生存下来就不容易。生和死,一晃就转换了,真的是无常。大家都工作在城市,每天比较忙乱,比较迷茫。我刚到城市,也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与自己从小的经历有关,没有安全感。现在我能感觉到,学会自己的心,学会每天观察自己的心态,非常重要。心是一刹那、一秒钟或者几秒钟想很多事情。我平时压住自己的心态,唸唸经,唱些平静的曲调,把自己心里的想法慢慢压住,以后就越来越简单。我每天只要活着,能吃饱,就够了。能把这些山区的音乐,老人们好的曲目留下来,这就是目前我想做的事。别的事我也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也没有想过。每次在这种小聚会,我都用心去唱。谢谢大家。才让旦刚才讲了,他唱的第一个叫“四皈依”,用的是梵语:“纳摩古鲁呗,纳摩布达雅,纳摩达玛雅,纳摩桑伽雅”。“纳摩”的意思是顶礼、皈依,过去汉语译为“南无”;“古鲁”是上师。藏传佛教系统里头,上师很重要,是佛法修行的关键领路人。合格的上师,会从深层影响行者终生的修持;“布达”是佛陀;“达玛”是佛法;“桑伽”是僧。这个“四皈依”,心是根本。以心皈依心,以心观心,以心印心,我体会是四皈依的精要。第二个唱的是观音菩萨六字真言。这在藏区,无论老小,几乎人人都会。乔美仁波切讲,观音菩萨象征慈悲。“观音”、“观世音”、“观自在”等等,这位大菩萨有十多个不同的称谓,称谓虽然多,却都源于慈悲。观音菩萨的形象,有男有女,也是为了顺应众生的心愿。形象虽然不同,慈悲的心却没有差异。再下来唱的叫莲师心咒。“莲师”指莲花生大师(660—804)。佛教在藏区稳固立足,莲花生大师是非常关键的人物。这里“大师”两个字,不同于平常大家随口的称呼,比如“电影大师”、“文学大师”、“音乐大师”、“陶艺大师”等等。佛家说的大师,专指德高望重,并能真实引导众生的得道高僧。从文化上看,藏传佛教的音乐很特别。在藏区,寺庙里的音乐和其它音乐不一样,是独立的一套系统。喇嘛的诵经以及大法号,在座各位可能听过,外加一整套仪轨、法器、乐器,寺院专有。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讲,藏传佛教音乐是不受世俗音乐影响的一个门类,是纯粹意义的宗教音乐。而佛教的精神、内容,反过来影响民间音乐,反过来影响民间歌曲。比如才让旦是个真正的民间歌手,他唱的歌,旋律有民间的,也有他自己的即兴,非常动听。他的即兴,其实就是民间传统的创作,是民间传统的承与传及其流变,是民间传统生命的自然延伸。而内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歌词来自佛教经文,或者民间生活化了的佛法智慧。才让旦用的乐器,也很有来头,每次起头,他都会轻敲它们,唸一些经,然后开唱。才让旦,你能不能跟大家讲讲你的乐器?这是Ta,是鼓神的意思,祭祀时候用的。刚才有位朋友说萨满有,肯定有,印第安人也用,这是青海的做工。有机会大家一定去感受一下每年藏历六月,神降临到人身体上的一种特别的舞。他降到特选的人身上,会讲出一些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比如今年有些什么自然灾难,农民要怎样做田地才能避开冰雹,等等。他也会说出村子里所有发生的事情。比如年轻人偷东西,他会知道偷的过程是怎样的,会罚这个年轻人,罚他敬酒(这个神特别爱喝酒),然后用棍子打他。我见过这个场面,很有意思的。他会做些常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一般人喝白酒,不知道谁能喝四五斤。被这个神降身的跳舞的人,能喝五六斤白酒,滚烫的油里他能抓东西,能吃树皮。这个鼓就是这类跳神时候用的的鼓。有这个鼓和没有鼓感觉不一样。现在的北京气候不是特别好。夏天刚下完雨,鼓的声音会非常非常好听,今天有点太干了,我也没有怎么敲。还有这个金属的法器,是母亲留给我的,我从小就带着,但是以前没有用过。在香格里拉,我的邻居有一个二百三十年的房子,过去是家庙,文革破坏了,但主体没有被破坏,非常好的一座老房子。2004年有一天晚上,我在那里,按过去传统的方式点火,突然想敲这个。从那天开始,我每次唱歌之前都会敲这个法铃。我是一个民间歌手,所以民间的歌我一直在唱。佛教音乐方面的,从那天开始我跟着经文唱,也寻找很多寺庙喇嘛的唱诵,跟着去学。寺庙喇嘛有自己的规矩,我是符合音乐去唱,但是我的主体,根还是属于藏传佛教,只是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去唱而已。我有一个朋友,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专家,专门研究宗教音乐。他讲,民间的单面鼓基本上都是萨满教法器。不过,才让旦用这个鼓,并非出于宗教的原因,他实际上把它当做共鸣器、扬声器。今天这个场地非常干,他的嗓子也比较干。平时他的声音要润得多。才让旦,有朋友想请您唱一首山歌,或者牧歌,可以吗?我认为真正的声音是从心里传出来的,所以和嗓子干没有关系。心态非常重要,嗓子破了都没有关系。这几天我嗓子不舒服,但是我会用心去唱。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老家的牧歌,是刚刚下完雨之后彩虹出来,牧人特别喜欢唱的曲。以前我不会唱牧歌,后来跟着老人学,就会了。大家应该注意到了它有楼梯的层次感,很有意思。牧歌和住的地方肯定有关系。四川的嘉荣也有藏族,他们住在山沟里,唱的牧歌是这样(演唱),声音是往上的。我们牧民在草原上,大家感受一下,(演唱),是往外走的。当时我跟老人们学四川嘉荣的声音,唱的时候用了这个鼓,有些老人不太高兴,认为这是跳神用的,不应该用来娱乐。我一直认为我没有娱乐,我把音乐当做我心目中的佛祖一样,非常神圣。如果用这个出什么意外,我也认了,因为我是真正通过它来传递爱的声音以及真正善的一面。我一直坚持用了五年,还是非常好。我们听到心灵的、宗教的、很出世的音乐,我不知道有没有语言表达上很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讨论。今天介绍了这么一个音乐,而且介绍的方式出乎我的意料。这个音乐听了以后很平静,大家感觉都是很类似的。当然,对我来说我就要考虑这样的平静是怎么带来的,对音乐来说这样的平静是怎么样带来的。除了心灵本身之外,包括环境、暗示性的环节、仪式性的要素、器具上的东西,非常独特的表现,这确实让我印象非常深。我再进一步想,今天我们讨论音乐并不是以哲学家迅速跳出来高开高去,并不完全是某一类。我们前段时间去过新疆,马上我们要去两趟西藏。我们确实认为在那个地方,谈现代性的生活,抛弃整个宗教生活方式,那个地方谈一切其它的东西都是很麻烦的。虽然我们不知道麻烦具体是什么,但会觉得很麻烦。另外一个问题与音乐有关,就是它的地域性。金岳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一个评论,他说现代数学你很难说有英国数学、法国数学、德国数学,但哲学确实可以说德国哲学、英国哲学,他说那话的意思是,哲学是地缘性的。西藏音乐本身,我们听过朱哲琴,现在又有一个叫萨顶顶。朱哲琴的《阿姐鼓》,还有萨顶顶唸经似的那个,网上可以听到。对这种灵性的东西,不知道瞿老师怎么评价?萨顶顶我没听过,我不会上网。《阿姐鼓》我听过,是因为《阿姐鼓》的音乐原创者是我的朋友,作曲家何训田先生。我喜欢何训田的作品,也喜欢《阿姐鼓》的音乐,但我不敢把它称为“西藏音乐”。何训田、朱哲琴,都是生活在现代都市里头的城市汉人。而才让旦,是一个生长在、并且生活在高原藏区的藏族人。他生长并且生活在他自己独一无二的传统里头。我想这是他们的第一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个根本的差别。这个根本的差别带来第二个不一样。对于有学院西式专业训练背景的作曲家何训田先生,西藏音乐是材料,不是本体。对于活跃于都市歌坛的歌手朱哲琴来讲,《阿姐鼓》只是她的一个时期,一段风格。而才让旦,我刚才讲过,他是个真正的民间歌手,他的歌,有民间的,也有他自己的即兴。他的即兴,本质上就是民间传统的创作,是民间传统的承与传及其流变,是民间传统生命的自然延伸。因而他的演唱,松弛,温和,从容,流畅,是一种真诚无华的流露,并不刻意追寻“风格”。他天然的根,是他自己的民族,崇尚自然并真真实实地敬畏自然的藏民族。更有一个不一样:佛教对于何训田、朱哲琴,是文化,是风格,是品味。对于才让旦,是灵魂的终极依托,是信仰。所以,如果说才让旦唱的是西藏音乐,我非但不会有半点疑问,反而会觉得,藏族人唱藏族音乐,是个自然的事,不需要特别标明。说何训田写的是西藏音乐、朱哲琴唱的是西藏音乐,却很奇怪。而且我猜想,他二人也不会同意这个说法。艺术家们看重的、强调的,是“我的独创”、“我的风格”,你把他归入不看重也不强调“我”与“独创”的大传统,他会觉得你低看了他。身在传统里头的民间歌手民间艺人,看重和尊敬的,是传统,不是他们自己,所以天生“低调”。“平常心”对于他们来讲,很平常,接近天性,不值得一说。我想这是另一个差别。这里我说这些差别,确实是在说差别,没有谁高谁低的意思。我对音乐是外行,不敢说话。艺术领域里,音乐的门槛是最高的,最抽象的,这点和数学、哲学可以相类比。我想谈谈刚才听到的歌。我的直接感受是听不懂,因为它没有歌词,相当于是一种很纯粹的东西。听不懂但是被感动了,听不懂又被感动这就违背我们的常识。我们日常交流用语言,我们听懂了才能被感动,听不懂怎么被感动呢?我认为这涉及到音乐的本性,音乐可能是纯粹性的东西,用纯粹性的声音来感动人。十九世纪奥地利的汉斯立克,音乐史家,他写过一本《音乐的美》,那本书写得很有哲学味。他说其实音乐可以唤起我们任意一种感情,这种感情是莫名其妙的。这位藏族歌手很深情地演唱,但每个人被唤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音乐不通过语言,直接进入心灵。这是直接感动我们的东西,这种情形是跟哲学冲突的。不但跟哲学冲突,而且跟一切用语言表达思想的学科都是冲突的,跟形像也是冲突的,所以这点非常神圣。 音乐的趋向越是接近心灵、越真实、越诚实,才能越感动我们。某种意义上音乐更神秘一点。说它神秘,往往有天赋、抽象、感性等等因素。有耳朵辨别能力的人能创造出美的音乐,很世俗、很算计的人可能就要差一些。这是谈我的一些感受。我们知道表达和表现,语言表达意思的功能和艺术的表现的区别我们基本了解。而且表现性的东西,要按叔本华讲的,世界是意志的表象。对尼采来说,音乐,特别是作为悲剧核心的音乐精神是意志本身。意志这种东西我们确实了解。本杰明提出一个问题:进入现代,艺术越来越进入都市化生活,越来越以复制为手段,以展示作为它的生存方式。这时候不同的展示性的东西就使它开始抽离,所以本原性的东西消失与它的灵性生活方式慢慢消失是相关的。瞿小松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要的音乐作品有歌剧《俄狄浦斯》《俄狄浦斯之死》《命若琴弦》及室内乐作品MENG DONG、《行草》等;已出版散文集《音乐闲话》《音声之道》《无门之门》等。
成蹊当代艺术中心主要致力于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研究,主张在整个文艺思潮下探讨当代艺术,挖掘和整理非官方当代艺术档案。试图从历史、社会、文学、艺术等多角度推进当代艺术,重建当代人文精神。
CHENG Xi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Beijing) upholds the belief “Independence of Spirit, Freedom of Thinking”. We are devoted to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d artistical researches and to promoting new art, new culture and new idea. We attempt to advance literature, art and history as an integral. We advocate discussing th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trend of literary thoughts, advancing the contemporary art from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and restoring the contemporary humanistic spirit. By means of exhibitions, academic exchanges, culture salons, experimental performances and publishing, we demonstrate and promote works and projects of academic values and with an experimental spirit, and help advance the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e through co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jects.
更多文章将陆续发布,敬请关注成蹊公众号
邮箱:chengxiart@163.com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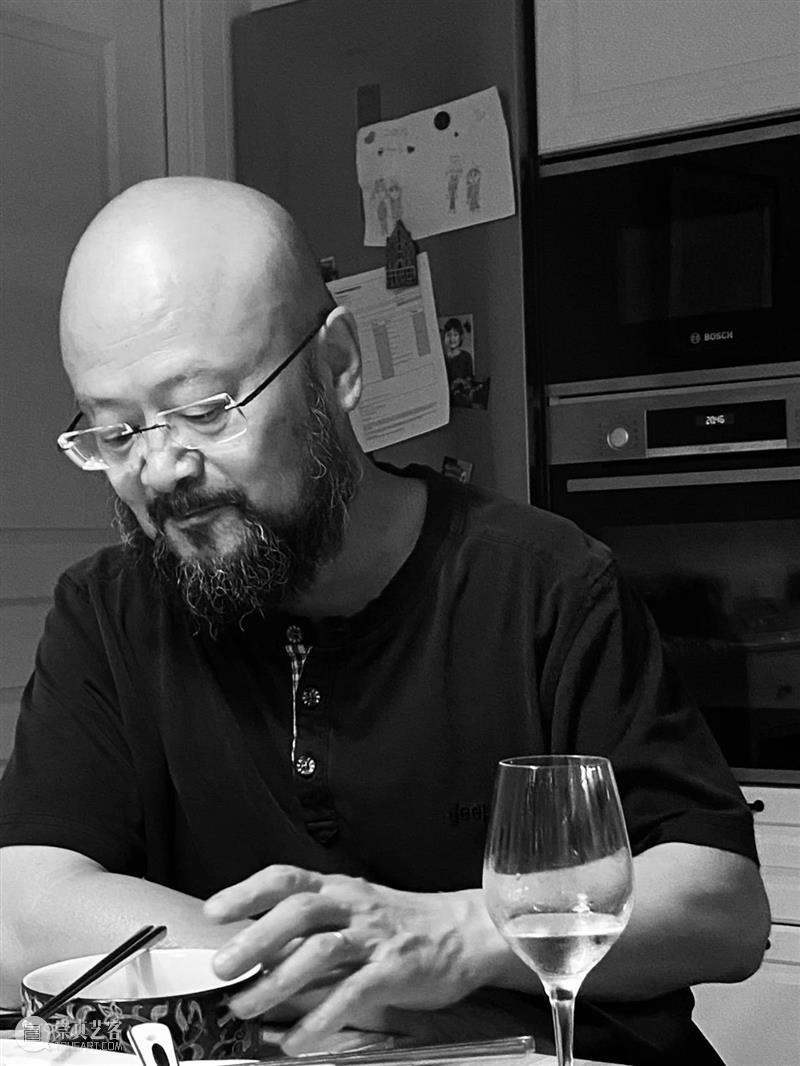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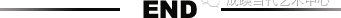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