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多伊格 Peter Doig:还原真实从不在我考虑范畴之内丨AMNUA艺术家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彼得·多伊格(Peter Doig),1959年4月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他是当今最有名的具象画家之一,自2002年以来就定居在特立尼达。2007年,他的画作《白色独木舟》在苏富比以113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创下了在世的欧洲艺术家拍卖纪录。2013年2月,他的画作《峡谷的建筑师之家》在伦敦拍卖会上以12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
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谈到他时说:“在21世纪流传于艺术的废话,冒名顶替,夸张的胡话和巨大的垃圾中,多伊格是一颗真正的想象力,真诚的工作和谦虚的创造力的一颗明珠。”
彼得·多伊格自幼便时常迁徙于不同国家城市间居住生活。1979-1980年移居伦敦,分别在温布尔登艺术学院和圣马丁艺术学院学习,并于1989-1990年在切尔西艺术学院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1989年,这位艺术家与他的朋友海顿·科塔姆(Haydn Cottam)在英国国家歌剧院兼职。他还曾在西班牙港口附近的加勒比当代艺术中心(Caribbean当代艺术中心)成立了工作室,自2002年起,定居于特立尼达,后也受邀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并时常往返于伦敦和纽约之间。
岛屿 2000-2001年 布面油画
77 x 91cm
青少年时,他其实对艺术并无没有浓厚的兴趣,直到1981年观赏了英国皇家学院《绘画新精神》一展后,才开始意识到内心对绘画艺术的渴望,他渴望成为一位艺术家,并享受当一名画家的生活。但那时代的青年艺术家们正在狂热追求各种新媒介、新观念的运用,他依旧专注于传统绘画,他说:我不追逐任何东西,绝对不是一个赶时髦的追逐者。
音乐街 2019 亚麻布油画
50 x 38 cm
在当代艺术界,极少有画家能像多伊格这样,既受到世界重量级收藏家的青睐,且影响力如此巨大。由1990年代至今20多年来,多伊格不但越来越受到学术与市场的双重重视,其创作的风格更是影响了一批批的新生代艺术家。很多欧美、日本甚至许多华人新生代、新锐艺术家,都受其风格影响,不时有“借鉴”手法的作品问世,在市场上广受欢迎。2017年,多伊格还成为白教堂画廊「艺术偶像奖」的得主。
狮子在路上 2019 亚麻布油画
200 x 300 cm
多伊格1980年代后期开始,独创了一种画面令人魅惑、神秘的景物画,画面以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进行构图编排,有一种梦幻般的叙事性,似乎隐藏着某种象征意义和潜意识的呈现,深深吸引了大批观众。这种集多样复杂元素并成功揉合于同一件作品中创新,是多伊格与其它艺术家重要区别。
鹈鹕 2003年 画布油画
276 x 200. 5cm
法国杂志《PURPLE》的记者Parinaz Mogadassi在2011年4月对他进行了一次全面访谈,在谈话中彼得·多伊格回忆了他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脉络,也谈及了一些与艺术“无关”的趣事。Parinaz Mogadassi= P. A:你的童年很大一部分是在到处迁徙中度过的,因此你现在的口音几乎微乎其微。Peter Doig= P.D : 我出生在苏格兰,18个月大的时候离开。从7岁到19岁我生活在加拿大,这个国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我们不是典型的加拿大家庭——不去露营、划独木舟、或者做类似的活动。但是我自己很喜欢户外运动,也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外出,后来这些主题曾出现在我的作品中,但是是被改造过的。P.D:我的绘画从来不是从我的直接经验得来,而更多来自于想象空间。还原真实或现实从来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P.D:我那时对艺术并不感兴趣。小时候,我喜欢和朋友一起攀岩、滑雪、探险;14岁时,我爱上二手书籍、服饰和唱片;到了16岁,我有很多朋友没完成学业就离开了学校,因为外面的世界太诱人了,我就跑到加拿大草原上的钻井平台上去工作,晚上在酒店房间画点画,同时也想着是不是能干点别的。那时候在多伦多,朋克正在流行,今天似乎也没什么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的乐队年轻多了。P.D:我出生英国,在那儿上过三年学。在11岁的时候,我感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重返英国,似乎那里会发生更令人兴奋的事情。我觉得自己如果可以进入任何艺术学校,应该就是在伦敦。起初,伦敦看起来是如此的庞大、坚韧和艰难。幸运的是,我第一份工作是为小型音乐会卖杂志。我们会卖一些早期的卡带和地下杂,没有报酬但被允许自己分一些杂志出售。当时我们的工作的对象是Certain Ratio, Pop Group, Joy Division, The Slits,和Cabaret Voltaire.P.D:对,六个月后,我到了圣马丁艺术学院。它是个最令人兴奋的地方,有很好的教师团队,其他学生也才华横溢,在伦敦的艺术学校中间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圣马丁的时尚设计专业非常优秀,造型艺术也很有名。我打工时售卖的I-D杂志早期就是圣马丁的一个二年级学生Robin Derrick设计的。圣马丁周边的街道、俱乐部,都和学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实说,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和这个学校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是很多事情就是在我们身边、眼前、耳边快速地发生和展开的,有些萌芽开始成为流派:后朋克、新浪潮、新浪漫主义、早期的摇滚乐、嘻哈,这些风格在学校里混合共存着。也许是受早期的OFZG杂志影响,Rosetta Brooks 和 John Stezaker当时发起了一个阅读小组,里面的成员有时尚设计师、平面设计师、还有一些优秀的艺术家。John Galliano经常待在在绘画工作室,他是 David Harrison的好朋友,就跟Isaac Julien一样,他当时正在学习电影。绘画正在经历一个浪漫的阶段,有很多关于崇高与超越的讨论。Max Beckmann和Phillip Guston的影响就跟皮疹一样在画室里蔓延。1981年皇家学院举办的展览《一种绘画新精神》成为一道分水岭,介绍了很多艺术家:基弗,里希特,波尔克,巴塞利兹,施纳贝尔等等,再加上巴尔蒂斯,培根,霍克尼,沃霍尔,佛洛伊德,托姆布雷和德库宁,学生们的脑子都乱套了,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毫无章法可循。金匠学院,伦敦大学的分院之一,在Peckham路,与其它学校有点不太一样,。我甚至有点记不起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时候,在那儿遇到过什么人,但在这段时间里,来自那里的年轻艺术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圣马丁——不过是在时装和设计领域,不是在纯艺术方面。P.D : 到那儿以后,我才意识到艺术世界里自己最感兴趣的是绘画。圣马丁位于伦敦市中心,对于一个从异国他乡来的人来说,这一点还挺有吸引力的。当时我对这所学校辉煌的历史一无所知,尽管在参观它的时候感觉很好,还有点紧张,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接纳——这儿有那么多前卫的人,正在创造着那么前卫的艺术。纽约 29 x 41 cm 印度墨 纸上水彩 1980
P.A: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你开始去纽约旅行。在你早期的作品中,有很多美国的痕迹,作为一个在伦敦的学生,你对纽约有什么样的认识?P.D : 我是1979年搬到伦敦的,我一个加拿大的朋友托尼,则搬到了纽约下东区。从加拿大回来的最便宜的方式,是从纽约转机,我就会和托尼待上几天甚至几周。纽约发生的事情让我觉得很振奋,也许是因为我生长在北美,和纽约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伦敦经常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英国电视,音乐、幽默、政治、残酷的战争等等,至少在那些日子里,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在伦敦的美国人。我做的很多事跟美国艺术有关。我接触到早期的摄影艺术,像Jack Goldstein,Robert Longo,Cindy Sherman做的那种,在圣马丁是通过 Brooks 和 Stezaker,与早期的嘻哈有关的艺术,还有更多来自芝加哥的作品,像H.C.Westermann,Ed Paschke,Roger Brown和Neil Jenney。跟英国比起来,这一切似乎更加激动人心。当时没有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能在伦敦展出,纽约艺术有它的优势,而且在伦敦有一定的反响。在那些日子里,资讯传递得很慢,杂志实际上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传递思想和图像的工具。我觉得是时候了…180.3 x 238.3cm 1982–1983  汉堡王 196.3 x 120.6 cm 1984P.A : 当时有什么艺术家给你造成持久的印象吗?P.D:留下了持久的印象的往往是那些年长的,或已经过世的艺术家,比如已故的Guston,Max Beckmann的三联画,Joseph Cornell,Günter Brus,弗朗西斯·培根,Edward Burra,那不勒斯的绘画等等,这些都在80年代前期的伦敦展出过。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也对我有影响。巴斯奎特很有力度,尽管除了在伦敦的ICA,我没看到他的作品在任何画廊展出过;克莱门特早期在白教堂有一个很棒的展览,还有Julian Schnabel和Eric Fischl,另一个是Don Van Vliet在沃丁顿的展览,但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能量,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P.A:去年春天,杰夫昆斯在高古轩为Ed Paschke办了一场展览,你刚刚赞赏过Paschke 和Roger Brown。P.D : 我不知道昆斯组织了这么一个展览,但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知道他的一些作品研究和参考过H.C. Westermann。我喜欢 Westermann带着幽默感看待生活的主观方式,即便是他在面对悲剧的时候,比如他曾经历过的南太平洋海军的沉船事件。他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让纽约和伦敦的波普艺术家都为之臣服,另外我认为霍克尼的早期自传体式作品那时候也显示出天马行空般的魅力。在我刚到圣马丁的第一年,我看了两场大展:Roger Brown和H.C. Westermann。1980年之前我并不了解H.C. Westermann的作品,我特别喜欢他的草图,版画和有插图的信,我也很喜欢Roger Brown和Ed Paschke的作品,他们每个人对于主题的阐释有着截然不同的途径。 《 Ed Paschke》展览现场 纽约高古轩 2010年3-4月P.A : 昆斯是与Paschke一起做研究的,我想Paschke是他的导师之一。P.D : 如果Otto Dix是一个波普艺术家的话他可能有点像Paschke,但也许更超脱。我还说过Roger Brown处理景观的方法,他和Paschke两人都是解说性的,他们使用材料和操作图像的方法完全与他们的主题一致,也因此把他们推到了目前的风格样式上。J-print 63X84cm 纸版画 H.C.Westermann 1972 P.A : 你曾说过,Westermann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用在你身上其实也适用。人们也许并没意识到你的个性实际上很活泼好动——你最近的画中很好地体现了对滑雪和乒乓球的兴趣,在我们曾经延续了好几天的交谈中,你晚上钓鱼,清晨打网球,还打乒乓球,由于生活在特立尼达,游泳和海上活动也曾出现在你的作品当中——你工作室外的生活是不是和工作室中的时光一样重要?P.D :工作室之外的生活,有时还更重要一点。也不可能有其他方式,我的灵感总是从外面获取的,不是在工作室里做研究,但有很多艺术家是这么做的。P.A : 是你还是其他艺术家曾说过“成为艺术家不是一份工作”?P.D: Chris Ofili说的,当我对没有完成某些画作感到有点伤心的时候,这句话很好地鼓励了我。P.D:我赶上了原先听说过或读到过的电影。十几岁的时候,在多伦多我已经看过不少电影,尤其是那些特别经典的。但当时的伦敦的电影院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影片可供选择,从经典的黑色电影,意大利和德国电影,到Curt McDowell拍的片子都有。我们会去固定的几家电影院,比如从圣马丁出来那条路上的Scala。下午我们离开画室去Scala,看什么完全由放映员决定,Scala还有一个通宵酒吧,人们能在那聚会聊天,然后喝上两杯。我们在那里接收到很多资讯,听过各式各样的音乐,但总的来说有点慢,你必须还得买些来自纽约的音乐。我从DJ那里买过一些唱片,因为他们会时不时飞到纽约。由于唱片不够全面,我甚至还买了一个纽约无线电收音机。刚刚说过,年轻的艺术家在画廊里没有展出机会,只能去找一些可以替代画廊的空间,可能会是俱乐部或商店。在这些地方做展览没什么好丢人的,因为选择真的是太少了。我和一群伦敦艺术家曾在佛罗伦萨的一家商店里做了个展览,其中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伦敦的画廊对它们不感兴趣。
汉堡王 196.3 x 120.6 cm 1984P.A : 当时有什么艺术家给你造成持久的印象吗?P.D:留下了持久的印象的往往是那些年长的,或已经过世的艺术家,比如已故的Guston,Max Beckmann的三联画,Joseph Cornell,Günter Brus,弗朗西斯·培根,Edward Burra,那不勒斯的绘画等等,这些都在80年代前期的伦敦展出过。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也对我有影响。巴斯奎特很有力度,尽管除了在伦敦的ICA,我没看到他的作品在任何画廊展出过;克莱门特早期在白教堂有一个很棒的展览,还有Julian Schnabel和Eric Fischl,另一个是Don Van Vliet在沃丁顿的展览,但这些都是令人兴奋的能量,而不是留下深刻印象的艺术。P.A:去年春天,杰夫昆斯在高古轩为Ed Paschke办了一场展览,你刚刚赞赏过Paschke 和Roger Brown。P.D : 我不知道昆斯组织了这么一个展览,但它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知道他的一些作品研究和参考过H.C. Westermann。我喜欢 Westermann带着幽默感看待生活的主观方式,即便是他在面对悲剧的时候,比如他曾经历过的南太平洋海军的沉船事件。他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让纽约和伦敦的波普艺术家都为之臣服,另外我认为霍克尼的早期自传体式作品那时候也显示出天马行空般的魅力。在我刚到圣马丁的第一年,我看了两场大展:Roger Brown和H.C. Westermann。1980年之前我并不了解H.C. Westermann的作品,我特别喜欢他的草图,版画和有插图的信,我也很喜欢Roger Brown和Ed Paschke的作品,他们每个人对于主题的阐释有着截然不同的途径。 《 Ed Paschke》展览现场 纽约高古轩 2010年3-4月P.A : 昆斯是与Paschke一起做研究的,我想Paschke是他的导师之一。P.D : 如果Otto Dix是一个波普艺术家的话他可能有点像Paschke,但也许更超脱。我还说过Roger Brown处理景观的方法,他和Paschke两人都是解说性的,他们使用材料和操作图像的方法完全与他们的主题一致,也因此把他们推到了目前的风格样式上。J-print 63X84cm 纸版画 H.C.Westermann 1972 P.A : 你曾说过,Westermann的生活已经成为他作品的一部分,这种说法用在你身上其实也适用。人们也许并没意识到你的个性实际上很活泼好动——你最近的画中很好地体现了对滑雪和乒乓球的兴趣,在我们曾经延续了好几天的交谈中,你晚上钓鱼,清晨打网球,还打乒乓球,由于生活在特立尼达,游泳和海上活动也曾出现在你的作品当中——你工作室外的生活是不是和工作室中的时光一样重要?P.D :工作室之外的生活,有时还更重要一点。也不可能有其他方式,我的灵感总是从外面获取的,不是在工作室里做研究,但有很多艺术家是这么做的。P.A : 是你还是其他艺术家曾说过“成为艺术家不是一份工作”?P.D: Chris Ofili说的,当我对没有完成某些画作感到有点伤心的时候,这句话很好地鼓励了我。P.D:我赶上了原先听说过或读到过的电影。十几岁的时候,在多伦多我已经看过不少电影,尤其是那些特别经典的。但当时的伦敦的电影院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影片可供选择,从经典的黑色电影,意大利和德国电影,到Curt McDowell拍的片子都有。我们会去固定的几家电影院,比如从圣马丁出来那条路上的Scala。下午我们离开画室去Scala,看什么完全由放映员决定,Scala还有一个通宵酒吧,人们能在那聚会聊天,然后喝上两杯。我们在那里接收到很多资讯,听过各式各样的音乐,但总的来说有点慢,你必须还得买些来自纽约的音乐。我从DJ那里买过一些唱片,因为他们会时不时飞到纽约。由于唱片不够全面,我甚至还买了一个纽约无线电收音机。刚刚说过,年轻的艺术家在画廊里没有展出机会,只能去找一些可以替代画廊的空间,可能会是俱乐部或商店。在这些地方做展览没什么好丢人的,因为选择真的是太少了。我和一群伦敦艺术家曾在佛罗伦萨的一家商店里做了个展览,其中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伦敦的画廊对它们不感兴趣。位于伦敦 Pentonville 路275号的 Scala 电影院
P.D:我从没有想过我会用艺术谋生。我过去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是这么干的,没有先例。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廉租房里,靠打零工过活,大家荣辱与共,分享一切。我们进入俱乐部的时候从不付钱,知道哪里能买到廉价食品。我在圣马丁路的国家歌剧院当过七年服装师,夏天我在那里给芭蕾舞剧配备服装。那是一份很理想的工作,因为是夜班,有食堂,有酒吧,这些在那段日子里很重要。我可以白天画画,傍晚上班,我离开的时候,可能还有20个我的朋友和同学在那儿。在后台我认识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所有的人都把我们当艺术家看待,尽管我们很少在那里展示我们的作品。P.D:1987年我搬到蒙特利尔,然后在89年下半年回到伦敦,进入切尔西艺术学院。P.D:当我从蒙特利尔来到切尔西之后,发现自己几乎有点无法应对。我必须得付租金,有一份全职工作。绘画变得困难又新鲜,因为没有任何同伴。那段时间有点像流放,尽管当时我并不这样认为。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所做过的东西,并创作了一批新的作品--虽然当时我觉得它们没什么创造性。当我刚回伦敦进到切尔西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在一两个月后,情形变了,在蒙特利尔待过的两年半时间突然变得丰富起来。我是年纪最大的学生之——30岁——我认为自己也有从七年前的大学经验里受益。我真的不关心自己的作品否要迎合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别人那样。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的作品逐渐开始被其他学生所关注。P.A:如果其他学生没有理解你所试图传达的信息呢?P.D:我不确定他们是否理解我的作品,其实我自己也不一定理解。我在作品里放进了一些有时近乎禁忌的情感和主题,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也承认某些元素可能触碰了感伤的边缘。银河 152x203.5cm 布上油画 1989–1990搭便车的旅行者 152x226cm 麻布油画 1989–1990P.A:你是如何在作品中处理这些的?和主题有关吗?
P.D我开始使用应用材料,装饰性的图像和颜色,并参考过去的艺术家,比如克里姆特。一个好几年没看过我作品的老朋友,在切尔西看到我的展览时说,如果不是瞥见作者的名字,还以为这些画的作者是个女人。他这种说法不是出于轻视,而是真的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峡谷中的建筑师之家 200×250 cm 布面油画 1991P.D:在切尔西的学生作品展之后。这都归功于我上过的大学。可悲的是,在目前的系统内,过了30岁的人很少有被展示的机会,团体展览则提供了这样的机遇。被授予白教堂艺术家奖之后的那一年,我的新作品被安排在白教堂画廊的楼上展览,辛迪·舍曼的展览在楼下,我还记得我那些画还没有干透,装在一些廉价的装饰板里,从她作品的板条箱中间拖过。两年之后,转折才真正发生。《弗里兹》杂志的Gareth Jones 1992年写了关于我的一篇文章,然后把我放进他策划的一个节目里,那个节目里有Gavin Brown, Matthew Higgs, Hilary Lloyd, Martin Creed, Jeff Luke, 和the Wilson twins。除了我和Creed,其他人都是纽斯卡尔艺术学校毕业的。这是我第一个在画廊里做的展览,它一直激励着我,在这之前,说实话,我一直是个孤独的旅行者。路边房子 193×248.9cm 布面油画 1991P.A:没错,Gavin Brown是从那时候开始了他的艺术家生涯,也是从那时起,你开始到纽约和他一起办展吗?P.D:是的。Gavin来伦敦时会来工作室看我。起初他是在303画廊,后来开始在其他地方办展。他很想把我的作品拿到纽约去,但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弄过去,最后我自己做了一个板条箱,运了几件作品。P.A:你怎么看待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伦敦,YBAs,你是否认为伦敦艺术界的气候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纽约当时的艺术做得挺专业。P.D:YBAs让伦敦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很多画廊改变了他们原本的计划,放弃了原本的艺术家, 然后把一些新的、专业的概念带进他们的空间,很多新空间开张,艺术家们带着藏家到处参观其他的艺术空间。P.D:有一阵子,商业世界——那些销售艺术品的画廊,对我做的东西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情况有所改变是在我的东西出现在《弗里兹》之后,可能是杂志的内容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也得到了诸如Dinos 和 Jake Chapman这些朋友的支持,他们不怕讨论我的作品,其他人却觉得有点尴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关键,你要记住,因为这是Twin Peaks的时代,我经常被指责是把Twin Peaks(80年代英国的通俗连续剧)做成了画。P.A:《弗里兹》的文章发表在1992年,就在1994年,在你拿到MFA仅仅四年后,你又入围了特纳奖。一夕之间,对你作品的关注似乎开始暴涨,你怎么解释这一点,这几年里你是怎么过的?P.D: 在 Gareth的文章发表之后,事情很快发生了转变. Gordon VeneKlasen开始联系我,就像 Victoria Miro 和 Gavin Brown所做的那样.幸运的是,我在工作室悄悄做了很多作品,这是一件好事,现在我才意识到,挺少见的,我能一下子推出20件大尺寸的、已经完成的作品。 松树屋 180×230.5 cm 布面油画 1994Cobourg 3 + 1 More 200×250 cm 布面油画 1994P.A:人们认为你带来了绘画的复兴。在皇家学院的那份工作是怎么找到的?P.D:学生能邀请艺术家来工作室参观,Chris Ofili,我在切尔西艺术学院的旧相识,是他的邀请。当然,等我到了皇家学院之后他就不在那了,作为交换他去了柏林,在那之后,学校请我每周去一天,就这样我干了很多年。我不喜欢“教学者”这个词儿,因为我认为没人能“教”艺术,我喜欢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待着,在作品还在创作期的时候讨论它们,气氛美好而特别。P.A:比较你在圣马丁和皇家学院体验过的环境和在杜塞尔多夫的现状,你最近又访问美国的艺术学校,你是否注意过它们之间的相似和不同?教授的职责是什么?是欠学生什么吗?P.D:我不知道欠学生什么。有人在美国一所艺术学校里曾经对我说,因为学生要支付这么高的学费,他们会要求你付出相应的时间,这很可怕,但我可以理解。在杜塞尔多夫,没有学生需要支付学费,这些日子很珍贵,每个学生能在那儿待上六年。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像一个巨大的工作室那样运作,有20个或更多的班,每个班由一个教授负责,每个教师都有不同的教学方法,两个班之间没有太多直接的交流,但他们之间会发生很多关联。我们的小组讨论很随意。我喜欢大家彼此谈论作品,而不是在规则下用教导的方式,就像在圣马丁。我喜欢这个系统,因为它缓慢,我相信在这种环境中能发展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圣马丁艺术学院更个人化,此外你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和教师。不过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这种方式还挺困扰我的,并不是真的那么有趣。在与不同的来访者的交谈之中我得到很多东西,有一些好的来访者,像Bruce McLean和Jack Goldstein一直非常鼓励我。在纽约,想让一个来访者对着你的作品说些有意义的东西还是挺难的,人们没有这个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话会慢慢开始。 后视镜194.9×270cm 布面油画 1999P.A:在你毕业之后这20年间,你是否目睹了学生关注点和态度的巨大变化?P.D: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们压力更大,因为已经有了明确的成功先例。如果他们的同代人成功了而自己却没有,学生们自然会焦虑。此外,他们的作品进入艺术系统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很多学生都在举办展览,大多数时候,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话虽如此,我已经在推动我的学生们进行展出。但是对教师选择学生进入他或她的班级上,杜塞尔杜夫有严苛的制度。如果你想要这样或那样一个班级,虽然不是一定做不成,但经常会不成。很艰难,不知为什么,但这确实是现实。P.D:就是避免在现实世界中形成某种联盟。但我试着去接受有挑战性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已经和我很亲近的学生,否则这个班级可能会变得过分安逸。P.D:在2000年获得艺术家居留之后,我2002年搬去了特立尼达。P.A:特立尼达是你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从你的画面上来看,你能对周围的环境有一种直觉式的描绘,这是你决定搬到特立尼达的理由吗?
后视镜194.9×270cm 布面油画 1999P.A:在你毕业之后这20年间,你是否目睹了学生关注点和态度的巨大变化?P.D:现在的年轻艺术家们压力更大,因为已经有了明确的成功先例。如果他们的同代人成功了而自己却没有,学生们自然会焦虑。此外,他们的作品进入艺术系统的机会比以前多得多。很多学生都在举办展览,大多数时候,我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话虽如此,我已经在推动我的学生们进行展出。但是对教师选择学生进入他或她的班级上,杜塞尔杜夫有严苛的制度。如果你想要这样或那样一个班级,虽然不是一定做不成,但经常会不成。很艰难,不知为什么,但这确实是现实。P.D:就是避免在现实世界中形成某种联盟。但我试着去接受有挑战性的学生,而不是那些已经和我很亲近的学生,否则这个班级可能会变得过分安逸。P.D:在2000年获得艺术家居留之后,我2002年搬去了特立尼达。P.A:特立尼达是你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从你的画面上来看,你能对周围的环境有一种直觉式的描绘,这是你决定搬到特立尼达的理由吗?
P.D:这是我想到的一些事物。第一批特立尼达的照片是我在那儿待过之后,在伦敦做的。我知道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我搬到这里时,我带了一些要用来画的照片,主要是在伦敦一家垃圾店找到的明信片,它们让我想起了特立尼达。有些来自印第安一个叫喀拉拉邦的部落的印第安人让我觉得很有趣,以他们为对象我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画的图像总会有些什么会跟特立尼达有关,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也没有计划过,我很惊讶自己居然画了一些相当直接的画,比如lapeyrouse墙。我曾经希望在这里画些雪景,但至今还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伦敦可以,在这里却不行。 Lapeyrouse Wall 53.2 × 38.2 cm 2004P.A:经过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以后,你的作品价格在持续稳健增长。2007年你的作品《白色独木舟》前所未有地卖到1130万美元,开创了欧洲在世的艺术家的拍卖纪录。然后在2009年,《反射》卖了超过1000万美元,还有许多其他绘画的卖价已经超过三、四百万。你和你的代理商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P.D:这让人很困惑,我可能永远也无法理解或接受这种情形。即使一件作品售出10万美元也够了不起的了,这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价值和感知价值,很怪,但它发生了。我身边的人没有因为这个感到高兴的,但艺术圈外很多人都说,我要是不让拍卖行卖掉我所有作品就是疯了。有一阵子我几乎有了创作障碍,这让我很紧张,就像一切都失控了。当然,一旦你出售或赠与你的任何作品,类似的事情就在所难免。P.A:你在泰特美术馆的大型个展,展示了你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的作品,你怎么筹备的?P.D:展览在2008年。我有大约18个月或两年的准备期,这并不算长,真的。我也想在展览的后期部分有大量的新作品。P.D:可能是五张大尺寸的,很多中等尺寸和小尺寸的,有一些是在 Gavin Brown 的公司里,Michael Werner 画廊去年在纽约展览过。你去看了吗? Michael Werne画廊的彼得.多伊格作品展览现场P.A: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展出的作品,那绝对属于人人都想一睹为快的展览之一。在这次展览之后你有什么改变?P.D:泰特美术馆的展览参观量让我很吃惊,也许人有点太多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观众。我很紧张,我相信任何艺术家的作品第一次放在这样一个平台上都会这样,这是对你20多年来创作成果的检验。但正如你所说,我认为许多人的讶异是因为看到原作,所有作品在现场看感觉更好。当最初看见自己20年来的作品,我相当不安。首先,当我看见所有的作品摆在泰特的地上的时候,我看到的都是工程作业,我意识到我自己的作品正在跑远。技术问题到处冒头——跟茎蔓似的!——在所有早期的工程作业中。但是渐渐地,作品被挂在墙上,一些感觉有点脏兮兮,一小部分开始光芒四射——我看到这些以后,渐渐镇定下来。一个画家看到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的作品被放在地板上,靠在墙上。它只是在适应环境,感觉很凄凉。所以,当一切都开始在墙上展现,我松了一口气。悬挂展示是成为艺术家最重大的部分,这是众多经验之一,就像在别人的工作室里一样。这是一项特权。P.A我们来谈谈你的另一个努力成果,你的电影工作室俱乐部,准确地说,它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P.D:它是我在西班牙港的工作室里做的一个电影之夜,在七年当中差不多每周都会有。我最初开始做它,是因为几乎找不到一个地方去看那些非正统的电影。这个灵感来自我在伦敦接触到的一些通宵电影院。我把它叫俱乐部,是为了到晚上我们有能把它转化成俱乐部的可能,比如玩玩音乐什么的。P.A:它似乎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个完整的组成部分,吸引了特立尼达本地人和外国人的注意力,电影海报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和魅力,你还没有主持过作家和制片人的发布会吧?P.D:我真的不认为这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虽然我知道当它不在了的时候, 人们还挺怀念它的。也许从一定距离看,它有点被神化了。从成立以来,我们有一些电影制作人在和特立尼达电影节合作。制作海报的初衷,是为了告知在同一栋建筑里的其他工作室的人们,这是一个老工厂,主要是用来酿造和储存费尔南德斯红酒的。我画海报的速度很快,然后把电影标题写在顶上, 就跟在大学咖啡馆里能看到的那种一样。当我被邀请展示它们时,我犹豫了一下, 因为这些海报对这个电影俱乐部具有特别意义,这些电影是经过我们精挑细选审核过的,后来我同意了。P.A:不管它是不是被神化了,这看起来总是个挺特别的事儿。P.D:在炎热和潮湿的环境里看电影真的很棒。经验如此不同。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进入AMNUA数字展厅;
为保证流畅体验,建议在wifi环境中观看;
投稿信箱:amnuamedia@163.com;
文章版权归AMNUA视野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汉堡王 196.3 x 120.6 cm 1984
汉堡王 196.3 x 120.6 cm 1984













 后视镜194.9×270cm 布面油画 1999
后视镜194.9×270cm 布面油画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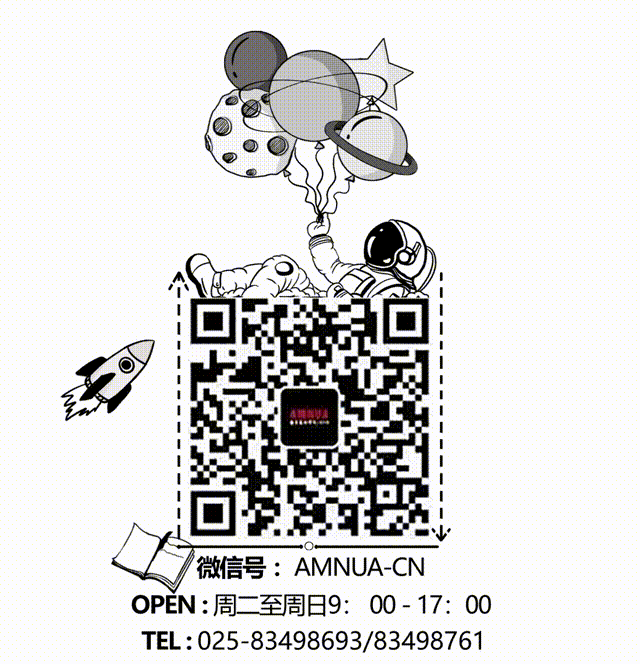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