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获得“第三十五届田汉戏剧奖”评论奖 · 一等奖。原载于《戏剧与影视评论》2020年1月总第三十四期。
作者介绍:织工 剧评人

罗周编剧的昆剧《浮生六记》,将沈复原作改写成了一个趣味殊异的故事。沈复书写了苏州小市民相濡以沫坎坷同行的烟火人生,罗周则用她的富贵想象和男性凝视,描画了一幅才子佳人盛世行乐图。
—— 评罗周剧作《浮生六记》
文:织工
也许只是因为《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是苏州人,而书中所记录的生活主要发生在昆曲的发源地,同属“地方文化名片”,所以去年才有两部新编昆曲《浮生六记》先后问世。本文将讨论的是上海大剧院出品、罗周编剧的《浮生六记》,并将重点放在罗周的剧作法上,至于舞台呈现之得失,并非本文的主要关切。
照理说,《浮生六记》和昆曲应该是相得益彰的,但是看完演出,我感到罗周讲述了完全不同于原作的另一个故事,一个脱离历史语境、改变阶级属性、触目皆是富贵气象的“纯爱”故事,因此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两百年前苏州小市民的烟火人生,已经配不上今时今日的高雅昆曲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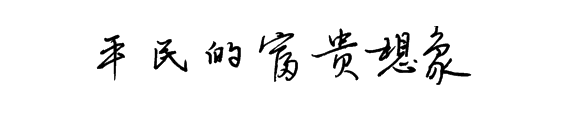
我第一次读《浮生六记》是在中学,印象中只有一对神仙眷侣,恩情美满,唯恨天不假年。到后来年纪大些、阅历多些,再来重读,才渐渐体会出复杂的人生况味,才发现沈复和陈芸的生活,在风花雪月的美满表象之下,是困顿流离的凄凉底色。而罗周的改编,却是要将这凄凉底色删抹干净了,好去点缀一幅太平盛世富贵行乐图。
故事从芸娘殁后回煞之夜,沈复期盼亡魂归来开场(“盼煞”)。中间有四场戏:“回生”讲述沈母为沈复续娶半夏,而沈复则将悼亡之情诉诸笔墨,芸娘的魂魄借沈复之书写而现身;“诧真”讲述芸娘的魂魄与沈复重温同游水仙庙之旧梦,众人皆以其为真;“还稿”讲述沈复思念成疾,沈母欲毁其文稿而半夏保存;“纪殁”讲述沈复忍痛写下死别情景,结束与芸娘的魂魄相流连的十年。最后以沈复病逝,与芸娘双双入冥收煞(“余韵”)。全剧没有可以称为戏剧性的情节,主要展现的是沈复如何将生离死别之情寄托在《浮生六记》的写作中。

△ 昆剧《浮生六记》剧照
当沈复初次登场时,虽则做思念亡妻的病中打扮,其形象却是毫不掩饰的年轻俊朗、服色鲜明,乍一看和柳梦梅、赵汝舟、于叔夜这些明清传奇中的才子无甚区别,令我颇感意外。我们当然不能用逼真写实去要求昆曲,但是按照原作记载,芸娘殁于嘉庆八年,沈复和她同年,彼时已经四十一岁,两人成婚已有二十三载,育有一子一女;且沈复早已放弃儒业,四处做幕僚、学生意,彼时穷困潦倒,寄人篱下,生计无着。我实在想不出,类似的情形在昆曲中有以巾生和闺门旦应工的先例,这不合情理。罗周这样分配脚色,也许是因人设戏,为了符合施夏明、单雯两位演员擅长的戏路和一贯的舞台形象;但若是如此,故事就不该从中年失偶讲起,或者,从一开始就不必选择《浮生六记》。
从错配脚色开始,罗周的富贵想象就替换了沈复的平民生活。因为巾生和闺门旦不只意味着年轻,还意味着一种对世道人情天真无知的权利。在昆曲舞台上,巾生和闺门旦的主业就是谈恋爱。但沈复写的是世道人情。他和芸娘,都不是富贵出身,没有权利对世道人情天真无知。芸娘四岁失怙,家徒壁立,全靠针黹功夫供养母亲和弟弟,自幼即体尝人生艰难。沈复虽然出身“衣冠之家”,是个读书人,但并没有取得功名,为了生计而常年外出游幕,卖过画,也做过一些小生意,都以折本告终。他不仅不是明清传奇中门庭显贵且动辄中状元的才子,相反,可以算是籍籍无名,潦倒以终。光绪三年(1877),当苏州人杨引传将他从冷摊上发现的《浮生六记》四卷手稿刊行时,只能从内容推知作者姓沈号三白,“遍访城中无知者”①。
① 沈复:《浮生六记》,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本文所引《浮生六记》原文皆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从沈复自述来看,在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他和芸娘也只是衣食无虞。乾隆五十九年,沈复三十二岁时在广州行商期间的花船冶游,前后四五月,花费百余金,可能是一生中最豪奢的时候。次年芸娘欲图名妓之女为沈复妾室,沈复的反应是惊骇:“此非金屋不能贮,穷措大岂敢生此妄想哉?”事终不谐。更多的时候,沈复和芸娘的生活是清贫甚至困顿的,所以《浮生六记》中多以“贫士”自称。“坎坷记愁”卷极言大家庭生活中金钱和人情两大困扰:“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绌。谚云:‘处家人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之议,渐至同室之讥。”自芸娘血疾复发,逋负日增,沈复偏又连年无馆,靠卖字画为生计,“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为了省钱,芸娘不肯服药,且抱病刺绣《心经》,以获厚价,而益增其病。其后又因债务纠纷,被父亲逐出家门,从三十八岁到四十一岁,芸娘临终前四年,夫妻俩流离他乡,贫病交加,几乎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其间女儿给人做童养媳,儿子改学生意,境遇之惨,实难形容。芸娘死后,沈复得友人资助,又将家中所有变卖一空,才得成殓。沈复对此并不讳言,他写封建大家庭中的勾心斗角与同室操戈,写被逐离家时夫妻共食一粥的情形、母子永诀的情形,写自己奔走告贷,枵腹忍寒,在旅店借火烘烤湿透的鞋袜,疲极酣睡,醒来袜子烧掉了一半的细节,皆是真实可感的惨淡人生。
但罗周的《浮生六记》中没有惨淡人生,因为巾生和闺门旦自不必操心金钱这等俗事。全剧中唯一一次提到钱,是第一场当沈复盼芸娘回煞之时,房东王婆前来催讨租金,并以举丧不吉为由,趁机敲竹杠,要求租金翻倍,押一付三。沈复立时应承。王婆举起大拇指夸他:“好慷慨,好情痴!”这种豪放作派,以及舞台上一切服饰器用,都在营造一种无忧无虑的富贵气象。不仅原作中两人遭遇的大关节统统隐去不表,一些细节的处理也耐人寻味。比如说,罗周从原作中撷取了芸娘喜食芥卤腐乳和虾卤瓜的细节。第一场“回煞”中,沈复备下芸娘的“舌尖之爱”以待亡魂,并追忆芸娘生时情景:“当年我最恶卤瓜、拒不肯食,芸姐劝我不动,竟笑笑嘻嘻,挟之强塞我口。我掩鼻试嚼,倒也清爽,开鼻再嚼,好不美味!”② 在原作中,芸娘曾有解释,喜食腐乳乃取其价廉,可粥可饭,幼年食惯,成年后亦不敢忘本;但是罗周将贫寒生活的背景完全隐去,仿佛腐乳卤瓜只是一种口腹甘嗜、夫妻情趣。我们甚至还可以辨识出言情小说中常见的富贵想象:有钱人山珍海错吃腻了,偏偏就爱清粥小菜呢。
② 罗周:《浮生六记》,《上海戏剧》2019年第4期。本文中的《浮生六记》剧本引文皆出于此,不再一一注明。
另一处细节是剧中芸娘提到的美好回忆之一“萧爽楼题画”,听起来也真风雅极了。现实却是夫妇二人因家庭矛盾,被沈父逐出家门,寄人篱下一年有半,靠着芸娘和仆役刺绣纺绩,以供薪水。即使在困顿之中,沈复仍是呼朋引伴好热闹的性子,多亏芸娘“善不费之烹庖”,而朋友知其贫寒,也会出些酒钱,但即便如此,有时还要芸娘“拔钗沽酒”。在沈复后来的回忆中,寄居萧爽楼的日子,虽然贫乏,却很自在,是一生中难得的“烟火神仙”的日子。只有当我们看到其中的“烟火”,想到这种风雅并非应然之事,而是以精神旷达对抗物质贫乏的结果,也是理解、体谅、隐忍和牺牲的结果时,这种风雅才显示其意义和力量,否则,我们只去羡慕“神仙”好啦,又何必写沈复和芸娘呢?

△ 昆剧《浮生六记》剧照
正因为遮蔽了原作的凄凉底色,罗周所描绘的沈复和芸娘的生活,就显示为一种巨大而空洞的物质堆积。在沈复的回忆中,有芸娘的“舌尖之爱”、芸娘所作的“人瘦花肥”诗句,有花烛之夕的并肩夜膳,有酒酿饼和碧螺春,有沧浪亭中秋踏月、太湖船携酒共饮,有萧爽楼题画、七夕节乞巧、插花论诗、焚香烹茗……简直是一部迎合中产阶级观众想象的古典生活品味指南。看着舞台上的沈复努力做深情科,我忍不住想,如果做了二十三年的夫妻,回忆里竟然没有世道炎凉、人情冷暖,没有任何真正深刻的东西,翻来覆去都是些琴棋书画、月貌花容,看似风雅脱俗,其实浮皮潦草,和萍水相逢的青楼中人都可做得说得,那么这所谓的伉俪情深,实在也深不到哪里去。哪怕人世间任何一对怨偶,回忆起半世同行的悲欢,都要复杂生动得多了!
我不会批评罗周在《春江花月夜》中描写才子佳人,因为她有为原创作品选择题材的自由;但《浮生六记》是改编作品,将原作中的困顿流离删抹干净,装成一派富贵清闲的景象,仿佛在沈复和芸娘的人生中,除了刻在脑门上的一个“情”字,再也没有旁的忧愁烦恼,这就未免太过势利心肠,而且也带了剧作法上的实际困难。沈复和芸娘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记述,不是因为爱情的完美,而恰恰是因为爱情的不完美。只有当那些许的亮色,是点缀在黯淡苍凉的人生图景之上时,它才显得如此璀璨,如此珍贵。而当充满烟火气息的人生困境都被删抹殆尽时,还有什么能为这一种巨大而空洞的物质堆积粉饰一点意义呢?似乎只有诉诸死亡了。
罗周在创作札记中写道,《浮生六记》的题旨是“文学之于死别的跨越,亦爱念之于死别的跨越”,她说:“我总是在剧中抒发‘死生亦大矣’的喟叹,又总是不吝用最浓艳的感情, 倾心赞叹人类扶摇于生死之上的伟力:爱的伟大、艺术的伟大。”③ 爱情,文学,艺术,死亡,每一个都是大词,加在一起,非常惊人。很多教编剧的老师可能都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生活的剧本最爱谈论生死,一些初学写作的学生,既不愿意揣摩世故人情,又不耐烦钻研叙事技巧,他们偏爱的捷径就是制造死亡:看看,人都死了,还不够强烈的戏剧性和深刻的悲剧感吗?死亡可以让厚重的更厚重,让丰沛的更丰沛,但并不能让轻浮变庄严,让浅薄变深刻,甚至反而映照出人生之空虚无聊。如果沈复和芸娘的人生只有琴棋书画诗酒花,那么这种爱情和死亡就只对当事人有意义;如果《浮生六记》记录的只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的爱情,那么这种文学和艺术也没有多大的价值。所以,对于罗周的所谓“死生亦大矣”,对于这种用死亡来回避生活的剧作法,我想,可以用孔老夫子的话来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③ 罗周:《一生浮梦归去来──昆曲〈浮生六记〉创作小札》,《上海戏剧》2019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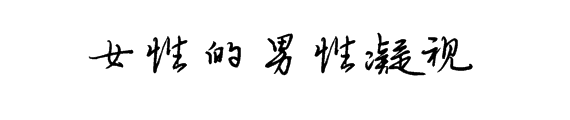
从剧作法的角度看,罗周改编《浮生六记》的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她选取了沈复的视角,重点不在沈复和芸娘从总角相识到死别生离的一生,而是沈复如何追忆这一生。她说:“昆曲《浮生六记》绝不是对沈复原著的戏曲化演绎,而是力图去触摸这本书从作者胸中呕血而出的灼热温度、怦然跃动。”④
④ 同注3。
诚然,芸娘是借沈复之笔才得永生,如果没有沈复饱蘸情感的描摹,我们不会知道曾有这样一个生气盎然的女人,两百年后,她的言语态度依然使人感到亲切;但是反过来,如果没有芸娘在他的书中活过,《浮生六记》实在算不得多么出色的文学,“浪游记快”卷中卖弄起才情来的顾盼自得,也实在有点儿令人肉麻。沈复的一生,志大才疏,俯仰随人,乏善可陈──并非说他不是好人,而是他没有什么值得摆上戏剧舞台的。只有芸娘,这个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⑤,是他平凡人生中最不同寻常的异色。
⑤ 林语堂:《汉英对照〈浮生六记〉序》,上海西风社,1939年,第5—9页。
在沈复的笔下,芸娘是美丽的,“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也是聪慧的,能自学识字,喜读书,通吟咏,谈吐有风趣,这是佳人风流;她恭谨,温柔,勤俭,善持家,对于公婆的无理和丈夫的无能,未尝稍涉怨尤,这是贤妻品德;她遇事有主见,有决断,“具男子之襟怀才识”,且无论境遇高低,皆有旷达心境,这是文士作派。在她和沈复的关系中,除了才子佳人的爱情,还有夫妻的相濡以沫、知己的相激相赏。但不仅如此,芸娘的世界并不是只有沈复,她有自己的社交,她的可爱主要在于“迂拘多礼”的外表之下,还有一种不安于阃闱的活泼生气,甚至隐含超越性别规范的欲望。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芸娘为夫谋娶名妓之女憨园为妾一事,乍看之下,这是符合封建女德的贤惠之举,仔细推敲却颇有意味。对于纳妾,沈复显得非常被动,除了经济条件的考虑,他还提出“伉俪正笃,何必外求”,而芸娘的回答是:“我自爱之,子姑待之。”自始至终,从晤面、相交到定盟,沈复都像外人,芸娘是兴致勃勃的主导者,她和憨园“欢同旧识,携手登山,备览名胜”,称赞其“美而韵”,“殷勤款接,终席无一罗致语”,“结为姊妹”,“无日不谈憨园”。当沈复开玩笑问她,是否要效仿李渔的《怜香伴》时,她回答:“然。”最后,当憨园被有力者以千金夺去时,沈复似不以为恨,反而是芸娘伤心逾常:“初不料憨之薄情乃尔也!”及至临终梦呓,仍有“憨何负我”之语。
对于为夫纳妾之举,传统的解释是芸娘宽容而贤惠,或因其自知患有血疾而主动选择“接班人”,为身后做打算。也有学者不满足于这种解释,如林语堂认为,这是“由于她太爱美而不懂得爱美有什么罪过”,爱美的天性使她“见了一位歌妓简直发痴”。⑥ 还有学者认为其中有保护弱势的成分,或者芸娘性情洒脱而不拘小节,或者从同性情爱的角度加以解释。我认为重要的是看到芸娘在整个过程中的主动姿态和情感投入,乃至“竟以之死”,显然已经超出了贤惠的本分,她不是仅仅作为丈夫的附属物去履行女德,而是作为一个主体在追求超越封建社会性别规范之外的某种寄托。
⑥ 林语堂:《汉英对照〈浮生六记〉序》,上海西风社,1939年,第5—9页

△ 昆剧《浮生六记》剧照
冒襄在追忆董小宛的《影梅庵忆语》中,塑造了一个从烟花之地回归正统家庭、自觉遵循封建伦理规范的完美女性形象,相比之下,沈复笔下的芸娘有一个从阃闱通向社会的反向轨迹,她对家庭之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因而常常有出格之举,展现了个体更加丰沛的生命状态,所以当我们想到她时,往往不是想到她病弱的身体,而是她兴致勃勃的样子。然而,这也就势必和严酷的家族威权、礼教规范之间产生紧张关系。芸娘的行事作派,加之大家庭中的误会、猜忌和挑拨,终于令她失欢翁姑,以“不守闺训,结盟娼妓”为由而遭到斥逐。整部《浮生六记》,读来最令人心酸的话,也许就是芸娘临终所言:“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
令人遗憾的是,罗周的改编不仅完全遮蔽了芸娘作为女性个体和父权制之间的张力,而且将芸娘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一个鬼魂和幻影。因为叙事视角的选择,全剧从芸娘殁后展开,重点在于沈复的追忆和创作,当他开始将回忆诉诸文字时,芸娘的魂魄出现在舞台上,随着文稿的写作,两人重温了旧日场景,而当沈复完成书稿时,芸娘也就消失了。沈复和芸娘的关系是创造者和造物,用罗周的话说:“他的文字,不但创造了一个‘芸娘’,进而更创造出一个‘世界’,仿佛真实世界的倒影,永存于岁月之河。”⑦
⑦ 罗周:《一生浮梦归去来──昆曲〈浮生六记〉创作小札》,《上海戏剧》2019年第4期。
这种塑造女性的方式是一种典型的男性凝视。芸娘不是作为一个有自我意志和行动力的主体出现在舞台上,而是一个男性凝视下的消极客体。不仅原作中关于她“具男子之襟怀才识”的记述统统不见了,而且她的生活经验被狭窄化为完全以沈复为中心,甚至在她和沈复的关系中,也刻意忽略了夫妻相濡以沫和知己相激相赏的层面,而仅凸显才子佳人的风流多情。罗周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绘芸娘的年轻、美丽与柔弱:“妙庞儿娇臻臻艳若桃杏”“这身畔娇媚,怀中香软,正是你嫡嫡亲亲的芸姐,我娇娇楚楚的妻”“灯下凝颦,案头迎笑,桃花笺书不尽桃花俏”“爱煞她一拧背人楚宫腰”“那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娇啭吁吁、粉汗盈盈,尽在俺文稿之内”。对芸娘的描写集中在她的身体,对身体的描写则充满诱惑性和情欲性,这是一个完全为了满足男性愉悦而存在的客体。
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有不少女鬼形象,比如杜丽娘、阎婆惜、敫桂英、李慧娘,她们求偶、诉冤、索命,展现出挑战现实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意志与行动力,这才是鬼魂上场的意义。像罗周的芸娘这样完全被动、只能被看的鬼魂,我想不出先例,这是以最极端的方式否定人的主体性。两百年前“三纲五常”的礼教社会,男性作者还能写出一个女人突破性别规范而充满生命力的样子;两百年后“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女性编剧却如此熟练地从男性视角凝视女性、贬抑女性、物化女性,彻底抽掉她的生命力,使她成为鬼魂和幻影,成为从未真正活在舞台上,而只存在于男性凝视中的客体。这显然不能用封建时代的历史真实加以辩解,因为就性别观念而言,从沈复的《浮生六记》到罗周的《浮生六记》,是实实在在的倒退。
除了由沈复“创造”的芸娘外,罗周的《浮生六记》中还有三位女性──沈复的母亲、续娶的妻子半夏,以及沈复和芸娘所生之女,她们都只是塑造沈复的完美男性形象、维护父权制权力结构的工具。半夏是罗周新添的重要人物,她在创作谈中写道:“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会在男女主角之外,塑造这么个可爱的半夏。我说一方面,是想表达:所谓爱情,除了沈复、芸娘之缠绵缱绻外,还有另外的丰富形态,另一方面,我也想说,《浮生六记》很好,可好的不只在书中,有了现实温柔的爱护,才有艺术纯粹的深浓。”⑧
⑧ 罗周:《一生浮梦归去来──昆曲〈浮生六记〉创作小札》,《上海戏剧》2019年第4期。
这不是罗周第一次写无欲无求无我的奉献型女配角,在《春江花月夜》中,曹娥为了助张若虚还阳与辛夷再见一面,拼着五百年修行不要,为他求来还魂膏,不过曹娥至少承认起了思凡之心,半夏则完全是被沈复和芸娘的爱情所感动:“奴年三九,见世间薄幸人多、真心人少,似沈相公这般,委实难得。”她没有自己的性格和欲望,在剧中唯一的功能就是沈复深情形象的捍卫者。被沈复醉后质问:“你一介生人,怎在我家?”她不愠不恼。读沈复记录他和芸娘的情爱,她不妒不恨。当沈母忧心沈复牵缠魑魅、病染沉疴,吩咐将书稿焚毁时,是她偷偷誊抄一份,并说服沈母:“一往情深,怎说是病?”连沈母都不好意思,说“亏欠你、委屈你”时,她表示:“妾虽嫁不得书中郎君,却得侍奉著书的相公。天缘如此,半夏之幸。”故事的结尾,沈复在对芸娘的思念中病逝,芸娘的鬼魂前来接引,两人亲亲热热地同往幽冥,对于无私奉献的半夏,对于还要仰赖她照顾的女儿,竟不置一词。
没错,沈复和芸娘,巾生和闺门旦,还有一个年已及笄的女儿。她没有机会出现在舞台上,母亲去世了,父亲忙着伤心,“回生”的鬼魂也只想着重温鸳梦,没有人关心过她的生活、她的情感。在最后一场戏中,她突然出现在半夏的叙述中,已经被后母安排了一桩婚姻,好给缠绵病榻的父亲冲喜。做父亲失败到这个地步,我一度怀疑这是反讽,然而罗周是逻辑自洽的:女儿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了证明后母的贤惠,而后母的贤惠就是为了证明父亲的深情。
当罗周采用男性凝视时,伤害的仅仅是女性形象吗?不是的,剧中的沈复也因此变得既面目模糊,又面目可憎。在原作中,沈复虽然顺从父权而无力调解家庭矛盾,但他毕竟发出了微弱的抗议。因为和妻子性情相投,他会感叹:“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甚至表示:“来世卿当做男,我为女子相从。”他纵容、鼓励芸娘的天性,实实在在地去拓展一个女性的生活空间。芸娘失欢翁姑,两次被斥逐,沈复不离不弃,与共进退,以父权制社会的标准而言,这并非易事。实际上,沈复作为男性,同样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如史景迁所言:“虽然直到最后沈复仍不明白命运为什么不让他们过得快乐些。‘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他问道,‘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为之累。’但是他所生活的社会却不再酬答这种逆来顺受的美德。”⑨ 但是在罗周笔下,沈复追求的爱情和自由与父权制之间仿佛不存在任何张力,他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也不存在一个压迫他的父亲和封建大家庭,他自己已经成为家长,所有女性都以他为中心,而他对母亲、妻子和女儿的痛苦与牺牲毫无体察,自始至终,他都是父权制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且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如果塑造这样的形象,是为了讽刺父权制幽灵不死,那倒是很有现实意义,但罗周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⑨ 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181页。

△ 昆剧《浮生六记》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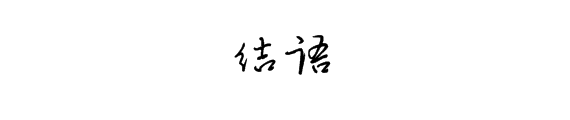
我并不是以忠于原著来要求一部改编作品,改编者有充分的权利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时代风尚违背原著,这种权利与一部改编作品的好坏并没有关系。我只想指出沈复原作和罗周剧本之间的根本差异:沈复写的是苏州小市民相濡以沫坎坷同行的烟火人生,罗周写的是王子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直到死亡将他们分开,死后犹不知餍足;沈复哀叹社会权力结构中受压抑、被排斥的不合时宜者和失败者的命运,而罗周赞叹现实权力结构中的支配者和维护者自我感动、自我崇高化的姿态。这种差异,在我看来,是云泥之别。
曾经,昆曲舞台是向普通人敞开的,是向不合时宜者和失败者敞开的,它描摹尽市井百态,刻画尽世俗人情。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如今的昆曲好像越来越“高雅”、越来越“美”了,于是那些不合时宜者和失败者渐渐消失了,普通人渐渐消失了,世态人情也渐渐消失了,帷幕拉开,多半是一幅太平盛世富贵行乐图。罗周的《浮生六记》并非偶然,它提醒我们,如果有一天,昆曲舞台上只剩下巾生和闺门旦,只剩下必须用年轻、美貌和财富加持的所谓爱情,那不过是消费主义和父权制的合谋,用丰富的物质包裹起陈腐的价值,去充当中产阶级“高雅”生活指南罢了。而充当中产阶级“高雅”生活指南这件事,可一点儿都不高雅。
— 感谢阅读 —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