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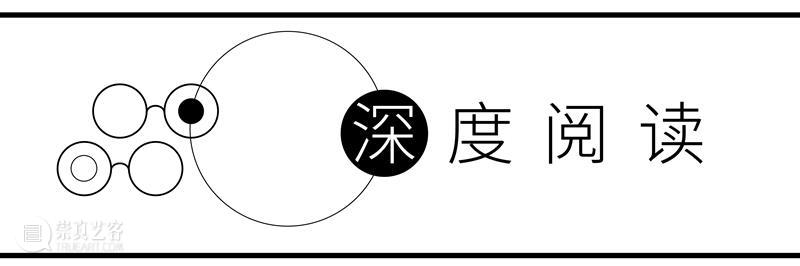

“书摊计划”由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发起,致力于人文社科新书联动宣推。同时,我们在微店专门辟出用于分销相应图书的“PAI书摊”,旨在让读者与书更好地相遇。目前,已有18家出版机构加入:大雅、鹿书、三辉、六点、精神译丛、光启书局、新民说、我思、鹦鹉螺、湖岸、斯坦威、领读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万有引力、东方出版中心、文化发展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微言。十分欢迎更多出版机构一起来玩,详情请加微信lonzr25咨询(添加时请务必注明“书摊+出版机构名”)。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37期:我思新书《列维纳斯传》。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是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犹太思想家。列维纳斯也是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这一经历对他的思想影响至深。西方与犹太在这位探究“他者”的哲学家身上共存。
本传记作者所罗门·马尔卡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跟随列维纳斯学习。在列维纳斯于1995年去世后,马尔卡花费五年的时间来为这部传记做准备。本书完整记录了列维纳斯出生于东欧,求学于法、德,成名于法国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发展历程。
列维纳斯既是典型的20世纪法国哲学家,发展了存在、有、他者等一系列重要的哲学概念,同时,他也是一位百分之百的犹太思想家,犹太文化独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贯穿着列维纳斯的一生。本书忠实再现了列维纳斯身上的双重属性,既关注《塔木德》的光辉,又关注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思辨。
“他出生了,工作过,然后死了。”这是海德格尔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课上说的。如果我们将这句话用到他自己身上,这位弗莱堡的哲学家可能同样会喜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他的许多法国仰慕者都对这句话表示赞同。他们称赞他的作品,将它们捧上神坛,对于传记中的那些“意外”则漠不关心。与纳粹主义同谋?加入纳粹党?出任校长的插曲?当然这些只是人生经历中的意外,是一时失足,一种愚蠢。而且,海德格尔只在 1933 年到 1934 年间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后来他就辞职了。这是在法国广为人知的海德格尔的哲学财富的立足点。关于《存在与时间》作者的政治问题的辩论从未结束过,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在法国,对海德格尔的接受史是混乱的。他同时担负着最好和最坏的议论。就像多米尼克·贾尼科在超过一千多页的厚厚的两卷本中就这个问题所揭露的那样,海德格尔在法国的接受史同时混杂着激情与误解,从战后初期威严扫地,被撤销了在德国的教席,到法国知识分子的来访,与让·波弗瑞和勒内·夏尔的友谊,他到法国的几趟旅行(巴黎、瑟里西、普罗旺斯的艾克斯、索尔)……直到 80 年代末的法里亚斯事件,这件事在朗代尔诺的哲学界引起了骚动,这次骚动的影响甚至超出了该地区。年轻的智利学者维克多·法里亚斯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后来成了柏林自由大学的老师,他就此事进行了调查,其结果是令人难以忍受的:马丁·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并不是迫于环境,他的辞职也不是出于抗议。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联系由来已久。
尽管在将现象学介绍到法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从来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在50 年代,瑟里西拉萨尔地区邀请这位德国哲学家来讲学,此时他正处于自己享誉全球的十年中。列维纳斯缺席了。他既没有参加,也没有受到邀请去参加海德格尔 1968—1969 年在索尔举办的研讨会。他从来没被算入信奉者中,甚至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
列维纳斯的弟子兼朋友雅克·罗兰记得,有一天,他听列维纳斯谈到了马丁·海德格尔:“如果战后我遇见了他,我不会和他握手。”让—吕克·马里翁对海德格尔有这样的观点:“您还指望什么呢?所谓虚无主义,就是这样。海德格尔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但他站在了纳粹党那边。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时代。”至于保罗·利科,他谈到海德格尔时则说,“永久处于论战关系中”。钦佩和排斥混杂在一起,既着迷又憎恶,极端的亲近又绝对的决裂,列维纳斯经常表现出这种自相矛盾,并强调正是因为那是海德格尔,所以他才更不会原谅。很快,他就要知道所有的一切了,其实他早就已经全部知道了。当维克多·法里亚斯的书出版时,人们去询问列维纳斯的意见。他回答道:“法里亚斯的书出版后,一些细节变得更清晰了,但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是前所未闻的。”而且,在接受《新观察家报》的采访时,他指出,他早就知道或猜想出海德格尔的亲纳粹立场,“也许甚至在 1933 年前”。
同样是在 80 年代,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eorgio Agamben)来当周六早上《圣经》课的助教,这门课由雅克·罗兰主讲。在课程的最后,两个人免不了进行讨论,列维纳斯问访客:“阿甘本先生,您在 60 年代末参加了海德格尔在索尔的研讨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阿甘本回答:“我只能告诉你我所看到的。我看见了一个温柔的男人。”列维纳斯则说:“您知道,我在 1928—1929 年也与他相识,但我见到的是一个强硬的人。您这样告诉我,我应该相信,但实在不能说服自己,这个男人是温柔的。”阿甘本稍后对罗兰说道:“必须说在那个时候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看法就已经注定了!”
对于列维纳斯而言,正如海德格尔那样有过“前期”和“后期”,但说到那比地狱更糟糕的失败,却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的失败,而是普遍地朝向“所有人”和每个人。不同于汉娜·阿伦特式的恋爱关系,在整个过程中,列维纳斯都怀着一种爱慕的迷醉,从学生时期在达沃斯的热情,到经过被囚而在成熟期产生的痛苦。这个犹太人跨过海德格尔,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并向他提出有比对存在的遗忘更重要的问题。这种关系并没有被会面、交流,甚至是争议所滋养,一直没什么变化。这位伦理学家的目光,包括他关于“义务”这个概念的看法,都只能在书中诘问那位哲学天才。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会惊讶地看到列维纳斯很少情绪激动,仅有一次例外。现任波士顿大学哲学教授威廉·J. 理查森以自己的方式,在 1993 年 5 月 20 日至 23 日在罗耀拉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这次会议是由阿德里安·佩佩扎克策划的,讲述了这件事。他从与列维纳斯的会面开始讲起。那是在 1963 年。理查森刚刚在马蒂努斯·奈霍夫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的标题是《海德格尔:从现象学到思想》,此书是他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答辩论文的修订版。结果是他受同一所大学邀请,出席申请副硕士(maître-agrégé)头衔的答辩,这个学位相当于法国或德国的博士。因此,他必须在国际答辩评委面前公开答辩。答辩者可以提出答辩评委人选的建议,建议被采纳后,将以大学机构的名义发送邀请函。对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提名立刻获得了同意。
和列维纳斯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他家里。这位法国哲学家礼貌地让理查森把书留给他,让他读一下,然后告诉他自己的回复。
第二次会见同样礼貌。列维纳斯同意担任答辩评委。但他坚持地告诫道,自己不是海德格尔的朋友,他要保留言论自由。理查森回答:“这就是我们邀请您的原因。”
会议举行得很庄重。轮到列维纳斯时,他再次展示出——用理查森自己的话——异常的友好。每个人都期望一场粗鲁的攻击,但是,他唯一做出的批评针对的是“非常学术性”的特征,文本太“说教性”了。但是,哲学家以问题的形式补充道,他想知道为何一个有信仰的基督徒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学习海德格尔”!
答辩结束后,在大学校长的住处举行了招待会。理查森,按照他的说法,从一个人走向另一个,和他们握手。忽然,他感觉有人出现在他的背后,并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看到了列维纳斯。他向列维纳斯伸出手,再次感谢他的出席和讲话。但列维纳斯无视了他伸出的手,而是直直盯着他的眼睛,对他低声说道:“我正和我的老朋友们谈论您这本让他们发笑的书。我想您一定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笑。您还记得在您书中有一处写道:1943 年,那是他思想上丰产的一年?”“是的,我记得!”理查森回答。“好吧,在 1943年,我的父母在一个集中营里,而我在另一个。那真是一个丰产的年份!”说完这句话,列维纳斯就转身走了。
理查森傻眼了。他看到了一个生气的人,与一个小时前还在答辩席礼貌地听他演讲的学者截然不同。“如果他想发动攻击,为什么不在答辩的时候这么做?如果这样,将会在学界内发生一场真正的对抗!相反,他却等到了会议结束!”那天,理查森感觉有点“不自在”,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将这种‘失态的瞬间’放在列维纳斯思想的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它?”今天他还被问起这桩旧日的逸事,再提到它也几乎还是用同样的话。“过去了的时间并没有改变我对列维纳斯的判断。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也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在我看来,这件逸事仅仅表明了他思想中的一种欠缺,没有考虑到人类现象特有的一个因素,即无意识。关于这本书的那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揭示他的这种欠缺。”
奇怪的领悟!他说的是什么无意识?是列维纳斯的?还是他自己的?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想到,对列维纳斯来说,读一本七百多页的关于海德格尔思想演变的著作——这本书除了以玩笑的形式写下的“丰产性活动”(activité prolifique)一词,丝毫没有提及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是一种怎样的折磨。理查森却更喜欢做一些精神分析的普遍思考,而不是站在列维纳斯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他无疑是在“无意识”地——就像他喜欢说的那样——加倍了那时他被谴责的麻木不仁。
这是列维纳斯罕见的“暴力发泄”之一。这个因过于审慎而受到批评的人,有时也知道该如何表现得粗暴。无论如何,这一插曲揭示了过往的痛苦总是鲜活的,从来没有真正平息。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