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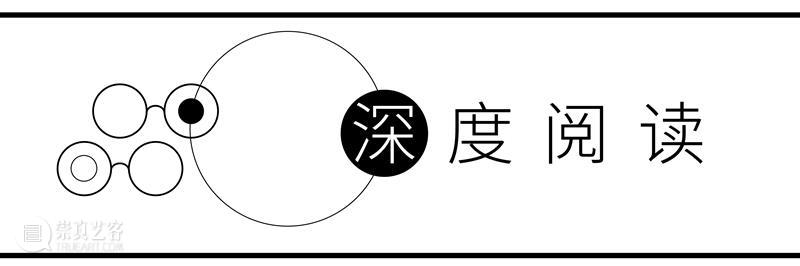

“书摊计划”由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发起,致力于人文社科新书联动宣推。同时,我们在微店专门辟出用于分销相应图书的“PAI书摊”,旨在让读者与书更好地相遇。目前,已有20家出版机构加入:大雅、鹿书、三辉、六点、精神译丛、光启书局、新民说、我思、鹦鹉螺、湖岸、斯坦威、领读文化、艺文志、后浪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万有引力、东方出版中心、文化发展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微言。十分欢迎更多出版机构一起来玩,详情请加微信lonzr25咨询(添加时请务必注明“书摊+出版机构名”)。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41期:后浪文学新书《山魈考残编》(黎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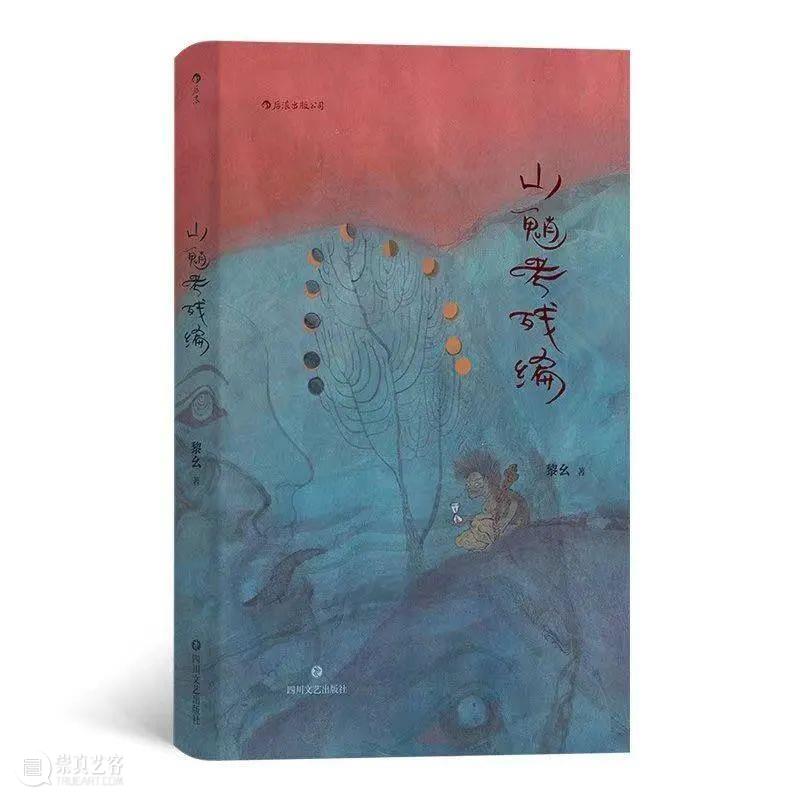
最后一位鬾阴人口述家族史
编者按:对于标题中的“最后”一词,虽自知不妥,但只因当事人一再要求隐去其姓名,我便自作主张,宁愿这一代称更加耸人听闻一些。不过,从时间的循环意义来讲,圆上任何一点俱可称“最初”或“最后”,我权作抛出一枚硬币,自二者中择其一而已。若是非要交出一个理由,也许因为疲惫已是我的常性,它令我偏好终结而非开端,偏好停驻而非起航。——奥坎·阿伊德
人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无法回溯其生命所造成的,或者说,由于其回溯生命的工具,即记忆本身,存在重大的缺陷。所幸,我的讲述无须从自己的记忆出发,而是跃至我的纪元尚未开始之前,投入那片茫茫大雾之中。那是我的史前时期,越过岁月的深谷,藉由一条基因之链决定了我全部的历史。我无法以炯炯的目光照亮身后那条漫长的道路,但那个即将宣布“要有光”的人早早地便已把守在路的尽头。
我的玄祖母与她的男人因为一条蛇而结合。被同一条毒蛇咬伤的人,遑论性别年龄,有何等关系,均须在彼此为对方吸净毒血之后共度春宵,这是鬾阴人最古老的习俗之一。蛇即代表某种天命所归的肉体契约。这位老祖宗只有四十重①,恰逢其时,她被勒令跨坐在一个九十重的壮年男人身上,被他刺穿,跌倒、昏迷在血泊之中。自那夜起始,在那条终将如捏造般、如涂鸦般生就我的血脉中便传承了那迷梦,抹上了那旖旎,沾染了那阴湿,感应了那疼痛,并携带了挥不去的血腥气。
①一重为一百二十一日,这少女失身之时不过只有十三岁,而她的男人却已年近三十。鬾阴人既然能将毒蛇视为红线(显然,要保证族群存续,这绝非是唯一一种联姻的方式),那么可想而知,在天意的戏弄之下,比这一对更为悬殊的情侣也大有人在。我们不禁要问,在鬾阴人的眼中,差异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差异是否真实存在?他们倾向于以完全随机的形式主导自身的繁衍,让一切差异转瞬即逝,借一种近乎液态均衡的运动之理令氏族社会始终处于变动不居当中。
对不起。对我而言,要避免过度抒情几乎不可能,这也是出自血统的一种硬性规定。
四重以后,那位少女产下一个男婴,黝黑的皮肤使他看起来像一道小小的影子。鬾阴人以肤论人,黄者为人,白者为煞,黑者为鬼。这只新生的小鬼并未得到族人的敬畏,也未曾遭人刻意地孤立与贬损,他只是被作为影饵,在每重一度的祭祀典礼中被摆在神龛一般的巨大沙漏里,在其中翻滚、嚎哭、抽泣,任由黄沙磨砺与涤荡他赤裸的黑色身躯。长到二十重上下,他终于第一次诱来了一条山魈。它的骨骼如同一只白色的笼子在体外生长、合拢,将血肉箍在其中;它的头和脚是同一副模样:呈不完整的椭球形,顶部(或末端)较平整,中间将分未分,左右各生一目。可以说在它的身体两端有两颗头或者两双脚,如果将它推倒在地,它将随机选择一端重新站立起来,它用上面的脑袋考虑有关天的问题,用下面的脑袋做出有关地的判断。它那副僵直的、瘦长的肢体从头顶到脚底,或者准确地说,从脚底到脚底上下对称。山魈不擅于运动,更可能的是,不喜好运动。它像根船桨一样吃力地左右摆动、戳刺地面,前进的姿态既缓慢又勉强,但总要比日头的起降稍稍保持领先。而要辨认它,还应以首要特征为准:它没有影子。也有人说会有一点,但稀少得像一把撒在地上的灰色粉末。
我的四世祖在整个部落的围观中被山魈囫囵吞下,所有人都为此雀跃不已。可惜的是,人们兴奋过了头,他们一拥而上,混作一团,罔顾猎人的嘱咐和祭司的提醒,随之而来的抓捕并未成功。臃肿的山魈将孩童吐出,恢复了削瘦与灵便,竟从晃动不停的人腿丛中钻出,倒在地打个滚便不见了。只有部落首领的独生儿子看清了它的去向。他跟随山魈冲下一道坡,淌过一条河,借助石缝中伸出的几条藤蔓穿越怪石嶙峋的峡谷,循着逐渐消隐的蛛丝马迹,一路风餐露宿,虽终无所获,却来到一片人烟稠密的市镇。六重之后,这个孔武有力的少年从北面归来,带回了鸦片、洋火和另外三种惊人的魔法。在他的脸孔中央,从浓密的黄眉到勾曲的鼻尖,形似一只展翅欲飞的鸡雏,作为部落首领的继承人,他承诺将视抓捕山魈为余生唯一的事业,同时宣布我的四世祖——那个自山魈腹中重生的七龄童,从此成为他的养子。
被食影的山魈吞吐一番,便如经历一次轮回,四世祖全身黑色尽褪,苍白似一张人形的纸,白得甚至无法融入夜晚,在黑魆魆的山林中也清晰可见。他追随养父,带领一队人马——包括两名最优秀的弓箭手、一名文书、一位独眼的占卜师、一个马伕和一个厨师——踏上征程,就此与自己的部族和家园分道扬镳。他们根据道听途说的法则,朝着影子的指向,时而东南时而西北,毫无成效地兜着圈子;他们不着寸缕,用炭灰将自己全身涂黑,嘴里念叨着没人听得懂的咒语。山魈未曾现身,马伕却患上奇怪的传染病。先是浑身发热滚烫如烙铁,接着骨骼便向体外快速生长,刺穿手肘、膝盖、胸膛和咽喉,死相惨不忍睹。
从痛苦的失败中,领袖提炼出一句堪称明智的训导:日出与日落像两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你向往她们,但却不可能同时占有她们。于是,他们停止盲目的追寻,每个白天和每个夜晚都在洞穴里或大树下休息,商议诱捕山魈的策略,做出一些无法证实的论断和无法实践的计划,只在黄昏时分向西面前进。在漫长得远超预期的行程中,又陆续发生了两次减员。厨师在从岩石、树根和黄土里刮出来的一丁点食材中,选择了一条通体乌黑的蜈蚣,佐以苔藓炖汤,尚未从火上撤下,只品了一勺便倒地不起;随后一名弓箭手在外出狩猎时遭遇不幸。他饥肠辘辘、体虚无力,被鸦片烟雾催生的幻象迷惑,不但没能射杀野狼,反被咬断咽喉。余下的路全由悲伤铺就,他们的远征,仿佛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前往各自生命的尽头。一浑过后,五个疲倦的人来到嘉峪关前,除了十倍的苍老,他们一无所获。“惟独一件事比捕猎山魈更加重要,惟独这件事能让我们停下。”领袖说,“我们要在这里找到我们的女人,留下我们的后代。”
他们在最近的村镇住了下来,忘掉了他们的誓言。
生来体弱的四世祖,虽备受磨难,却仍旧没能锻造一副耐用的躯壳。十六岁那年他讨到一房媳妇,那女子丰乳肥臀、腰肢纤细,令他回想起自己曾经置身其中的,玻璃子宫一般的巨型沙漏。他用生命剩余的十二年养育了十一个子女,七个并非亲生,另四个中有三个早早夭折,仅余的独子却是一个傻子。在他婚后不久,领袖与占卜师经过商议决定继续践行已被废弃许久的祭影仪式。每重之中月华最为窄细,星光最为稀少的夜晚,四世祖便涂黑自己惨白的身躯,径自走进幽暗的窑洞。占卜师陪同他来到洞口便停下脚步诵念咒文,枯瘦的头颅上唯一的独眼,似一只小小的蚌壳,蕴含着或洁白晶莹,或阴暗腐朽的秘密,在寂静的深海中隐约闪动。待到他念罢离开,四世祖便孤身一人,整夜蜷缩在洞里,像一块被恐惧软化的石头。三十重,即大约十年以后的一个深夜,一阵沉重的、节奏迟缓的脚步声,将他从自童年起便不断改头换面,却始终纠缠他的噩梦中唤醒。一条船桨般的白影闪进洞口,蹦跳着向他靠近。他哭喊着后退,大声叫唤养父和占卜师的名字,但没有得到回应。他因失望而瘫软,继而又因绝望而癫狂。一身漆黑的四世祖像一头受惊的非洲水牛,忘记了自己的出路,只不顾一切地冲向山魈,撞倒它、撕扯它。他的风暴卷走了一副由麻绳和浆糊粘连起来的骨架,刮掉了一只头套,最后被一张熟悉的脸挡住。他松开他的养父,他们挂着同一种惊愕的神情向后退却,仿佛照镜子一般,不自觉地模仿对方的动作、迎合对方的节奏。领袖用犹豫的、不自信的、微微颤抖的、但又有点恶狠狠的、如同犯罪者一边忏悔一边拒捕的矛盾语气对他发出虚弱的叫喊:“我不能等了,不能再等了……”他的身体不自觉地痉挛抽搐,似乎被马鞭一般的声带抽打着。
四世祖在黑夜中一路疾奔。土地上仿佛隆起一个个高高低低的浪头,将他抛上抛下,他跌倒在地,像一个线团越滚越少,他细若游丝地呻吟着,用肩膀轻轻顶开家门。孩子们都在外间,挤在同一张炕上。他没有忘记怜爱地轻抚小女儿微热的脸蛋,确认自己尚有爱的力量令他感到安慰。他蹑手蹑脚地走进自己的房间,轻轻掀开被角却摸到两具赤裸的身体。在妻子的惊呼声中,独眼的占卜师将他推倒在地,逃出门去。交替起落的双脚如同斩断视听的板斧,片刻之内,踩过坡顶不可见,踏出山外不能闻。
自那夜起始,四世祖的日月与星辰从头到脚、由印堂至涌泉,向着他生命的地平线如暴雨般飞快地滑坠。我的祖父亲眼目睹他的父亲在几个昼夜间,肤色由苍白转为蜡黄。几个月之后,在去世的前一晚,他周身的皮肤终于如初生那夜一般黑如墨色。在咽气以前,四世祖留下了最后的一段话:“所谓生命,不过是每一天陪同这个世界一起,脱掉自己的影子然后再穿上它,直至无力继续。因此,我的开始和结束都是温暖的,尽管中段总伴着彻骨的严寒。我的孩子,你的一生却自始至终如同一个秋日的黄昏,半遮半掩地抵御着温和却又顽固的暮色。低眉只见片片落叶,侧耳只闻声声雁鸣。有些微的舒适、又有些微的风凉,时而惬意、时而忧伤。”
被娘亲抛弃的祖父在一块泥地上走过半生,身边总跟着一头慢悠悠的老黄牛。他从未坐下或躺下,即使酣然入睡仍保持站立,仅在地表占有三百平方厘米的最小面积。洋人的马队经过时,他正用刚刚拔下的一把杂草擦拭小腿上的污泥。农忙尚未结束,插秧的人还须挨过数月的饥饿,擦净泥以后,在泥样的、半干的河水里涮几下,这把草就被他连根带茎地吃了下去。马队的翻译要在村里雇几名脚夫,除他以外无人乐意。为了让他们知道他瘦小的身躯里有惊人的力气,祖父肩挑两大筐黄土,在田埂上跑了一个来回,偷偷吞下一口混着血沫的口水。
法国人伯希和②骑在一匹高大的牝马背上,同时却仿佛蹲守在自己思想的角落,他总是一言不发地望向地平线,忽而微笑、忽而叹息。随行其余皆盲从之辈,惟其马首是瞻。他高挑的背影像一只沙舟孤独的桅帆,悄无声息地起降、扯动、紧绷、弯曲、收拢,引领众人涉过晨昏风雨,有时竟也被同样无声的巨大黑潮彻底淹没。他们的行程并不遥远,行进速度却异常缓慢。他们在深夜出没于偏僻的村落和荒野,与孤狼和枭禽为伍,在山腹中凿壁,在戈壁上刨坑,穿过五百只蝙蝠栖身的地下宫殿,从一根石像的断指和一块残破的陶片中揪出被遗落在地底的前朝古尸。我的祖父曾听见一颗婴儿的头骨在突如其来的朔风中张口哭泣,看见面目狰狞的石兽对他频频眨眼,在一道刻有诅咒的台阶上有生以来第一次摔倒。疼痛过后,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令他获得了一种美妙的,对于空间的纵向意识。思想与感觉——他的影子和肉体,停止了自他出生起便不断重复的相互追逐与交替领先的游戏,终于合二为一。在那个决定性的片刻,只有鞭子才能让他再次站起。
②我等无意对这位杰出的汉学家有任何不敬。之所以照录原文,无非是想说明,对于弱者而言,那种来自强者的善意亦有可能被理解为一种冒犯与侵害。当代学者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谈到,所谓“东方”本就是西方所生造的概念,它被迫在欧洲人的心灵深处扮演异域与他者,从而让他们在不断地与之对照当中完成自身。在今天有无数的“世界主义者”,我们要质疑这种天真,尽管这让我们显得残忍。我们仍然要追问:你们所设想的那架世界的天平,它的平衡状态是否可能?美国后现代思想家让•鲍德里亚在一篇名为《狂欢节与食人族》的文章中引述了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在《想象的动物》中提及的一个镜中的族类,作为战败者他们被流放到镜子里。在博尔赫斯的文本中,太过遥远的胜利将使胜利者的后裔们忘却危机,镜中人终究会觅得可乘之机,越过镜面的藩篱回归现实,并反过来将那些曾囚禁他们的人囚入镜中。但鲍德里亚的观点却认为,反攻早已通过一种更为隐蔽也更为有效的方式打响了。当那些意得志满的胜利者们一次又一次地面对镜子,欣赏自己的姿态、修饰自己的仪容,沉醉于对自我的虚假的崇拜之中,他们便已经主动缴械投降,认可了镜中人对自己形象的所有批改。于是,镜中的虚影成了一种缥缈的现实,而现实的身体却成了一道可以触摸的虚影。在这两种想象的结局之中,无论我们认同哪一种,都不可能回避一个悲哀的问题:若是我们所有人都平等地分享现实,那么谁来填补镜中的空洞?当心啊,我的读者们!我的作者们!
十个白天和十一个夜晚之后,他们在一个叫作敦煌的地方停了下来。发号施令的翻译出于轻蔑而一言不发,只将一块石头丢在祖父的脊背上,制止他继续前行。祖父听到自己像一扇门那样被敲了一下,沉闷的回声在他空洞的身体里激荡了几个来回才蹿进脑海。他停下脚步看着眼前的一片黄土,感到十分茫然。两天之后,道士王圆箓引着伯希和一行走进了莫高窟。所谓“一行”,并未包含祖父和其他的苦力。他在洞外灼人的烈日下仰卧,百无聊赖地打量着翻译声情并茂地中转着左右二人的虚伪与狡诈。经过一整天的等待,他们的工作在入夜之后才开始进行。祖父和另几条汉子用一根浸过油的麻绳拖着一个沉重的木箱翻越鸣沙山,他嘴里喃喃自语,跟所有的沙粒一起背诵妖魔的诗句。绳断箱落,他追逐着被风沙裹走的卷宗与经文,在瞬息万变的沙丘上翻滚。当他终于抢出一张半朽的绢纸,竟突然从蛛丝般伸进耳孔中,纠缠着他的风缕里听到了祖先的开示。而此时他发觉,这风已不眠不休地在他的耳膜上挠了三十年。
纸上画有九个奇特的形象,三列三行,分别是四种工具、三种动物,以及一个人和一个复杂的图形,似乎旨在讲解某种智力游戏的玩法。在他的眼中,图在放大,而自己的影子却萎缩为杏仁大小,在其中奔突不已。他手捧着自己的整个世界,向它的深处逃遁而去,整整一天一夜,枪声接连在他耳后响起。在他的前方,新疆像一条由雪山、草原、沙漠、盐湖与化外之族构成的巨蛇,在中国西面盘绕了十一匝。他来到它的嘴边,肩头被咬了一口,又一次重重地跌倒在地。救助他的是一对年轻的哈萨克牧民,男人用英吉沙刮出弹头,在伤口浇青稞酒,女人将一碗羊奶递到他的唇边。他苏醒过来,开始说一种他自己也听不懂的语言,然后又突然停住,陷入沉思。最后,他终于微微一笑,说道:“对不起,我忘记了自己曾经活着。”
若有若无的启迪零星地出现,令祖父的旅途时而中断,时而折返,但在总体上仍一路西行。指引或以铭文的方式出现在某块墓碑上,或以一根插在马粪里的鸟羽为他点明方向。有时他不得不久久地等待、苦苦地寻求,他曾混迹于十一个民族当中,装扮成他们的模样,学会用七种语言咒骂、恐吓与求爱。他心甘情愿卖身为奴,跟随波斯商人穿越沙漠,经过印度与巴基斯坦,最后到达伊朗。在纸上的迷宫里,他已缩至微尘,渐不可认。
与祖母相遇的那天,他的身份是大不里士的一名花匠,他在金盏草、麝香和百合花中走过,双手沾满泥土,唇间叨念着古代经典中的职业教诲:“每一种花卉都专供一个神灵。”那位什叶派少女,巴列维王朝的一个稚嫩的牺牲品,在他管理的花园中跌倒昏迷。他用颤抖的手指轻触她被铅弹重创的肩头,领悟到那条缠绕他的巨蛇竟是整个世界,根本无从挣脱。他将她窝藏在自己的小屋里,怀着悲痛与释然的心情——他的旅程被迫终止,而他也因此得以卸下重负——每晚同她交媾,如同退勤的太阳骑乘着黑夜,驰骋在另外的半颗地球。
父亲的年代,世界的獠牙正高悬在欧洲的头顶。这个羸弱的早产儿,在成年之前始终直面死亡的阴霾。一岁时感染肺炎;三岁时被肝病折磨得死去活来;七岁时大战爆发,遥远的炮火似乎穿越重洋点燃了他,连续的高烧和几乎致命的脑膜炎令他神智不清、视听俱乱,他听到黄色的星辰划过红色的夜空,看到紫罗兰凋落和葡萄胀满枝头的巨响。十三岁那年,父亲失去了母亲,在祖母弥留之时,他首次开始作画。她垂死的躯体,让他感受到一种纯粹视觉的情欲。手执画笔的他,倒映在她的迷蒙的眼中,像被软禁在一滴水里,从未,也不可能再次拥有这种深不可测的亲密。在昏暗的烛光之下,他绘出了她呼出的最后一缕,混有弃世的嘲弄、恋世的欢歌和渎神的呐喊的气息。
过人的天资与难堪的贫困令他自暴自弃,早早地流连于低等的娼妓和丑陋的酒徒们中间。十七岁时他便染上梅毒,幸而也正是在同一年赢得了属于他的救赎。父亲天才的画作被收藏家们所留意,虽是绝对的小概率事件,但也是人力促成的结果。它们被年迈的祖父摆在花园的各个角落,在灌木丛中、在厕所的墙壁上,与浮萍一同在水面飘荡,随一根无花果树的枝条伸出墙外。对一个站在园外抬头看画的人,玩世不恭的少年说道:“对于我的画,你最好不要看它,而要闭起眼睛听它。”而这人便是我的外公,他身份未及确认的岳丈。他收购了他所有的画作,并带着他迁往伊斯坦布尔,让他住在他栽满郁金香的宅院中。他的房间里摆有三部留声机,在屋檐下、窗台前挂满大大小小的鸟笼,在西贝柳斯、帕格尼尼和李斯特形成的涓流、瀑布与喷泉周遭,清脆悦耳的鸟鸣声像彩色的雨点在房间里四下飞溅。
懵懂无知的母亲被浓艳的声色世界所诱,向他臣服、被他毁灭,成为他不可理喻的天份的牺牲品。父亲对房事并不特别热衷,但却着迷于女子缤纷的呻吟,从细不可闻的轻声叹息到惊痛交集的刺耳尖叫,在他的眼中仿佛一列美不胜收的光谱。他令她兴奋、令她迷惑、令她欣喜、令她受辱、令她疼痛、令她羞愧,他炮制她像肆无忌惮地、疯魔般地挤压一支颜料管。他留下了数百幅她的裸体肖像,造型无不荒淫,色泽无不怪诞,如同一朵朵在梅毒中溃烂的花蕾。
父亲的画作在伊斯坦布尔当地赢得了不大不小的关注,其中的一些被几位颇具影响的收藏家买下。在形形色色的沙龙与聚会中,这个言行傲慢但气质不俗的年轻人也俘获了几位贵妇、几个小姐和几名女仆。他因与一位恩主的妻子偷情,遭到毒打之后,被灌进一种由蜣螂虫、犀鸟粪、白松香以及少量的阿月浑子③调配而成的药物。他的头发、睫毛、眉毛和阴毛全部脱落,他的额头、双眼和阳具一一起癣生疮,仿佛在一个白日梦中衰变为一枚阿刻戎河里浮肿发臭的银杏。听觉于他,已退化为一种低级的底片感光技术,色彩全无、只余明暗;视觉则不再能判定一种气味的属性,只对其刺激强度有隐约的感知。也许只有嗅觉,是啊,也许嗅觉仍在加固他的生命印象。他像一只寒武纪海洋中的草履虫,嗅见严寒与疼痛,嗅见锋利,嗅见残忍的与猥亵的词语,嗅见妖魔的抽象。更进一步的,他嗅见了自身生而为人的另一种轮廓。
③生活于公元九世纪与十世纪之交的阿拉伯名医穆罕默德•本•扎卡里雅•拉齐(法国著名的阿拉伯学家于阿尔称此人为“伟大的医生”)在其著作《医学集成》中提到了这种毒物,他说,当时的巴格达贵族常常配制这种邪恶的药水,用于毒杀自己的政敌或情敌。另外,美国汉学家劳费尔在其著作《中国伊朗编》中对“阿月浑子”这种植物从文献学的角度做了全面的整理和辨析:阿月浑子,唐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称其为“阿月”;唐末五代时期药学家李珣的著作《海药本草》则称阿月浑子原产于中国,中文名称为“无名子”;在《广舆记》和《本草纲目拾遗》等中文古籍中则采用波斯词语的音译,称其为“苾思檀”,《广舆记》在介绍其形貌时说:“树叶类山茶。实类银杏。”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阿月浑子必为一种古代波斯人喜食的坚果。那么它的毒性又是从何而来呢?公元十世纪的阿拉伯学者和旅行家伊本•法基赫曾记录了一则奇闻,他说,有些食物在其产地是美味,但被游客带走之后,其性质却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异变,或变为石头,或化为灰烬,或干脆变成了剧毒之物。莫非,这毒药竟然就是乡愁?而故事中,这位凭听觉作画的艺术家罹患的以花为名的恶病本身也是一种“他乡之物”,一种极为奢侈和恐怖的舶来品。当然,其所谓的“异域”属性,主要是相对于欧洲人而言。事实上,考古发现表明,在原始人中即已有梅毒病例,但其在欧洲的大范围传播却和哥伦布远航美洲相关:“从庆祝哥伦布归来那时起,梅毒就使巴塞罗那居民惊恐万状,后来更飞快地蔓延开来;这是一种传播迅速、能致人死命的流行病。在四五年内,该病已周游欧洲,并以种种假想的名称从一国传到另一国,如那不勒斯病、法兰西病等……人们说,这是失败者的礼物和报复。”(引自费尔南•布罗代尔著作《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我的父亲死于梅毒,或死于一次影子的反噬。病榻、墙壁、地板,以及他置身其中的整个房间一起变得异常柔软。他在木材、砖石、布料和泥土拱起的浪头上翻滚,在肉体的泡沫中漂浮。一个船桨般瘦长的身影——被空间拧转、扭动,仿佛一条直立行走的水蟒——在他弥留之际,左右摇摆着向他靠近。它像一个爱人、一个智者,拥抱他、亲吻他,伸出巨大的舌头包住他的头颅,终结了一切迷惑。
在他的最后一幅画作中,只有一片黑暗,如你所知,这便是他留给他唯一后代的全部财产和全部真相,而我一生当中,从未脱下这层家传的、厚实的黑茧。一个将双眼遗落在前世的新生儿仰躺在肮脏的小床上,独自体验着令人难耐的阴冷潮湿,无动于衷地任由小便在两腿间流溺,略带遗憾又不无自得地感受着微微发胀的膀胱——像一只发酵的苹果——在胯下散发着些许的甜意。那便是我生命的开端,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所有。
必须到此为止了。在这个故事中出现的一干无名无姓的人们,他们此刻都已死去,像一群无助的羔羊被光阴的利爪扑倒在地,如一簇零落的秋叶静卧在自身的影子中。他们的离逝给了我某种授权。而我,这具苟存于世的活尸,尚未被允许谈及自己。
○●○●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