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阐释、重构与偏离
——浅谈《阿Q正传》的三部话剧改编
毛夫国
内容摘要:鲁迅的经典著作《阿Q正传》发表后,1949年前陈梦韶改编的《阿Q剧本》、许幸之改编的《阿Q正传》和田汉改编的《阿Q正传》都曾搬上舞台。通过对《阿Q正传》的三部话剧的改编过程、演出情况等相关史料的梳理和辨析,从而进一步分析和探讨三部话剧的改编策略,可以看出,三部改编话剧在阐释和重构《阿Q正传》中,均偏离了小说的创作主旨。
关键词:阿Q正传 话剧改编 阐释 重构 偏离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2)01-0032-11
毛夫国,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话剧史论、戏剧批评等。出版专著2部,合著3部,参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2部,在《戏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与批评》《艺术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先后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课题十余项。
导语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在1949年前曾多次被改编成话剧并搬上舞台,影响较大的有三种:1931年陈梦韶改编的六幕话剧《阿Q剧本》、1937年许幸之改编的同名六幕话剧《阿Q正传》、1937年田汉改编的同名五幕话剧《阿Q正传》。本文试梳理1949年前这三种话剧的改编过程、演出情况等,并对其改编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在鲁迅的小说中,两万多字的《阿Q正传》是最长的一篇。其成书过程与鲁迅其他小说不同,是唯一一篇在报纸连载的作品。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提到:“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1]真正创作《阿Q正传》是“挤出来的”[2],1921年底,鲁迅的学生、《晨报副镌》[3]的编辑孙伏园,约鲁迅为其附刊“开心话”栏目撰稿,于是《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镌》连载起来。为契合“开心话”栏目宗旨,鲁迅把笔名更换为“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4]之意。《阿Q正传》第一章的叙述语态和以前作品相比也变得“滑稽”,鲁迅曾说这“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5]
连载过程中,《阿Q正传》的文风有所转变,“表现的深切”开始流露,当连载到第二章时,鲁迅“似乎渐渐认真起来了;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6]。至1922年2月12日,《阿Q正传》连载完毕。
《阿Q正传》尚在连载时就得到很高的评价。1922年,沈雁冰在回复谭国棠的《通信》中说:“至于《晨报附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7]
《阿Q正传》发表后引起评论家和读者的关注,如果将其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以过去《阿Q正传》读者的众多,一旦搬上舞台,他的轰动,是不卜而即可预知的了”[8]。陈梦韶的剧本《阿Q剧本》,是根据小说《阿Q正传》最早改编的一个话剧剧本。
陈梦韶原名陈敦仁,是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读书时因话剧剧本改编与鲁迅交往较为密切。早在1926年,他就把古典小说《红楼梦》改编为十四幕(加上“序幕”为十五幕)话剧剧本《绛洞花主》,该剧本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版的将《红楼梦》改编为话剧的单行本。鲁迅为《绛洞花主》作序,建议陈梦韶寄给北新书局,看看能否出版。此书1928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但未及发行,国民党当局查封了书局,书和纸型被毁[9]。后来,陈梦韶又想把《阿Q正传》改编为话剧剧本,1928年春完成了改编,而此时鲁迅已离开厦门。同年《阿Q剧本》在厦门演出,由吴剑秋饰阿Q,李昭彩饰小尼姑。1931年华通书局出版了修改后的《阿Q剧本》,在该书前言中陈梦韶谈到了成稿及出版过程:“《阿Q剧本》脱稿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为双十中学校新剧团表演而写的。原稿匆促草成,难快人意。今春归自金陵,偶尔念及,复取旧稿,重行修改润饰。剧中许多对话动作仍从《阿Q正传》原文,编者既省许多麻烦,而实际上有些地方也并无重新措辞的必要。”[10]
华通书局的《阿Q剧本》“目次”中,首先即是“孙贵定博士序”,然翻阅全书不见该序。多年后,陈梦韶在《新版〈阿Q剧本〉后叙》中予以说明:“初版《阿Q剧本》,承教育家孙贵定博士,用炉火纯青之英语作序。因出版书局无英文铅字设备,被抽出。只于《目次》中保留‘孙贵定博士序’条目。余曾为之悒悒不乐,特此一语以表歉意。”[11]。从一本书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许多珍贵史料,《阿Q剧本》的英文序言惜已散佚。
许幸之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经过多次修改。
许幸之创作《阿Q正传》时,正值“上海各剧团春季联合公演之后,而准备着盛大的秋季公演前夜”,许认为作为中国戏剧节的联合公演,要有自己的创作剧本,为“发扬民族艺术的光华”,他决定把《阿Q正传》改编成剧本。当时曾有朋友劝他《阿Q正传》本身“缺乏戏剧性”,并且“连鲁迅先生生前,也颇不愿把《阿Q正传》改编为戏剧或电影”[12]。但他仍决定进行改编。
改至第三稿后,许幸之邀请夏衍、阿英、沈西苓、宋之的、孙师毅等举行了《阿Q正传》的剧本批评会。然而让许失望的是,这些“戏剧界的先进”们都觉得改编的《阿Q正传》是部失败之作。他们或认为“太拘束于原著”,或认为“太缺乏故事性”,或认为“结构上有许多问题”,总之都认为是一部“不堪入目的剧本”[13]。
改编剧本的工作暂时放下,不久许幸之听说中国旅行剧团的唐槐秋坐守南京,敦促时在南京的田汉将《阿Q正传》改编为剧本,以备在卡尔登戏院进行职业演出。许幸之给田汉写信,把油印本寄给他作为参考资料,希望田汉的剧本早出,作为自己“改编工作的楷模”[14]。但田汉的剧本迟迟不发表,许幸之再次修改后,把《阿Q正传》交给沈起予在《光明》半月刊发表。1939年,上海中法戏剧社出版了许幸之的《阿Q正传》。
1939年7月,中法剧社在上海的辣斐花园剧场进行了首场公演,并且作为该社建社的开幕大戏,许幸之亲自导演《阿Q正传》。为扩大影响,中法剧社刊行了《中法剧社公演〈阿Q正传〉特刊》,该刊在介绍了中法剧社的筹备和组织后,开篇即是景宋(许广平)所作《阿Q的上演》一文,同时收录了许幸之《〈阿Q正传〉的改编经过及其导演计划》和一些评论文章。
许幸之导演《阿Q正传》一直演至30日,历时半个月。7月30日的上海,同时又有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的工华、益友、精武、职妇四剧团联合演出田汉改编的剧本《阿Q正传》。在1939年沦陷的上海,同日竟有两个剧团上演话剧《阿Q正传》,被当时的评论家称为“孤岛剧运史上之盛事”[15]。
田汉的五幕话剧《阿Q正传》,改编历时也较长,始于1934年。《田汉全集》介绍说其:“第一幕及第二幕的一部分曾在《中华日报·戏》周刊1—9期、11—21期(1934年8月—12月)连载”[16]。这个记载是不准确的,应当加以适当说明。当时《中华日报·戏》周刊刊登的是袁梅(即袁牧之)的《阿Q正传》,是根据田汉的剧本改译成绍兴话,似乎两人都是作者为妥[17]。但至少可以看出,1934年时,田汉已写出部分《阿Q正传》。直至1937年他又重写《阿Q正传》,剧本发表于创刊号的《戏剧时代》,同年由上海戏剧时代出版社出版。
田汉话剧《阿Q正传》,1937年12月由中国旅行剧团首演于武汉,洪深任导演。田汉认为其上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我们应认识目前的抗战便是辛亥革命的任务的完成。《阿Q正传》写的恰是辛亥革命前后,而直至今日止当时的主流革命对象仍然存在。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之流,以汉奸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左右。第二,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在对日抗战中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这妨害我们采取正确的战略,妨害我们认清谁是我们的朋友。第三,阿Q作者鲁迅氏至死不妥协的精神在滔滔的今日有提倡宝爱的必要。”[18]可见田汉的改编着眼于时代的现实意义。田汉话剧《阿Q正传》演出场次较多,1938年在上海由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同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皖南新四军军部礼堂演出第二、四幕,由李增援任导演;1939年在上海由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的工华、益友、精武、职妇四剧团联合演出;1942年国防艺术社在桂林演出。
二
将小说改编为话剧,首先面临的是对作品的细致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改编既是一种研究,“因为要改编,就必须理解作家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基本情况,对所改编的作品更要求有透彻的理解”[19],也是对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阿Q正传》,尤其又是著名作家鲁迅的作品,对于小说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的解读无疑至关重要。
关于《阿Q正传》创作的主题思想,鲁迅曾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说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20],后又从自身经历言:“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21]
《阿Q正传》发表后不久,评论界非常关注。1922年3月,周作人评价其主旨是“一篇讽刺小说”,多用反语和“冷嘲”,认为小说“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副苦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阿Q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总体上,阿Q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22]对于阿Q的类型性,沈雁冰亦有同感:“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但或者是由于‘解减饰非’的心理,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23]
但《阿Q正传》是一部改编难度很大的作品。首先,《阿Q正传》思想性强,情节性不强,缺乏戏剧性,需要对小说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上世纪30年代唯易看到了《阿Q正传》改编的危险:“首先是阿Q正传的‘戏剧性’。鲁迅先生的原作,只是着力的刻画了这一人物的灵魂,性格,以及那人物所处的背景,当时的社会情态的片面。在结构方面,是不怎么严密的,从实说来,这小说的描写深刻有余,而情节的紧凑则不足。……《阿Q正传》这小说搬上舞台,我很担忧不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因为戏剧和小说所表现的材料应当略有不同,前者必须有紧密连贯的‘情节’,而后者有时都可以无须。”[24]这是对鲁迅小说的话剧改编极为深刻的见解。对此,当时的评论家欧阳凡海也有同感:“《阿Q正传》这篇小说要编成剧本,比任何其他的小说困难得多。这篇小说的全体所叙述的是一个阿Q,除阿Q之外,出场的人物很少。”虽然有的短篇小说有固定的场面,以时间作为纵的线索,适合改编成剧本,但《阿Q正传》“既不是固定于一时一地的短篇小说,也没有严整的故事发展,其中所写的阿Q的各种经历只是当作阿Q一生中的几件大事藉以表现他的性格,在一个小说家的笔墨之下要叙述一个人,很容易地可以由叙述这人今年的事而一笔掉到他明年的事,可以由叙述这人的在这儿的事而一笔掉到他那儿的事,转折之间可以活泼自如。而写戏剧就不这么便当,这儿那儿,此时彼时的事,都要在一定的场面或一定的人嘴里表达出来。就如《阿Q正传》中,原作者只要以阿Q为中心,其他阿Q的环境,阿Q的经历与个性,阿Q过去,现在的各种事故,以至将来的愿望,阿Q在这里那里的行动,全都可以绕着阿Q由作者就笔调遣的丝丝缕缕。”[25]欧阳凡海谈论了文学和话剧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的区别,从改编的实际操作上进行了详细阐述,当然,他的论述起点是忠实于原著的改编。
其次,对作品思想主题和阿Q人物形象的理解也是难点,《阿Q正传》刻画了“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达到对国民性的批判,也表现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群众的不彻底性,这些都是不易呈现于舞台的。欧阳凡海看到了如改编不好,容易把阿Q塑造成一个可笑或无聊的角色:“在内容上,阿Q的性格可以说比什么人物的性格都难把握,倘使一不小心,就会把他变成一个可笑或无聊的角色搬到舞台上供观众一哄而散。此外阿Q的身世,他前后所经的各事都很平常,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小说的读者因阿Q而出神,至于舞台上的效果就并不这么容易了。看戏好像听音乐一样,没有起伏抑扬到底是不行的。虽然这起伏抑扬并不一定要惊心动魄,但就是家庭琐事的叙述,剧作者也不应该忘记了在有限的几个舞台面上予以波动。而要将《阿Q正传》编成剧本时不在这块暗礁上失足,在我看来,也是一件困难的事。”[26]唯易也认为阿Q精神不易用戏剧的动作性加以表现:“但更重要的是‘阿Q精神’动作的表现,恐怕未必比文字的刻画更为胜任。阿Q一上舞台形象化固然更形象化了,但精神许不会比纸上更为饱满活跃。”他甚至认为《阿Q正传》的剧本改编“决不比创作一部好剧本较为省力”[27]。
三
对于《阿Q正传》的改编,鲁迅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话剧或电影,另一方面又警惕改编脱离其创作的主题思想。1930年王乔南曾将《阿Q正传》改编成电影剧本《女人和面包》[28]收入《阿Q及其他》(时名为《阿Q》),把剧本寄给鲁迅征求意见。同年10月13日鲁迅在《致王乔南》信中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信后又言:“我也知道先生编后,未必上演,但既成剧本,便有上演的可能,故答复如上也。”[29]《阿Q正传》的思想性强,鲁迅深知小说的情节性不强,唯恐改编后只剩滑稽或哀怜,远离小说的创作初衷。《阿Q正传》第一章“序”,“戏说”写法所带来的“喜剧”色彩明显,契合“开心话”栏目,但随着创作的进行,鲁迅创作“表现的深切”开始流露,第四章起则疏淡很多,这种同一篇小说前后话语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差异,已有学者关注到[30],这也给小说创作主旨的理解带来障碍。在同年11月14日鲁迅在《致王乔南》信中又说:“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31]似乎对王乔南的改编很不满意,王乔南把改编后的题目命名为《女人和面包》,《阿Q正传》的主要内容变成了色和食,通俗性尽显,离原著主旨相距甚远。
对《阿Q正传》话剧改编,鲁迅还是热心支持的。1934年,袁梅(袁牧之)改编的《阿Q正传》剧本,刊于《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每隔一周发表,共连载了十九期,但未连载完毕而停止。《戏》周刊曾刊发了致鲁迅的公开信,征求对改编的意见。鲁迅曾先后复信两封,在第二封回信中,对于《戏》周刊上刊载的话剧使用绍兴方言、人名等提出了建议。他谈到为避免另生枝节,《阿Q正传》中的人物用《百家姓》上最初两字,不造成阿Q是绍兴人的感觉,因此鲁迅不太赞成使用绍兴方言:“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在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Q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32]对于改编成绍兴话,鲁迅是持批评意见的,并且鲁迅说剧本中阿Q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33],袁牧之是浙江宁波人,看来他所改译的绍兴话还是不纯正的。
甚至连阿Q画像,鲁迅也发表了指导意见:“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34]这对于舞台演出具有重要意义,可见鲁迅对这个剧本的上演还是期待的。但袁牧之的改编剧本既未连载完,亦未上演。多年后,未完成稿剧本收入《袁牧之全集·话剧卷》出版[35]。这是唯一一个与鲁迅有互动的《阿Q正传》的话剧改编剧本,因为袁牧之是在田汉剧本基础上改译的,两个剧本在结构和内容上基本一致,所以某些程度上,也可看成是鲁迅对田汉改编剧本的意见。
至1936年,在《致沈西苓信》中,鲁迅对于某些改编极其不满甚至有些愤怒:“我现在的意思,以为××××××乃是天下第一等蠢物,一经他们××,作品一定遭殃,还不如远而避之的好。”[36]明确表示不同意改编成电影:“况且《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37]鲁迅对《阿Q正传》发表后的评论都不甚满意,改编成话剧也会面临相似情况,他对于脱离其创作主旨的改编是愤怒的。当时曾有评论家表示了同样的担忧:“一听到《阿Q正传》被编成戏剧,而且正式上演,我就担心阿Q要成了‘小丑’,在老爷,太太,小姐,少爷,‘花钱快乐’的口号下,成为‘取辱’的工具。”[38]
四
小说家的笔触可以任意触及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运用语言描绘环境甚至心理活动等,全方位地展示人物与情节。相较于小说不受时空的局限,戏剧舞台的时空受限,其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节等都需高度集中。前面所谈《阿Q正传》的三部话剧改编,在分幕设置、内容增删上都进行了适合剧情的调整和处理。
分幕设置上,陈本分为六幕,地点分别选择在未庄酒店、赵太爷家、土谷祠、静修庵外和审判厅公堂。许本也是六幕,前面还有“序幕”,地点分别为赵太爷家、静修庵门前、咸亨酒店、土谷祠、县衙门大厅、监狱和刑场。田本分为五幕,地点分别为咸亨酒店、赵太爷家厨房、静修庵外、咸亨酒店、绍兴监狱。三个剧本地点的选择相差不大,区别在于许本第六幕地点有两处,其中最后一处是刑场,表现鲁迅小说《药》中的主题;田本最后一幕将地点设在绍兴监狱,以反映封建社会的腐败,激发人们的斗志。
分幕设置与地点的选择有关。彼时的话剧演出尚不能利用灯光等做不同场地的灵活切换,陈梦韶曾对阿Q出现的场地进行了汇总和分析,为了让剧情在一定的地点展现,他选择了能够“概括阿Q一生生活的事实的”、“最适切明白的表现的”事实、“富有表演的情感和趣味的”事实[39]作为场地进行舞台呈现。
其次是内容的增删。将小说改编为话剧,要在对文学作品细致解读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取舍和解构,然后重新组织编码。在人物选择上,陈本主要围绕小说《阿Q正传》设置人物,基本为小说之内的。许本和田本则不拘于小说《阿Q正传》,把鲁迅其他小说中的人物也纳入进来,许本采用了鲁迅小说《明天》《药》《孔乙己》中的人物,而田汉不仅把《明天》《药》《孔乙己》《故乡》《风波》等短篇中的人物收进来,而且还增加了马育才、吴之光、陈菊生等人。
对于话剧改编中的人物不限于小说《阿Q正传》,鲁迅是表示赞同的。1934年他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40]鲁迅的这点意见,20世纪80年代也被陈白尘和梅阡在改编《阿Q正传》时所采用。
对于许本和田本,当时有评论家曾对这两个剧本的人物扩展表示了担心:“许幸之改编的,将鲁迅先生自选集中孔乙己等人物全拉了进去,据说,这是为了要增强戏剧性的原因,同时在原作中阿Q不大说话的,现在舞台上的阿Q,已变成罗唆多话的人物了。”从忠实于原著的角度,希望“改编者务必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勿多事更动,以免丧失了原作的精神”。[41]人物的扩充,使许本和田本所表现的主题必然要包含其他小说,然而都取名《阿Q正传》,剧中表现阿Q的戏份肯定会有所减少,某些程度上可能会存在文题不符的问题。
关于剧中人物的性格,陈梦韶在改编时,侧重于对阿Q形象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阿Q是无产阶级和无智识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只能做个“忠诚的劳动者”“徒具有‘人类性’的孤独者”和“人间冤抑的无告者”[42]。基于此,在《阿Q剧本》里,陈梦韶“处处要表现阿Q是个忠诚的劳动者”[43],把造成阿Q悲剧的原因归咎于社会环境。
许本在出场人物介绍中,除外形外,还包含了人物性格方面的介绍,如把阿Q介绍为:“为人忠厚,憨直,愚昧无知,不善言语,发急时且有口吃。……受人打骂侮辱后,每用精神胜利法以自慰。痛恨豪绅,排斥异端,而歪曲革命。”这种人物性格的介绍不仅有些地方与原著不太符合,而且限制了观众的想象。另外,许本对原著中一些人物的性格进行了改写,吴妈的形象由安分守己的农村妇女变得风骚有情趣,且和赵老太爷有染;他还增加了假洋鬼子追求小尼姑的情节,削弱了剧本的思想表现力度。
一般来说,话剧注重情节的线性叙述。但小说《阿Q正传》前三章“序”“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并非线性叙述,而是对阿Q精神胜利法等性格层面的介绍。龙永干曾注意到小说的这个特点:“就整个作品的结构来看,前部是‘断面’的,而后部则是‘线性’的。”[44]所以在改编成话剧时,陈梦韶、许幸之和田汉都是从小说的第四章开始的,前三章的故事适当予以保留,舍去了其中的解说性文字。
内容设置上,陈本在第四幕静修庵门外戏份不足,于是添加了一位男汉,增加了阿Q和男汉对话的情节,然后他们一起进城,但二人对话中交代前面的事情过多,稍嫌多余。许本有幕外音介绍剧情,如开始对阿Q的介绍,赵太爷不让他姓赵等,在剧情处理上比较灵活。相较而言,田本对原著内容增删是最多的,尤其是最后一幕,添加了一些揭露官场腐败的内容,如陈菊生与赵老太爷打官司失败而坐牢,革命党马育才在监牢受苦,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宣传鼓动色彩鲜明,一些情节明显与原著不太相符。
小说中几处关键情节的改编,三个剧本的处理各不相同。一是小说中阿Q从城里回来后,未庄的人看到他发达了,都很敬畏;又听说阿Q在白举人家做工,愈加敬畏。尤其听说阿Q带来了蓝绸裙和洋纱衫,连赵太爷都开始关注,请阿Q来赵府询问。然而感觉阿Q有抢劫的嫌疑时,未庄人对阿Q的态度又“敬而远之”。未庄人态度的几次变化,在线性时间上剧本无法在一段时间内予以表现,陈本中只有未庄人第一次敬畏,赵太爷来到酒店见阿Q,称呼未改。许本和田本中则没有这段情节。二是小说中阿Q在未庄听到革命能让人敬畏和害怕,酒后高呼革命,未庄人惊惧,连赵太爷都改了称呼叫其“老Q”,赵白眼称作“阿Q哥”,是因为他们害怕革命者;随着时局的变化,未庄人看到革命与阿Q无关,对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受到冷落的阿Q又去找假洋鬼子要求革命,被拒绝。这段情节在陈本中没有,许本是在赵太爷买东西时称“老Q”,只有田本表现了赵太爷怕革命称“老Q”。三是小说中描写逮捕阿Q时很夸张,用了一队团丁,还在土谷祠外架起了机关枪。陈本和田本中无此处,田本是以阿Q在监狱中用回忆形式出现抓捕和审问情节的。许本有抓捕但未提到机关枪。四是小说描写辛亥革命后,城里没有什么大异样,城里知县大老爷仍在官位上,带兵的老把总也依旧。陈本和许本均没有表现,田本是监狱中马育才在对话中谈起这点的。
把《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能否表现阿Q人物形象和作品主题,是改编者首先所要着重考虑的,“情节虽可改窜,改窜之后的效果是否会比原来的小说好,甚至能否保持原作的精神,实在是一个问题。”[45]1939年,许幸之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剧作者任务并不在于忠实原著”,改编的重点在于“要使原著在获得多数的读者之外,获得更多数的观众,这才是剧作者忠实于原著的唯一方针”。[46]但不同的人对于忠实原著有着不同的理解。
整体来看,陈本在人物和事件上基本符合原著,但表现的内容在思想性上存有差距。许本重在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表现小说内容,他曾对《阿Q正传》中的人物进行了分类:“为了分析那典型的环境中所产生的典型人物,我特为把《阿Q正传》中的人物分为四种集团:一是以赵太爷为中心,赵太太,秀才,秀才娘子,赵白眼,赵司晨,邹七嫂等处理成封建的豪绅地主及其走狗的一群。二是以假洋鬼子为中心,县官,差人,地保,刽子手等半封建的贪官污吏及其走狗的一群。三是以老拱为中心,蓝皮阿五,掌柜,酒保,单四嫂,王九妈,老尼姑,小尼姑等,处理成小市民的中立主义者的一群。四是以阿Q为中心,吴妈,孔乙己,王胡,小D等,处理成在以上两大势力之间被压迫害的一群。”[47]许本在幕外音的运用上较合理,但剧本内容暧昧感情过多,主题表现有些游离。田本重在表现反封建的主题,剧本借马育才的话说:“死了一个天真的农民。朋友们,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残余封建势力还非常的大,我们还得继续奋斗。不过我们首先枪毙我们每个人意识里面的阿Q吧。”[48]宣传鼓动的意味较强,体现了改编的当下性,某些程度上只表现了《阿Q正传》的部分主题思想。
总体来看,1949年前改编的这三部剧本,在阐释和重构《阿Q正传》中,偏离了小说创作的主题思想,20世纪40年代曾有论者认为许幸之和田汉都“未能抓住原著的精妙处”[49],《阿Q正传》的话剧改编实在是一条艰难之路。
参考文献:
[1]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6页。(以下《鲁迅全集》版本同此,不再标注)
[2]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4页。
[3] 1921年10月12日《晨报副镌》出版时,报头是《晨报副镌》,报眉却是《晨报附刊》。主编孙伏园曾解释说,《附刊》是鲁迅取的名字,他认为《晨报》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登载学术文艺,随同《晨报》附送,所以取名《附刊》,即“另外一张”的意思。后来请《晨报》总编辑蒲伯英题写版头时,把“附刊”写成了“副镌”,为了尊重鲁迅的原意,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见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中《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注释中说“本篇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这个注释有误,1925年7月14日报头才由《晨报副镌》改为《晨报副刊》,一般说《晨报副刊》是1925年10月后徐志摩任主编时的刊名。本文采用《晨报副镌》。
[4]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6页。
[5]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6页。
[6] 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97页。
[7] 《通信》,《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第2号。
[8] 鸿勋:《搬上舞台的〈阿Q正传〉》,《月报》(上海),1937年第1卷第3期。
[9] 参阅陈梦韶《回忆鲁迅为〈绛洞花主〉剧本作〈小引〉的经过》,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四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153页。1935年,陈梦韶据其大意进行“节录”,在《闽南日报》副刊连载,仅载八幕,报社又停刊。1980年陈梦韶根据八幕铅印剪贴本,整理恢复原剧面目,《绛洞花主》于2005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10] 陈梦韶:《写在本剧之前》,《阿Q剧本》,上海: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第16页。
[11] 转引自陈元胜:《梦韶〈阿Q剧本〉英序逸闻新证》,见《上海鲁迅研究·鲁迅与上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28页
[12] 许幸之:《〈阿Q正传〉话剧改写本后记》,《阿Q正传》,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社,1939年,第10页。
[13] 许幸之:《〈阿Q正传〉话剧改写本后记》,《阿Q正传》,第10—11页。
[14] 许幸之:《〈阿Q正传〉话剧改写本后记》,《阿Q正传》,第11页。
[15] 松青:《这一月》,《剧场艺术》,1939年第10期。
[16] 见《田汉全集》第四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4页。1983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田汉文集》(五)就没有类似记载,《第五卷说明》中只说“发表于五至六月《戏剧时代》第一卷第一、二期”。
[17] (日) 饭冢容的《中国现当代话剧舞台上的鲁迅作品》(《文化艺术研究》,2009年第5期)和何吉贤的《从三个角度看“抗战演剧”的实践》(《艺术评论》,2010年第5期)文章中曾有具体探讨。
[18] 田汉:《关于〈阿Q正传〉的上演》,《抗战戏剧》,1937年第3期。
[19] 邵伯周:《〈阿Q正传〉研究纵横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77页。
[20] 鲁迅:《〈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七卷,第83页。
[21] 鲁迅:《〈阿Q正传〉序》,《鲁迅全集》第七卷,第84页。
[22]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镌》,1922年3月19日。
[23] 雁冰:《读〈呐喊〉》,《文学》周刊,第91期,1923年10月8日。
[24] 唯易:《论阿Q搬上舞台》,《东方快报》(北京),1937年4月22日。
[25] 欧阳凡海:《评两个〈阿Q正传〉的剧本》,《文学》月刊(上海),1937年第9卷第2号。
[26] 欧阳凡海:《评两个〈阿Q正传〉的剧本》。
[27] 唯易:《论阿Q搬上舞台》。
[28] 该电影剧本收入《阿Q及其他》中。见力工(王乔南)著:《阿Q及其他》,北京:北平文化学社、东华书店,1932年。
[29] 鲁迅:《致王乔南》,《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45页。
[30] 龙永干:《报纸约稿、题旨取向与〈阿Q正传〉的叙事骨架及肌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期。
[31] 鲁迅:《致王乔南》,《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247页。
[32]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50页。
[33]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48—149页。
[34] 鲁迅:《寄〈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54页。
[35] 2019年8月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阿Q正传》剧目下注释:“原剧系田汉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由袁牧之译成绍兴话。”
[36] 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中,说此空字系刊载手迹制版的《电影戏剧》编者所删。“××××××”具体指谁,已不可考。
[37] 鲁迅:《致沈西苓》,《鲁迅全集》第十四卷,第119页。
[38] 冶秋:《阿Q正传》,《抗战文艺》(重庆),1940年第6卷第4期。
[39] 陈梦韶:《写在本剧之前》,《阿Q剧本》,第4—5页。
[40] 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48页。
[41] 影:《阿Q正传》,《东方快报》(北京),1937年1月29日。
[42] 陈梦韶:《写在本剧之前》,《阿Q剧本》,第1—2页。
[43] 陈梦韶:《写在本剧之前》,《阿Q剧本》,第8页。
[44] 龙永干:《报纸约稿、题旨取向与〈阿Q正传〉的叙事骨架及肌理》。
[45] 唯易:《论阿Q搬上舞台》。
[46] 许幸之:《〈阿Q正传〉话剧改写本后记》,《阿Q正传》,第13页。
[47] 许幸之:《〈阿Q正传〉话剧改写本后记》,《阿Q正传》,第13—14页。
[48] 见田汉《阿Q正传》,《戏剧时代》,1937年一卷第2期。
[49] 佩寒:《〈阿Q正传〉与〈阿Q正传〉剧本》,《华光》(北京),1940年第2卷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关于我们
《戏剧艺术》是上海戏剧学院主办的学报,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高校社科精品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投稿须知
《戏剧艺术》是一份建立在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基础上的学术期刊。本刊欢迎戏剧理论、批评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来稿。内容希望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尤其期盼关注当前戏剧实践、学理性强的力作。来稿篇幅在万字左右为宜,力求杜绝种种学术不端现象,务请作者文责自负。所有来稿请参照以下约定,如您稍加注意,则可减轻日后编辑的工作量,亦可避免稿件在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反复修改,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将不胜感激。
本刊实行在线投稿。在线投稿网址:
http://cbqk.sta.edu.cn系本刊唯一投稿通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刊不接受批量投稿(半年内投稿数量大于1则视为批量投稿),更不可以一稿多投。
本刊审稿时间为3-6月,审稿流程含一审、二审、三审、外审等,最终结果有退稿、录用两种情况,其他皆可理解为正在审理中,敬请耐心等候。如有疑问,可致函杂志公邮theatrearts@163.com,编辑部将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本刊从未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若发现类似信息,可视为诈骗行为。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站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相关机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附:《戏剧艺术》稿件格式规范
1.作者简介:姓名及二级工作单位(如,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
2.基金项目:含来源、名称及批准号或项目编号。
3.内容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篇幅为200-300字。
4.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5.注释和参考文献:均采用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格式如下(参考2020年以来我刊):
(1)注号:用“①、②、③······”。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请注意各注项后的标点符号不要用错):
① [专著]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② [期刊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第*期。
③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④ [报纸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
⑤ [外文版著作、期刊、论文集、报纸等]采用芝加哥格式: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名首字母大写。书名、刊名用斜体。
6.正文中首次出现的新的外来名词和术语、新的作家作品名和人名请附英文原文,并用括号括起。
欢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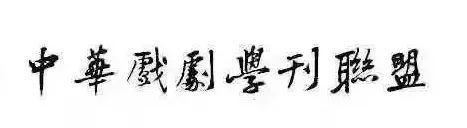

制作:史晶
责编:计敏
编审:李伟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