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華(主持):各位來賓大家好。第19屆上海市社會科學普及活動周——佛教文學座談分享現在開始。這也是悅悅沙龍第300場活動,在此特別感謝悅悅圖書,也感謝上海市古典文學學會。
首先給大家介紹一下兩位嘉賓:陳允吉老師,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中文系的前系主任。張煜老師,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中國文學的研究員。感謝兩位老師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陳允吉,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復旦中文系前系主任。

張煜,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

彭華:接下來,作爲責編我給大家講一下這本新書。它收録了新的篇目——“賈島詩‘獨行’、‘數息’一聯詞義小箋”是2018年的。其次是兩篇訪談録,談季羨林先生和饒宗頤先生。再看裝幀,陳老師是把它作爲《唐音佛教辨思録》(修訂本)的姊妹篇推出的。

彭華:《唐音佛教辨思録》原是1988年10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最初的版本,初版是簡體字的。當時的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編輯們對它評價很高,在介紹新書的時候説:這本書運用了很多實證材料,善於就由一個小的話題進行縱深的開掘,分析非常細緻入微,又很有獨創性。果然這本書在1992年的時候獲得了全國第二屆古籍優秀圖書的一等獎。這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權輸出的案例,它向中國臺灣地區輸出了一個繁體字版,後來復旦大學出版社獲得了這本書的版權,就推出了繁體修訂版。我抛磚引玉的環節就到此爲止,接下來由張煜老師接著講講書中的精彩篇目。
張煜:大家好!今天到這裏來,主要抱着學習的態度。對陳老師的書,我並不敢進行點評。
書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就是《關於王梵志傳説的探源與分析》。這篇文章非常能够看出陳老師從事俗文學研究的功力。書裏陳老師也談到了他和饒宗頤先生的一些學術交往,饒先生對這一篇評價很高,説這篇文章通過對王梵志傳説的探源與分析,從而對王梵志詩的作者問題做了很有價值的探索,“基本上是一錘定音的”。
學術界關於王梵志的研究情況:多數學者認爲王梵志實有其人;而入矢義高和戴密微認爲這是神話故事,不具有記録或暗喻真人真事的史實價值。項楚在入矢義高、戴密微的基礎上有所拓展,並援引了類似的材料,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最終還是從“伊尹生空桑”的角度理解王梵志降生故事。陳老師從佛經裏面找到源頭,給出了很有説服力的分析解釋,並且通過實證的方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另外就是像《王維的輞川〈華子岡〉詩與佛家“飛鳥喻”》,這篇文章是發在《文學遺產》上的。陳老師的文章有個特點,經常都是從非常具體的、小的問題入手,比如像這首詩的話,它就是一首非常短小的詩:“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陳老師把它和佛經裏面的一些譬喻相聯繫。因爲在佛教譬喻裏面,爲了善巧方便,會有“Avadāna”。陳老師的文章除了能够找到這些中國文學表述在佛經裏面的一些具體的出典以外,還都寫得非常優美,我覺得這篇文章也是一個代表。他説:“故當詩人向晚偕裴迪登上華子岡、目送衆鳥相繼高飛遠去漸至影蹤消匿之際,憑他平時研習佛典積累的體驗,能借用這些譬喻於介爾一念間契入悟境,由鳥飛空中之次第杳逝而了知世上所有事物的空虛無常。就同樹木百草春榮秋謝、含生群品死亡相逼一樣,人縱爲萬靈之長,亦安能歷久住世。它們全都處在刹那相續的生滅變化之中,猶如飛鳥行空不稍停歇。”陳老師的文章並不是只有學理。他平時對我們的要求也是這樣,既要有義理,同時還要有考據,另外還要有辭章。就是説文章需要寫得從容,同時也要優美。
張煜:像《王維的〈鹿柴〉詩與大乘中道觀》,也是陳老師自己感覺寫得比較好的。陳老師的單篇論文,幾乎每一篇裏面都會有新意,包括這一篇有關“大乘中道觀”的文章。羅宗強先生認爲像這篇文章所作的細緻分析“海內無第二人”。它裏面主要談到了,王維的詩歌經常喜歡寫一些瞬間的變幻,比方像朝露,或者像一些很細微的光綫或者聲音,忽隱忽現的這樣一些東西,他這樣的一種很細微的感觸覺知,其與“大乘中道觀”之間,比如説“空”和“有”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文章裏面聯繫到龍樹的《中論》,説到“衆因緣生法,我説即是空。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我這樣講聽上去是枯燥的,但是陳老師他能够用很優美的語言,非常從容地來論述,最後得出結論,即王維詩歌和這些哲學思想之間的關係。陳老師經常跟我們説,研究哲學的人很多,研究詩歌的人也很多,怎樣能够把宗教和文學結合起來研究,就好像做衣服一樣,你要把它縫在一起,需要很多極其細密的針綫,而不是牽強附會地把它們湊在一起。既要有精細的分析,還要有透闢的感悟。
張煜:講李賀的這一篇《説李賀〈秦王飲酒〉中的“獰”——兼談李賀的美感趣味和心理特徵》,我覺得大家也可以關注一下。這篇文章從“獰”這個字出發,有些人認爲這是一個錯字,而陳老師認爲這個地方沒有錯。事實上正是這個用字,反映出李賀那種非常特別的詩風,他有一句話叫做“筆補造化天無功”,就是説他的藝術實踐能够創造出一個高於我們所看到的真實的自然界,帶著他非常強烈的主觀色彩的世界。大家可以看到“獰”這個詞在李賀的詩歌裏面出現次數很多。
張煜:另外還像這裏面談到大目犍連小名“羅卜”的問題,現在很多人都學過梵文,我也學過一點梵文,在梵文裏面,目連就是一種類似豆子的東西,但是你怎麼樣把豆子變成“羅卜”,這個就是會梵文的人也不一定能够找到這些資料。而陳老師就通過《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集》《文殊師利問經》等典籍,能够深入進去解決這樣的一些問題。然而他並沒有只是停留在這樣一個對具體問題的探討,而是繼續向前推,説其實變文並不一定是唐代才有的,很有可能是在東晉的時候已開始流行。所以我的同門馮國棟曾經這樣稱讚陳老師的一些文章,他説:“讀先生文,如涉險道,山環路轉,百折千回,造勝入微處,忽雲開雨霽,冰解的破。始知先生佈局之巧妙、結撰之用心、針脚之細密、析辨之精微。故其文不特爲文史考據之作,以美文視之,無愧也。昔柳河東讀昌黎文,歎云: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吾于先生之文得之矣。”大家看陳老師的文章,能够從裏面感受到這樣一種非常驚心動魄的過程,就像是在跟龍虎搏鬥一樣,深入這些材料之中,一步一步地推導,最後得出結論。我就講這麼多。謝謝。

陳允吉:今天很高興,以這種沙龍的形式跟同學們見面。接下來我想談談我的唐代文學研究,以及跟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關係。
我研究佛教,是在痛苦當中做出的抉擇。大概大學三年級的時候,聽王運熙先生給我們上“唐宋文學史”,我是課代表,所以有較多機會向王先生請教。從那時候開始就專門讀唐代文學的東西。我記得讀的第一本唐代文學專書,就是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讀下來以後覺得古書浩如烟海,應該要系統地讀一些書了。所以後來再讀《唐人選唐詩》《唐詩紀事》《唐詩品匯》《唐賢三昧集》,讀唐代的一些筆記小説和文學史的著作,又讀《全唐詩》,到大學畢業的時候,《全唐詩》看了一百五十多卷。還看《歷代詩話》《歷代詩話續編》,那時候《清詩話》已經出來了,我都看了一遍。後來留校了,王先生是古典文學教研室的領導,他跟我説你唐代文學看得倒蠻多,也應該多看點歷史,多看點哲學,多接觸一些古代文化。我當時下了一個決心,我不僅看《史記》《漢書》,而且要看《後漢書》,要看《三國志》,最好把二十四史全部讀一遍。顧頡剛先生,二十四史從頭至尾讀了兩遍。這個還不算多,呂思勉先生曾將二十四史從頭至尾讀過三遍。
我定下來的這個研究的方向,還是研究唐代文學。但是碰到個主要的問題,自己寫不出什麼有新意的東西,不管哪一個作家,李白、杜甫,或者劉禹錫,寫的東西好像人家都已經談過了。
陳允吉:後來偶然的機會,讀了任繼愈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對我的影響非常深刻。我開始的時候呢,什麼都讀不懂的。比如《五燈會元》是本什麼書?很想得到解釋。但條件艱苦,資料匱乏,一度沒有人可問。後來偶然碰到機會,在學校附近一家小飯店裏請教郭紹虞先生,才知道是一本記載禪宗僧侶言論的燈録。這時我就開始學習佛教相關的東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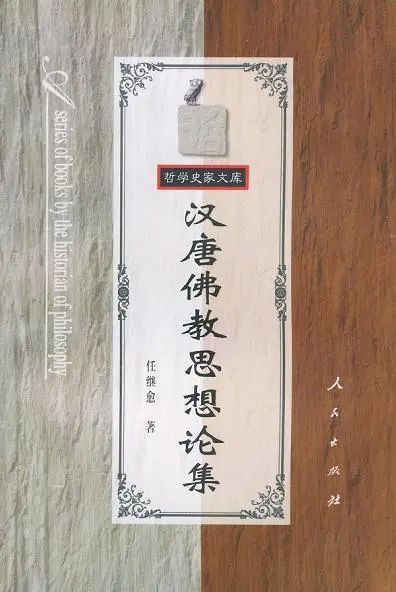
1971年春開始參與點校二十四史裏的《舊唐書》。點校二十四史給我們帶來一個很大的機遇。當時圖書館是封起來的,不能借書。點校二十四史要查大量的書,我們二十四史組有一張集體借書的卡。可以到書庫裏面去隨便挑書。在“文化大革命”當中,在整個氣氛非常封閉的情況下,居然能够有機會讀到佛經,這是很好的條件。所以我有一長段時間,白天點校二十四史,晚上看佛經——《妙法蓮華經》《思益梵天經》《維摩詰所説經》《大般涅槃經》《金剛般若經》《楞伽經》《華嚴經》等等,逐漸對佛教的教義有所瞭解。開始的時候一定讀不懂的,又沒有人指導你。有一個辦法,這個辦法也是很笨的辦法,不管懂不懂,只管看下去。有些概念,有些名相,經過多次接觸慢慢曉得它是個什麼意思了。
陳允吉:到了“文革”後期,我開始鑽研一個問題:佛教思想同王維的山水詩究竟有些什麼關係?當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出了本文學史,説王維的佛教思想主要體現在説理的詩歌中,至於他那些刻劃自然美形象的代表作呢,就沒有什麼佛教的思想了。我當時就覺得不以爲然,覺得王維的山水詩受佛教思想影響主要應表現在那些最有名的、寫得最好的代表作當中。但文章不容易寫,一方面是抽象的哲理,王維的山水詩是通過具體的形象來展現的。但是談到大乘佛教的“中道觀”,或者説是“中觀”,這個問題就比較好談了。就是你要表現“空”啊,你不能直接講“空”的,要從他寫“有”的當中來看他的“空”。他同樣可以寫這種美景,但這種美景在他看來是一種“假有”。“假有”即是真“空”。倘然直接從“空”裏面談“空”,永遠也談不出來。在“文革”當中,白天都要做二十四史點校,晚上才有時間寫這篇文章。
開始的時候就是這樣困難,在不知不覺中水準就提高了。在此過程中也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魏同賢的支持,他向我約稿。我寫文章進度很慢,有的文章前後加起來花了兩年時間才寫出一篇。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魏社長説和我的稿約依然有效。《唐音佛教辨思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交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加上現在繼續出的那一本——《佛教中國文學溯論稿》,可以説是花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四代領導的心血——魏同賢社長、李國章社長、趙昌平總編輯、高克勤社長。高克勤先生,就是《唐音佛教辨思録》的責任編輯。今天參加這個會,我要感恩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允吉:第二點,談談我對自己那些文章的特點的認識。我很少寫題目跨度很大的文章。一般都是題目比較小,還比較注意深挖。我們古典文學界裏面,有的老師把它概括成兩句話,“突破一點,縱深開掘”。我想這個是我自己比較能够掌握得熟練的一種方法。有的文章寫作時間很長,比如《論唐代的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和《從〈歡喜國王緣〉變文看〈長恨歌〉故事的構成》,這兩篇都花了大量的時間。
我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像我在《唐音佛教辨思録》的後記裏面講的,一是注意辨明事實的情況,就是“辨”。“思”呢,也就是你思維空間要擴大一點,能够有一種宏通的想法。所以在80年代的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未定稿》有個編輯訪問我,説:85年是方法論年,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我説新方法當然要注意運用,這樣我們的學術研究才會進步。但是有些東西不能拋棄掉,比如實證研究。所以,我的研究方法比較簡單,一方面要擴大思維,另一方面也要堅持實證研究。我的文章裏,考證的部分是相當多的。但考證不能枯燥無味,要跟思辨結合起來,要把文章盡量寫得漂亮些,就是所謂有義理,有考據,也有辭章,這是我覺得比較理想的一個文章境界。
陳允吉:這個過程中得到很多人的幫助,我想總結一下自己所接受的前代人的影響和幫助。首先是復旦的老師。我這些文章裏面有很多觀點都來自復旦的老先生。比如講韓愈的“以醜爲美”,原話出自清人劉熙載的《藝概》,但與此相同的話我第一次是聽陳子展先生講的。他説《元和聖德詩》寫把劉闢一家在長安殺掉,前面的小嘍囉被砍殺,他的兒子還是小孩子被腰斬,劉闢被凌遲,肉一塊一塊被割下來,最後再被剁成肉醬。這都是很恐怖的東西,但是韓愈把他當美的東西來寫。我寫文章談及地獄變相意象對韓詩的影響時,就把陳子展先生這個意見吸收進去了。
又比如講《長恨歌》受變文的影響,實際上也是我們老先生的意見。朱東潤先生在“文革”後期寫了《杜甫敘論》,實際上他寫的就是杜甫傳記。朱先生特別欣賞杜甫的《哀江頭》,但是不喜歡《長恨歌》,認爲《長恨歌》寫楊貴妃的美寫得太露骨了。他説《哀江頭》是事變發生以後沒有多久,詩人杜甫在長安得到消息後寫下的感受,《長恨歌》不過是事變數十年以後的一篇變文。
陳允吉:除了復旦的老師以外,還有兩位前輩對我影響非常大,陳寅恪先生和饒宗頤先生。我的《唐音佛教辨思録》所受最大的影響來自陳寅恪先生。陳寅恪《論韓愈》是解放以後寫的,這篇文章所論及的韓愈與佛教的關係對我啟益非常大。這一問題,清代沈曾植《海日樓劄叢》較早談到了韓愈詩歌受佛畫影響。後來包括饒宗頤先生,也對韓愈詩歌受佛教影響這一問題有所推進。陳寅恪先生的研究特點,不單是傳統的考證,其中包含着諸多他個人天才成分。人特別聰明,悟性特別好。所以他談有些問題,雖然給你羅列大量的證據,有不少論點都是根據他天才的預判,但此種建立在過人遠見卓識基礎上所作的研判,猶如“金針度人”,一下子切中腠理。他講過以後,往往需由後人來給他做補充論證。比如像《四聲三問》,開始時他從《高僧傳》等材料中所記當時很多審音僧人給梵唄定音的活動談起,由此而觸發他對中土聲律的形成問題產生的聯想,這一份學術敏感顯得極其難能可貴。但是接下去他講印度的圍陀三聲和中國四聲的關係卻沒有什麼根據,對此郭紹虞、羅常培等先生都作了很多中肯的批評。像陳先生這樣的大學者,雖然有的時候難免犯錯,但其新見在很多情況下是振聾發聵的,給人的啟發是特別強烈的。
陳允吉:到後一個階段,饒宗頤先生跟我接觸比較多一點,因爲當時我在系裏工作的時候,聘請饒宗頤先生來當我們復旦的顧問教授。我寫《韓愈〈南山詩〉與密宗“曼荼羅畫”》時,因爲若干年前饒先生在京都大學的《中國文學報》上發表過一篇《韓愈〈南山詩〉與曇無讖譯馬鳴〈佛所行贊〉》,對我有很大的幫助。隔了幾年我有機會細細地讀了一下韓愈的《南山詩》,覺得這首詩裏有“曼荼羅畫”的痕跡。剛好到1996年,饒宗頤先生80歲,他的老家潮州市政府辦了個學術研討會。我參加這次研討會提交的文章,就是論韓愈的《南山詩》同密宗的“曼荼羅畫”之間關係的,想在饒先生的研究基礎上再有所推進。這篇文章的論題饒先生早就知道,到我發言的那天下午,饒先生説:今天看你的哦!會議閉幕的那一天,饒先生最後作總結,他説了這麼一段話:“陳允吉先生在陳寅老的基礎上對韓愈的繼續研究,我們是同意的。”過數月後,設在潮州開元寺內的嶺東佛學院有一個研究刊物叫《人海燈》,就把這篇文章發表了。同時還給我寫了一封信,説你這篇文章在饒先生的基礎上有新的發現,我們給你刊登出來了。應該説,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饒先生對我幫助很大。特別是寫王梵志降生故事的那一篇,一開始有點想法的時候,就向他請教過。饒先生説:“你談到的這些想法,是從根本上去觀察問題的,這件工作可以去做。”到第二年再見面時,他又提示我“要從複雜的材料中理出頭緒來”。1993年秋,我到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訪問,順便去中國文化研究所拜訪饒先生,饒公同我講了兩件事,我覺得很有意思。第一件事,他早年到歐洲去,曾見過一位德國的老太太,一生都在研究王梵志詩。她收集了很多很多的材料,還同饒先生交流過。可是一直到現在,她的成果還沒有發表。第二件事是説他去日本做訪問研究時,曾去旁聽入矢義高教授給研究生上課。入矢教授把王梵志的重要作品選了好幾首,分給研究生每人負責一首。第一個禮拜,由甲來談王梵志這首詩的體會,其他同學輪流發表意見,最後由入矢義高教授來總結,下個禮拜再繼續這樣討論。他講“Iriya(入矢義高名字的日語發音)厲害!”言談之際透溢着欽佩之情。入矢義高先生在日本有很多學生,比如跟我比較熟悉的關西大學森瀨壽三教授,他在新世紀初過訪復旦時,嘗話及入矢先生對饒公旁聽他的課程感到非常高興,也經常和他的弟子們講起這件事。《關於王梵志傳説的探源與分析》這篇文章,動筆寫的時間倒不太長,但醖釀的時間有十多年。在這過程中,饒先生對我的幫助顯得彌足珍貴。
陳允吉:最後講一講我對李賀的認識,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的影響很顯著。我有一段時間接觸精神分析學,很少看其他人的著作,但弗洛伊德的著作基本上翻譯過來的我都讀過。我寫關於李賀的文章從來沒有引過弗洛伊德的一句話,但細心閱讀仍能看出它們曾經受到過弗洛伊德某些想法的沾益。比如張煜剛才講到“筆補造化天無功”,本來它是李賀對韓愈詩歌創作特點的稱頌,但反過來考察李賀本人的詩歌創作也同樣適用。李賀年紀很輕就掉頭髮了。不僅掉頭髮,而且有白頭髮。本來掉頭髮的人頭髮不太會白,白頭髮的人頭髮不太會掉。他又掉頭髮又少年白頭。他對時光的流逝與生命的短暫特別敏感,極善於借助幻想和豐富多彩的直覺,把自身對於缺失的抱憾靈敏地轉換到它的相反方向,由之使這種補償以一種想像性的願望形態出現。所以他喜歡寫“綠鬢少年”的頭髮,更喜歡寫青年女子濃密的頭髮。他自己頭髮白了或者快掉沒啦,就通過在詩中寫濃密的頭髮來補償,這也是“筆補造化天無功”。所以有的時候我感到精神分析學的理論,對瞭解李賀的創作思想非常有幫助。我的第一篇討論李賀的文章,叫《李賀詩中的“仙”與“鬼”》。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中文系第一次開學術報告會時,我以此爲題作過報告。該文不久後在《光明日報》的《文學》專欄上發表,當時北方高校的一位老師撰文跟我進行辯論,説李賀怎麼會一天到晚擔心人有沒有死亡的問題呢?因爲按照當時通常的理解,李賀對政治非常關心,是應該把他作爲一個法家來看待的。這本書裏面還有一篇《李賀——詩歌天才與病態畸零兒的結合》。我在動手寫作之前,把茨威格寫的《巴爾扎克傳》非常仔細地讀過一遍。如果大家知道了此中曲直,可以在文章裏面找到一些熏習浸染的蹤跡。
陳允吉:至於我談一般佛像藝術的論文,其藝術觀頗得益於丹納《藝術哲學》的啟迪。從材料的組織和行文上看,則受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主潮》的影響較大,它那種清新灑脫、收縱自如的行文特點我很喜歡。李澤厚先生的有些作品,如《美學論集》《美的歷程》,在寫法上也對我有所啟發。
陳允吉:今天零零碎碎地向大家匯報這些,我感到非常高興,謝謝。

彭華:非常感謝陳允吉老師精彩的講話,他回顧了自己從事佛教文學的研究歷程,以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種種淵源,感恩了對他研究有各種幫助和啟示的前輩,包括復旦的陳子展先生、朱東潤先生,包括從事佛教文學研究的陳寅恪先生,還有饒宗頤先生。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提問的環節,先請張煜老師提個問題吧?
張煜:好的。陳老師您這本《佛教中國文學溯論稿》出版以後,很多讀者都感興趣,它和《唐音佛教辨思録》之間有什麼聯繫與區別?
陳允吉:我在這本書後記裏面提到過和《唐音佛教辨思録》的聯繫,説是姊妹篇。兩書總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都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些不同。不同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唐音佛教辨思録》中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寫的那些文章,其時作宗教文學研究的客觀條件很差,能够見到的材料甚少,社會上多數民衆也不太願意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你發揮主觀努力去鑽研。點校二十四史結束後,我們不能够方便地借書,回到系裏以後讀佛經變得很難。當時《大正藏》,我們學校裏面有兩部,一部在哲學系資料室,一部在歷史系思想史教研室。因爲歷史系這個教研室裏,朱維錚老師是我的同鄉,姜義華、李華興兩位老師亦較熟悉,我閱讀《大正藏》都是去那兒看的,承蒙他們幾位爲我提供方便。寫《唐音佛教辨思録》裏這些作品時,我不過三四十歲,闖勁十足,非常願意鑽研,而且能够堅持下來。比如韓愈寺廟壁畫那一篇,還包括《長恨歌》那一篇,儘管碰到的困難很大,最後都能善始善終撰寫完成。《辨思録》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那時我在學術上不成熟,比如《論王維山水詩中的禪宗思想》,其撰作過程中所付出的精力至巨,於溝通佛教哲理與詩歌藝術形象之關係上頗有特色,但是現在我不大重視這篇文章。爲什麼呢?這裏面有一個問題。你講這個是王維的禪宗思想,確實是禪宗的思想,但又不止是禪宗,佛教的其他宗派都可以這樣講,實際上就是佛教的般若思想。那麼爲什麼當時會這樣寫呢?這跟當時整個學術界的認知情況有些關係。其實禪宗跟其他宗派的不同,不在於哲學思想,而主要在於修持理念及其接引學人的方法。所以講禪宗的思想特點,講得最簡明扼要的,是黃懺華先生爲《世界佛教大辭典》所寫的“禪宗”那一條(《中國佛教》,第一冊324—325頁,知識出版社,1980年)。
那麼後面一本書呢,就是現在出的這本《佛教中國文學溯論稿》,應該説思想比較成熟一點,梳理佛教傳播在中國的影響也比較全面一點,所走的彎路也比較少。但是這一段時間的科研也是有缺陷的,總的説來,鑽研精神遠不如前。在此期間,我寫過一篇東西,注意力集中在柳宗元《江雪》這首詩上。詩歌只有簡單的四句:“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目的是想探討它的佛經記載來源。爲此我認真讀了一遍《柳河東集》,並花了許多時間去爬梳《大正藏》,還對永州的南亞熱帶氣候作了仔細查考。按照提綱寫了三個部分,基本上都寫好了,到最後還是沒有堅持下來。可能是因爲進入垂老之年,鑽研的勁頭逐漸消退。另外還有一篇想探討柳宗元的《羆説》。《羆説》一眼看去我就覺得印度故事的味道很濃。爲了這件事,我曾專門向內蒙古大學的蒙古學專家請教,在蒙語中羆跟熊有什麼差別。他説羆爲體型很大的熊,還有一種説法就是“可怕的東西”,熊就是一般的熊。我寫了一封信向季羨林先生請教,熊跟羆在梵文中有何區別。不到一個禮拜,季先生就寫了回信,他説最近家裏正好在裝修,書堆得很亂。但是根據記憶,我可以告訴你它們是有不同的,他分別給我寫了兩者的梵文。若此之研究條件足够充分,但最後文章仍然沒有寫出來。這種情況跟從前明顯不同,從前哪怕寫得再苦,最後拼了命也要把文章出來。人到了五十多歲以後,精力不是很旺盛了,就容易放鬆對自己的要求。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大多年輕時放下了健康追求事業,中年一過要保重身體了,就放下了事業來追求健康。
彭華:好,各位同學來賓有什麼問題的話,請現在舉手。我們跟陳老師互動一下。
提問同學1:謝謝老師們的精彩講演。有一個問題想請教陳老師,我們都知道您的駢體文寫得非常的好,而且在這本書裏面也收録了您用駢體寫作的書序。想請問一下您是怎麼樣練習駢文寫作的?謝謝。
陳允吉:我童年時曾在一位老先生的指導下讀《千家詩》,於平仄屬對等事略有所知,並未花很多功夫去歷練駢文寫作。後來又怎麼會喜歡去寫駢文的呢,應與參加二十四史的標點實踐有很大關係。當時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都是老先生,我能够參與其中,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了。在此期間我主要參加《舊唐書》的點校,並參與承擔通讀該書全部點校稿的任務,按點校體例反反復復地看稿子,等於將《舊唐書》前前後後看過多遍。《舊唐書》裏收録詔制奏議,基本上都是駢文,有些甚至是最典範的駢文。那麼不斷地標點,你儘管不一定把它讀出來,實際上會受潛移默化的影響,已經印在我腦子裏面了。類似於此的感受不斷地積累,必然會對這種文體產生愛好。所以其後我和人家通信,常會夾帶一些駢對的句式,包括像《〈唐音佛教辨思録〉後記》這類文章,也都帶有顯著的駢儷化傾向。至上世紀末我開始專門寫作駢文,這同我的老鄉朱維錚先生還有點關係。我剛才講過潮州主辦的饒宗頤先生八十歲的學術研討會,維錚先生與我都應邀參加,會議期間又同去參觀當地的饒宗頤學術館。饒宗頤學術館是一幢五層樓建築,修得蠻漂亮,先生的部分藏書和書畫,以及其他的一些資料都放在裏面。此地是原來饒家的榨油作坊,後來饒先生在海外很有名了,在他開始跟大陸有聯繫之後,當地區政府就把這塊地方辟出來並投入部分資金,港商陳偉南先生則出了大部分的錢,造起了這棟氣派頗大的建築。在大門口右邊牆壁上,鑲嵌著一塊長方形的石碑,上面刻了一篇《建饒宗頤學術館記》,作者就是我們的朱維錚老師。當時我同朱先生在學術館門口拍了一張照。朱先生長我三歲,在復旦學習時高我兩屆,我對他一直是很欽佩的。他給我的印象,總是那麼英氣逼人、才華橫溢。若論思維之敏捷,議論之深刻,氣度之瀟灑,講演之吸引人,我與之相比簡直望塵莫及。第論遣辭屬對等雕蟲小技,我自覺尚有一技之長。如同上面所提到的這篇文章,我還是寫得出來的,要是日後付以更多努力,可能會寫得更好一些。就在那年秋天,我同陳引馳先生主編的《佛教文學精編》垂將出版,當時責任編輯要我寫一篇序,我想就寫一篇駢體文試試。一共兩千二百字,花費約一個月的時間,總算寫出個初稿。此後又從頭到尾改了好幾遍,還向上海文史館劉衍文先生、厦門大學周祖譔先生請教過。例如該文第六段“是故才士半成居士,文心屢雜禪心”兩句,就是採用了周祖譔先生的設計;同一段後面“或矜賈島瘦冷,刻削窮形,挾枯寂之氣,索漠冥之道。終墮末流,枉捐苦力”等句,則經過了劉衍老的措意修改。這裏面有些偶然的機緣。當然寫駢文也是很難的。我自己寫的水準很一般,若説個人喜好,我以爲清代的駢文寫得最好。清代的駢文變化多端,而且講究的套路愈多,要花的時間就更多啦。寫駢文殫思竭慮,非常辛苦,所以千萬不能長時間耽在裏面。

彭華:好,謝謝陳老師的耐心解答。還有哪位要提問?這位同學,請。
提問同學2:陳老師您好。我想問一下,您剛才提到的説我們在做新研究的時候,一定要有實證的基礎來支撐我們的想法。因爲我也看過這篇《論唐代寺廟壁畫對韓愈詩歌的影響》,我想您能不能以這篇文章爲例,説説有新想法的時候,我們要找怎樣的一些證據,或者説找到怎樣的程度才可以開始我們的研究?
陳允吉:這一篇是我耗時很長的作品。開始的時候有這個想法,是因爲韓愈的詩裏面,經常談到佛教的壁畫。“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我想探討這佛教畫跟韓愈的詩歌有點什麼關係?這篇文章引用的材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錢仲聯先生《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二、《大正藏》所輯佛經的有關記載;三、敘述唐代寺廟壁畫的繪畫史著作。後來找到一個比較容易突破的地方,就是韓愈的《陸渾山火》詩。《陸渾山火》詩,沈曾植就講過,“作一幀西藏曼荼羅畫觀”。這篇文章我寫得比較滿意,是因爲發現了另外兩點:一點是它和地獄變相比較像。地獄變相寫地獄的火,地獄這個大鐵城,東南西北都有很高的門,門都是關起來的。大火一起,周遭猛燒,那些在陽世作了惡事的人,墮入地獄以後,被大火趕得東南西北到處逃竄,最後燒得皮焦肉爛。《陸渾山火》不是講陽世犯罪的人,是講山間的動物。它們在大火中,一會逃到這兒,一會逃到那兒,最後都燒得皮焦肉爛。所以就證明他不僅受曼荼羅畫的影響,而且還受到地獄變相的影響。另外就是《元和聖德詩》。因爲陳子展先生跟我談起過這首詩,使我聯想到佛教的壁畫那些虐待囚人的場面:刀山、劍樹,把人綁起來支解摧殘,開膛破肚挖眼睛。跟《元和聖德詩》裏面寫把劉闢的那些幫兇,包括他的兒子處死很像。韓愈居然喜歡這種東西,其實都是有佛教來源的。而饒宗頤先生那篇發表在京都大學《中國文學報》上的文章,是同教研室一位老師見到後推介給我的,我一看來得正是時候,這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因爲陳寅恪先生講韓愈的“以議論爲詩”同佛經文體有關,他只是直接給出一個判斷,並沒有提供什麼證據。饒先生那篇文章一出來以後,就證明了陳寅恪先生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那麼陳先生的此項發現就更加立得住了。我就按這個思路寫下去。
彭華:好,我們的問答環節就到這裏結束了。感謝兩位老師的精彩講話。感謝各位來賓的光臨。
(録音由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薄王逸整理,上海外國語大學張煜、上海古籍出版社彭華校訂,經陳允吉老師審定)
文章轉載自“中國俗文學研究”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