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有两部华语电影在影坛引起广泛关注——《瀑布》与《美国女孩》,两部影片不约而同的关注疫情、母女关系、身体疾病、坠落的中产阶级,导致了一次题材“撞车”。


在疫情焦灼的当下,看这两部以疫情为背景的影片,每一个观众恐怕都有切肤之感。当然,再相似的选题,不同的创作者视角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侧重与情感关注。作为影片的重中之重,两部影片中的「母女关系」,就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面貌。
疫情之水
《瀑布》改编自导演钟孟宏友人的真实经历,讲述在单身母亲罗品文和女儿小静一起生活在公寓内,然而疫情来临后公司要求员工降薪、女儿班上也查出确诊同学...种种压力致使品文丢掉了工作,而她和女儿的生活也因房贷、精神分裂等问题摇摇欲坠了起来。

和前作《阳光普照》中借由“阳光”去描述父子关系类似,该片中借由“瀑布”去指代疫情对家庭的冲击,对母女关系进行探讨。瀑布是窗外蓝色的巨布、是母亲思文耳边的嘈杂声、在疫情的瀑布之下,每个家庭都不可幸免被现实洪流裹挟着,沉浮、前进。

围绕品文与小静这对母女,剧情前后进行了转换。在前半段的剧情中导演试图营造一种悬疑的色彩,叛逆的女儿、压抑的蓝色,一切都让人难以喘气。而以品文臆想中大雨为转折点故事进行了反转,生病的人从女儿变成了母亲,母女身份在此刻进行对调。女儿小静转化成照顾者的身份,以水一般的东方内敛温柔包容着母亲。她开始联系中间公司卖掉房屋、邀请同学给家里增添生气,从开篇女儿封闭房间不愿交流,到最后告诉母亲“有什么事要打给我哦”,小静和母亲关系从泛起涟漪到重归平静。

片末,山间洪流的剧情似乎是对品文生活能否重归平静的最后一次考验,而最终小静被救起,品文也开始了新工作,母女相互扶持着,在阳光下迎接新生。
青春冲撞
而《美国女孩》的故事背景为非典期间,主要围绕即将步入青春期的少女展开,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从美国重新回到台北),大女儿芳仪和母亲莉莉不断争执。女儿厌恶母亲面对癌症的无能为力,而母亲则因为女儿的叛逆心力憔悴。

比起《瀑布》,《美国女孩》是对家庭争执场景细腻而有真实的再现,聚焦逆文化的冲突,借由姐妹二人英语交流、爱吃汉堡而非中餐和为了进入学校就读建成短发等图景展现,体现少女在陌生环境与青春期加持下的不适、躁动、冲撞、探寻自我认同。而最终以妹妹被隔离为转折点,在父亲的巴掌和母亲的眼泪中,一夜之间忽然成长。

美国梦的破碎与对母亲的迁怒是对女儿芳仪对母亲憎恨的缘由。她恨每天在家里抱怨病情的母亲、恨自己回不了美国、恨严苛而又不熟悉的台湾的教育环境。而她将这些全都怪罪到母亲身上,以伤害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在演讲稿中她写到:“这个世界上我最不想成为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然而爱与恨是一体两面,她恨母亲总是说自己会死,其实是出于对母亲的死亡、现实不顺的逃避,也暗示她对母亲的爱之深切。

电影是对时代的融合与缩影,翻盖手机、父亲往返大陆间去打工、非典、网吧里周杰伦的歌,对台湾真实家庭进行细腻的刻画。
母亲、母亲
母与女是最直接亲密的血缘关系,有着直观的传承。《瀑布》中,借由母女身份的倒错,拉近了母亲品文和女儿小静的距离。小静变成了照顾者,在18岁懵懵懂懂的人生之潮中跌跌撞撞前行,体现的是一种东方式的温柔内敛。

而在《美国女孩》中,通过讲述文化冲突和青春期的冲撞——芳仪一直追寻象征自由的白马,却无法套上马鞍;而学校环境的不适使得她只能将郁闷通过与母亲的争执宣泄出,也是一种西方式的宣泄和外放。同时,美国女孩是芳仪也是母亲莉莉,母女之间达成一种镜像的重合。重新回归台北后莉莉也重新成为一名家庭主妇,每天承担着为家人洗衣做饭的职责,莉莉的美国生活也因患上乳腺癌而破灭。

疫情是情绪的放大镜,密不透风的狭小空间、被迫面对面的两个人,问题无法再被逃避,争执也无可避免。将人物的活动范围缩小到具体的”家“中,借由对家庭内核心成员的关系描写,对每个人进行重新关注。而通过最直接的母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彼此情感的联系、以及与世界的联系。
借由影片《春潮》中的一句话:“你与你母亲的关系,决定了你与世界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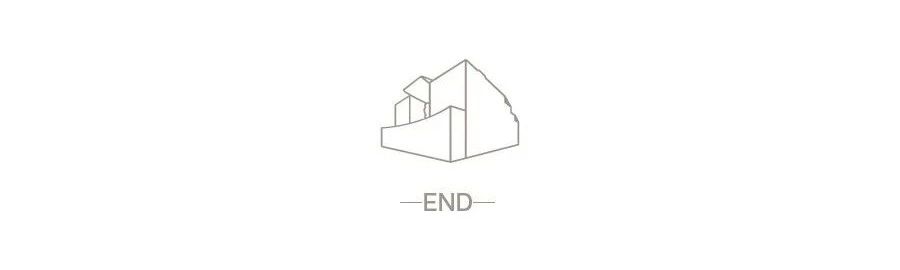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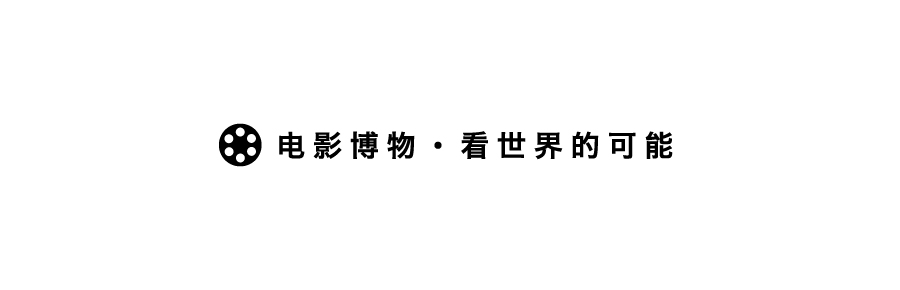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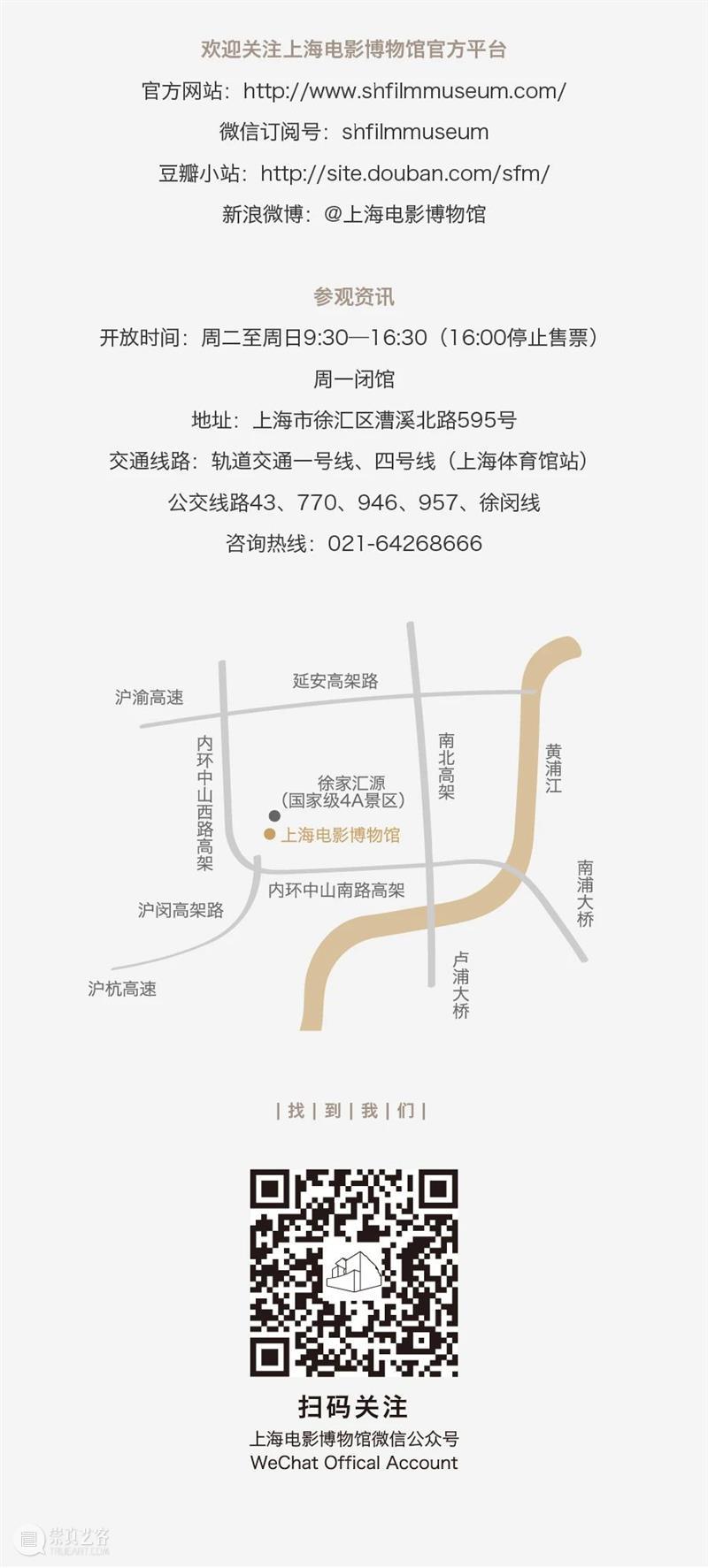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