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体的舞台呈现与戏剧共情
——论玛格丽特·埃德森剧作《灵智》
李晶
【内容摘要】美国当代剧作家玛格丽特·埃德森在普利策获奖剧作《灵智》中关注受癌症折磨的身体。主人公薇薇安是研究玄学诗歌的教授,在她看来,身体是从属于灵魂的次级物。然而,癌症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临床医学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冲突以及人文感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都在薇薇安的病体中得到具化。摆脱肉体束缚与禁锢后,薇薇安最终超越了身体与灵魂的对立,回归到人性的温暖之中。埃德森通过患者的身体叙事,唤醒观众的同理心,实现了戏剧共情。
【关键词】玛格丽特·埃德森 灵智 身体共情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943X(2022)02007009

李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香港浸会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哲学博士,美国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戏剧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现当代戏剧、文学伦理学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出版学术专著(英语写作)《群体中的自我:20世纪美国女性戏剧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20),并曾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华中学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十数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新世纪戏剧的对话性伦理研究”,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当代美国戏剧的老龄伦理研究”。
导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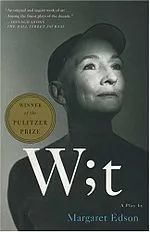
美国当代女剧作家玛格丽特·埃德森(Margaret Edson,1961)的代表作《灵智》 (W;t,1991)别树一帜地书写了癌症患者生命尽头的经历与感悟,斩获评论界与观众的一致好评,获得1999年普利策戏剧奖。埃德森在剧名上使用了巧妙的文字游戏,是W;t而非Wit。乍一看似乎就是英语单词Wit,有才智、机智的意思,实则用分号“;”代替了“i”(有自我的意思),用分号隔离了寓意智慧的 “W”(Wisdom)和技术的“T”(Technology)。这种分割也提示剧中人文感性与工具理性的对立导致患者主体地位的丧失。而这部戏剧的主题正如埃德森在访谈中回答的,“是关于爱、知识和恩宠的,它探索了我们是如何受挫,我们如何自我设障不得治愈,我们又如何重新获得痊愈,而不是被治好疾病”[1]。这种痊愈既包括肉体也包括灵魂层面。缘于此,本文将该剧W;t剧名翻译为《灵智》。正如戏剧评论家玛丽·K·德莎哲(Mary K. DeShazer)所指出的,“女性的表演叙事与其他癌症叙事不同,通过在舞台上使用‘露骨的身体’来标记癌变的卵巢”[2] 。《灵智》这部剧就此意义而言,是关于患癌女性身体的表演叙事,通过身体的戏剧呈现来表达剧作家的医学人文关怀。
表演叙事中的身体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力量,例如基督教神学还有笛卡尔的二元论都使肉体贬值,甚至企图抹煞肉体”[3]。埃德森在《灵智》中将身体,还是患上绝症的身体,作为文本呈现给观众审视,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是埃德森成功地通过《灵智》中病患的身体叙事唤起观者的共情。该剧“给出了定义同理心和同情的场景,它引发观众思考:你如何治疗濒临死亡的病人?你会说些什么来抚慰而不是加重伤害?”[4]与此同时,女主人公薇薇安·贝宁(Vivian Bearing)在人生不同阶段,对文学文本中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的不同解读,也发人深省。
剧中主人公年逾五十的教授薇薇安·贝宁对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痴迷性研究,佐证了她本人在灵与肉的对立中坚决地站在了灵魂的一端。比较讽刺的是,在对诗歌进行研究性解读并追寻人类体验的答案时,她关注文学文本的物质性存在:语言符码的解密。身患绝症的她被收院治疗后,薇薇安遭遇身体最隐私部分被审视的羞耻和屈辱,直接体验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套价值体系的对立。身体被剥去文明的外壳直接放到舞台中央,这种直观的体验,令人震撼,迫使观众直面疾病对人的身心摧残,进而反思自身。直到生命弥留之际,薇薇安才重回人类本性纯真的状态,通过死亡摆脱了疾病与痛苦。这种妥协式的结局折射了埃德森对生命尊严的敬畏及其个性化的医学人文观。
剧本的身体性解读
《灵智》伊始,薇薇安即被确诊患上第四期卵巢癌。必须要指出的是,卵巢癌既不易察觉,又具有鲜明的文化性别指征。R. M. 尼斯(Randolph M. Nesse)和G. C. 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在《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Why We Get Sick:The New Science of Darwinian Medicine)中指出“生命似乎就是处在某种程度的癌前状态”,同乳腺癌、子宫癌一样,卵巢癌也是女性生殖器官癌,“这种现代瘟疫的部分原因是富裕的工业国家里妇女新的生育模式”[5]。这种论述不仅指出了现代人携癌生存的状态,更指出了性别化的疾病背后的文化因素,某些疾病的获得与病人“不恰当”“不适宜”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薇薇安教授事业有成,却没有结婚,没有丈夫,没有小孩,父母已逝,也没有兄弟姐妹。这种生活状态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活状态。[6]她情感世界是压抑的,而卵巢癌无疑是长期情感压抑的恶果。在获知自己患有晚期卵巢癌时,薇薇安感到有点令人震惊,仅此而已。薇薇安并没有意识到患病是对她“不良”生活方式的惩罚。
薇薇安不仅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以为意,还对自己的生存状况进行调侃。全剧以她的独白开场,“我活不长啦,他们给我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7],打破第四堵墙,直接面对观众的凝视。剧内薇薇安生命流逝的时间紧迫感与剧场中时间的流淌同步起来。观众在这里充当了镜子的功能,薇薇安对着观众剖析自我。这一行为对薇薇安的性格来说非常震撼。剧中,薇薇安外表冷漠、强硬,善于理性分析,却拒绝与人交往,认为这些情感“陈腐”和“伤感”。这样一个冷冰冰的角色能够紧紧抓住现场观众的心,令其产生悲悯的共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薇薇安孱弱的身体清楚地说明,她时日无多。化疗后的光头、病号服、依靠输液杆前行的蹒跚步伐,配合这种直接的言语展示了人物的悲惨状况:她濒临死亡,失去了工作和生活目标。癌症侵蚀了她坚硬的外表,她向观众求助,寻求她生活中一直回避的不自然的情感安慰。该剧开始的舞台指示中清楚地描绘了薇薇安的身体细节,“薇薇安左乳房上有一根中央静脉导管,所以静脉导管在那里而不是在手臂上”[8]。薇薇安的身体被输液杆限制了自由,晃动的静脉导管提示着观众这是一位病患。此时舞台上的身体是疾病的符号。它的脆弱激发了观众和演员共同的感受。
实则身体从来都不只是灵魂的载体,它还是政治的产物,同时也是个体自由抉择的媒介。诚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必须保卫社会》中论及后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管理技艺时指出,“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技术也针对人的群体,但不是使他们归结为肉体,而是相反,使人群组成整体的大众,这个大众受到生命特有的整体工程,如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等的影响”[9]。按照汪民安的阐释,福柯所强调的权力管理生命的形式对于薇薇安而言是身体的解剖政治学[10],身体受到权力话语场的形塑,其健康或疾病、生与死的状态都受到权力控制机制的监视与管理。与此同时,“身体本身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11]。薇薇安的身体塑造受到权力控制机制的凝视,却又保有其个人倔强的坚持。
薇薇安对自己身体的政治化,一直坚持理性至上的原则,这与她对邓恩诗歌的解读和研究一样:与生命直观体验的人性表达被撇至一边,对字词断句乃至标点符号的使用才是薇薇安孜孜不倦的研究主体。邓恩的《圣十四行诗》艰深晦涩地探讨了死亡的意义。作为邓恩诗歌的资深研究者,薇薇安似乎“知道一切的生与死”[12],深谙生命的真谛。实则她只关注诗歌的语言形式,例如词汇解读、标点符号运用,而对诗歌中生命体验的反思视而不见。基于此,薇薇安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玄学派诗歌的研究脱离了立足肉体的生命直观经验。基于此,薇薇安无法理解学生由于祖母过世而申请延期提交课程作业,并下意识地质问学生“别告诉我,你的祖母去世了”[13]。在薇薇安的认知中,人情世故、悲欢离合等情绪表达都与权力无关。
薇薇安对人生与世界的认识以及权力话语的获得主要依赖文字符码的解读。她对文字符码的解释,始于幼年时期在父亲的引导下对童话故事里“soporific”(昏睡的)一词的词义解析。以此为契机,薇薇安从无知稚子转化为权力话语场的认知主体。成年后,薇薇安跟随E. M. 阿什福德教授(E. M. Ashford)从事玄学派诗歌研究,依然秉持这一客观原则。薇薇安对邓恩第六首神圣十四行诗最后一句的曲解源自版本的错误。阿什福德教授认为该诗歌正确断句应该为 “死亡将不复存在,死神你将死去”,而非按照薇薇安所选的版本中的“死神将不复存在;死神,你将死去”[14]。她认为薇薇安理解的谬误在于句中的分号将死亡与永生割裂开来,使死亡成为了永生的对立面;正确分割应该只是一个逗号,是生命与永生之间一个小小的停顿和喘息,人的生命纵然逝去,但人的灵魂会在上帝的护佑中长存,生死之间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薇薇安却认为断句方式的差异表明不同的人对邓恩诗歌有不同的理解,而这恰好是邓恩作品诡辩机灵之处。尽管阿什福德教授提醒薇薇安不要过度依赖文字来解读文学作品,要多与同学朋友沟通谈心,从生活体验中寻求真谛[15],但薇薇安并不认同,坚持去图书馆从故纸堆中进行文本解读。
埃德森在处理主人公薇薇安的文本解读中,以其对文字的过度倚重,为其之后对工具理性的批驳以及从人际交往中寻求情感安慰的转变埋下伏笔。入院治疗后,作为病患的文学教授薇薇安试图通过掌握专业词汇以获得主体认可。尽管医学词汇枯燥乏味,她仍然积极主动学习,去查阅“寻常变异”“肝毒性”“神经死亡”[16]等词汇的特指意义。在她看来,能规避身份之空的“唯一防御手段就是词语习得”[17],似乎这样她就能知道医生到底要对她这个患者干什么。语言是生命政治在临床医学中实施的具体途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与医学技术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有着深刻根源的自发的重合现象……虽然基于不同的理由,却往往使用相似的语言,要求克服建构这种新空间的各种障碍”[18]。很显然,埃德森借由薇薇安徒劳的尝试将本应该有相似性的语言刻意划出了鸿沟,直指临床医护人员缺失人性的温暖。而这冷冰冰的观感与之前薇薇安对待学生的不近人情如出一辙。
身体沦为医学文本解读对象
薇薇安入院后一直努力配合主治医生制定的最大剂量的试验性治疗方案,却丝毫未意识到这一套方案对人性尊严的无视。这种毫无抵抗的“顺从”无疑来自个体生命的政治化,来自教授本人长期对权力话语和语言文字的关系的理解。因为生命政治对人的自然生命的管理,“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9]。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薇薇安身体健康的时候,她并不顺从;患病住院后她变得顺从,从而为临床医学提供实验数据而变得更有用。这种循环的代价是生命尊严的泯灭。
从解读文本的文学教授转变成被解读的医学文本,薇薇安对生命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医生问诊提问“医生(Doctor)”时,薇薇安自然而然地回答“是的,我有博士学位(Yes, I have a Ph.D)”[20]。这表面看来是一词多义的误解,实则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错位。薇薇安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她已经是一个患者,值班医生询问的是 “[谁是你的]医生”,而非问她“是不是博士”。这番对话表明医护人员和病人之间的权力场域的变化。薇薇安的死亡权力和生命权力都在这种绝对话语的统治下变得一文不值。她现实生活中,生命体验的完整性被割裂。她不仅不再是一个拥有政治权力,拥有个体自由,能够掌控自己身体的社会人。她俨然沦为一个没有话语权,只能被分析和解读的医学文本。
薇薇安自觉将自己置于病患的从属地位,敬畏柯里奇安医生所代表的权威力量。临床会诊时,柯里奇安不满年轻的医学生看不出抗癌药物对薇薇安造成的明显副作用,他转而向薇薇安提问,问她有什么身体反应:“为什么我们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呢,贝宁博士?”而薇薇安愉快地回答:“我也不知道,柯里奇安博士。”[21]此时的薇薇安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作为研究的对象,已经成为她的主治医生和实习医生解读和研究的“文本”。化疗引起的脱发现象和病人的感受都被淡化忽视,正如薇薇安之前解读诗歌时,倚重词汇和标点符号,把诗人借助诗歌表达的情绪、心灵的顿悟弃之一边。
薇薇安最终发现医生们所使用的专业医学术语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物。柯里奇安医生在解释薇薇安的病症时用了“insidious”一词来表明癌症“潜伏性的”特征,而薇薇安出于自身文学研究的认知将其视同为文学意义上“奸诈的”含义。很明显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对同一个单词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释义。这种简单的字词在不同场域的不同释义,辅以对话中语轮主导者转换的权力争夺,不仅表明了薇薇安获取文化权力的失败,还表明在医院这个权力话语场,患者是绝对的弱者。患病改变了话语场的权力分配,身体的这种转变导致了薇薇安对人生体验的不同看法,“疾病或者残疾可能使人转向内心,使他们成为虚拟的黑洞,吸收能量而不是发光照明”[22]。薇薇安开始反思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理性至上的原则,反思自己对情感抒发的抑制。
薇薇安很清楚临床医学试验是医疗发展的重要方式,所以当她的主治医生柯里奇安说“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给你的最有力的治疗,而且,作为研究,它将对我们的知识做出重大贡献”[23]时,她很乐意为“知识”积淀做出自己的贡献。出于这种考虑,薇薇安毫不犹豫地表示接受八个疗程最大剂量的治疗实验,遂成为医学治疗的控制对象。当柯里奇安医生询问薇薇安是否可以忍受使用最大剂量的试剂时,她骄傲地回答“你不必担心这个问题”[24]。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薇薇安理性至上,个人感受其次。这种认同和世界观,在薇薇安还未曾意识到的时候,已经与她的自我认知融为一体。生命政治在后现代社会对社会人的生命管理已经与权力话语混为一体,通过规训与惩罚的力量渗入到薇薇安理所当然的思想中。
如果说埃德森对于剧中主人公文学教授身份,尤其是邓恩玄学派诗歌顶级研究学者的身份设置是对生命的文本性解读,那么薇薇安在癌症晚期,接受最大剂量的八个疗程的试验性治疗就无疑是埃德森对身体作为表演叙事的探究。从这个角度看,薇薇安入院接受治疗的过程,就是一种生命政治策略。“对个体的社会控制,不仅由意识或意识形态执行,而且在身体里或与身体一起进行。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正是生命政治首先关系到生物、躯体、身体。身体是生命政治现实;医学是生命政治策略。”[25]薇薇安从身康体健的资深文学教授到濒临死亡的癌症患者的身份转换并非单纯的生命状态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标志着生命的政治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伴随而来的身份错位与心理落差都与薇薇安之前过度僵硬的理性至上的文本解读息息相关。健康的时候,薇薇安只看重邓恩诗歌中的标点符号、文字使用的理性解读,不在意诗歌对人类情感体验的关注。她患病后,医生只关心她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实验数据,却完全无视她作为病人的失落、孤独和痛苦。这种情感上的冷漠促使薇薇安发生蜕变,反思自己之前的思想偏颇。
模仿实践与戏剧共情
薇薇安的身体被置于群体与个体交汇的场所,在医生的“临床凝视”中成为了为他人而存在的身体。她在经历身体折磨和苦难的同时,内心也充满被当作医学实验品的“羞耻感”。薇薇安需要忍受她之前的学生杰森为她做骨盆检查,这对她来说是“彻底的侮辱”以及“难以想到的羞耻”[26]。大查房时薇薇安要在大庭广众下由她曾经的学生杰森“拉开她的衣服,露出她的整个腹部”[27],然后一群年轻的医学生在她的腹部上乱按以积累实践经验。同时薇薇安还要为研究提供数据,每天记录并汇报她的饮水输入量和尿液排出量。曾经作为个人隐私的私密身体状况被众人公开研究与讨论。通过演员的模仿实践,临终患者的身体实况被赤裸裸地展示在舞台上。
作为最大剂量癌症治疗实验的活体,薇薇安为临床医学研究提供实验数据。她身体的各项指数在精密医疗器械的监测和主治医生的密切关注下被仔细探究。而薇薇安因为身体的控制权旁落而产生的羞辱感和生命尊严被践踏的痛苦完全没有人理会。她只是一组临床症状符号。薇薇安不禁哀叹:“我被隔离是因为我正在接受癌症治疗,我的治疗危及我的健康。”[28]治疗并不能延续她的生命,反而有损她的生活质量。薇薇安经过一系列的屈辱性的身体体验终于认识到,“在他们看来,我只是样本瓶,只是防尘套,只是一张有小黑点的白纸”[29]。癌症的治疗不仅没有遏制癌细胞的裂变衍生,伴随这种僵硬、机械化治疗而来的心理折磨还降低了薇薇安的生存质量。这位以冷漠和坚强著称的著名教授遭遇前所未有的孤独、无助和失落。

百老汇舞台剧《灵智》(Wit)剧照
健康时,薇薇安在文学研究中推崇理性,贬斥感性,否认肉体,对人际交往保持冷漠,排斥情感交流。患病后,由于身份地位的倒置,薇薇安对临床医生对人性的冷漠,感到恐惧和无助。年轻的实习医生杰森对实验数据的狂热执着,从某种意义上说,同他就读医学院时期对待人文科学知识的忽视保持一致。他认为医学院的必修课程“医疗保健工作”对“研究人员来说是时间的巨大浪费”[30],学习17世纪诗歌唯一的用处就是要忘掉那些伤感的东西,尽量远离诗歌中让人变蠢的“生活垃圾(所谓的人生意义)”[31]。他认为疾病只不过是“客观且具体存在的病症”,不必关照病人的主观感受,因为临终关怀无法产生研究效益。这种冷冰冰的规则和秩序与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相比,如同薇薇安所说“你只是在观察,而我在体验”[32]。身体经验的个体私有性是个体自由的至关重要事项,对身体的有规律的控制是自我获得社会认同的手段。当工具理性以压倒一切的势态来统领临床医学时,身体的私密性被摧毁,个体的自由被弃之,其碾压性的恶果就是生命尊严的泯没。埃德森最后让薇薇安充满揶揄地问候观众“你今天感觉怎么样”来嘲讽医护人员的机械性冷漠。薇薇揶揄医学专业人士与生俱来的超然的不关心,他们发问却根本不听。这种有问无答,与演出实践中演员无暇顾及台下观众的观感相似。扮演薇薇安的演员发出这种提问,却对观众有没有回答,回答什么毫不在意。演出现场的模拟实践与剧中人在医院的感受相互呼应。
埃德森还巧用约翰·邓恩的诗歌为薇薇安的情感表达做互文式的注解。治疗期间薇薇安掉光了头发、恶心、呕吐,变得虚弱不堪,倚着输液架拖曳而行,然后一次一次地吟诵邓恩的诗歌来寻求情感的慰藉。最著名的是十四行诗第十首,“死神,别得意,虽然有些人曾称道你/强大而可怕,因为,你其实并非如此,/因为,那些你以为打倒的人们并不死,/可怜的死神,同样你也无法把我杀死”[33]。然而诗歌的吟诵并不能减轻剧痛,薇薇安最后实在忍不住,大声对自己说:“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呀!我疼得受不了。薇薇安,说出来!就像炼狱一般,真的痛死啦!”[34]这种身体之痛令人崩溃,这种歇斯底里式的反应使观众直面身体的最原始反应。观众在同情她之余,更多地开始思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薇薇安在接近人生尽头时,对生命的感悟产生了骤变,挣脱了理性至上的枷锁。她选择在停止呼吸后,不采取紧急复苏措施,在回归生命纯粹中保留自己对生命的最终掌控权。值得注意的是,值班护士苏茜称她为“甜心”“亲爱的”,以及二人共同分享的棒冰成为薇薇安整个灰色治疗过程中的唯一亮点。护士是临床医疗体系下医护二元对立中弱势的一方,却能以人性的光辉温暖薇薇安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苏茜告诉薇薇安,目前并没有确实有效的治疗晚期卵巢癌的方法,但是否采取“紧急复苏”的措施,病人仍然有知情权和决定权。最终薇薇安决定放弃紧急复苏,借此重获对自身身体和生命的最终掌控权,拒绝再做研究的实验对象和数据供给者。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而且如果它在本质上是致命的,那它也是疾病的终结;随着死亡到来,极限终于实现,真理得以完成,而且由于这一跳跃,在死亡中,疾病达到自身过程的终点,归于沉寂,变成了一个记忆之物”[35]。对死亡方式的选择最终使得薇薇安超越自我,将疾病以及隐藏在治疗体系之后的政治权力、后现代社会的生命形式治理都抛之脑后,重获自我身体控制。
总体而言,《灵智》成功地完成了癌症患者的身体叙事,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例如,护士苏茜拥有世俗人性温暖,与之对立的医生显得冷漠无情,似乎是刻板化的人物塑造。此外,以死亡来实现身体和生命控制权的复得多少有些悲观主义的色彩。令人心碎的一幕是薇薇安的老师阿什福德教授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她深情地读了一本儿童读物《逃跑的兔子》。其中的儿歌“无论你在哪里,上帝总能找到你”[36],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心灵与肉体的对立,乃至身体与政治的对立都消解融合。这一系列冲突的弥合之机都归到神秘的宗教原旨主义既唐突又无来由,皆因之前的种种对立与冲突似乎与宗教未有纠葛。戏剧的最后几个场景让观众在参照薇薇安的身体之痛时,切身感受到人情淡漠,禁不住反思后现代社会人类的真实处境。
结 语
埃德森剧作《灵智》是美国当代戏剧中少有的专注疾病与情感的戏剧, “智慧上具挑战性,且情绪上有直观性”[37]。在这部剧中,剧作家通过主人公薇薇安教授生命即将逝去的过程,表达了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认识,或者说进行了一场生命政治的文学想象。剧本结尾“赤裸着身体的薇薇安是美丽的,向着光明[走去]”[38],有着明确的启蒙喻示,表明她的整个人生观改变了。埃德森以这种结局再次唤起共情,呼吁个体专注生命进程,感受自身内在“精神”不可抗拒的力量,用追求生命尊严和身体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的方式,警示后现代社会文化价值观中的理性异化。
注释:
【1】2020年2月25日,亚历山大·王(Alexandra Wang)采访玛格丽特·埃德森时,询问该剧主题,埃德森做了回答。https://madameactivist.wordpress.com/2020/03/19/maggie-edson-advice-on-playwriting-and-healing/.
【2】Mary K. Deshazer, “Fractured Borders:Women’s Cancer and Feminist Theatre,” NWSA Journal 15, no.2 (2003):3.文中外文文献除特别注明外,均为笔者自译。
【3】G. Thomas Couser, Signifying Bodies:Disability in Contemporary Life Writing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9.
【4】Mahala Yates Stripling, Bioethics and Medical Issues in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dical Humanities Press, 2013), 102.
【5】[美] G. C. 尼斯、G. C. 威廉斯:《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易凡、禹宽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162、168页。
【6】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23.
【7】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6.
【8】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4.
【9】[法]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6页。
【10】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11】[意] 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70页。
【12】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22.
【13】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72.
【14】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2324.
【15】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15.
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15.
【16】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50.
【17】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53.
【18】[法]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19】[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刘北成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12年,第156页。
【20】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26.
【21】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49.
【22】G. Thomas Couser, Recovering Bodies:Illness, Disability, and Life Writing.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7), 6.
【23】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21.
【24】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21.
【25】于奇智:《福柯的生命政治》,《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30页。
【26】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41.
【27】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45.
【28】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56.
【29】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98.
【30】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64.
【31】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86.
【32】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53.
【33】[英] 约翰·伯恩:《艳情诗与神学诗》,傅浩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第215页。
【34】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70.
【35】[法] 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158页。
【36】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93.
【37】Mahala Yates Stripling, Bioethics and Medical Issues in Literature (San Francisc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dical Humanities Press, 2013), 123.
【38】Margaret Edson, W;t (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85.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新世纪戏剧的对话性伦理研究”(19BWW0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欢迎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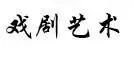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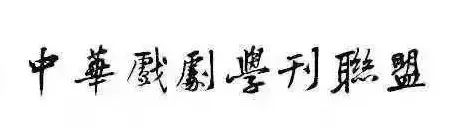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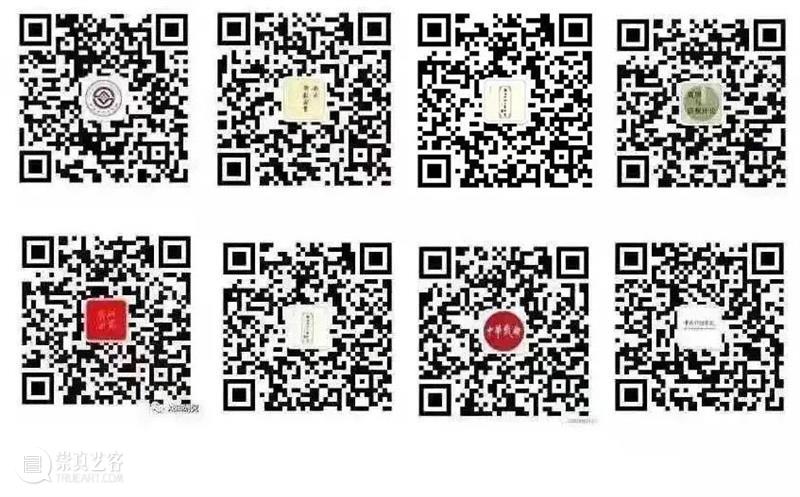
关
于
我
们
《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创刊于1978年。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来源期刊。以繁荣戏剧研究,推进戏剧教育事业为己任,坚持古今中外兼容、场上案头并重,关注戏剧热点问题、鼓励理论创新,力推新人新作,曾以发起“戏剧观”大讨论为学界所瞩目,又以系统译介国外当代戏剧思潮、及时发表戏剧学最新优质研究成果为学林所推重,是国内最重要的戏剧学学术期刊之一,在戏剧研究界享有盛誉。
投
稿
须
知
《戏剧艺术》是一份建立在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制基础上的学术期刊。本刊欢迎戏剧理论、批评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来稿。内容希望有新材料、新观点、新视角,尤其期盼关注当前戏剧实践、学理性强的力作。来稿篇幅在万字左右为宜,力求杜绝种种学术不端现象,务请作者文责自负。所有来稿请参照以下约定,如您稍加注意,则可减轻日后编辑的工作量,亦可避免稿件在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反复修改,本刊编辑部工作人员将不胜感激。
本刊实行在线投稿。在线投稿网址:
http://cbqk.sta.edu.cn 系本刊唯一投稿通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刊不接受批量投稿(半年内投稿数量大于1则视为批量投稿),更不可以一稿多投。
本刊审稿时间为3-6月,审稿流程含一审、二审、三审、外审等,最终结果有退稿、录用两种情况,其他皆可理解为正在审理中,敬请耐心等候。如有疑问,可致函杂志公邮theatrearts@163.com,编辑部将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
本刊从未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审稿费等费用,若发现类似信息,可视为诈骗行为。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等网站或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相关机构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附:《戏剧艺术》稿件格式规范
1.作者简介:姓名及二级工作单位(如,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
2.基金项目:含来源、名称及批准号或项目编号。
3.内容摘要:直接摘录文章中核心语句写成,具有独立性和自足性,篇幅为200-300字。
4.关键词:选取3-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
5.注释和参考文献:均采用页下注,每页重新编号。格式如下(参考2020年以来我刊):
(1)注号:用“①、②、③······”。
(2)注项(下列各类参考文献的所有注项不可缺省,请注意各注项后的标点符号不要用错):
① [专著]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② [期刊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第*期。
③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论文集主要责任者:论文集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④ [报纸文章]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
⑤ [外文版著作、期刊、论文集、报纸等]采用芝加哥格式:用原文标注各注项,作者名首字母大写。书名、刊名用斜体。
6.正文中首次出现的新的外来名词和术语、新的作家作品名和人名请附英文原文,并用括号括起。
制作:高诗怡
责编:秦宏
编审:李伟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