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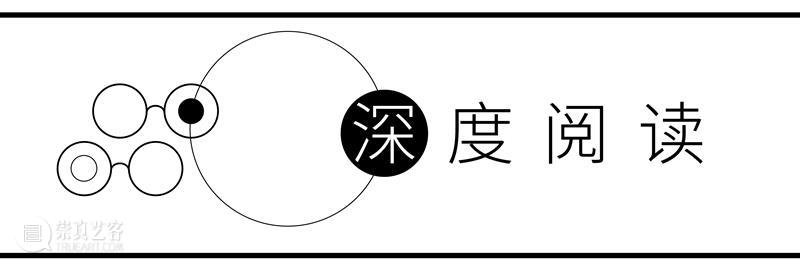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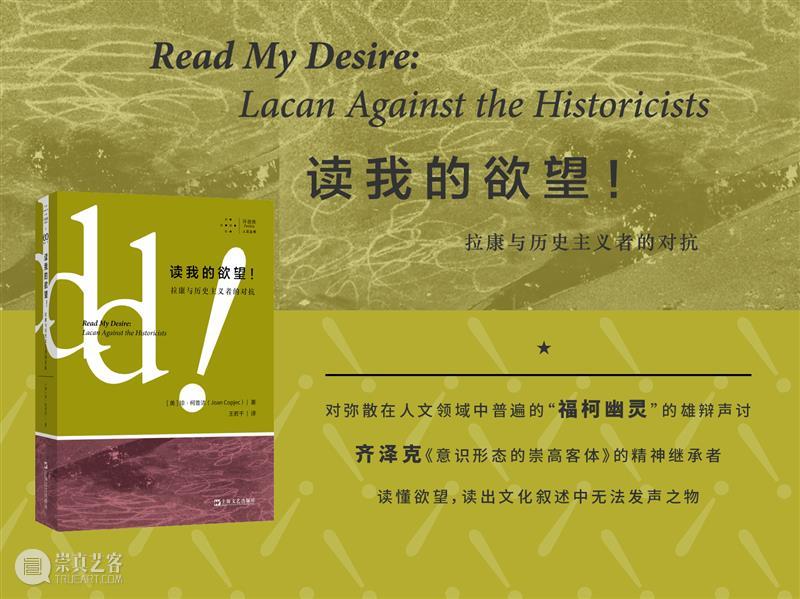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琼·柯普洁)的书摘。此书现已在我们微店开启预售,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预订。
无能的大他者:歇斯底里与美国民主
(节选)
你并不必事先了解整栋建筑的平面图才能以头撞墙,事实上,正是你的无知担保了这些意外的发生。当我观看电视上的各类节目时,发现它们喜剧性地反复进行着与我们所谓“特氟龙(Teflon)总统”[1]的斗争,我不禁回想起拉康的评论——某种意义上它反讽地效仿了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对贝克莱主教(Bishop Berkeley)的反驳[2]。晚间新闻反反复复播放摄像机捕捉到的每一个白痴般的错误、每一个厚颜无耻的谎言,并直接与反驳总统言论的图像并置,从而暴露总统言论的虚假性。然而,尽管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一个接一个地断然驳斥他的言论,但媒体却不能——连它自己都在将信将疑中审慎地承认——威胁到总统自身的地位。从所有这些证明其说辞无能且虚伪的证据之中,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几乎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就像美国拥有了自己的都灵裹尸布(Shroud of Turin),对所有从纤维分析中得出的质疑都保持免疫。
[1]里根作为一位极富魅力的美国总统,总有避免任何指摘的能力,就像特氟龙涂料的不粘锅一样,任何多余的东西都不会粘住他:无论他的对手揭露多少他的丑闻,选民们都会原谅他。——译注
[2]贝克莱主教认为“存在即被感知”,他据此否认在精神以外的任何物质的存在。英国文人萨缪尔·约翰逊博士听闻友人认为这种思想虽不正确却无法反驳的时候,他用力踢向一块大石头,并在脚被石头弹回来的时候表示“我据此反驳!”约翰逊博士的这一反驳显然也是无力的。——译注
我们可别沦落到懒惰地进行谩骂的地步,切莫仅仅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电视被证明是更大的蠢蛋,分析注定会失败,除非能够指明其中确切的错误。而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必须(更准确地)指出,电视最终暴露的是自身的“现实主义愚昧”(realist imbecility)。这一弊病在《〈失窃的信〉研讨班》(The Seminar on ‘the Purloined Letter’)上得到了自己的临床命名,拉康用它来解释,警方为何无法找到从方法上就已经误导的搜查目标:女王失窃的信件。那些警察为何没能找到那么一目了然的目标呢?因为他们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它。只有在不可见性不仅是一种物理条件,更是一种精神条件的时候,某物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正是那封信的藏身之处)被隐藏起来。警察对地理性的空间进行了地毯式搜索,但完全忽视了“主体间的”[3]或者说能指性的空间,而那是这封信未被察觉的所在。因此,现实主义愚昧正是在为“指涉性充盈”(referential plenitude)服务的过程中所犯的一种错误。正如巴特在他的论文《现实主义效果》(The Realistic Effect)中所描述的,这种愚昧源于对“符号的三方参与的本性”(tripartate nature of the sign)[4]的篡改,即为了指涉物(referent)而割舍(sacrifice)所指——也就是主体间性真理的维度。此外,严格来说要割舍所指的话,需要先抹除陈述(statement)中能述(enunciation)的痕迹。换言之,为了维持“指示性的幻觉”(referential illusion),也就是为了使人们有可能相信,仅凭指涉物就决定一句陈述的真理价值,必须抹去发声者(enunciator)。自19世纪以来,正是对抹除著作者声音这一指涉痕迹的信念,导致了“客观”历史的统治。现实因此变得自明(free standing),它独立并先于任何人所可能做出的陈述。历史因而顺从于现实,它从“那时发生了一些事情,那里存在着一些事物”的事实中浮现。历史唯一的功能就是告知我们曾发生过的往事。
[3]这里所说的“主体间的”并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它所指的并不是那种能够彼此认同对方立场或想法的主体间关系。——原注
[4]由皮尔斯主导的一种符号学理论认为,符号的本质是一种三方的关系,分别是符号的物理形式、符号所对应的(客观世界的)对象,以及符号的使用者。——译注
巴特在1968年关于“现实效果”的论文中举出图坦卡门(Tutankhamun)展在当时的成功来证明,历史赋予事物“曾在”(having-been-there)的特质如何持续地引发最为可观的反响,又如何持续地构筑我们的世界,并指挥我们的行动。他出色地为指涉物的现代泛滥提供了例证,唯独缺乏说明其中可谓荒诞的维度,为此,美国电视节目又一次提供了一个更新的例子。临近1989年末,主流的本地电视台一时之间都将自己的摄制组和新闻工作者派遣到科罗拉多州的阿斯本。是何原因如此兴师动众?各家电视台都是为了获得一个特别的影像:邦尼饭店门口,伊凡娜曾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对峙的那片空地。[5]而正是由于愚昧地忠实于指涉物,电视新闻在与里根的战斗中沦为受骗者。新闻工作者们如此地痴迷于去弄清总统的谎言和错误——让我们将这些称为里根的指涉性失败(referential failures)——以至于他们忽视了去思考整件事情的主体间性维度,他们忘记了把美国观众对里根强烈的爱纳入考虑。如果你对爱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就必然也懂一点拉康,你明白他所说的“爱就是给出你所没有的东西”(love is giving what you do not have)。拉康的意思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是爱对方身上某种溢出了的东西(something more than the other),某些超出了对方的外显(manifestation)、超出了一切他所能给予的却又无法名状的东西。我们接受一个人的礼物和照料是因为我们爱他,而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些礼物而爱他。正是因为我们爱的是某些超越了礼物的东西,而非礼物本身,我们有可能厌恶这些礼物,或在对方的外显中挑出毛病,但依然爱对方——正如歇斯底里的行为向我们所证明的那样。这个被人所爱的不可名状的过剩、这个超出其外的东西,就是拉康所说的对象a,我们可以说电视并不需要了解任何拉康的理论也会被这个对象撞倒。电视所攻击的是总统的陈述(statements),却完全无损于对象a,也就是能述的位置(instance)——而它正是“现实主义愚昧”总会且必然(作为其可能性的条件)无视的。正是这个对象让里根成为里根,正是在这个对象之中——显然不是在他的陈述里——人们发现了他的一致性。美国人不是因为里根所说的话而爱他,他们爱他,仅仅是因为他是里根。
[5]此处存疑。根据互联网上可查到的媒体报道,1989年特朗普一家在阿斯本的这家饭店用餐,期间,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凡娜·特朗普和他后来的第二任妻子马拉·梅普尔斯(Marla Maples)狭路相逢,两人在饭店发生冲突。——译注
重点在于,不要将对象混淆于某些诗意的、本质主义的主体观。这个对象并不先于陈述,相反却是它的回溯性效果,或者说是超出了说出来的东西的剩余,并且这个剩余“总是回到相同的地方”,回溯性地——无论与产生了它的陈述是如何地自相矛盾——命名了同一个事物。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仅仅诉诸指涉物的举动、任何对主体言论的反驳都不能够驱散它——因为它假定了一个无须自我等同却又同一的主体(a subject that is the same without being self-identical)。
人们普遍注意到,美国对新闻媒体的欠缺尊重与它对里根的爱相互平衡。人们也注意到,像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国度”(拥有长期民主制度的国家)对警方不甚抱有好感。这些观察并不是无关要紧的,因为这可能暗示着正是因为媒体类似警察那样的行径,才使他们惹人不悦。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像警方那样行动”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因此会涉及一种特定的小说类型——它最初且最主要诞生于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类小说总是意欲诋毁这些行动:它被称为侦探小说。为了褒扬后者,这种小说系统性地从警方的法则(law)中分化出侦探的法则。而我的假设则是,侦探小说是现代民主的一种产物,因此,我将论证侦探的法则如何导向(subtend)了民主,同时我将解释它又如何受到来自警方的法则也就是科学现实主义法则的戕害。
当然还有一些人会继续坚持将侦探小说的源头追溯到希腊喜剧,但大部分批评家都愿意承认,作为一种历史性地形成的特殊形式,侦探小说仅仅从1840年代才开始伴随着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这些作家问世。然而,持前一种信念的人通常会争论说,这个类型是由科学理性的兴起以及实证法(laws of evidence)的确立而带来的。紧接着他们会提出,侦探小说颂扬了科学理性,而侦探正是实证主义思想的范本。该论点的拥趸所忽视的是,在侦探小说中,科学理性仅仅以被嘲弄和被颠覆的方式而出现。他们所一直无视的是,侦探参与的是一场“符号突变”(symbolic mutation),而这场突变在别的地方被称作民主革命。[6]不过,我并非认为在科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没有联系,事实上联系的确存在。
[6]在这里我要致谢克劳德·勒弗尔的杰出著作所带来的帮助。勒弗尔并没有仅仅将现代民主制度理论化为一种政府形式,而是提出了更为根本性的认识:它还是一场“符号秩序的突变”。在接下来的章节,我将会更充分地描绘这场突变所包含的事物,而它又如何开始被第二场突变所取代。——原注
为了理解这种联系——以及这两项之间差异的微妙性——让我们回到“特氟龙总统”的现象上。设想一个与我们所提出的观点不同的看法是有可能的:人们可能相反会认为,随着美国电视观众继续相信这位总统,哪怕对他的言辞越来越起疑,他们正重复着——以一种独特的20世纪的方式——17世纪晚期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姿态。因为笛卡尔所做的难道不就是揭示一个位置(根据语言学的理论,我们一直把它称作“发声位置”[enunciating instance])的存在吗?这个位置超出了主体所可能做出的一切说明或陈述内容。我思(cogito)不是别的,它正是这个发声的位置,笛卡尔将它孤立出来,而这成就了他意义非凡的、产生历史性影响的观点:纵使一个人所想的一切,所说出的一切,都可被怀疑、可被证明对某些错误或欺骗负有过失,但怀疑的位置(the instance of doudt)——这个思想或言说的位置——却无法被怀疑,在所有犯错的指控跟前,它始终是无罪的。
美国人并不是第一次被怀疑抱有笛卡尔式的同感。例如,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第二部分的一开篇,阿列克谢·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断言,笛卡尔主义是民主政治思想的自然模式。与其仰仗他人的权威,仰仗前辈学者所确立的知识传统,德·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之下的民众宁愿将他们的想法建立在常识上,或者说建立在那些清晰而明确的观念上,而从原则上,任何愿意对自己的想法进行彻底怀疑的人,也就是任何愿意自觉清除其所有主观色彩(subjective particulars)的人,都具备这些观念。当然,这一根本性运作所提炼出的是一个纯净的主体模式,简单地说,也就是属于现代科学的那个去自然的(denatured)、普世的主体。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笛卡尔的思想中有不少非科学的把戏,比如他利用上帝作为伎俩来欺骗科学,但这种看法不过是一种误解,因为笛卡尔的上帝只不过说明了(上帝这个)“大他者正如你一样”这个原则。而现代科学也正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根据这一原则将形成一种完全共识(total consensus)的可能性。
然而,这不仅与科学相关。这一原理同样也激发了18世纪种种伟大的民主革命,作为科学之父的笛卡尔也成为美国革命之父。因为若不是笛卡尔孤立出这个抽象位置,人们就不会想到要为一个普遍主体——其价值并不由种族、信仰、肤色、性别或者生活中的身份位置所决定——的种种权利而斗争,人们也将不会想到要代表全部主体的自由与正义而发动一场以没有特征的民主主体为名的战役。
美国对自身“根本无罪性”(radical innocence)的意识极为深刻地根植于一个信念:有一种基本的人性,共享这一人性的公民尽管是多样的却不会将之改变。民主是一个全称量词(universal quantifier),美国——“熔炉”“移民国家”——通过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全体公民能够被称为美国人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分享了任何实证的特征,而是因为我们被赋予了权利去摆脱这些特征,也就是在律法面前将自身呈现为一种非具身(disembodied)的权利。我抛开了实证性的身份(positive identity),因而我是一位公民。这是民主的独特逻辑。这个逻辑同样也能够被用来解释特氟龙总统的现象。一个被国旗煽动起情感的美国公众,对国旗所代表的基本民主原则的信念也会增倍。里根在很大程度上要为煽动这一情绪而负责,他成为一个象征库(emblematic repository),同时他最为显著地受益于这种信念——相信存在着一个我们得以认出自身的珍贵、普遍而“无罪”的位置,它超越了所有从这个位置上做出的那些形形色色、半信半疑的陈述。
于是,现在我们有了针对同一个现象的两种不同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认为针对里根的种种责难都没有击中要害,因为它们都只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人——他的阶级从属以及盟友(布鲁明戴尔[Bloomingdale]的朋友们),他作为一名演员的职业背景,他的“心理素质”(他对“干涉”行政事务的不情愿,对回忆起细节的无能或不乐意)等。然而,通过在对象a和我思之间、在精神分析的解释和哲学的解释之间建立平行性,难道我们不会重新招徕那个最常见的、对精神分析的控诉吗:精神分析是非历史的,它为推崇一个抽象而普遍的主体,而忽视了具体的个体。这个控诉又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呢?
我们必须首先想到的是,“普遍主体”这个概念本身并不是非历史的,正如我们已提到的,笛卡尔在17世纪末才将它引入,所以相反地我们必须承认,它是一个现代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概念——而没有这个概念,精神分析将会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精神分析同样在处理一个有关非实在的主体(nonconcrete subject)的问题,唯名论者宣称,在每日的现实中遇到的所有个体都是特殊且确定的,而精神分析却将自身建立在对这个观点的否定上。在精神分析看来,主体从来不是完全确定的,并把这种不可确定性作为主体的真正特性。这便是为何对精神分析主体概念的历史主义回应如此地误导人。这种回应——许多当代理论都以此为特点——将普遍主体理解为一个模糊的概念,只要稍加努力以及更贴近的历史知识,就能赋予它以更加明确的属性。这种草率的历史主义未能理解的是,普遍主体并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查尔斯·皮尔斯意义上的一般(general)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并非不充分地或者说错误地描绘了一个其结构已实际确定了的主体,而是准确地揭示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客观不确定性(objectively indeterminate)的主体。与对普遍主体的流行批判相左,精神分析强调这个概念的政治重要性。
然而,尽管我们承认了精神分析主体观与笛卡尔式主体观之间的相似性,但我们也已经开始强调它们的差异了。因为如果这两者都宣称自身缺乏实体性及确定性的存在的话,那么也只有精神分析的主体能够在严格意义下被称为不确定的。与之相反的是,我思是一个确定性的位置。这之间的差异该如何解释呢?在爱的面向下的对象a,就是我思。
让我们再一次援引拉康的公式:爱是一个人给出他/她没有的东西。不过,这一次让我们把视角放在回顾需求(need)、要求(demand)和欲望这三者的差异上。在需求的层面上,主体能够通过大他者拥有的某些事物而得到满足。一个饥饿的小孩能够被食物所满足——也仅仅是通过食物。如果母亲错误地领会孩子哭的意义,给了他一块毛毯,那么她当然就不能满足这个孩子。能满足需求的总是一个特殊的客体,比如营养或者温暖。这个问题并不是无所谓的,一个事物不能被另一个事物所替代。而爱位于下一个层级上,也就是处在要求的层级上。对一个通过哭喊来表达对爱的要求的孩子而言,给他毛毯、食物或者哪怕是责骂,都不会有多少区别。客体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在这里被废除了,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满足——只要它来自要求被传达的那一方。换句话说,不同于特定的需求,要求是绝对的、普遍化的。无关紧要的客体全都被当作大他者爱的信号而接受。不过,这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客体开始代表了某些比它们自身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这里大他者似乎给予了某些比这些客体更多的东西。这“多出来的东西”(something more)是什么呢,那么爱又是什么呢?这更多的东西正是大他者(或主体)的存有中尚未确定的部分(用拉康的术语来说就是对象a),也就是说,大他者(或主体)就是这个“多出来”的部分,但它并未拥有(have)它,因此也无法给出它。然而,爱的欺骗性在于,大他者能够给出对象a,它能够将自身存有中不确定的部分交付给主体,而主体也因此成为大他者唯一(solo)的满足、它存在的原因(reason to be)。这个关系是相互的,与此同时主体也将它所缺失的东西交付给大他者。最后是欲望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大他者保留了它所没有的东西,并没有将它交付给主体。于是,主体欲望所针对的是一种特殊的绝对(particular absolute),绝对的意思在于,如同要求那样,主体针对的是超越了特定客体的“更多的东西”;特殊在于,大他者拒绝交出它,这也就意味着它对大他者而言始终是独有的——也就是不可让渡的(nontransferable)。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我思的确定性源于大他者之爱。在我思的确定性以外,爱的逻辑解释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当笛卡尔开始通过我思来建立他的确定性并对我思的全部想法进行怀疑的时候,他(以及由他所赋权的历史主义)却最终默许了我思消失在其想法及陈述的真理之下。只要这些无关紧要(indifferent)且可疑的(doubtable)客体是从我思那里来的,它们便被接受了——既作为大他者爱的能指,也作为那些将一个我思与另一个我思相联结的真理和互通性(communicability)的能指。
但美国的情况稍微有所偏离。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为了颂扬差异与特殊性而抗拒属于我思秩序的普遍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去爱我们的领袖。不幸在于,我们依旧参与到爱的欺骗当中,认为大他者将会给予我们它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简言之,我们依旧要求有一位主人(master),不过这位主人与那个维系着我思的大他者有显著的不同,因为我们需要这位主人郑重地认可我们的独一性(singularity),而非我们的共性(commonality)。然而,在向被选举出来的领袖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美国人遭遇了一种进退两难:每个委派(accreditation)的信号(sign)[7]都取缔了它们本以为在证明的差异,因为正是通过证明差异、通过沟通差异与差异,任何信号都自动地普遍化了它们所在代表的东西,也就因此抹杀了自身的独一性,那么,该怎样才能同时既维持与一位主人的关系又保留自己的独特性?
[7]指选票。——译注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美国的解决方案是歇斯底里式的:它选出了一位明摆着并不可靠的主人——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不称职的主人。若仔细观察,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障碍的东西其实是一种解决:美国爱他们的主人们,不仅不顾忌他们的虚弱,而且恰恰因为他们的虚弱。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以多元主义(pluralism)为特征的美国民主制度有赖于我们对一位无能的(unvermögender)大他者的忠诚[8]。如果这位大他者所说或所做的一切未能履行我们所寻求的委派,如果大他者所有的回应都被证明是不恰当的,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差异性就得到了拯救,它将完好如初,如同我们的忠诚一样未被削弱——而我们的要求,锁定了大他者而不是它的反应。事实上,正是要求与回应之间的错位——我们对大他者回应的期望的落空——维系了我们的差异性以及我们的忠诚。在我们与我思的关系中,我思的全部陈述都被视为真理,不同于此的是,我们与这个无能的大他者的关系确保了它的陈述都将被视作谎言。
[8]在描述她的父亲时,杜拉使用的短语是“ein vermögender Mann”(手段很多的男人),而弗洛伊德从中察觉的却是“ein unvermögender Mann”(没有办法、无能、阳痿的男人)。通过给出这个描述,杜拉表明她要求有一位主人,而通过进一步诠释她的描述,弗洛伊德指明了歇斯底里者偏好的主人类型。——原注
那么,电视新闻——为了总结我们对特氟龙图腾的思考——并不像我们最初认定的那样,是为了让里根声名扫地而指出他陈述中的错误。相反,通过折损他的信誉,电视新闻意图使我们保持对他的关注。正如杜拉投身于成全她那无能的(invalid)父亲[9],为了使那个召唤了主人的美式要求保持活力,新闻也将自身投入了歇斯底里的电视展示当中。
[9]在杜拉的案例中,她认为自己充当了父亲婚外恋的道具:父亲拿她与K先生交换K太太。——译注
不过必须澄清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这个支撑着这一特定的、与主人的美国式关系的悖论,是民主本身所特有的。民主将主体歇斯底里化了。许多无法弥合的悖论都可以证实这个观点,但我们将只提出其中的一个,也就是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的实践所产生的悖论。而根据这一权利的相关条款,每一位公民都被给予了机会去表达他或她的个人意志;每一位公民都被给予了重要的一票。悖论在于,它只能被计为一(one),也就是只能作为一个抽象的统计数据。个体的特殊性因此恰恰就在这一表达的行动中被取消了。[10]一个人的差异性,如果根据定义就是那种没有得到承认的东西,那么任何的承认都会偏离目标,留下某些不被注意的东西。民主的主体因而被持续地歇斯底里化,分裂在寻求命名它的能指与拒绝被命名的谜团(enigma)之间。
[10]勒弗尔利用这个悖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普选权阻挠了“人民”的观念被具体化,因为数字有害于实质(substance)。它们将“人民”的形象去实体化了。——原注
民主的美式形态的问题在于,无论它如何公然地谴责大他者的行动,它仍然继续信仰着大他者所拥有的权力,相信大他者能够认可其公民自我声称的那些不胜枚举的差异。而这种信念催生了一种“微小差异的自恋”,弗洛伊德以及所有其他“布尔乔亚个人主义”的批评者们早已就这一点警示过我们。这种自恋助长了面对差异时那种固执而危险的防御,而这将因此把我们从我们的邻人那里彻底孤立出来。然而,对赋权大他者(the Other-who-authorizes)的信仰,使我们深信(无视每一种相反的迹象),这种隔绝从原则上是能够和平地维持下去,同时大他者主持着一个非冲突的空间:在那里,全部的差异都能和谐共存。
拉康对美国的自我心理学及——更进一步的——“美国生活方式”的系统攻击,也是为了保卫一种不同的差异观而展开的。这种差异观所认为的差异并不要求在当下就得到关注与承认,相反,这种差异在时间的流逝以及与他者的关系之中等待着被剥离(exfoliated)。只有当我们放弃了对大他者的吁求之时,也就是当我们接受了并没有“大他者的大他者”(no Other of the Other)这个事实的时候,这种别样的差异方能出现。没有什么能担保大他者的确定性、一致性或完整性。大他者并不拥有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也不拥有可以确认我们存在的东西。
从类似里根/新闻的关系这些本土现象,再到我们对法律所扮演角色的基本设想,方方面面都明显地说明,美国还未抵达能够理解这种差异观的关口。在美国,为了不妨碍每个主体的个体性茁壮发展,人们假定民主的原则(the law of democracy)在于退居幕后,越退后越好,尽可能少地进行干预。人们推动大政府退场,驱使它声称自己仅仅作为监督个体保护的中立方。为了阐明这个原则,我想提醒读者想一想美国一直以来从很大程度上进行空间布局的方式。在1785年的土地条例中,托马斯·杰斐逊(另一位“民主之父”)颁布法令,西部的领土将会按照一个网格状方案(grid plan)来布局,而这一方案取材自一些重要的东部城市。如果要说什么是一种笛卡尔式的姿态,那么这就是,因为网格忽略了所有地形学上的特征,使美国屈从于一个抽象的法律。为之辩护的一种观点认为——也是它能被如此广泛地接受的原因,这个方案被认为是合法分割空间的方法中最不突兀也最为中立的那个。网格并没有在事先规定建筑、城市或者任何将要占据特定象限的事物的种类,它被理解为一种没有规划的方案(a plan without a program)。
这样一种律法观念的背后是一个信念,即相信有一位可提供保护的(针对我们将马上提到的情况)、前后一致的大他者,它从原则上能顾及其公民的所有要求。精神分析的律法观却与之不同,它眼中的律法表现出某种异乎寻常的暴力,并不仅仅表现得“中立”。在法的自身内部有着某种目无法纪(lawless)的东西——参照网格的形象,让我们把它称为百老汇(Broadway)[11]。可以说,拉康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批判其矛头直指我们对“百老汇”的抑制。在美国人的观念里,正义只需要被分配,而与之对立的是,精神分析的观念相信,正义必须被创造出来。
[11]众所周知,纽约的街道按照网格状来设计,以数字为名,比如著名的“第五大道”。而广义上的百老汇横跨了数条街道,剧院林立,事实上早已溢出了这种网格规划。——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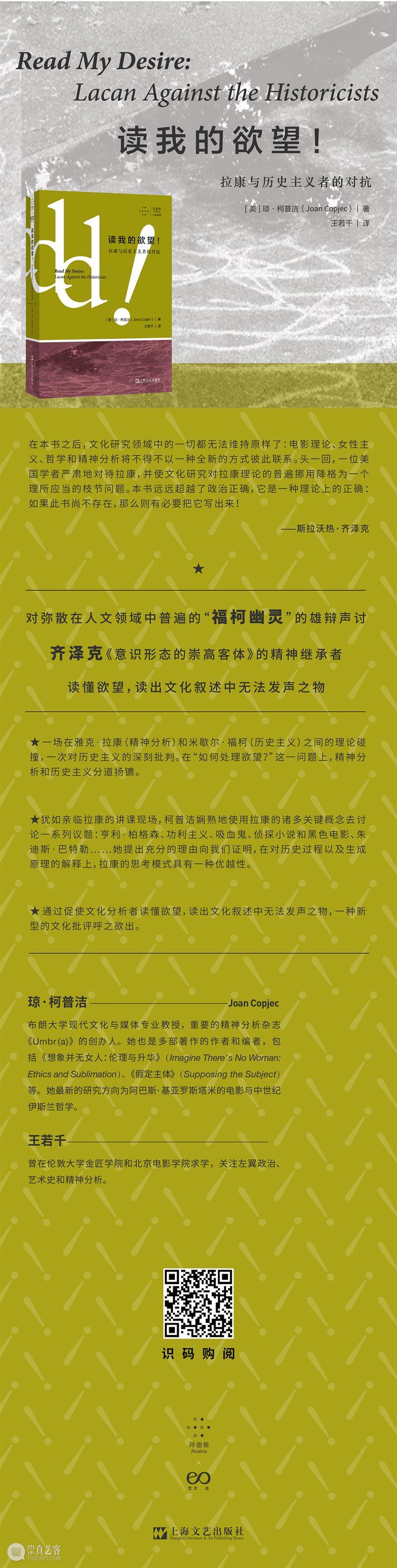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