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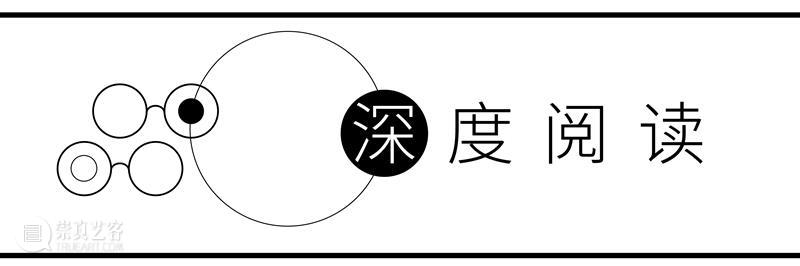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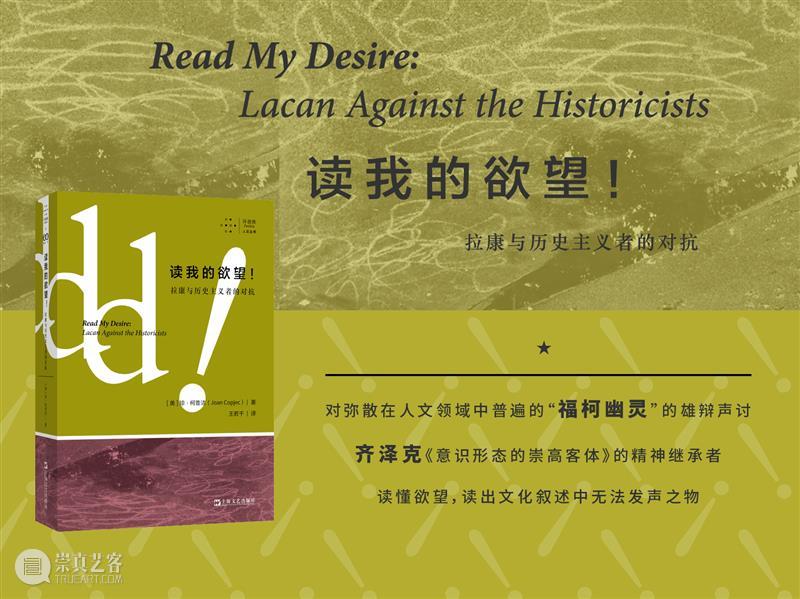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读我的欲望!拉康与历史主义者的对抗》(琼·柯普洁)的书摘。此书现已在我们微店开启预售,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预订。
导论:结构不上街
(节选)
1968年5月的一天,一个愤怒的法国学生在索邦大学某个教室的黑板上草草写下:“结构不上街”(Structures don’t march in the streets),这个句子瞬间成为表达学生不满的一句标语。作为华兹华斯那句“起来吧,起来吧我的朋友,抛下你的书本”的现代翻版,这个法文短句却丝毫没有沾染萦绕着这句话的暧昧性,它把一个特定的、土生土长的理智主义形态——结构主义视为自己的攻击对象。对这些学生来说,结构主义已经彻底死亡了,因而完全无力应对他们身陷其中的那些紧迫而混乱的事件所提出的理论挑战。结构主义因其普遍化的方案及其对空洞、僵死形式的固守而遭到谴责,并被认为一股脑儿地把所有一切都视为已成定局。而学生们反叛的动力恰恰正是结构主义似乎打算排除掉的东西:不只是特殊(the particular),更是在最自发且最具体形式之中的特殊。对此,他们不假思索地进行礼赞。
在“后1968”的年月里,这种礼赞固化为若干概念,其中之一就是“庶民”(pleb),它对某些政治话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到今日它都时常在“多元文化主义”或“政治正确”的旗帜下重返。这个概念最初由安德烈·格里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提出,它命名了许多特殊性的纯粹事例,这些特殊性有着破坏一切权力的普遍化结构的潜能。这个“庶民”,作为她或他,体现在工人、学生、移民身上,体现在因为这个社会而变得贫穷、不幸、卑微或者边缘的人们身上。它(庶民)被认为赋有“从苦难和抵抗的现实中所获得的直接知识(connaissance)”。而遵照这一定义,任何“起源”于庶民的话语都被认为具有政治性的价值和正确性,并自动地排除(foreclosed)了那些“起源”于权力位置的话语。
格里克斯曼“不拘一格”地借用了米歇尔·福柯的观点,发展出他的“庶民”概念,而福柯转而将格里克斯曼的概念纳入他自己的思考之中——但并非毫无保留的。在“逻辑的反抗”小组(Révoltes Logiques collective)对他的访谈中,福柯表达了他对庶民的警惕,并将其形容为“权力机器不变且始终沉默的靶子”。
毫无疑问,“庶民”绝不能被设想为历史的永恒基础⋯⋯一个从未完全熄灭的反抗的炉床。毫无疑问,“庶民”并没有任何与之对应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但是确实总有一些事物在某种程度上逃脱了权力关系,它们存在于社会肌体、阶级、团体和个体自身之中,而这些从来都不是一味顺从或被动反应的原材料,而是挣脱而出的离心运动和反向能量。毋庸置疑的是,“这个庶民”(the pleb)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庶民性”(plebness)⋯⋯并不能将是否外在于权力关系作为其限定来衡量庶民性⋯⋯从这个视角来看庶民⋯⋯我不认为这会与某些新民粹主义所给出的名词相混淆,也不会与某些新自由主义所喋喋不休的基本权利相混淆。
最后那句对基本权利的轻蔑评论,或许有人会不同意。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确认,福柯不加争辩地接受了对权利的新民粹主义式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新民粹主义者声称权利可以被简单地理解为自主且自我中心的个体所表达的自身需求,这些个体知道并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理由(reason)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这里我们先简单地做一个标记,我会在后文中引入探讨权利问题的其他方法并给出解释。首先冲击我们的是福柯在这段话中将庶民观念去名词化所体现出的审慎和睿智。福柯不再把庶民理解为掌握着一种特殊的知识或历史——相对于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而言——的个体或者由这些个体组成的阶级,取而代之的是,它完全抽空了内容并因此在结构上不可知、不可想也最终自然不可历史化。庶民所发出的抵抗并不来自某个外部,相反它来源于权力系统自身的局限,并因此不会被它消解。
接下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福柯在论及抵抗时所使用的特殊说法(dialect):“‘这个庶民’并不存在,存在的是‘庶民性’。”读者难道觉察不出这是一句拉康式的改写吗?在福柯的句子背后是否能听到几个著名的拉康派公式在低语着“女人并不存在”(La femme n’existe pas),以及“有一些一”(Il y a d’l’Un)?拉康式句子跟福柯式句子的共同之处在于对两种存在做出了区分,两者分别由动词“存在”(exister)和短语“有”(il y a)来暗示。第一个分句所暗示的存在从属于一个谓词判断(predicative judgement),同时也从属于一个对存在的判断,这就意味着,这是一种其特性或性质能够被描述的存在。而第二个分句所暗示的存在却仅仅从属于一个对存在的判断,我们只能说它存在或者不存在,却不能够说出它到底是什么并以任何方式来描述它。如果像福柯说的那样有一种“庶民性”的话,我们却不能够说出它到底是什么——“庶民性”的真理因此将永远被定位在任何人的知识之外,包括那个占有它却不能再被我们称为“庶民”的他/她本人(“the” pleb him- or herself)。
本书的论点是,尽管福柯在此前我们所引用的段落中对“庶民性”给出了独到的见解,我却想指出,他可以被指控提出了其他反对乃至排除庶民性之可能的论点。为了更加准确地勾勒出这些“其他论点”究竟有哪些,并说明它们如何违背了他在“逻辑的反抗”访谈中所表达的观点,接下来的每一章我都将关注福柯式问题意识(Foucauldian problematic)中的一些概念或现象——它们都是福柯本人或者他的学生们已经给予许多理论关注的概念或现象。所以,福柯这个名字在这些章节中并不指代这位作者的全部写作或观点,而是特指其中一部分,它们令人遗憾地触发他偏离了在表达有关“庶民性”的观点时所蕴含的理念,关于一种没有谓语的存在,或者换另一种说法,关于一种不能在社会的实证性(positivity)中被把握的剩余存在。具体而言,我所要批判的观点并非贯穿福柯的全部著作,而仅局限于他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以及1970年代中晚期的论文和访谈,在这段时期,他对语言学和精神分析理论发生了立场上的转变。像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那样,他在一开始根据结构主义所定义的符号结构和精神分析所定义的精神结构来剖析社会事实,但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一时期,他不仅抛弃了这两个学科,甚至还激烈地与之相对立。在这个时期所做的一篇访谈中,福柯简要地说明了这个转向:“我相信我们应当将战争和斗争作为那个大的参照模型,而不是符号和语言。承载和决定我们的历史是战争式的(war like),而非语言式的(language like)。是权力的关系,而非意义(sense)的关系。”事实上通过这句声明,他与那些拒斥结构主义的异见学生实现了某种团结。不是语言学那象牙塔般的结构,也不是一种自反的符号学那干瘪的形式结构,而是战争与权力的结构,是在街头存活的结构:上街了的结构,这就是福柯似乎在拥护的。
我并不想通过将其简化为单纯的修辞策略来琐碎化(trivialize)福柯对语言学或精神分析的分析模式的摒弃。相反,我首先要强调那个切实地让学生们的不满与福柯的不满相并行的部分,或许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建设性地提出要取消普遍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而代之以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后者不再要求自己对某种支配一切的宰制结构(structure of domination)进行分析,而是将目光转向具体的权力机构。这并没有什么错——对特殊性的转向具有无可置疑的合理性。如果有人根据他对特殊的强调,去或多或少地质疑他与一种新的民粹主义的崛起存在某种共谋关系——尽管他确凿地谴责过这种民粹主义,那么只要想想福柯所真正关切的是小规模权力关系系统的微观运作(microworkings),而不是它们所产生的那些被宏观历史所忽略的“小人物”(little people),我们便很容易驱散这种质疑。虽然他总是关注细节问题,但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位置,在他分析中的这些最小要素都从未被视作一个孤立的切入点,而是被当作一种关系去把握的。
这就引入了我们的第二个论点。尽管关注权力与知识关系的福柯主义广受推崇,因为它被认为必要地纠正了那些更加天真地将这两项当作独立实体(discrete entities)来处理的政治理论,但我们则要说,将社会简化为这些关系是成问题的。福柯反对有些社会学理论,它们试图借助对权力系统的描述来解释特定的社会现象,认为权力系统从外部介入并歪曲了这些现象;而福柯则认为,权力体制是内在地透过现象本身而运作的。例如,从18世纪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科学文献将性变态的种种形态进行归档并对各位家长、教育者、行政长官和医生发出忠告,告诉他们如何来保护他们的被监护人。我们不能按照一种由压制性权力(repressive power)所颁布的法令来看待这些科学文献,它们并不只是决意要杜绝这些私人行为,而其自身也是权力网络的一部分,通过将性构建为自我(the self)的隐秘内核,在不同的个体间倍增了交互点与关系的形式。换句话说,福柯不再将权力理解为施加于社会的外在力量,而是将它看作内在于社会的(immanent within society),正是这些不对等关系所形成的“精致的、差异化且连续性的”网络构成了社会的根本。这样一来,社会就恰好与一整套权力关系的体制相吻合,因此前者便不再被认为是由一种外在权力所结构的,而是一种自我结构(structure itself by itself)。
本书想要与之进行论战并不断地斥之为历史主义的,正是这个内在性的理念,这个将原因理解为内在于其效果的场域的理论倾向。由于我不打算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给历史主义下一个简要的定义(我希望一种更加灵活的定义会在我们的讨论所提供的不同语境中自然呈现),那么或许可以先在这里尝试提出一个:所谓的历史主义就在于把社会化约为它内在的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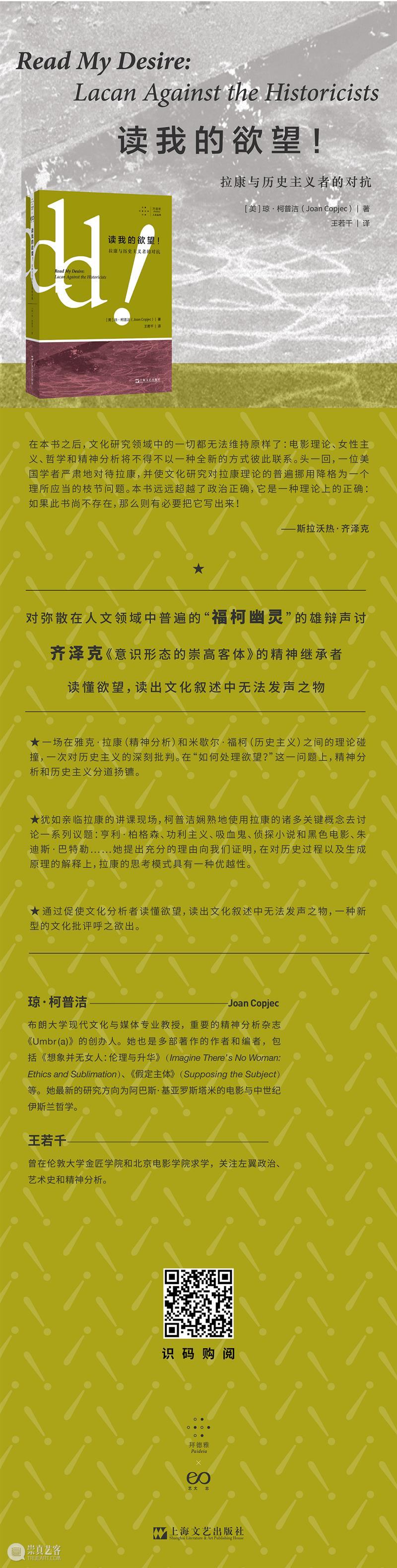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