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尽柏,记忆与意识》创作背景概述
一个由文字、图表、装置三个层次构成的作品。
它描绘了以我(人类中的一个个体)的生命和柏树(松柏门植物中的一个科)的生命为双轴线展开的复杂因果关系。作品广泛截取与追踪着多种心理、物理、社会模式的起源、发展、交互与再现。里面遍布着对线形与辐射形这两种基本几何结构——以及对逻辑思维和整体思维这两种基本思维方式——的展示与探索。
作品里涵盖的每一个现象都是纪实的,而作者的真实用意和情感均匀地分布在它的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里。
创作年份1994-2022
我在6.75岁、刚入小学不久时进行过一个行为。当时的我注意到,我入小学前的记忆由于周围环境的改变而迅速流失。因此,我决定用在时间轴上沿着一个选定的原点对折的方式,每经历新一天就复习前一天的记忆,以一种特定的算法递增记忆量,力求将从前的记忆彻底不漏地复习完,并永久地整合到自我中。这个行为开始后不久,就因为种种当时无法克服的技术困难和心理困难而被我放弃。接着我就彻底忘了这个行为存在过,也没再逆转入小学前的记忆的流失。2018年底的一天,我脑中突然凭空出现一行字,“双尽柏,记忆与意识”。这行字被我分为两股去探索。第一股是前三个字,“双尽柏”,我称之为“原初意象”。第二股是后五个字,“记忆与意识”,我称之为“原初疑问”。称后者为“原初疑问”是因为我直觉理解到这个短语的背后是一个更长的句子 —— 确切地说是一个更长的疑问:“在我的生命里,记忆机能与意识机能哪一个先出现?”
我一开始探索“记忆与意识”这第二股,它就立刻将我引回了我6.75岁做过的那个行为,让我完整地回忆起那件事的始末和细节,克服种种困难把它还原和记录下来,并借用周围文化中存在的“项目”这个观念强调它的创造性意义,因此把它正式命名为“记忆项目”。在回忆起“记忆项目”的同时,我还回忆起了6.75岁时的另一件事,但最终没有把第二件事包括进这个作品里。
在接下来的两年半内,我几次岔开,又在意志的驱使下回访2018年底那个原初意象和原初疑问同时迸发的瞬间。“记忆与意识机能在我的生命里哪个先出现”,这个疑问既有客观价值又有主观价值。从科学的角度,它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但不是类似问题里唯一值得问的。完全可以提出和它切入点不同、但最终趋向殊途同归的疑问,比如“感受与意识机能在我的生命里哪个先出现”,“感受与记忆机能哪个先出现”或“逻辑与想象功能哪个先出现”。但当时在我脑中诞生的之所以是那个疑问而不是其他疑问,我相信是因为“记忆”与“意识”这两种机能和我当时的生命历程的线索和卡点特别相关,是我的潜在疑问网里的热点,回答那个疑问有可能解缠并融解很多其他疑问。询问 “记忆和意识机能在我的生命里哪个先出现”,其实就构建了一个契机,通过细究它们的异同去探察它们各自的本质。询问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哪个先出现,也是在以平行方式追问它们在地球上的生命现象演化史中哪个先浮现。通过逐渐尝试回答这个疑问,我慢慢驱散了其他许多给我带来窒息感的存在层面议题,并对这个疑问作出了初步(可能不是最终)结论:在我的生命里记忆机能先出现。
对“双尽柏”这一原初意象的潜入、探索,也与对那个原初疑问的探索不同步地展开;展开的过程中,两者自发地彼此交织。起初,我暂把“双尽柏”三个字解释为“两端都是树冠、向各自的方向生长到尽头的柏树。也许说,这柏树的一端是记忆,一端是意识”。但我明白,这是它的字面涵义。它的内部包含着更多的讯息和关系,其中的一些一旦被识别,将会修正甚至颠覆它的首层涵义。最终,我逐渐化开了“双尽柏”三个字紧紧裹着的涵义体系。“双尽柏”、“记忆与意识”这两股探索开始更深入地交织 —— 并因为交织带来的直径收缩,能以较接近于作品的方式被截取。
同时,我一直在试图回答:“是什么造成了 ‘双尽柏,记忆与意识’ 这八个字在2018年底看似凭空的诞生?”我的答案是,“是它之前的许多系客观进程和主观进程的交织。”继续问,“那这个作品的真实起源是什么时候?”我的答案是,“可以说是3亿多年前松柏门植物起源的时候;可以说是远古人类与柏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可以说是我6.75岁的时候;可以说是 ‘双尽柏,记忆与意识’ 这八个字诞生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介于以上事件之间的某一个时间点。”作品里的“装置”部分,是对“作品的真实起源所位于的过去某一个时间点(特别是 ‘远古人类与柏树第一次接触’这一可能存在的时间点)”的想象性抽象;也是对这个作品在将来有可能将我带到的生命状态的期盼、以及对这期盼的内容的抽象。



展览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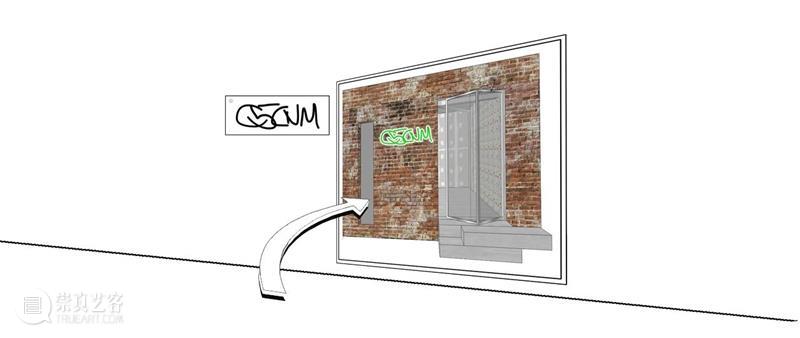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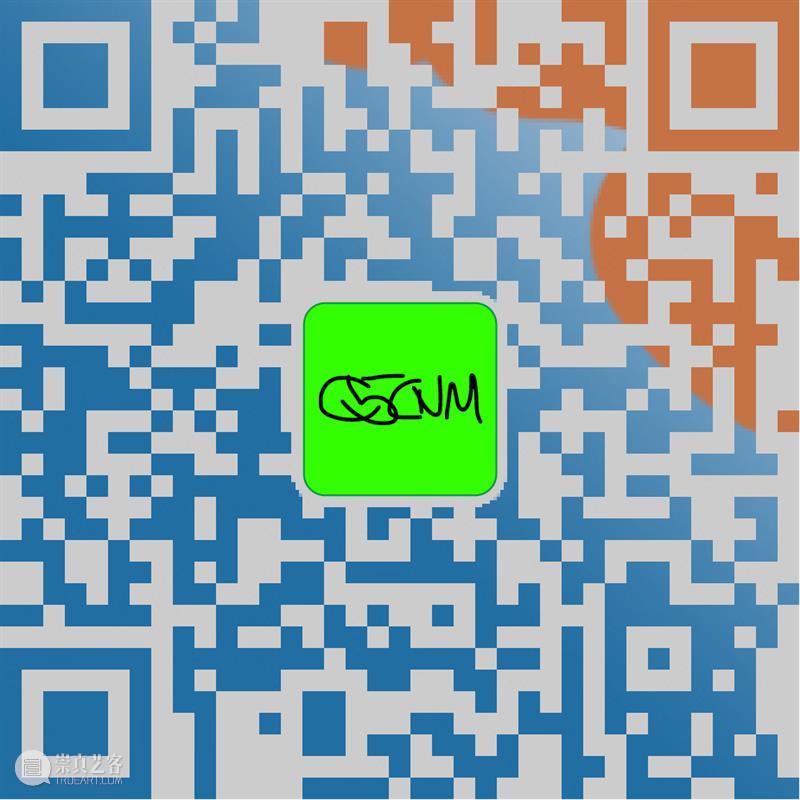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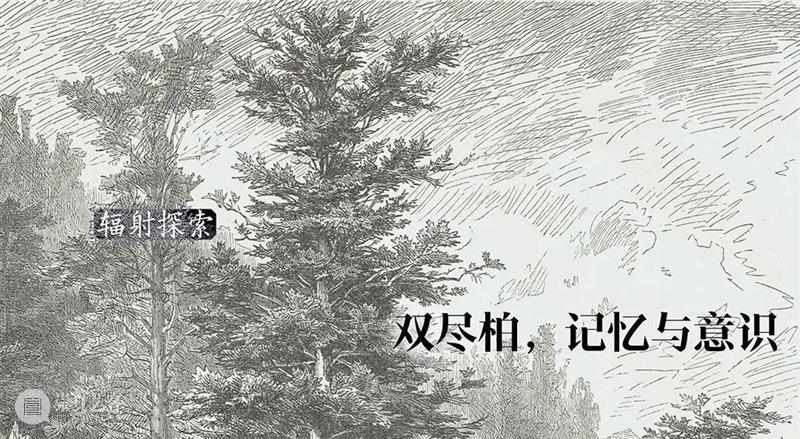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