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原刊登于《画刊》杂志2022年第1-2期

图:1937年“堕落的艺术”展览 ,德国柏林
1937年“堕落的艺术”展与图像的伦理体制
王志亮
——恩斯特·布洛赫,1937年
1937年,“堕落的艺术”展览开幕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布赫洛写下了上面这段让人感觉阴森恐怖的语言,包含这段话的文章后来也被研究该展览的学者不断提及。[1]“堕落的艺术”因其表现主义倾向,内容多显得阴森恐怖,所以有关这类作品的展览有时被称作“恐怖的房间”。布洛赫是当时“堕落的艺术”(表现主义)的支持者,并把它们看作当代德国文化的象征。可是,在“恐怖的房间”里,这类艺术已被宣布死亡,并且遭受大众嘲弄,这让正在流亡中的布洛赫感到无比悲愤。他的短短几句话,揭示了“堕落的艺术”展览的几个关键点,一是涉及展览作品本身,“恐怖的房间”与“堕落的艺术”的命名与艺术风格的关系;二是在作品传播方面,观展的公众与“堕落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三是在艺术的价值判断方面,不同知识群体对“堕落的艺术”给出的不同价值判断。
一、恐怖的表现主义与无意义的拼贴
1937年7月19日至11月30日,最大型的一次“堕落的艺术展”在慕尼黑的德国考古研究所开幕,展出112位艺术家的650件作品,帝国视觉文化部部长阿道夫·齐格勒(Aldolf Ziegler)主持开幕式。[2]德国考古研究所空间狭小,再加上展品众多,布展时间短,于是显得凌乱不堪。与此相对,提前一天开幕的“伟大的德国艺术展”在刚刚建成的德国艺术之家开幕,展场空间高大明亮,展览由阿道夫·希特勒(Aldolf Hitler)主持,展示被认可的德国艺术。1937年同时举办的这两个风格对立的展览,已被学界认为是当时第三帝国从意识形态领域干预艺术的最高峰。根据学者克里斯托夫·楚施拉格(Christoph Zuschlag)的研究,从1933年第三帝国领导德国开始,艺术界就已经陆续展开清理前卫艺术的活动,其中“恐怖的”和“堕落的”是形容这时前卫艺术的两个关键词。前卫艺术的内部划分也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化,一切具有革命性倾向的作品,都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前卫艺术,其中主要的创作手法包括表现(或原始主义)、抽象和拼贴。
1937年之前,以“恐怖的房间”命名的展览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33年4月17日,在德国纽伦堡的城市画廊举办,另外一次是1935年11月27日,在德国哈勒(Halle)的莫里茨堡博物馆举办。[3]在纽伦堡城市画廊的展览中,参展艺术家里,奥托·迪克斯(Otto Dix)、科纳德·弗里克斯穆勒(Conrad Felixmüller)、汉斯·普尔曼(Hans Purrman)和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Karl Schmidt-Rottluff)后来被划入“堕落的艺术”行列,在慕尼黑的展览中被集中展示。同样,在莫里茨堡博物馆的展览中,“恐怖的房间”里展出的也是表现主义绘画和雕塑,其中包括李奥尼·费宁格(Lyoney Feininger)、恩斯特·凯尔希纳(Ernst Kirchner)、奥斯卡·柯克施卡(Oskar Kokoschka)、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和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这些艺术家都是后来“堕落的艺术”展中的主要艺术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莫里茨堡博物馆的这次展览是长期陈列展,展品来自博物馆自身的馆藏作品,这也表明,在1935年,博物馆内部已经开始用某种贬义的描述方式,挑选出表现性和抽象性的作品,进行自我清理。
1933年在德累斯顿举办的“堕落的艺术”展,成为后来1937年慕尼黑展览的样板,其展览主题、布展细节乃至巡回模式都如出一辙。1933年9月23日,在德累斯顿的新市政庭院举办的这次展览,包括42件油画、10件雕塑、43幅水彩和112幅图画作品,风格多为表现主义。之后,展览在德国8个城市巡展,一直持续到1936年,最后作品整体并入1937年慕尼黑的展览。[4]巡展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次事件重合。1935年9月7日,“堕落的艺术”巡回到纽伦堡的城市画廊进行展出,该画廊在1933年时曾组织过“恐怖的房间”艺术展。众所周知,纽伦堡在1933年被选为第三帝国代会举办城市,1935年展览举办时恰值当年党代会举行之时。因此,“堕落的艺术”在继1933年只为少数内部人士参观后(其中包括戈培尔和希特勒),在该画廊正式与大众会面。据资料显示,参观人数达到12706人。按照楚施拉格提供的资料,在纽伦堡的这次展出,画廊还在德累斯顿展品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件迪克斯的作品《舞者阿尼塔·伯伯尔肖像》,该作曾在1933年的“恐怖的房间”展出过。

图1:The Dancer Anita Berber,Otto Dix,1925

图2:Portrait of Karl Krall,Otto Dix,1923
迪克斯是继桥社和青骑士之后德国重要的表现主义艺术家,被归入德国新客观主义(new objecttivity)。1937年的“堕落的艺术”展中,展览馆分两层,楼上一层为主展厅,分七个房间展示,地下一层为辅,分三个房间展示。迪克斯和其他德累斯顿艺术家的作品多被放在地下一层的第一展室进行展出。《舞者阿尼塔·伯伯尔肖像》虽然没有在慕尼黑展出,但在地下一层的展室中,我们能看到相同风格的《珠宝商卡尔·克拉尔肖像》以及其余25件作品。两件作品(图1,图2)采取同样的创作手法,模糊人物背景,扭曲人物形体,以背景和服装色彩来烘托人物内心情感。迪克斯并不强调狂放的笔触和厚重的色彩,基本使用平涂技法,在改变人体结构的过程中强调线条的流畅性。舞蹈演员伯伯尔被置入红色背景中,浓妆艳抹的面部已经具有后来《卡里加里博士》的烟熏妆效果,苍白的面孔在鲜红色服装和背景的环绕中格外显眼。珠宝商克拉尔的面部被描绘成暗紫色,浓重的黑眼圈让整个肖像看起来精神萎靡,神情奸诈。艺术家也特意扭曲了肖像的身体结构,凸起的背部肌肉与臂膀严重脱节,手臂丝毫不遵循解剖结构,抽象的衣纹包裹瘦弱的手臂,以对比宽大的胸部轮廓。所有这些不合适,都在强调肖像的非常人状态抑或是病症。在与这类肖像一起被选入展览的其他作品中,死亡和恐惧是贯穿迪克斯创作的两个主题,所以,这类作品自然被看作是“恐怖的房间”展览的代表作。

图3:The New Man, Otto Freundlich, 1912

图4:Crucified Christ, Ludwig Gies, 1921
20世纪初,在现代艺术中流行的原始主义,也是表现主义的重要元素,同样在“堕落的艺术”展中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在这次展览中,被广泛提及的是两件雕塑作品:一件是奥多·弗罗因德里希(Otto Freundlich)的《新男人》,后来被作为该展览导览册的封面图像广为传播;另一件是路德维西·吉斯(Ludwig Gies)的《基督钉上十字架》,被放置在第一层的入口处(图3,图4)。在一篇回忆录中,作者彼得·冈瑟(Peter Guenther)谈到后者带来的视觉冲击:
我清楚地记得那件恐怖的作品,它被放在上层展厅入口处的台阶上,占据整个墙面。对我来说,除了感到震惊,这件现代艺术作品还让人想起格吕内瓦尔德在16世纪创作的《伊森海姆祭坛画》,充满痛苦和悲伤的情感。这两件作品在效果上同样让我热泪盈眶,但是,眼前这件作品的展示方式却让它效果尽失。[5]
这两件雕塑的变形幅度要远远大于迪克斯代表的新客观主义,究其原因,主要是甩掉了前者存留的那一点点精致,显得十分粗犷,充满未经驯化的野性力量。这类风格后来被称为“原始主义”,其代表艺术家还有桥社的恩斯特·凯尔希纳等。
带有表现主义特征的作品因其夸张地使用色彩,扭曲对象的形体,从而显得恐怖。如果这类“恐怖”或“丑陋”可以算作堕落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些将表现推向抽象的作品,以及使用了蒙太奇手法的作品,它们虽然不恐怖,但也因挑战了新古典艺术的法则,被算作“堕落”的另一个衡量指标。在这部分作品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康定斯基。抽象类的作品被集中挂在一个墙面,康定斯基的作品最多,另外还有几张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和利西茨基(El Lissitzky)的作品。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康定斯基与达达艺术的混杂中,也就是说,康定斯基不仅被作为抽象风格的代表,而且还被归入达达主义。广为流传的那张图像档案,就是以放大了的康定斯基作品细节为背景,倾斜悬挂保罗·克利(Paul Klee)和科特·希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的作品,照片中希特勒与其他展览组委会成员正在参观展示达达作品的那面展墙。在第三帝国看来,达达的无意义拼贴和没有具体形象的抽象是一回事,消除意义就是“堕落”的标志。展览可能因为很难找到德国达达的具体作品,于是在墙上张贴了两张拉乌尔·豪斯曼(Raoul Hausmann)制作的《达达》杂志封面。希维特斯是柏林达达的间接参与者,但他的贡献在于创造了Merz这个与Dada具有相同意义的词,通常与德语的bild(图片)连用,于是通过拼贴创作的作品就有了自己的名称——“拼贴画”(merzbild)。在这面展墙上,还张贴了一张关于希维特斯拼贴画的说明:
科特·希维特斯那些敢于冒险的画作,通过自身的组合,产生和谐的色彩,让人感觉一新。废品材料轻柔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从未有过的和谐感。
——科特·希维特斯,1924[6]
那位署名Weiderkop(韦德考普)的作者,发现了拼贴画在意义之外寻找的和谐形式,在他看来,现成品材料本身的组合即能产生优美的形式感,因而具有艺术意义。而希维特斯却恰恰因为无意义本身具有的反艺术特征,强调无意义的意义所在,这正是典型的达达态度。一方面是无意义拼贴创造出的美感,另一方面是反艺术,这看似矛盾的两种言论,在我们结合展场情况分析时,会发现他们不过都是在就艺术谈论艺术。而恰恰是这类形式主义的分析方式,与整个“堕落的艺术”展的宣传话语形成巨大反差。控制“堕落的艺术”展的话语是一种被朗西埃称为“图像的伦理体制”的话语,其与“艺术的美学体制”的话语形成对照。
二、去艺术化
——伦理判断的必然结果
在第三帝国的一系列发言中,“堕落的艺术”展的目的被描述得再清晰不过了:
那些不能让人愉悦的艺术,不能得到广大健康人民真心赞同的艺术是不可忍受的。这类艺术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孤芳自赏,但又不足为奇。它不是肯定,而是试图迷惑人民准确的直觉。[7]
1937年7月18日,也就是在“堕落的艺术”展开幕的前一天,“伟大的德国艺术展”在刚建成的德国艺术之家开幕,希特勒发表了讲话,上面一段引文正是出自这次讲话。按照彼得·冈瑟的回忆,当他在1937年到达慕尼黑时,报纸和广播还在处处宣传这个展览,报纸上刊登了希特勒的讲话原文,该讲话的主要内容便是攻击现代艺术。[8]上面短短的几句引文,正好呼应我们在文章开端提到的“堕落的艺术”展的第二个关键点,即在传播过程中,展览组织者如何设定了作品与观众的关系,同时也足以让我们总结出第三帝国判断艺术的基本逻辑:首先,优秀艺术的标准是让人愉悦;其次,他们将这个愉悦感的评判者定义为占大多数的“人民”,而且是身心“健康”的人民;最后,不符合上述标准的艺术都被判定为异类,必须予以反对,以避免它们误导“广大健康人民”的直觉。
上面这一判断艺术的方式属于典型的伦理判断,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将其总结为“图像的伦理体制”。第三帝国所言之人民,实际上是被编织出来的谎言,背后却预先设定了某种伦理秩序的统治意志。表现主义和拼贴画显然不是以愉悦观众为目的,所以,必然会被第三帝国认定为可能误导人民的艺术,甚至被认为会进一步鼓动人民扰乱正常的伦理秩序。进一步回顾图像的伦理体制的几个重要方面,能帮助我们厘清“堕落的艺术”展览背后承载的一系列意识形态目的。
按照学者让-飞利浦·德兰蒂(Jean-Philippe Deranty)的总结,朗西埃的艺术体制(regime)是指“思想、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这应该与1968年之后当代艺术界出现的体制批判(institution critique)区别开来。前者更加类似于乔治·迪基(Gorge Dickie)“艺术惯例”论中的institution,只不过朗西埃将其中之意义历史化了。[9]在朗西埃的三种艺术体制中,图像的伦理体制出现时间最早,其次是艺术的再现体制和审美体制。但这三类体制一旦出现,就不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它们各自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用户群体和付诸实践的对象。
按照艺术体制是处理思想、语言和世界之间关系模式的定义,我们可以将艺术的伦理体制转述为:使用者采用伦理标准来建立艺术与思想、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接下来的关键词其实是伦理(ethical)。虽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政治体制中的伦理规范各不相同,从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艺术的伦理体制。但是,自从柏拉图采用伦理判断的方法来规范诗人的模仿行为,艺术的伦理标准一般就包含了这样两层含义,第一是真理与假象,属于存在论层面,即以艺术作品是否再现了真实为标准;第二是影响,属于道德和政治层面,即艺术作品对整个社会民众的道德影响以及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影响是否积极。
在2010年的新近文章《美学异托邦》中,朗西埃再次谈到了美学中的伦理问题,这次他使用的词汇是“伦理原则”“伦理分配”和“伦理秩序”。依然通过回到柏拉图,朗西埃从中总结出在社会治安中伦理分配所遵循的原则,即“这意味一种等级原则:人们所能感知的,和他们所能理解的,是他们所作所为的严格表述;他们的所作所为由他们是什么决定,他们是什么由他们的位置决定,反过来,他们的位置又为他们是什么决定。”[10]一个社会秩序能够按照上述伦理分配运转,就达到了理想的伦理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什么人处于社会中什么位置,做什么事,能够理解什么,如何进行表达都得到严格限定。总之,伦理秩序是依据个人能力分配彼此在社会中的身份和位置。所以,伦理秩序要求确定性和稳定性,惧怕不确定性和混乱(chaos),“不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是在这一秩序下常用的口号。
在图像的伦理体制中,对艺术进行伦理判断,最致命的结果便是某类艺术的艺术性被取消。图像“不能表现什么”和“必须表现什么”,这两个问题的衡量标准都不在艺术风格本身,而是以外部的意识形态要求为参照系。也就是说,那些不符合外部意识形态要求的图像被作为混乱因素的代表,必须予以否定。如果对比一下朗西埃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出发总结的艺术的再现体制,伦理体制的特征可能会更清楚。在朗西埃看来,艺术的再现体制是西方古典艺术原则的体现,它包含了四条核心原则,分别是虚构原则、题材性原则、得体原则和现实性原则。[11]两种体制的区别在于,一个专注于艺术内部,一个专注于艺术外部。两者虽然都包含不平等的元素,但内容大不相同。再现体制中的不平等是指艺术内部的不平等,例如题材的等级次序、故事内容是否合适等;伦理体制中的不平等是指艺术外部的不平等,如艺术与外部现实相比,要低一层次,不同的艺术造成的影响不同,因此要有等级之分,甚至被剥夺艺术的身份。然而有时在具体的意识形态中,伦理体制和再现体制又并非泾渭分明。当再现体制中的艺术作品等级制度一旦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联系,对艺术的判断便再次来到外部,再现体制瞬间演变为伦理体制。这种体制的混合形态在第三帝国评判“堕落的艺术”时,体现得再明显不过。

1937年11月,在“堕落的艺术”展览即将结束时,主办方制作了一本32页的导览册。这本画册遵循了慕尼黑展厅内的布展方式,作品旁边辅以解说性文字,来引导读者的判断,间或穿插希特勒的发言,以显示判断的权威性。整本画册文字成为当代研究第三帝国艺术观念的重要文献。画册的封面是那件粗犷的《新男人》雕塑,下方“艺术”(kunst)一词被设计为扭曲、放大的红色字体,并且加了引号。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嘲讽,是对这类作品可否称之为艺术的质疑。我们甚至可以判断,对第三帝国来说,这类作品根本就不是艺术。因为,依据伦理判断的道德和政治标准,它们必须被公之于众——宣告其危害,然后再被销毁掉。[12]
“德国人民”被构造出来,以区别于“非德国人民”或“非人民”,而“非人民”创造的必然是“非艺术”。两个“非”之间往往可以进行颠倒,即“非艺术”必然出自“非人民”之手。因此,人民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区隔的工具,时刻意味着对立面“非人民”。在展览导览册最后,一篇名为《终结艺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再次强调了第三帝国设定的“人民”意义。正如上文所论,“人民”是健康的人民。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又为健康的人民作了进一步设定:健康人民只存在于新时代的德国(第三帝国时代),具体体现为“强壮”和“美丽”。相较于此,那些不健康、孱弱和丑陋的人,应该被划为“非人民”。由此可见,第三帝国规定了“人民”是新时代德国的唯一真实,所以是可以被再现于画面的合法群体。而那些“非人民”,既是指画面中扭曲和丑陋的形象,也被用来指创作这些形象的艺术家。总之,“代表德国人民”成为正义的化身,“堕落的艺术”展正是要“代表德国人民”,“禁止任何类似不幸的发生——遭受视觉缺陷的受害者,避免(这类艺术家)欺骗大众接受他们信以为真的扭曲的视觉形象,甚至是自以为是的‘艺术’。”[13]可见,表现主义作品中那些非再现性的色彩被作为艺术家病态的标志,从而被划为不健康的“非人民”。
从身体的自然素质到身体的种族属性,再到身体的政治倾向,“非人民”被具体定义为病人、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在第三帝国的图像的伦理体制中,艺术家及其作品被按照政治和道德标准归入这三个群体,视为“非人民”,并且指认他们又进一步在绘画中描绘了现实中的“非人民”,或者把“人民”扭曲为“非人民”。
首先,病人、无产者和妓女等群体因为病态、孱弱和丑陋,被以“非人民”的伦理和道德标准划为堕落的标志。艺术家作为病人,创作了这类“非人民”形象或者是不能被“人民”理解的视觉形象。“人民”与“非人民”在这样的划分中,被进一步极端化为“人”与“非人”。“堕落的艺术”展览导览手册,为了让展览在巡回过程中达到更明确的教育目的,将整个展览的作品划分为九组,其中,第一、五、七、九组分别批评愚蠢的绘画选题,谴责妓女题材的不道德,讽刺艺术家表现傻子、白痴和残疾人的行为,以及将抽象绘画判断为艺术家的精神病导致的结果。这些否定式语言,不禁让我们回想起柏拉图对诗人模仿行为的担心。卡尔·施密特-罗特鲁夫和恩斯特·凯尔希纳创作的女性形象,被贴上了标签——“娼妓的道德楷模”;奥托·迪克斯和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的作品,也被贴上了“‘现代’妓院艺术”的标签;欧根·霍夫曼(Eugen Hoffmann)和保罗·克利的作品则被拿来和精神病人作品比较,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甚至不如病人的作品更具人性;科特·希维特斯等人的拼贴画体现出较为抽象的形式,被评价为“这样的作品,竟然被严肃讨论,甚至卖出了好价钱!”[14]这些赤裸裸的贬低或是反讽式的评价都与艺术无关,仅与道德判断的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相关。
其次是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两者往往被同等对待,既是基于种族主义,更是基于政治目的。展览的第三、四、六、八组围绕前面两个群体展开,把布尔什维克党甚至犹太人艺术家煽动阶级斗争的企图分为三类,一是表现无产阶级的痛苦,二是表现资产阶级的腐朽,三是表现战争的残酷。只要是与这三类主题相关的作品,都被贴上“‘艺术’煽动阶级斗争”的标签,这里的“艺术”被故意加了引号,在所有评价性文字中,甚至“艺术家”也均被加了引号,这正是处处呼应封面红色扭曲的“KUNST”,不断提示展览中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不是艺术。奥托·迪克斯因为创作一系列反对战争的新客观主义绘画,从而成为堕落艺术的典型代表,其作品被评价为“破坏国家防卫的绘画”。因为在这类绘画中没有犹太商人的形象,于是该群体被怀疑是这类艺术作品的幕后利益集团。更有甚者,那些表现黑人的作品被认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要抹除最后一点种族意识的痕迹。这一判断显然是在指涉现代艺术流行的原始主义倾向。部分犹太艺术家被放到一组给予论述,摘录的希特勒发言更是从阴谋论的角度指责犹太人的诡计:“犹太人很大程度上通过操控媒体,在所谓艺术批评的帮助下,逐渐搞乱正常有关艺术功能和目的的认识,而且摧毁这一领域的健康回应。”[15]
最后,在对宗教题材的评价中,图像的伦理体制和再现体制体现出了交叉融合。相较从伦理道德和政治层面考量,“非人民”和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都必须予以彻底否定,那么对宗教题材而言,则是如何表现的问题。这其实涉及艺术的再现体制的题材性原则和得体原则,但是,又因为第三帝国总是否认艺术的虚拟性,往往将艺术与外部的现实道德、政治相联系,这又让判断标准滑入图像的伦理体制。法国古典主义的评价原则被第三帝国毫无保留地用来判断什么是“伟大的德国艺术”,而表现主义艺术家却并不认同这套古典法则。在再现基督教圣人事迹这类古典题材中,诺尔德(Emil Nolde)等表现主义艺术家将基督教人物表现得形象扭曲,面目狰狞。面对这类作品,“堕落的艺术”展的导览手册使用的判断语言是:只要有点正常感知的人便会发现,这类作品“是对宗教观念的无耻嘲弄……那些基督教的形象带着恶魔的面具向我们淫笑。[16]”导览手册的编写者一定从这些表现主义的形象中读到了对宗教严肃性的羞辱,正如19世纪末期,沙龙的评论家感受到马奈的《奥林匹亚》是对女神肖像的羞辱一样。同样的体裁没有得到合适的再现,于是与再现体制的标准产生了冲突。但是,“堕落的艺术”展对这类作品的判断并未止步于此,有失体面的宗教绘画从再现滑入道德,再次进入政治领域。在涉及到是什么赞助了这类表现主义的宗教绘画时,导览手册给出的答案是:犹太人。手册指责那些卖给犹太商人的出版物竟然给了这些作品正面评价,认为“这些可怕的形象揭露了德国宗教情感的真相”[17]。所以,导览手册评判的表现主义宗教绘画,最终依然导向第三帝国排斥犹太人的政治目的。
三、拿什么拯救艺术?
——施莱默与布洛赫的反馈
直到1937年“堕落的艺术”展开始时,也并不存在区分前卫艺术和现代艺术的相关理论话语,其实也没有区分的必要。偏向形式自律的现代艺术与整体上批判艺术体制的前卫艺术,两者在德国的艰难处境高度相似。它们在多数情况下被统称为现代艺术。但是,在艺术实践领域,现代主义钟情于情感表现与形式探索,而前卫艺术则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两者的差别日趋明显。在面对“堕落的艺术”的指控,两者所占的份额、受到的指控以及引发的反应各不相同。作为前卫艺术的超现实主义、达达艺术和构成主义,已经开始自觉放弃“艺术”和“艺术家”的焦虑,直接投入日常生活、工业生产和政治抵抗。整体而言,在“堕落的艺术”展览中,上述前卫艺术所占比例并不高,即使是那些无意义的拼贴也更多是形式主义的。具有左翼倾向的包豪斯学院,由于很难找到绘画类作品,于是主要展出了档案。展览所能展出的,也只能是康定斯基、克利、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等人的绘画作品。
在充满战争的革命环境中,艺术自然遇到了本体论的危机,一方面是艺术内部的自我批判:这方面的问题集中在艺术还有必要吗?艺术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角色?艺术的现代形式还有无更新的可能?艺术家被允许和不被允许创作什么样的艺术?从当代的视角回顾时,我们会发现,那些追求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创伤情感的艺术家,那些追求形式探索的艺术家,往往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作品本无政治目的,却被赋予了政治属性;自身本无政治倾向,却被划归了政治阵营。而在政治上,那些属于左翼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家,则要理清如何判断“堕落的艺术”。
“堕落的艺术”展对现代艺术“艺术性”的剥夺是全方位,它不仅剥夺了艺术作品的艺术性,也同时剥夺了创作这类作品艺术家的身份,使他们失去了表达自我的权利。面对严苛的艺术的伦理体制,被卷入其中的各类从业者应该如何拯救艺术呢?最开始受到冲击的是那些收藏现代艺术的博物馆馆长,这些馆长也是最早通过各种方式保护现代艺术作品的人,有些馆长甚至被解聘,例如曼海姆美术馆的古斯塔夫·哈特劳勃(Gustav Hartlaub)成为第一位被解雇的馆长。[18]
在这场以伦理标准剥夺艺术之名的清理中,艺术家和理论家显得毫无招架之力。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各自进行了应有的抵抗。“艺术”与“艺术家”的称谓,对某些我们今天称为前卫的艺术家而言,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但是,最难受的那些艺术家,当属于维护形式自律的艺术家。得益于艺术家奥斯卡·施莱默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如何被摧毁,他是如何为自己辩护,而后又是如何郁郁而终。
曾是包豪斯重要一员的施莱默,与克利同一时间成为包豪斯的“形式大师”,其排演的舞台实验《三元芭蕾》、油画和壁画都以人物形象和空间的反装饰、简洁的机械形式著称。可就是这些看似无害的几何形式,早在1930年便以“非艺术”的名义遭到破坏。[19]施莱默坚信自己的作品仅是形式探索,而无任何政治色彩,但这也是他所认为的恐怖之处:“这场文化抵制的可怕之处在于,它针对的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而是纯艺术的智力与美学探索的作品。仅仅因为它们新颖、原创、与众不同,就被视为‘布尔什维克主义’。”[20]显然,施莱默低估了“堕落的艺术”的涵盖范围,非常天真地认为在艺术的伦理体制和再现体制中,还有纯粹形式的位置。他甚至试图用艺术自律的观点来说服“堕落的艺术”展的策划者戈培尔.1933年4月25日,施莱默写信给戈培尔,为艺术的非政治性辩护:
在1910到1914年间,那些重视艺术的国家,像德国、俄国和法国,都在经历艺术观念自发的变革。从这些变革中诞生的艺术作品不可能与俄国共产主义或是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联,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些概念……强加给他们的政治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失当的。艺术家根本上是非政治的,而且必须如此。[21]
用“艺术自律”的说辞来试图拯救那些被定义为非艺术的“堕落的艺术”,显然无济于事。在柏林开幕的“堕落的艺术”展依然没有放过施莱默,他的数件作品被选入展览,紧接着又被选入“揭下面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展。
随着选入“堕落的艺术”展的作品被定义为“非艺术”,艺术家的身份也随之被取消。施莱默丢掉教职,不得不放弃绘画,要想维持艺术创作,他就必须另谋职业。这是所有受到牵连的艺术家的普遍境遇,失去教职,无法出售作品,意味着艺术家作为职业的终结。与部分艺术家试图在德国之外谋求艺术之路不同,施莱默不得不在斯图加特的一个涂料公司工作。恶劣的战争环境,必要的日常工作和理想的自由创作之间的矛盾,最终结束了施莱默的艺术之梦。
“堕落的艺术”展在流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内部也引起激烈讨论,这就是我们前几节所提到的“表现主义论争”,流亡在莫斯科的德国文学杂志《发言》成为这次论争的阵地。正如上文所论,1937年的“堕落的艺术”展中,一战前后兴起的表现主义绘画占据了展厅的大部分内容。当第三帝国将所有表现主义作品都贴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标签,将之定义为“非艺术”时,那些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们又是如何定义这类作品?更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在那个特殊战争时期,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才是合法的?他们秉承的判断标准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们给出的答案也各不相同。最有代表性的一方当然是卢卡奇开出的现实主义“药方”,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示,将现实主义定义为新时期唯一具有革命潜能的艺术形式;另一方自然是恩斯特·布洛赫对表现主义的坚定支持。1937年“堕落的艺术”展开幕后,布洛赫立刻发表《绞刑架下小丑组织的展览会》一文,紧接着又有《当下的表现主义》《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再论表现主义的问题》等文章为表现主义辩护。[22]在《发言》杂志发文支持表现主义的作者,多数都与布洛赫的观点保持一致。
理论家们并不像艺术家施莱默那样天真地为纯粹的艺术形式辩护,尤其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理论家。无论表现主义艺术家有无政治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要拯救岌岌可危的现代艺术,尤其是表现主义,必须论证这类艺术的进步性与革命特征,无论是形式的还是内容的。
如果说“堕落的艺术”展恰是假借“人民”之正义,夺取了现代艺术的“艺术”之名分,那么,布洛赫及其同道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恰是因为表现主义的人民性,才创造了德国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艺术。显然,两者所指之“人民”有着天壤之别,布洛赫所谓的人民,可能正是被第三帝国贴上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人、精神病人等标签的“非人”。第三帝国理想中的德国人民应该有着“伟大的德国艺术展”中的新古典主义气质,健康、美丽和充满活力。那么对布洛赫来说,情况恰恰相反,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德国艺术之家”被他形容为“绞刑架”:“然而,在绞刑架附近的大厅(译者注:‘堕落的艺术’展厅)才悬挂着所有杰作,它们给德国艺术和大师们带来新的荣耀,让他们名副其实。”[23]于是,弗兰茨·马尔克、马克思·贝克曼(Max Beckmann)、奥托·迪克斯、康定斯基等人才是布洛赫认为的伟大艺术家,代表了真正的德国艺术。相比代表贵族趣味的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与民间艺术、原始艺术、边缘群体的亲缘关系,使它具有了真正的人民性:
表现主义没有表现出疏离人民的傲慢,相反,蓝骑士社临摹了姆尔瑙市的五彩玻璃画,它首先打开眼界去注意那种令人伤感的、凄惨的农民艺术,去注意孩子们和囚犯的绘画,去注意精神病患者的震动人心的文献,去注意简陋的艺术……表现主义表现出对“野蛮艺术”巨大的兴趣,但这是基于以人为目的的,它的一切几乎完全是以人以及人的另外说法的表达形式为中心的。[24]
这段话已经把布洛赫认为的表现主义的人民性陈述得十分明确,人民的艺术,也即真正的表现主义是以人道主义为标志,是能够将德国的民间艺术现代化的艺术形式。所以,这里的“人民”具有明显的左翼特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布洛赫很自然地从论述表现主义的人民性过渡到了“人道主义”,从而引出他那句著名的判断:“人道主义是区分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分水岭。”[25]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表现主义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特征,最终经由布洛赫的“尚未意识”体现为对资产阶级趣味的批判。表现主义把“不再意识(no-longer-conscious)整合入尚未意识(not-yet-conscious),久远的过去整合入确定的未来,幽闭的古代整合入敞露的乌托邦之中”[26]。关于“尚未意识”,国内学者陈岸英曾做过论述,认为它与乌托邦意识、期盼意识和希望同义,共同指向人生背后最强的动力。[27]可见,“尚未意识”指向未来和解放,与之相对的“不再意识”则如同夜晚做梦时的无意识,沉迷过去,受到压抑。在论述表现主义的上下文中,布洛赫试图将两者辩证地结合起来,指出表现主义既立足古代又孕育未来。与此对立的,当然是第三帝国试图复活的新古典主义趣味,它不过是那个“不再意识”,只有过去和压抑。落实到现实世界,表现主义因着“尚未意识”,其革命性体现为一种内在批判,它“在资产阶级内部反叛资产阶级,在神话内部战胜神话,敢于从压抑的黑夜提炼光明”[28]。在1937年到1938年那场“表现主义论争”中,支持表现主义超越了资产阶级而非导向法西斯的理论家们大多都赞同布洛赫的论点。例如,赫尔瓦特·瓦尔登(Herwarth Walden)大量引用布洛赫对表现主义的判断,批评庸俗的表现主义,支持真正的表现主义。他认为真正的表现主义者“大多数都是革命者。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不为统治阶级所承认,反而受到严厉的批判”[29]。这类艺术家学习“野蛮人”,不过是表现主义人民性的体现,因为在瓦尔登看来,只有这些“野蛮人”才是未受第三帝国影响的大众。再如署名为彼得·菲歇尔(Peter Fisher)的作者,则认为表现主义的非理性是对资产阶级审美观的批判,反对资产阶级强调的安宁与秩序,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第三帝国为什么反对表现主义。分析至此,我们发现表现主义艺术似乎成为一个白板,可以任意涂抹,多幅面孔可以随时转换。
小结
无论布洛赫及其拥护者如何贬低新古典主义的当代价值,如何强调表现主义在形式上与民间传统艺术的关系,他们的最终落脚点依然在艺术外部的道德和政治。也就是说,表现主义的支持者到头来还是采取了与反对者相同的审美策略,即图像的伦理体制。两者的差异仅体现在道德与政治标准方面,即纳粹的种族主义、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也恰是图像的伦理体制本身的二律背反,它可以让同一个对象既成为让人绝望的魔鬼,又成为让人燃起希望的天使。
1937年“堕落的艺术”展中的那些作品,对第三帝国来说确实是让人绝望的魔鬼,而对部分流亡在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则是充满希望的天使。当然,夹在天使与魔鬼之间的,则是任人摆布的艺术本身。那些被判断为“堕落”的艺术作品,不是被当作垃圾烧毁,就是被当作换取金钱的工具,在拍卖市场以英镑交易,然后收入第三帝国的国库。在艺术的伦理体制之内,真正进退两难的是施莱默这类为艺术本身辩护的艺术家,他们断然拒绝自己是魔鬼,也不希望自己是天使,他们探索着视觉表现的新语法,却被剥夺了艺术家之名。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因为集各类话语冲突于一身,所以成为今天我们讨论现代艺术早期各类艺术思潮发展状况的理想环境。“堕落的艺术”展又是这一理想环境中的典型事件,它将艺术界的话语冲突推向高潮。在今天看来,无论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和拼贴画是魔鬼还是天使,都无法改变自身求新求异的批判特性。只要图像的伦理体制试图为某种同一性的秩序服务,艺术永远不可能作为艺术自身而存在,这一规律放在今天的当代艺术体制内部,依然有效。
注释:
[1]至今研究该展览较全面的一本英文著作是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其中作者Christoph Zuschlag的文章就引用到了布赫洛的文字,详见该书第83页。布赫洛的文章详见:Jugglers’ Fair beneath the Gallows(1937)[A]. Heritage of Our Time[M]. trans.,Nevill and Stephen Plaice. Oxford:Polity Press, 1991, pp.75-80.
[2]本文有关该展览的数据和现场资料主要来源于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Entartete Kunst, Munich 1937: A Reconstruction[A].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3]展览历史文献源自 Christoph Zuschlag. An “Educational Exhibition”[A].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99.
[4]Christoph Zuschlag.An “Educational Exhibition”[A].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p100-101.
[5]Peter Guenther. Three Days in Munich, July 1937[A]. 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36.
[6]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Entartete Kunst, Munich 1937: A Reconstruction[A]. 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57.
[7]Mario-Andreas von Lüttichau. Entartete Kunst, Munich 1937: A Reconstruction[A]. 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47.
[8]Peter Guenther. Three Days in Munich, July 1937[A]. 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36.
[9]加上朗西埃的艺术体制论,现在主要存在三种艺术体制论,第一种是彼得·比格尔的艺术体制论,其体制指每个历史阶段艺术的生产、接受和功能因素,更偏向于艺术面临的社会实体结构,如美术馆、画室、皇室赞助、沙龙等;第二种是乔治·迪基的分析哲学路径,更加偏向于指对艺术约定成俗的看法,因此又被翻译为惯例。前两者英文用词都是“institution”。第三种是正文中所论的朗西埃的艺术体制论。关于朗西埃本人的论述详见: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ranslated by Gabriel Rockhill,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4. .
[10][法]雅克·朗西埃. 美学异托邦[A]. 蒋洪生译. 汪民安、郭晓彦.生产[C].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200页.
[11][法] 让-菲利普·德兰蒂. 朗西埃:关键概念[M]. 李三达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 第154-155页.
[12]被第三帝国指责为“堕落的艺术”的部分作品被销毁,部分作品被拍卖,还有部分作品因各种原因得以幸存下来。关于这些作品的下落,可参见:Andreas Huneke. On the Trail of Missing Masterpieces:Modern Art from German Galleries[A]. 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p.121-134.
[13]同上, 第386页。Andreas Huneke. On the Trail of Missing Masterpieces:Modern Art from German Galleries[A]. 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386.
[14]同上, 第378页.
[15]同上, 第366-368页.
[16]同上, 第366页.
[17]同上, 第381页.
[18]学者Annegret Janda以柏林国家美术馆为个案,研究了历任馆长在第三帝国期间如何试图保护现代艺术,详见:The Fight for Modern Art:The Berlin Nationalgalerie after 1933[A]. Stephanie Barron.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C].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Inc., 1991, pp.105-117.
[19]按照施莱默的书信记录,他为魏玛包豪斯的作坊大楼创作过一批壁画,但在1930年,作为第三帝国建筑师的保罗·舒尔茨-瑙姆堡(Paul Schultze- Naumburg)及其同僚摧毁了这批壁画作品,认为它们是“缺乏艺术价值的习作”。参见:[德]奥斯卡·施莱默, 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M]. 选编:图特·施莱默, 周诗岩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357页.
[20][德]奥斯卡·施莱默, 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M]. 选编:图特·施莱默, 周诗岩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358页.
[21][德]奥斯卡·施莱默, 奥斯卡·施莱默的书信与日记[M]. 选编:图特·施莱默, 周诗岩译.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年, 第392页.
[22]布洛赫与“堕落的艺术”展相关文章,收录在他的文集 Heritage of Our Times[M]. translated by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23]Ernst Bloch. Jugglers’ Fair Beneath the Gallows (1937)[A]. Heritage of Our Times[M]. translated by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77.
[24]张黎.表现主义论争[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第147页.
[25]Ernst Bloch. Expressionism, Seen Now (1937)[A]. Heritage of Our Times[M]. translated by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240.
[26]Ernst Bloch.Expressionism, Seen Now (1937)[A]. Heritage of Our Times[M]. translated by Neville and Stephen Pla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p.238.
[27]陈岸瑛. 恩斯特·布洛赫对梦想的分析及其他[J]. 浙江学刊, 2004年,第6期.
[28]张黎.表现主义论争[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第238页.
[29]赫尔瓦特·瓦尔登(Herwarth Walden)是一位流亡苏联的德国作家和艺术史家,他参与“表现主义论争”的文章《庸俗表现主义》发表于《发言》杂志1938年第2期,载张黎.表现主义论争[C].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第47页.

作者简介:王志亮,博士,副教授。先后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建筑与艺术史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兴趣集中在前卫美学,当代艺术史、艺术批评方法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美术史。出版著作《话语与运动——20世纪80年代美术史的两个关键词》(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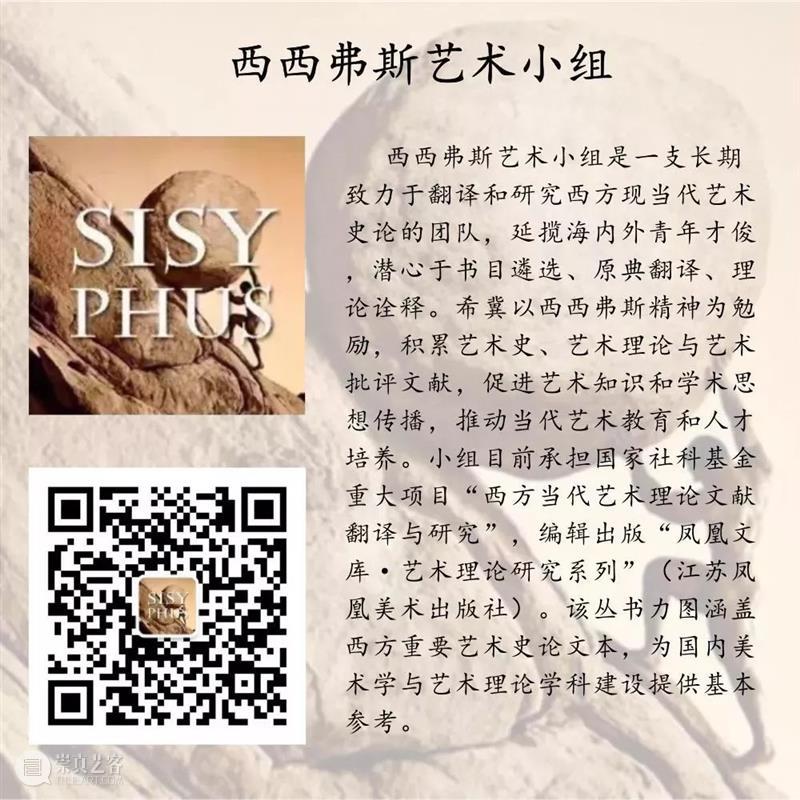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