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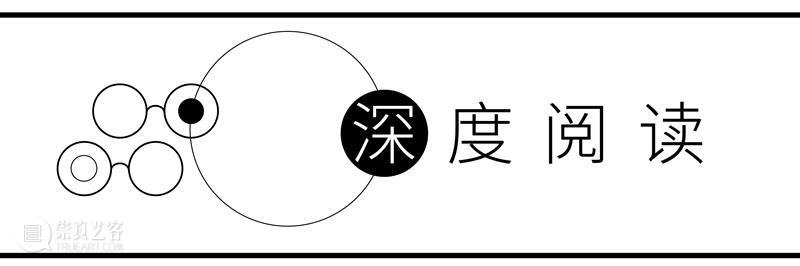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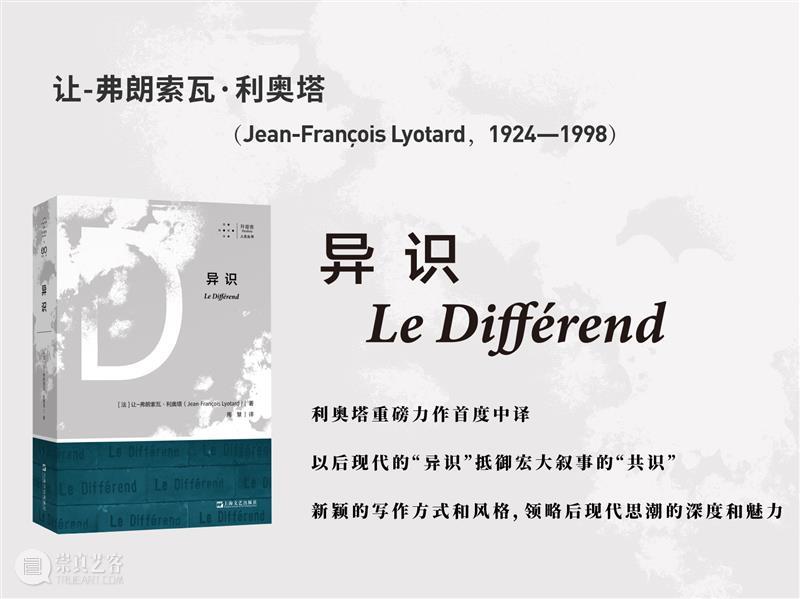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异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书摘(节选自《译者导言》)。此文较长,一万余字,但十分值得收藏,本书译者周慧在这部分导言中对《异识》一书给出了非常好的导读,请搭配本书阅读(此外,周慧还在导言中梳理了利奥塔的思想发展历程,并扼要介绍了《异识》这本书的特色,见我们之前的推送:尊重“异识”的社会才是公正的社会)。此书现已在我们微店开启预售,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预订。
《异识》一书的主要概念及核心观点
作为该书的书名(Le Différend),“diérend”一词无疑是全书最为重要的核心概念,也是开启利奥塔本书乃至他此阶段思想的一把钥匙。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该词进行一些辨析。
1.“diérend”的第一义:语位体系之间的不可通约
在法语中,“diérend”通常被理解为“con‑ictd’opinion”,大意是“冲突”“不和”“分歧”或“争端”。利奥塔的“diérend”无疑有这些意思,但又不完全等同于上述词义。《异识》的英译者及评论者毫无例外地直接引用了这一词,回避了翻译的障碍。作为中文语境下的读者,我们却无法回避这一难题。译成“异识”,原因有二:一是可以表达该词的本义,即“意见不合,见解不同”,二则有意与哈贝马斯的“共识”相对,暗示知识分子为走出现代性危机而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
当利奥塔谈“diérend”时,实际上有两层含义。“diérend”的第一层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为语言游戏之间的不可通约。
利奥塔在《异识》的开篇,就给出了该词的含义。“异识不同于诉讼,它是在(至少)两者之间的某种冲突状态,由于不存在对论辩双方都适用的判断标准,这导致了该冲突无法得到公正的解决。一方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不合法。对两者采用单一的判断标准,试图以此消除异识——仿佛这只是一场诉讼官司,将会(至少)伤害到他们中的一方(如果双方都不承认这一标准的话,两者可能都会受到伤害)。”(参见“本书说明”对书名的解释)由此,“diérend”的第一层意思,是指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即“在异质的风格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判断标准”,这一点,他在该书中反复强调(参见本书说明,155,178,179,203,231,252等)。
尽管利奥塔不断提醒我们,每种语位体系(régime de phrase)都有不同的规则,不存在一个可以支配所有领域的元叙事。但事实上,每个时代都存在这样的宏大叙事(基督教的爱的叙事、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思辨话语机制、资本主义的经济霸权、无产阶级革命、自由主义原理、科学认知话语……),它们总是试图僭越其他领域,建立起可以支配所有话语体系的系统语法。例如,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主要分析了现代科学知识合法化所依据的两个元叙事,一个是思辨机制,另一个是解放机制。前者是日耳曼式的德国唯心主义传统,涉及真理的指示性陈述,目的在于探讨如何获得关于世界、关于人类自身的客观真理;而后者是18世纪的法国革命传统,涉及正义的规定性陈述,目的在于追问如何获得人类的最终解放和自由。一个涉及真理的指示性陈述,叙事主体在这里表现为认知主体,回答“谁可以决定真理的条件?”而另一个涉及关于正义的规定性陈述,叙事主体表现为实践主体,回答“谁有权为社会做出决定?”在后现代社会中,这两大元叙事的地位受到质疑并最终失去其合法性基础,利奥塔称之为“去合法化”。但是,启蒙叙事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宏大叙事的寿终正寝。尽管人们不再相信普遍真理的神话,也不再寄希望于英雄的正义事业,但是小叙事的繁荣并没有到来。新的元叙事在科学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中产生了,它就是“技术科学”。自此,认知型话语统领一切,成为宏大叙事的新版本,即便是科学知识,也一样要服从少投入、多产出的最佳性能原则。
在《异识》中,除了以上几种机制,利奥塔还尤其警惕以下几种话语霸权模式。在第一章中,他首先批判了科学认知语位的霸权,即实证主义的证实程序。在是否存在大屠杀毒气室这一问题上,倘若我们用一种认知的方式来寻找证据(“真正亲眼看到过毒气室”),那么根本无法证明毒气室的存在,而对于死难的犹太人的伤害就是不可避免的。要么p,要么非p,如果非p(如果你不是受害者),那么p为假(因此证词是假的,Fp);如果你是受害者(p),但既然你还能说话,还活着,你就不属于受害者(non-p),那么你的证词还是假的(Fp)(参见本书8)。用认知游戏规则来解决一切问题,即用诉讼或实指的方式来解决毒气室存在与否的问题,将陷入悖论并导致不公正。因此,“承认‘异识’的存在,就是要建立起新的受话者、说话者、含义和指称,由此让错误得以找到表达的途径,让原告不再沦为受害者”(同上)。犹太人的悲惨历史,集中营的惨无人道,拒绝用认知语位的方式来证实或反驳这一事件。
在利奥塔的哲学思想中,“奥斯维辛”这一事件反复出现,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异识》的始终。某种意义上,“奥斯维辛”是知识分子对理性的限度以及文明为此背负的债务的深刻反思,是当代哲学家用以检验自己理论价值和思想意义的试金石。在西方文明的摇篮里,人文主义的理性传统居然结出了纳粹主义、大屠杀的恶果,这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挥之不去的噩梦和擦抹不掉的创伤。对于20世纪下半叶的思想家来说,只要他仍负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就无法不去面对这一通过理性的管理手段来对数百万人的生命进行有序屠杀的现代性事件。因为这一创伤就处在知识分子与其历史关系的核心地带:令人痛苦的事实不在于大屠杀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恐怖事件,也不在于极端的种族仇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得不遭遇的文明的偶然偏离,而在于大屠杀是现代理性的总体性思维和同一性叙事发展到极致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创造与毁灭,连同光荣与耻辱印刻在“文明”这一枚硬币的两面,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现代文明都包括了死亡集中营里束手待毙的人们,包括了那些被盖世太保送往毒气室的犹太人的亡灵。在某种意义上,“奥斯维辛”不仅是一个大屠杀事件,它也是一个昭示着文明罪行的记号。
因此,在第四章“结果”,利奥塔不遗余力地声讨了黑格尔的思辨机制和由这一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所结出来的思想和现实恶果。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并不害怕死亡,而敢于担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它是一种魔力,可以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死亡并不是绝对的终点,它只是一种对有限存在的否定,而精神会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使得死亡向存在转化,并让有限生命最终升华为无限真理。真理既不在生命的实存之中,也不在死亡的否定之中,而是在两者的合题即绝对精神中,它是理性在超越了有限的生命之后而回归自身的更为丰富的存在。这一更高的存在通常是以“我们”的名义来实现的,当个体是为了民族、集体、同胞、人类或是子孙后代而慷慨赴死时,死亡就拥有了对抗恐惧的力量,它在真理的指引下缓缓升向天国,最终上升为“美丽的死亡”(参见本书153,156,157,160,168)。但是,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彻底摧毁了这一绝对精神的魔力。“在集中营中,死亡有了一种新的恐怖感:自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来,怕死意味着怕是比死更糟糕的事情。”(152,153)之所以害怕,是因为大屠杀这一事件没有任何可以让人超越的理由。几百万生命的消逝,既不是为了正义和救赎,也不是为了人类的解放事业,它停止了向更高存在的转化而成了绝对的终点。当死亡不再是精神由有限向无限转化的契机时,一切关于绝对精神和永恒存在的说辞都只留下讽刺的意义。利奥塔尖锐地指出,在“奥斯维辛”中,纳粹永远占据着规范性话语的说话者一极,而犹太人则永远处于指令性话语(义务)的受话者一极,前者是规则的立法者,后者是义务的承担者,它们之间不可能融合在“我们”这个自律的主体中,根本就不存在从犹太人走向纳粹世界的通道。“奥斯维辛”是绝对异识的体现,它彻底摧毁了“合题”“结果”“自律主体”“绝对精神”的形而上学臆想。
在第五章“义务”里,利奥塔再三强调描述性语位与伦理性语位不可通约,他提醒我们尤其要警惕通过描述性话语来处理伦理、正义问题而导致的伤害。他认为,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存在着混淆两种语言游戏,从认知推导出伦理实践的话语模式。利奥塔将其概括为:Si (si P, alors Q), alors R,其英文表述为If (if P, then Q), then R。“if... then...”是描述性话语的经典模式,它是一种逻辑上的蕴含模式,即后件可以通过证明、推论、演绎从前件之中推演出来。这个公式可以解读为:如果我们获得了“什么是公正”的定义(如果开启理论性话语),那么我们将拥有一个公正的社会(由此可以推导出指令性话语)。正义就是对“正义的本质”的摹仿,这意味着存在正义的标准,可以为我们所认识,并用来指导实践。根据这一观点,“理论”高于“行为”,“知识”高于“意见”,“真理是什么”理应支配着“什么将发生”的问题。由此,“知识引导行动”的理性传统贯穿西方思想史发展的始终,而哲学也被定义为一种行对知的从属关系。通过现在来规划将来,通过已知来推测未知,知识带来了确定性,克服了盲目性,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安全、稳定、可预见。然而迷恋确定性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行为不再听从道德诫命的无条件召唤,义务不再是个体面对道德法则时油然而生的敬畏感,伦理实践已经成为权衡利弊、计较得失、规避风险的场所,一切存在者及其行为都被带入理性的计算公式和市场的价值游戏。利奥塔认同亚里士多德、康德和列维纳斯的观点,认为无法从知识推导出行为的准则,正义不是服从的问题,道德命令不可以被推演出来;恰恰相反,过分细化的义务往往造成不公正的结果,而那些最服从的人往往是最不公正的人。
在最后一章“历史的征兆”中,利奥塔尤其担心经济话语风格的无孔不入和无往不胜(参见本书240-260)。在资本主义话语体系下,一切皆可用于交换,只要对象所包含的时间是可计算的。知识失去了救世主的这层光环,化简为可操作的信息量,它不仅进入了资本流通环节,而且成了首要生产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的权力竞争中成为最抢手的稀缺资源;劳动力成了商品,成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前提条件,而生命、灵魂、婚姻、情感,这些标示着人的尊严和存在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市场中明码标价;道德伦理不断受到资本逻辑的侵蚀,即便是最富于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文学艺术,也不得不向资本低头,沦为营利和谋生的手段。生命、宗教、价值、艺术,所有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表象的东西,如今都成为考察、研究、计算的对象,无时不刻受到市场规范的威胁和利益最大化的诱惑。“经济话语以及它从一个语位到另一个语位的必然链接模式,排除了发生、事件、奇迹,以及对情感共同体的期待。”(252)
利奥塔坚持认为在关涉认知、伦理和审美判断的陈述之间没有共同本质,认为没有普遍的元规则可以统领各种语言游戏,这一立场显然与康德的批判精神一脉相承。对康德而言,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是道德的政治家(参见本书评注:康德4,§2),即承认自由以及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的存在,并试图将道德和政治结合起来的人。[1]一个道德的政治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念的维度,就会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理念被康德称为“指导线索”(参见本书评注:康德3,§3;康德4,§2)。利奥塔认同康德,道德命令和理性共同体,都只是一个理念,不可以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它只是一个标示着进步的“历史的征兆”(第七章)。当我们僭越了理念的超验性,将超越于一切经验范畴之外的理念运用到现实世界,即将理念实体化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所谓的“先验幻相”(康德1,康德3,§2,康德4,§1,康德4,§5)。在他看来,不管是黑格尔、马克思、新康德主义,还是分析哲学、哈贝马斯都试图寻找证明这一总体性的途径,好像它可以在认知上被证实,在现实中得以实现,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一先验幻相之中。
[1]康德在《普遍历史的理念》中区分了两种人类社会的状况,一种是现实的,一种理想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常态并不是一种和平状态,而是一种战争状态。人的卑劣使得战争与冲突此起彼伏,以至于康德想起人类在世界大舞台上的表现,就无法抑制他的厌恶之情:尽管在个人身上可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就全体而言,一切都是由愚蠢、虚荣甚至是幼稚的怨恨、毁灭交织而成的。但如果光是承认这样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并且满足于一种实用主义的政治学或是智者式的审慎的政治学,那么他就只是一个政治的道德家(un moraliste politique),因为他的目的就只在于选择对于既定目标最为有利的权宜手段。道德的考虑在这一实践政治中毫无空间。对康德而言,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是道德的政治家(un politique moral)。参见本书评注:康德4,§2。
利奥塔的理念虽然从康德而来,却又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不同于后者。在康德那里,理念是“有关一个给予的有条件者的诸条件的总体性的概念”,因此它的任务就是使单称判断中的综合统一性尽可能地统一于无条件的东西之下。总体性在道德的领域表现为理性存在的整体,在政治学的领域表现为人类的共同体,一个通往永久和平的整体。在这一点上,利奥塔并不认同康德,因为他的理念不再是一个总体性的理念,而是一个多样性的理念;换言之,是一个异质、差异的理念,而不是总体、同一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再是替民众提供普适价值和凌驾于一切话语之上的元规则,而是应当把小叙事的游戏尽可能地最大化。而“语言”的流行模式,应该是去仪式化后的小叙事(参见本书230)。后现代思想家的任务就在于打破认知模式和资本市场的垄断,关注那些无法用科学技术和思辨话语表象出来的细微差异,恢复思想的尊严,还原人类有血有肉的感性和特殊存在。
2.“diérend”的第二义:语用事件的“独特性”
“diérend”的第一层含义我们并不陌生,它基本上是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现代版本。只不过,在《异识》中,利奥塔用“语位体系”(régimes de phrases)代替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用一个“多样性”的理念替代了康德的通往人类永久和平的“总体性”理念。真正富于创见,也引发众多争议的是“diérend”的第二层含义。
“diérend”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语用事件(phrase)的独特性,或者说语用事件之间的不可通约。“phrase”是《异识》的关键词,但是它的翻译却颇成问题。在法语中,它有“句子”,也有“短语”的意思,但是作为语用事件,“phrase”却既可以不是句子,也可以不是短语。英译者阿比勒将其原封不动地照搬过去,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也容易产生误会,因为英语中该词只有“短语”而无“句子”之意。有些评论家将其译为“sentence”,但这样处理也不妥,因为熟悉语言学的人都知道,“句子”是一个语法单位,相应的语用单位是“言说”(utterance),而利奥塔的phrase肯定是一个语用而不是语法单位。那么,是否可将phrase 译作“言语行为”(speech act)呢?也不能,因为phrase不仅包括语言内的句子或短语,也包括非语言现象,如手势、表情、信号、音乐标符等。
王宾在《文化多元论的语用学审视》一文中谈到了这一困境,笔者觉得言之有理,沿用其译。他将“phrase”译为“语位”,理由如下:利奥塔将“语位”看作语用学的基始单位,与“事件”同义。这样一来,“语位”就是一个函项,与语形学的“词位”(lexeme)相区别,又与表示具体行为的语用单位“语步”(move)相联系。不过其动词phraser译作“语位化”颇有些费解,改为“语位链接”或“语位表达”。
语位是一个语用事件,它是一个殊例(token)而不是一个类型(type)(参见本书104)。殊例是无法重复的,每一次重复,都意味着另一个token的发生。在西方思想史传统中,一个个存在着的东西,或者每一个发生的事件只是共相的某种显现,它们往往被认为是从共相中浮现出来的殊例,在哲学上并不具备真理的价值,也不是哲学要考察的对象。只有共相才是事物存在的理由,是世界产生的原因,为保证绝对真理的获得,时间可以忽略不计,或是被概念化。因此,时间,尤其是此刻、当下(maintenant)没有进入哲学的考虑。不仅如此,对于共相和确定性而言,时间中的万事万物瞬息万变,它始终是导致不确定性的罪魁祸首,是力图在普遍中把握特殊的哲学思考必须首先清除的东西。在这种普遍哲学的思维模式下,感觉的贫困化和时间的数字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遭遇。在现代社会中,生活和行动的所有方面都服从于合理化过程,服从于一个最终的原则:争取时间。标举差异的当代法国思潮显然是对这一哲学传统的反动。在这场思潮中,哲学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各种二元对立(同一/差异、必然/偶然、理性/感性、结构/事件、普遍/特殊、共相/时间)的关系:为什么前者始终是比后者优越的东西?在一个由科学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一个生活世界被彻底对象化和概念化的时代,或许后者才是让哲学家仍然可以保持以思想为业的尊严的主题呢?
由此,利奥塔区分了“表象”(presentation)和“处境”(situation)(参见本书“表象”一章),即区分了事件的“直接发生”和通过概念来再现这一“发生”的“间接意义”。“表象”“处境”二分意味着存在着两种时间性,而这两种时间性是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的分析来引入的。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有很多将时间期间化的表述。不过,亚氏在将时间理解为连续之流的同时,也看到了将时间实体化的困难:这个介乎“之前”和“之后”之间的“le maintenant”似乎不是原初意义上的“此刻”(maintenant)。因为后者根本就无法为我们所言及,它不可重复,不可指涉,试图与“此刻”同一的设想似乎是荒诞不经的,因为它根本不作为“实体”而存在。为此,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性:一种是“maintenant”,“当前-事件”(l’événement-présentation),它是不可重复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我们若把“此刻”放入既定的情景或关系中,加一个定冠词,就变成另一种,“le maintenant”,独一无二的本体论事件就被实体化了,绝对因此转化为相对,被赋予了确切的意义(参见本书评注:亚里士多德)。利奥塔受亚氏的启发,用“表象”和“处境”来表示这一对立。在他的诸多作品中,这一区分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用拉丁文“quid”和“quod”(参见本书131,132)来表示,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用“il arrive”和“ce qui arrive”(104,131,132,184,190),英文里,前者相当于“what it happens”,而后者对应于“what happens”。这一区分不仅是语位语用学的关键,也成为他论述先锋艺术的崇高美学的基石。
每一个语位在“发生”时都由四个要素构成,即言者、听者、含义和指称。[2]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语位事件在“发生”时,它们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此刻我们并不能确知发生了什么,但我们知道“此刻”肯定“有”某事“发生”了。这个“有”,并非具有确定内容和权威的大写的“存在”(l’Etre),而是一个朝着多种可能性开放的、小写的“存在”(un être)(参见本书113)。换言之,这个“有”,并非作为实体而存在的“存在者”,不是一个个在具体时空中的经验事例或事物,而是尚未有任何具体内容之前的、无法为我们的意识所识别的混沌世界“il y a”(190,193)。
[2]这四个要素法文为“instance”,英译者直接照搬,造成了诸多误解。不少中国学者引用英文,将这四个要素理解为“事例”,却不知英文的“instance”有“事例”之意,而法文的“instance”却没有这个意项(该词在法语中,多指“决策机关”“要求”“权威”“诉讼”等意思)。在逻辑学中,“instance”可以表示(在固定公式中可随意替换的)“项”“代入项”,在此书中,译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此词翻译为“语位项”,少数情况下译为“权威”,如220,或是译为“要求”,如评注:卡西纳瓦,§5。
第二,语位在被表象出来的瞬间,其言者、听者、含义、所指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接下来的语位可以把它们放到具体的情景和关系之中,即“处境”之中,由此确定它们的内容、意义、性质或是价值。后边的语位虽然可以解释并评价前一个语言,但它并不能抓住先前语位的全部含义,“它只是把表象限制在更为具体的处境之中,并且消除了在最初语位的表象中所产生出来的众多可能性。”换言之,把“表象”限制在具体的“处境”之中,就是将最初语位所暗含的众多可能性转变为一种现实性。由此,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对语用事件的原初理解,因为对语位的任何理解都只能是此事件之表象的某种可能处境,而“处境”不能还原为“表象”。在已经实现的链接和可能的链接之间,存在着le diérend,存在着不可解决的冲突;在未实现的多种可能的链接方式之间,也存在着le diérend,即不可通约性。
由此,利奥塔改写了传统哲学对实在、意义、主体、历史的一贯理解。例如,利奥塔既反对实证主义的实在观,又反对现象学的实在观;前者将实在看作一个外在于语言的客观存在,后者将实在看作意识的主观建构。对后现代思想家而言,实在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规定的,不是一个已经存在只需指认的客体,而是在语用实践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过程。在语用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实在”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它的含义需要后面链接的语位来确定。因此,利奥塔断言:社会的性质总是被不断推延的(195)。从诠释学的角度来讲,“表象/处境”二分意味着对语用事件的意义诠释是由下一个语用事件来完成的,其有效性不是由它自身决定,也不是由说话的主体或先在的共时系统所决定,而是由后边的“迟到者”来赋予的。如此,既不存在本原的意义,也不存在对意义的唯一正确的再现;意义的阐释不再是唯一的,每一次阐释都是诠释者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加入自己的特定理解将其再语境化的过程。
3.语位链接规则和后现代美学
语位链接的规则是:“链接是必然的,如何链接则不必然。”(40,102,136;评注:康德2,§6)链接是必然的,是指任何言语行为,甚至包括以非语言方式来完成的语用行为,都是一个语用事件。即使我说“没有语句发生”,此否定本身就是一个语位;即使保持沉默,拒绝做出任何链接,这一拒绝也是一个语位。眨眼、耸肩、跺脚、脸红都可以是语位(110),链接的必然性逃脱了主体的意志。虽然链接是必然的,但如何链接却不必然。这意味着我们有创造的自由。如果我们不想让自己的链接完全被市场逻辑和确定性思维所钳制,那么最好的方式便是突破既定的规则,打破体制下的共识,创造新的链接,感受在“此刻”这一瞬间“事件”所绽放出来的无限可能。
语位链接除了见证不同语言风格之间的“不可通约”,还要创造新的链接方式。因此,在这本书的开篇,利奥塔就声明,“这本书的模式是哲学的,不是理论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要义在于发现规则而不是将自己的知识预设为原则”(参见本书说明)。他反复强调,“文学、哲学或者政治学的关键,就是在创造语位的过程中,见证这一异识”(22)。“哲学话语将发现规则视为自己的规则:这一规则的先在性是哲学的关键”(98),对于哲学家而言,思想的责任在于发现异识,寻找新的链接方式(参见本书评注:黑格尔;180,202,228)。因此,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艺术家;哲学和艺术在任何时代都肩负着双重的职能,一层是否定的批判职能,一层是肯定的创造职能。语位链接的第二个任务对于利奥塔的语用学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姿态,思想家就会陷入令人沮丧的虚无主义:体制的力量过于庞大,对此,我们无能为力。在这里,利奥塔从康德的第三批判那里获得了灵感:没有预先的判断规则,由此我们所使用的就是“反思判断”,从特殊出发来寻找普遍。“后现代”就是这样一种寓于现在却对现在构成威胁、指向未来而为未来书写规则的批判和创新精神。
利奥塔虽然借鉴了康德的思想,但是他对“事件”独特性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康德对想象力的强调。在第三批判中,康德特别强调天才的独创性与鉴赏力的评判之间的和谐一致,后者甚至比前者对于美的分析而言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审美共同体的一致认可,天才的作品即便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有灵光闪现,也只是毫无意义的胡闹,转瞬即逝,注定要被历史淘汰掉;只有当想象力和鉴赏判断达成共识,天才的作品才可能成为典范,为艺术颁布规则。所以,康德始终认为,想象力固然重要,但是美的艺术,一定是想象力和知性、天才和鉴赏力和谐作用的结果。必要的时候,康德宁可牺牲天才的洞见,而把合法性的决断权给予普遍化的要求。如果说康德的反思判断强调的是从特殊到普遍的先天能力,以及想象力的独创与知性共识的平衡,那么利奥塔的“判断”侧重的则是“事件的发生”,他要捍卫“事件”在“发生”时的各种可能性和特殊性。对他而言,处在边缘却坚持批判和创新的精神,远比普遍化的结果更可贵,因为任何先锋理念一旦被纳入体制,被共同体所接受,成为现实规则的受益者和制定者,那么它的创造力就枯竭了,它通往自由的大门也封闭了,它甚至可能摇身一变,从捍卫理想的革命者变成捍卫自身利益的独裁者。这也是为什么利奥塔如此看重康德关于崇高的论述,因为崇高不同于美的分析,前者是富于创造性的想象力和已达成共识的知性之间的极端冲突,而后者是各种认识能力的协调一致。正是由于对语位事件及其独创性的青睐,利奥塔的“后现代”不是一个居于现代之后的时代概念,而是一种不断推陈出新的实验精神,它通向的是表象不可表象的崇高美学。“后现代”不在达成共识、获得合法性的终点,它永远处于冒犯读者,与共识相背离的起点。它是一种生产和创新的能力,而不是消费和评判的能力。
另外,和康德不同的是,利奥塔并不将美学看作沟通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而是试图将康德的反思判断扩展到所有领域。例如在《论公正》里,利奥塔认为,他试图发展的判断力是某种类似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和康德第三批判中的想象力的东西;而在第三天的谈话中,他更是宣称,公正游戏导向的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即某种语言游戏的实验事业。伦理实践没有判断的先在标准,我们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中逐例判断。在《后现代状况》里,利奥塔将“悖谬推理”(la paralogie)看作科学合法化的模式。“悖谬推理”指“与既定的话语规则相悖,与现行的道理、逻辑相悖”,即任何认识论革命总是从发现反例和悖论开始的。虽然利奥塔承认,在信息化时代,知识越来越与个体的思辨、精神的愉悦脱离了关系,成为某种技术化的、功能性的需要,科学研究也已经成为富人的游戏。但是,在精英们进行独创时,最佳性能和效率的逻辑并不是决定科学发明的核心要素。当资本和社会共同体对发明产生浓厚兴趣,承认它们的价值,并由于可以为自己带来可观的利润而对其趋之若鹜时,这一价值判断往往是迟到的。因此,在《异识》中,利奥塔的判断力并不像康德那样,拥有一块独立的美学领域,它是各种话语游戏得以建构起来的边界和通道。利奥塔用群岛来比喻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而判断力则是各个领域孤岛的建立者和管理者,通过它,各个孤岛之间得以互相交往(参见本书评注:康德3)。语用事件的独特性——“反思判断”——充当了连接异质的语言游戏的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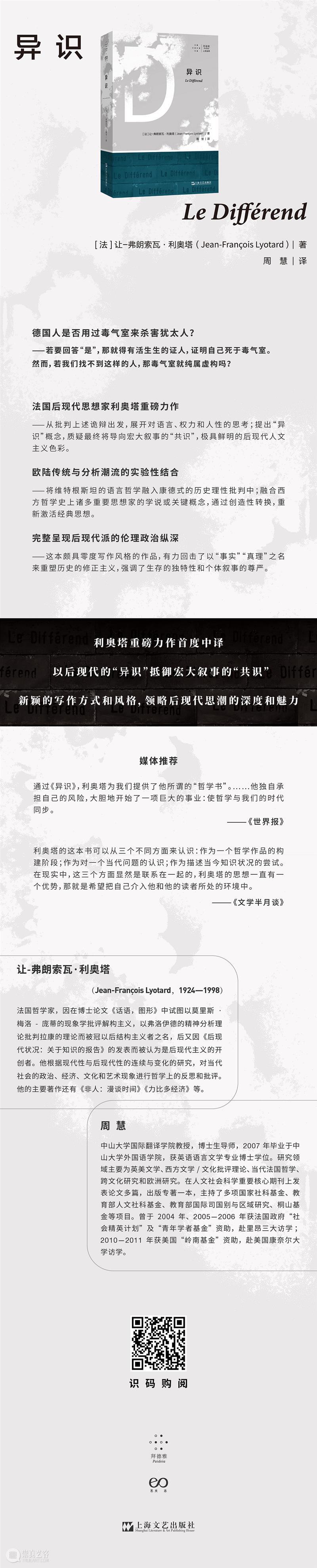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