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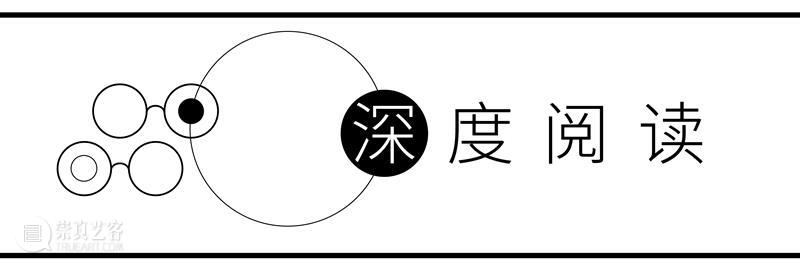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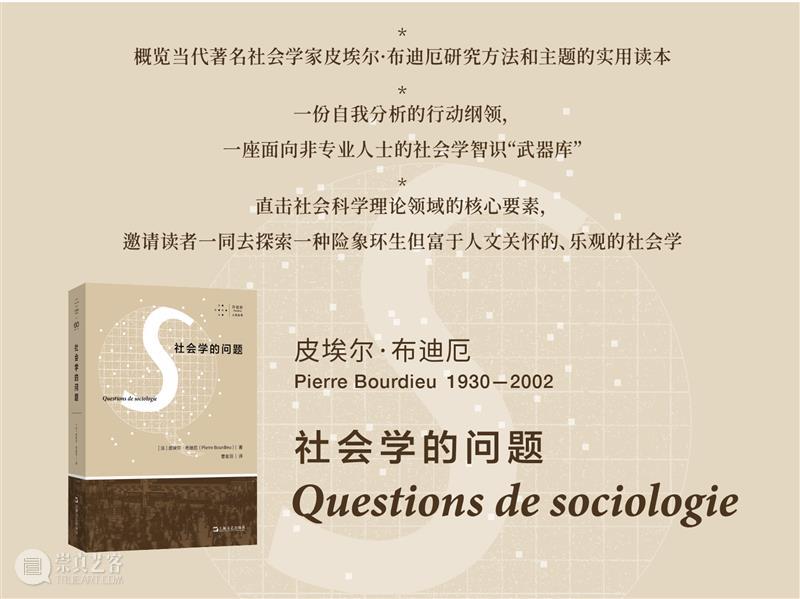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新书《社会学的问题》(皮埃尔·布迪厄)的书摘。此书现已在我们微店开启预售,欢迎大家点击文末“阅读原文”预订。
社会学家的社会学
1975年5月,巴黎,“马格里布的民族学与政治”(Ethnologie et politique au Maghreb)讨论会会议论文,发表于《看的问题》(Le mal de voir, Cahiers Jussieu 2,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 coll. 10/18, Union Générale d’éditions),第416-427页。
我想试着联系特定案例——殖民化和去殖民化国家的社会科学——提出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即可能性的社会条件和一种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科学功能。我所要讲的内容带有即兴性质,这可能意味着一些危险的立场……这是我必须承担的风险。
第一个问题:你决定在此谈论有关社会科学的社会史的问题。那么,这里面有相关利益吗?人们从来没有问过此类问题。如果我们在这里谈论它,那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很有趣。但是,说我们对一个问题感兴趣是一种委婉的方式,它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我们与我们的科学成果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不是直接的经济或政治利益;我们感觉它们无关利益。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有着无关利益的兴趣,他们对无关利益有兴趣。在我们看来有趣的问题,背后有利益牵涉其中。这意味着在某个特定时刻,某个特定的学术团体——在没有任何一个人作决定的情况下——将某个问题定义为有趣的问题。召开会议,创办期刊,写文章、书和评论。这意味着这个主题是“值得”写的,它会带来利润,与其说这种利润是版税(尽管这很重要),不如说它是声望、象征性的满足,等等。所有这些只是一段开场白:在没有首先或同时进行自我社会分析之前(只要这是完全可能的),不应该从事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有什么用?殖民地科学的社会学是为了什么?科学话语的主体需要被问及与该话语之对象相同的问题。研究人员如何以及凭借何等权利向过去的研究人员提出他没有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反之亦然)?
除非人们意识到科学的过去与现今的科学斗争利益攸关,否则不可能对过去的科学博弈的利益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复原的策略往往掩盖了象征性的投机策略:如果你试图诋毁智识对手所处的血统,那么他的学说的价值就会暴跌。人们说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或结构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就意在于此。总之,我们需要问是什么吸引着人们去做社会学的社会学,或其他社会学家的社会学。例如,不难看出,右翼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几乎都是由左翼知识分子完成的,反之亦然。这些对象化所得是偏颇的真理,而这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看清对手的真理、看清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在解释左翼知识分子时,右翼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唯物主义者),能带来利益。除此之外,人们从未理解那产生出这些对抗策略的立场的系统,因为这将迫使分析者自问,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有何利益,等等。
除非假定社会科学的社会史除了给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存在的理由,没有其他功能,也不需要其他理由,否则我们就得问,它对今天的科学实践是否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社会科学是今天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前提吗?更准确地说,研究“殖民地”“科学”的社会科学,是否是一个刚去殖民化的社会中的社会科学真正实现去殖民化的前提条件之一?我很想承认,社会科学的过去总是社会科学的主要障碍之一,对我们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涂尔干在《教育思想的演进》(L’Évolution pédagogique en France)中所说的那样,无意识就是对历史的遗忘。我认为,一门学科的无意识就是它的历史,它的无意识是由其社会生产条件构成的,是被掩盖和遗忘的。产品一旦脱离了它的社会生产条件,其意义就改变了,该产品就会施加意识形态的作用。一个人在做科学研究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一个认识论的简单定义,其前提是他知道自己用到的问题、工具、方法和概念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有鉴于此,没有什么比为马克思主义传统撰写一部社会史更为迫切的事情了,这件事的目的是在它们的产生和相继使用的历史背景下,重新调整因忘记历史而固化的、为人所盲目崇拜的思维或表达方式。)
从那个我眼中唯一有意义的出发点——当今阿尔及利亚社会的科学进步——看来,“殖民地”“科学”的社会史将有助于了解我们看待这个社会的思想范畴。今天上午发表的论文已经表明,在某种意义上,殖民者被自身的统治所支配,是其智识工具的第一个受害者;这些工具也仍然可以“困住”那些仅对它们作出“反应”,而不了解其运作的社会条件的人,因为这些人很容易陷入相反的错误,而且无论如何都会剥夺自身关于某些对象的唯一信息。所以,为了理解那些留给我们的事物——语料库、数据、理论——我们必须对该对象的社会生产条件进行社会学研究。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不首先研究一个相对自主的科学场域的出现和该场域自主化的社会条件,就不能对“殖民地”“科学”的社会生产条件进行社会学研究。一个场域便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生产者的特征由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即他们在某一特定的客观关系空间中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与孤立的个人研究的预设相反,例如,在“作者及其作品”类型的文学史中,每个生产者最重要的特性存于他和他人的客观关系中,也就是说,存于自身之外,存于客观竞争的关系中,等等。
我们首先需要确定,在场域中马斯克雷(Masqueray)、德帕尔梅(Desparmet)或莫尼耶(Maunier)等人的“殖民地”“科学”生产出了殖民话语的场域,这一场域的具体属性是什么,以及这些属性在不同时期是如何变化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分析这个相对自治的科学领域与殖民国家、中央智识权力(也就是当时的宗主国科学)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着双重依赖性,而且它们会互相抵消。在我看来,这个相对自主的场域的普遍特点是(除了杜特[Doutté]、莫尼耶等人所讲的)高度依赖于殖民国家,但高度独立于国家(和国际)的科学场域。其“科学”生产的一整套特性由此而生。那么,我们就必须分析这个场域与国家、国际科学以及当地政治场域之间的关系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如何在生产中被转化。
场域的重要属性之一在于它隐含地定义了“不可想象”的东西——那些甚至未经讨论的东西。有正统和异端,但也有信念(doxa),即一切不言而喻的东西,特别是那个决定有趣/无趣的分类系统,那些因没有需求而无人认为值得一提的东西。今天上午我们谈到了这些不证自明的东西,夏尔-安德烈·朱利安(Charles-André Julien)描述了一些令我们十分震惊的知识背景。最隐蔽的事情是大家一致同意——同意到连提都不提——的事情,无可置疑、无需赘言的事情。这正是历史文献极有可能掩盖得最彻底的事情,因为谁也不会想到要把不证自明的事情写出来;而这也是线人沉默着闭口不言或省略不说的事情。当某人想做社会科学的社会史的时候,他如果想做的不仅仅是分配赞扬和责备,就必须去思考这些无人提及的事情。问题不在于把自己设定为法官,而在于:去了解这些人为何不能理解某些事情,无法提出某些问题;去确定(必然的)错误的社会条件,因为错误是历史条件、决定的产物。在特定时期的“不言而喻”中,有法律上不可想象的、不可名状事情(例如政治上不可想象的事情),有禁忌,有不能处理的问题,也有事实上不可想象的事情,有当时的智识工具不可能想到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错误不是按好意或恶意来分配的,也是为什么好意可以做出坏社会学。)
这样一来,人们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与研究对象——本地的或外地的、“同情的”或敌对的研究对象,等等——的特权关系问题,人们对殖民社会学的讨论和去殖民化社会学的可能性就被困于这种特权关系中。我认为,从一个享有特权的角度出发提出的问题需要被取代,代之以对与科学对象之关系的科学控制(在我看来,这是构建真正的科学对象的基本条件之一)。无论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选择什么样的对象,这个对象——他构建对象的方式——并不会提出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作为个体主体的问题,而是会提出社会学家的相关社会特征和研究对象的社会特征之间的客观关系问题。社会科学的对象和研究者对待它们的方式总是保有一种与研究者的可理解的关系,因为研究者是在社会学层面上被定义的,即由某一特定社会出身、大学系统内的某一特定位置、某一特定学科等指标所定义。例如,我认为,在科学的框架内,主流价值观的支配是通过一个中介来实现的,该中介就是学科的社会等级制度,它把哲学理论放在顶端,而把地理学放在底层(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经验观察,学生的社会出身随着从哲学到地理学,或者从数学到地质学而下降)。每时每刻,都存在研究对象的等级制度和研究主体(研究者)的等级制度,它们对研究对象在研究主体中的分配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来没有人说(或仅有少数人说):“考虑到你的身份,你应该学这一科,而不是那一科,应该用这种方法——‘理论的’或‘经验的’、‘基础的’或‘应用的’,而不是那种方法,应该用这种方式——‘聪明的’或‘严肃的’,而不是那种方式来呈现结果。”这样的提醒,在大多数时候相当多余,因为人们只需放手让内心的审查自由发挥,这种审查只是社会和学术审查(“我不是理论家”,“我不会写作”)的内化。所以,没有什么比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更缺少社会中立性了。
重要的是,要具备把自己与客体的关系客观化的能力,这样一来,关于客体的话语就不会是某种与客体的无意识关系的简单投射。当然,一切科学装备都是使这种客观化成为可能的技术;只要人们明白,这些装备本身必须受到历史的批判,因为它们每时每刻都继承了先前的科学。
最后,我想说的是,外人或本地人的特权问题无疑掩盖了一个非常真实的问题——无论是在分析卡拜尔仪式的时候,还是在分析这个房间里、学生示威中,或汽车厂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会出现:作为观察者或能动者意味着什么,一言以蔽之,实践是什么。
进阶阅读
皮埃尔·布迪厄,《科学场域》,载《社会科学研究学报》(Le Champ scientifique,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2-3, juin 1976, pp.88-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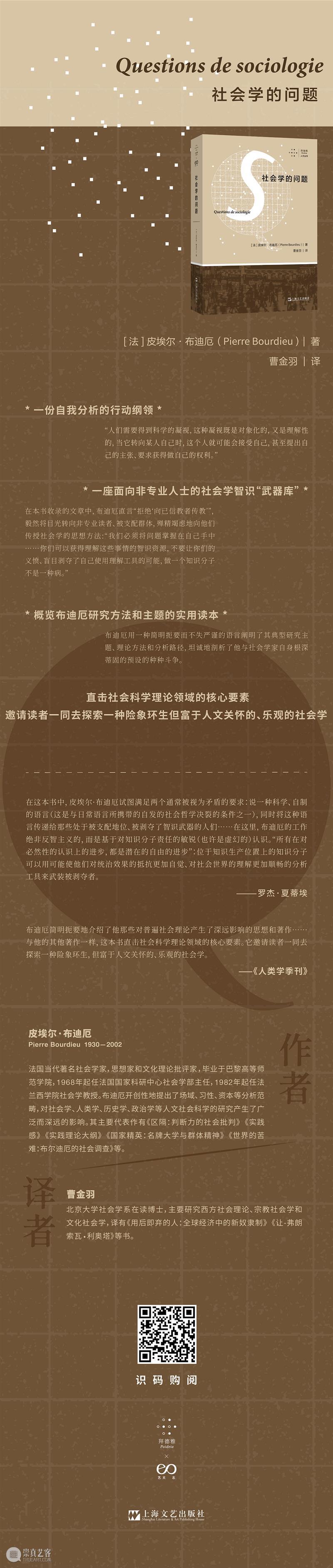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