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M公教 | Humans in the Museum公共艺术项目Vol.15:为了在席卡上写好梁文道三个字我练了好几遍
![]()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newsData.publisher_name}}
{{newsData.update_time}}
浏览:{{newsData.view_count}}
来源 | {{newsData.source}} 作者 | {{newsData.author}}

Humans in the Museum公共艺术项目以美术馆的空间为核心,用现场采访和多元的衍生活动等方式,和公众建立深度的联接,收集、记录美术馆里的“人”与他们的故事,呈现出美术馆独有的艺术生态。美术馆开馆是17年11月18号,我是17年9月26号入职的,是开馆最后的准备期。到岗那天我们安保部刚成立,一切都是新的,蛮锻炼人的,我那时候都轻了好几斤。我们现在的一套体系和流程很成熟完善,都是当时一步一步打下的基础,根据经验教训,不行的地方就改掉,好的地方保留下来。安保更多的是责任心,道理很简单,把美术馆当家,基本上这个工作就能做好了。实事求是讲,我现在对艺术方面是有一点进步的。田学森老师的“华山十年”我就很喜欢,他给我的感觉是淡泊功名的,专注在创作上,毕竟能在山上待十年,相对来说就不是追求物质的人。他跟我们安保也会聊一些他的作品,完全没有架子,我们也愿意请教他一些问题。给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汛期的时候,有天雨很大,草坪那边坑里积水很深,除水机又坏掉了,工程、保洁、安保都是冒着雨拿桶在外面紧急排水,大家衣服都湿光了。雨是一直在下的,大概两个小时没有停过。当时已经下班了,办公室几个加班的同事都赶了过来,有人连鞋子都来不及脱,穿着皮鞋就进去,水里泡了一个多小时,鞋子也废了,但是也没讲什么。发生的时间是8点过后了,我们安保早班和夜班已经交接完,但没有人提出回去,大家都在努力。这件事情我记了很久,到现在也很感动。我来美术馆快一年了。改革开放的时候赶上外资进上海,一直在外企,直到2014年转入文化行业,开始美术馆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当时我在国外工作回来,一个很巧的机会认识了大藏家余德耀先生,他正好在上海开设在中国的第一个美术馆。是他把我领入这个行业的,对我影响很大。那时候他跟我谈了差不多有一个礼拜,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觉得我不是专业出身。后来余先生说自己本身也不是艺术行业的,但是因为喜欢,可以慢慢去多看、多学。对于美术馆的创办理念、运营机制,包括对美术馆怎么在专业跟商业之间做一个平衡,他都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前一段时间听到他离世的消息我很伤心,他是很值得崇敬的一个人。宝龙美术馆的工作对我来讲是另一个挑战,不管是从体量或者是文化行业整个链条上来看涉及的面都要更广。它的运行机制非常好,有学术的要求,也有对整个美术馆能够持续运营的要求,只有这样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才能走得更长更远。所以一开始我压力还蛮大的,比如说美术馆的一系列造血机制,包括品牌合作、场地合作、艺术衍生品、咖啡厅、餐厅、儿童教育等等,这些都是美术馆自我造血功能,运营得好,那对美术馆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才有更多的资金来做更好的展览,其实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每次朋友问起,我都会回答,是的,我还在宝龙。我加入的时候,美术馆还在建造,看着它从工地状态到落成开馆,再到如今的第五年,不知不觉已经成了美术馆的“老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执行,最难的是在协调。不管是内部沟通、还是外部协作,每个展览的完成都是每位美术馆人的辛苦付出。也正因为每个部门同事的默契配合,彼此间的感情才更深了。一个展览的成功,除了优秀的美术馆团队之外,经验丰富的布展人员也是至关重要,不仅能保障展览的品质,也能节省出很多时间去做其他事,比如休息。记得18年我们做了一个“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展览,也是开馆展之后的第一个重要展览,由于时间比较紧张,开幕前一晚刻字的供应商才来现场施工,可能经验也比较欠缺,我们一定要在现场时刻盯工,一有问题就得马上调整。当时大家都很困,盯着盯着,天就亮了。想起那时候还挺感怀的。我工作半年多了。第一次在总部培训的时候,我发现宝龙真的是人才济济啊。当时有一个环节是分享之后的职业规划,大家的理论和概念各方面的阐述都挺好的,我很佩服。美术馆殿堂很大,我是第一次接触艺术类的公司。馆里的人都没有拘束感,没有心机,很简单朴实那种。我就感觉挺好的,工作很开心。居家期间我做了差不多两个月的志愿者。刚开始疫情比较严重,团购、分发抗原、核酸检测,这些流程我们得不停整理、做表格,工作很多很多。还有精神上的压力,就是劝导一些偷偷出来的人回去。那时候足不出户,其实是为了自己也为大家着想,然后经常会有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没有这种意识,你必须要和气一点,有耐心一点去沟通。疫情慢慢好转,志愿者也慢慢轻松了。现在大家都逐步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希望美术馆早点开馆。我是艺术商店的店长,艺术品鉴定专业的,在美术馆工作四年多了。刚来的时候商店还是一个毛坯的状态,货架、展柜,收银台都还没有呢。当时就是天天在盯工程,一点点把商店布置起来。我喜欢自己的工作,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原创商品或者精选后的艺术商品周边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与支持。商品被购买证明是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挑选商品的时候首先我们是很想把带有艺术美感的产品跟大家去分享,另外就是做了一些市场调研,掌握更多的风向标,甄选最具特色的展现中西方文化的艺术商品。从美术馆开馆初期到现在非常荣幸也很开心能跟很多的知名艺术家跨界合作,开发设计出大家喜欢的商品。我们的客人都是天南海北的,这次疫情在家,我在朋友圈发商品的时候很多客人都在留言问有没有能够帮上我的,真的觉得挺温暖的。和他们已经不仅是商业客户关系,更像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
我在美术馆负责采购工作整整一年了,之前没有接触过文化艺术行业,最大的不同是工作氛围。我在熏陶下更能发现身边的艺术,留意到了很多以前从未留意的。我们工作就是满足美术馆其他各部门的采购需求,主要就是核价、成本控制。我们整个供应链很完善,战略内的供应商都是很优质的。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在通过沟通、观察慢慢地筛选,完善自己的供应商库。这是个漫长而重要的过程,只有把资源最优化才能高效地帮助到各部门的运营。记得之前帮助艺术商店开发张占占个展的配套衍生品,我们当时是在20天内顺利完成了和艺术家谈授权定稿,到打样生产上架,一气呵成,最后商品大卖。我来美术馆刚好三年。我是学陶瓷绘画和雕塑的,现在对典藏的岗位熟悉了就比较喜欢,平时在库房能近距离地看到很多真迹,一些不为人知的技法都能看得很明白,里面的学问很大。尤其是书法作品,有的一笔下来,墨能分五层,墨是有肌理和层次感的。以前都是在一些书籍或者是网上看的,到底有多厉害是不明白的。我们主要负责珍藏展,每次布撤展的时候,整个书藏楼、典藏部和展览部的人员聚在一起协调方案,要连续加班两天左右,晚上可能会到半夜。大家蛮团结的,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不管是美术馆的藏品或者是展品,进到美术馆,典藏部就要进行接收、登记和后续消杀、出入库这些操作,走一成套的流程。很多艺术家学术水准比较高,为人也比较低调谦虚。当时公教部组织的百米长卷活动,我带着孩子去参加了,画了几只企鹅,张弛老师在现场给指导了一下,还拍了几张合照。孩子现在还记着呢。我来美术馆一年半了。年前最后一次会员活动,我们刚结束一场论坛下楼,一个会员拉着我说,你们的活动真的越办越好了。作为美术馆的会员她收获了很多,她觉得这样的文化交流是美术馆的价值所在。突然被当面肯定了还是挺触动的。美术馆很多事情都是现场发生的,总有一些突发的情况需要去处理,开馆时间整个人要在待命状态。最紧张的一次应该是展厅门口新换了闸机,投入使用的当天设备突然跟我们的系统没办法兼容,当时观众已经入场了,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判断,不影响当天正常运营,再去一步步排查技术问题。还是挺有挑战的。记忆深刻的是何曦展览的开幕论坛请到了梁文道先生,他是主持人,也是展览的策展人。听了很多年他的节目,当一个很喜欢很认同的人出现在你的工作中时,那种感觉就很神奇。他的晚宴名牌是我写的,为了在席卡上写好“梁文道”这三个字我练了好几遍。当时好多观众找他签名,大概得有一个多小时,我最后过去的时候挺不好意思的,但他第一句话是对我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他比我想象中更加谦逊。我来美术馆三年了。我家在黑龙江佳木斯,大城市待遇比较好,就选择来了上海。我们住宿舍,离得比较近。有的时候早上会做消防演练,做一些培训。因为我在部队待过,这些强度都不算什么。我以前是武警,在特别偏僻的一个地方站岗执勤,配真枪实弹的,周围是荒野,看不到什么人。当兵两年没有出去过,都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了,有这种感觉。馆内很多工作都是需要我们的,肯定有辛苦的地方,印象中有一回雨下得特别大,我们好多人紧急出去做漏水防护,身上都湿透了。巡场的时候,观众经常会和我们说这个展挺不错,一般我们也不会过多的交流,因为主要负责安全稳定这方面,把工作做好就是我的原则。疫情期间美术馆空荡荡的,期待你们归来。我是学市场营销的,从事餐饮行业10多年,来美术馆三年了。在工作中有过情绪激动流眼泪的时候,当时挺为自己难过,觉得这么大一个人了,工作也这么久了,居然还在职场中因为小的事情去流眼泪。后来理解了很多其他层面的事情,其实是让自己有所成长的。不管在人生还是在职场,这种事情未必是坏事情。“西方绘画500年”的时候有一幅莫奈的睡莲,我们餐饮做了一块巧克力,印上那幅名画,很多人还蛮喜欢的,觉得很新奇。我们近期开发了一个草间弥生的南瓜蛋糕,客人评价很好,特别是端上去后,他们都会发出“哇”的声音。新品开发上我们都蛮用心的,主厨 Alex主要负责开发,我负责成本核算、拍摄、推广之类的。我们去展览里面研究展品、寻找元素,找到合适的产品推出去,是挺花功夫的。我是2018年8月正式入职的,专业是设计。很多时候我们是活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执行者,整个流程有很多琐碎的工作去对接,就是希望能给到参与者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来美术馆参加这个活动是有收获的。有些活动需要我们整个团队一直忙到深夜或凌晨,回到家之后互相道一声晚安。大家一起为了一件事情去努力,这是支撑我工作的一个动力。其实公教活动很多时候是一种服务,哪怕是音乐会,我们现场都不能好好地去听去感受,不是在核对签到人数,就是在拍照,或者对接下一个流程,一直在一个紧张的状态。有一次去陆平原的工作室探访,整个活动挺放松的。我们包了一辆车,带大家一起去工作室,短短的一段路,天气很好,车里的小伙伴有聊天的也有画漫画的。到了工作室,听陆平原讲他创作灵感上的怪诞故事,感觉自己也是一个参与者。报名的来自各个行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所有人围坐在大大的桌子前面,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经历交错在一起,跟现场的陌生人发生了联结,是很微妙的一个体验。我一直盯着工作室角落一个破旧的沙发,阳光整个照在上面,有种时间静止的感觉,而我们又在一旁讲着故事。我是学设计的,来美术馆三年了。我蛮喜欢“瘾瘾作乐”,这个展览的内容有科技的含量,也有一定的艺术内核和思想,两者结合得挺好。当时我负责了他们的开幕式,非常神奇。因为我之前工作做过这一类的,所以也是能力范围内。我一直是陈志光老师的粉丝。我还是学生的时候,陈志光老师在上海人民广场有一个展,他的作品就爬在那个钟楼的外面,密密麻麻的小蚂蚁,当时觉得很酷,这是我对当代艺术的一个初印象。后来他在宝美做了“魔都蚁行志”的个展,我和他合影过,算是追星成功,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真人,之前只是仰慕他的大名。他还会给我们美术馆寄水仙花,他是漳州人,水仙是漳州的特色,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又有自己性情的艺术家。
{{flexible[0].tex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good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newsData.transfer_cou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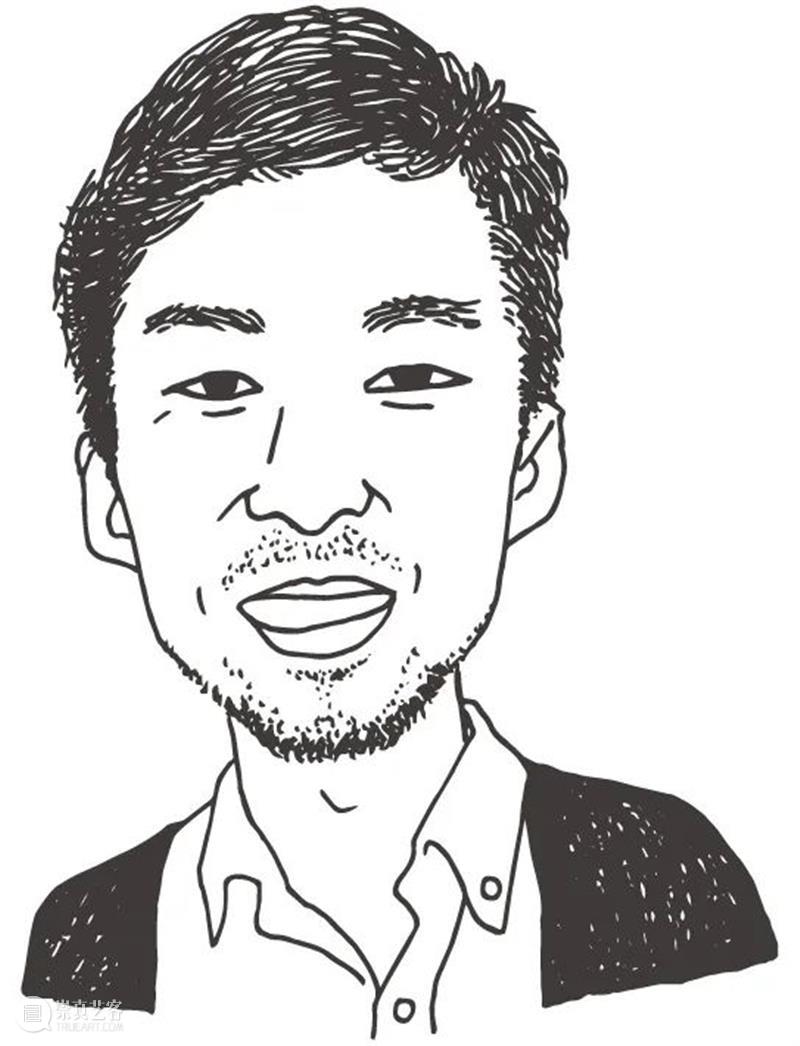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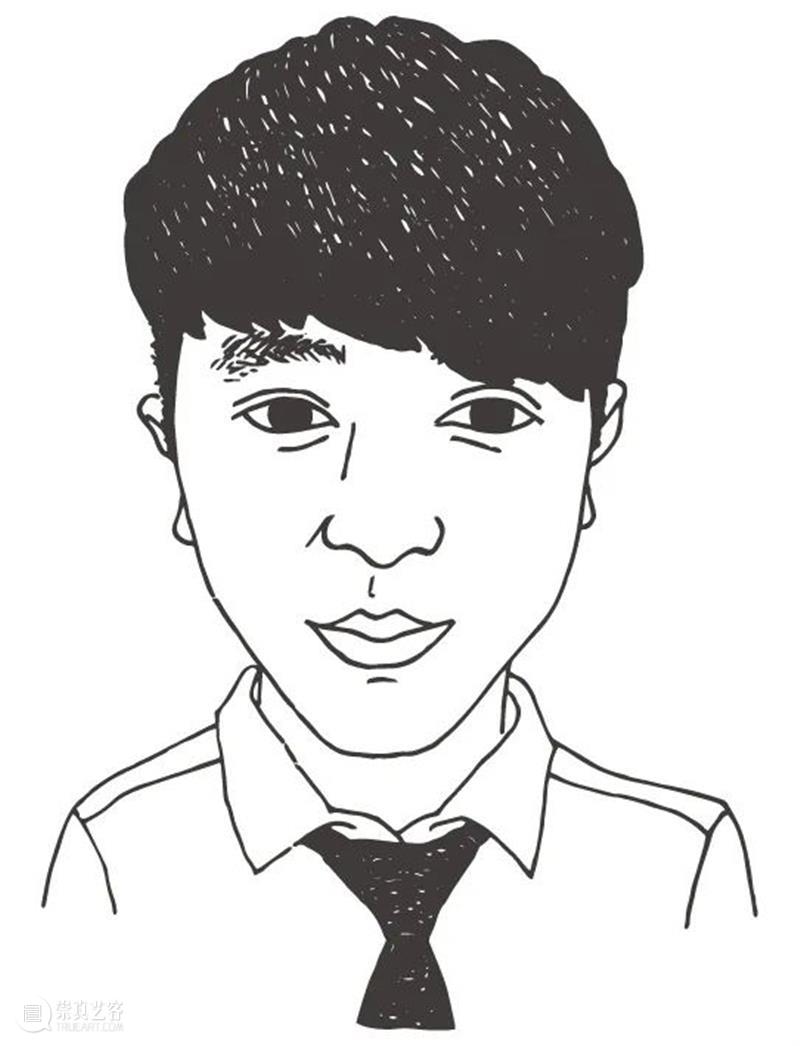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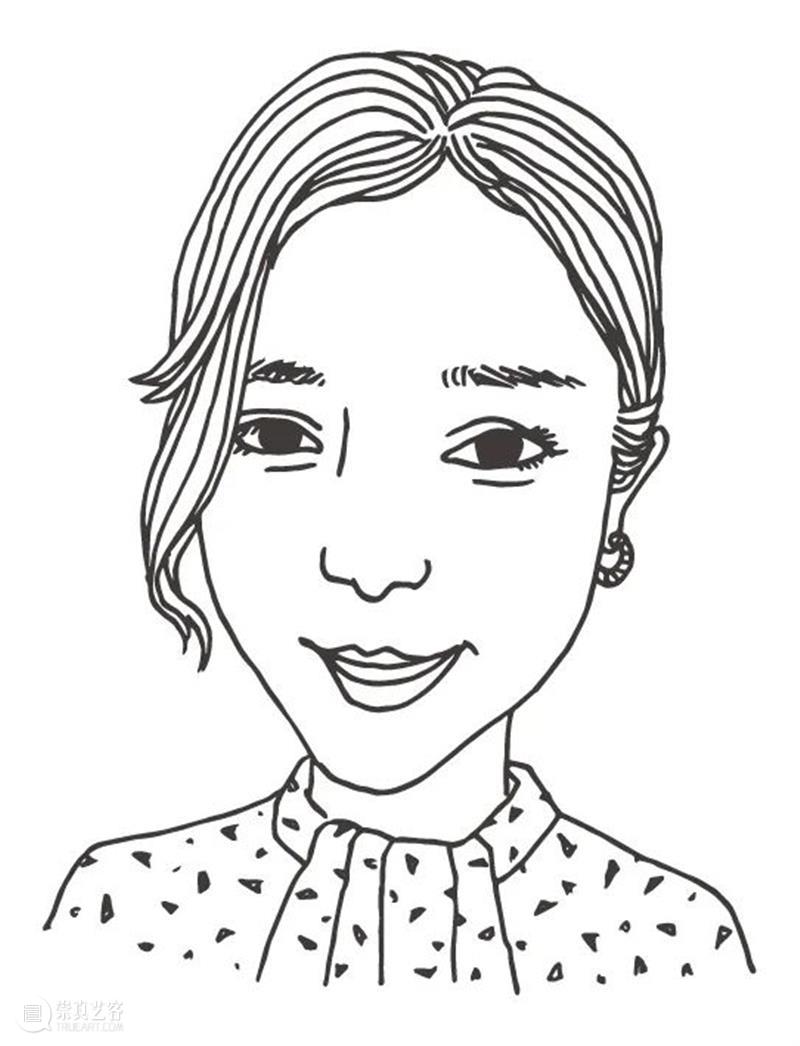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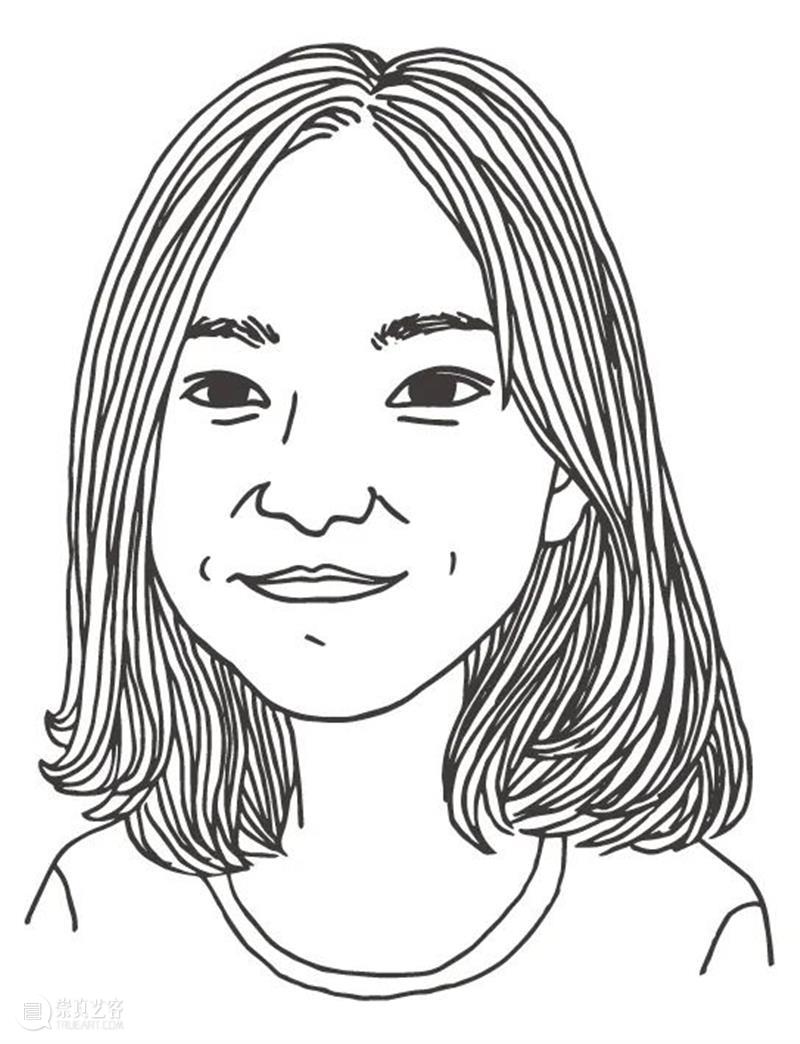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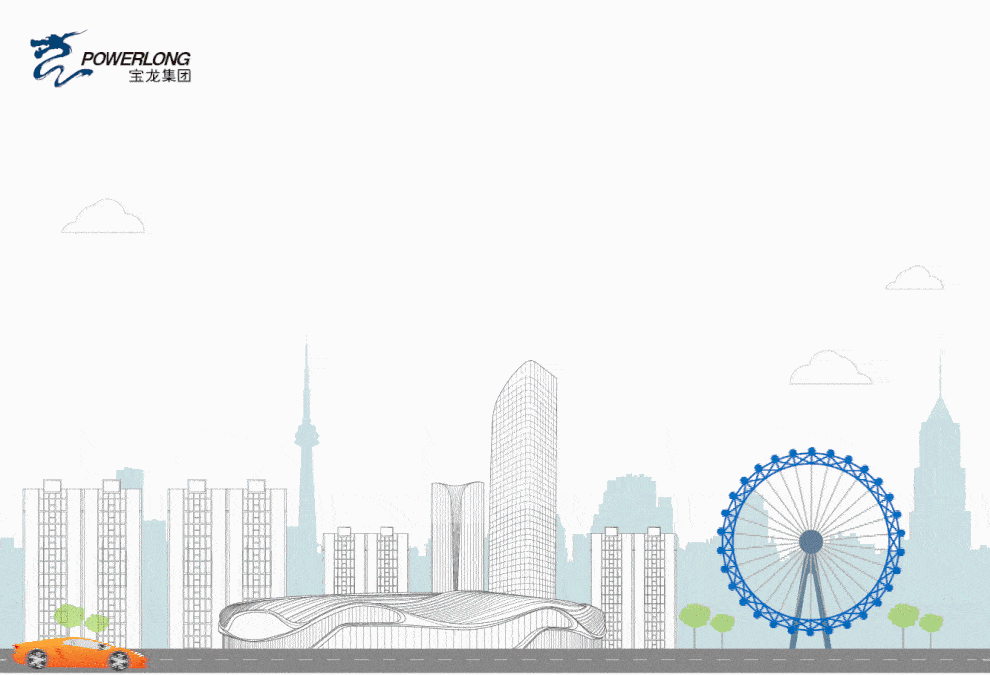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