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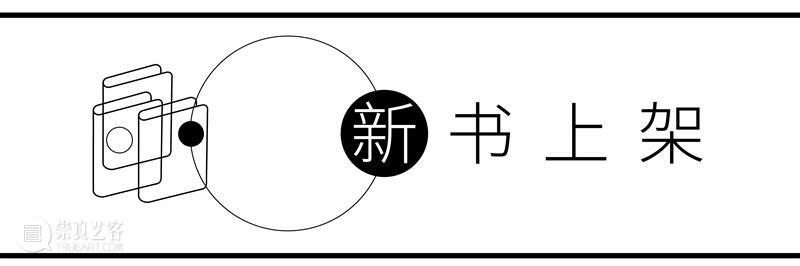
大家好,近日我们推出了工作室2022年的第9-12种新书:
“人文丛书”两种:
《虚无的解缚:启蒙与灭尽》(雷·布拉西耶 著,聂世昌译);
《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布鲁诺·拉图尔 著,刘鹏、安涅思译);
心理学向图像小说两种:
《亲爱的斯嘉丽:我的产后抑郁经历》(伍婉儿著,两进一译);
《万事大“急”:我与强迫症的故事》(杰森·亚当·卡赞斯坦著,张仲宇译)。
四种新书目前均已在我们微店上架,欢迎大家购阅。感恩大家的支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虚无的解缚:启蒙与灭尽》一书的序言(注释、致谢、声明从略)。
序 言
自哥白尼以降,人类由中心滚落到了X的位置。(Nietzsche 1885)
宇宙越显得可以理解,那么它也就越显得无意义。(Weinberg 1978)
“虚无主义”这个术语展露出了它陈腐的一面。关于这个主题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过度的曝光(overexposure)削弱了这个词语曾经可能传达的紧迫感。结果就是,它被乏味的过度熟悉性(over-familiarity)以及朦胧的不确定性浸染。即便如此,也很难有其他的哲学论争能够像虚无主义——在最“朴素”的通行意义上,虚无主义意味着“生存毫无意义”——的主张那样吸引对哲学问题不怎么感兴趣,或者说根本没有兴趣的人。尽管探讨这个主题的学术书籍与论文浩如烟海,不过我仍然确信这一极为庸常的主张中仍然潜藏着还未被哲学家钩深极奥的东西,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所在。虽然关于虚无主义的哲学文献数不胜数,其中一些著作更是让我获益匪浅,但我坚信某种具有基础哲学价值的东西还未言明,并被淹没在了探究虚无主义历史起源、当代分支以及长远影响的学术研究中,这是我写这本书的依据所在。事实上,由于虚无主义的这些层面已经被非常透彻地描绘过了,所以阐明本书意图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解释它没有做什么。
首先最重要的是,本书并不把虚无主义当作一种需要对其诊断并给出解药的病症。不过,它既不赞赏有限之情(pathos of nitude),并将其视为抵抗形而上学狂妄自大的壁垒(Critchley 1997),或者庆祝解释的不确定性,并将其看作摆脱(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所带来的)压抑普遍性的皆大欢喜的解放(Vattimo 1991 & 2004);也不试图在怀疑主义以及非理性主义面前重新确立理性的权威——不管是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大肆破坏中为柏拉图主义辩护(Rosen 2000),还是利用黑格尔主义来反击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明枪暗箭(Rose 1984)。最后,它也不愿提供一种虚无主义的概念谱系学(Cunningham 2002),不想就虚无主义中成问题的部分,写就一部批判性的史前史(Gillespie 1996),或者综述它在19世纪、20世纪哲学及文学中的诸种影响(Souche-Dagues 1996)。
这本书有两个基本论点。首先,启蒙运动打破了“存在之链”,污毁了“世界之书”。作为启蒙进程的结果以及理性力量焕发的必然产物,世界的祛魅标志着知识发现呈现出令人振奋的趋势,而非灾难性的衰退。这一观点直接受到了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著作的启发。启蒙运动可以说是两千年以来影响最深远的(而且一直在进行的)知识革命,乔纳森重述了哲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他的这一权威论断是对反启蒙修正主义思潮(20世纪的许多哲学都与之脱不开关系)有益且必要的修正。我们应当欢庆世界的祛魅,而非报以哀叹,因为它是心智成熟的果实,而非不断衰弱的贫乏。这本书的第二个基本论点是,虚无主义并不像雅各比(Jacobi)和其他哲学所坚称的那样是主观主义病态的恶化,即宣告整个世界的无效,并把现实化约为绝对自我的关联项;相反,它是实在论信念的必然结论,因为后者坚信,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实在,无论人类做出何种自恋的假设,它都对我们的生存漠不关心,视“价值”和“意义”若无物——尽管我们通常会将“意义”和“价值”覆于实在之上,使其显得更友善一些。自然既不是我们或任何人的“家乡”,也不是一个特别仁慈的起源。哲学家们最好停止继续发出如下的指令:人们需要重建生存的意义、生命的目的或者修缮人与自然破碎不堪的、不再和谐的关系。哲学不应只在人们可悲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时扮演安抚者的角色。虚无主义不是生存的困惑而是思辨的契机。思考和生存就其所拥有的旨趣而言并不是完全契合的;事实上,思考的旨趣不仅可能,而且已经与后者产生了对立。我所想要探究的正是后一种可能性。本书有着显而易见的缺陷,令人遗憾的是,理想与能力之间的差距意味着它既不彻底也不全面,因而无法确保其中的论证足以令人信服。本书的主要论点肯定会引起质疑性的反驳,如果想让本书的论证足够坚实有力,能够回应这些反驳,那就需要做出更多的说明。不过,无论本书多么令人不满,由此出发所讨论的主题都应被视为一次准备性的介入。我希望之后的著作能够对此进行更充分的研究。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1部分的主题为“摧毁明显图像”。第1章通过考察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在“世人”(man in the world)的“明显”图像和“科学”图像之间所做出的区分,引入“摧毁明显图像”这一主题。接着,本书将探讨常识心理学话语和新兴认知科学之间的对立:前者倡导规范性,后者则彻底消除对“信仰”的信仰,以使心灵重新融入科学图像。第2章分析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启发下,以理性与自然之关系的替代性概念(an alternative conception),对科学合理性做出极具影响力的批判。第3章(第1部分的最后一章)阐明了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对“相关主义”的批判,后者构成了“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解释理性和自然关系的基础。随后,本章将指明梅亚苏试图恢复数学直观时所面临的困难。第2部分描绘“否定的剖析”。作为该部分的开端,第4章将考察阿兰·巴迪欧如何通过存在的缩离概念(a subtractive conception of being)来回避梅亚苏诉诸智性直观(intellectual intuition)时所遇到的困难。虽然巴迪欧避免了直观观念论(idealism of intuition),但付出了走向同样成问题的书写观念论(idealismof inscription)的代价。第5章通过借鉴弗朗索瓦·拉吕埃尔(François Laruelle)的著作,试图在关联的观念论与数学直观观念论/书写观念论的僵局中寻找一条出路,并详细说明一种依据否定的非辩证逻辑来运作的思辨实在论。本书的第3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时间的终结”,试图将这一逻辑付诸实践。第6章批判性地重构了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中具有本体论作用的死亡与时间的关系。最后,结合前几章中逐渐形成的批判性见解,第7章首先概括了尼采对克服虚无主义的描述,然后提出以思辨性的方式重写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在其中,后者的升华被视为把握求知意志和虚无意志之间紧密联系的关键。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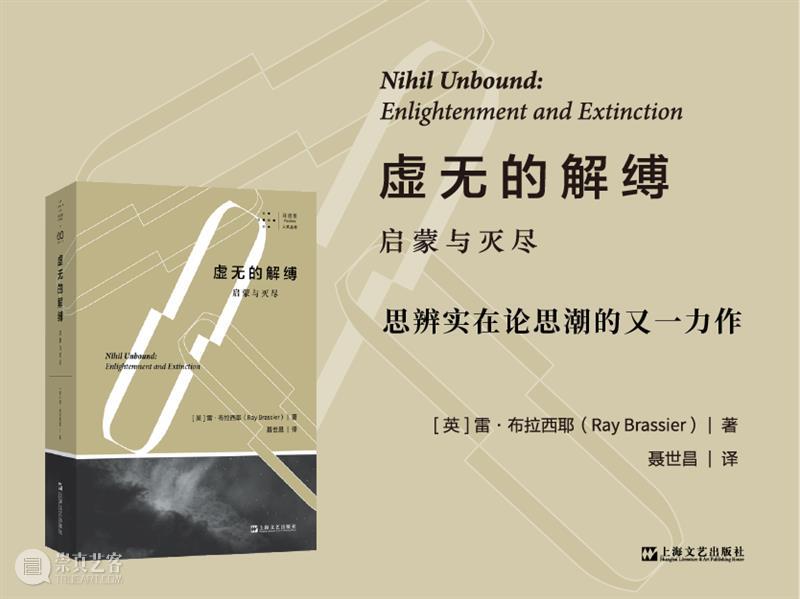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