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绵延”
戴米安·萨顿 大卫·马丁-琼斯丨文
林何丨译
选自《德勒兹眼中的艺术》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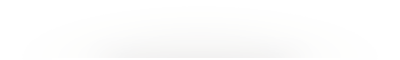
公平地说,我们完全知道什么是时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时间是衡量生命的方式。我们按时间周期来衡量日常生活。60秒是1分钟,60分钟是1小时,24小时是1天,7天是1周……了解时间概念,我们就能每天早上起床,计算花多少时间上学或上班,可能晚到一小会儿,熬着时间直到吃午餐,如此等等。这种时间周期是累积式的,7天构成1周,52周构成1年,然后每10年又构成1个10年的周期,以此类推。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体验到时间流逝是一种线性发展。道理相当明显。比如,每过1次生日我们就增长1岁,或者我们常常在镜子中瞥见自己又变老了的脸,又或者意识到以前轻松慢跑就能赶上正要开走的公共汽车,现在要靠拼命冲刺才行。以上关于时间的看法简明易懂,但受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影响的德勒兹看待时间却与此略有出入。基于柏格森的绵延(duration)概念,德勒兹对电影时间进行了研究。
柏格森的绵延指的是对时间的理解,但并不完全是我们通常用的那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观看一场足球比赛能坚持到结束哨声吹响,那么就可以说我们“一直(绵延)在那儿”。因此,“绵延”一词用于对时间进行具体的估量,可以暗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在做某件事情。比如,假如我们曾被困在电梯内,而又不得不和某个非常令人讨厌的人待在一起,我们就不免暗自叹气,承认当时“一直(绵延)在那儿”。而在柏格森看来,绵延是指开放的、不断延展的整体时间,一旦它被空间化,或者一旦时间流被固定在四维坐标中,通常只有人类才可理解。德勒兹吸收了柏格森这一概念并加以改造,并就电影表达时间的方式作出了惊人的判断。
会不会是柏格森和德勒兹这两位法国哲学家时间多得用不完,所以就把简单的事情弄得过于复杂?不过在作出这样草率的结论之前我们最好记住,德勒兹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电影如何表达时间的观察。德勒兹并没有说我们通常对时间的理解是“错误的”,而是说,某些电影提供了另类的方式去思考充满大量分叉的时间,而这也是我们想象我们日常身份的方式。
柏格森认为时间是一个虚拟的(virtual)、不断延展的整体,他名之为“绵延”。他论述这一概念的主要著作有:《时间与自由意志》(1889)、《物质与记忆》(1896)、《创造进化论》(1907)和《绵延性与同时性》(1921)。柏格森的哲学博大精深,要想考察他的种种思想而又不产生无数的误解和曲解,那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柏格森关于时间和绵延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关注过去。在《物质与记忆》一书中,柏格森认为记忆并不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相反,过去是对时间的虚拟存储。他认为,当我们记起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以虚拟的方式旅行在过去时光这一巨大的虚拟库中,寻找着种种记忆和回忆。柏格森的著作甫一发表,就产生了巨大轰动,特别是在艺术圈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思想的影响可在全世界很多作家的著作中看到,其中最杰出的当数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的代表作《追忆逝水年华》(1913-1927)使用并发展了柏格森的思想,来追忆叙述者马塞尔(这一人物原型取自作家本人)的生平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在法国的生活。普鲁斯特的小说将柏格森的思想向前发展了一步,表明不经意的记忆可以促成出其不意地向虚拟的过去回跳。普鲁斯特表明气味、声音、味道或身体姿势可以不经意地给我们带来回忆,他以一块玛德琳蛋糕的味道,突然将叙述者立即带回到童年的记忆。柏格森的思想对文学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到今天都很明显。在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2001)中就能清楚地看到柏格森式的时间概念。事实上,尽管这种观念——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虚拟记忆库中的时间旅行者——最容易在柏格森时代被转换到文学中去,但随着20世纪虚拟媒体的发展,要寻找对绵延进行艺术表达的最明显的地方莫过于就是现在的电影、电视和各种各样的新媒体(比如互联网和电子游戏)。例如,在电影、电视甚至电子游戏中的一个闪回中,观众或游戏者被带入了叙述者的虚拟过去之中,通常……这是以一种柏格森方式进行的。
让我们更进一步来了解柏格森的时间概念。柏格森推论,虚拟的过去是不断延展的。时间在它的每一刻分裂为德勒兹后来称之为的“不断流逝的现在和被保存的过去”。现在的时刻我们通过实际所做的日常事务来体验,而过去的时刻则是这些日常行为的影像,它以虚拟的方式存储下来。在时间的每一刻,我们所做的事情存在实际的和虚拟的两种向度。当我们努力记起过去的时候,过去已经存储在我们想寻找的过去的虚拟影像之中了。过去常会不请自来地闯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例如,有时无意识的记忆会把我们“闪”回到过去,这通常是因为我们的实际现在(某一味道、声音、气味或身体姿势)匹配上了存储在虚拟过去某处的某个虚拟影像。因此,我们回到的正是这样的虚拟过去(柏格森将其设想为一个巨大的圆锥体)。另外,我们之所以有持续的现在的感觉,是因为我们意识到了发生在当下的行为那实际的一面。正是由于这一点——既是空间也是时间——我们通常才能觉察到时间流逝的线性发展。
在《创造进化论》中柏格森发展了他关于过去的概念,他认为整个宇宙是处于不断延展的过程中的。如柏格森所说:“真相就是我们永不止息地变化。”宇宙存在于时间之中,相应地,时间也是一个不断延展的整体:绵延。下面的话概括了他的立场:
绵延是过去的持续进展,它吞噬着未来,而它前进时自身也在膨胀。过去在不停地成长,因此时间的保存永无限制。记忆……并不是一种将回忆放进一个抽屉或者为之登记注册的技能……在现实中,过去自动地保存自己。
在柏格森看来,因为时间的每一刻都在创造着新的“影像”,这一“影像”又被添加到过去的储存库之中,所以过去以虚拟的方式保存,并不断地在每一刻被添加,或者说,被“自动地”记忆。此外,虚拟过去的重量(weight)不断地将时间向前推进到现在,每一个新的影像被添加到过去,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使时间“吞噬”未来的动量(momentum)。
通过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时间,柏格森得出结论,当我们观察变化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对现在和过去的状态之间的差异进行测量。用一个简单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果我们观看童年时期的照片,可以立即看出那时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之间的差异。因此,当我们处于比较实际的状态时,差异显而易见。但是要去捕捉并测量变化的持续过程,那就要困难得多。事实上,当我们测量时间的流逝时,我们将绵延进行了空间化,制造出“剪辑式”(cut-out-and-keep)影像,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比较从而构想变化。既便如此,柏格森坚持认为,在这些可以清楚测量的状态之间,依然存在一种发生在时间中的连续变化的进程。我们觉察到的实际现实,其实是一个永恒的虚拟生成进程的一张快照或者一个定格镜头,这个进程就是绵延。我们通过将时间空间化来测量时间。
在《电影I》(1983)和《电影II》(1985)中,德勒兹发展了柏格森的思想。简要来说,柏格森对电影能否以视觉的方式呈现绵延是持怀疑态度的,而德勒兹觉得某些电影可以将绵延时间的流进予以视觉化,他将它们称为“时间-影像”(time-image)。同时,他认为还存在“运动-影像”(movement-image),它们也能记录时间的流逝,但只采取将时间空间化为时空聚块的方式。时间-影像是对时间本身的绵延的一瞥,也是时间对自我的绵延的一瞥。而运动-影像,在我们理解日常生活的时候,则有助于我们理解虚拟的时间整体如何被意识所空间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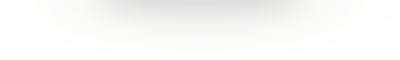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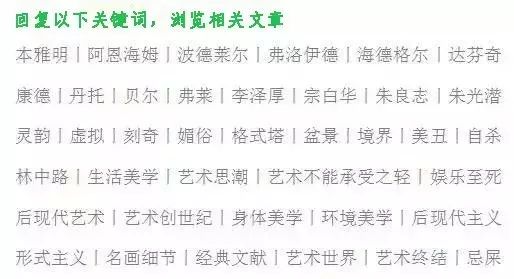



已展示全部
更多功能等你开启...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