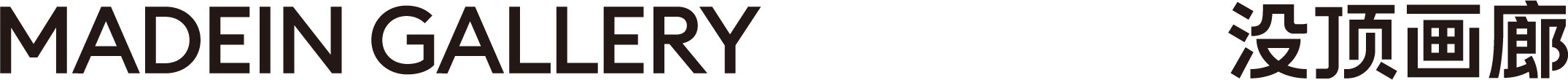
陈英个展今日7月8日在没顶画廊正式开幕。我们同时发布画廊与艺术家的文字对谈。陈英具体介绍了自己的创作逻辑和艺术视野,并为观众剖析了此次展出的系列作品在其职业生涯中的独特意义。展览现场,“陈英”,没顶画廊,2022.7.8-8.31
Q: 陈英,可以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吗?到目前为止,你的职业艺术家道路分为哪几个阶段呢?
A: 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设计专业,毕业后一边做舞台设计的项目,一边进行绘画创作。2015年开始,我成为了职业艺术家。
展览现场,“陈英”,没顶画廊,2022.7.8-8.31
我的绘画大体分三个阶段。我是在正统的中国美术教育体制成长起来的,在大学时非常迷恋德国表现主义,深受那时期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影响,在这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创作了很多关于物体、风景的作品,这算是第一个阶段;之后对德国表现主义有了不同的看法,就阶段性地探索并调整自我,这个过程用了大概有十年,观念才基本定型,开始有针对性地对几个方向进行探索,包括波普类的、抽象类的;现在我算是进入了职业生涯的第三个阶段,在之前第二阶段工作的基础上,我更加明确了自己观念绘画的面向,要求自己的创作回应时代,特别是数字时代的超工业审美的泛滥和平庸化,以此作为我未来工作的起始点,而不仅仅满足于是否画一张好画。展览现场,“陈英”,没顶画廊,2022.7.8-8.31Q: 你提到不满足于“画一张好画”,我对此表示认同,毕竟艺术家不应该是活在真空之中,或如格罗伊斯所言,一个艺术家应该主动寻求“感染”。但是你的第三个阶段的创作面貌,特别是绘画技术上,至少从画面结果判断,呈现出某种“退步”,请原谅我说的这么直接,我确实感觉不到第三个阶段绘画的难度在哪里,而在前两个阶段这是很明显的,比如对于构图,用色的思忖……但是第三个阶段,我认为我也可以画,我认为观念不能以牺牲绘画为理由。不知道你有什么可以回应或者分享的吗?
A: 这次是我这些年来转变最大的一次,除去了很多以前习惯性常用的做法,选择了一种极其统一、或者可以说是“单一”的输出方式,来直达我所针对的问题。过去的画更像是完成一张作品,而现在更像是形成一个系列,从“集中”到向广度延伸。在这系列作品成形前,我曾尝试创作过在一张画内变化和隐喻非常丰富的画作,但画了几张后,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过于丰富会导致作品的“作品化”,反而降低了其与社会对应的宽泛性。我必须摒弃这种“丰富”,以一种常态的面貌,对问题做出更直接的回应。

展览现场,“陈英”,没顶画廊,2022.7.8-8.31
我的绘画只拣取了最基本的几个要素:简单的造型、明快且流行的色彩。这个系列是利用“流行化”、“商业化”来传达我关注的社会问题:一切看似明快的表象都是经过设计的结果。我相信,这一作画逻辑,同时也是现代社会运行的逻辑。我只是对社会面貌、社会生态进行再现和扩大,对观众起到惊醒作用。
说到这里,我可以再补充一句,这种对绘画的“复杂与否”的判断还是一种非常“中国式”的对绘画的理解。放眼全世界,在这个时期,绘画不能按照“表现”或“写实”的逻辑来做画面的判定,或者说这些既往的范畴已经失效了。
展览现场,“陈英”,没顶画廊,2022.7.8-8.31S: “一切看似明快的表象都是经过设计的结果。” 这一点可以请你具体展开说一说吗?
A: 在我看来,人现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在一个被驯化过程中,我们都在一种被“设计”的环境中长大,包括审美的同质化、大数据等等。不管是短视频还是图片,我们都被其“计算”引导,所有人都被无形地被驯化过。不单单是美学上的设计,整个生活的逻辑,都是被设计出来的。我这次的作品既统一,又在其内部有变化,这种变化是我通过基于“设计”的结果的“再设计”。这批绘画我使用的颜色基本都是“原始颜色”,即颜料的色谱上既有的颜色,而没有使用艺术家个人的情绪化的调色。我把这些流行语汇、颜色造型直接“拿来”使用,并较为随机地进行组合,添加在我的作品里。通过明快的色彩,我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生态,你逃避也好,承认也好,它就在那里。
展览现场,“陈英”,没顶画廊,2022.7.8-8.31
S: 那造型呢?我们第一眼看到这批作品的画面,呈现出一种平面性,但是走近一看,发现了笔触的痕迹。如果追求平面性,用打印或喷枪的方法来处理不是更加快捷和高效吗?如果追求绘画性,一般人反而会求助于画面的复杂,刻意制造视觉阅读上的障碍,可是您没有,虽然您展现了绘画的笔触、姿态等等……为什么刻意制造这种矛盾的工作方式呢?
A: 这次的画作,我都是徒手完成描绘,没有借助任何丈量式的、计算的工具,包括传统绘画中会用的米字格、九宫格底板,这保持了我对绘画的控制。
电脑制图、刻录制的工业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我有试过,但它们远达不到我对作品的要求。这种对平滑形状的选取,以及视觉效果与创作手段的反差,而产生的张力和矛盾感,正是我之前表达的“设计”和理念传达的一部分。

展览现场,“陈英”,没顶画廊,2022.7.8-8.31
A: 我想做到将屏幕上的视觉和现实中的视觉的区别拉大。这一系列展览对尺寸的选取是有意的。这让我的作品在手机屏幕上看的感觉和实际观看原作的感觉的差别是巨大的。
A: 苹果系列产品也有大有小,对吧。为什么Iphone 要有pro、max的区别,为什么有了电脑,手机还需要Ipad,便携性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点,我想在这里就这个点进行提问。在使用者看来,不同的苹果设备对应的是不同的价位、功能,但是在苹果公司看来,这是为了苹果的占有率。商业的本质是传播,便携性也是为了传播。

展览现场,“陈英”,没顶画廊,2022.7.8-8.31
S: 这提醒了我,所以你的绘画中的曲线和直线造型是来自于数码设备的工业设计?
A: 数码技术、数码文化、互联网产品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种文化。作为一个人,它不可能不影响你,而作为工具,它也已经根深蒂固了。
在我看来,“线上”社会和“线下”社会的区隔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南北、东西方的地域差异,将它们逐渐抹平、统一化了。当代人花超过50%的时间使用屏幕,生活在屏幕给他(她)的讯息里,被包括视频、文字、新闻、各式各样的资讯围绕。艺术家必须与社会共振,并且在这种共振这种做出自己的个人裁决,这是包括绘画在内的一切当代艺术必须完成的工作。
陈英,198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2010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舞台设计专业,现生活工作于上海。在构图简洁、色彩明快的抽象画面之下,陈英将创造、破坏和转化的力量纳入到相互关联的画面之中,以此实现与经典的绘画技术和认知的碰撞,从而形成自身作品的时间感和游戏属性。在近来的创作中,陈英从哲学、社交媒体、文化人类学中汲取参考资料,以质疑当下社会数字技术的滥用和数字图像的泛滥,但他更关注不可思议的心理力量和对抗张力,而不是任何直接批评。
陈英展览包括: “形式的‘密谋’”,剩余空间,武汉,2020;“图像感到了不安”,没顶画廊,上海,2020;“陈英个展”,金杜艺术中心,北京,2019;“极限混合”2019广州空港双年展,广州,2019;“有痕可迹”,没顶画廊,Condo Shanghai,没顶画廊,上海,2018;“现像——陈英个展” ,没顶画廊,上海,2017;“思考本质不如消费形状”,没顶画廊,上海,2017;“力的能见度”,J GALLERY,上海,中国,2017。
杨紫,独立策展人,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他于2020年获选为首届“希克中国艺术研究资助计划”研究学人,并担任画廊周北京评委;2019、2021年担任年度华宇青年奖初选评委;2017年入围Hyundai Blue Prize年度艺术大奖。
杨紫具有近十年的艺术评论写作及策展经验,2011年任《艺术界LEAP》杂志编辑,并长期为《艺术界LEAP》、《艺术论坛》中文网和《艺术新闻中文版》等杂志撰写文章。杨紫还曾任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展人及公共项目总监,策划多场展览及公共项目活动,包括参与策划了“例外状态:中国境况与艺术考察2017”、“Pity Party”、“敢当:当代神石注疏”、“韶华”、“装饰”等群展,以及多位艺术家个展。
没顶画廊成立于2014年上海,由当代艺术创作及策划平台没顶公司所发起创办,公司创始人徐震是一位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
没顶画廊致力于推广优秀的艺术家和项目活动,推动当代文化的发展与国际交流。自成立至今,画廊已为新锐艺术家和知名艺术家举办了众多具有策划性的、高品质的个展与群展,成为一个独特而重要的艺术平台。没顶画廊善于挖掘和培育具有天赋的年轻艺术家,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活跃于中国及国际当代艺术舞台。没顶画廊代理艺术家包括:蔡坚、陈英、丁力、何岸、李汉威、刘成瑞、陆平原、苗颖、莫少龙、佩恩恩、商亮、沈莘、史莱姆引擎、苏予昕、汪建伟、王思顺、王梓全、徐震®、杨深、杨扬、尭、郑源、周子曦。没顶画廊合作艺术家包括:陈冷、艾略特·多德(Elliot Dodd)、方阳、冯至炫、葛辉、龚剑、刘娃、郎港澳、陆博宇、蒲英玮、善良、宋琨、王新一、夏诚安、夏云飞、徐大卫、张联、张珂、钟慰、张文怡。madeingallery.com
周二至周日 10:00 - 18:00 (周一闭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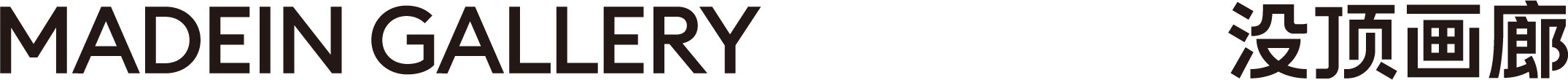

















 分享
分享